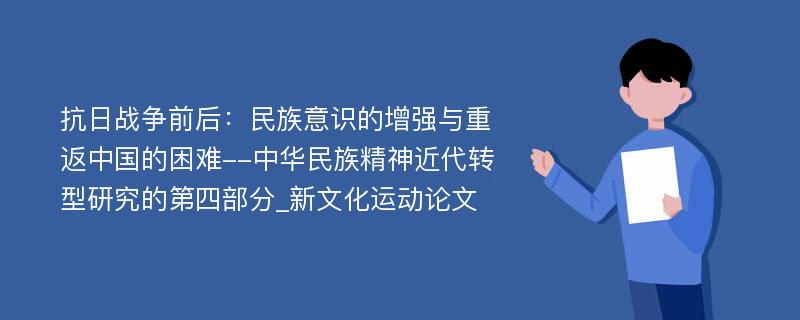
抗战前后:民族意识的强化与返本开新的困顿——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研究之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顿论文,中华论文,之四论文,化与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将西方文化简化为科学主义,从而将宗教精神摒除在外。这一点,由于有中国大传统中的实用理性作底蕴,很快便被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尽管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以学衡派与张君劢为代表的少数人士对科学万能论提出质疑,但在科学即真理的社会心理已经定型的大背景下,学衡派所主张的人文主义与张君劢所主张的直觉主义毫无抵抗能力,迅速败下阵来。对此,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内都曾身任要职的叶青曾经有一总结,1933年,叶氏在一篇文章中相当武断地写道:
“历史给了我们以答案。打倒神学的是玄学,打倒玄学的便当然是科学。所以批判玄学的方法就是发挥科学理论,伸张科学,以阐明科学底万能。科学如果万能,那非科学的观念论、多元论、机械论就消灭了,以它们为中心的一切非科学的学说思想,不就说也‘树倒猢狲散’,不能存在。”[1]
这里面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即玄学是对神学的否定,而科学则是对玄学的否定之否定。
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际,不管在政治思想上有何分歧,中国思想界的多数人士都能接受科学在解释自然与社会方面的权威地位。这方面一个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以提出“厚黑学”著称于世的四川民间思想者李宗吾。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之下,李宗吾甚至“主张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一切法令制度,当建筑在力学之上”,其理由则是“人为万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种种变化,也逃不出力学公例”。[2](P110—111)
既然西方文化等同于科学主义,那么学习科学也就等同于学习西方。但是,中国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际开始被动现代化进程之后,即一直怀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情结。一旦认识到西方文化只有科学而无宗教,中国思想界将宗教视为帝国主义愚民与侵略的工具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此,我们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之间的“非基督教运动”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主义盛行的一个逻辑结果。曾有论者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就不再单纯地由于它是‘洋教’,而是由于它不具有科学性。”[3](P304) 换言之,这时的非基督教是建立在科学精神优于宗教迷信的信念之上,而非过去的中国伦理优于西方伦理的幻觉之上,因此更具有学理性。
本来,自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颇为迅猛。在辛亥革命期间,基督教甚至直接介入实际政治,像刘静庵、曹亚伯这类既是基督徒又是革命党的人士比比皆是。正因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强大影响力,1912年9月,当孙中山北上时,曾对基督教的社会功能颇为期许,他在一次集会上说过:
“……但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虽然民国告成,自由平等,万众一体,信教自由,亦为约法所保障。但宗教与政治,有连带之关系。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兄弟希望大众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之所不及,则中华民国万年巩固,……”[4](447)
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虽然孙中山从未提出类似“中华归主”的主张,但他对基督教称赞和期许却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在孙中山之后,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国家领导人以如此口吻来夸奖基督教似乎再无其人。而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之下,作为迷信与侵略之代名词的基督教亦开始萎缩。以东北为例,据1930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统计,在东三省(辽宁、吉林与黑龙江三省),1915年有基督徒26000余人,1920年减至21000余人,1925年减至18000余人,而到1930年,则已减至15000余人。[5] 本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阻力主要来自受中国大传统影响的知识阶层,而非受中国小传统影响的下层百姓。但是,由于新文化运动是将中国大传统逐渐渗入小传统,科学主义同时也影响到下层民众。譬如1929年底的山东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反教运动,其参加者除了知识分子之外,还有大批工人。据基督教会的媒体报道:
“周村区会于(192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男女信友,适在大礼堂举行圣诞礼拜,时有长山县党部房崇岭等率本镇千余工人手持铁棍及标语等件,突然闯进教堂,摇旗呐喊,口呼‘打倒基督教’,杂以种种谩骂,秩序一时大乱。男女学生睹此情势,遂由便门躲避,牧师执事等仍以善意招待,惟彼暴众毫无礼法,肆意将堂内桌椅玻璃捣毁无余,兴尽而去。临去之前,又复遍堂内外张帖‘信基督就是反革命’等等标语。事后周村区会同人亦虽依法向本县申诉,无奈县长慑于党部,不敢依法处理。”[6]
此外,即使在基督教内部,由于科学主义的影响,一些基本教义亦受到直接挑战。譬如,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中国基督教代表人物吴雷川即在一本著作中为流血革命辩解,他认为:“基督教唯一的目的是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也就是寻常所谓革命。……如果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取得政权,而取得政权又必须凭藉武力,倘若基督教坚持要避免革命流血的惨剧,岂不是使改造社会底目的成为虚构的终古?”[7](P290) 这种观点与当时流行的武装革命论已十分接近,但与基督教(尤其是新约)的仁爱说有了质的不同。
二
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之下,不仅基督教出现萎缩,小传统也渐趋衰微。1930年初,天津《大公报》记者曾经报道了南京政府废除旧历后天津一处庙宇的颓败情形,其中一段写道:
“宫内游人,日来格外拥挤,购货者十之五,率子女闲游者十之二,其他均为进香而来,故善男信女,出入不绝,当以小家璧玉,龙钟老妇为多,香火最盛者,当推天后圣母。以礼教关系,门前树有‘此处不准男子站立’之木牌,顾伫立而观者,更形踊跃。当局者匍匐祈祷于偶像之前,旁观者评头品足以资谑笑,圣母有灵,不知作何感想,香火最冷清,当推土地爷,身高不过一尺,形类侏儒,前尚浑身灰土,今年竟御新装,精神焕发,所苦门前冷落车马稀,谁谓神界女权不高哉?”[8]
在中国民间,下层百姓基本上是以小传统作为建立行为规范的标本,而小传统的被摧毁自然会引起行为规范的缺失。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地区出现比较广泛的道德滑坡,其原因除了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的农村社会中“赢利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而小传统的被蚕食与颠覆,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一个长期在外求学的青年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回到河北农村家乡时的感受。
“我自京旋里时,我的最堪怜悯、最可亲爱的母亲,再三的说她在外的艰难与困苦,要想回家过这个乡间的安乐生活。我来家一看,乡间古风已不复古了,人情已经大变了,绝不像以前朴素厚诚的乡间了,成为鬼诈的、奸滑的、刻薄的、无情的、暗淡的社会了。”[9]
从当时一些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看,这个青年的感受并不是限于个人经验的多愁善感,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对于科学主义的弊端,当时亦有少数学者提及一二。譬如贺麟先生即在20年代末指出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过分夸大了西方世界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并且指明:“我们没有科学,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殉道者。我们之所以研究科学,是因为它有用;西方人对科学的研究是为其无私利的内在价值及其宗教意义。……在一种怪论的意义上,可以说基督教是科学的庇护者,那些认为基督教与科学相冲突而反对基督教的人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基督教在中国决不会成为科学发展的障碍。”[10](P160—161) 不过,这种观点的赞同者并不多见。非但如此,虽然新文化运动在实质上只是以强调实用理性的大传统压倒了讲究神道设教的小传统,但它毕竟借助了西方文明的形式而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权威。而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与民族存亡之间的相关性,于是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实质是以大传统反宗教)的形式亦受到质疑。对此,可以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夭折为例。
在新启蒙运动发起之初,其推动者基本上仍是秉持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其目的也在于恢复五四时期反对传统与推重科学的理性主义。按照他们的原话,就是:
“在中国,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也是理性主义的运动,但是伴随着民族资产者的‘不幸短命而亡’,五四时代的理性主义也遂即被反理性主义所篡夺了。五四时代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的具体而微的小照,而近十年来的中国的腐败哲学也恰好就是欧洲十九、二十世纪的反理性主义的哲学缩影。但是最近几年来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中国的腐败哲学吹进了一点生气,使得他又有可能重新走回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来,这是一个实践的要求!”[11]
然而,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在发生环境上已经不同于新文化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迫切与深重,人们对于具有民族象征意味的传统文化已经不像五四时期弃如弊屣。因此,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在一开始就对传统文化表现出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要继承“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指斥孔子的哲学是“统治者的哲学”、“服从的哲学”、“愚民的哲学”,认为“某民族的一种学说、一种哲学、一种宗教,如果是适合于使人安分守己、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同时也仍可由异民族用为压迫自己民族的工具”。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要容忍“爱国的尊孔者”,说:“有的不愿意反对孔子,不反对宗教,但却愿意传播爱国的思想,我们还是要联合他。”[12](P12,14) 随着这一运动的开展,推动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便愈来愈微弱。在运动的倡导期,他们还号召人们“要摆脱一切传统思想的镣铐,大无畏地从事批判一切”[12](P21);至高潮期时,就仅提倡打倒“‘孔家店’被敌人以及汉奸利用的这一方面”[13];到了收尾期,新启蒙运动的推动者便给传统文化的取舍定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标准,即“凡是文化思想在终极的效果上有利于民族,能够提高民族力量,对于抗战救亡有一点一滴的贡献的,都应当许可它自由存在、自由发展”[14](P236)。这已与“新启蒙”的宗旨大相径庭。
总之,在抗战前后,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崛起,中国思想界虽然也有不同声音,譬如,中共领导人在抗战期间即批评“大后方很多人正利用民族口号鼓吹儒家与复古独裁思想”,强调“民族的形式就是人民的形式,与革命内容不可分”;[15](P326) “战国策派”中坚林同济亦曾将矛头直指孔子的儒学,认为“传统圣人讲道德,太钻入‘爱’的一字打跟头了。‘宽大为怀’的人生观,便是以‘爱人如己’为根据的。到了今天,太多好好先生,滑头老板,到处交头攘臂,相栩‘爱人爱人’。”[16] 不过,总的看来,这时的中国思想界主要思考的问题不是应否反对传统,而是如何改造传统。因为在他们中的大多数看来,民族精神的存亡与中华民族的存亡是不可分离的同一件事。如果说在抗战爆发之前,人们将传统的复兴仅视为救济道德的一种手段,那么在战争爆发之后,人们便自然将传统的保存视为民族延续的一个前提。哲学家贺麟先生的一段话颇能代表这种心声。1941年,在抗战的关键时刻,贺氏写道: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17]
三
严格地讲,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两次传统复兴,即民国初年的传统文化回潮与抗战前后的儒家文化再起。不过,对于这两次传统复兴而言,第一次更多地是因为道德救济而起,而第二次更多地则是因为民族危机而起。非但如此,因为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传统的问题逐渐被大家所共同认识,所以,相对于民国初年回归传统的呼声,抗战前后的传统复兴更具有“返本开新”的意味——即复兴传统,但不拘泥于传统;而是力图在传统中阐发出新的时代意义。这一点,从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即可窥见一二。
有论者认为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新生活运动之际,其动机完全是以中国传统儒学的仁义之说约束大家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此解释有一定根据,譬如在运动过程中,蒋氏曾反复强调:“我们所做的新生活运动,就其方式与内容来看,完全是一种社会教育,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人人都能‘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能够人人学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学术和技能,尤其是‘礼’与‘乐’两种首要的东西。”[18](P27) 这似乎是完全要回到先秦原始儒学。除此之外,蒋介石在同时对新文化运动也颇有微词,他曾向部属反问道:“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孔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选择地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那样,那我们要的新文化实在太幼稚、太便宜,而且太危险了。”[19](P25—26) 一方面倡导学习六艺,另一方面抨击五四。从这些论述看,蒋介石确实有复古主义的苗头。然而,如果我们将其在新生活运动中的所有言论综合考察,则会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
首先,蒋氏在提倡新生活运动时曾拿教会牧师做表率,说:
“尤其是现在居陕各国外侨,大半皆为教会之牧师,富于服务社会之精神与劝导民从之经验与能力,其原来许多服务社会之工作,如提倡体育,注重卫生,举办公益以及种种增进民众健康与社会福利的事业,皆与新运相合,故吾人推行新运,必与彼等密切联络推诚合作,籍重其助力,接受其指导,尤须效法其服务之精神与办事之方法。”[20](P40)
其次,蒋氏在发起新生活运动时曾对中国道德表失望,说:
“至于我们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乃是‘昨死今生’的运动,亦即一种‘起死回生’的运动,是因为国民的精神道德和生活态度实在太不适合于现代,而整个民族的生存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危险,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生活,以求民族之复兴。”[21](P46)
前面一段反映了蒋氏对作为西方文明之结果的基督教会的部分认同,后面一段则反映了他对作为中国传统之结果的国人精神的彻底否定。虽然蒋氏没有从中得出以西方道德取代中国传统的结论,但与回归传统的复古主义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事实上,蒋氏在思想上已经陷入一个原因与手段不能谐调的二律背反之中。一方面,从蒋氏的诸种言论看,他发起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国人的道德失范,而道德失范乃是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因此,从理论上讲,传统文化必须经过扬弃。另一方面,在蒋氏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独立的哲学,或有了独立的哲学而不能发扬光大,那么这个国家必然难以生存。因此,从手段上讲,传统文化必须彻底回归。也正因为这个二律背反,蒋氏以极大的雄心与期望发起了旨在改变与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新生活运动,但结果却导致一场“革心”运动的庸俗化。
事实上,尽管蒋介石感受到中国传统的弊端而未能明说,但国民党内部一些高级官员则已经认识到儒家传统的内在困境。譬如,曾任广东省主席的粤系军人陈铭枢曾在一次演讲中对儒学提出严厉批评。他说:
“我们要晓得,所谓道德,非自天降,非自地出,是起于人群之不得不然。所以一方讲仁义一方也要受物质的引诱。二者交战,无时或已。儒家要人克去物欲,来就理想中神圣的生活,故苦口婆心谆谆不已。但是各人的禀赋既不同,物质的引诱的压迫,又不能免,哪能就办到理想中的神圣生活呢?所以讲者自讲,而做者自做。而且讲得太玄妙,往往反与实际的生活相隔得远。”[22](P239)
陈氏甚至坦承中国的传统道德对人性要求过高,“适于大同世界,而不适于现在连小康都办不到的世界”。[22](P249) 这种对传统的批评之严厉程度可以说不亚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与胡适。
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作为民族象征的传统必须回归;民族危机之所以出现,作为源头之水的传统难辞其咎。正是由于这两个相反而又相关的矛盾动因,中国思想界的一些人士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即“不守旧”又“不盲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原则,其做法类似于后来新儒家所提倡的“返本开新”。从理论上讲,这些人士的建议颇为中庸——对于传统道德,他们讲究的是“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无”;对于西方文化,他们强调的也是“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23] 这很有点类似于后来有人所说的“取其菁华,去其糟粕”。然而,在中西文化之中,何为所当存?何为所当无?对于这类更为具体的问题,这些中庸派却难以有所创见。他们只能笼统地说“在纵的方面不主张复古,在横的方面反对全盘西化”。而在最后,这些人士只能以目的取代手段,提出文化建设的三个目标,即“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与“争取民族的生存”。[24] 然而,随之而生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些中庸派人士所极力反对的“复古主义”与“全盘西化”也可以实现这三个目标,那么它们是否也可被认定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手段呢?
四
从文化讨论的广度看,抗战前后的中国思想界不亚于五四时期;而从文化讨论的深度看,抗战前后的中国思想界则远逊于五四时期。在五四时期,一些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如杜亚泉、吴密、梅光迪、张君劢等人,他们深切地认识到新文化运动的弊病在于夸大理性功能的科学主义,而这一点,恰恰又可以纠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痼疾——实用理性。而在抗战前后,中国思想界一些人士在强调传统时,他们大多看重的是传统文化作为民族象征的符号功能,对于其中所蕴涵的过分功利化的实用理性取向,却不仅不加以针砭与匡正,相反却是以一种与实用理性相适配的科学主义来强化。譬如,蒋介石发起以强调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新生活运动时,仍然要反复指明这一运动的“科学化”本质;而王新命等10教授在发起“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运动时,也谆谆告诫大家要“应用科学方法”。[23]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特质导致了国人缺乏超越功利目的的终极关怀。因此,要弥补这一先天缺陷,应该通过各种形式在国人中间确立一种合理的怀疑论——即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持一种谦虚态度,相信人类理性所能掌控的已知世界与人类理性不能把握的未知世界并不能重合,后者要远远大于前者。如此,才可以建构超越人类理性(既可能是大众的,也可能是精英的)的社会制度(包括各种规范)之先验性,从而确立起社会制度的真正权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对任何生物来说,最大的恶是崇拜自己或崇拜自己的创造物。这种崇拜之所以是万恶之罪,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对真正依附上帝这一绝对实在的状况所能作出的最严重的道德和理性反叛,还因为它为所有其他的恶打开了大门。 ”[25](P144) 而崇拜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的自我崇拜,因为崇拜科学的潜台词就是崇拜人类自己的理性能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特点,是将西方文明简化为科学精神。这一点,对后世的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到抗战前后(甚至更晚的时期),这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基本共识。譬如,主张全盘西化的熊梦飞在20世纪30年代认为“西洋现代文化的根本”首先就是“科学化的学术思想”,其次者是与科学相适配的“机械化的工业与农业”以及“民主化的政治社会与家族组织”。[26] 而在1944年,信守国家主义的陈启天也同样认为:“近代西洋文化,不但对于自然和社会的研究科学化了,即对于哲学和艺术也科学化了;不但对于思想的体系科学化了,即对于生活的形态也科学化了。这种科学文化,对于人生确立了三个基本信念:一是随时进化的信念,二是人定胜天的信念,三是实事求是的信念。本此三个信念,于是科学愈进步,文化也愈进步。科学文化,是近代西洋文化之母。”[27](P12) 言下之意,科学思想已经不仅能等同于西方文明,甚至可以等同于现代文明。在当时就有人认为“与其谓提倡文化建设,不若曰提倡科学建设之更为直截了当”。[28]
当然,对于实用理性与科学主义的弊病,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也不是毫无认识。譬如,贺麟先生即敏锐地发现: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而言,基督教并非一无是处。因此他不仅反对“附会科学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甚至提出“须吸收基督教的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17] 后世的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等人也非常注重从形而上学的角度重新阐发儒学的现代意义。但是,这些人所孜孜以求的“返本开新”并没有超越五四时期学衡派的水准(尽管个别人物的学说更为精致化与学理化),换言之,迄20世纪上半叶,新儒家们的主张也只是停留在玄学的境界,而非神学的境界。其中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悖论:一方面,如果现代中国人将儒学的复兴仅止于玄学的水准,那么他就如同中国原有的大传统,只能对少数人(君子)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如果现代中国人硬性将儒学提升为一种宗教性道德(即进入神学境界),那么它可能完全丧失中国大传统的本来品性,而成为一种非传统(甚至反传统)的东西。然而,如果只是停留在玄学层次,而不能进入神学境界,中华民族精神的改造便可能面临两个无法回避的困境:即在“科学”或“玄学”层次,如果放弃精英人物对社会的硬性道德规范,那么这个社会可能陷入完全的功利主义境地,将“是否对自己有用”视为惟一的行为标准;而如果强化精英人物对社会的硬性道德规范,那么这个社会又可能陷入完全的专断主义境地,将“是否对政府有用”视为惟一的行为标准。
1946年10月19日,一位中国著名大学的教授在当时发行量颇大的《观察》杂志上撰文感叹道:
“本来所谓‘国于天地,必有以立’,这个‘有’原也不指武器,而是指某一种社会中人群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则——几棵思想上的大柱子,顶住了这个社会(或国家)的组织机构。一般人称这个机构为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这几棵大柱子有的时候叫作三纲五常,有的时候叫做四维八德,有的地方叫作民治思想,有的地方叫作共产主义。不管叫它什么,重要的是在这个社会中的人群必须能同意支持这些柱子,这些原则,否则整个机构垮下来,必酿成极大的灾祸。尤其重要的要同意支持,不是强迫支持。”[29]
而在一个对个人理性无所限制的社会之中,要么是没有柱子,要么就是强迫支持。因此,这个学者在抗战结束一年之后的哀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失败的一个必然结果。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培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研究”(03JZD0027)。
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科学主义论文; 基督教论文; 新生活运动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民族精神论文; 玄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