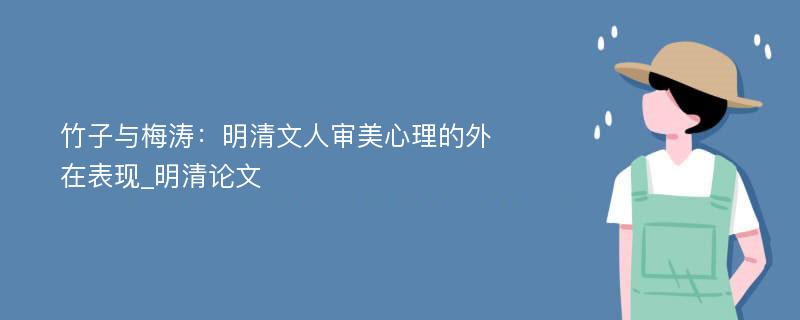
拗竹与媚桃——明清文人审美心态的外在表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明清论文,文人论文,外在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审美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受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文化氛围、时代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和制约,会产生为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现象。明清文人对拗竹和媚桃的偏爱,正是在明清之际大兴文字狱、禁锢和取缔“异端”思想的高压政策统治下,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启迪,强烈要求凸现个性、独抒性灵和以“情”为核心,追求世俗趣味审美心态的外在表征物,并使这种审美心态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丰富和完善。
审美心理研究表明,人们的审美情趣是以偏爱的形式表现出来,意味着主体的审美活动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习惯于按照某种心理定势来进行。同时,审美情趣标志着人们的潜在审美需要外化成为现实。审美活动一般是以个体为本位而进行的,由于个体的审美理想、审美能力等的不同,因而在审美情趣方面呈现出明显差异。但是从历史的宏观角度审视,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文化氛围、时代精神等因素共同作用和制约着个体的审美实践活动,这些历史宏观因素构建和铸合成特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以人们的审美实践为中介,又转化和构建成特定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因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同,个体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又呈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共同特征,从而会产生一些为这一时代所具有的独特的审美现象。例如唐代对秾桃艳李的偏爱、宋元对寒梅秋菊的执著、以及明清文人对拗竹和媚桃的嗜好,便是这种独特审美现象的体现。
对“拗竹”的青睐和垂爱由来已久、历代文人仕子赋予竹以深厚的内涵,把它与松、梅视为“岁寒三友”而倾注大量溢美之词。《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宋人刘延世喜欢画墨竹,题诗曰:“酷爱此君心,常将墨点真,毫端虽在手,难写淡精神。”(《画继》)然而,给“拗竹”赋予深刻的社会意义,把它转化和提升为重要的情感符号,用以表达主体的某种政治意愿或情感意绪,并且成为一种社会所认同的普遍倾向,在社会生活、文学艺术领域中大量存在,则确是明清时代所特有的审美现象。文人墨客把“拗竹”比作“君子”,对它的清风亮节和孤傲的禀性由衷赞叹。
明代钱宰《卢德民双竹》:
此君一本森双干,恰似孤竹生夷齐。
清风节操终并立,明同环佩长相携。
或骑两龙齐上下,又挟苍风随高低。
何当联镳入云去,玉笙吹向滛池西!
詹同《题李息斋墨竹》:
翠凤振秋翎,箨龙堕春影。
有美君子交,玉立在清境。
思之劳梦魂,日暮湘云冷。
刘基《题柯敬仲墨竹》:
苍龙倒挂不入地,回首却攀云上天。
夜深去散明月出,化作修篁舞翠烟。
而清代的明遗民和众多骨鲠之士更是把拗竹当作喻情明志的审美对象。郑燮《题竹石图》:“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用以寄托自己的生活和道德理想。黄景仁《癸已除夕偶成》:“寒甚更无修竹倚,悉多思买白杨栽”。——因贫寒无力栽种修竹而痛感人生的悲哀。清代画家金农绘画常以竹、梅抒傲然之情,“予僻性爱竹,爱其陵霜傲雪,无朝华夕瘁之态”,故“暇日则写其貌”。他“学画竹,前贤竹派不知有人,宅东西种植修篁以千万计”,“即以为师”。而吴历酷爱墨竹,“竹之所贵,要画其节操,风霜岁寒中,卓然苍翠也”,“兴来画竹,要得其风雨流韵,霜雪洒兮,乃得竹君之品格”。——把人的种种品格精神赋予竹子,而后又从竹的形象中审视和观照自身。
对于桃花,由于它的艳丽外观和蓬勃生机而受到人们的垂爱。唐代文人墨客更是把桃花视作时代精神的象征,作为自身审美心态的外在表征物:宋元时期桃花一度受到冷落;而到了明清时代,桃花再度成为文人仕子的重要审美对象,而倍受青睐。如明代沈周《题画》:“嫩黄杨柳未藏鸦,隔岸红桃半著花。如此风光真入画,自然吾亦爱吾家”。徐祯卿《偶见》:“深山曲路见桃花,马上匆匆日欲斜。可奈玉鞭留不住,又衔春恨到天涯”。而唐寅:“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把“一茅屋”、“万树桃花”视作人生的最大满足。清代马日璐《杭州半山看桃》:“山光焰焰映明霞,燕子低飞掠酒家。红影到溪流不去,始知春水恋桃花”。而舒位《蜘蛛蝴蝶篇》:“蜘蛛结网诱青虫,桃花飞入怨东风。蝴蝶寻花尾花往,打尽桃花同一网。蜘蛛不语蝴蝶愁,丝丝罗织桃花囚。桃花隔雾看蝴蝶,可似天女逢牵牛。潇潇春雨当窗入,沾泥花片胭脂湿。蝶粉蜘丝一劫灰,青虫自向墙根立”。——诗歌撷取一组风雨桃花,蝴蝶青虫和蜘蛛互相制约的春天景象来描写,构思颇为奇特。
除直接描绘外,在明清诗词创作中,有“拗竹”、“媚桃”作为背景,以此构建诗词境界的,更是不胜枚举。这种现象并非是一种孤立的审美现象。吴功正先生曾指出:“审美以个体活动为本位,现象存在于个体活动之中。个体审美活动有其特定的心境、方式、境界。但个体审美活动无法也不能脱离群体氛围,个体审美心理屏幕有着群体氛围的投影,群体意识包括文化、审美历史意识和氛围”①因而,对这种独特审美现象的揭示和阐释,必须从文化的、历史的角度进行审视,特别是从生成这种现象的终极原因——社会生活的角度进行审视和阐释。
自明代中叶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反对传统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倾向日趋显明,最终形成为以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为标志的启蒙思潮。虽然明清两代在文化思想上采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以此禁锢和取缔“异端”思想,但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产生为基础的,以市民阶层为主导力量、以主体意识觉醒为标志的启蒙思潮,仍然给明清时期的哲学、文艺等领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对“拗竹”的酷爱和对“媚桃”的嗜好,便是受启蒙思潮影响的一种独特的审美现象。
一、“拗竹”——凸现个性,独抒性灵的审美心态的外在表征
明清时期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是从否定天理人欲之分开始的。程朱理学是严申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所谓“治心”就是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到了陆王心学,陆九渊提出“心即理心”,使人心理获得了天理的资格;王守仁提出:“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把一切归结为致自己的良知。“致良知”的提出,就使程朱理学的“治心”变成了陆王心学的“致心”,即回到自己的本心。正如成复旺先生指出的,陆王心学“填平天理人欲的鸿沟,把‘治心’变成‘致心’依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激励自主意识、启发怀疑精神、接受生产实际等三点,综合起来就成了对人心的某种程序的解放。所谓某种程序的解放,是说陆王把天理移植到人的心中,是要把外在的束缚变成内在自觉;这也就是外在束缚的缓解”。②
王畿、王艮向前发展了王守仁的心学理论,王畿强调良知是人的自然本性,故只当“坦怀任意”、“随其所谓”而“不须防检”,从而给了人心以充分的自由:而王艮则从“尊身立本”的原则出发,把良知推向了人的现实生存,“尊身”之道就是尊重一切个体的人的生命和生存权力的道。而“异端之尤”的李贽则从“人心有私”的命题出发来建构一个新的心灵世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使争取心灵自由落实为争取人的现实生存的自我意识、反叛传统社会理性的自由。主体意识的觉醒至此才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思想体系。
明清时代文网极严,统治者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企图以消灭肉体的形式来取缔“异端”思想;另一方面采用八股取士的形式来僵化和禁锢人的头脑。但是没有能够阻止启蒙思潮的发展和蔓延。以主体意识觉醒为标志的启蒙思潮在文艺创作和审美领域中的反映和表现,便是凸现个性意识,独抒性灵这样一种审美心态的铸合而成。
李贽极力倡导“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所谓“童心”便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李贽所提倡的“童心”即是同社会理性对立的个体感性心灵,就是对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假人、假言、假文的已经异化了的文化的反叛。徐渭竭力否定和排斥一切外在加于人的、凌驾于人之上的统一准则,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性,因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准则;每个人的自然情性就是自己的准则。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疏纵不为儒缚。”汤显祖有一腔“伉壮不阿之气”,他在《艳异编序》提出:“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这种“伉壮不阿之气”实际上就是傲视权贵、鄙弃世俗的独立不羁之气。袁宏道受李贽的影响,强调文学创作中“性灵”的作用,认为诗人写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并且认为“大抵物真即贵,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与丘长孺》)不同的诗人表现出各自的创作个性。同时,力图否定和挣脱社会对于人的一切束缚——“凤凰不与凡鸟共巢,麒麟不与凡马共枥。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笔,听人穿鼻络首?”(《中郎先生行状》)因为在他看来,人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识张幼于箴铭后》)诗也可以怨而伤,写得很露骨,“但恐不达,何露之有?”袁宏道的“性灵说”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明文坛的复古派给予了极大的冲击。
清王朝的全面复古以及在文化上实施高压政策,企图重新用理学来禁锢和扼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但启蒙思潮仍然不绝如缕,同时其中更渗透着异族统治的强烈反抗意识。清初黄宗羲对阳刚之美的倡导,就包含着对异族统治的反击。廖燕则提出:“从来著书人,类皆自抒愤懑,”(《自题四书私谈》)要“笔代舌,墨代泪,字代语言,以笔约代影照,如我立前而与之言,而文著焉。则书者,以我告我之谓也。”(《二十七松堂集自序》)即要求用自己的笔描绘自己的真性情。八大、石涛、髡残、张仁等于明亡后出家为僧,以示不臣服清廷,他们主张“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和“借古以开今”。袁枚反对以儒家“诗歌”为主旨的“格调说”、“肌理说”,主张创作个性自由,又倡导和鼓吹“性灵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味适口,其音悦耳,便是佳诗。”(《随园诗话》)认为情感只有无阻碍地从自身内心中渲泄出来,才是真情实感,由此而论,清代的“性灵论”同样凸现出强烈的个性意识。
龚自珍提出“面目之完”的观点,实指心灵、性情之“完”,亦即整个心灵、性情真实无隐,完好无损地表现出来。因而他认为真正的艺术产生于不可遏止的激情的爆发,激情只有象厉风冲孔动楗,潼河破隘蹈决那样地爆发出来,才是真正的“诗歌序记词辩”。那种“受天下这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的激情所创作的文艺才是天下最伟丽的文艺。郑燮更是提倡“血性”:“英雄何必读书史,直摅血性为文章。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偶然作》)也就是无所顾忌地直抒胸臆。
这种要求强烈地凸现个性意识,独抒性灵的审美心态制约着明清文人的审美情趣和审美情感,而主体必然要凭借某种对象物以使这种情感和情趣外在化或客观化,并且通过这种对象物来观照自身。如成复旺先生所论:“中国传统的审美,实质上是对自我人格的欣赏。但是人格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要成为审美对象就必须外化为物,或者叫物态化。中国古代的各种人格往往都要从物中寻找根据,以证明自己合于自然”。③而“拗竹”的自然属性使之成为最适宜把文人墨客的这种审美情感和内在人格外在化和对象化的物体,或者说,成为明清文人强烈凸现个性意识,独抒性灵的特定审美心态的外在表征物。诗人歌咏之,画家描绘之,并且把自身的情感融入艺术形象之中。
徐渭在《风竹图》题画诗中写道:“画里濡毫不敢浓,窗前欲消碧玲珑。两午梢上无多叶,何事风波满太空!”——他要求自甘清苦萧条,以保持心灵的平静,但世间的风波却依然袭扰和折磨着他。他又在《雪竹图》的题画诗中写道:“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社会现实的摧残可以使他萧骚困苦,却不能摧折他那顽强的生命,越是摧残,他就越是愤怒,越要抗争。徐渭曾评论一位友人的绘画说:“余观梅花道人画竹,如群凤为鹘所掠,瓴羽腾闪,捎捩变灭之诡,虽凤亦不得而知。而评者或谓其赝,岂理也哉!”(《书梅花道人竹谱》)这与其说是现实世界的竹的真实,勿如说是画家的心灵世界的激情的真实。
郑燮禀性骨鲠,酷爱竹,不但用丹青描绘之,并曾题画竹诗有几十首,以赞美竹的刚劲风骨。郑燮在《题竹石图》云:“画根竹枝插块石,石比竹枝高一尽。虽然一尽让他高,来年看我翻天力。”其愤世嫉俗,掀翻天地的激情势不可遏。在《劲竹凌云图》这幅墨竹图的长跋中,郑燮又如此写道:“画竹之法,不贵拘泥成局,要在会心人得神,所以梅道人能超最上乘也: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故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依于石而不囿于石,是其节也;落于色相而不滞于梗概,是其品也;竹其有知,必能谓余为解人。”在这幅画中,画家把竹子表达得高而劲挺,是有深意的。画家借题发挥,以竹的自然特性比拟人的秉性节操,寄寓他自身“瘦劲孤高”和“豪气凌云”的个性意识和激愤心态。
“拗竹”所表征的强烈凸现个性意识,独抒性灵的审美心态,在其他艺术领域特别是小说、戏曲中,通过塑造人物形象而充分体现出来,这些同样是明清启蒙思潮影响的产物。
二、“媚桃”——以“情”为核心,追求世俗趣味审美心态的外在表征
“桃花”在唐代曾受到文人墨客的极度青睐。因为唐代正处于国力强盛,事业如日中天的封建社会的颠峰阶段,文人仕子充满自信力,渴望建功立业,博取功名,这种视野向外拓展,生气勃发的社会文化心态铸合成唐人的追求博大、宏丽的审美心态。而桃花所具有的外在的“力”的图式与唐人的内在心理图式正相契合,因而桃花在很大程度上便提升和转化为唐代文人审美心态的外在表征。值得提出的是,唐人对桃花的审美观照,在满足感性享受的同时,更多地给予了理性的审视。
“桃花”在明清时期再度受到文人的偏爱,并几近狂热的程度,然而其中所蕴涵的社会意义以及它所表征的审美心态,与唐代相比照,便具有本质的差异。明代中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新兴的工商业城镇日趋增多,市民阶层力量日益壮大。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要求冲破各种束缚而自由发展相呼应,新兴的市民阶层要求摆脱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日趋强烈,由此而形成一股以主体意识觉醒为标志的启蒙思潮。
主体意识的觉醒,使人回归到人的现实生存之中。因此,明清的启蒙思潮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既不象儒家那样站在社会的立场,也不象道家那样站在自然的立场,而是站在个体感性的人的立场;既不象儒家那样要求个体感性的人服从社会,也不象道家那样要求个体感性的人服从自然,而是要求社会和自然一齐服从个体感性的人。亦即要求社会和自然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符合人本性的内在情感欲望。这种社会文化心态体现在审美领域,便是以“情”为核心,追求世欲趣味的审美心态的生成。因此,尽管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程朱理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束缚人的心灵,但世俗的“情”和“欲”依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权利,在文艺启蒙思潮中,被提到首位的是“情”。
李贽根植于人的现实生存,提出:“人必有私”和“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并且把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作为他判断善恶的唯一标准,一切外在于人、压抑人的本性,禁锢人的情欲的社会理性,没有存在的依据。而他所倡导的“童心”便是同社会理性相对立的、充满世俗情感欲望的个体感性心灵。李贽发其端,众人继其后,充分肯定“情”的地位和作用。他们的思想核心即是:主宰人的不是某种超越性的先验理念,而是感性的人自身的情感欲望,审美的目的是在情感欲望的表达中获得自身的满足和肯定,而不是某种道的阐释。谢榛认为,“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四溟诗话》)汤显祖把“情”作为一种普遍人性加以歌颂,“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者,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记》)题词)并把这个“至情”观渗透到创作实践中去。徐渭认为,诗文骚赋产生美感作用的因素,“无他,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选古今南北剧序》)并强调“俗”:“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欲,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杂一毫糖衣,真本色。”“点铁成金,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动人。”(《又题昆仑奴杂剧后》)
黄宗羲论述道:“诗以道性情”而“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南雷文定》)并且把“性情”分为属于表现怨女逐臣“一编一曲”的“一时之性情”和表现属于人的普遍善性的“万古之性情”两类。而叶燮则把情与理相提并论,同视为圣人之道,同归于“物之数”。王夫子论述“情”与“物”尤为细致:“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膺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絜天下之物,与吾情相当者不乏矣。”(《论邶风·匏有苦叶》)——把“情”看作是人与物相交感而产生的主观心理现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冯梦龙还对“情”的类别及社会作用特别是男女性爱作了深入探讨,如《情史叙》中曰:“私爱以畅其悦,仇憾以伸其气,豪侠以大其胸,灵感以神其事,痴幻以开其悟,秽累以窒其淫,通化以达其类。”不同的“情”会产生相应的情感效应。在这种以“情”为核心的、追求世俗情趣的审美心态的制约和趋使下,明清文人墨客的审美观照和审美体验则更加侧重于悦耳动目的官能满足。曾经为宋代理性美学所鄙视的“桃花”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倾心观照和描述的审美对象。因为桃花的艳丽眩目的色彩和妩媚烂漫的姿态正符合他们感性主义的心理图式。
因而唐寅把“万树桃花月满天”当作人生的乐趣和满足;袁宏道对桃花更抱有痴情:“寒食后雨,余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雨后游六桥记》)而在《晚游六桥待月记》中因“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拒绝友人赏梅邀请。这种对桃花的嗜好和痴恋,不存在对其所蕴含的意义内涵的理性思索,而纯粹是对官能感受的魇足和享受,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心理陶醉。明清文人的以“情”为核心,追求世俗趣味的审美心态,用“媚桃”作为自身的外在表征物,确实是非常契合的。
同样,在这种以“情”为核心的,追求世俗情趣的审美心态的制约和趋势下,明清文坛上产生了大量描写世故人情和男女性爱的小说、戏曲等作品。主体无所顾忌的情的发露,绝非以往那种含蓄敦重、循规蹈矩。《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红楼梦》等即是以男女爱情悲剧为主线的,当然作者把它放在社会环境大背景中加以描述,把爱情悲剧和家国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更加深刻的内涵。而《金瓶梅》则更是无所顾忌地放纵情欲、追逐淫乐,在道德品质上极端败坏堕落的现象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这种毫不隐晦的纪录式描写,与其说是对社会腐朽本质的揭露,勿宁说是人的情欲本能长期受到压抑后的一种心理变态和扭曲的反映,是一种心理能量的不正常渲泄和释放。
特别是明中叶后,因市民阶层兴起而导致通俗文学创作的繁荣。以《三言》、《二拍》、《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为代表,其作品内容具有共同特色即:大量描绘情爱和市井生活,三教九流、凡夫俗子成为作品主角,带有浓厚的市民意识。此外,民歌受到文人的青睐,称《锁南枝》等为“时调中状元,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散曲的创作亦从求仙访道的巢臼中解脱出来,回归到民歌化、俚俗化的路子。在启蒙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明清通俗文学,“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把当时由商业繁荣所带给封建秩序的侵蚀中的社会作了多方面的广泛描绘。多种多样的人物、故事、情节都被揭示展览出来,尽管它们象汉代浮雕似地那样薄而浅,然而它所呈现给人们的,却已不是粗线条勾勒的神人同一、叫人膜拜的古典世界,而是有现实人情味的世俗日常生活了。对人情世俗的津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饮羡渴望,对性的解放的企望欲求,……尽管这里充满了小市民种种庸俗、低级、浅薄、无聊,尽管这远不及上层文人士大夫艺术趣味那样高级、纯粹和优雅,但它们倒是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是对长期封建王国和儒学正统的侵袭破坏。”④
总而言之,明清文人所倡导的“情”,决非是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维护正统伦理观的儒家情愫;也决非是“竹林七贤”藐视功利、啸傲山林,与自然相亲和的道家情韵,而是根植于人的本性和基本生理需要的“情欲”和“情趣”。它不是理性的而是感性的,不是雅正的而是世俗的。“情”的地位的肯定和提高,标志着明清文人审美心理结构的更趋完善。
注释:
①吴功正:《中国文学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
②成复旺:《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页。
③成复旺:《神与物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④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