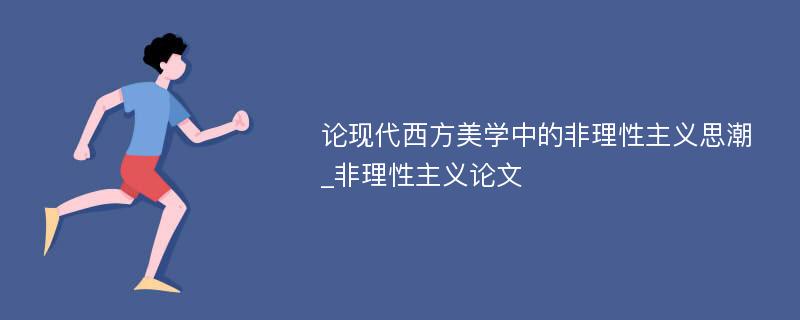
现代西方美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理性主义论文,思潮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西方美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以现代西方相应的哲学流派作为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是后者在美学领域中的逻辑延伸和审美衍化。这种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具有鲜明的反传统反理性倾向,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和总体倾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简要地分析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现代西方美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形态演变和基本特征,以便推进对文艺美学中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深入认识。
一、形态演变和渊源回溯
现代西方美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以一些重要的美学流派为代表,如唯意志论美学、直觉主义美学、表现主义美学、精神分析美学、存在主义美学、新托马斯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和解释学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美学的后期代表马尔库塞的“新感性”论也属于此列。唯意志论美学以德国的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叔本华认为艺术通过“观审”(即神秘性直觉方式)来把握理念(意志的客体化);摆脱意志的纯粹主体在直观事物时自失于对象之中,达到主客体同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在审美直观中主体成为对象本身。叔本华的“观审”说确认审美活动的直觉性、非理性和非功利性。尼采认为艺术是对人生的肯定和对人生价值的提高,视艺术为超越人生痛苦和实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的手段,并把日神(阿波罗)精神和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两种艺术冲动视为艺术拯救人生的内在动力机制。尼采把审美活动作为主体自我对事物对象的创造,突出了审美主体性。直觉主义美学以法国的柏格森为代表。柏格森认为,艺术直觉作为特殊的知觉方式直接感知独特事物并伴随着独特情感。艺术直觉无外在目的性,以自身为目的。艺术作为生命绵延的一种方式具有不可分割、不能分析的整体性,艺术的创造和欣赏必须依靠神秘的直觉。他还提出艺术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表现感情,不如说是为了使我们接受感情”,“艺术将感情暗示给我们”。这种艺术情感是个别化、新颖性的情感,是出现一次就永不重演的东西,带有美的性质。柏格森的艺术直觉概念,不但指对审美对象的直接领悟,而且具有取代理性认识直达事物本质的功能。表现主义美学以意大利的克罗齐为代表。克罗齐提出了艺术是抒情的表现的观点,并把艺术即直觉作为这一观点的前提,坚持把艺术的抒情表现同时看作心灵的纯粹直觉活动。克罗齐把情感与直觉直接相连,强调情感是直觉活动的基础和内容,情感给予直觉以连贯性和完善性:直觉则赋予情感以形式,情感必须通过直觉方式表现出来才能构成艺术。克罗齐把直觉与表现等同起来,论证了美和艺术的非理性和表现性。精神分析美学以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和瑞士的荣格为代表。弗洛伊德把无意识理论和性本能理论作为美学和艺术的基础或出发点。他认为性本能构成了艺术活动中最重要的动力和它所要满足的基本欲求,把美的本质和艺术创造潜因归结为性力情结作用:提出文艺创作是被压抑的性本能的转移和升华,艺术的功能主要在于本能欲望的幻想性满足。荣格则强调美和艺术建立在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原型)之上,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的根本因素,决定着艺术的本质。对于这种原始意象的审美接受则是一个直觉性的神秘参与过程。弗洛伊德把艺术创作的本质、动力和功能归结为无意识和性本能,虽有泛性主义倾向,但其文化目标在于通过揭示个体感性自我与社会理性规范之间的矛盾关系而求得两者的协调。存在主义美学以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法国的萨特为主要代表。海德格尔以独立的、不可重复的此在的历史性生存为基点确认艺术最终必然表现充满其种神秘直觉性的心理体验(如畏惧、厌烦、焦虑、绝望、死亡等),重视非理性的“领悟”,指出艺术的本质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作品寄寓着被创造的个体存在。萨特的美学思想的核心是自由和想象。他把艺术定义为“由一个自由来重新把握世界”,认为艺术的价值在于对现实的否定中寻求自由,审美因自由而意识到自己的本质性主体地位,进而整体性地把握世界。由想象所建立起来的自在与自为相统一的世界(非现实的世界)就是美和艺术。
新托马斯主义美学以法国的马里旦和吉尔松为代表。马里旦提出以神学直觉主义为中心的艺术论,认为艺术作为创造性的心灵活动,有别于知性分析与理智活动,是一种由上帝给予启示的神秘直觉。最高的存在(即上帝)只有通过神秘直觉才能认识,诗是对最高存在的一种“创造性直觉”,它源于“精神的无意识”(不同于本能的无意识),以自由的直觉方式与纯粹的存在精神直接沟通。马里旦要求“艺术为神效劳”,使艺术隶属于神学目的。吉尔松认为 绘画艺术是通过形式手段赋予存在以形式,人们通过对绘画所创造的形式的直觉,可以具体领悟到上帝的存在。新托马斯主义美学竭力把直觉、无意识等现代新概念引向神学轨道,把符号的象征指向一种自身之外的存在即上帝,表现出唯灵主义。现象学美学以波兰的英伽登和法国的杜夫海纳为代表。这一美学流派以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为基础。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强调通过非理性的“本质直觉”方法获得纯意向性意识。英伽登引用意向性理论来解释审美和艺术活动,认为艺术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的意向性活动,艺术作品是一种以自由想象形式出现的纯意向性客体,要求充分揭示创作主体的意向性特点及艺术作品的内在结构:指出意向性特点把审美主客体联系起来,赋予内在统一性。英伽登关于欣赏主体“重建”活动的理论是以纯意向性意识为思想基础的。杜夫海纳把研究的重点由创作主体的意向性转向欣赏主体的审美经验,指出审美感知和审美对象相互作用,在情感“节点”上合成审美经验。审美经验中主客体统一的基础是“情感先验”,情感先验由于既先于主体又先于客体,所以同时规定着主体和客体,使审美感知和审美对象实现内在统一,而这种情感先验又源自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自我理论。解释学美学以德国的加达默尔为代表。在加达默尔看来,“理解”活动作为人自身的基本存在方式,超越于科学认知方式而以非逻辑思维和领悟方式为其主导性特征。加达默尔重视对艺术作品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强调只有通过审美理解才能发现人类的生命内容和自由本性的真理性认识。他把鉴赏主体的审美理解规定为艺术作品存在方式的本质要素,突出鉴赏主体的审美理解活动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了审美理解的历史性特征(即理解的即时性、差异性和无限性)和认识性特征(即作为一种特殊认识以领悟形式表现出来,不同于概念性认识)。解释学美学的审美先见、视野融合、效果历史等观点与审美理解这种主观相对的特殊认识有内在关联。法兰克福学派的后期代表、美国的马尔库塞在美学上提出了新感性论。他以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为前提而提出人的本质是“爱欲”的观点,并由这一观点推出人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的结论。他强调为了实现爱欲解放和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必须进行本能革命。这种本能革命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审美和艺术。马尔库塞认为现代社会技术理性的全面统治导致人性异化,使人沦为丧失创造性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只有在艺术的“审美之维”中才能消解“人的工具化”、非人化弊端,恢复人性和自由。他企图把审美和艺术问题包括在作为保证爱欲自由实现为条件的“非压抑性文明”方案中,提出了“爱欲—自由—审美—生活”的模式,并把艺术的否定性、肯定性双重社会功能与感性解放的自然人性要求联系起来。
上面对各个美学流派理论形态的分析,主要是就其理论基础、思想特色、建构维度中所展示的非理性主义的实质而言的,它们的理论形态的递相嬗替,就形成了现代西方美学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整体流变。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对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文艺流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文学、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黑色幽默等,虽然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各不相同,但基本上以非理性主义为美学取向,都着重于主体内心世界的自我意识,执着追求直觉体验、本能冲动、潜意识心理、瞬间情绪、梦境幻觉等现代感觉。它们以非理性的灵韵来表现对社会异化的反思:世界一片“荒原”,社会充满“荒谬”,人生犹如“城堡”,他人成为“地狱”,生活就是“等待”;人成为了丧失自我的“局外人”、“机器人”、“空心人”,或异变为非人,即“毛猿”、“犀牛”、“甲虫”等。那种用夸张、变形、暗示、幻化、象征、隐喻等手法所渲染的陌生感、孤独感、焦灼感、恐惧感、幻灭感、绝望感、荒诞感、无归宿感,真切地表达了处于理性铁幕下的个体感性存在寻找自我、寻找精神家园的根本意向。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的崛起和发展,从社会背景和现实原因来看,受到了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直接影响。西方近现代发生了由理性至上理性崇拜向理性危机理性反思的历史性转换,理性主义的极度发展实质上引发了非理性,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正是传统理性主义本身危机不断深化和发展的产物。现代社会全面理性化和“技术中介化”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征服世界认识自身的理性能力和信心,而人凭借自身理性能力创造的物质技术文明又成为压迫人的异己力量,科技文明发展却以对人自身的侵犯、剥夺、奴役为代价,导致人的物化、工具化和非人化,人不成为人。高度的科技文明和严重的精神危机形成巨大反差,理性困境、人的异化、生存危机成为现代西方美学非理性主义思潮涌动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原因。再从思想渊源来看,从古希腊到近代的非理性主义传统流脉成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的历史渊源。古希腊美学中普遍存在的灵魂理论(灵魂不朽、灵魂轮回),具有原始神秘主义色彩。赫拉克利特的生成主义,皮浪的怀疑论,高尔吉亚的不可知论,斐洛的神秘主义,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灵魂论(涵盖了理性和非理性),“迷狂”(delirium)说,“卡塔西斯”(katharsis)论,共同构成了西方美学中非理性主义的源头。中世纪的神学美学,其非理性主义特点则以宗教形态出现,神示、天启成为审美和艺术的动力和旨归。奥古斯丁提出的上帝之美,圣·维克多推崇的“看不见的美”,托马斯·阿奎那强调的美感直觉性,都充满着神秘主义和直觉主义,也是西方古典美学非理性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中世纪神学美学的非理性主义在现代新托马斯主义美学那里得到了复活。西方近代美学中,浪漫主义美学思潮(包括前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崛起,崇扬情感和感觉,崇尚感性自我,成为近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表现形态。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休谟所提出的怀疑论,为近代非理性主义美学心理学取向寻找到突破口。从德国古典美学来看,费希特的“自我”哲学高扬主观自我和情感意志,谢林的神秘性美感直观强调直觉和灵感,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把灵魂不死、上帝存在和自由意志归于不可认识的本体界,为非理性和信仰留下了地盘。黑格尔辩证思维本质上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统一。他在把理性主义推向极端的同时,又大力肯定不断生成和超越的非理性存在,极为重视非理性精神那种永不满足的超越本性,“辩证的思维就是理性—非理性的思维”②。黑格尔美学“情致”说非常强调渗透着理性意蕴的个人的情感和意志。总体来看,西方从古希腊至近代的美学发展中,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对立分流、相互消长的。象柏拉图、黑格尔等作为传统理性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也同时存在着非理性主义倾向;象德国古典美学这样影响巨大的学派,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同时并存。现代西方美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并非无源之流。自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在理性危机中乘势兴起,以空前的声势和巨大的影响力而成为现当代西方美学的主潮或主导倾向。
二、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流派虽然表现形态和理论重点相互歧异,但存在着如下的基本特征:
第一,在艺术本质论上,把个体感性存在和非理性因素看作美和艺术的本质。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实质上是以人为本位的现代人本主义,它从人出发,把个体感性存在和非理性因素提升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高度,作为世界的本原和美学研究的核心。在人性建构问题上,把主观心灵的直觉、无意识、本能、意志、情感、欲望、信念、潜能、人格等非理性因素视为人性的构成维度和人的本性,否弃人性中的理性因素。在艺术与人的关系上,以人为中心,把个体感性自我和非理性实在视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创造的深层动因。它肯定艺术的本质与个体感性存在的精神本质结构的一致性,把艺术本体与创作主体鉴赏主体的心灵实在和心理功能联系起来,把艺术本质归结为个体自我内心体验的非理性本质,强调艺术的创造和欣赏过程中主体对非理性因素的追寻、探索和深化,寻求人性的复归和自我的解放。柏格森和克罗齐把本能性直觉看作艺术的内在动力,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个体的主观的心理体验,加达默尔则突出了审美理解者作为历史中的独特的个体感性存在。在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美学流派看来,审美和艺术领域充满着生命的活动和主观的创造,主要表现为心灵实体的非理性活动,个体存在的感性特征与审美、艺术活动的感性特征契合。它抛弃了近代美学侧重于研究抽象的理性人类和人性的理性的构成因素的基本倾向,高度重视对个体的感性自我和人性的非理性构成因素的探讨,把审美和艺术同个体主体的心理体验、感觉实在、生命本能和自由本性联系起来,并把个体感性存在和非理性因素加以本体化,作为艺术的本质。
第二、在艺术功能观上,突出审美的非功利主义。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思潮由传统美学所致力于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转向对人本身的研究,由对艺术对象(客体)的研究转向对审美主体的研究,注重审美主体的心理功能和内心体验。这种研究重点又是从普遍性转向个体性,从理性转向非理性,从思辩性转向体验性,割裂了主体与客体的实践性关系,把个体主体的现实存在理解为一种观念性存在,否认感性自我的社会实践基础以及这种社会实践基础对美和艺术的根源性作用,使美和艺术失去客观现实基础而成为个体主体的主观意识和心灵体验的产物,追求审美的绝对自由和超越。因而排斥审美功利性,把主体的非功利态度作为审美的首要条件,把艺术引向与真善相隔离的超验的神秘性道路。如叔本华的“观审”方式确认审美活动中的非理性和非功利性,柏格森认为艺术直觉无外在目的性,克罗齐强调艺术因无目的性而不可能是功利性活动,萨特认为艺术创造需要自由的情感,自由情感就是一种超脱目的和功利的情感,它使作家也超越了自身。这些美学家都把超越功利关系作为艺术自由创造和获得美感享受的基本条件。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把审美和艺术说成是心灵活动的产物,强调审美主体自我体验的自由性能动性,在引入非理性直觉和领悟时把超功利性视为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内在规定性。从西方美学审美无功利关系思想的历史发展来看,托马斯·阿奎那指出审美在本质上与欲念无关,不涉及外在目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舍夫茨别利和哈奇生强调美感不能夹杂占有和功利的欲念,审美活动不计较利害关系。康德提出美与有利或有害无关的命题,首倡审美判断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流派则突出强调了审美无利害关系的思想,使它成为其美学理论的一个根本观点和流派本身的一个重要标识。
第三,在艺术思维方式上,把直觉思维方式作为艺术创造活动的根本思维方式。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把个体感性存在和非理性因素提升到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高度,作为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创造的动力机制。而这种个体感性存在和非理性因素又不能为理性思维所认识和理解,只能以直觉思维方式来加以体验和领悟。它在艺术功能观上突出审美的非功利主义,把艺术活动视为非理性的超功利的主体内省体验活动,强调艺术凭借非理性直觉方式来把握世界的本质。它把美学眼光转向个体感性存在、个体主体的自我意识,把注意力转移到审美经验的研究,从纯粹主观感觉经验出发而忽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主体同审美对象之间关系的认识,由外在观察转向内在直觉,向经验性的艺术心理学方向发展。如叔本华明确肯定直觉在审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柏格森强调审美直觉的神秘性和流动性,克罗齐的艺术直觉论强调艺术活动依靠主体的直观与对象的直接同一,英伽登认为艺术品作为一种纯意向性存在必然通过本质直觉来把握,萨特强调艺术凭借非理性方式透视和把握存在的本质。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强调感觉高于思想,直觉高于逻辑,经验高于规范,贬低理性思维在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意义和功能,抬高直觉思维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在审美直观中依靠内在直接体验或领悟去把握对象的本质和全体,而不需要通过认知方式和逻辑推理,把直觉神秘化,成为脱离理性思维的一种先天能力和思维方式。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以感性自我为本位,以直觉思维为手段,强调个体的生命体验的唯一性、感性经验的创造性和审美观照的领悟性。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对美和艺术的研究,由抽象的美的本质转向实在的审美经验,由客体的对象世界转向主体的内心世界,由普遍的理性人类转向个体的感性自我。它所推崇的个体感性存在(生命冲动、情感体验、强力意志、本能欲望等)已经不是近代美学意义上的那种属于理性本身的一种普遍要求的个人独立、个体自由和个性解放,而是获得了超越普遍理性的规范的具有独立自足的意义和价值的感性自我,具有独特性、偶然性和不可重复性。它因脱离理性认识而成为绝对的超验自我,脱离历史群体而成为孤独的个体自我,脱离社会实践而成为精神的观念自我,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唯我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
现代西方美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流向是与理性主义流向相对而存在的,两者之间正在形成互渗互补、交汇合流的发展趋向。从传统特点来看,西方美学发展史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两种倾向是对立统一的。柏拉图在《斐德诺篇》中把灵魂比喻为车手驾御一对飞马,车手喻指理智,两匹马分喻意志和情欲。这个比喻生动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和制约的关系。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则以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来指代艺术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日神精神包蕴着理智和理想选择,通过对梦幻世界美丽外表的超然静观寻求恬静乐趣以摆脱生存变幻的痛苦。酒神精神象征着本能放纵与情感激荡,主张在狂醉世界的纵情欢乐中个体与自然合为一体。前者在理性静观中保持节制与和谐,不去追求真相和本质,后者在情感狂热中表现出强烈生命力而与本质相沟通;前者是个体自我肯定性冲动,迷恋瞬间而超然无为,后者是个体自我否定性冲动,放荡不羁而向往永恒。两者相激相荡,相反相成,形成了审美和艺术活动中的动态张力。再从深层目的来看,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美学流派和文学流派,在反理性的背后深藏着深层的理性目的。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作为理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旨归就是对极端理性主义的反拨矫枉和补偏救弊,企图通过非理性主义途径达到救正理性的本来目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在理性精心设计下的反理性,其表现手段和深层目的在悖逆形式中相反相成。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流派在反理性的呼号中包含着理性的清醒与自觉。海德格尔曾深刻地指出:“因为不论谁,当他想把哲学标榜为非理性时,他总是用理性作为衡量的尺度,而且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再次承认了某种是理性的东西”③。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学流派反理性倾向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反思主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即关于在现代异化和荒诞环境下个体自我的生存目的和生存意义的哲理性探索,这种探索并没有脱离人类的理性认识规律。从认识论意义和创作构思来看,西方现代派作家是从理性的内视点来驾驭非理性表现形式的。加缪就说过:“为了使一种荒诞的作品成为可能,以其最清醒的形式出现的思想必须参与其事”;“荒诞,就是确认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④。以理性的自觉意识构造荒诞,外在的非理性形式与潜在的理性目的保持着同一性的审美向度。
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美学(现代人本主义美学)思潮(或流向)与理性主义美学(科学主义美学)思潮(或流向)在互渗互补中正朝着综合化趋势发展,成为一种新动向。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美学流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英伽登指出审美价值判断活动既包括意向性特点和直觉性情感反应,也包含一定的理性认识因素和“理性把握”的特点,其美学思想又带有理性主义色彩;杜夫海纳承认审美经验中包含理解等认识性因素和审美对象中包含有理智性再现意义,甚至认为审美情感具有认识的特征和理智的功能,其美学理论也有一定的理性主义倾向。加达默尔的审美理解具有领悟形式和非理性特点,但也没有完全排除理性认识因素。他指出美和艺术与真理保持着内在联系,强调审美理解就是达到真理性认识,未彻底否定理性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则试图将理性的普遍必然性与非理性的个体自由性统一起来。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理论的证明,杜夫海纳对审美经验的分析,都借助于经验实证方法,而存在主义美学、解释学美学都重视语言分析方法。
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美学思潮以自然主义美学、实用主义美学、语义学美学、分析美学、形式主义美学、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符号学美学、结构主义美学、解构主义美学、接受美学为代表,它以科学主义为支持,以实证主义经验为方法,是在承认科学理性至上地位的前提下力图对审美和艺术领域的精神现象作出科学的精确分析和实证阐释。这一美学思潮直接运用现代数理逻辑和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新工具来进行理论建构和解释文艺现象。现代美学、现代文艺与现代科技在形式层面紧密结合,使美学和文艺研究“科学化”,即信息化、量化、形式化、数理化、符号化、模式化、精微化,标举形式、符号、结构、系统、范式、模型、话语、操作等新概念及其一套技术术语(概念秩序、符号系统、结构方法、形式模型、语义分析等)。它以技术为中介,以形式为手段,大搞形式崇拜,见物不见人,把形式主义推演到极端。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美学把概念符号、形式技巧、结构方法、技术操作问题放在首位,并以此代替真善美之类的传统美学概念,把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归结为形式主义本体问题(如某种符号体系),对美学、艺术同科学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的探求,成为它的一大特色。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美学流派一些代表人物带有不同程度的非理性主义趋向。如桑塔亚那突出审美经验与生物本能实现的关系,自然地把理性解释为人的生物性“本能”;杜威把“经验”视为主体与客体、理性与情感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贝尔和弗莱把重点放在非理性非功利的审美情感上;维特根斯坦提出“不要思而要观”的名言,力图用理性直观跳出逻辑思维的框架;苏珊·朗格强调情感生命的抽象形态和审美直觉的理性特征;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研究把语言结构和人类早期的无意识结构联系起来。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美学流向和非理性主义美学流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代整体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辩证综合的发展趋势,鲜明昭示了人类在克服自身对人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走向全面把握的重要进展。
注释:
①见蒋孔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136页。
②转引自杨寿堪编译《黑格尔之谜》,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6页。
③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中译文见《现代外国哲学》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见《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86、389页。
标签:非理性主义论文; 美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自我认识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