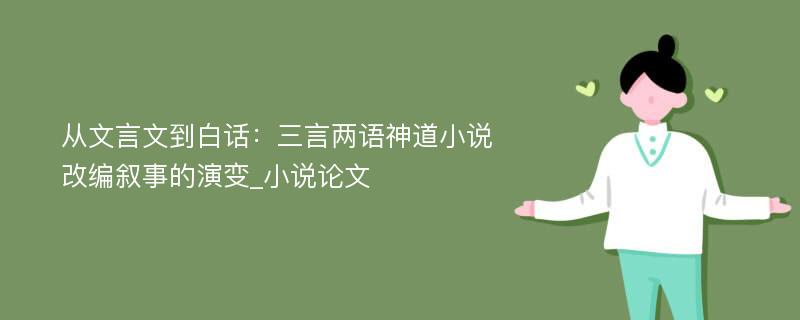
从文言到白话:古典叙事的演变——论“三言”对神道小说的改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道论文,文言论文,白话论文,古典论文,三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言”是冯梦龙在搜集整理宋元以来话本的基础上,编辑成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冯梦龙虽然对大部分作品从题目到内容都作过一定的改动,但这种改动一般不伤及小说的本来面目,因此它们仍保留着早期话本的特征。
话本小说伴随着说话艺术的发展而大量产生,为了满足听众的需要,说话人往往直接从现实生活中选取鲜活的素材进行创作。所以“三言”中大多数作品都以宋、元、明三代社会上的中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市民生活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与构成作品主体的市民题材相反,在“三言”的一百二十篇小说中,关于神仙道化内容的总共只有十篇(属于佛教题材的不算在内),而且多数由说话人从前代文言志怪小说改编而成。这类作品由于要受文言小说原有内容的束缚,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相对较差,长期以来不大受研究者的重视。但是从中国小说发展的整体历史来看,也许正是这类和现实生活距离较远,主要由前代文言小说改编而成的作品,更能体现出职业化叙事者——说话人的出现,对白话小说创作意图和叙事方式的影响,以及白话和文言两种小说形式在处理同一题材的故事时,各自侧重点的不同。
从故事的内容看,“三言”中的十篇神仙道化小说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1)度人成仙故事:《张道陵七试赵升》、《杜子春三入长安》、《李道人独步云门》、《福禄寿三星度世》。(2)神仙生活故事:《陈希夷四辞朝命》、《张古老种瓜娶文女》。(3)神仙除妖故事:《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旌阳宫铁树镇妖》、《一窟鬼癞道人除怪》。(4)神佛斗法故事:《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其中成仙故事和除妖故事所占比例较大,神佛斗法的故事只有一篇。这些小说的本事除《福禄寿三星度世》一篇目前尚不确切、《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出自戏剧《万仙录》外,其余八篇都见于早期的文言小说。本文拟以这八篇为例,通过它们和文言小说的比较,来分析这两类小说形式在叙事上的差别,使我们对这八篇小说的叙事特点,以及白话小说改编同题材文言小说的一般规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进而探寻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
细察这八篇小说,可以看出说话人对它们的改编总体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基本保留了原来故事的内容,并作过一定的改写和补充;另一种情况是,说话人从不同文献中摘取有关材料,重新加以组织安排,构成故事,有的甚至采用了“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的办法。下面将分别讨论这两种类型的具体情形,并及其在小说叙事中造成的效果。
一
在前面所提到的八篇被改编小说中,属于第一种类型的作品有五篇,即:《张道陵七试赵升》、《张古老种瓜娶文女》、《一窟鬼癞道人除怪》、《杜子春三入长安》、《李道人独步云门》。考这几篇小说的本事,《张道陵七试赵升》事出《神仙传》;《张古老种瓜娶文女》本事于《仙传拾遗》和《孝德传》中均有近似的记载,但以《续玄怪录》所收为最详,白话小说的结构基本来源于此;《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原系宋元旧篇,冯梦龙对之稍有改动,其本事最早见于《鬼董狐·樊生》;《杜子春三入长安》故事在《酉阳杂俎续集》(卷四)和《传奇》中都有记载,唯人名不相符,今本《太平广记》(卷十六)收自《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一篇,所记始与白话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相一致;《李道人独步云门》唯见于《太平广记·李清》,内容与白话小说无太大出入。这些作品所讲的故事在文言小说中都有比较完整的记载,所以当它们被改编为话本时,在叙事上就表现出了许多共同的特点。试分述之如下:
首先,由于有文言小说的叙事作基础,说话人基本上沿用了原有故事的时间顺序,但又不愿受文言小说叙事方式的束缚,大大放缓了小说的叙述速度。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言志怪小说向来被视为“史之余”,其叙事必然要受到传统经史传记的影响。经史叙事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义理和揭示史实,加之它的作者和读者一般都受过一定经史子学的薰陶,因而乐于接受富于暗示性的叙事方式,即使刻画人物也多选取最能传神的言话和举动,往往点到为止,其余则尽可能交代得简单明了。[①]唐人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论及《春秋》、《左传》时,就极力称赞其叙事的特点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意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向外。”志怪小说受这种特点的影响,其叙事基本上都比较简单,叙述的速度也相应的较快。这类小说被改成话本以后,职业化叙事者为了增强叙事的趣味性,使故事变得耐听,就得努力放缓叙述的速度。放缓叙述速度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为原故事添加新的情节,另一种是运用人物语言。
在大多数情况下,故事情节的添加可以增加叙事的波澜,强化小说结构的张力。但事件比例的变化也往往会改变作品原有的主题。《张道陵七试赵升》本来是根据葛洪《神仙传·张道陵》改编的,话本在正话一开始,首先就叙述张道陵出生前,他母亲所做的一场异梦,接着又叙述他和弟子王长在龙虎山的奇遇。这两个情节都是《神仙传》中所没有的。从说话的角度讲,加入这两个情节可以使叙事从一开始就显得离奇神秘,有吸引力。但从改编的角度讲,这类异梦和奇遇又使成仙对张道陵来说变为命中注定的事情,从而冲淡了文言小说原来所宣扬的依靠潜修才能升仙的主题。此外,话本还在原来故事的基础上增添了张天师制伏白虎神和消灭八部鬼帅的故事。通过增添这些情节,话本的叙述速度明显放慢了。同样,在《杜子春三入长安》中,叙事者让杜子春第一次因睡过头而爽约,第二次因吃酒欠钱而被酒家厮闹。这些情节在原文言小说《续玄怪录·杜子春》中都没有,显然是说话人为了放缓叙事速度,给叙事增加波澜而添上去的。同样的例子在这类小说中还可以找到许多,兹不赘述。
在组织故事的时候,话本的叙事者用来放缓叙述速度,使故事耐听的另一种方法是广泛应用直接语气。文言小说一般较少使用直接语气的人物语言,即便有也很简略。但到了话本中,叙事者模拟人物口气的对话已经成为叙事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点通过《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续玄怪录》在记述张古老的故事时,有他和媒人之间的几句简单对话,但到了白话小说中,不仅原来的对话内容增多了,还加入了两个媒人之间的对话。另外《杜子春三入长安》在叙述杜子春第一次得到老者赐钱的消息后,有一段说话人模拟他的心理活动的对话,亦可算作一例。人物语言的增加缩短了叙事接受者与话本人物间的心理距离,使其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同时也打破了情节的直线性和平面性,使事件的意义相对地被放大。
其次,在话本中,说话人为了使所讲的故事真实可信,对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背景性因素比文言小说的叙事者更加重视。“七试赵升”的故事在《神仙传》中只提到第七次的地点是在“云台绝岩之上”。改编成话本以后,差不多对每次相试的时间和地点都作了具体交代。如叙述赵升第一次投师的时间是:“来年七月初七日,当正午”;第二次相试是在田边的一间“小小茅屋”,时间是一个“月明如昼”的晚上;第三、四两次相试的时间是秋天,地点在“后山”等等。其他几篇小说中对背景因素的强调虽然不象“七试赵升”这样突出,但和同一题材的文言小说相比,仍有很大进步。例如,《李道人独步云门》的本事据《太平广记》记载是出于《集异记》,《集异记》在《李清传》的开头只说:“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对故事的发生时间并未作说明。但改编成话本后,其开头就变为:“话说昔日隋文帝开皇初年,有个富翁,姓李名清,家住青州城里,世代开染坊为业。”不但有了时间,而且人物活动的地点也更确定。确定的背景能帮助故事接受者建立清晰的时空概念,也有利于展开叙事,渲染气氛,加深叙事接受者对故事的理解和感受。
第三,尽管说话人把原来的文言小说改编成话本时,还不能完全摆脱原有主题的束缚,但由于叙事者在叙事中不断插入对事件进行评论,这些评论或是从世俗经验角度所作的道德判断,或是纯粹为了增强叙事的趣味性而说的俏皮话。总之,它们都可能冲淡文言小说原有的主题。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能起到这种作用的主要还是小说的篇尾诗。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的篇尾诗:“一心办道绝凡尘,众魅如何敢触人?邪正尽从心剖判,西山鬼窟早翻身。”这就使一个原本专讲吴洪遇鬼经历的恐怖故事,有了道德说教的味道。而《张古老种瓜娶文女》篇尾诗所谓的“一别长兴二十年,锄瓜隐迹暂居廛。因嗟世上凡夫眼,谁识尘中未遇仙。授职义方封土地,乘鸾文女得升天。”告诉人们的也只是人不可貌相这样一条世俗的经验。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话本的叙事者在努力摆脱文言小说主题的束缚,使其尽可能地适合宋元以来新兴市民阶层的人生经验和欣赏口味,从而为故事赋予了新的意义。
二
如果说在前一种情形中,改编者(说话人)还有点被动地服从于文言小说原有结构的话,那么在后一种情形中,他们的主动性就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三言”所改编的神道小说属于这种类型的是:《陈希夷四辞朝命》、《陈从善梅岭失浑家》和《旌阳宫铁树镇妖》。这三篇作品的本事虽然也见录于文言小说,但是构成同一话本的不同事件往往零散地收录在不同的文言著作中,而且这些事件之间多数原本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有的甚至还人不符其事。因此在这几篇小说中,说话人创作的因素很大。他们充分地发挥了想象,运用虚构的办法把许多零散的事件联缀起来,大大地突出了事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使其有了新的统一主题。很明显,叙事者不象在前一种情况中那样过份受原材料的限制,其主动性在组织故事的方法上得到了充分表现。从对故事的组织形式看,这三篇小说分别体现了改编者处理原有材料的三种不同方法,这三种方法基本上也可以代表后来的小说作者处理已有题材的一般规律。
1.在文言小说中,《陈希夷四辞朝命》的故事分别见于宋人的笔记如《河南邵氏闻见录·前录》(卷七)、《玉壶清话》(卷八)、《东轩笔录》(卷一)、《渑水燕谈录》(卷四)、《青琐高议》前集)和《宋史·隐逸传》、《历代仙史》(卷四)等书中。话本叙事者围绕着“四辞朝命”这一主要线索,把有关道士陈抟的小故事从各书中摘取出来,进行统一编排,构成了全书的叙事。因此,改编前后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保持着统一,没有出现大的改动。另外除了个别过渡之处有所增损外,作者也没有太多地虚构新的情节。
就改编后的小说叙事来看,这篇话本的特点之一是说话人对故事的控制能力较强。从篇首的入话诗开始,叙事者就向听众交代了主题,后边正话的叙事也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个主题的思想。当然,职业化叙事者对有趣故事的青睐,在这篇小说中同样被证实。在叙述“四辞朝命”的主要故事时,叙事者插入叙述了陈抟能预知未来和辟谷服气等特异功能,就为整个叙事增色不少。
第二,和“三言”中的大多数作品一样,这篇小说也基本按照时间从先到后的顺序展开叙事,只有中间叙述完陈桥驿赵太祖登基故事后,叙事者闪回倒叙了唐末年间,陈抟遇见杜太后携太祖、太宗避乱,和后来在长安酒肆重遇太祖、太宗、赵普二事。这种倒序在话本叙事中的功能是交代因果,为陈希夷第二次辞朝命的起因作解释。这也是后期话本的叙事者控制故事能力增强的一种表现。
最后,这篇话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人在叙事过程中虽然很少加入评论,但由于话本篇尾诗句与入话诗意思一致,首尾呼应,同样很好地揭示了主题,显示了叙事者对小说结构功能的发现和重视。
2.《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是宋元旧篇,最早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它处理材料的方法和《陈希夷四辞朝命》恰恰相反。这篇小说基本上可以说是创作,但故事的基本框架则是文言笔记提供的。在现存文献中,《广东通志》卷三百三十四之《杂录》对这一故事只有不到一百二十字的记载,叙述十分简略。原文如下:
白猿洞在城北八十里梅岭下,洞广丈余,深百步许。昔有白猿居其间。邑中沙角巡检陈辛,开封陈留人,偕妻之任,过梅岭,投宿店中,白猿乃变为人,摄其妻归洞中,俾执奴隶之役。后辛以考满,过失妻之所,遇紫阳真人于红莲寺,以情恳告,真人斩白猿,夫妻遂获同归焉。
改编成话本后,叙事者努力控制住了叙述速度,使故事发生的两条线索(陈辛和陈妻各代表着一条线索)在时间的序列中交替展现。这两条线索最早由叙事者借角色人物之一紫阳真人的口预示给叙事接受者,在中间,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又多次通过叙事转移将其分别展开。叙事转移常用的语言标志是“且说……”和“不说……且说……”等句式。故事到了结尾时候,紫阳真人的再次出现使两条线索的叙事又重新统一到陈辛夫妻团圆同归这一条线上,完成了话本的叙事。这篇小说和其他大多数作品一样,人物语言的大量运用和细节性事件的补充,再次有效地延缓了叙述速度,例如在陈辛夫妇南投的路上,罗童的捣鬼,陈妻如春的不耐烦等,都是很好的证据。
预言的反复运用是这篇小说的主要特点。预言为小说叙事设置了悬念,能使故事接受者产生期待心理,引起内心的焦急感,这样很有利于叙事者控制叙事接受者的注意力。另外,小说在叙述陈辛失妻、寻妻、得妻的故事时,还插入叙述了他平定强盗镇山虎的事。从小说故事的构成讲,它似乎与主要故事没有太大联系,并且还造成了结构上的松散。但从职业化叙事的效果看,这样做既避免了因叙事中断所可能产生的尴尬,又把公布故事结局的时间向后推迟,大大地吊足了听众的味口。同时,在整个叙事中,叙述者并没有交代神魔斗法的过程,而且神仙的出现也没有改变人物命运的不辛,他们的作用似乎全在于为叙事增加波澜,使其显得不平凡。因此有人把这篇话本称作愚行小说[②],道理并不是很充足。
3.《旌阳宫铁树镇妖》在对材料的运用上与以上两篇小说又有所不同。尽管它的情节主要也来源于文言小说和历史传记,如《晋书·吴猛传》、《酉阳杂俎》、《朝野佥载》(卷三)、《十二真君传》、《集仙录》、《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和《历代仙史》等书中。但在这些笔记和史传中,有的情节是事非其人所有的。改编成话本后,说话人充分运用移花接木的方法将其安排在主要人物身上,突出了叙述对象。这样改编后的人物和事件都有相应的变化,和原材料中的记载有较大出入。如根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以炭化美人的本来是道士吴猛,所试对象为吴氏的弟子许逊。话本则将其改为许逊试其弟子陈勋等人的故事。这篇小说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较多,为了将纷繁的事件统一起来,说话人一开始先叙述了太清仙境中群仙们的一席对话,借孝悌王之口预言了故事的基本线索,形成了全篇叙事的总纲。小说在接下来的叙述中,除了运用上述几种书中的有关事件来组成主要故事外,又吸收了大量后来的传说(如关于许多地名的来源),将其镶插在许逊驱妖镇妖的过程中,丰富了叙事的内容。这篇小说的情节离奇曲折,叙事往往出人意料,主要就是靠了事件的叠积。但是同时,对于传统故事的过份偏爱又使叙事者常常表现出对所叙事件的失控,如中间关于小姑潭老龙出处的叙述便是一例。这样就使话本后半部分的叙事显得比较混乱。这也许能代表职业化叙事的一个普遍不足。总的说来,这篇小说的成就不高,但由于它代表着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进行改编的一种方法,因此在文学史上仍然值得重视。
三
关于改编后引起话本小说叙事变化的原因,主要还得从话本的职业化特点和冯梦龙的编辑态度入手分析。话本小说是民间说话艺术发展的产物,而说话从一开始起就是一种娱乐形式,这决定了这种从唐宋以来形成的文学形式在其本质上不具有“言志”或“载道”的严肃性。为了谋生,说话人首先必须保证自己所讲的故事能够吸引听众。故事性强因之是话本小说的首要特征。在早期的话本中,叙事者对事件本身趣味的重视有时甚至超过了所叙事件的思想价值。如《一窟鬼癞道人除怪》,主要就是通过讲述吴洪遇鬼的一连串离奇事件来构成故事,其中并不寓含任何说教意义。这类作品无论其文字水平和道德性质如何,其首要目的是满足娱乐。它必须把叙事接受者引到除此之外便不能获得的经验里,使其在一个决不会与现实世界对等的虚构世界中“历险”。因此判断这些小说的并不在于其思想价值,而应是它的叙事艺术。
其次,说话是一种口头艺术,故事的叙述者(说话人)和接受者(听众)之间通常构成一种直接的交流关系。声音语言一般不象文字符号那样具有稳定性和含蓄性,经得起反复分析和体味。因此它要求叙事者要尽量把故事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讲得清楚、明白,减去不必要的插叙和倒装,以免造成听众理解上的混乱。另外从接受者的角度讲,说话的主要听众是普通市民,其文化水平一般不会太高,传统的历史传记和文言小说通常采用的一些概括性极强的叙事方式,不大适合于这些“里巷之耳”。这样,按照清楚的时间顺序和因果联系所展开的叙事就受到了肯定。所以,“三言”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展开叙述,只有极少数如《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叙事是从中间开始的。
第三,在说话艺术中,说话人和听众之间一般是面对面,听众总是希望叙事者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评价一切,所以在话本小说中就很少采用人物角度进行叙述。这同时造成了话本小说中叙事者不断插入评论的特点。叙事者的评论是引导听众参与理解故事的一个重要手段,他的评论必然力求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引起听众共鸣的主要方法是把道理讲得通俗易懂,浅显明白,并使之和普通人的生活产生联系。有时候,说话人还模拟听众的口吻进行提问,然后作出回答,这同样是唤起听众注意的手段,并可以对事件的因果关系作解释。在许多从文言小说改编成的话本中,这样的评论和提示往往可以消除文言小说纯叙事的暗示性在说话中可能引起的意义上的模糊。
第四,话本的叙事受职业化特点影响,为了吸引听众,情节之间的铺垫(即催化)相应增多。细节描写的增多对作品的意义不足以产生大的影响,但是却可以使作品所反映的世界具体化,也使这个世界血肉丰满地呈现出来,增强它的“真实”性。可是同时,与之相矛盾的是,叙事者在控制故事结构的时候,为了能使情节紧凑和主题明确,避免分散听众的注意,在描写环境(有时甚至描写人物)时又常常使用程式化的诗句与套语,而不作人物角度式的报道。这样往往有利于叙事集中地展开,但也造成了早期小说程式化和简单化的缺陷,容易引起人物和环境、事件之间的失衡,使其在艺术上显得单薄、粗糙。
话本小说受职业化影响的特点如上所述,冯梦龙在编辑“三言”时又对其做了一定的补充和发展。虽然职业化叙事者对通俗故事的偏爱出于谋生需要,冯梦龙看重的是其社会价值,但他们对作品故事性的强调则是一致的。冯氏认为:“大抵唐人迭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迭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③]正是由于冯梦龙认为“谐于里耳”的通俗小说比正统经史有着更深广的社会教育意义,所以他在编辑“三言”的时候认为只要“情真”、“理真”,完全可以“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④]这样就彻底摆脱了早期文言小说叙事要讲求信实的观念,对小说的虚构性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基于此,冯梦龙在编辑“三言”时,为了达到他借小说以资教化的目的,对有些宋元旧篇从内容上还作过不同程度的改写。
可见,随着话本小说的出现,不论是创作者还是编辑者,他们的主观态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早期文言小说的作者相比,话本的作者对故事的爱好已经取代了文言小说作者借作品来“补正史之不足”和“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兴趣。[⑤]就“三言”中的十篇神仙道化小说来看,作品的主要目的已不再是宣扬神仙的法力和出世思想,而是充满了各种世俗的社会经验。《吕洞宾飞剑斩黄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通过吕洞宾因少年气盛而与黄龙禅师斗法失败后,悔过潜修终于成仙的故事,所寓含的意义似乎与神佛思想本身都无关系。故事中,神佛在人们心目中的严肃性全然丧失,他们跟普通人具有相似的情感世界。这同早期的文言志怪小说是大相径庭的。
总而言之,话本小说的创作既有其职业化要求,冯梦龙编辑“三言”时又在其中注入了自己的主观意识。这都使“三言”中的神仙道化小说和同题材的文言小说相比,在对待故事的观念、叙事的目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小说史上,白话和文言的差别并不仅仅是语言形式上的问题,它表明了小说观念和小说形态的一次根本转变。虽然前者在内容上对后者有一定的借鉴,但不论从叙事的方式还是目的来看,二者之间的差别都是很明显的。严格说来,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从一开始就走着各自的路子,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白话小说努力地摆脱了文言小说叙事方式的束缚,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征。这就为它日后反映更趋复杂的社会生活奠定了基础。同时职业化叙事者的出现也使白话小说在题材选取、审美趣味和叙事手法上都趋向平民化和通俗化,从而拥有了更多的听众和读者。随着读者群的扩大,话本小说也逐渐由勾栏瓦舍中的口头演讲进入文人的案头阅读,使其在结构上更加定型,在艺术上也更加完整细腻,为小说创作下一个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经过宋元以来说话艺人和明代通俗文学家们的长期努力,白话小说的创作能在明末清初出现繁荣,就不是偶然的事了。
注释:
①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
②P·韩南《中国白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③《古今小说序》。
④《警世通言序》。
⑤干宝《搜神记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