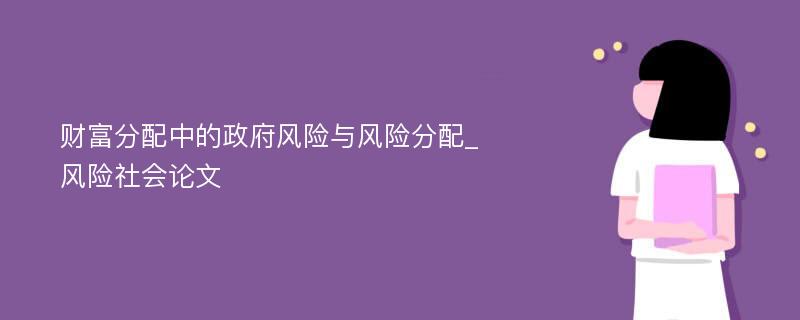
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中的政府风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论文,风险论文,财富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问题。财富分配的必要性在于任何财富都是稀缺的,而任何社会的分配过程,均伴随着种种围绕分配的社会冲突。
与财富不同,风险则是因为太多而产生了分配问题。预防风险、承担风险、化解风险都需要消耗、投入一定的社会财富。如果一个社会的风险太少,为承担风险而耗费的财富可以忽略不计,那么,也不会有风险分配问题存在。也就是说,风险分配问题,归根到底仍是财富分配问题。
不论任何社会,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都有对抗与冲突。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存在对抗与冲突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社会形态的不同,是对抗与冲突方式不同的原因之一。原始社会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均与财富相关。
现代社会风险的存在,已经成了每个人都能够直接感受到的现象,已不再是少数几个“专家学者”的不祥的鸦鸣。风险的分配已经不再只是哪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也同时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国际问题、外交问题。不管人们对贝克的风险社会有多少疑问,风险分配问题都已成为一个南北吵闹不休的全球性问题和引起种种冲突与不安定的政治问题。
二、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产生的政府风险
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不论是不是由政府这只手在分配,其所产生的种种后果皆与政府命运相关,围绕分配产生的冲突都可能转化为政府的风险。政府风险也同样取决于社会风险。社会有多大风险,政府也同样会有多大风险,两者的正相关是没有疑问的。同时,社会风险的内容、形式、特点、分配机制与结果,与政府风险的性质与特点也同样息息相关。
(一)传统社会或农业时代和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风险与工业化社会风险,呈现如下不同特点
1.风险的主要内容已由贫困、短缺转化为安全与健康。从原始社会直至20世纪前半叶二战后初期,整个人类的根本问题就是物质财富的短缺。贝克的“短缺专制”极其精准地刻画了短缺对人类社会的困扰,而造成短缺的首要因素是自然规律。除了技术原因造成的短缺与贫困外,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则会造成人为的“短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即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农民也难逃谷贱伤农的厄运。事情到了20世纪中叶,社会发生了人类诞生以来的根本性变化。实施工业化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解决了狭义上的“面包”问题。然而,在这些国家还没来得及充分品味富足带来的满足时,种种新的不亚于“贫困”威胁的问题接踵而至,关于人类“末日”来临的种种预言越来越多,威胁人类安全的因素隐藏在人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更不用说成为人类整体生存问题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等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手段飞速进步,同时也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2.风险的承担主体已由阶级转化为个人和全人类。工业化过程,也是社会急剧分化的过程,与社会分化急剧进行相伴随的,则是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工人阶级在工业化过程中作为承担贫困风险的主体,是作为一个阶级而不是个人来承担贫困风险的。作为个人的工人,可以通过奋斗摆脱贫困风险,而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能摆脱承担社会贫困风险的命运。而工业化过程之前的农业时代,贫困风险的承担者,无论在任何国度,都是农民阶级。当工业化过程结束,工业社会出现之后,社会风险的承担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使富人和发达国家,也不能躲进没有风险的世外桃源,“飞去来器效应”使他们也要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3.围绕风险展开的诉求由平等转变为安全。“阶级社会的驱动力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饿!另一面,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表达为:我害怕。”“在阶级社会到风险社会的转变中,社群性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概括地说,这两种类型的现代社会表达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阶级社会在它的发展动力上(在它从“机会均等”到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各种变体这些不同的表述中)仍旧与平等理念相联系。风险社会就不是这样,它通常的对应方案——这既是它的基础又是它的动力——是安全。‘不平等的’价值体系被‘不安全’的社会价值体系所取代。”贝克认为,现代的工人政治与工会运动正日益成为被未来腐蚀的既得利益的保护者,作为未来领导者的角色,已被巨大的已经争取的利益削弱。工人阶级已经由个别的贵族化演变为整体贵族化。因而,平等的诉求已经被安全的要求取代,财富分配的要求已经被风险分配的要求取代,这也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根本性转折。
(二)由于以财富分配为主题的阶级社会与以风险分配为主题的风险社会的社会风险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由此产生的政府风险也有了根本的变化
1.政治事务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即风险性显著增大。短缺专制、贫困风险主导下的政府,由于社会结构简单,社会运作中的不确定性极少,因而政府要应对的风险其实可测性相当大。同时,由于传统社会的相对静止性和社会政治现象的重复性,政府对可能遭遇的风险可以有比较准确的预测。而进入工业社会后,甚至在工业化过程中,政府所要处理的政治事务后果的不确定性比过去大得多。现代的民意调查技术、信息技术和计算技术,对变化莫测的社会几乎无能为力。政府无法从一个阶级的生存状况去判定其政治态度。“政党不能再指望‘固定选民’,而必须运用所有手段去向选民献殷勤”,德国的摇摆选民已从1963年的10%增长到今天的20%~40%之间。20世纪后期的伊朗革命和“苏东波”,并不是政府财政危机的产物,而是在社会经济十分正常甚至是繁荣的情况下的不速之客。
2.政府行为受到越来越严厉的制约与监督,却要为自己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负责。社会设置政府、建立组织的本质,就是给相关的机构或职位设定责任与权力,设定责任与权力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设定责任与权力的依据则是政府要处理的各种事务。如今,人们对政府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限制政府权力的要求也接踵而至。这不论在“自由世界”还是第三世界,都是相当普遍的呼声。这种世界性的需求要求政府一方面扩大责任,一方面收缩权力的潮流,在政治制度极其不同的国度同时出现,说明这并非是政府权力普遍过大、政府责任普遍太小所导致,而是当今世界急速变化,全球沟通加深加宽的产物。但是,这种政府责任与权力反向变化的趋势,必然是政府风险的快速增长。正如对一辆车子,一方面给它加载重量,一方面又在减小它的马力和承重能力,因而导致它的瘫痪的可能性也在同步增大。
3.政府将面临要么失败、要么走向极权化的两难选择。政府权力与责任的反向发展趋势如果失去使权责趋向平衡机制的制约,势必将出现政府失败的风险。而政府要避免失败的风险,极权化将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极权化的政府意味着政府将面临丧失合法性的风险。这种使政府无论向任何方面变化都难免风险加重后果的两难选择,是极其现实的问题。在种种风险已经隐隐触手可及的未来,政治上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政府,其次才是政治体制上可能的极权化变异。如何使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应对社会风险,又不使可能的极权政体成为现实,是需要社会和政府共同破解的难题。
三、我国政府面对的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问题及其产生的风险
在西方高度发达的、富裕的福利国家,虽然“每天的面包”不再是首位问题,但面包(财富)分配的问题仍然存在。虽然凭借财富、知识、权力不能摆脱的人类共有风险越来越多,但是,还是有大量的风险可以运用财富、知识、权力去摆脱。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仍然纠缠在一起,这在西方发达国家如此,在我国更是如此。如果说,西方国家仍然有发展与安全的两难选择,仍然面临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带来的双重冲突,那么,我国在这两者之间的抉择更为艰难,更为复杂,我国政府面临的不只是两难选择,而是多难选择。而选择的艰难,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
我国过去要解决的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实质上只是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改革与发展两者并非对立而是一致的。对立与冲突只是发生在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现在这个“老三角”问题虽然不如过去严重,但仍然存在。如果说,我们过去为解决发展问题,遭遇到的只是改革与改革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这两者之间的冲突,那么现在,又有了一个发展与社会安全的冲突掺和进来。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改变一个民族落后就要挨打的规律,改变的只是挨打方式的不同。发展仍然是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的“第一要务”。然而,过去发展要忌讳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面包如何分配的问题,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还没有成为发展需要考量的一个结果参数。而现在,安全的发展不只是我国遭遇到的国际社会的压力,同时也是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在安全发展问题上,消费者与厂商、地方与中央四者之间将会展开错综复杂的较量。
过去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效率与平等的关系如何平衡。而改革与稳定的本质则是财富分配问题即平等问题。过去要改革的是平等、平均的财富分配倾向,现在要改革的则是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弊病。
中国政府的改革风险虽然已经大大减小,但由于社会安全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突出,这就使我国政府面临着极其复杂的风险分配问题以及由风险分配引起的社会冲突与危机。谁为风险埋单以及如何埋单,已经不只是一个经济发展会不会受到影响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稳定会不会受到影响的问题,中国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如何摆平财富分配、风险分配和经济发展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高风险问题。同时,由于中国的“我饿”即贫困风险仍在困扰相当一部分人口,因而风险分配是一个远比西方社会敏感而又严重的问题。相当多的人会因为对风险的承担由已经脱贫而重新返贫,这样,如果双重的分配不公即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不公一齐压在他们头上,其后果之严重性可想而知。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即政府之命运,就取决于政府如何处理财富分配、风险分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防范、化解由社会财富分配、风险分配引发的政府风险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