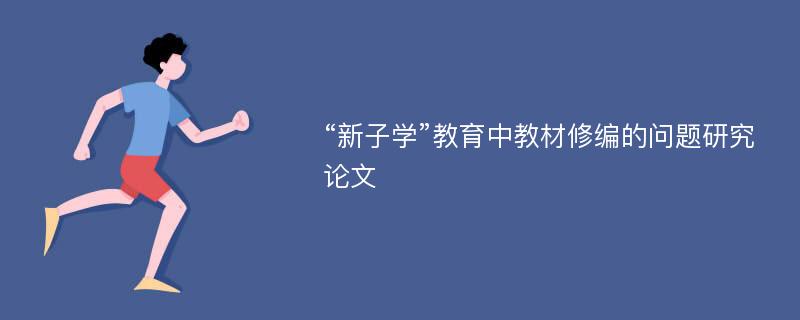
“新子学”教育中教材修编的问题研究
陈祥龙1,陈祥凤2
(1.曲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2.青岛工学院 建筑工程学院,山东 青岛 266300)
[摘要] “新子学”相关理念的传播离不开教育活动的参与。经历了近百年的文化断裂,传统经典需要以崭新的面貌再现。传统儒家教材注重经典性,兼具现代课程与教材的双重属性,表现为以教材定课程、以课程定学程、以教师定教材、以考法定教法等特点。现代教材则在学科规划下编写,重视学习者的认知特点,表现为以学科范畴规划教材、以认知规律编纂教材、以课程标准教授教材等特点,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教材经过现代学科的规划改变了儒家经典教材的既有形态。儒家教材的沿革过程是诸子学说在传统教育中沿革的缩影,对其特点进行梳理有助于探索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新子学”教材。
[关键词] 新子学;儒家;教材;课程;四书五经
在传统教育中经与子相对应,学校教育以经学为主体,以史、子、集为辅翼。近代以降,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学以强势的姿态进入我国教育领域,先秦原典开始以西方学科范式重新规划。在新的学科体制的压仄之下,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传统教本开始以学科知识的形态融入现代教材。传统教本与现代教材在编纂逻辑和教育过程大相径庭,其差异性反映了原典教育的独特之处。“新子学”的提出符合了中西文化近代交融的背景,对于重新构建原典教育体系意义重大。在“新子学”理念下,观照传统教本与现代教材的异同,研究其利弊得失,对于构建全新的原典传承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一、兼具现代课程与教材属性的儒家原典教本
从三代“王官学”时代的“六艺”教育到汉代以后的经学教育,我国传统教育实现了第一次重要转变。“六艺”教育时期,典籍著于简帛,藏之秘府,官守学业,官有学而民无学。孔子开私学,删述“六经”,实现了从“六艺”教学到“六经”教学的转变,开启了我国教育的新篇章。汉武以后,儒术独尊,开太学以养士,五经博士的设立使得经学教育体系初具规模。宋代以后,四书学兴起,儒家“十三经”的教材体系形成,以经学为主干,以史、子、集为辅翼的经学课程体系开始完善。在教法上,传统教材针对童子与成人形成了经学记诵和义理阐释的两级学习模式,塑造了“以考促学”的教育形态。分析传统教本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2.对生物多样性和特异性的认识,以及对基因重组作为生物变异主要来源的认识,为知识的灵活应用奠定了基础。
在描述界线时,应将具有代表性特征的走势方向、长度以及经过的标志性地物、地势、地貌等自然要素和人工要素均进行清晰、完整的描述,且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整体要做到对界线的描述完整、准确、简明、扼要。
(一)以教材定课程
先秦“六艺”教育时期,课程主要以礼、乐、射、御、书、数六类“活动课程”进行分类。《周礼·地官·司徒》中认为作为教师的“保氏”的职责是:掌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根据郑玄解释,“六艺”主要包括“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1]267-268通过郑玄的注解,我们知道西周“六艺”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课程体系。到孔子时,夫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教人,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运篇》),传统的课程开始从“活动”转向“文献”。例如当时楚庄王命大臣申叔时教授太子,申叔时的建议是:“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2]528-529在他开列的课程中,基于文献典籍的教本已经占据绝大多数,而且在其课程设计中还没有严格的经、史、子、集的区分。
汉代设立五经博士,确立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的核心教材地位。到唐代时,中央建立起“六学一馆”的官学教育体系,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将教授的经学分为正经和旁经,其中正经有九:《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旁经有三:《孝经》《论语》《老子》。学三经者,于大、中、小三经中各选一经。学习五经者,大经全选,余则各选一经,《孝经》《论语》于正经以外,皆需兼修,以资补助。[3]191至此,经学教材从汉代的“五经”发展为唐代的“十二经”。经过宋儒的表彰,《孟子》超子入经,进入到经学教育核心,构成了儒家“十三经”的教材体系。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筹备“十大本土最具发展潜力房地产企业”的颁奖典礼了。高潮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工作上,他想用绝佳的创意,为自己策划的这次活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以此向田卓向马老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
我那时候喜欢听新闻,对于科学界的几位泰斗,比如高士其、童第周之类的名字还算熟悉,虽然不知道严济慈是何方神圣,这名字可是听过好多次了。他亲自来请熊老夫人,那熊老夫人又是何许人也?
传统儒家教本的选择由不同时期官方教育机构对原典重要性的判断来决定,这些教本的学程由什么来决定呢?从唐代官学教育的规定来看,选修《孝经》《论语》者,以一年为限,选修《尚书》《公羊传》或《谷梁传》的各以一年半为限,选修《易》《诗》《周礼》或《仪礼》的,各以两年为限,选修《礼记》或《左传》的,则各以三年为限。[3]192这种学程的分类标准一个主要依据是经书字数的多少和难易程度。从南宋国子监主簿、经学家郑耕老统计的“九经”字数来看,分别是:《毛诗》39 124字,《尚书》25 700字,《周礼》45 806字,《礼记》99 020字,《周易》24 207字,《论语》15 700字,《孟子》34 685字,《孝经》1 903字,《春秋左传》201 350字,大小九经,合484 495字。[5]264对比唐代官学的学程安排,显然经书的字数是学程长短的重要考量。
(二)以课程定学程
观察儒家原典教材的特点,我们就会发现《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类似于现在的教材,但也有所差别。例如:传统教材本身就是课程分类标准,以《论语》为例,首先,在《论语》这一课程下,有不同的诠释版本,何晏的《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等都曾经作为官方教材。其次,《论语》在学习过程占据特定的学程,出现了童子与成人的两级分段,具有现代课程的属性。正如有学者所说:“现代中小学教育依据课程命名教材,传统私塾教育由教材命名课程。”[4]我们将传统原典教材的这一显著特点命名为“以教材定课程”,而以“教本”来命名原典教材。
教科书的概念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随着教会教育的侵入而逐渐进入中国的。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教会学校的教学需要,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负责筹备一套初等学校课本。这样,中国近代第一个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正式诞生了,并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12]3教科书不同于传统教本,它不是对原典的直接选择,而是在现代教育理念的前提下进行重新编纂的。其主要特点表现为:
与现代教育相比,传统教材在教法上的创新尤为不足。其主要原因在于对人的心理认知规律还没有深层次的把握,教学过程主要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现代教育过程中,从“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的转变使得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教法探索方兴未艾,各种教育测量手段的兴起也为教法的改革提供了评价标准。相比之下,传统教材以“考法定教法”造成的师生之间的紧张在现代教育中得到了一定的缓释。
在爆破设计中将预裂孔逐孔编号,通过测量现场放线获得预裂孔孔位实际高程,根据爆破设计计算出每个预裂孔的实际孔深,制成实际造孔参数表下发作业队并进行技术交底,作业队按造孔参数表控制预裂孔孔深。边坡特殊开挖段(如渐变段等),技术人员要逐孔进行计算,计算出各预裂孔的方位角、倾角及孔深,并在造孔过程中配合质检员现场校核各预裂孔的钻孔参数。预裂孔造孔严格执行“三定”制度。在钻机开孔前,对钻工进行详细的技术交底,严格执行“定机、定人、定岗”制度,对每个孔的孔深、倾角及钻孔责任人实行挂牌标示,做到责任到人。在每台钻机上设置有钻工作业明白卡,明确了钻孔工艺的程序和质量要求。
(三)以教师定教材
传统儒家教本的选择中,教师是很大的影响因素。汉代经学教育中讲求“师法”与“家法”,学习过程中选择了特定的教师即选择了相应的教本,例如《诗》学的韩生、申公;《书》学的伏生;《易》学的杨何;《春秋》的胡毋生;《礼》学的高堂生等;(《史记·儒林列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为保持“师法”的纯洁性,不敢有一字悖师。到宋代时,书院兴起,跟随不同的理学大师学习,决定了对经书的不同理解,教师决定了教本的选择。其次,教师还决定了经书的学习次序。例如朱熹就对四书的学习次序做出了自己的安排:“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7]419朱熹的后学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对于经学教育的学程做出了详细规划。他认为:“八岁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用来取代《千字文》,并让儿童诵读朱熹《童蒙须知》。八岁入学以后,读《小学》书正文,《小学》书毕,次读《大学》经、传正文,次读《论语》正文,次读《孟子》正文……前自八岁约用六七年之功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五经》正文可以尽毕……十五岁以后,先读《大学章句》、《或问》,《大学章句》、《或问》毕,次读《论语集注》、次读《孟子集注》、次读《中庸章句》、《或问》,次钞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读《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次读本经。”[8]7-14
到明清时期,基本上形成了先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主的“识字”书,再学习《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最后学习《五经》的学习次序。当然,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具有一定的选择空间。蔡元培回忆他小时候入私塾的学习经历时提到:“进入家塾以后,那时候初入塾的幼童,本有两种读书法:其一是先读《诗经》,取其句短而有韵,易于上口。《诗经》读毕,即接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一是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等书,然后接读四书。我们的周先生是用第二法的。但我记得只读过《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种。”[9]268-272
目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因城镇化失去了土地而成为失地农民。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预计将超过1个亿。[1]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尽管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会获得一定额度的安置补偿款,但是“仅仅依靠安置补偿款无法保障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2]。要解决长远生计,对于那些尚在劳动年龄段的失地农民而言,最好要能以非农就业方式重新就业。
(四)以考法定教法
在教法的选择上,传统教育相对单一。教法的僵化导致了“槚楚二物”成为延续千年的惩戒工具。当然,传统教法的流行与考试的方法息息相关。汉代的“对策”与“射策”主要考察应试者从经书中寻找应策方略的能力,而五经博士则考察学习者对“师说”的掌握程度,这些内容都要以熟记经书为前提。唐代的明经考试方法主要是“帖经”与“墨义”,《唐六典》记载:“诸明经试两经,进士一经,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每帖三言。通六以上,然后试策,《周礼》、《左氏》、《礼记》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皆录经文及注意为问。其答者须辨明义理,然后为通。通十为上上,通八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其通三经者,全通为上上,通十为上中,通九为上下,通八为中上,通七及二经通五为不第。”[10]45在这类考试中,类似于填空题和简答题,考生对经文和注释的熟悉程度是最主要的测试方面。
北宋以后,科举考试转向经义文,明清时期变为八股文,经学的学习内容还是主要在“十三经”体系内。这一时期的教学法基本形成了“童年诵经、成年明理”的两级学习模式,即童年主要背诵经文的内容,成年以后开始研读经书的注解。具体的教法还是以让学生背诵为主,《红楼梦》第九回记载,贾宝玉入学堂以后学习了《诗经》,而贾政则对伴读李贵说:“那怕是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你去请学里太爷的安,就说了: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11]135-136清代科举考试主要从《四书》中命题,考生需要依从朱熹的《四书集注》来作答,这也决定了教学过程以熟背经典为前提。
陈桂生教授认为“古代课程”实际上是“学程”。[6]110从现代教材来看,教材知识按照学科进行划分,学制阶段划分主要的考虑是学习者的心理和生理成长规律和对学习内容的接受程度。传统教材没有这些心理学研究为基础,教材的学程安排更多地考虑教学需求,依靠教学经验定夺。经书本身的难易程度,教学过程中的掌握程度成为学程安排的主要依据,教师在学程安排上具有很大的决定权。传统教材的这一特点可以称为“以课程定学程”。
二、现代教育理念下儒家原典教本向教科书转化
大数据背景下,民航服务在迎来全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遇到了相应的挑战。比如在服务内容方面。民航服务人员通常将自身服务内容局限在安全、礼貌及微笑等层面上,将服务范围限制在服务过程上。但在当前大数据时代中,面对移动智能网络及设备,旅客的需求有了明显的转变,航班信息服务是当代民航服务的核心内容。旅客需要运用大数据移动网络来提前了解航班所有的服务信息,从旅行开始到结束的相关服务内容。这些要求,完全颠覆了民航服务以往的服务认知,需要民航服务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为旅客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
(一)以学科范畴规划教材
近代教育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西方学科重新规划传统文化,实现了对原典的重构。从经学科来看,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小学堂和中学堂阶段,《四书》、《五经》开始进入到“读经讲经”科,而“读经讲经”与算数、历史、地理、体操、中国文字等同为学科之一。高等学堂阶段,经学科与理学、政法、文学、医科、农科、工科、商科并列为学科之一。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第二条明确规定大学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工科、农科、医科,[13]663经学科在学科建制上被取消,这标志着在学科分类上,西方的文、法、理、工、农、医、商“七科之学”正式取代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左玉河认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之《大学令》,取消经学科,将其内容分解到史学、哲学及文学等门类中,正式确立了七科分学之新学制体制,这标志着中国‘四部之学’在形式上完全被纳入到西方近代‘七科之学’知识系统之中。”[14]329
从经学教材来说,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庄俞就批评道:“令无初辨之稚子,以短促之四百小时,从事于《孝经》、《论语》、《礼记节本》三大古书,恐资质鲁钝者,仅能成诵,尚觉困难;资质聪颖者,亦不过囫囵吞枣,食而不化。”[18]罗振玉也认为:“各国教育最重德育,其修身诸书多隐合我先哲之遗训;但必相儿童之年龄为深浅之程度,不似我之以极高深之圣训,施之极幼稚之儿童耳。夫令儿童读极高深之圣训,是何异陈光施于盲人之前,奏九韶于聋者之侧,道则高矣,其如程度不合何?迄年岁既长,知识日进,则又将幼时所读之圣训弁髦弃之,而专力于所谓制举文字,故中国名为尚道德教育,其实则否也。”[13]153显然传统教材没有考虑儿童认知规律与教材呈现之间的关系,而现代教材在这一方面极大改善。
从上述描述中,我们也能看出,传统教本的选择和教授中,虽然具有“字书—四书—五经”这样的次序,但是教师对具体教本的选择有很大的权利。现代教材的编纂中,课程标准是重要的依据,通过合理的学程安排完成相应的课程目标是编纂者首先考虑的问题。现代教材与学制安排和学科知识结构相匹配,教材的选择集中于教育主管部门,教师的选择空间并不大。传统教育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应付入仕的资格考试,在具体教学中,每一阶段的教本选择,依从那些学者的注本,教学过程的具体次序等都由教师来决定,即“以教师定教材”。
(二)以认知规律编纂教材
新式教科书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教科书的编写开始注重对学习者认知规律的遵从。自赫尔巴特以后,心理学成为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例如从教学过程的初始阶段来看,传统教学法从“立志”开始,而新式教学法则从“明了”或“感知”开始,它们的区别在于传统教学过程靠外在驱动力强迫学生学习,而现代教学则注重按照认知规律,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编纂时就提到教科书编纂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已知及未知,按儿童脑力体力之发达,循序渐进,务使人人皆有普通之道德常识,然后进求古圣贤之要道,世界万国之学术艺能,庶几拾级而登,无或陨越”。[17]534
民国以后,中小学废止读经,经学科失去生存的空间。在高等教育阶段,经学科也被其余学科肢解,蔡元培认为:“《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之必要。”[15]86-87经学科的这种变化导致了《四书》、《五经》这类经学教材以传统知识的形式进入到现代学科中。这种以现代学科知识为划分依据的教材中,经典的权威性被消解,正如张汝伦所说:“按照现代的学科分类,它(《论语》)充其量是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或中国文化史的文献。教学《论语》,就像教学《水经注》或《十七史商榷》一样,教者教的是历史典籍,学者学的也是历史典籍,目的是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历史知识。”[16]255这一论述揭示了现代教材与传统教本的根本不同,即教材的选择和教授过程都是知识本位的,编者、教者、学者都是以“知识”为中心展开,而且“知识”按照学科逻辑以教科书的形式来呈现。
(三)以课程标准教授教材
现代教材的教授过程中,课程标准起到了指导作用。课程标准规定了教育主导者期望学习者达到的目标,这一目标要通过教材的学习来实现。现代教材按照学科的不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相比传统课程注重综合,现代课程更加关注学习者从浅入深的专业学习。教科书是按照课程标准对学科内容进行系统阐释而形成的文本,它是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媒介。教科书的编纂不是随意的,而是要依据课程标准而进行。在编纂过程中,可以选择不同的内容,以不同的形式最终达到课程标准规定的目标。这就预示着教科书的编纂要有大致相似的基本内容,例如某一学科的核心知识要在教科书中呈现,这也成为教科书区别于其余著作的根本特点。
现代教材的教授过程要依循课程标准的设计。传统教材的教授过程则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例如教师先教《论语》还是先教《孟子》,采用“三、百、千”开蒙还是利用《唐诗》或《诗经》开蒙,主要由教师来决定。现代教材是严格按照知识逻辑的结构来形成的,蒋维乔在民国商务印书馆编的小学教科书中提到:“初等小学第一年,因儿童识字不多,故第一册全用图画;二册以下,始用格言;三册则引用古事之可为模范者,皆每课附以图画,共计十册。”[19]143这些教材是按照学制阶段严格匹配的,实际教学中只能按照第一册到第十册的顺序来进行。高等教育阶段的专业学习,教科书的编排次序更加明显,只有按照课程标准先教授专业基础课程,才能开展专业课程的学习。课程标准成为现代教材在编写、教学、评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依据。
三、“新子学”视域下原典教材的编纂构想
相比起当代新儒家强烈的教化冲动,新子学在教材编纂领域起步尚晚。方勇教授指出:所谓“新子学”,就是要突破传统四部分类法,把子学作为学术思想主流去把握,对于纳入经学的孔子、孟子等作离经还子的处理,明确区分经学化的儒家与子学化的儒家,重新清理和整体考察历代子学,寻绎中国学术的内在肌理。[20]“新子学”的提出是对西学学科割裂传统经典的一次反动,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上试图进行一次传统文化的重构。“新子学”的研究范式要求整体地看待原典教本,而不是进行学科化的切割,对于建构新的原典教育方式意义重大。对比传统教本和现在教科书的特点,我们认为新子学教材编修方面至少要进行如下的改进:
(一)超越西方学科规范重新构建“新子学”教材体系
从原典教本的沿革来看,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现代教育完全抛弃了儒家原典的教授模式,中小学废止读经,高等教育阶段以文史哲等西方学科模式和理论重新规划原典的内容,并将其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各个学科,这种分科繁荣了各种新的词汇和理论,却彻底扼杀了经典作为整体的思想脉络。西方的学科理论给予了理解传统经典的视角,但是也产生了“以今观古”“以洋观中”的弊病。
“新子学”理念提醒我们超越学科界限,回到经典本身,将先秦诸子放在整体、平等的角度去看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完整的、统一的,这就预示着从某一学科角度去看经典,只能如盲人摸象,观其一端。在新的子学教材的编纂中要注重原典作为整体的统一性,在教材设置上,让学生直接接触原典,恢复经典的育人职能。现代教育过于注重知识的授受,忽视了经典的育人职能。脱离学科范畴下将原典作为知识授受的弊病,回归原典育人与传承的本质是文化复兴的努力方向。
(二)在“新子学”理念下重新认识经学教材的地位
退出经学系统的儒家教本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光环,成为与其他知识平等的资源。传统教育中,在“尊经崇圣”的意识形态下,把经学看成“万古常道”,放置于教育的中心位置。“新子学”的提出揭示了子学才是推动传统学术演进的核心动力,从整体平等的角度去认识经学,才会批判辩证地看待经学的利弊之处,从而真正揭示经学教材的现代价值。
当前,全球教育改革中,核心素养成为最受瞩目的焦点。文化理解与传承,审辩思维、创新、沟通、合作成为未来人才必须具备的五项基本素养,其中文化理解与传承成为21世纪核心素养的首要方面。文化的理解、认同和践行是个体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前提,塑造现代中国人要吸收传统文化的一切优良元素。这就预示着传统文化教育不应该再走向崇经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道路,而是将古代经典放在同等标准下去考量,构建反映当代和未来核心价值的经典课程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陈青之.中国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4]王明建.蒙学教材范式的现代化——兼论传统蒙学的复兴何以不可能[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5):27-31.
[5]阮葵生.茶余客话(全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十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8]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9]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2]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13]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4]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5]崔志海,编.蔡元培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16]陈来,甘阳,主编.孔子与当代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7]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18]庄俞.论学部之改良小学章程[J].教育杂志,1911(2):34-36.
[19]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0]方勇.“新子学”申论[J].探索与争鸣,2017(7):73-77.
Issues Related to the Revision of Textbooks in the Education of “Xinzixue ”
CHEN Xiang-long1,CHEN Xiang-feng2
(1.Institute of Education,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2.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Qingda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Qingdao 266300,China)
Abstract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cept of “Xinzixue”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participation of education.Afte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of cultural breaks,traditional classics need to be recreated.Traditional Confucian textbooks pay attention to the classics,while having the dual attributes of modern curriculum and textbooks.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textbook deciding the curriculum,the curriculum deciding the learning,the textbooks deciding the teacher,and the examination method determining the teaching method.The modern textbooks are written under the discipline planning,pay attention to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earners.They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planning of textbooks in the subject category,the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by cognitive rules,and the teaching of textbooks by curriculum standards.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textbooks represented by the 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under the planning of modern disciplines,have changed the existing form of Confucian classic textbooks.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Confucian textbooks is the epitome of the evolution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s in traditional education.The study of its characteristics is helpful to explore the “Xinzixue” textbooks that conform to the rules of modern education.
Key words :Xinzixue;Confucianism;textbooks;curriculum;four books and five classics
[中图分类号] B 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889X( 2019) 04- 0046- 06
[收稿日期] 2018-11-05
[作者简介] 陈祥龙(1984—),男,山东临沂人,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传统教育与高等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杨中启)
标签:新子学论文; 儒家论文; 教材论文; 课程论文; 四书五经论文;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论文; 青岛工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