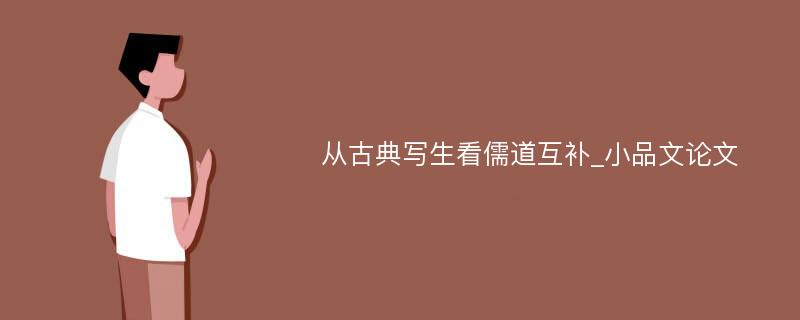
从古典小品文看“儒道互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品文论文,儒道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品文作为一种篇幅短小而又富有抒情色彩和讽刺意味的独特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小品”一词,来自佛学,本指佛经的节本。它形式上属于散文,但涵盖的文体多样,如随笔、日记、杂文、书信、游记、序跋、寓言、铭、赞乃至骈文、辞赋、小说等,几乎所有文体都可以写成小品。小品文的渊源及流变十分复杂,从它问世之日起,便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思想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的论述对象主要集中于首次显示出独立文体意义的晚唐小品文和此种文体达至鼎盛时期的晚明小品文。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互补”
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春秋时期“周文疲弊”[1](P27)。为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诸子百家兴起。儒家用仁学改良周礼,以使周礼重新焕发生命力。道家用道学批评周礼,为使人性获得自由自在的发展。它们的出发点都是追求人性的健康,都希望建立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欺压、没有苦难的合理社会。儒、道两家的终极目标是相通的,只是理论的侧重点和进路不同。而儒道之互补,则是以两家学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广泛而明显的差异为前提的。
儒家之“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就其性质而言,即是“仁”。“仁,亲也,从人二。”[2](P161)字面意义正在于表明二人的结合,其所隐含的哲学意义即对立面的统一。孔孟以“仁”为“道”,意味着“道”这一范畴已隐含着合二为一的意义。孔孟在讲“仁”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礼”的作用,亦即肯定人与人之间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因此,合二为一绝不意味着要消除对立面之间的差异性,而是以肯定差异或对立为前提和基础的。孔孟之道的底蕴绝不仅仅在于合二为一,更在于一分为二,即对立统一。儒家对立统一即矛盾的思想是儒家哲学的理论基础,贯彻于其哲学的各个部分。
如果说儒家矛盾观的本质特征在于抹杀矛盾同一性的话,那么道家矛盾观则走上了相反的另一端。老子在一定程度上也看到了现实世界中的矛盾,但他过于强调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关系,夸大了矛盾的同一性,以至于抹杀了矛盾转化的必要条件,从而导致其学说的相对主义色彩。从一定意义上说,庄子有关“道”的哲学正是老子矛盾观发展的历史产物。换言之,道家之“道”就是其矛盾观的高度概括。其于混沌未分之“道”的归依,充分显示了它在矛盾问题上要求消除对立和差异的倾向。
正是由于儒道两家的“道”目标相似、路径相反,其矛盾观各执一端,儒道学说才可以且有必要互补。由此造成了其发展过程中渐趋合流以至于相互融合的必然之势,中国哲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儒道互补”的特点。这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既入世而出世”,“它就是最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最现实主义的;它是很实用的,但是并不肤浅”[3](P5)。
从人生价值取向来看,儒家的人生哲学是积极进取的,它围绕着对社会伦理的关注而展开,“仁”、“礼”的关系问题是其核心。“仁”指的是个体的道德内在性,“礼”则是为亲疏远近、尊卑贵贱关系建立一整套的等级规制。它既体现着儒家哲学理想的历史王道,也是他们心中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的政治秩序。个体必须使自己成为自觉的历史王道的传承者。因此,“内圣外王”是儒家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设计:一方面,使人们朝心灵内部探求善的内在源头,加强修养,在道德上、精神上完善自己,即“内圣”;另一方面,又使人们的追求落实到现实社会,认为价值生命的归宿在于体现历史王道的现实世界中,即“外王”。古人将这样的人生道路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则是人生努力的目标。但是,怀抱圣王理想而意在现存统治秩序的儒家学说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内在困顿。实际上,理想性的历史王道的代表人物尧、舜只不过是家长式的氏族首领,其“道”具有原始氏族部落的血缘情感及民本政治特色,而春秋战国以来几千年的封建君主制下的君王,则是家天下的专制君主,推行封建专制政治。不可否认,君主专制的政治基础仍是以血缘情感来维系的宗法等级制度,但毕竟与孔孟理想化的历史王道相去甚远。[4](P61)另外,儒家学说的内在困境不仅表现在理想化的历史王道与现实社会政治的冲突,而且,现实生活中个体命运的偶然性,也使很多怀有“治国平天下”抱负的仁人志士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虽然本身就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这样一些互补观念,但在“穷”与“达”两途间,儒家人生哲学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双向选择的终极价值体系,因此,现实的人生实践也就必然需要另一种价值意义上的心理依托和精神慰藉。
道家人生哲学强调个体生命要保全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从社会纷争中退出,回复到超功利、超道德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命状态中去。首先,在道家哲学看来,仁义道德的演进和提倡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在价值形态上的倒退。因此,“内圣外王”不仅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而且恰是人生意义及生命价值的失落和毁灭。其次,道家追求的是自然之真与美,而向宇宙天地的回归也就是向自然真与美的回归。这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活动即“体道”,它是排除一切心智、计虑,通过淡化主体来达到物我的合一。因此,人们也就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超然于社会困苦、伪善和纷争的自然之真与美的存在,由此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再次,道家人生哲学强调对个体自身的关怀。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是社会动物,具有群体性,其本性中就包含着关心家庭、他人和社会的意识;另一方面,人又是相对独立的生命个体,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欲望、感情、个性和自由意志,其本性中同样包含着关心自我、追求个体幸福与自由的意识。
总之,儒家思想强调人的群体性,而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的人生哲学强调人的个体性,重视个体的安宁与精神自由,道家人生哲学的特征是面对现实人生的困境,以求得精神的超脱,从而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足。它为世人找到了一种面对现实困境与人生困途的解救路径,因而成为几千年来文人们不可或缺的另一种精神依托。
二、从古典小品文看文人“儒道互补”的心理结构
林语堂先生说:“我们大家都是天生一半道家主义者和一半儒家主义者。”[5](P20)
在封建制度下,出仕与退隐、兼济与独善、乐观进取与消极退避是任何一个文人都需要面对的人生选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即士阶层从小就接受文化典籍的训练,熟悉孔孟老庄的思想并接受其熏陶,很容易形成儒道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他们一方面积极入世,向往建功立业,并恪守儒家的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又追求超然物外、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彷徨于尘垢之外,逍遥于无为之业。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每当危难当头,舍生取义、慷慨悲歌;另一方面又孤高自守、愤世嫉俗。一方面心存魏阙,胸怀天下,政治清平则乐观进取,奋发有为;另一方面又身在江湖,乐隐渔樵,社会动乱则消极退避,全身自保。
这种儒道互补的心理结构作为中国文人的人格基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古典小品文中,同样典型地呈现出文人们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
先看晚唐时期。这是一个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已走向末路。许多社会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个王朝,牛李党争、宦官擅权、藩镇割据、社会动乱、生灵涂炭,这些都给心忧天下、命运多舛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以强烈震撼。以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为代表的晚唐小品文作家,大都出身寒微,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而又怀抱利器,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身处末世,不平则鸣,纷纷以无情之笔,揭露黑暗,抨击现实,宣泄不满,为民请命。他们从“愤世疾邪,舒泄胸中不平之蕴”和“警当世而诫将来”[6](P218)的目的出发,以短小精悍的小品文作为批判的武器,毫无顾忌地将讽刺锋芒指向晚唐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匕首寸铁,刺人尤深”[7](P84)成为晚唐小品文的显著特点。这些作品常常寓讽刺于议论之中,直接干预现实政治,无情揭露社会矛盾,言辞激切,意旨鲜明,如皮日休的《鹿门隐书》、《十原》、《九讽》等,陆龟蒙的《野庙碑》、《记鼠稻》、《禽暴》等,罗隐的《辩害》、《越妇言》、《秋虫赋》等,孙樵的《逐鬼记》、《武皇遗剑录》、《书何易于》等,都是辛辣大胆讽刺黑暗现实的力作。应该说,这些作品都折射出小品文作家们文化心理结构中受儒家精神影响的一面。
生逢末世的皮、陆、罗等作家,面对晚唐衰败的国事,希望以一己之志,拯危救弊,挽狂澜于既倒。然而,社会黑暗,命运坎坷,理想与抱负总是被现实击碎。他们在时代的迷雾苦海中,思想感情呈现出复杂性。鲁迅先生曾作出过中肯的评价:“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8](P575)试以陆龟蒙为例,他出身官僚世家,举进士不第,曾任苏、湖两郡从事,后隐居甫里,经营茶园,岁取租茶,自为品第,常携书籍、茶灶、笔床、钓具泛舟往来于太湖,自称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陆龟蒙所著诗文很多,有《甫里先生集》、《笠泽丛书》等文集。其诗多写闲适隐居生活,风格清隽秀逸,时人给予很高评价,与温庭筠、李商隐相提并论;其散文成就尤高,多用比喻、寓言、借古讽今。“惟杂文则龟蒙小品为多,不及日休《文薮》时标伟论,然闲情、别致,亦复自成一家。”[9]这里的“闲情”、“别致”主要是指陆文立意和表现形式的新奇而言。“闲情”指的是陆龟蒙作为“江湖散人”、“布衣之士”的创作心态。他不是在朝重臣,“敢谏鼓不陈,进善旌不理,布衣之说无由自通乎天子。丞相府不开,平津阁不立,布衣之说无由自通乎宰执”[10](P8393)。因此,只好以闲淡之心静心构思“别致”之文,以揭时政之弊。陆龟蒙这种“处江湖之远而怀庙堂之忧”的情怀,不正是传统士大夫“儒道互补”心理结构的外化表现吗?
再看晚明时期。此时正值明清易代之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较大的松动,“异端”思想大放光彩。文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上发生了改变,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传统、人生和自我,从而掀起了一场复苏人性、张扬个性的思潮。这种思潮促使文人们大胆追求现世的乐趣,充分享受生活的快乐,极力肯定自我的人性、人情、人欲。晚明士人们普遍表现出对自我个性与情感价值的重新体认,主动放弃以往那种对道德完美的理性追求,重新向内发现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创造性价值;从抽象、虚伪的道德说教回归到符合人性发展的现实与情感中来。加之,晚明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文人们渐渐失去了对政治与现实的热情与关注。为了躲避乱世,他们纷纷远离世俗,隐居山林,以山人名士自居,以道家虚静无为、崇尚自然为日常生活与创作的指南。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及思想背景下产生的晚明小品文,形式轻灵隽永,体制短小精悍,且极富个性色彩。它们一改传统诗文载道的厚重,以“芽甲一新,精彩八面”的风貌,远离敏感政治,深得晚明士人喜爱,一时“丽典新声,络绎奔会”[11](P1),几乎可以视为晚明文人心灵的宣言书。通过对晚明山水小品、闲适小品的解读,人们可以感受到,一股追求精神自由、个性率真的时代风气正扑面而来。从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晚明文人这种追求超尘绝俗的清高之趣与隐逸之风正是受老庄人生哲学影响的结果。
虽然晚明时期思想呈解放之态,但绝大多数文人仍不能真正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我道德完善的最高标准,“学而优则仕”则高度概括了他们求知的目的。因此,以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为主旋律的晚明小品文中同样不乏贴近现实、反映当时文人不平之情、慷慨悲歌的作品,由此呈现出了一种“儒道互补”的心理结构。这在晚明性灵小品的代表公安派及张岱等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出现在明朝万历年间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由于深受进步思想家李贽及汤显祖的影响,极力推崇“性灵”,反对复古,要求体制、风格上创新。“三袁”都是通过八股取士而步入仕途的,对功名的汲汲追求在袁中道的《心律》中表露无遗:
追思我自婴世网以来,止除睡着不作梦时,或忘却功名了也。求胜求伸,以必得为主,作文时,深思苦索,常至呕血,每至科场将近,扃户下帷,摒弃身命,及入场一次,劳辱万状,如剧驿马,了无停时,岁岁相逐,乐虚苦实。屈指算之,自戊子以至庚戌,凡九科矣。自十九入场,今年亦四十一岁矣。以作文过苦,兼之借酒色以自排遣,已得痼疾,逢时便发。头发已半白,鬓已渐白,须亦有几茎白者,老丑渐出,衰相已见,其何得果何如也?设使以此精神求道,则道眼已明;以此精神求仙,则内丹已就;以此精神著书,则垂世不朽之业已成,而所苦丘山,所得尚未毫厘,今犹然未知税驾。[12](P952)
张岱作为明末小品文成就最高的代表,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著作中保存了不少小品文的佳作。他一生未入仕途,但早年也曾有功名之念,自己未得科第,曾以功名教子,他在《课儿读諟》中说:“一战不胜,当思裹甲复来;再则弗售,何惜抱荆三献。”“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平日弗用功,自到临期悔。”[13](P70)清兵南下后,他入山不出,有很高的民族气节。动荡的时代和亡国的现实,还使张岱形成较为“自觉的忏悔意识”[14](P459)。在遭亡国之痛后,张岱心态陡然转变,作品中充满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沧桑感。“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铁氏佘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歌楼舞榭,弱柳夭桃,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矣。”[15](P1)字里行间可以分明感受到一种家国破败之痛!
三、从古典小品文看“儒道互补”的文学品格
在作品的内容与题材方面,小品文也呈现出“儒道互补”的文学品格,在晚唐和晚明的小品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典型。
以孔孟为主体的儒学,在文艺思想上,一方面主张文艺要“事父”、“事君”,为巩固现存的统治秩序服务;另一方面又肯定文艺具有“怨”、“刺”腐败政治与改革社会的功能。因此,儒家强调文艺要对现实的社会政治起积极作用,“要求文学作品具有充实的社会人生内容、有风骨、有兴寄。反映在题材上,儒家正统文学往往是现实主义的,要求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针砭时弊,抒发个人的政治抱负与家国之感”[16](P58)。道家在文艺观上反对人工雕琢,标举自然与浪漫不羁的想象,追求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和独特个性的表达。受道家人生哲学的影响,文人们追求心灵上的宁静自足、自由逍遥,而这种人生境界与人格发之为文,多表现为谈玄说道、山水闲适、鬼怪神仙、情志穷愁等。
晚唐讽刺小品可说是儒家文艺观的具体实践。综观晚唐小品文,它们大致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一是取材广泛,善于以小见大,以日常生活中寻常事物反映民生疾苦、针砭时弊,如罗隐的《说天鸡》:文章先谈狙氏父子养鸡之事。说父亲养的鸡见敌则勇,伺晨则鸣,因此被称作“天鸡”。而父死后,儿子却不得其父养鸡之术,“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彩错、嘴距恬利者,不与其栖。无复向时伺晨之俦,见敌之勇,峨冠高步,饮啄而已。吁,道之坏也有如是夫!”[17](P178)其目的是借以讽刺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无德无能、峨冠博带的达官贵人。再如陆龟蒙的《记稻鼠》:文章先写震泽以东的吴兴大旱,而越是大旱,群鼠便越在夜里盗稻谷;接着写大旱与鼠患越是严重,官吏索赋征税就越苛刻残酷;然后进一步斥责道:“上捃其财,而下啖其食,率一民而当二鼠,不流浪转徙,聚而为盗,何哉?”[18](P102)此文正是《诗经·硕鼠》主题的深化,把官吏比作老鼠,代表了晚唐人民忍无可忍的心声。
二是善于以虚构寓言故事的形式讽喻现实,抨击时政,如陆龟蒙的《蠹化》。文章借毛虫的变化及遭遇,巧喻官僚的为人处世,意在抨击“灭德忘公,崇浮饰傲,荣其外而枯其内,害其本而窒其源”的官僚,警告他们将要面临“为大蝥网而胶之”的下场。文章从“桔之蠹”写起,再巧妙引申,谓“天下,大桔也;名位,大羽化也;封略,大蕙篁也”[19](P110)云云,直落到官僚身上,然后对其歹行好一顿数落。罗隐的《秋虫赋》将封建国家的法网比作“绳小不绳大”的蛛网,对其虚伪性的揭露既贴切而又含蓄,言简意深,笔调诙谐,鲜明地体现出了晚唐小品文的文章风格。
三是常常采用托古讽今手法来借题发挥,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例如罗隐的小品文《迷楼赋》。文章紧扣“迷”的含义加以生发,痛斥隋炀帝承袭文帝后,荒于朝政,沉溺声色之娱,任将相擅权,最终国亡身殒。显然,作者是在借炀帝之事讥刺晚唐昏庸无道、奢靡纵欲之君。
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晚唐小品文作家在其作品中奏响的是激越的现实主义乐章。他们生逢末世,在时代的迷雾苦海中,思想感情呈现出复杂性,普遍表现出“儒道互补”的文人品格。这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心理结构必然会贯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多表现为情志穷愁之作,重在抒发一种孤高自守、愤世嫉俗的情感。罗隐的《叙二狂生》、《答贺兰友书》等即显露出此种感情:表明自己虽有志于入世,却不愿随波逐流、趋炎附势,而要保持忠贞正直、孤傲脱俗的人格品位。在小品文《后雪赋》中有更为鲜明的表述:
邹生阅相如之词,呀然解颐曰:“善则善矣,犹有所遗。”梁王属酒盈卮:“惟生少思,苟有独见,吾当考之。”生曰:“若夫盈净之姿,轻明之质,风雅交证,方圆间出;臣万分之中,无相如之言。所见者,藩溷枪吹,腐败掀空,雪不敛片,飘飘在中。污秽所宗,马牛所避。下下高高,雪为之积。至若涨盐池之水,屹铜山之巅,触类而生,不可殚言。臣所以恶其不择地而下,然后浼洁白之性焉。”梁王咏叹斯久,撤去樽酒。
相如悚然,再拜稽首:“若臣所为,适彰孤陋。敬服斯文,请事良友。”[20](P173)
这篇翻案文字,抓住“不择地而下”作为翻案的支点,一个“恶”字,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那些不讲气节、甘于同流合污的人的鄙夷及嘲弄。这也无疑是在表明作者自己择善而从、贞洁自守,绝不随波逐流、汲汲名利、趋炎附势的高洁人品。
晚明文人情有独钟的小品文明显受道家文艺思想的影响,其中有很多文笔清隽、意境深远的山水小品,如:公安派的袁小修的日记《游居柿录》中即有“夜雪小大,时欲登舟至沙市,竟为雨雪阻。然万竹中雪子敲戛,铮铮有声;暗窗红火,任意看数卷书,亦复有少趣”[21](P2618)之类的文字。张岱也十分善写此类灵动清新的小品,如《湖心亭看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22](P170)
道家人生哲学强调对个体自身的关怀,追求精神的逍遥自由,而不是追求道德的完善。晚明小品文中大量的闲适小品、清言小品则明显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晚明文人们酷爱探幽访胜、登山临水,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享受人生的闲情逸趣,如袁宏道的《雨后六桥记》:“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子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23](P2538)晚明小品中还有很多关于茶的文章,如张岱的《兰雪茶》、《闵老子茶》,陆树声的《茶寮记叙》,周履靖的《茶德颂》,张大复的《云雾茶》、《试茶》、《茶说》等,充分反映出晚明文人追求自由闲适的人生意趣。
清言小品是晚明小品文中最能传达士大夫通过参禅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一种文学形式。所谓“清言”,即一种清谈人生的言论。这个“清”字中既包含了发表这种言论的士大夫的一种清高、清雅的态度,也反映出这类言论小品所具有的清远、玄妙的特点,所以人称这类小品为语语俏丽、字字珠玑。清言小品到晚明可谓层出不穷,出现了诸如田艺衡的《玉笑零音》、陆树声的《清暑笔谈》、吕坤的《呻吟语》、洪自诚的《菜根谭》、屠隆的《婆罗馆清言》、陈继儒的《岩栖幽事》、黄汝亨的《寓林清言》、吴从先的《小窗四纪》、祝世禄的《祝子小言》、彭汝让的《木几冗谈》、李鼎的《偶谭》、乐纯的《雪庵清史》等许多清言小品集。从晚明清言小品对人生哲理的深悟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士大夫心态上的变化——原来儒家那种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渐渐被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淡泊心态所代替。
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24](P575)以晚明小品文名家夏完淳、陈子龙为例,他们在遭丧国之痛后,心态陡然转变,直接投身于抵抗清军的斗争中,被捕后牺牲。夏完淳在明亡后,所作诗赋散文,抒写国破家亡的悲痛,具有饱含血泪、悲壮淋漓的独特风格,如《土室余论》、《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等,均是血性文字。陈子龙的小品文,如《许氏之鹤》、《翁氏之鳩》等,也和公安、竟陵诸家所作不同,其托物咏志,颇与唐末的讽喻小品文相似。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先秦诸子百家中,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和以“道”为指归的道家向世人展示出各自独特的价值体系,得以广泛流布和发展,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从而在确立中华民族精神和铸造民族之魂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肇源于先秦的中国古典小品文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古代散文不断发展的结果,就其内容与题材以及作品中反映出的文人风貌来看,无不彰显出“儒道互补”思想影响的深刻印迹。换言之,只有将小品文置于“儒道互补”的文化语境之中,才可能真正品味出创作主体独特的心理结构和作品别具一格的文学品格。
标签:小品文论文; 儒道论文; 儒家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陆龟蒙论文; 国学论文; 道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