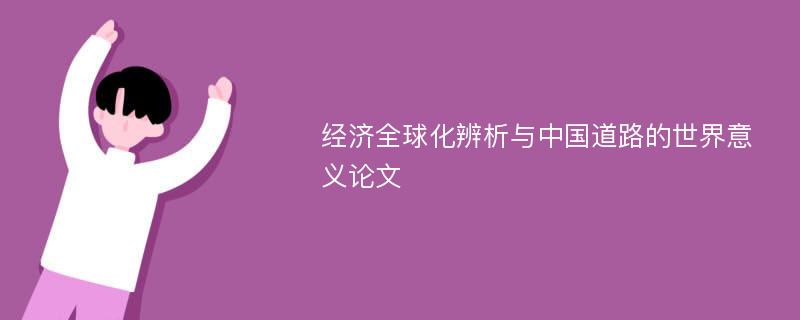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研究
经济全球化辨析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周 文 包炜杰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然而,在全球化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反对声音,其中既有部分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两极分化的现实从而“反全球化”,又有部分发达国家将本国衰落归咎于全球化进而“逆全球化”。归根究底,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反思全球化进程中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现实困境,首先要破除经济全球化等于西方化的错误认知。其次,经济全球化不是去工业化。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过于强调贸易的重要性,陷入“贸易原教旨主义”而忽视了生产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再者,经济全球化不是完全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过于强调市场化违背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市场的跨国性与政府的国界性是全球化的一组悖论。对发达国家而言,全球化正是其崛起的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的去工业化和过度金融化才是西方衰落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40年正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40年,全球化视野下中国道路的成功至少具有以下三点意义:第一,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凸显国家主体性;第二,注重以政府为主体的有效市场的建构,保持国家竞争优势;第三,突破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回归全球化的价值属性。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西方化 去工业化 完全市场化 中国道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即各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作为一个确定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明显。据统计,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额的82%,而占全球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分别仅占14%和18%,世界上20个最富有国家国民的平均收入是20个最贫穷国家的37倍,两者之间的差距比40年前增加了一倍。因此,既有早先此起彼伏的“反全球化”声音,又有近年来以特朗普“美国优先”策略主导的“逆全球化”浪潮。究其原因,长期以来,对于全球化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吗?为什么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崛起而许多国家遭遇失败?究竟什么才是全球化的真面孔?换言之,全球化中国富国穷之谜的答案是什么?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必须澄清关于全球化的认知误区,进而重新界定全球化。对全球化的认识,不应仅仅停留在现象层面,更不能只是把它看作近四十年来的短暂性现象,而应该放到全球史视野下来审视,从整个世界体系变迁的历史维度加以考察。
一、 经济全球化不是西方化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陌生现象。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随之而来的贸易活动促成世界开始紧密地联系起来。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大爆炸和交通运输方式革新更加深刻地改变了全球交往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场广义上的全球化运动是这样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 20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日益突破信息传播的地理界限,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化再次掀起高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这场经济全球化运动下过一个定义:“跨国商品及服务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长,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 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第5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94页。 这一定义突出了现象层面的全球化表征。可以说,全球化既是突破国别地域界限进行国际贸易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
然而,长期以来,全球化叙事存在一个欧洲中心论的理论预设。所谓“欧洲中心论”,主要是指关于全球化的叙事往往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关联在一起,而后者又以西方的兴起为背景,加之后人总结的诸多欧洲文化的历史优越性要素,如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基础、新教伦理以及西方的理性主义等,欧洲由此获得了向世界扩散“现代性”的道义和权力。欧洲中心论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基于这样的认知方式,欧洲及其分支(如美国)相较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地位是必然且持久的。从本质来看,欧洲中心论是“一个神话、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理论或者一种主导叙事”。[注] 马立博著,夏继果译:《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 15-21世纪》(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页。
正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的逻辑,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标西方,误以为西方化就是全球化、现代化的本质,结果给本国经济与社会造成巨大伤害。这种“伤害”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形成包括经济在内的多重依附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固化了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在繁荣的表象下暗藏着非均衡状态,从侧面反映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不稳定性和不公平性。萨米尔·阿明将中心国家的这种非理性行为归结为五种垄断力:“技术垄断”、“对世界金融市场的金融控制”、“对全球自然资源开发的垄断”、“媒体和通讯垄断”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注] [埃]萨米尔·阿明著,丁开杰等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二是发展中国家对西方陷入制度崇拜,盲目西化,丧失国家自主性。政府的国界性与市场的跨国性一直是全球化的最大悖论,在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实现一国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有效互动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土化和适应性问题。以俄罗斯为例,在采用“休克疗法”的过程中,快速自由化引发了宏观经济失衡,金融和石油寡头们趁机操控国民经济,结果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造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转型经济衰退”[注] [俄]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著,孙梁译:《荣衰互鉴:中国、俄罗斯以及西方的经济史》,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7页。 。
因此,反思全球化进程中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现实困境,首先要破除全球化认知中的西方化倾向。从这个角度讲,全球化非但不是西方化,而更应回归多元化和世界性。所谓“多元化”,就是指全球化应当是多元、多中心的而非一元主导。基于欧洲中心论的全球化叙事存在“自我夸大”的根本缺陷,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通过经济史考证得出这样一个更让人信服的结论:在1800年以前“我们有的是一个多中心同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的世界”,“只是在19世纪工业化充分发展之后,一个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有意义”。[注] [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页。 归根到底,那种认为西方文化具有历史优越性的观点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假说只是一系列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的产物,并不具有永恒性。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势必推动全球化重新回归多元化;至于“世界性”,则是指全球化应当走向世界历史而非西方一元论的历史。“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等一般性的理解和说明,实际上就是关于全球化的基本阐释。”[注] 丰子义、杨学功、仰海峰:《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 全球化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然而,关于世界历史、“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美好愿景正与当前全球两极分化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因此,驱散西方化的迷雾,更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彻底批判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谬误。
二、 经济全球化不是去工业化
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就论证了分工的重要性,“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注]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7页。 。在讨论是否应当限制从国外输入本国能够生产的货物时,斯密认为,“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注]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33页。 。那么,如何进行全球化中的国际分工和对外贸易呢?
江河湖海,可能“何”天生要比“胡”小一些,我认识的女孩子都是姓何居多,岛上最漂亮的一个姑娘叫何禾。这里的名字都是单名,是因为这里的风大,单名更好喊,而且这里的姓氏少,所以大家都习惯了只喊后面的名,站在楼上一扯嗓子,整个岛几乎都能听见。我就叫“生”,我听到的最多的就是“禾”。因为何禾漂亮,所以在放学的路上所有的男生都喜欢和她玩闹几下,她走路又慢,所以回家总晚。至于我的邻居兄弟胡来和胡去,因为名字比较纠缠,就会麻烦些,反正我老听到他们的妈妈在那里喊:快来,去。去吧,来。
从理论基础来看,比较优势理论主导着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如果一个国家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强调,各国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各国应生产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产品。按照上述比较优势理论的推演,国际分工有利于专业化生产最适合本国生产的产品,国际贸易则使贸易双方实现交换以获得更大效益,这似乎是一套“完美”的全球化方案。然而,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发展差距的事实,比较优势显然存在着严重缺陷。
尽管市场化改革一定程度上适应开放经济的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全球化不是完全市场化。早在1791年,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认为,工业无需政府支持就能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与制造业繁荣休戚相关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财富,甚至还有这个国家的独立。每一个为实现其伟大目标的国家,都应拥有满足本国需求的所有基本市场要素。”[注] [加]瓦克拉夫·斯米尔著,李凤梅、刘寅龙译:《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1页。 市场作用的发挥同样依赖于国家的自主性,也就是有效的“国家建构”。在那些经济转型取得出色成绩的东亚国家中,始终离不开政府的身影。
1.1 资料来源 选取2009年1月-2016年9月本院妇科行子宫切除后经病理学证实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100例为子宫内膜癌组,年龄38~82岁,平均年龄58.17岁;绝经后患者68例,绝经前患者32例。其他良性疾病切除子宫患者30例为正常子宫组,年龄26~62岁,平均年龄42.75岁,绝经后患者9例,绝经前患者21例。记录患者年龄、家族史、绝经情况等基本信息。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后随访4~56个月。本研究中患者均由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由鄂州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究其原因,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过于强调贸易的重要性,陷入了“贸易原教旨主义”的泥潭,而忽视了生产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国际贸易不是万能的,工业化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就此做了很好的揭示。他指出,技术变迁(创新)、规模经济(报酬递增)和协同/集群效应是富国的三大关键因素,并共同作用于一个国家的生产体系,而“一个国家的财富取决于这个国家生产什么”[注] [挪]埃里克·S·赖纳特著,杨虎涛、陈国涛等译:《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一方面,18世纪的工业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推动形成了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从而确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历史发展时指出,“它(指‘大工业’,笔者注)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这生动地揭示了正是工业化开启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全球化的深入展开也有赖于工业化的新发展,而非“去工业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创新,而创新则集中体现于工业或制造业中。毋庸置疑,制造业是现代化社会技术创新的第一来源和基本动力。正如以研究美国制造业发展史著称的思想家瓦克拉夫·斯米尔是这样评价制造业的:“如果一个发达的现代经济体要想真正地实现繁荣富强,那么就必须有一个强大、多样和富于创造性的制造行业,它的目标是不仅能在资源约束下提供高质量产品的制造业,而且是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制造业。”[注] [加]瓦克拉夫·斯米尔著,李凤梅、刘寅龙译:《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Ⅳ页。
根本上,市场的跨国性与政府的国界性始终是全球化的一组悖论。因此,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成为全球化能否促进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如果只知市场优势而不见市场失灵,那么,无疑将一国发展让位于资本逻辑主导,这一“短视”也必定给全球化打上折扣。因此,当前世界范围内对于全球化的反对浪潮也可以看作是对完全市场化的排斥。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东欧等地区的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非但未能摆脱“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深受不平等的国际规则制约和资源环境破坏之害,从而旗帜鲜明地“反全球化”。面对完全市场化带来的国际资本市场管制取消、发展中国家承受开放其贸易和投资市场的压力日增,以及实际造成的严重贫富差距,罗德里克在《全球化的悖论》一书开篇就提出了两个原理,其中一个就是“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两者缺一不可”[注] [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页。 。尽管这个观点听上去并不那么新鲜,但是那些鼓吹市场好处多多、政府弊端重重的“弗里德曼们”不得不面对支持他们观点的基本事实依据的改变。
三、 经济全球化不是完全市场化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正是西方兴起的关键原因。全球化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交织在一起,正如欧洲中心论所宣称的那样,现代世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总是有利于西方的。按照资本主义形态的历史变迁,从商业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再到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场资本主义不断对外扩张的运动。资本是追求财富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注] ⑤ 《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71、860~861页。 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中,“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⑤,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挣得了第一桶金,使得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获得了全球化的主导权。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推动了工业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指出的那样,“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页。 工业资本主义依靠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进一步拓宽了世界市场,加速了全球化,并按照它的生产要求作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安排。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进而形成了垄断统治。然而,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或通过发动战争或施行新政以缓解矛盾,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出台,都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应激反应。“二战”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重新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秩序。随着8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又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复兴。当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造成资本过度积累危机时,“资本总是要通过地理扩张和时间重配来解决”[注] [美]大卫·哈维著,周大昕译:《世界的逻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299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一种“帝国主义”,存在着多次“掠夺式积累”,而这种积累归根到底推动了西方的兴起。
从现实来看,1982年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是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品”,上世纪90年代更是拉美国家全面推进结构改革的10年。“华盛顿共识”的市场化调整方案不仅要求相关国家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而且直接要求放松政府管制和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在结构改革中,市场化加速了贸易自由化并助推了私有化,对拉美国家的工业部门造成巨大冲击。从根本来看,新自由主义不断趋向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倡导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这尤其表现在针对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而抛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上,其实质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转向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注] 周文、包炜杰:《中国方案: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当代回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3期。
改革开放的40年,正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40年。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按照可比价格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约9.5%,从1978年的3645亿元增长到现在的80多万亿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被称为“中国奇迹”。究其原因,一是对内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融入全球化,打造开放经济。的确,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失败了。因此,中国道路的成功对于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发展至少具有以下几点启示:
基于比较优势的理论逻辑,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因此,国家发展将必然滑向“去工业化”或“非工业化”。所谓“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工业部门就业占比和增加值占比持续下降的现象。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的生产和贸易体系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应当大力发展农业而非工业,例如尼加拉瓜将专注于生产香蕉。然而,类似国家将面临着沦为世界生产体系中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的风险。上世纪50-70年代,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采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模式,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基础,经历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期”;然而,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使拉美国家被迫接受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的要求,放弃原有发展模式,全力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以争取外贸盈余,偿还债务。在这场拉美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中,过早实施“去工业化”是导致拉美国家20多年经济滑坡最直接的原因。[注] 苏振兴、张勇:《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拉美国家工业化模式的转型》,《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 同时,对于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国家而言,“理应”利用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对外输出进而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建立远离本土、遍布世界各地的“代工厂”,加速了自身的“去工业化”进程,美国的苹果、通用等跨国公司就是典型案例。此外,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去工业化”,尤其是金融业、房地产行业催生的经济泡沫。总体而言,无论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还是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都表现出了“去工业化”的倾向,以至于给人造成全球化就是去工业化的错觉。那么,在全球化进程中“去工业化”究竟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什么影响?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西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但很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家”甚少、“产业政策”匮乏、“工业体系”不健全,无法有效消化,从而使其更加远离制造业和技术创新,陷入更深层次的贫困中,“资本流遍全球,利润流回西方”描述的正是这种情况。这也正是全球化中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根本逻辑所在。
2.DCC-GARCH模型。对于一般的多元GARCH模型,动态相关系数的多元模型DCC—GARCH可以在赋予条件相关系数时变性的基础上较好的解决参数过多和假定相关系数为常数的问题(Engle&Sheppard,2010)。另外,该模型还可以有效地计算出大规模金融变量之间的时变相关系数矩阵。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采用DCC-GARCH模型研究“深港通”启动前后深港股票市场之间波动率的时变相关系数特征。
四、 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崛起而不是西方衰落的原因
另一方面,西方衰败的真正原因在于过度金融化和去工业化。当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客观地看,美国中产阶级退化与就业不足的原因之一确实是市场全球扩张运动,但全球化并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有研究者指出,美国就业岗位消失仅有13%源于贸易,其他近87%由于自动化以及一些本地因素减少劳动需求所致。[注] 陈伟光、蔡伟宏:《逆全球化现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科学文摘》2017年第8期。 特朗普对于全球化的判断只是停留在现象层面,他所描述的只是美国民众不断看到工厂一个个倒闭、产业工人不断失业,以底特律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化城市不断破产。他指责中国导致了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因而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贸易逆差意味着市场压缩,利润减少,债务增加,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激增。殊不知,美国社会的大量财富早已随着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转移到华尔街金融资本家的手中。过度金融化已经深刻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金融投机泛滥进一步加剧经济风险,出现金融泡沫,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深陷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泥潭,在微观层面上则导致家庭债务持续上升。[注] 托马斯·I·帕利:《金融化:涵义和影响》,载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变化与结构性危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3页。 此外,西方国家过度金融化的同时伴随着去工业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革命的扩散是美国去工业化的直接动因,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则是根本原因。[注] 苏立君:《逆全球化与美国“再工业化”的不可能性研究》,《经济学家》2017年第6期。 美国在奥巴马时期就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先后出台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以期重振美国经济。然而,资本追求的“时空最优组合”的动能不会停止。就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而言,以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立国,造成产业空心化,进而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总体而言,过度金融化和去工业化最终导致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三大新变化之一。因此,就现象而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而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理论表现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在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通过美国抛出的“华盛顿共识”[注] 华盛顿共识(1990)的十项政策工具:(1)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经济学家》2004年第2期。 的方式得以表现;在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可以概括为“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其核心为“市场化”。那么,全球化就是市场化吗?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无论是早期的荷兰和英国,还是后来居上的美国。但是,当前部分发达国家认为本国利益在全球化中受损,进而从全球化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以美国为例,特朗普将美国的衰退归因于全球化,他认为全球化摧毁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导致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财富向海外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因此,自2017年1月特朗普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策略主导下,美国在经济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在政治上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与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世界各国陷入贸易摩擦和冲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浪潮。那么,全球化真如特朗普所说是美国衰落进而是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衰落的根源吗?其实不然。
五、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通过市场实现的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注] [埃]萨米尔·阿明著,丁开杰等译:《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页。 全球市场同样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那些极力鼓吹市场优越性(比如认为市场能够形成自发秩序)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他们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全球化本身不能给一个社会带来这些能力(指生产能力,笔者注),它只能让已经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好地利用现有条件。”[注] [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廖丽华译:《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0页。 因而,那种认为全球化能够通过市场化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企图”也最终未能实现。从危害来看,如果无条件向外资敞开贸易和投资的大门,这显然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那种过度强调开放市场重要性的全球化主张忽视了不同经济体之间发展的根本性差异。与此同时,市场具有的负外部性也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其苦。市场自由化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资本过度积累危机,过度市场化很容易产生泡沫,不受监管的杠杆作用会带来系统性风险,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例证。此外,完全市场化很容易走向私有化。完全市场化将会催生垄断行为、扩大收入差距,往往与私有化相伴而生,导致国民经济失衡,影响社会稳定。保罗·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深刻揭示了世界经济中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两种剥削方式:一是“简单的商品交换”,即贸易自由;二是“通过在后一个国家中拥有资本所有权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即“资本自由移动”。[注] [美]保罗·斯威齐著,陈观烈、秦亚男译:《资本主义发展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357~361页。 而完全市场化正是促成这种“自由”、实现剥削的“通行证”。
第一,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凸显国家主体性。所谓全球化的“普遍主义”,是指那些把全球化教条地等同于西方化的做法。全球化不是西方化。如果简单照搬西方标准对标本国发展,必定会产生“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后果。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生产要素全球流动以及生产在全球范围的水平和垂直分工的同时,资本市场自由化也对本地市场带来冲击。尽管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是自由贸易也要讲求时机和条件。普遍主义忽视了比较优势理论背后的国别差异性,忽视了技术外溢性对于一国经济成长的深层次作用,以及对于边际报酬递增产业的筛选。相比而言,在融入全球化的40年间,中国的探索立足于国情,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逐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具有“特殊主义”的基本国情既包括发展特点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更包括制度属性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既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失败的深刻教训,又借鉴了拉美等后发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历史经验,首先在发展导向上破除了全球化、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如果离开了具有特殊主义的“国家主体性”,那么必然会滑向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泥潭。
由此看来自主性学习能力与高职生的英语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假定自主性学习能够促使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那么在成绩优异的学生当中,有较高学习自主性的学生往往能够得到更高的成绩,而缺乏学习自主性的学生往往在英语方面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学生的成绩可能会出现两极分化。
第二,注重以政府为主体的有效市场的建构,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在西方的认知里,资本主义总是优于社会主义,其中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市场经济总是优于计划经济,如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就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一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断加强各经济体彼此联系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广泛传播。在这背后,涉及到经济运行的核心命题,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古典学派到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传统中始终存在着“强市场弱政府”的传统。基于市场逻辑,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平均利润率下降导致的“去工业化”顺理成章,国际热钱竞相逐利进而影响一国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也变得理所当然。显然,这一逻辑是错误的。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将作为一种制度属性的“社会主义”与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与“全球化=完全市场化”的教条相对应,中国坚持的恰恰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两点论”和“辩证法”。此外,如何在整合静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保持竞争优势?西方的市场理论同样不能给出回答。反观之,有效的国家建构和政府治理凸显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的崛起,绝不仅仅只是因为人口红利、资源丰富、土地广袤等比较优势,这些只能理解为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注] 周文、冯文韬:《中国奇迹与国家建构——来自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验与总结》,《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4)清洗冷冻机冷凝器确保冷冻机制冷量。制定冷冻机维护措施,冷冻机连续运行时间超过半年则需对冷冻机制冷效果进行分析,确保冷冻机能够正常工作或备用。
第三,中国道路突破了国强必霸的西方逻辑,回归全球化的价值属性,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既产生了“中心—外围”非均衡的世界体系,又“意外地”出现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因此,西方世界盛行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当前,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也可视为对中国崛起的遏制举措。然而,全球化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趋势。“新经济地理的融入、新科技革命、国际贸易理论的自由化取向、全球经济治理的完善等现实基础都将使其继续发展。”[注] 裴长洪、刘洪槐:《习近平经济全球化科学论述的学习与研究》,《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4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失的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注] 《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面对“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全球发展失衡”的现实,中国率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旨在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世界分享发展成果,通过经贸与人文的交流将世界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切中的正是全球化的本质目标,即真正的全球化应当致力于通过多种经济合作方式促进共同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
高校行政机构在高校中有着重要作用,它协调、监督学校各方面的后勤和教学工作的开展。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发展,高校教育改革的进度不断加深,内部管理的规模也在持续地扩大和改变,使得行政管理的范围也随着扩大,行政管理工作的内容、复杂程度也不断增加。因此,只有进行行政管理的改革,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才能使得各行政部门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管理学研究
Analysi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a Path
Zhou Wen1 Bao Weijie2
(1.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 2.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 )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a definite trend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 among countries. While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prosperity, it has also faced many voices of oppositio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faced the reality of global polarization and thus “anti-globalization.” Meanwhile,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attribute their decline to globalization and then “de-globalization.” In the final analysis, there are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reflect on the reality of rich countries richer and poor countries poorer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we must firstly eliminate the erroneous perception tha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equal to westernization. Seco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not deindustrial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trade too much and falls into “trade fundamentalism,” which neglects the importance of production to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ov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not completely market-oriented. Neo-liberalism emphasizes too much marketization against the fact that the transnational nature of the market and the borderline nature of the government are a paradox of globalization. For developed countries, globalization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ir rise. The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over-financialization caused by the decline of average profit margin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re the real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t the same time,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exactly the 40 years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globalization. The success of China Path under the vision of globalization has at least the following three significances: first, seek a balance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to highlight national subjectivity; seco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ffective market with the government as the main body to maintain the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ird, break through the western logic of national power and hegemony, return to the value attribute of globalization, and strive to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esternization; deindustrialization; completely market-oriented; China Path
[作者简介] 周 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包炜杰,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吕晓刚]
标签:经济全球化论文; 西方化论文; 去工业化论文; 完全市场化论文; 中国道路论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论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