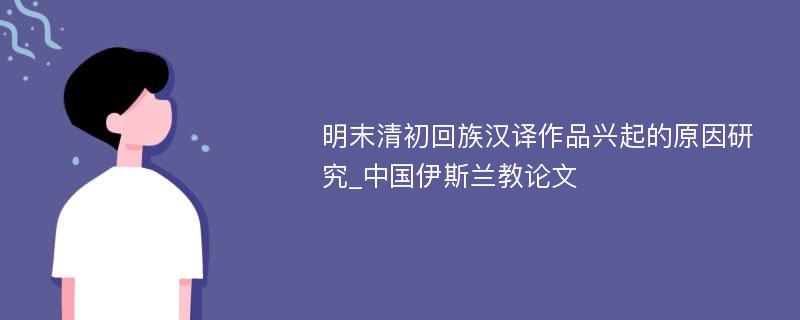
明末清初回族伊斯兰汉文译著兴起的原因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论文,回族论文,译著论文,明末清初论文,汉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堂教育本质上是唐宋以来“蕃学”的延续和发展,而汉译伊斯兰教典籍的出现则恰逢明末清初。阿拉伯和中国“精神文化的交融的代表性时期是明末清初,”(注:蔡德贵:《中国和阿拉伯:异域的两种文化及其融合》,载《阿拉伯世界》1993年第2期,第33页。)指的就是汉译伊斯兰教典籍活动。这其中既有伊斯兰教内部发展的原因,也有回回穆斯林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背景变化的因素,还应该考虑伊斯兰思想和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间相互融通的理论前提。以此为线索,本文着重分析明末清初汉译伊斯兰典籍活动产生的原因。
一、伊斯兰教在中土发展的困境——“经文匮乏、学人寥落”
“伊斯兰教自唐入华后,迄明中叶止,不甚盛行于世。”(注:冯今源:《“来复铭”析》,载《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148页。)以元代来说,尽管不少回回穆斯林当时有着相当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但是伊斯兰教的传承主要还是凭借着父子之间的“家传心授”,局限于礼拜寺的内部,不注重教理的对外宣传,穆斯林学者似乎并不希望教外人士了解伊斯兰教。白寿彝先生称之为“伊斯兰移植(中国)过程中所表现的缺憾”。(注: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这种“缺憾”一直延续到明代中后期,这时候不仅教外人士对伊斯兰教义茫然无知,许多回回穆斯林对于教门也只是“沿其迹,不得其真性。”(注:明万历三十七年福建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载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穆斯林在元代尽管已经“勒籍版图”,但伊斯兰教作为他们固守的精神信仰,其传播的范围却只局限于回回人的内部,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况且他们的周围是以儒家思想为价值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更造成了伊斯兰教传播的困难,形成了“吾教自唐迄明,虽有经籍传入兹土,而其理艺难传,旨义难悉,故世代无一二精通教理之掌牧,以致多人沦落迷途,漫漫长夜而甘醉梦之不觉也”(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真回破衲痴序〉,杨永昌、马继祖标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的局面。
明代中后期,随着回回人口的不断繁衍,他们受到儒家思想和周围汉族的影响日益加深。具体表现是回回人宗教信仰的淡化和敦门的式微。泉州《丁氏族谱》中有《祖教》篇记载明嘉靖十五年(1536)事说:“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文义,亦不求其晓,凶吉皆用之。……夏(衍)稚年习见如此”。又有《感旧记闻》说:“嘉靖丙申岁(1536),余方弱冠……当时见闻寡昧,不识赛典赤何义,妄以意度,番地番语,难于史册稽也。”(注:转引自《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如果夏衍的上述记载真实,这说明至少在嘉靖十五年(1536)以前泉州的部分回回穆斯林已经不懂得《古兰经》的文义,也没有要求懂的愿望。更重要的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已经被称为“夷音”“番语”,说明汉语这时已经取代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为他们日常的交际语言。陕西咸阳“修建胡太师祖佳城记”碑文中也有“唯吾教之流于中国者,远处东极,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杨之无自。”(注: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页。)马之骐的《修真蒙引·序》中说:“忆予稚年受业于先大掌教太所马公,乃骐外祖也。万历甲寅岁(1614)授一经,名曰哈题卜稚纳,……后马公捐馆,骐意欲此经流行,以汉字译之,且欲解释其义。”(注:转引自《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页。)由此可见,当时供蒙童学经的小册子《哈题卜稚纳》已经需要译成汉文才能流行了。《清真指南·指南序》的作者也认为:“(伊斯兰教)惜无著书遗世,徒以心援,失学拘儒,南辕北辙,于是教之所及者及之,教之所不及者,则不及之。”(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一〈马承荫指南序〉,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这些都说明无论在东南、西南、还是在西北,伊斯兰教都面临着同样的发展困境。《清真指南》卷一记载清康熙年间事说:“康熙十八年己末,皇上狩于蠡城(今河北境内),登清真阁,见架置天经,徘徊不忍去,诏寺人能讲者来,蠡人无有应诏者。二十一年秋,西域国臣以天经进,上谕礼部侍臣即传京师内外,诏能讲者来,”(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一〈援诏〉,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结果有“一教领”应诏,但该教领只能诵读原文,不会讲解其义。康熙下诏求人讲解《古兰经》,这是宣传和解释教义的良机,但结果却是“无人应诏”。即使有人应诏,也只是会诵读原文,而不能阐述教义了。《清真指南》卷八还记载了作者对于伊斯兰教门衰微的八“忧”。
“真教之入中国,不详所自始,世鲜有通其说者;而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第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故寝以失其初意,而承讹袭舛,真派之堙且久矣。”(注:明万历三十年(1602)浙江《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回回穆斯林大多数是靠“祖习、风俗、自性”和“家传口授”“父子相传”来获得教理教义知识的,清真寺或礼拜寺的教职人员只能依靠为数不多的穆斯林学者以及他们的后代充任,以至造成宗教职业人员的日益缺乏。这必然会在回回民众中产生信仰危机,引起伊斯兰教的“中湮危险”。甚至于出现“虽其先守教之家,今亦掉臂而叛去,此教之所以繇衰”(注:明万历三十七年(1639)福建泉州《重修清净寺碑》,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又见马以愚:《中国伊斯兰教寺墓考察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的情形。
当然,明代中后期伊斯兰教的衰微除了其自身发展的因素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回回穆斯林一直不注重对教外人士进行教理教义的宣传和解释。“其国之人皆真诚朴讷,不欲立言以自广,或有之,则又聱牙估倔不能通中国之典,畅彼此之怀也。”(注:(清)刘智:《天方性理》、〈天方性理图说序(俞序)〉,京江谈氏重刊版,中华民国十二年印。)结果是,回回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仅受到舆论的歧视和非难,也受到一些政府官员的猜忌和疑虑。回汉之间的文化隔阂日益突出,所谓“卑鄙者流,墨守其师说,而弗轨于理;第于饮食起居,纤细琐屑之末,排异教如寇仇,争是非如聚讼。”(注:明万历三十年(1602)浙江《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因此,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外在环境的压力。伊斯兰宗教学者要振兴教门、改变伊斯兰教衰微的局面,他们除了在回回穆斯林内部传承和端正教门信仰外,同时还面临着向周围的非穆斯林,特别是向汉族士绅阐扬和宣解伊斯兰教理教义的任务。伊斯兰教信仰要得以世代相承,就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二、回回民族意识的觉醒——“阐正教于中华”和“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在本土化、中国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适时的“主动性”,即主动为维护“清真正教”而进行“辨难”或“释疑”;主动地吸收和借鉴中国儒家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的内容来阐释和宣扬伊斯兰教,积极融入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之中。“主动性”是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教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也是回回民族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汉译伊斯兰教典籍的出现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中“主动性”的具体体现。我们从这一时期汉文译著家们自己写作的“叙”或“序”中,可以看出这些先知先觉的伊斯兰学者期望“阐正教于中华”(注:(清)马注:《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公茔碑总序》,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5页。)的努力,以及“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注: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页。)的责任感。
王岱舆在《正教真诠·自叙》中说:“予不佞亦得以阐发至道,而使天下正人君子略其芜蔓之词,大明正教之理。”(注:(明)王岱舆:《正教真诠·自叙》广州清真堂刊本,余振贵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正教真诠·问答记言》中还有“夫清真教道,指迷归正,劝人作善,止人为非,乃人道当然。无此,则人道为不备。予既真知正学而不言,是为隐匿斯道。即作书言之,而不能恺切诚恳,犹无言也。”王岱舆认为自己既然知道清真教道之正学,假如不通过自己的著述加以宣传的话,实际上就是隐匿了清真教道,其过错当属不小;即便是自己通过著述对教义进行了宣传,倘若阐述得不够恺切诚恳、精确得当,其实就等于没有著述。王岱舆在这里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不仅要用汉文进行编译伊斯兰教经典的工作,而且要言之恺切、言之诚恳、言之精当。王岱舆的译著工作对后来的伊斯兰学者影响很大,马注称赞“岱舆王先生奋起吴俗,惧道不彰,著为《真诠》一集,可谓清夜鸣钟,唤醒醉梦,苦药针砭,救济沉疴”。(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一〈自叙〉,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而他自己著译《清真指南》是为了“辟邪说,正人心,承先圣先贤之教,以禁夫天下万世之从异端而不知害者。不知害,则叛道远矣。”(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八〈跋〉,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他期望“是书也,……为习儒者通经之捷径,习经者指迷之药方。”(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八〈授书说〉,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9页。)在马注所著的《清真指南》卷一中有“进经疏”“援诏”“请褒表”等篇,他的意图是希望将《清真指南》“缮呈御览”,期望能够“黜异扶儒”修齐治平”。(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一〈进经疏〉,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7页。)他甚至希望康熙能“用颁海内”,并且“遴选清真实学,回儒兼通”的学者“缮经呈进,以立一家之法言,垂教万世,救正天下人心。”(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一〈请褒表〉,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马注显然有借助清朝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伊斯兰教的想法。刘智在《天方性理·自序》中说:“经则天方之经,理乃天下之理。”他纂译《天方性理》的目的是使天下人“共闻”“共明”伊斯兰教经典中的“天下之理。”(注:(清)刘智:《天方性理》〈自序〉,京江谈氏重刊版,中华民国十二年印。)刘智还声明:“予孳孳之意不息,笃志阐天方之学以晓中人。”(注:(清)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书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可见,王岱舆、马注、刘智这些伊斯兰学者已经自觉地、公开地肩负起“禁异端”“辟邪说,正人心”的宗教使命,他们第一次有意识地“阐天方之学以晓中人”,第一次把“阐正教于中华”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已经认识到“抱道不出,其咎在己”。(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一〈郁速馥传〉,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一位署名“八公边闻钦”的人在评价王岱舆的《希真正答》时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是集欤。观其志,本为阐扬正教,指引迷途,使聋聩者得有见闻;恍惚者心归一定,……其理本为鼓舞天下之英才,其事更欲唤醒世人之醉梦,”(注:(明)王岱舆:《希真正答》〈边闻钦又序〉,余振贵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清真指南·指南序》作者说:“圣后(即马注)惧正教久湮,异端左道眩惑人心。著为是集,经号《指南》,遵而行之,可以指一人,亦可以指千万人。”刘智的老师袁汝琦在给《天方性理》所作的序中说:“《密迩索德》、《勒瓦一台》、《额史尔》等经,既行于天方,又传之中国。凡吾教学人,皆知诵习之矣。奈何文语屹崛聱牙,不能通习于儒,则天下之公理似属一家之私言。千百年来,无与其事者,乃刘氏介廉慨然独认,会同东西之文,而汉译之。采精挹萃,辑数经而为一经。”因此,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伊斯兰学者们的汉译经典活动客观上起到了“指引迷途”“唤醒世人之醉梦”的作用,从而使作为“天下之公理”的伊斯兰教义能够被人们遵行,并进而得到阐扬和光大。另外还有一些伊斯兰学者,愤于当时社会现实的压力以及教门的“卒沦”,他们针对教外士绅对伊斯兰教的非议和责难,起而进行汉文著译。清乾隆初年任职翰林院四译馆的金天柱著有《清真释疑》一书,在该书的自序中金天柱说:“兹释疑之说,亦迫于各教之横议而起者。清真者,吾教之宗,《释疑》为何而作也?由于各教莫能思吾教之行事,蓄疑团于千百年而莫释,未学吾教之书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正是由于来自外界环境中非穆斯林的误解和疑惑,加上对“清真之理卒沦,没于庸众人之齿颊,不大显于斯世”的悲愤,所以金天柱著译《清真释疑》,其目的是“予期告无罪于前辈,并期阐厥义于今日。”(注:(清)金天柱:《清真释疑·自序》,海正忠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2页。)据记载《清真释疑》还曾献呈乾隆皇帝御览。金天柱著译《清真释疑》虽然是出于社会环境的压力,但是他维护“清真”形象的自觉意识十分明显,这也是回回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重要体现。
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家们在自己的译著中一方面“笃志”于“阐天方之学以晓中人”;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寻求伊斯兰教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合适道路,当他们站在这条道路的入口时,他们不得不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抉择,那就是对伊斯兰教的教义理论进行适当的调整。他们认为:“应该在‘变’中审视伊斯兰教,教义思想应与世偕进,随时代而推移。教义说不能胶柱鼓瑟,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注:秦惠彬:《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载《中国伊斯兰文化》,《文史知识》编辑部等编,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2页。)王岱舆所谓“理不圆融机不活,空读清真万卷书”,(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八〈授书说〉,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9页。)马注的“权教者从其俗便”,“因教者因其乡文”,(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四〈因教〉,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理要圆融”、“权教”、“因教”都是指要“变”,而且是“从其俗便”“因其乡文”的“变”,是与现实社会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相适应的“变”。大约与刘智同时代的米万济著有《教款微论》一书。他在自叙中说:“本教惟务其实。故每于宣传条约之际,讲贯告诫之时,咸以俗言注释,令人易解。……予之著斯言也,直欲通达之士,于致知博学之余,知清真之教有可尚可崇之道,以致寻真而问化。又欲本教之师长,于问答讲论之际,知儒理有相通相籍之资,便宜化贤士以归真。故以寥寥数语,用伸倦倦之惆忱耳。”(注:(清)米万济:《教款微论》〈自叙〉,1934年北平清真书报社刊本。)
由此可见,米万济著译《教款微论》的目的是用儒理来阐释教理,期望通达博学的儒士知道清真正教之“可尚可崇”,进而至于“寻真而问化”;又可以使本教之师长清楚儒理中也有和教理“相通相籍”的内容。米万济的著述主要体现了“伊儒互补”的思想,并且已经开始用“俗言”注释宣讲经文了。我们可以看出米万济的著述思想与刘智的“会同东西之文”十分接近。因此,“伊儒互补”应该是体现了当时伊斯兰学者的时代性思想倾向。
三、扬伊斯兰的必由途径——“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
目前还没有文献资料显示在明代中期以前已经有学者(包括穆斯林宗教学者和非穆斯林学者)开始了伊斯兰教典籍的汉译工作,尽管此前已有汉文作品的清真寺碑铭。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明代中叶以前回回穆斯林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的母语,一般还能读懂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典。一是伊斯兰教的传统观念反对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中有“我降示给你们阿拉伯文的《古兰经》”(20:113)。在穆斯林心目中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才是纯正的宗教语言,他们担心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会影响教义教理的纯正。一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仍有人认为不应该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因为这样使“经不杂”,不会有损教义的纯正。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李光缙所撰的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中有:“余按净教(伊斯兰教)之经,默德那国王谟罕蓦所著,与禅经并来西域,均非中国圣人之书。但禅经译而便于读,故至今学士谭之;而净教之经,未重汉译,是以不甚盛行于世。”但是“禅经译而经杂,净经不译而经不杂”,因此,他认为“多言诡道,不如冥冥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注: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又见马以愚《中国伊斯兰教寺墓考察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李光缙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穆斯林学者的共同观点,而且“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提出也说明了这些穆斯林士绅已经受到了儒家文化相当的影响。
一般认为,唐宋时期的回回先民大多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宋人岳珂的《桯史·番禺海獠》云:广州回回先民住地“有堂焉,以祀名,……称谓聱牙,亦莫能晓……。堂中有碑,高袤数丈,上皆刻异书如篆籕。”(注:(宋)岳珂:《桯史》卷第十一〈番禺海獠〉,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5页。)所谓“称谓聱牙”“刻异书如篆籕”,这说明当时的回回先民平时的交际语言是他们的母语。元代东迁而来的穆斯林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和其他一些民族成分的人,他们各自使用着自己的民族语言,这对于他们相互之间的日常交际和交流思想十分不便,所以选择一种便于交流的共同语言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尽管明万历年间浙江“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中还有:“夫其教本出西域,国自为俗,流入华土,各仍其世而守之,用以无忘厥祖。……其人相见,则以其语自通,蔼如一家,有无相济,适万里可无賫”的记述(注:明万历三十年(1602)浙江《嘉兴府建真教寺碑记》,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但是到明代中后期,随着使用母语环境的渐渐消失,穆斯林使用母语的机会也必然会减少,阿拉波文和波斯文的使用明显地衰微。他们在和周围汉民的交往中渐渐地学会了使用汉语,穆斯林后来日常使用的语言中虽然也一直保留了不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但是他们已经不能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进行正常的交流,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逐渐淡出他们的日常交际,汉语取代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成为他们新的通用语言。在新的语言中保留下来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则采取了汉字音译的形式。前面引述的泉州《丁氏族谱》中称阿拉伯语或波斯语为“夷音”“番语”就足以说明,至少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以前,泉州的部分回回穆斯林已经普遍地使用汉语进行交际了。至于伊斯兰金石碑刻的文字由起初的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发展到汉文阿文分刻或合刻,以至后来的全汉文碑刻,这也反映了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使用式微的趋势。比如,刻于元至大三年或四年(公元1310年或1311年)的福建泉州阿拉伯文建修碑记,其碑文都是带有点号的大号古阿拉伯文,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古的一块阿拉伯文碑记;(注: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浙江杭州伊斯兰教历707年碑(公元1307年,即元大德十一年),其双面铭文都是阿拉伯文;福建泉州先贤古墓阿拉伯文碑立于伊斯兰教历722年9月(即公元1323年,元至治三年),也是全阿文的碑刻;浙扛杭州伊斯兰教历730年碑(公元1330年,即元至顺元年),其碑文也只有阿拉伯文。民国十六年(1927)扬州城南挡军楼出土四方元代穆斯林墓碑,分别刻于元大德六年(1302)、元至大三年(1310)、元泰定元年(1324)、元泰定元年(1324)。(注: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0页。)四方墓碑共有八面文字,其中只有一面有两行竖写的汉文楷书,其余七面皆是阿拉伯文,这七面阿文碑文中有一面中间夹着一些波斯文,每方碑文中都有“异乡之死,即是殉教”的圣训。福建泉州艾哈迈德碑是现存的惟一用波斯文记载泉州古称“宰桐城”的墓碑,双面刻字,一面为汉文,一面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泉州的“番客墓”碑则是“汉阿合刻”,即一面碑文中既有汉文又有阿文。明末以降,大多数有关清真寺(礼拜寺)的碑文则全部是用汉文刻写。但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的墓碑一般均为汉文和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分刻或合刻,并且都是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介绍伊斯兰教理教义,用汉文来介绍墓主的生平和生卒年月日。这表明尽管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在回回穆斯林中已不通行,但是它们作为记载伊斯兰经典的文字仍然受到穆斯林大众的崇敬。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坚定的伊斯兰信仰,因为“教本主命,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不敢易尔”。(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二〈客问〉,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页。)
所以明代中后期的情形是:一方面,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母语地位巳被汉语所取代;另一方面,回回穆斯林仍然有着坚定的教门信仰。同时,随着经堂教育的兴起和发展,不仅要培养能够阅读伊斯兰教原文经典的经师,而且还需要这些经师学者们向他们身边虔诚的穆斯林民众宣讲教义、教理和教法知识。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必以授学习学有人,方能继圣指迷,传经宏教,启迪后学,导引新进。”(注:(清)赵灿:《经学系传谱》〈真回破衲痴序〉,杨永昌、马继祖标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5页。)因此,这中间存在的语言问题非常突出。因为伊斯兰宗教经典使用的是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经师和阿訇们要是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讲经,一般的穆斯林很难听懂。对于怎样教授刚刚学经的蒙童来说,这个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张中在《归真总义》中明确指出:“读西方之书,未易通晓。解天经,而非中国之语,安所传宣,势不得不参用之。”(注:(明)张中:《归真总义》〈凡例〉,中华民国二十年陇右马福祥题本。)于是,一些经师和阿匍们开始发明了一种用阿拉伯语(也有部分波斯语的语音)拼汉语的拼音文字,这种拼音文字被称为小经、小儿经或小儿锦。小儿经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蒙童学经以及穆民的日常记账、书信和记事。但是小儿锦的创制没有统一的规范,随意性很大;而且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这项工作本身就存在许多困难;加上小儿锦既不便于记诵,也不便于推广。所以后来并没有多大的发展,没能普遍地流行。白寿彝先生也认为:“明代曾发明以阿拉伯文字母,作为拼写符号,拼写经典注释及日常账目书信等,不过没有统一的标准,不能普遍的流行。”(注: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小儿锦的使用只是暂时顺应了形势,满足了一时之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回回穆斯林习学经典的语言上的困难。此外,这一时期随着经堂教育的兴起又出现了另一种用汉语音译或意译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一类词汇被称为“经堂语”或“经堂用语”。“经堂语”或“经堂用语”也是在清真寺经堂的特定环境下、在满足穆斯林学经的特殊需要下出现的,后来虽然有一部分“经堂用语”成为穆斯林的日常用语,但毕竟不能满足日常交际的需要。用“经堂语”或“经堂用语”来翻译伊斯兰教经典更是远远不够,如果全用汉语音译或意译经典,其实也行不通。再加上伊斯兰学者对小儿经和经堂语的使用也有分歧,著名的译著家刘智就反对用经堂语翻译经典,他主张用典雅的汉文译经。他在《天方典礼》例言中说:“经文汉文,原相吻合,奈学者讲经训字,多用俚谈,未免支离,有失经旨。愚不惮烦,每训文解字,必摹对推敲,使两义恰合,然后下笔。览者勿谓愚反经异俗,是反俗合经耳。”(注:(清)刘智:《天方典礼》〈例言〉,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智认为自己用汉文译经是“反俗合经”之举,而讲经训学中的“俚谈”则“有失经旨”。
“经堂语和小儿锦的出现,本身是从应用外来语言于宗教生活到应用汉语于日常宗教生活的一个过渡。”(注:金宜久:《中国伊斯兰教探秘》,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小儿经的难以推广,经堂语的有限功能,从而使得汉语成为宣传伊斯兰教理教义的必要手段,经堂教育中学习汉语也成为一种需要。在这种情势下,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成为阐扬和宣传教理教义的当然途径。“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成为一些“回儒兼通”的学者适时的选择,“汉克它卜”(即“书”,阿拉伯语为“kitab”)随之出现。“惟是经文与汉字不相符合,识经典者必不能通汉文,习汉文者又不能知经典。自《正教真诠》出,遂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注:粤东城南重刻《正教真诠》序,载王岱舆《正教真诠》,广州清真堂刊本,余振贵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在形势上已经成为必需,但在教理上是否合法,这还需要汉文译著家们做理论上的说明,以便让一般穆斯林消除思想上的疑虑。王岱舆在他的《希真正答》中论证了用汉文翻译伊斯兰经典的合理性,有人问:“凡以一句‘哈他(差错)’文字,杂于清真,真主之慈即止,而罚且随之。若以‘哈他’文字注释正教之经旨,岂不大悖乎?”王岱舆回答说:“所谓‘哈他’者,乃其教道非其文字也,”“文字比如土木,可以建礼拜寺,可以造供佛堂,正道异端互相取用,其功过不在材料,唯论人之所用何如耳,”所以“由是言之,明命圣谕,何尝拘于一方,无非便于世人,本为阐扬正教,岂区区执着于文字也哉。”王岱舆还特地强调这种认为“正教之经旨”不能用汉文注释的观点虽早就存在,但是“今之为此说者不明耳”,(注:以上引文均参见王岱舆:《希真正答》,余振贵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285页。)王岱舆所谓的“不明”即是指对形势没有理性的清醒认识。这说明用汉文翻译经典已成为必然趋势,而且当时的许多伊斯兰教学人实际上也已经是“读一句西域经典,必以一句汉言译之”,(注:以上引文均参见王岱舆:《希真正答》,余振贵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285页。)这样的状况又使得伊斯兰经典汉译的工作更容易被接受。据传胡登州也曾“慕本教经书,欲译国语”,并且是“按东土之音配合其节,究于理之赅而不偏,辞之平而有味”(注:(清)赵灿:《经学系谱传》,杨永昌、马继祖标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的标准来进行翻译的。根据现存的史料,我们对胡登州的译经活动知道的很少,他也没有译著传世。但是从他“欲译国语”的想法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一些伊斯兰教学者对汉译伊斯兰教典籍的态度。刘智的父亲刘汉英(三杰)曾说:“天方经典,析理甚精,惜未有汉译,俾广其传于东土也。”(注:《刘介廉先生墓碑》,参见余振贵、雷晓静主编的《中国回族金石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页。)这同样说明“言本天经、字用东土”(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一〈援诏〉,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的汉译经典活动具有教理上的合法性。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用汉文译经在回回穆斯林中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逐渐被认同接受的过程。马伯良于康熙戊午年(1678)编译成《教款捷要》,在这本书中他对一些重要的宗教术语仍然采用阿拉伯文词汇,没有用汉文翻译。他认为“盖以非用汉文译经,固不能启大众之省悟,纯用汉文,由难合正教之规矩。”(注:转引自余振贵、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文献著译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马伯良的心态代表着当时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学者观点。但无论如何,“本韩柳欧苏之笔,发清真奥妙之典”(注:(清)金天柱《清真释疑》,马廷辅序,海正忠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的活动是逐渐展开了。
四、必要的、适时的选择——“回回附儒以行”和“以儒诠经”
现代统治者宣扬和提倡程朱理学,从而使讲究“性理之学”的程朱理学盛行其道。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产生了广泛的交流和接触。应该说,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天道观等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都与伊斯兰教哲学和教义教规有相通之处。刘智认为:“(伊斯兰教礼法)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注:(清)刘智:《天方典礼·自序》,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马注也认为:“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他的《清真指南》主要内容就是“晰诸教异同之理,阐幽明死生之说,上穷造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注:(清)马注:《清真指南》,〈马承荫指南序〉,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这些所谓“先圣先王之教”、“造化”、“修身”等等,对于一个稍微涉猎过儒家经典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用它们来解释“清真之学”和“天方之礼”是明末清初的伊斯兰译著家们影响深远的选择。他们这种“回回附儒以行”的译著活动,客观上也是为了使伊斯兰教适应中国传统社会现实的适时选择。因此,汉文译著家们首先要从理论上来阐述“以儒诠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宋明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认为世界的本体是“太极”或“无极”,被称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更是认为:“(太极或无极是)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柢也。”(注:(宋)朱熹:《太极图说解》,载《丛书集成初编》周濂溪集,卷之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太极与万物之间是“由体而达用,由微而至著”、“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注:(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75页。)因而,在朱熹看来“太极”是万事万物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还特别强调:“所谓太极者,只二气五行之理,非别有物为太极也。”(注:(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65页。)明末清初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家们将周敦颐和朱熹的这种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吸收过来,借用来阐述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教义。只不过是在汉文译著中“太极”已并非“本然之妙”,(注:(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70页。)“气”也不能依据太极的动静之理而生阴阳,进而由阴阳化生万物了。汉文译著家们认为“造化天人运行理气者”(注:(清)刘智:《天方典礼》卷三〈识认篇〉,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乃是“真主”。“真主不凭一物而造化天地万物,始于无极,成为太极,化为水火。”(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三〈四行〉,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即所谓“真一乃造化之原主,无极乃万命之原种,太极乃万性之原果,两仪乃万形之原本。……真一有万殊之理,而后无极有万殊之命,太极有万殊之性,两仪有万殊之形。”(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三〈格物〉,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也就是说“真一”(或“真宰”)才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原因。并且“真一本然非从所生,亦无从生,无似相,无往来,无始终,无处所”。(注:(明)王岱舆:《正教真诠》上卷〈真一〉,广州清真堂刊本,余振贵点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尽管在朱熹看来“太极”也是“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注:(宋)朱熹:《朱子语类》卷第九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69页。)“太极”和“无极”在汉文译著家这里还是降到了从属于“真一”的地位。这样,汉文译著家们为他们“认主独一”的伊斯兰信仰披上了宋明理学的外衣。同样,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也被汉文译著家们用来“穷理”和“体道”。《清真指南》中有“万物之理,莫不尽付于人”和“心能格万物之理”的说法。(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三〈格物〉,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页。)刘智也认为:“夫致知格物,乃万学之先务也,不能致知格物,而曰明心见性,率性修道,皆虚语也。”“圣人曰:明己,则明主矣,是谓认主,先以认已为要也。”实际上正如刘智自己所说的“吾教致知格物之学,以认识主宰为先务焉”。(注:(清)刘智:《天方典礼》卷三〈识认篇〉,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可见,宋明理学家和汉文译著家都强调“格物致知”,但理学家的目标是“穷理”,汉文译著家们却是要“认识主宰”。此外,儒家的“人性论”思想也被汉文译著家们“拿”了过来,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朱熹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都是汉文译著家们所关注的重点。王岱舆的“天赋人格差等思想”与儒家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观念似出一辙。朱熹的“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而言,是至善的,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但是具体表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就会与不同的“气”相结合而显示出善恶有别的“气质之性”。人们应该“善反之”,以求得存“天理之性”,最终达到“明明德”。汉文译著家们把程朱理学的这种个人道德修养方式用来类比穆斯林的“认主”“体主”的过程,所谓“正学有三:曰‘大学’,曰‘中学’,曰‘常学’。大学者,归真也;中学者,明心也;常学者,修身也。归真可以认主,明心可以见性,修身可以治国。”(注:(明)王岱舆:《正教真诠》上卷,正学广州清真堂刊本,余振贵点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身不修,不可以明心。心不明,不可以见性。性不见,不可以合天。”刘智这种“勤德敬业”“穷理尽性”“克己完真”的“三乘”修炼法即是一个典型。(注:(清)刘智:《天方典礼》卷一〈原教篇〉,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马注认为:“性有二品:一真性,二禀性。真性于命同源,所谓仁、义、礼、智之性;禀性因形始具,乃火、风、水、土之性。”“惟凭学问之琢磨,才智之参想,明德之分辨,方可复命归真。”(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三性命〉,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1-92页。)然而,汉文译著家们对宋明理学中违背伊斯兰教理的观点毫不犹豫的予以扬弃。王岱舆就反对二程和朱熹的“性即理”或“性便是理”的观点,认为这样就是“认性为主”,不符合伊斯兰教的“神造人性”观。王岱舆强调“性气皆异”来批评的宋儒的“理同气异”和“气同理异”观。他认为之所以使“理性中自有殊异”(注:(明)王岱舆:《正教真诠》上卷〈迥异〉,广州清真堂刊本,余振贵点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乃是由于真主的前定。也就是“若论性命之本体与情用,均出真主之造化。”(注:(明)王岱舆:《正教真诠》上卷〈性命〉,广州清真堂刊本,余振贵点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7页。)
对于直面社会现实的译著家们来说,中国传统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思想是用来阐述“圣教五功”的有力工具,这样广大穆斯林可以将教门的“五功”与生活现实中的“五典或五伦”相互对照。刘智说:“圣教立五功,以尽天道,又立五典,以尽人道者,天道人道,原相表里,而非二也。”“人伦之理本乎三,而尽乎五。三者,男女也、尊卑也、长幼也;五则,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也。”(注:(清)刘智:《天方典礼》卷十〈五典篇〉,〈总纲〉,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智除将伊斯兰教法体系中的念、礼、斋、课、朝称为“五功”外,还将有关社会伦理关系的内容称为“五典”,“五典者,乃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常经,为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礼也。”(注:(清)刘智:《天方典礼》卷十〈五典篇〉,〈小序〉,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智在这里将穆斯林的“五功”“五典”与中国传统社会“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联系起来。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也将伊斯兰教的“五功”(王岱舆称之为“五常”)与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结合起来,他认为“五常”之首曰念,念念不忘于真主,“若饮水思源,不忘于本”,这就是正教记念的“仁”,即“仁寄于念”;“五常”之二曰施,无论是“己之施”,还是“物之施”都是正教之“义”,也就是说施的举动可以称之为“义”;“五常”之三曰拜,“礼拜真主”,“礼拜君亲”,就是“中节之谓礼”;“五常”之四曰戒持,“戒者戒自性也,持者持智慧也”,懂得并遵行“戒持大义”才可以称得上“智”;“五常”之末曰聚,“聚会之谓约,全约之谓信。”“平生一次朝觐天房”是穆斯林与主的约定,是“正教聚会之信也”。(注:(明)王岱舆:《正教真诠》下卷〈五常〉,广州清真堂刊本,余振贵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2-87页。)《正教真诠》中还有这样的话:“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注:(明)王岱舆:《正教真诠》下卷〈真忠〉,广州清真堂刊本,余振贵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五典说”是儒家思想在中国伊斯兰教义中的反映,汉文译著家们认为“五功”与“五典”同样重要。所谓“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敦崇五典,人道尽矣。”(注:(清)刘智:《天方典礼》卷一〈原教篇〉,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穆斯林既要完成念、礼、斋、课、朝“五功”,也要遵守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五典”。只有这样,穆斯林的义务才算是圆满完成。实际上“尽人道,即是尽天道。未有尽天道,不始于人道者也。”(注:(清)刘智:《天方典礼》卷十一〈五典篇〉,〈子道〉,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十分关键的步骤,也是汉文译著家们的重大贡献之一。
由此看来,在理论上汉译经典不仅可行,而且回儒之间本来就可以“相通相籍”。接下来的一个现实问题是伊斯兰经典中有关教法的内容如何与当时社会世俗法相协调。白寿彝先生认为,明末清初穆斯林汉文译著活动中,特别是王岱舆至刘智阶段。译著者的“兴趣几全限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的方面”。(注: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明末清初的汉文译著家们对伊斯兰教法的“选译”或“择译”也是“回回附儒以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伊斯兰教法产生于中世纪的阿拉伯社会,它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现实,即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体系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明末清初的伊斯兰学者在译介伊斯兰教法时,他们有意识地进行着内容和方法的取舍和选择。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来自教外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能使回回穆斯林树立教法和世俗法相协调的观念。他们翻译教法著作一般都不是全文翻译,而是有意识地作了选择。刘智在《天方典礼》的《例言》中说“礼法原有全书,因其浩繁,特择什百之一二”。这样有选择的翻译处理方法就是要避免在教民心中产生“教法”与“世俗法”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刘智的“礼乘”(即舍礼二,刘智将阿拉伯语中伊斯兰教法的专用术语shari'ah音译为“舍礼二”)是“总载天道人道,一切事功之条例”,(注:(清)刘智:《天方典礼》卷一〈原教篇〉,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这里的“天道”是指“敬服五功”,“人道”是指“敦崇五典”,再加上“一切事功”。可见,刘智的“舍礼二”包括了伊斯兰教法的全部内容。
对一个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法不仅约束着他的内心观念,同时也约束着他的外部行为。法律、宗教和道德伦理的一体性是伊斯兰教法的显著特征。以“真主”名义降示的“经训”,大多强调“劝善惩恶”的效用,人们在最后的“末日审判”中有不同的归宿,要么进“天国”,要么入“地狱”。在汉文译著中,这些已经觉醒了的伊斯兰学者试图给穆斯林勾画出依据经训的规范和条例,他们将“顺命或逆违”真主的赏罚推向道德法庭,推到遥远的“末日审判”。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指出:“夫归回后世,得者永得,失者永失。非若今世善恶杂处,祸福均受,可以侥幸其得失。”(注:(明)王岱舆:《正教真诠》〈后世章〉,1931年中华书局刊本,余振贵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更为重要的是,从“真主之明命,合当地之风俗”(注:(明)王岱舆:《希真正答》,余振贵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5页。)的圣训出发,汉文译著家们还不断提醒教民要遵守世俗法律,忠于世俗君王。刘智在《天方典礼》中说“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念主而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注:(清)刘智:《天方典礼》卷十二〈臣道〉,张嘉宾等点教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马注的《清真指南》中有:“人极之贵,莫尊于君。君者,所以代主宣化,摄理乾坤万物各得其所。”“命曰‘天子’,天之子,民之父也。三纲由兹而始,五伦由兹而立。”(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五〈忠孝〉,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212页。)应当指出,提倡遵守世俗法律有利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有利于穆斯林融入到社会现实中。
清康熙时的内阁学士徐元正在给刘智《天方性理》写的序中说:“中国将于是书复窥见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则是书之作也,虽以阐释天方,实以广大吾儒。”另一位清初人景日盻在给《天方典礼》写的《一斋书序》中也说“(刘智)能折衷于六经,研辨于性理大全,深得儒者精微之奥旨”。兵部侍郎鹿祐的序文说:“清真一教,来自天方,……予向疑其立教在吾儒之外,”等到他读了刘智的《天方典礼》后才知道“清真一教,不偏不倚,直与中国圣人之教理同道合,而非异端曲说所可同语者矣。”鹿祐前后态度的变化正可以说明刘智编译《天方典礼》已经起到了宣传和解释伊斯兰教的积极效果。同样,清初何汉敬在给王岱舆《正教真诠》写的序中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汉文译著家们在“以儒诠经”的时候没有忘记用伊斯兰思想来分析问题,在伊斯兰和儒家思想两种因素中,他们是“以伊斯兰为体,儒家为用”(注:孙振玉:《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比如,汉文译著中常借用儒家的“天”字来指“真主安拉”,但儒家经典中“天”的内涵和伊斯兰教造物主“安拉”并不一致。所以他们强调:“吾教事主之外,凡主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曰事主非事天也,作此志者,或以万物莫尊于天,故以天之名称主,非曰即主也。阅者于事天拜天等语,俱当以天字作主字观,慎勿作天字观也。”(注:(明)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载,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二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印。)
“以儒诠经”和“回回附儒以行”是中国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一次思想交流,它显示了伊斯兰教的适应性,反映出伊斯兰教义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协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融合”。明末清初回族伊斯兰学者的汉文译著活动是伊斯兰和儒家两种文明对话和沟通的最初形式,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伊斯兰汉文译著家们顺应时代潮流和民族历史发展趋势,面对社会现实做出的自觉选择,它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所谓“经不通儒,不能明修齐治平之大道;儒不通经,不能究原始要终之至理”(注:(清)马注:《清真指南》卷之十〈慎蒙童〉,余振贵标点,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5页。)正是这种对话和沟通后得出的结论。这说明“我国回族伊斯兰教,虽然长期以来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体系,但却有积极融入我国社会现实的重要一面,它(指汉文译著活动)也更深刻地反映了,广大回族穆斯林也早已把自己融入到中国社会之中这一事实。”(注:孙振玉:《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121页。)从此,伊斯兰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的本土化、中国化是汉译伊斯兰教典籍和经堂教育活动产生的重要背景;同时伊斯兰教经典的汉译和经堂教育的逐渐兴起客观上传播和扩大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影响,使许多非穆斯林,特别是封建士绅在观念上了解甚至是认同了伊斯兰教义。这样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成果又反过来促进了伊斯兰教经典汉译和经堂教育的开展。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汉译伊斯兰教经典和经堂教育的逐步展开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本土化进一步深入的重要表征。明末清初回族伊斯兰学者汉译经典的出现,“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回族形成(和发展)这一历史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汉文译著家们在他们的译述中)也以他们个人的创造性贡献直接而及时地推动了回族民族思想意识的发展,从而也推动了整个回族历史的发展。”(注:孙振玉:《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32页。)他们“以儒诠经”的基本思想“也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探讨到了一条适宜的道路”(注:孙振玉:《王岱舆及其伊斯兰思想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所以说“‘以儒诠伊’是我国文化史上一项独特的、合乎客观需求的创造,使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与外来的阿拉伯文化交流和融合,它的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注:林松、和:《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91页。)
标签:中国伊斯兰教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回族论文; 明末清初论文; 清真饮食论文; 阿拉伯文论文; 古兰经论文; 波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