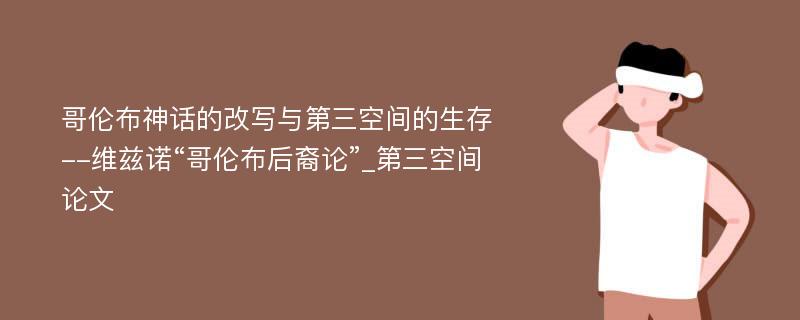
哥伦布神话的改写与第三空间生存——评维兹诺的《哥伦布后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伦布论文,后裔论文,神话论文,空间论文,评维兹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1934- )是当代美国最重要、最多产的印第安裔作家之一,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美洲土著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等奖项。在创作中,维兹诺一方面致力于解构白人文学经典“臆造并维护的浪漫的、悲剧性的刻板印第安身份”,另一方面“把印第安部族神话和当代政治有机融合,创造出有关解放和生存的恶作剧者寓言”(Blaeser 262-63)。维兹诺认为,白人话语中的“印第安”①是“来自西方的错误字眼”,体现着白人殖民者对美洲土著的歧视和主宰(Vizenor,Manifest Manners Vii)。为了帮助当代印第安人摆脱殖民者强加于他们的刻板悲剧形象的桎梏,维兹诺提出“后印第安生存”(postindian survivance)这一概念,以“后印第安勇士”(postindian warriors)形容“具有同情心的、喜剧性的……凭借机智和幽默取胜”的印第安恶作剧者(Bruchac 292-93),以“生存”(survivance)“形容当代印第安生存是幸存(survival)、承受(endurance)和抵抗(resistance)的复杂结合体”(Tillett 122)。1991年,在西方世界准备隆重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前夕,维兹诺发表了《哥伦布后裔》。在这部作品中,他从印第安视角出发,运用戏仿手法改写美洲发现史,把自哥伦布抵达美洲以来白人与印第安人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颠倒过来,并进而塑造出一组哥伦布与玛雅人混血后裔的恶作剧者群像,通过他们对“第三空间”(Bhabha 39)的构建,形象地诠释了他对当代印第安生存的独特见解。
一、哥伦布神话的戏谑性改写
在欧美白人的历史书写中,哥伦布的美洲之旅以及由此引发的地理大发现不仅促成了西欧在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等方面的快速增长,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额的资本和广阔的市场,而且把先进的白人文明带到了依然处于蛮荒时代的美洲,因而,白人史书把哥伦布发现美洲与迪亚士开辟绕好望角航线赞誉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事件”(Sale 3)。但是,在作为美洲原住民的印第安人看来,他们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就已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是哥伦布的美洲之行导致了欧洲白人对美洲印第安文明的灭绝性殖民统治;此后的几百年间,蜂拥而至的白人殖民者迫害、杀戮印第安人,掠夺他们的土地和资源,加上他们从欧洲带来的各种传染病的侵袭,致使印第安人及其丰富多彩的文化濒于灭绝。从这种观点出发,许多著名印第安作家和学者如莫马迪、韦尔奇、吉奥加玛、小狄洛瑞尔、邱吉尔等都对以哥伦布美洲之行为开端的白人殖民统治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和抗议。在他们笔下,哥伦布是一个“导致南美洲、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印第安人被大规模屠杀的罪魁祸首”(Hardin 26)。对哥伦布美洲之行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维兹诺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在“哥伦布的恶作剧者后裔”一文中,他指出,单纯地谴责、抗议白人殖民,会使当代印第安人囿于受害者的属下地位不能自拔,永远生活在对前哥伦布时代的留恋之中,不利于他们在当代多元社会的生存。虽然“作为受害者在政治上的确有好处,但从一个具有治愈能力的好故事中获益更多”(Vizenor,"The Trickster Heir of Columbus" 103)。基于这种看法,他在《哥伦布后裔》中构想出一个荒诞滑稽的故事,试图通过对哥伦布美洲之旅的重写,把印第安人遭受白人殖民征服的悲剧改写成混血恶作剧者的生存喜剧,“以诗意的、想象的方式治愈受害者”(Vizenor,"The Trickster Heir of Columbus" 103),帮助他们摆脱白人历史叙事的羁绊,卸除沉重的受害者心理负担。
在《哥伦布后裔》中,维兹诺设计了并行的两种叙述,把白人历史书写中的哥伦布及其发现美洲的航行与虚构的哥伦布及其混血后裔的故事穿插并置,以后一种叙述质疑前一种叙述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引导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反观历史。前一种叙述所占篇幅不多,主要由有关哥伦布的白人史书、传记、档案等材料的摘录组成。按照这种叙述,哥伦布是一位伟大的探险家、航海家和发现家,他克服种种困难、历尽艰辛,在历史上首次横渡大西洋,成就了发现美洲的丰功伟业,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后一种叙述是从印第安视角出发对白人话语中的哥伦布神话的戏仿:创立人类文明的不是白人而是美洲的玛雅人,玛雅手语者发现了欧洲,“把文明带给欧洲的野蛮人”;哥伦布则是玛雅人留在欧洲的后代,他之所以远航到美洲,是因为他想逃离“旧大陆②的死亡文化”,回到祖先的家园,因而他的美洲之行不过是归家之旅(9)③。不惟如此,维兹诺接下来讲述了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后的故事。他遇到一个叫做萨玛娜的印第安手语者。这个手语者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从此他的后代便在美洲世代生存繁衍,并在五百年后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故事在篇幅上占据绝对优势,对书中零散出现的白人历史叙事形成合围,构成整部小说的主体。
在小说中,维兹诺让前一种叙述穿插点缀于后一种叙述之间,“在不同的叙述风格、叙事视角之间纵横驰骋,恣意地剪裁破碎,或进行反讽模仿”(博埃默 236),把貌似真实公正的白人历史叙事肢解为湮没于印第安叙事之中的碎片,借这种方式表述自己对欧美白人史书中哥伦布神话的质疑,向白人历史叙事的权威性提出挑战。与此同时,维兹诺在后一种叙述中以戏谑笔法重新书写历史,突出表现了美洲印第安文明之于欧洲白人文明的领先性。按照维兹诺的描述,“是玛雅人最早创立了世界文明……首先想象出这个宇宙”,他们把心灵视作想象力和部族文明的中心,把太阳描绘为宇宙的中心,以日心说推翻了当时流行于旧大陆的地心说,把算术、历法等传授给了旧大陆的白人(25-26)。几百年来,诸多白人史书所记载的均是欧洲白人如何发现新大陆,如何给当地的蛮族带来文明,而维兹诺的叙述所彰显的却是高度发达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如何传播到旧大陆,玛雅手语者的“生存印记和血脉中的故事”(28)如何把那儿的白人从蛮荒时代的黑暗中解救出来。借助这后一种叙述,维兹诺颠覆了几百年来白人历史叙事所构建的白人与印第安之间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更耐人寻味的是,维兹诺反复强调了两点。其一,在欧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白人从美洲印第安文明承继颇多,但却“从来没有按时偿还”他们所欠下的“文化债务”(26)。这一说法不仅否定了白人历史叙事着意渲染的印第安人的落后和野蛮,而且巧妙而隐晦地讥讽了欧洲白人受惠于美洲印第安文明却矢口否认、知恩不报的行为。其二,欧洲白人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旁支后裔,甚至“耶稣基督和哥伦布都是玛雅人”。哥伦布在玛雅母系祖先的生存印记引导下远航美洲,耶稣也是在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光辉映照下才得以开创基督教的精神事业(26-27)。借助对欧洲白人与美洲印第安人关系的戏谑性改写,维兹诺把几百年来白人文化与印第安文化之间文明与原始、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颠倒过来,推翻了白人历史叙事所蕴含的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偏见和歧视,引导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认识历史。
维兹诺不仅以印第安视域中的文学想象改写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白人历史记录,而且把白人话语中哥伦布的高大形象贬黜为一个欧洲大陆“死亡文化”的受害者,一个疾病缠身的卑微小人物。在维兹诺的笔下,哥伦布的生殖器先天畸形,“无论是手淫还是性交对他都是痛苦的折磨”,甚至于“一想到性交立刻就会感到疼痛”(31)。他前往美洲既非受西班牙王室之命远航探险,也非出于基督教徒的天降使命感,而是受到蛰伏在自己血液之中的玛雅人故事的驱使,到祖先家园去寻找“能够帮他解除隐秘痛苦魔咒的女人”(31)。当他历尽千辛万苦抵达美洲时,肢体已经残缺不全。一群印第安药师用烤热的石头为他修补躯体,把他重新创造出来。而“有着蓝色手掌和金色胸脯”的印第安手语者萨玛娜用自己的美艳和情欲治愈了他的病痛,“从儿时起一直折磨着我[指哥伦布]的隐秘痛苦就此终结”(38)。更意味深长的是,萨玛娜的激情释放出潜伏在哥伦布血液中的玛雅故事,“解放了他的灵魂”,使他领悟到玛雅人留给他的“生存印记……在精神上真正回归新大陆那条伟大河流的源头”(38-39)。借助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维兹诺消解了白人话语赋予哥伦布的耀眼光环,把那个立志“为基督教王国开辟通往财富的新路”(33)的伟大航海家、探险家和发现者描画成一个滑稽可笑的形象。他在欧洲大陆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病痛折磨,迫不得已冒险前往美洲,到祖先家园去寻求救治良方,最终在印第安女人的怀抱中获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解放。在白人殖民话语中,是来自欧洲的白人“创造了”土著,“教会他们讲话,教会他们思考”,因而前者理所当然对后者拥有绝对的主宰权力(Said xviii)。但在维兹诺笔下,来自欧洲的哥伦布却被描写成一个需要印第安人关注、重构甚至拯救的弱者,这样一来,自哥伦布抵达美洲以来白人与印第安人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以哥伦布为代表的白人跌落到被动的、从属的地位,而长久以来被白人话语贬斥为原始、野蛮的印第安人则恢复了美洲大陆拥有者和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在《哥伦布后裔》中,通过对白人历史叙事中哥伦布神话的戏仿和改写,维兹诺嘲弄了宣称白人是美洲发现者的白人殖民话语,推翻了白人对美洲土著的主宰。琳达·哈琴认为,“戏仿亦是一种必要的创造进程,在此进程中,新涌现的形式赋予传统生命活力,开拓出新的可能性”(Hutcheon 50)。同样,维兹诺的戏仿性改写,为当代印第安人重新审视历史“开拓出新的可能性”。几百年来,在白人话语中,美洲印第安人是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应当被高度文明的白人征服、甚至消灭。这种白人种族主义立场不仅影响着白人,也被相当多的印第安人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因而,他们总是在怀念往昔,怀念哥伦布到来之前的印第安传统生活方式,把自己的民族视作注定消逝在白人文明进程中的牺牲品,而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必然导致印第安人把自己放在白人属下的位置上。维兹诺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白人叙事的戏仿,打破了这种束缚印第安人的思维定势,引导他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构历史、恢复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按照他在小说中的叙述,当欧洲人还处在蛮荒时代时,玛雅人来到欧洲,给他们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美洲文明;而当欧洲文化已经堕落成“死亡文化”时,玛雅人的后代逃离欧洲大陆,返回美洲,寻求新的生存。因此,欧洲和美洲的开拓和发展都应当归功于美洲印第安人。借助于这种戏仿和改写,维兹诺帮助印第安人“打破一切束缚”,摆脱“他们自己血缘的羁绊”(Hochbruck 275),把他们从边缘的、从属的地位解放出来,在嘲讽与戏谑之中抹去了白人强加于印第安人思维的受害者印记,抚平了几百年白人殖民给印第安人留下的精神创伤。
二、混血印第安人的第三空间生存
作为混血印第安作家,维兹诺一方面承认当代印第安文学作品中“祖先传统的丰富记忆……对白人主流文学形成抗衡”,另一方面对印第安文艺复兴所提倡的返回祖先土地、回归部族传统的归家范式持有不同看法,认为这种对本真传统的回溯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白人臆造的印第安身份的回归,可能导致当代印第安人“陷入主流文学设定的他者情境”(Vizenor,"The Ruins of Representation" 22-24)。因而,他在创作中舍弃印第安文艺复兴的归家范式,转而“关注印第安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妥协与交融”(邹惠玲 丁文莉49)。的确,无论人们对哥伦布的美洲之行如何评说,历史都无法逆转;而且,由于长久以来的白人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所有的文化都交织在一起,没有一种是单一的、纯粹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糅的、包容异质的、离奇变异的、混合而成的”(Said xxv)。自哥伦布抵达美洲以来,印第安人长期处于属下地位,在血统、身份和文化诸方面都“与白人搅和在一起而无法分开”(博埃默 263)。对于这一点,维兹诺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哥伦布后裔》中,通过一群哥伦布混血后裔在当代美国社会中探寻第三空间生存的故事,表现这些“后印第安勇士”一方面抵制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从未完全置身于殖民情境之外”(Krupat and Elliott 142)的生存喜剧。
维兹诺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具有鲜明的印第安恶作剧者特征,《哥伦布后裔》亦是如此。小说一开篇,维兹诺就通过讲述“富于同情心的部族恶作剧者娜娜波兹霍”创造世界的故事,巧妙地界定了混血后裔们的恶作剧者身份(5)。而后,他不仅描写了这群混血恶作剧者独特的行为方式,而且突显出他们在当代社会艰难生存的窘境。与侧重表现印第安人遭受白人内部殖民的印第安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不同的是,维兹诺笔下的混血恶作剧者们承受着来自白人和印第安部族的双重敌视和歧视。一方面,聚居在密西西比河源头附近草原上的混血后裔们始终坚持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屡屡与白人当权者发生冲突。例如,他们从神圣的药袋、哥伦布和庞克洪塔丝④的遗骸中汲取想象力,凭借“在语言游戏中解放心灵”的恶作剧者故事医治族人的精神和肉体伤痛(82)。但白人为了利用印第安传统文化“盈利和娱乐”(79),霸占了药袋和遗骸。虽然后裔们最终以恶作剧者方式夺回了这些东西,恢复了讲述故事的能力,但也付出了包括生命在内的沉重代价。另一方面,混血后裔们的恶作剧者行为方式也让恪守传统的印第安部族首领觉得无法容忍,他们甚至把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冲突归咎于后裔们讲述的故事。尤其是当混血后裔们在药袋和庞克洪塔丝遗骸问题上与白人发生争执之后,部族政治家们认为,他们“给保留地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成千上万的白种病人和残疾人涌到保留地看病”,扰乱了保留地的安宁,于是“决定解除混血后裔们的部族成员身份,把他们逐出部族”(120)。借助这种对混血恶作剧者们遭受两面夹击的描绘,维兹诺反映了在“美国政府以‘血缘份额’或者‘血缘比率’把美国印第安人的个人和政治身份系统化、固定化”(Allen 94)的情况下,混血印第安人较之纯种印第安人更为艰难的处境。他们既不为白人所容,无法在主流社会立足,同时在保留地也找不到安身之处,因为那些自以为坚守传统的部族首领们拘泥于白人主流所界定的印第安他者身份,把混血印第安人排斥在部族群体之外。
具有创新意义的是,维兹诺并未停留在描写当代美国社会中混血印第安人的两难处境这个层面,而是着力描绘混血后裔们如何借助印第安恶作剧者传统跳出文化夹缝,开拓第三空间,构建一种新型的印第安恶作剧者生存模式,并以此回馈世界,在多元文化的杂糅中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存。按照维兹诺在小说中的描写,由于遭到白人和部族首领的两面夹击,混血后裔们在美国本土无法生存下去,于是在斯通·哥伦布的带领下,移居到阿斯尼卡角(Point Assinika),在1992年10月12日即哥伦布抵达西半球50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筑起一座“比自由女神还要高”的“自由恶作剧者雕像”(122),成立了一个“没有监狱,没有护照,没有公立学校,没有传教士,没有电视,没有税收”(124)的混血恶作剧者国家。维兹诺笔下的这个国家在多个层面上体现着霍米·巴巴所谓的“文化杂糅的刻写和表述”(38)。首先,这个国家“位于华盛顿州的塞米阿摩和加拿大的温哥华岛之间的佐治亚海峡中”(119)。不仅使混血后裔们摆脱两国白人政府的管辖,避开部族首领的干扰,而且赋予他们自由自在探寻杂糅身份的“第三空间”。其次,这个国家“抵制血缘份额、种族身份、部族注册等观念”(162),不以印第安血缘比率或者是否在某个部族注册作为标准,既接纳所有认同印第安身份的人,也收容来自其他各个种族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创立这个国家的混血后裔们拥有已经相传五千多代的玛雅手语者“生存基因”(119),他们把这种“部族生存的基因密码”(132)传递给从世界各地前来加入混血恶作剧者国家的人,使他们化身成为玛雅手语者的混血后代:“德国人最终继承了苏人的基因,成千上万不愿继续做白人的金发女郎,可以变成霍皮人或者奥吉布瓦人”(162)。于是,在这个国家里,来自各个种族各个国家的人汇合成一个杂糅体,构建起一种基于印第安生存印记、且包容多种异质的普世部族身份。这样一种身份不仅超越了白人话语设立的主宰与被主宰者的二元对立框架,而且“抹去作为歧视手段的历史差异”(Hardin 45),把美洲土著遭受白人殖民的悲剧转化为一种体现着世界大同理想的生存喜剧。
维兹诺不仅描绘了在这个混血恶作剧者国家里人们和谐共存的喜剧场景,还突出表现了混血恶作剧者们如何凭借着印第安传统与现代科学的有机结合,在“第三空间”中探求适合当代印第安人的新型生存模式。维兹诺在小说中多次提到,旧大陆的文化已经堕落成“死亡文化”,那儿的各个民族在肉体和精神上都伤痕累累,而美洲由于几百年来一直处于殖民统治的阴影之下,也正在走向衰亡。最为严重的是,象征着人类未来的孩子们遭到“抛弃”、“虐待”和“毒害”,濒临死亡(147)。与上述情境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维兹诺把混血后裔们的恶作剧者国家描绘成医治创伤、拯救人类的希望之地。由于这个国家拥有洋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印第安生存印记,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将其视为理想的研究基地,纷纷来到这里从事“基因疗法和生物遗传”的研究(122)。与其他印第安部族坚守本真、敌视白人、摈弃现代科技的态度截然相反,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混血恶作剧者们为白人科学家的研究提供各种便利,协助他们运用高科技手段把部族生存的基因密码植入伤病者体内。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在更深的层次上,这折射出维兹诺对于当代印第安生存的独特见解。在他看来,印第安人尤其是混血印第安人若要获得有意义的生存,就不能囿于印第安本真传统,一味因循守旧,而应当与时俱进,“把具有破坏性的文化冲突”转变为“对差异性的接受”,“将过去、现在、未来混杂起来,把殖民者文化也带入其中”(Ashcroft,Griffiths and Tiffin 35-37),在与白人主流既冲突又联手的矛盾共存中构建出包容异质的新型印第安生存模式。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消解了“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Bhabha 116)中,虽然白人的现代科学技术与印第安传统生活方式互为影响、互相渗透,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混血恶作剧者。在维兹诺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科学家仅仅是治疗的一个组成部分”,“最重要的治疗者”是混血恶作剧者们自己(164)。在植入基因密码的同时,他们给那些伤病者讲述恶作剧者幽默故事,为他们举行部族典仪。这些典仪和故事构成一种能够激活部族基因密码的能量,它们与基因密码共同发挥作用,治愈了伤病者们的肉体和精神疾病。这种叙述彰显了印第安恶作剧者在“后印第安生存”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虽然这些混血恶作剧者认可并接受异族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但他们并未因此放弃自己部族的传统。相反,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恶作剧者幽默故事和典仪承载着强大的印第安生命力,只有凭借它们,才能“粉碎白人至上的妄言以及印第安性的刻板表现”(Gruber 97),才能在“过去与现在、本土与西方的杂糅”(Ruffo 7)中把握主动权。按照维兹诺的叙述,正是由于混血恶作剧者们继承并创造性地运用了作为印第安传统文化载体的故事和典仪,他们才能够不仅成功地治愈几百年白人殖民的精神创伤,而且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界限,把强大的印第安生命活力注入来自世界各个民族的伤病者,赋予他们新的生命(146)。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哥伦布后裔们与恶魔温迪戈的对决,维兹诺进一步彰显出“过去与现在、本土与西方的杂糅”(Ruffo 7)对于第三空间中后印第安生存的重要意义。温迪戈是奥吉布瓦部族传说中的一个恶魔,他企图在赢得鹿皮靴赌局⑤之后,毁灭整个部族,但在最后的紧要关头,冰女神把他冻住,拯救了奥吉布瓦部族。以这一传说为架构,维兹诺设计了恶魔温迪戈与混血恶作剧者的鹿皮靴赌局。不过在他的叙述中,温迪戈是印第安传统意义上的恶魔和白人种族灭绝政策的结合体,他是“被政府解了冻”的,“如果温迪戈赢了,”混血恶作剧者国家将面临灭顶之灾(179-180)。而混血后裔们为了阻止温迪戈猜中答案所采取的那些恶作剧手段,既具有鲜明的印第安传统特色,又明显植入了白人主流元素。例如,他们藏在鹿皮靴下面的既有他们部族传说中最致命的武器“战争草”(war herb),也有印着哥伦布头像的白人钱币,这两种不同文化的东西增加了猜中答案的难度,使温迪戈迟迟做不了决定。又如,当温迪戈苦苦思索究竟哪只鹿皮靴下面藏有东西时,他们以各种恶作剧方式捉弄温迪戈,有的“用蓝精灵捕手和熊爪旗帜奚落他”(180),有的击鼓吟唱,还有的假扮成正在现场直播的记者,举着麦克风采访他,使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思考。尤其是当温迪戈即将拿起那只将会给这个恶作剧者国家带来灭顶之灾的鹿皮靴时,混血恶作剧者们并未因大难临头而惊慌失措,更没有试图以强力阻止温迪戈,而是凭借恶作剧者的语言游戏和现代科技制造出来的激光影像,促成温迪戈放弃赌局。他们的首领斯通·哥伦布调侃温迪戈,假如他拿起那只鹿皮靴,那么随着人类的消失,他不仅再也享受不到鹿皮靴赌局的乐趣,而且将永远地失去自我:“如果没有后裔们和孩子们来让你恐吓,你将变成什么?……即使是恶魔也需要人类”(182)。与此同时,被称作“激光恶作剧者”(82)的阿尔莫斯特·布朗借助白人的技术在天空中展现出耶稣、哥伦布、疯马⑥、黑麋鹿⑦、瑞尔、庞克洪塔丝⑧等人物形象,并让这些人物围绕着自由恶作剧者雕像翩翩起舞,这一情景让温迪戈感到“赌局永远不会结束”,心甘情愿地“退隐到暗影中”(183)。
维兹诺所设计的这个结局,强调了印第安恶作剧者对于当代印第安生存的至关重要。作为印第安传统的一个重要构成,恶作剧者特有的行为方式突显出印第安人特有的幽默:“戏谑是印第安人控制社会局面的一种方式”(Deloria 147)。在诸多印第安传说中,当理想的平衡被打破时,往往是恶作剧者借助嬉闹、狡黠的恶作剧手段,重构万事万物的和谐。小说中的混血恶作剧者亦是如此,面对意欲毁灭人类的温迪戈,他们坚信“在自由恶作剧者雕像下没有什么会输掉”(179),依靠恶作剧者传统成功地挫败了对方的企图。然而,在“传承印第安传统文化”的同时,维兹诺笔下的混血恶作剧者亦“被赋予鲜明的时代特征”(丁文莉 29)。在与温迪戈的对决中,他们不仅创造性地运用白人的激光技术,把白人的救世主耶稣和哥伦布等形象改造成一种对付温迪戈的恶作剧手段,而且让他们加入由印第安首领、先知、传奇人物等组成的行列,成为自由恶作剧者雕像的拥戴者和属下。混血恶作剧者的这种做法表明,他们并不否认与白人文化的共谋:相反,他们“不断把本土与侵略者的文化创造性地编织成一体”(博埃默264),凭借着融入了异族文化和现代科技的新型恶作剧者传统,大大增强了自身的生存能力,在印第安传统和白人主流既冲突又联手的矛盾共存之中构建当代印第安生存的新型模式。
在《哥伦布后裔》中,维兹诺讲述了一群混血恶作剧者在第三空间中探求生存之路的故事,形象地诠释了他本人一贯倡导的“后印第安生存”。通过对哥伦布美洲之行的戏谑性改写,他表达了当代印第安人抵制白人殖民、挣脱白人历史叙事羁绊的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在消解印第安与白人二元对立的同时,他着力表现杂糅了不同民族文化遗产的“后印第安勇士”的强大生命力,“寓言性地表现了文化杂糅之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邹惠玲 丁文莉 49-50)。虽然我们不应当把文学形象与作家本人等同起来,但如果把《哥伦布后裔》中的混血后裔们与维兹诺的出身经历比较一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他笔下那些混血恶作剧者形象反映出他本人的双重文化视角。和他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一样,维兹诺是印第安人与白人的混血后代,他的父亲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白土地”保留地,有一半印第安血统,一半白人血统;他的母亲则是白人。维兹诺不到两岁时,他父亲便被人谋杀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维兹诺有时在保留地和祖母一起生活,有时离开保留地去母亲那里,有时又住在收养他的白人家中。长大以后,他曾在美国军队服兵役,退役后先后进入纽约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学习。这种复杂的出身和经历,促使维兹诺在创作中不断地寻求、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他把自己称作“跨血缘(crossblood)恶作剧者”,并通过他所塑造的一系列跨血缘恶作剧者形象,致力于为自己、也为当代混血印第安群体重新确立文化归属。在论及欧洲移民作家和本土作家时,后殖民批评家博埃默曾经指出,“这些作家致力于建构一个‘真正的’或有根基的自我属性时,便发现自己身处与欧洲文化形式既冲突又联手的局面之中”(131)。在表现混血印第安人的第三空间生存时,维兹诺同样将自己置于与白人文化既冲突又联手的矛盾共存之中。借助于跨越文化边界的写作,他表现印第安与异族文化的冲突、交融和共存,言说当代印第安人与美国社会主流文化平等共存、重构包容异质文化身份的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构。
注释:
①维兹诺用小写、斜体的“indian”代指白人话语中的印第安人,具体请参见Joseph Bruchac,"Follow the Trickroutes:An Interview with Gerald Vizenor," Survival This Way:Interviews with American Indian Poets(Tucson:U of Arizona P,1987)292。
②小说中英文为“The Old World”,指欧洲。
③本文所有相关作品引文均出自Gerald Vizenor,The Heirs of Columbus(Hanover: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1),以下仅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④庞克洪塔丝(Pocahontas,1595-1617),印第安酋长帕瓦坦之女,嫁给白人殖民者约翰·罗尔夫(John Rolfe),后来随他前往英国并皈依基督教,最终因患上天花病逝于英国。
⑤鹿皮靴赌局是印第安奥吉布瓦部族的一种赌输赢游戏。对阵双方互相猜测对方在四只鹿皮靴之中哪一只下面藏着东西,以猜中者为胜方。
⑥疯马(Crazy Horse),印第安苏族首领,以作战勇敢而著称。在印第安战争中,他指挥的印第安人歼灭了白人将领卡斯特率领的军队并击毙卡斯特。
⑦黑麇鹿(Black Elk),印第安苏族先知,以《黑麇鹿如是说》一书而知名。
⑧路易斯·瑞尔(Louis Riel),加拿大梅提斯人(原住民与法裔加拿大人的后裔)的领袖,因领导抵抗加拿大政府的暴动而被处死。
标签:第三空间论文; 印第安人战争论文; 神话论文; 美洲文明论文; 印第安文明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大航海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