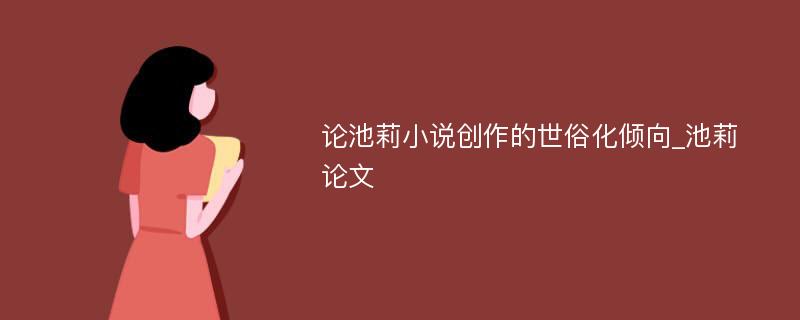
论池莉小说创作的世俗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俗论文,倾向论文,小说论文,论池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一批小说家专注于重建世俗世界,着力表现凡人、凡俗的生活,再现生活的原本色相和人的原生状态,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所不同,他们的作品因此被称为“新写实小说”。而池莉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她的小说创作所体现的鲜明的世俗化倾向成为新写实小说创作的标识,同时,也预示着九十年代文学精神的变异和分化。
一
池莉在创作中站在体验者、观察者的立足点上,从理想彼岸的想象回到现实此岸的审视,选择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主要视角。正如她所说:“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入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观点。”(注:池莉.我.花城.1997(5).)因此池莉的创作视点下沉,鲜明地体现出“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倾向。
在对平民世俗生活的叙述中,池莉选择了“细节仿真”的切入方法,注重对现实日常生活进行精确的模仿和复制,但又并非简单化的“镜子式”的表现手法。池莉认为自己的小说“全部都是重建的想象空间。不要在读小说的时候犹如身临真实生活就认为作家是站在大街上随意写的。有一种想象叫仿真想象,它寻求的是通过逼真的诱导,把鼓点敲在人的心坎上。”(注:池莉.想象的翅膀有多大.池莉文集(4).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从池莉的作品中, 我们可见她对现代人的生活苦相和窘态的揭示均借助于大量的平民化生活的日常琐细细节,而且突出强调真实性,诱导读者进入仿真想象中,从而与作品达成默契。比如她的代表作品《烦恼人生》描述的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印家厚的一天生活经历:吃饭、赶车、上班、干家务、带孩子、睡觉、做梦……作者描摹的是一种原生状态的生活情况,不少生活图景显得纷乱、琐屑,而且非常逼真,确实,作品中没有怪诞的事件、传奇的情节,更没有抽象的理念,只有生动、自然化的生活图景。又比如《太阳出世》从赵胜天夫妇的婚礼写起,然后描述了他们孕育、抚育孩子的全过程,同时叙述了这对年轻夫妇与各自父母兄弟乃至社会的复杂关系网及其情感纠葛,故事中的细节如同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平实,作者没有在事件中隐含什么独特含义,也没有特意凸现什么典型意义,总之池莉所展示的是社会和人性的原始之象。而正是这种“真实”和“原始”的呈现姿态往往令读者产生震撼的感觉,它打破了读者平日内心不真实的幻觉,让读者醒悟到自身的当前处境,因此,池莉的小说对日常生活流程进行还原描述时,展示了主人公的生存境况和情绪状态,同时也呈现出当代人的普遍存在和精神困境。
日常生活的细节是世俗生活的真实背景,也是作家传达生存体验的情境所在。纵观池莉的作品,对笔下人物的日常生活状态的理解都聚集在“世俗关怀”中,这种关怀主要是对普通人的当下境遇的关怀,对个体生存的物质幸福的关怀,与人文主义者强调的“终极关怀”有所不同,更突出“世俗化”的特征。作家注视着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尽量淡化社会历史背景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的社会冲突,淡化标志着不同社会形态的带有本质性的社会关系。作家着重表现了生活中的平庸、琐细、凝滞和灰暗,以及这种沉重而又无所不在的沉闷氛围对人的灵性和生命的窒息,权力网、关系网和无尽的生活烦恼对平凡人的围困和磨炼。作家深切感悟到日常生活中诗意的消解,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于是她把一种世俗化的平和的生活渴望溶入世俗性的文化语境中,以关怀、体谅之心来祈祝生活更合符平常人的心意,因此,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和行动往往抱以包容性和宽厚性的理解和尊重。比如在她的小说《云破处》描述了一桩发生在子夜里的复仇血案,手刃死者金祥的正是他的妻子曾善美,而作者又为这一出表面看似不合理的案件设置了合情合理的源由,曾善美手刃亲夫是情势所迫,因为金祥十一岁时往家乡工厂的食堂的汤里扔了一条河豚的内脏,导致曾善美父母双亡以及后来她被人污辱的生活悲剧,而金祥心安理得地欺骗了她二十多年;对于金祥来说,“投毒”并非蓄谋杀人,只是因为工厂占了农民的土地又不让农民的孩子进去玩,这更象是一场恶作剧。按常理,本来曾善美了解真相后可以报案,金祥也可以主动忏悔并去自首,但作品让两位主人公在黑色的夜晚中进行灵魂之战,撕裂了往日的温馨情爱,当他们的命运悲剧真相大白时,灵魂冲突也达到了极端,最终只能用毁灭来结束这场悲剧,但白天平静的日常生活又掩盖了黑夜里的真实残酷,曾善美最后并未受到法律的追究。在作品中,现行的伦理判断标准已模糊,只剩下合情合理。由此可见,池莉的创作淡化了旧有话语强烈的宣谕性和教化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体恤民心的温情和认同。
日常生活是文学形象存在的生活区域。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日常生活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当个人的人文目的与社会现实冲突对立时,知识分子便隐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于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常生活便充满诗情画意,成为诗意人生的象征;另一方面,当知识分子以强烈的入世精神去进行社会改造,行使启蒙责任时,又会否定、批判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日常生活又意味着某种消磨理想斗志的庸俗化的人生模式。而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徘徊于日常生活的肯定或拒绝之中,这预示着知识分子对终极理想的追求和实践的历程。直到八十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处于精英文化的失望状态,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从社会启蒙中心位置返回到个人天地中,理想的失落加上生活的烦恼和焦灼令他们消解了生活的诗意,对理想彼岸的怀疑和逃离又使他们产生了从众倾向,他们于是平和地把日常生活实在化,既不把它处理成诗情画意,也不把生活视作平庸。在池莉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梦醒后的平淡,“只剩下一个愿望,好好过日子”。在这种日常生活的表述后面,道出了当前知识分子主体定位的迷惘,他们在日益商品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中难以确立自己的位置,于是不自觉地与公共性的日常生活准则融合,以“活着就好”,的生存态度为迷失的自我寻找一条逃避的途径。
池莉的小说在近似“零度情感化”的创作中,包含了对世俗日常生活的悄然认同以及对日常世界的现行秩序的肯定。显然,这是一种世俗化的创作倾向。
二
评论者在谈到新写实小说的人物时,多数会用“非典型化”来概括。确实,池莉笔下的人物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的典型人物有很大不同。在对日常生活的写实性描述中,庸常的世俗凡人成为了主角,他们的精神定位和内涵也充分体现了池莉创作中理想主义话语的沉沦和鲜明的世俗化的社会价值取向。
池莉面对市场经济的商业时代,把作品中的人物置于具体化的世俗生活舞台中,人物的情感体验和生活态度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纵观池莉的小说,她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日常化、平庸化的生活画面,平凡、琐细,往往令人压抑,磨损人的心志,同时不带理想主义色彩。池莉摒弃乌托邦的想象,把这种日常生活形态逼真化、写实化,揭示普通人在失乐园后的尴尬境遇。且看,在《烦恼人生》中,印家厚必须面对住房条件的窘迫、上班行程的艰难、工作环境的人事纠纷等问题的困扰,对他来说,孩子既是他对未来的希望又是沉重的负担,蛮横粗俗的妻子既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又令人厌倦和遗憾,年轻真诚的女徒弟让他既心动又进退两难,可以说,印家厚艰难地扮演着各种生活角色,而这种种角色既给他带来无尽的烦恼又让他在承受责任中不断成熟。池莉在作品中制造了一种苦涩的现实生活氛围,点明了普通人的日常生存状态。
池莉笔下的人物面对生活实际境遇,经受了现实的冲击,表现出从不平衡逐步趋向平衡的心理历程,同时以特定的方式应对生存烦恼,坚韧地生活着。
池莉小说的凡人在琐碎困窘的俗世中遭遇着个体与外在环境的冲突,这种永恒的对抗关系往往让他们产生一种焦虑感,于是他们常有一种困惑、苍茫的感慨,比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在上班的轮渡上,“伏在船舷上吸烟,心中和江水一样茫茫苍苍,”“莫名的感伤情绪和喷出的轻烟一样弥漫开去,”而且当同事们争论起名人的名气、地位和待遇时,他心中“愈加苍茫”,而且“忿忿不平”,心理极不平衡。但对于生活中的不如意不合理,这些普通人并未表现出改造世界的热情或反抗命运的激情,他们只是挣扎在苦恼人生中,想行动又甘于现状,浮躁心态也逐步转向顺应环境后的平衡状态,这种心理转化意味着他们的困惑和痛苦逐步消解。
生存的目的决定着生存方式和生存态度,池莉为主人公设计的生活目标是“活着”,这是一种“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达观知足的心态,而且在他们看来,生存目标的实现更多是指向世俗的物质欲望的满足,同时能在家庭与社会中保持安稳状态。为了寻找心理平衡的支点,池莉笔下的人物主要是通过解构理想来逃避现实矛盾,进行自我排解,最终抑制个性,随遇而安。
在池莉众多小说中,无论是写历史生活题材还是当前“过日子”的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都有一条或深或浅的主线——爱情与婚姻,更确切地说,是两性关系。作为女作家,池莉并不象陈染、林白等人着意表现女性解放的意识和女性性别体验,她更多是以中性意识着重审视两性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成长历程和生存状态,小说最终表达的现实生活内容远远超过了情爱内容。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通过解构理想实现了普通男女在适应困境中寻求平稳关系的目的。本来,爱情是人性内在的诗性显现,在所有小说题材中爱情是最具有诗性品质的,它是人的内在心灵的诗意栖居,作家们在表现爱情时,往往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有的甚至是超越凡俗社会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而在池莉看来,爱情首先应附丽于现世生活,因此她的创作摒弃了爱情的诗性想象本质,淡化了浪漫主义情怀,更加强调两性间基于欲望的情爱的社会化内容,特别是突出了义务、责任等社会结束力的影响,池莉把两性关系表现得更加理智化、实际化,爱情在她看来是水中之月,她就是要使主人公从这种带有理想色彩的梦想中清醒过来,正如池莉为一部作品取名“不谈爱情”,目的正是要解构爱情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内质,把两性关系拉回到日常生活的世俗化原则中来审视,并因此确立平衡的支点。在文本中“不谈爱情”是作家对两性关系的理解和态度,其中包含了两个层面:一是强调两性关系中的生活法则,二是粉碎爱情神话,逃离理想的爱情。这是一种世俗化的生存逻辑。
在《不谈爱情》这部小说中明显地体现出作家对爱情理想的解构以及对现实生活法则的认可。作为知识分子的庄建非在与小市民出身的妻子吉玲吵架后清醒地发觉自己的婚姻并非与众不同,“揭去层层轻纱,不就是性的饥渴加上人工创作。”吉玲当初为了走出自己粗俗破落的家,为了出人头地,看中了庄建非的家庭背景,他们第一次相遇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吉玲包里掉出的“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的故事》,手帕包着的樱花瓣、零花钱和一管香水”赋予吉玲一种浪漫的色彩,给庄建非留下优雅纯情的印象。在恋爱中,吉玲又巧妙地排除了家庭出身问题这一障碍,并与家庭配合演了一出好戏,最终令庄建非堕入网中。整个恋爱过程对于吉玲来说是个精心预谋的“人工创作”,而庄建非成为她预谋的目标。吉玲婚后为得到丈夫和庄家的充分重视,又与娘家一起闹出一场闹剧,甚至闹到庄建非单位,惊动了庄家,并直接威胁了庄建非的前程,吉玲最终原形毕露,当年樱花树下的美好记忆成了带有讽刺意义的一幕。但她胜利了,迫使庄建非从迷梦中惊醒,重新正视现实,重视作为丈夫的责任、义务;认识到婚姻并不是单纯的两性间的情感维系,也不是理想化的空中花园,而是现实的,充满实用意义的,它是一种多重的社会契约,于是庄建非在这场婚姻危机中终于认可现实法则并在妥协中找到了平衡点。
很明显,池莉把家庭婚姻设置在社会秩序中,直面世俗婚姻的同时意味着理想爱情的溃退,相对于稳固的现实生活形态来说,爱情是脆弱的,这也是对理想世界的一种拒绝。池莉的小说《来来往往》正是一个范例,男主人公康伟业便在婚姻与爱情的抉择中尝尽了理想破灭的伤痛。在他的生活中先后出现的四个女人象征着他人生道路的四个阶段。戴晓蕾是少年康伟业的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迷梦,是甜蜜而又带有忧伤的青春烙印,因为错过而成为遗憾,却成为一个永远留恋的理想之梦。而妻子段莉娜使康伟业开始了实际人生,由于段家原是高干家庭,曾给予康伟业不少实际恩惠,因此段莉娜一直居高临下,而康伟业则处于被动和压抑状态,两人关系并不平衡,直到康伟业下海经商,经济条件大大改善,而段家开始没落,两人关系再次不平衡,段莉娜并未改变自己以适应外界变化,而是用蛮横手段干涉丈夫的事业和生活,两人情感距离越来越大。这是一段无爱情却实实在在在的婚姻现实。于是,康伟业只好从明髦的白领丽人林珠身上寻找情感寄托,经过几番你来我往的感情“揉搓”,他们从商业合作的关系转为情人关系,在缺乏爱情的物质环境中,他们都认为自己奇迹般地拥有真正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谁知,当康伟业历经艰辛与妻子打一场离婚战,同时准备与林珠共同步入理想中的完美婚姻殿堂时,林珠却无法与他过“通俗”的日常生活,爱情与婚姻之间形成巨大的鸿沟,他们只能在脱离世俗的理想世界中相爱,最后曲终人散,爱情之梦“破于旦夕之间”。之后,康伟业与第四个女人时雨蓬的关系变得“非常地简单”,两人之间只有调侃、取乐,不曾有过真正的感情交流,没有痛苦和忧伤,也失去了往日的激情,彼此只有金钱交易,康伟业虽然感到很轻松但这又是一种不能承受之轻。从康伟业与这四个女人的来来往往的关系,我们可见他在理想与现实间的彷徨,康伟业始终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的支配,正像他始终无法抛弃段莉娜一样,段莉娜代表着一种稳固的日常生活形态;而他与林珠的浪漫情爱虽使他的理想之梦得到满足,但它却经受不起现实生活的敲打,显得虚无脆弱;此外时雨蓬恰恰隐喻着商业社会理想主义彻底败落的境况,小说结尾,康伟业再次“回到了他日常的忙碌的生活中”,意味着康伟业和印家厚、赵胜天等人一样最终抛弃浪漫的理想情怀,对寻找精神支撑完全绝望后回到原地——凡俗生活,这部小说成为了反讽爱情理想的现实文本。
池莉的另一部小说《绿水长流》则成为逃离爱情的典型注本。这是一篇专写爱情的作品,男女主人公邂逅于富于浪漫情味的庐山,作家却并未让他们上演一幕理想化的传统爱情故事,因为女主人公“我”面对情感诱惑一直在理智地规避。作品中随处可见作家对两性关系冷静地阐释,她把爱情神圣的面纱毫不留情地揭去,并把它放逐到世俗人生中,同时以自觉的疏离态度进行解构,从而真正顺应庸常的、缺乏理想色彩的现实生活,达到心灵的平静。在池莉其它小说作品也可见这种对爱情理想的逃离姿态,在《你是一条河》中忙于生计的寡母辣辣在苦难岁月中拼命挣扎,为子女耗尽心血,这个孤苦的女人却从不曾陶醉于虚幻的爱情之中,特别是与钟情于她的小叔子一直若即苦离,永远无法沟通,因为一个耽于实际,一个耽于幻想,理想化的爱情是不合适辣辣的生活原则的。《烦恼人生》中印家厚对女徒弟雅丽虽然有点心动却拒绝了她的感情;在他看来,老婆“憔悴、爱和他扯横皮”、“粗粗糙糙”是一种遗憾,但他还是接受这个事实,摒弃了“花前月下的爱情,精神上微妙的沟通”的幻想。《不谈爱情》中庄建非在择偶时不选择浪漫的高知家庭出身的王珞而选中耽于实际的吉玲,对比之下,因为吉玲更符合现实生活的要求。池莉的作品通过主人公在理想爱情与现实婚姻之间的抉择显示出世俗化的价值取向:瓦解爱情神话,结构理想世界。
由此可见,池莉的小说揭示了平凡人在现实苦境中挣扎,为了适应现实生活的秩序,他们在不平衡的状态下解构理想,从而顺应了环境,并获得了平稳的生活状态和平衡的灵魂世界。
池莉创作中表现出的“固定而实际的人生观”往往在直面人生的同时也使人们溺于庸常的日常生活,从对生存困境的不满转为对生存困境的亲和顺应,这不仅表现在她的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中,甚至在她的历史生活题材“沔阳系列”(如《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凝眸》等)中主人公对政治历史风云变幻的理解也是耽于实际,从普通人的角度阐释出个人在历史中的渺小、无助,以及荒诞的历史给平凡人的命运造成的荒谬、无常的结局。总的来看,池莉笔下的人物放弃了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个性的磨损和反抗激情的失落,没有对命运的反抗,没有对生存困境的超越,也就导致了池莉小说缺乏真正的悲剧精神,因为“美学上悲剧并不在于展示人生不幸,呈现生存困境,而在于它通过对困境、不幸、苦难的刻意表现,代表了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反抗命运的方式,体现了一种人生态度,一种超越困境的态度。”(注:刘永泰.悲剧的缺失——对新写实小说的美学检视.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1).)从根本上说文学的本质精神正是在与现实的抗衡中产生出来的,如果放弃了艺术精神的对抗特质,自然就缺少悲剧精神。将理想放逐也导致池莉小说创作的世俗关怀只是停留在平民生存的现实需求层面,没有进一步探讨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方向,也就缺乏对人的存在性必要的深层探析。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适应只能证明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不能也不应成为生存的最高目标,适应确实是人类的需要,但是,在生存关系中,发展人类自身,完善自我,也就是如何创造更适宜于人的生存条件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机制。因此,“就人类最理想的人性来说,应该是有利于人类生命存在和更有益于有助于人类发展的价值系统和精神心理动力”(注:何锡章.中国现代理想人性探求.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而理想正是一种完善和改进人生的强大的精神心理动力。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卡西尔在他的著作《人论》第五章中就指出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理想与现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在他看来,人的生活世界之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生活在“理想”的世界,总是向着“可能性”行进,而不象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特别是在当前商品化的经济社会中,传统的价值观正处于重构阶段,困顿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缺乏的正是理想信念的支撑,因此,作家应在世俗关怀的同时加强理想的引导力量,树立生存和发展相统一的世俗观,打破中国人头上的各种宿命论的精神枷锁,变消极的被动的无为的生存方式为积极的主动的有为的生存方式,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更为强大,具有“争天抗俗”的力量,形成强健的社会生命意识,让人们获得既在自然社会环境中独立于自然环境之上的品格,体现出人的生命特征。
池莉小说创作在表达人的存在问题时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她的世俗化写作也一度成为创作时尚。在告别了以往先锋小说叙事的艰涩和超验、贴近民众的同时,作品中平实的世俗价值观和摒弃理想、顺应环境的人生态度又限制了池莉小说的精神品位,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现实困境面前的退却姿态。作家在创作中若只能停留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中,这样对人物的刻划也只停留在性格表层性格,削弱了自身的艺术表达空间。因此,当前的作家应该改变“不可承受之轻”的零度创作状态,强化时代的精神体验,通过对人物的文化心理的阐释与批判抒写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转型期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趋势,将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时代的生活风貌、精神境遇结合起来,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
从池莉的世俗化写作可见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创作精神的分化状态。作家逐渐从一种“共同的话语”世界中分化出来;他们的写作立场、精神追求、艺术表现形式更属于个性特征,各自构造着自己的写作空间。池莉在分化中确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她只有在对艺术个性的自觉追求中以丰富的内在精神执着地抵抗市场经济社会的外在负面冲击,并逐步形成博大的人间情怀和深刻的艺术灵魂,真正的富有艺术性的好作品才能实现,池莉才能在两个世纪的转折时期再创辉煌。
收稿日期:1998-0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