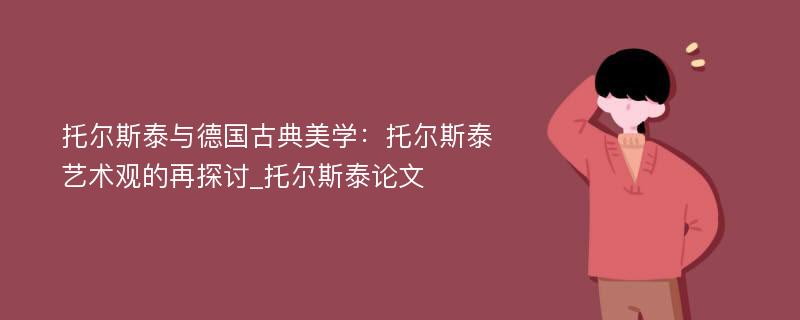
托尔斯泰与德国古典美学——托尔斯泰艺术观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尔斯泰论文,德国论文,美学论文,古典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曾对托尔斯泰的美学观点作过现象上的某种考察,本文拟从他和德国古典美学的承续关系对他的美学作一个哲学的探讨。
以康德、黑格尔和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古典美学对托尔斯泰有重大的影响。托尔斯泰关于美和艺术的本质论,建立在对黑格尔等人真善美“三一体”思想的批判基础上,他批判所用的工具,近似康德等人的双重认识论。托尔斯泰对康德哲学(部分地包括美学)的首要缺点,即未将自在之物对于主体也是客体形式明确加进主体认识之中的认识,与其说是从谢林美学,不如说是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中得到启发的。
一
托尔斯泰在写作其主要美学著作《艺术论》的过程中(1882-1897)激烈反对真善美“三位一体”,说“把这三个完全不同的、就意义来说甚至是不能比较的字和概念结合为一,纯粹是一种幻想”①。在他看来,美是我们一切热情的基础,而善往往是和热情的克制相符合,美和善不相容;美的主要条件是幻想,而真大多揭穿诈伪,美和真也不相容,善是我们意识的本质,它不能用理性判断,而能判断其他一切,善与真、美也各不相同;真是事物的表达与它的实质相符,或者与一切人对该事物所共有的理解相符合,因此真是达到善的手段之一,但它本身既不“善”,也不“美”。这里要指出,托尔斯泰在写作《艺术论》期间,对美和美的艺术基本上是否定的。这和作家的前后态度不合。1908年,他向人承认,“认为美毫无意义,这是可惜的错误”②。此时,他认为可用某种感情判断任何一部作品,而这种感情却能和善相通。他在同年的一则日记里写道:“第二次听演奏时就一个问题想了很多:我用某一种感情,某一种情绪去解释任何一部(音乐——译者)作品,把它纳入语言艺术领域,结果是有感动,有快乐,有激情,有惊惶,有柔情,有精神的美,有庄严,有忧郁,以及其它等等,只是没有一点非善意的因素:没有凶狠、谴责、讥笑等等。艺术的审美描写何以能如此呢?”③他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他毕生在思考,并有其哲学根据的。
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托尔斯泰的哲学文字看,他偏重人的主体研究。他把哲学界定为生命的科学,认为研究人的生命力的内涵与指向,是哲学的主要对象。他在《哲学的目的》(1847)提出的这个任务,可视作他理论研究的方向:“我们还不能理智地发现真理,但我们可以预感到它,因此我要阐明生命的法则”④。托尔斯泰在这里提出的两种实体(存在)观,一种是能用理智把握的,另一种则不能用理智把握,却可以预感到它。理智能把握的是一种什么实体?作家的看法大致是这样的,他在《论在我们所了解和认识的生命之外的灵魂及其生命》(1875)一文中,认为理智能把握的有:无机界,有机界那种遵循和无机界一样法则的自然法则,而有机界那种按照另一种法则发生的生命现象则不为我们的理智所理解。换言之,“生命对无生命的关系——(理智)能理解”,而“生命对生命的关系,我们不能靠理智理解,却能从内部直接地充分认识它,认识物(生命)自身”⑤。他在《论生命》(1886-1887)一书中,从人类理性意识角度确定人生命的内涵,所以该书在扩大理智的把握范围的同时,更加明确理智的认识作用有限。它认为人的生命固然同动植物(有机体)和物质这两种存在形式相联系,但人却不能参与这两种存在形式,因为“构成了人体的肉体和物质总是自为地存在的”⑥。如此,人的理智固然不但能把握物质规律,而且也能发现植物、动物以至人身上那种观察得到的生命现象,但是却不能揭开人身上那种没有自我的努力便不会实现的生命的秘密。而这种秘密只有靠人的“内在认识”才能理解。总之,作家认为理智能把握的是那种表现于时空关系中的事物,而那些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都不能确定的东西,理智不能把握。这种不能把握的东西托尔斯泰称之为“在我们所了解和认识的生命之外的灵魂”,而理智,他曾一度如此看重,视之为人类灵魂的主要特征,他后来认定它“只是释放、表现灵魂的实质——爱的工具”⑦。
托尔斯泰在提出两种实体论的同时,把灵魂的概念视作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真实。他说:“灵魂的概念是生命的概念”,如果不认识生命,不认识统一体,我们非但不能认识生物,也不能了解任何非生物;”⑧他断定,唯有意识到自己是有生命的有机统一体这种意识才是真实的,而其他方面的知识,如动物界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我们在自我中所知之物的影子了,而物质界更是影子的影子了。这种从人的生命概念考察真实性的方法表明,托尔斯泰把人的认识机能提高到人心意机能上来认识。这样他就从黑格尔返回康德,不像黑格尔那样把心灵本质归结为思考,而把人心视作“思维的我”和“感性理解的我”⑨的对立统一。这里说的“感性理解”,相似于康德说的“内直观”,托尔斯泰则称之为对自己意志的自在自为的意识,对组成自己生命实质的意识,内心完全自由的感觉⑩。而“思维”类似于康德的广义的“知性”,即包括把握能力、抽象能力和思考(反思)能力在内的一般认识能力。托尔斯泰运用该字(сознателъностъ)也是指人认识真理的健全的思考力,相当于他经常运用的另一词“理智”(paзym)。他认为“理智是生命器官的生命之产物”(11),它对生命意识来说是受动者,所运用的物质、力量、空间、时间、原因、结果以及数、圆等认识客体事物的概念无非是人自身生命意识的抽象化,所以理智的认识是派生的、间接的、相对的;同时理智必然要寻找事物的因果链,为此它要探索事物的时空关系,因此它的表现形式是必然性。与之相反,“感性理解”既然是一种不凭借感觉器官的直接感知,作为它对象的自由意志不能给定义,因为它本身就包括空间,并且处在时间之外,不受因果链约束——它是因,也是果,所以它不但不服从理智,而且每每和理智的认识相对立。托尔斯泰举例说,我们心灵对日蚀所产生的黑暗的感觉,破坏了太阳是发光体这个常识。
这样说来,前后两个“我”的对立,表现于人的认识(知识),用康德的话,是客体的自然体系与主体的自由体系的对立,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则是必然与自由的对立;表现于人的心意,用康德的分类,是认识与欲求的对立,而用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就是“脑”和“心”的对立,用词极为相似。同时在这双重对立中,托尔斯泰和康德都一样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康德),两者“互相排斥”(托尔斯泰)。他们都一样认为这两者的认识或实践对象分别、单个地看都是不可认识的,只是在康德看来,不可知的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自在之物”,而在托尔斯泰看来,虽然可用感官感觉到但不可领会的单独存在的自然力(如引力、惯性、电力、兽力等)和可以意识到但还不能了解的自由力(生命力、意志、爱——“爱就是生命本身”)。至于这双重对立间的关系,托尔斯泰和康德的看法虽说有重大分歧——康德从整体上否定自然概念对自由概念的影响,而托尔斯泰肯定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但他们在肯定自由概念对自然概念的影响上却是惊人地一致。康德认为“精神是人心中灌注生气的原则”,主体里超感性的东西能够规定感性的东西,而判断力则是沟通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桥梁。托尔斯泰区分出人身上的两种认识机能——“必然力”和“自由力”,他不但看到这两种力的对立,还指出自由意志对必然力的制约。他说的判断力也具有中介性质。一方面,判断力由领悟——重新接受力发展而来,它是人高级的必然力;另一方面,意志对领悟——重构力、想象力和判断力本身必然发生影响,出现了接受判断、想象判断和意志判断,实现了必然向自由的转化。由于这些相似性,托尔斯泰和康德一样,都在寻找美学这样一个“作为自然界基础的超感觉界和在实践方面包含于自由概念中的那些东西的统一体的根基”。不过,正是在是否承认自然概念(“必然力”)对自由概念(“自由力”)影响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托尔斯泰又把他的美学和康德的美学区别了出来。
二
自鲍姆嘉通(1714-1762)将美学定义为“感性学”以来,人的心理机能愈发成了美学主体研究的对象。康德把机能看作是“借助它的诸表象而成为这些表象的对象的现实性的原因”,根据这个观点,他把人的心意机能分为:认识的机能,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机能和欲求机能三种。而知、情、意这三种心意机能又和悟性(现译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这三种认识机能相对应,所以康德把美(或美的艺术)看作是介于自然与自由的中间物,是由情感和判断力先于思想(知性)表象出来的理性直观,这种直观在同一主体中同“我思”有一种必然的联系,透露出知性思维无法把握的那自由的整体,即理念。康德和黑格尔殊途同归,他最终也是把美仅仅看作是人的自由精神的产物,真、善、美在他们看来,实际上仍是同一序列的哲学范畴。
托尔斯泰固然和康德一样认为人的精神活力要以意向为前提,竟至断定活力就是不可满足的渴望或内心斗争,而作为人的认识受客体制约,由外界给予,包含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力,就其受动性这一面说,还不能称为有活力的机能,但他并不完全否定这必然力的主动性,说它还不全是一种运动而是具有部分活力,其作用是无限的。托尔斯泰没有象康德那样过分强调自由的主体,从而把必然和自由割裂,而是看到必然中的自由,必然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由。即使在他否定美的积极功能那个时期,他也说:“美既可以与生活现象、道德的和不道德的现象相伴随,又可以与科学知识相伴随,同样也可以与艺术现象相伴随”(12)。托尔斯泰在此指出了美和生活现象同在,这就肯定了美的客观性,否定了把美和真、善视为同属于人的主体性范畴的观念论美学。不过,托尔斯泰在这里像他往常的态度一样注意的不是单纯阐明美的客观属性,而是论证主体在客体自然中建立起来的美(尤其是美的艺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精神属性,即论证美作为主体宾词的客观性。他是怎样证明的呢?
首先要说明,俄文中有两个“美”字,它们虽可互用,但其含义有别。据俄罗斯当代美学家万斯洛夫说,一个“美”(кpacoтa)偏重于现象的形式美,它相当于汉字“妍”;另一个是指现象内涵与形式相统一的整体美(цpeкpacнoe)(13)。托尔斯泰强调美的道地的俄文用法,在他的文论中经常见到他用的是“妍”字,他用此字首先表明“美只不过是使我们感到快适的东西”,美是“直观”到的东西,所以美和对象的形式,和我们对它们的快感密切相关,但是,托尔斯泰在用“妍”字时,不但重视对象的形式,而且注重探索现象的实质——它何以为美,它和人的关系如何,这就把人的主体精神,人对现象的论理评价注入现象之中,他所用的“妍”实际上包含有“好”这一欧洲思想赋予“美”的新意义。这样,美之“直观”本身暗含有知性活动,包含有意志力的倾向,美所引起的快适,不是感官愉快,而是理智化—理性化的情感判断。我们参照托尔斯泰早年哲学文字《无题片断》(“假设人没有欲望……”,1847)(14)对人的心意机能与认识机能的关系的看法,把他所理解的美具有客观性的精神属性,归纳为如下几点。
审美感(“诗的情感”)源于生活的回忆。这个观点托尔斯泰于1852年在他的一份手稿《童年》中提出后,毕生坚持,他的1909年10月14日日记,就有类似提法。回忆在他看来虽然还属于人认识的必然力中的初始力,但已和感官不同。感官印象属于肉体意识,而回忆属精神意识,它不产生于人的身体感受,而是出于人的领悟(或称重新接受)力。托尔斯泰肯定美感不是单纯的物质印象,而是物质的精神现象,或用他的话说,艺术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机能”。其次,在他看来,回忆与其说属于人的精神意识,不如说属于人的情感意识和精神意识中的表象意识。他认为,人们先前思念过的事物,其内容容易忘却,而思念的性质(是忧伤、沮丧、沉重,还是愉快、振奋)和思维过程的情绪转换(如由忧郁而平静),则往往记忆犹新(15);铭刻在记忆里的是性格特性,记忆能把不同的人、物、感情融为一体(16)。记忆的这种带有情感性和某种综合功能的表象能力,决定了审美感的性质,表现在不同的种类的艺术,便有不同特色的审美感。“诗歌的情感是对于饱和着生活形象和情趣的生活的自觉回想”,绘画的情感是“对于形象的回想”,而音乐这种“情感的速记”,由它唤起的“审美感的本质是对情感和情感转换的不经思考的回想”(17)。
审美感依存于想象。托尔斯泰所用“想象”(вooбpaжeннe)一词就其古义是“提供形象、形态、神态”这一点说,其功能几乎等于回忆,所以他把这两者并列为人的领悟力。想象和回忆一样偏重于思维的特性而漠视思维的本质,所以想象仿佛和思维相伴随,有时则会先于思维或后于思维而产生。托尔斯泰的《昨天的故事》就描写了思维和想象交替出现的心理现象,但想象和回忆也有区别,回忆过去固然离不开人对感性存在物的改造和综合,但是预见将来更须对感性存在物实行重大的以至脱胎换骨的改造。可以说,综合在回忆表现为类聚,而在想象已表现为建构——如事物对立属性的统一,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统一,“非我”(人把它称为自然界)和“自我”(人有时把它称为神)的统一。托尔斯泰说艺术家不是靠论据,而是靠拟态(或称拟容等可见的符号)来表达自己的观念,这“拟态”就是想象的产物,是事物的客观属性和人的主体把握相结合的结果,它和客体比较,已是一种变形。这一点,托尔斯泰说他有亲身体会:“抱着描写目的去观察事物的人,事物便在他面前变形”。托尔斯泰在《〈莫泊桑文集〉序言》里还讲到“幻像”在反映生活上的作用,这“幻像”也是生活形象和“作者对事物的独特的道德态度的统一”。也就是在这篇序言中,托尔斯泰把美归结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称美是“我与人们、我与全世界的另一种、另一样的统一”。以上讲想象在改造客体,发现客体美上的能动作用。此外,托尔斯泰认为想象还具有超越事物的时空形式的猜想作用。他认为诗人之所以比预言家还要高出一头,就在于“他提前思考并理解到别人和他自己感觉到”以及“尚未感觉到的东西”。这些都是指超时空的生活。他在1910年1月25日的日记中,就有类似的记载:我“特别生动地思考着关于那只跟爱相结合的现在的超越时间空间的生活”。托尔斯泰在这里已把直觉视为想象,认为人之所以能产生直觉形象,其根源固然不在外界事物,而在人的主体感觉,可是其初始推动力却在外部世界,所以直觉形象就是由人的“精神的视力”对自身真正生命的认识。作家的日记也有类似的记载。某晚,“忽然在黑暗中看见了我真正的生命”;“在你觉得痛苦的时候,要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要去找火柴,而要灭掉那妨碍你看见真正的自我的光”,“我忘记了上帝……把真正的我与糟透了的我混在一起”。这些话表明,理想的审美是感性下超感性的合成,美或美的艺术无非是“感性之超感性”(马克思语)的事物。
在阐释回忆和想象对审美感知的作用上,托尔斯泰和康德、黑格尔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康德和黑格尔都不重视回忆,而看重想象。康德把回忆看作是想象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想象力的功能是“在主观的意图里为再现的手段服务”。他这句话含有唯物主义因素,暗示了在审美领域不存在人无法感知的“自在之‘美’”(他说,“鉴赏力就是在想象力中对外部对象作出社会性评价的能力”),但它的重点是强调想象力的联想规律服务于主观意图,这就表明,他所说的想象,正如他认定的直觉的表象一样,虽然偕伴着感性的符号,却是“完全不含有属于客体的直观的东西”。黑格尔比康德走得更远,他不谈想象力的某种服务于再现手段的功用,而迳直将想象和“心灵渗透到感性事物里去”联结一起。与之相反,托尔斯泰强调回忆的作用,说“生活是真实的东西。人所体验到的一切留在他心中成为回忆。我们永远是以回忆显生的”。他所说的想象力,事实上也以生活再现为前提。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常常是他“和那些被我描写的人物所共同体验到的”,通过人物的“拟容”描绘,他自身的观念每每被克服,他揭露的可能不但是他认为是好的,而且是他热爱的东西。他对超越时空的生活的思考,也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并且“正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实现生活上面”。在他,直觉之产生,也是由生活经验提示的,由现实的我分离出来的。“理性、经验和内心的感情会引导出对于要求思考上帝以及未来生活的人本身的一定的东西”(18)。
审美判断是对客体作用于超感性主体意识的情感判断。我们从审美感的来源已见出审美感的两重性。一种偏重于从感觉器官获得的痛苦与愉快,大体上属于人感官的东西,由物象的形状、色调或音响引起,是对形式美的感受;另一种侧重于精神自由的感知,其情感虽然由客体的影响引起,却源于人对自身地位、尊严和生命的意识,是人的生命意识对客体生命力的回想把握。由于人是一个有机体,在人身上,感官印象,精神意识和理智思考密不可分,生理现象实际上是心理现象的产物,人的任何愉悦和痛苦都产生于人对客体的重新建构之中,而美感,无论是增殖的喜悦,性爱的愉快,“从胃里发出的抒情”(普列汉诺夫语),还是精神的振奋,生活的恋念,献身的渴望都是一种增殖感、再生感、创造感。康德讲美在形式,就是侧重于精神重建,他说,“美是一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这一点,托尔斯泰注意到了。他说,对于康德,比之色彩,他更爱形式;比之女性,他更喜欢建筑物的装饰。这就证实托尔斯泰的一个重要结论:我们平常说的情感或热情就归属于这种重建力,正是它演变判断力,判断力由此具有双重的两重性:作为判断力本身看,它既是情绪判断,又是理智判断——科学知识也是对感觉经验的重建,审美和科学认识相随;从判断力来源看,它固然已是主客体的结合——托尔斯泰说欲望的作用是和感官的影响同时并存的,但由于这种欲望还植根于感官印象,和外界事物与人肉体本身有着密切关系,其客观物质成分仍占较大比重,它虽已是高级的认识活动,但在总体上还只能看作是人认识和审美判断的必然力。要把这必然力发展为自由力,只有跟人的自由意志结合。自由意志在托尔斯泰看来是人的这样一种欲望,它本身自在自足,其存在原因不在外界事物,其表现形式也不依赖外物,它本身也不可能作用于五种感官,不过它影响人的接受力与判断力,而高级必然力赋予自由意志以意向、方针和目的。这种自由意志实际上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的人内心的道德法则。在它影响下,人的理智活动合理化,人的情感或情绪体验理性化,对象的形式“合目的”化,物与人的关系或人际关系伦理化(合乎自由精神),客体存在生物化(化为有生命的存在)——审美活动在这里不但和科学认识同源,而且和艺术思维合一。托尔斯泰因此得出他的另一重要结论:审美感的两重性根源于人欲望的两重性,“美学是伦理学的表现,用俄语说就是艺术表达艺术家体验到的感情”,“艺术是人类生活中把人们的理性意识转化为感情的一种工具”。这里说的内心体验,显然是指从经验出发对善的领悟,而所谓理性意识,固然包含由理智掌握的科学论据,但着重是指人对“善是通向人类联合的标志”的意识。无论是从感觉经验到对善的领悟,还是化理性意识为情感运动(感性直观),都说明美和“艺术是跟事实打交道”,高级的审美判断是对客体作用于超感性主体意识的情感判断。上文提到的艺术审美描写之不能引起人们邪念或恶感而能和善相通,其奥秘似在此。
对审美判断的特点和性质的看法,直接牵涉到对美的本质的理解。从哲学上说,美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是对客体的一种热情,还是对主体的道德意志的意识?托尔斯泰对这些都给以双重的回答,就是说他都是站在对立面的一方来看待并接受另一方的。他一方面把物质看作是精神之物质——说“物质无非是独立于世界的我的表象”,另一方面又把精神看作是物质之精神——认为笛卡尔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只有在我知道我是活着的前提下才是可信的,亦即是我这个物质存在在先,然后才有思维;但这句名言就时间和空间不是先天就有而一切处于运动之中这一点说是错误的,因为离开运动去作某种判断等于空元。从这点出发,他批评黑格尔的观念(非物质的精神存在)论和叔本华的意志论,说它们都是武断的、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一方面把幻想看作是美和艺术的主要条件,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和真一样,都是客体让人在心意上觉得美好的条件。这说明,他说的幻想实际是指对人或物的生命本质的直觉或感性表现。难怪他在给费特的一封信上说,“只有理智显现上帝”,“理智即上帝”。他在这里所用的“理智”(paзym)一词,按其古义是指善解事物的内涵,用在人身上,就是说善于在时空关系中理解人的理性。这又表明在他看来,理想的感性即理性之物质性(物质性即感性),而理性即感性之理性。这就把柏拉图的“理念”具体化为“意型”(按柏拉图的“理念”一词曾译为“意型”),化为事物意义与形式的统一。同理,在托尔斯泰说美是热情的基础的时候,如果把热情仅仅看作是为有形事物所激动,那它自然会和善相对立,但如果把热情理性化,即为心灵所激动,那么它又能和人的自由意志相沟通。这就是说,他说的热情应该是人的道德追求,而人的道德信念应当是精神仰慕。在托尔斯泰这随处可见的近似康德的三分法中,就他强调物质——生活、现实或感性这一面看,他的美论超越了康德、黑格尔而接近费尔巴哈——托尔斯泰实际上和费尔巴哈一样不把美看作是某种类概念的存在物,而是看作人的生命属性的存在物,不过就他强调精神本源——与生活客观法则对立的爱的本源这一面来看,他的美与艺术论从总体上超脱不了康德而更接近叔本华。不过,似应看到他在美与艺术论中所贯彻的三分法,可能为我们揭示审美奥秘提示了某种方向。我们从托尔斯泰的分析中看到,如果把美看成是人生命的一种属性,那么真、善、美是同一的,因为真和善也是人的一种属性;但若单独地看,美独立于人的客观存在——即便直觉中的形象也独立于人这主体的客观存在(或称在时空关系中的存在),这和真与善仅仅作为人的一种精神实体而存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不过,美之客观存在与其说是作为形式,不如说是作为内涵——或者更确切地说形式是作为有意味的形式而发生作用的,因为单凭形式,可能不会引起美感而生邪念和恶感(如“恶之花”),这又将美的客观存在和人的主体精神联结在一起,美的客观性就寄寓在人的主体精神中,美的客观性即合人的目的性,亦即理想性,美的事物在其影响上才和真与善发生共生现象。但这种共生又各有其特点。美作用于人,经人接受与改造之后,仍以“形”而存在,它虽然不是客体的那种单纯的物质,却仍是精神之物质,思绪化的感性。这和真,理智把握的真不同。它虽然也是对客观经验的综合与改造,但其过程是由表及里,舍表取里,真理愈带普遍性则愈加抽象,仅仅从其时空关系的表述上还窥见其客观物质性的特点。对客体的这两种把握方式,不但形成人把握过程中的不同的情绪体验,而且造成美与真对人的超感性实体即自由意志的不同关系。美作用于人之后,既然始终不离形,那么愉悦情绪也始终伴随——审美感总是跟感觉意识到的声音、调式和色彩结构相关,以致可以说,形在即情在。而对于真,人的情感大多附着于对感性经验改造之始,和对感性经验作理论概括之末,而且这种情感,不单有“甜”,而且有“苦”,多属知性的愉快,获得某种真理的满足。这和美感的感性愉悦(源于“形”的感受性)不同。前者是人在思维过程中的感受,后者是在感知对象时的感受。这样,真和自由意志虽然隔着一道“概念”的屏障,却能和善相通,美感虽则能和人的内直观直接相通,但是经常发生由感觉把握到的外在现象和内感官这灵魂的器官产生的诸表象之间的某种不协调。所以美和真不同(它们只是在合人的目的上,因而在是否具备令人满意的条件上是相同的),它是客观对象和人的超感性实体的一种情感关系,而真则是客观规律和人的超感性实体的一种概念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用得着托尔斯泰的一句话:真即善,而善不等于真,也不等于美。
注释:
①托尔斯泰《艺术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63页。
②(17)《列夫·托尔斯泰论文学与艺术》第一卷,135、72页,苏联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135、72页。
③⑦(15)(16)《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七卷《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321、317-318、128-129、246页。译文个别有改动。
④(14)《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一卷,232、233-236页。
⑥托尔斯泰《论生命》,见《天国在你们心中》,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74页。
⑤⑧(11)《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七卷,346页。
⑨参见《托尔斯泰全集》第一卷,226页。
⑩参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尾声第二部第八节。
(12)《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十四卷《文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120页。
标签:托尔斯泰论文; 康德论文; 艺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美学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德国生活论文; 文化论文; 再生活论文; 判断力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