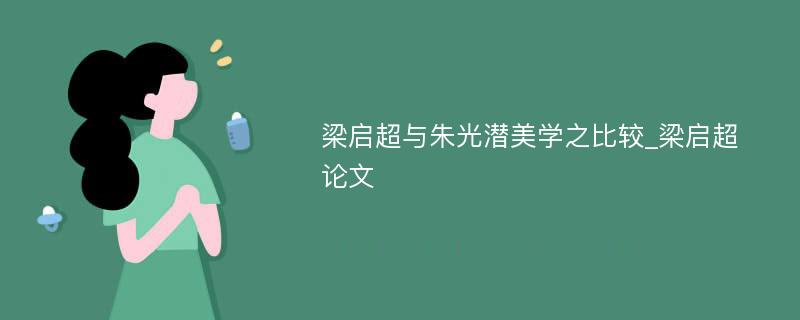
梁启超与朱光潜美学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朱光潜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9.1;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0)05-0023-05
朱光潜与梁启超虽然在年龄上相差整整一代,但他们所面对的西方文化对中土文化的挑战是大致相同的。而且,令人惊奇的是:朱梁两先生在美学思想的许多方面都极为相似,如人生的艺术化和情趣化,白话文代替文言以及适度的欧化;在对科学的态度方面甚至是为学与做人方面也颇相近。无怪乎朱光潜多次谈到幼时读梁任公著作时大受感动的情景。其实,哲学家的灵心妙用多起于对人生的彻悟,生与死、人世与出世这些问题都不断地逼迫着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回答,在我看来,梁先生和朱先生都大致以一种积极乐观的精神予人生以解答。比较两位近现代中国美学大家的思想理趣也是一件极有意味的事。
一、“人生生活于趣味”与“人生的艺术化”
梁启超在《美术与生活》一文里提出了“人生生活于趣味”的观点,朱光潜在《谈美》里也提出了“人生的艺术化”的美学命题。这一前一后,骨子里都是要在苦闷的现实外求解脱,是要拿艺术来激发情趣以对付生活的窘迫,是要拿艺术的观照以求“形象的解脱”。因此,他俩的人生观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反对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
梁启超曾经很打趣地说: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在他梁启超的字典里是没有的。梁启超何以能达到这“仁者不忧”的境地呢?这是因为他深知这个世界、宇宙有不圆满的地方,你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既然如此,你只管耕耘,不问收获,以“无所为而为”的态度对付生活,你的生活便是“纯然趣味化”的了!
应该说,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的人生观多少包含着些佛家空无的意味,是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纯然超脱观点。由于看到人的渺小,能够把小我和宇宙的大我打成一片,也就能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何以会有悲观和厌世态度呢?所以,他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元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甚么就不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的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种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那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①
这里,梁启超的“仁者”的人生观就是审美的人生观,他是把儒家的“仁”、“智”、“勇”分别对应于西方心理学中的“情”、“知”、“意”,所以他说“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梁启超把“仁”和“情”看作一致有无根据呢?回答是肯定的。事实上,孟子说:“仁,人心也。”这其实就是说仁是一种合乎礼义、发而中节的情感,而且这个情感是一个“美情”,是与生俱来的。这与生俱来的“美情”要靠“孝”、“悌”、“忠”、“义”来表达和维护。因此,“仁者”的人生观,也可以说是“情”的人生观。这个“情”不是守着小我,而是把小我溶入大我的宇宙大化中,是“宇宙的人情化”②。
总之,梁启超的“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既是仁者的人生观,也是美情的人生观。他把“美”和“趣”合而为一。他坚信“美”是人类生活的一大要素,甚至认为:“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③
无独有偶,朱光潜提出了“人生艺术化”的美学命题,这和梁启超的“人生生活于趣味”的命题实在是异曲同工。
首先,朱光潜和梁启超一样,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缺陷,并不完美。恰恰是因为不完美,才会尝尽与困难作斗争带来的快慰;也恰恰是有缺陷,我们才会有奋斗的空间,希望和想象就多几分,这个理想的可能空间就是“无言之美”!因此,要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要像尼采那样以日神的光辉把现实的苦难照耀,以“从形象中求解脱”,化痛苦为快悦。相反,如果不是这样,只见这世界落个“悲”字,则易于走绝世之路;或者,只图享尽人间快乐,游戏人生,则易于落得个玩世的名分,甚至更有遁入空门者,则以逃世为终了。凡此种种消极的人生观都有欠缺。朱光潜给的答案是:绝我而不绝世。他说:“所谓‘绝我’,其精神类自杀,把涉及我的一切忧苦欢乐的观念一刀斩断。所谓‘不绝世’,其目的在改造,在革命,在把现在的世界换过面孔,使罪恶苦痛,无自而生。”④ 可见,朱光潜的人生观和梁启超的人生观都以“悲”字开始,以夹杂痛苦的“乐”字收尾,只不过朱光潜更强调人生的严肃的一面。
其次,朱光潜也和梁启超一样,把人生的艺术化和趣味化看作是一种超越小我利害的境界追求。朱光潜说:“文艺到了最高的境界,从理智方面说,对于人生世相必有深广的观照与彻底的了解,如阿波罗凭高远眺,华严世界尽成明镜里的光影,大有佛家所谓万法皆空,空而不空的景象;从情感方面说,对于人世悲欢好丑必有平等的真挚的同情,冲突化除后的谐和,不沾小我利害的超脱,高等的幽默与高度的严肃,成为相反者之同一。……一个对文艺有修养的人决不感觉到世界的干枯或人生的苦闷。他自己有表现的能力固然很好,纵然不能,他也有一双慧眼看世界,整个世界的动态便成为他的诗,他的图画,他的戏剧,让他的性情在其中‘怡养’。到了这种境界,人生便经过了艺术化,而身历其境的人,在我想,可以算得一个有‘道’之士。”⑤
不难看出,朱光潜的这个破“我执”的人生态度和梁启超主张的在生活中体验美就应该具有宇宙“未济”和人生“无我”的情怀,二者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
再次,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特别注重美感经验的分析,在美感经验的分析中,他最看重的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这个“玩索”就是“观照”。他认为:“‘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⑥ 换言之,“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⑦
显然,朱光潜把“趣味”和“欣赏”联系起来,进一步阐述这个“欣赏”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这就和梁启超对“趣味”的定义——“总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终”以及“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是‘无所为而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大概也只是侧重点不一样罢了:梁启超更侧重“趣味”的过程,所以他特别举出了“劳作”和“游戏”;朱光潜则更看重对“趣味”结果(目的)的“玩索”(观照)。
顺便指出,朱光潜虽然在前期美学思想里徘徊于写实与理想、分享与旁观、文以载道与为文艺而文艺、演戏与看戏、内容与形式、联想与直觉等的矛盾中,似乎以“距离”说来调适这些矛盾,主张“不即不离”,但从总体上看,朱光潜更强调理想主义,更愿意把自己放在“看戏者”的行列。这也还是因为“人生艺术化”的精义在于“超脱”,这就是“看”而不是“演”。所以,他说:“谈到文艺,它是人生世相的返照,离开观照,就不能有它的生存。……所以我们尽管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有深刻的情感,若是止于此,我们还是站在艺术的门外,要升堂入室,这些经验与情感必须经过阿波罗的光辉照耀,必须成为观照的对象。由于这个道理,观照(这其实就是想象,也就是直觉)是文艺的灵魂;也由于这个道理,诗人和艺术家们也往往以观照为人生的归宿。”⑧
最后,梁启超的“人生生活于趣味”和朱光潜“人生的艺术化”都是把“情趣”和生命联系在一起。梁启超讲“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实在就是讲生命的创化和生香活意,“趣味是活动的源泉,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⑨。“人类若到把趣味丧失掉的时候,老实说,便是生活得不耐烦,那人虽然勉强留在世间,也不过行尸走肉”⑩。朱光潜也说:“趣味是对于生命的澈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水停蓄不流便腐化,趣味也是如此。”(11) 又说庄子“所谓‘心死’就是对于人生世相失去解悟和留恋,就是对于诗无兴趣”(12)。
由此可知,梁启超和朱光潜都把“趣味”提高到和“生命”一样的“本体”高度。在他俩看来,人生和艺术就是以这“趣味”连接着,倘若艺术缺少了“情趣”,也就缺少了“魂”。而人生(生命)缺了“趣味”,则生如同是死的。也许,我们可以把梁启超和朱光潜前期美学的本体框定在“使情趣成体”的架构里。
二、梁启超的“新文体”和朱光潜理想的“新文学”
周作人曾说过:“在清代晚年已经有对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反动倾向了。只是那时候的几个人,都是在无意识中做着这件工作。来到民国,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才很明白地意识到这件事而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来。”(13) 周作人把梁启超和胡、陈一起看作“文学革命”的先驱,这无疑显出他的慧眼。而在我看来,胡、陈的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革命不免有些过头,倒是梁启超的“新文体”暗示了未来“新文学”的趋向。
朱光潜步入文学的道路,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的。这在他《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里有详尽描述:“我读到《饮冰室文集》。这部书对于我启示一个新天地,我开始向往‘新学’,我开始为《意大利三杰传》的情绪所感动。作者那一种酣畅淋漓的文章对于那时的青年人真有极大的魔力,此后有好多年我是梁任公先生的热烈的崇拜者。有一次报纸误传他在上海被难,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小子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为他伤心痛哭了一场。也就是从饮冰室的启示,我开始对于小说戏剧发生兴趣。”(14)
本来,朱光潜属于“桐城谬种”之列,但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毅然放弃了作了十五年的文言,学着用白话文来写作。应该说,梁启超的“新文体”确如他自己的评价:“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多年之后,朱光潜客观地对梁启超的这个贡献也给予了肯定:“由古文学到新文学,中间经过一个很重要的过渡时期。在这时期,一些影响很大的作品既然够不上现在所谓‘新’,却也不像古人所谓‘古’。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林纾的翻译小说,严复的翻译学术文,章士钊的政论文以及白话文未流行以前的一般学术文与政论文都属于这一类。他们还是运用文言,却已打破古文的许多拘束,往往尽情流露,酣畅淋漓,容易引人入胜。我们年在五十左右的人大半都还记得幼时读《新民丛报》的热忱与快感。这种过渡时期的新文言对于没落时期的古文已经是一个大解放,进一步的解放所要做的事不过把文言换成白话而已。”(15)
虽然朱光潜是处在“新文学”发展时期,但是他对文言和白话乃至欧化问题的看法几乎和梁启超如出一辙。
就文言和白话说,梁启超并不认为白话优于文言,两者都是文字,都是传达思想和情感的工具,只要调和得好,即便是文白错杂也未尝不可。所以,他说:“就实质方面而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文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16) 这里,所谓“好意境”也就是指的情趣和意象的契合,一句话,能够体现生命的活意。
同样,朱光潜也不赞成拿文字的古今来定文字的死活,认为这是某些提倡白话者的偏见,只有“嵌在有生命的谈话或诗文中的文字,无论其为古为今,都是活的”(17)。又说:“文言和白话的分别并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大。第一就写作的难易说,文言要做得好都很难,白话也并不比文言容易。第二,就流弊说,文言固然可以空洞俗滥板滞,白话也并非天生地可以免除这些毛病。第三,就表现力说,白话与文言各有所长,如果要写得简炼,有含蓄,富于伸缩性,宜于用文言;如果要写得生动,直率,切合于现实生活,宜于用白话。这只是大体说,重要的关键在作者的技巧,两种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的手里都可运用自如。我并没有发见某种思想和感情只有文言可表现,或者只有白话可表现。第四,就写作技巧说,好文章的条件都是一样,第一是要有话说,第二要把话说得好。思想条理必须清楚,情致必须真切,境界必须新鲜,文字必须表现得恰到好处,谨严而生动,简朴不至枯涩,高华不至浮杂。文言文要好须如此,白话文要好也还须如此。”(18)
就语言的欧化问题来说,梁启超的“新文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既然是欧西的“文思”,一个民族的思想和语文是分不开的,这样,梁启超的这个提法势必也就要主张部分的欧化。
朱光潜讲得更干脆,他认为如今的白话文不能说尽善尽美,尚须扩充和精炼,其中一个办法就是适度的欧化,因为“西文所有的紧凑的有机组织和伸缩自如的节奏在中文中颇难做到”(19)。
当然,梁启超的“新文体”还不是朱光潜未来理想的“新文学”,“新文学”在朱光潜心目中还只是处于摸索阶段。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里谈到但丁倡导以“俗语”写作以代替拉丁文,这很类似于我国五四时期用白话写诗文以代替文言的境况。朱光潜认为:“白话(相当于但丁的‘俗语’)是否比文言(相当于教会流行的拉丁语)更适宜于表达思想情感呢?白话应如何提炼,才更适合于用来写文学作品呢?这里第一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事实证明:只有用白话,才能使文学接近现实生活和接近群众。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还在摸索中,还不能说解决了,特别是就诗歌来说。因此,但丁的《论俗语》还值得我们参考。”(20)
或许,梁启超的“新文体”的提法还带有颠覆旧文体的性质,而到了朱光潜那里,他更从思想和语言的一致,以及情感的凝炼来深化这一语体的革命,其思路和理趣还是大致相当的。
事实上,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朱光潜,他们的文学革命都是来自于生命情趣本体的外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体”和“新文学”都是“人生生活于趣味”和“人生的艺术化”人生观的体现。
总而言之,梁启超和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有许多共鸣之处,这里不一一对比研究,唯举上述两条,粗陈鄙见聊供同仁参较。
注释:
① 梁启超:《为学与为人》,《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65页。
② 《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0页。
③ 梁启超:《美术与生活》,《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017页。
④ 《朱光潜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75~76页。
⑤ 《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62~163页。
⑥ 《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⑦ 《朱光潜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⑧ 《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⑨ 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
⑩ 梁启超:《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梁启超全集》第7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963页。
(11) 《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52页。
(12) 《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54页。
(13)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0页。
(14) 《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92页。
(15) 《朱光潜全集》第9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25页。
(16) 转引自金雅《梁启超美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5页。
(17) 《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18) 《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45页。
(19) 《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50页。
(20) 《朱光潜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