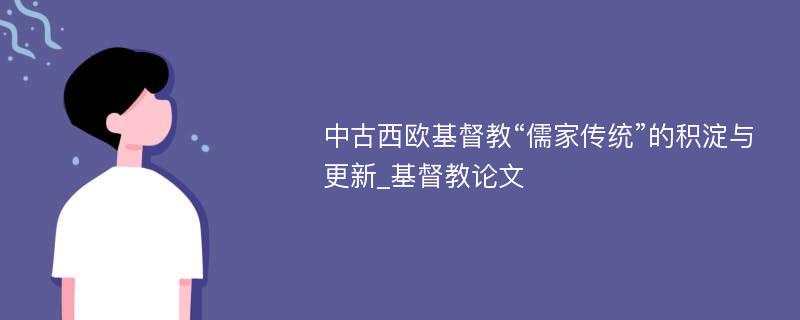
中古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的积淀与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欧论文,基督教论文,经学论文,中古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2)01-0038-07
大凡社会历史的变动,皆与思想文化的演进相互促进与激荡。而思想文化中具有实质 性意义的巨大嬗变,又总是与“经学传统”的发展密切关联。所谓“经学传统”,即是 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或学派在对其崇奉的原始经典进行发掘、翻 译与梳理、释读的过程所形成的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与诠释模式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 在儒家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中都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它的积 淀与更新都无一例外地影响这些文化形态的裂变与重构,进而影响到其所植根的社会历 史发展进程。因此,从基督教的“经学传统”演进的角度来清理“前近代时期”西方文 化的脉络,进而审视它与中古西欧社会变革的联系,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本文仅就所掌 握的材料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
西方的“经学传统”,实际上就是指基督教的圣经学文化传统。自基督教产生后一直 到中世纪的千余年间,历代神学家都极其重视对基督教原始经典《圣经》的翻译、注释 与其神学内涵的发掘、阐证。在这一长期的“经学”过程中积淀起来的“经学传统”, 成为中世纪天主教神学思想的理论源泉。
作为基督教原始经典的《圣经》,本系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2世纪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 的古代传说、历史、宗教律法等编纂而成,直至公元前397年的第三次迦太基宗教会议 上被正式确定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分为《旧约全书》与《新约全书》,前者是犹 太教的圣典,共39卷;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新编的,共29卷。
罗马帝国后期“拉丁教父”编译与阐发《圣经》的学术活动,开启了中世纪经学传统 的端绪。公元前4世纪以前,《圣经》几乎都是希腊文版本。《旧约全书》是从犹太教 那里继承下来的,最初用希伯莱文写成,大约在公元前2—3世纪又用当时流行的希腊文 编译而成。据传,大约在公元3世纪中叶,应托勒密国王勒代尔佛斯的邀请,耶路撒冷 的70名犹太学者来到亚历山大城,将《旧约全书》译成希腊文,称为“七十子文本”。 这个版本谬误不少,甚至有原书的文句与章节顺序被改动的情况。该版本首先在亚历山 大被不熟悉希伯莱文的犹太人所应用,一直流行在巴勒斯坦,后来基督教产生后又在罗 马的基督徒中流行。《新约全书》最初也用希腊文写成,基督教产生后渐被译成拉丁文 ,其中错漏不少。随着基督教的国教化与罗马帝国日益分裂成为东西两部分,为适应西 罗马帝国统治阶级的需要,必须完全实行《圣经》的拉丁化,编定出一部统一的拉丁文 本《圣经》;还必须从《圣经》这部内容繁琐庞杂、历史典故与神话传说相互交织的原 典中发掘神学伦理的内涵,并将之转化成系统化与理论化的教义,用以规范信徒的思想 取向与行为规范。此外,为了同当时的阿利乌斯派等异端做斗争,维护基督教的正统地 位,也需要深入到原典中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为反异端的神学观点提供理论依据。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约在公元前4—5世纪,一批神学家本着这一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开始了对《圣经》的翻译与阐发工作。他们被教会尊称为“教父”,因系罗马帝国 西部讲拉丁语地区的学者,又以拉丁文来翻译《圣经》,故被称之为“拉丁教父”。
在《圣经》文本的拉丁化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著名的拉丁教父圣·哲罗姆。他精 通希腊文与希伯莱文,曾经在君士坦丁堡校译与注释《圣经》。382年他赴罗马,任罗 马大主教的教务秘书,并受命编定一部统一的《圣经》拉丁文译本。他通过30多年的劳 作,参照希伯莱文原本翻译与校订《圣经》,最终集成《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成为中 世纪正统的《圣经》文本。此外,他还撰写了一些有关《圣经》的介绍与注释的著作, 这在中世纪被作为《圣经》评论的标准。在翻译与注释《圣经》时,哲罗姆使用了意义 近似与隐喻的方法,其中有不少与原意不合的错误。有史家认为,由于哲罗姆的学说处 于权威地位,“他的翻译错误与解释就是整个西方中世纪所接受的《圣经》传统的一部 分”[1](P80)。此后不久,著名的拉丁教父圣·奥古斯丁在阐释《圣经》时,也同样使 用了哲罗姆的方法,并且对这一方法作了论证。在他看来,《圣经》之所以用模糊的形 式和朦胧的语言写成,是因为上帝为了以此来征服人的傲慢与自负,让那些漫不经心的 读者一无所获。故在阅读《圣经》时,切勿仅仅看到字意表达的对象,而必须洞察到其 字词所指向的存在于物质现实之后的超世俗的神圣真理。《圣经》的语言只是一种指引 读者从有形之物转向无形之物的工具。他指出:“被撰写的事物不被理解有两个原因: 由于它们被陌生的或模棱两可的符号所模糊了。因为符号有字意的和比喻的特性,从字 意上看,它们表示某一事物;而从比喻上讲,它们同时也意味着其它某种事物。”[1]( P84)圣·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一书,是一部侧重于论证如何发现《圣经》字面 意义背后之神圣真理的方法。在此书中,他要求人们去发现《圣经》字意所指的超世俗 的神圣内涵,并阐述了完成这种任务的诸方法。不拘泥于经文词句字面意义的解释,而 是致力于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体悟到字面背后隐藏或包含的“上帝”的意志和启 示。通过“拉丁教父”的神学活动,以《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统一而权威的版本、以 探求《圣经》中“神意”为主旨、以主观主义的阐发与体悟为诠释模式的“经学传统” 开始形成。
二
封建时代既是西欧基督教“经学传统”日益积淀与流播的时代,也是这一传统逐渐僵 化与封闭的时代。进入中世纪后,随着基督教与新兴蛮族封建王权政治联盟的形成,基 督教教会得到了世俗王权庇护与封赐而日益封建化,不仅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而且 取得了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绝对支配地位。与此相应,作为基督教原典的《圣经》也 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在教会看来,《圣经》是人类过去与现在同“上帝”订 立的契约,是“上帝”、“神灵”的启示,是不可怀疑的信仰准则,也是真理的源泉, 甚至具有法律效力,《圣经》的解释权只属于教会。由此,“圣经学”逐渐兴起,成为 封建西欧学术文化领域中的“显学”。早在中古之初,西欧的神学家为了充分发挥《圣 经》的学术指导作用与伦理教化功能,就十分注重对《圣经》版本的重新校订。当时由 于“蛮族”征服罗马帝国所引起的社会大震荡对学术文化与宗教信仰的冲击,《圣经》 文本常常遭到篡改与切割,拉丁教父所奠立的“经学传统”濒于断裂。直到8世纪后期 法兰克王国的君主查理曼即位后,《圣经》文本的杂芜与混乱还十分严重,当时的一位 学者撒谬尔·伯格对此曾指出:
优秀的文本与低劣的文本可悲地混杂在一块儿,有时同一书的两种译本并排放在一起 ,更老的版本居然与拉丁文《圣经》的惟一公认本混淆到区别不开的程度,每一部手稿 中抄录的《圣经》顺序都不一样。[2](P59)
为了统一基督教的神学信仰,发展学术文化,查理曼委托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神学家阿 尔昆对《圣经》进行重新校订。阿尔昆组织人搜集不同《圣经》版本的手稿,然后以圣 ·哲罗姆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参照依据,从章节顺序、经文乃至标点上都进行认 真的校勘、辨误与订正[3](P158-159)。从公元797年起,经过三年多的劳作,终于编定 出一部权威的《圣经》版本。这是对圣·哲罗姆文本的精致重建,也是“加洛林文艺复 兴”的重要成果,它有力地促进了“经学传统”的复苏与中古神学文化的发展。阿尔昆 等人的“经学”活动,应被视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端。不过,后来的经院哲学家却违 背了阿尔昆等人的求实求真的学术精神,不仅将“经学”重新纳入拉丁教父之“经学传 统”的框架之中,而且进一步将之引入教条化的轨道。
查理曼帝国瓦解后,西欧陷入封建割据的局面,罗马教廷的神权日益凸现,但教皇仅 在名义上是西欧基督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并未实际掌握对各国教务的支配大权。各国教 会的封建化与世俗化所导致的高级教职由俗权任免、教务由俗权控制的情况依然存在。 自11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封建经济的复苏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出现,英、法与德意志的封 建王权逐渐崛起,进一步加强了对本国教会的束缚。而一些城市自治运动的勃兴,也对 当地教会的神权政治势力予以了有力的冲击。为有效地控制各国教会,在整个西欧真正 建立起大一统的最高神权权威,罗马教廷利用克吕尼宗教改革运动的风潮,开始与世俗 王权争夺教职叙任权和教会司法权,其神权也随之急剧膨胀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 境中,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发展起来。
经院哲学家以当时兴起的大学为基地,以《圣经》为学术根底,从阿拉伯人阿维森纳 、阿威洛依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著作中,吸取了有关哲学本体论与方法论 的营养,来构建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的兴起,导致《圣经》注疏活 动的展开。当时学者比较重视的《圣经》注释本有两部,其一《普通注疏集》,一般认 为是9世纪上半叶由神学家斯特拉波依据古代拉丁教父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著述编成, 其继承了哲罗姆与奥古斯丁的主观体悟法来解释《圣经》文句的内涵,权威性很高,曾 经被神学大师阿奎那在其著作中反复引用。另一部则是12世纪由著名的经院哲学家安瑟 伦所编撰的《行间注疏集》,其仍然沿袭拉丁教父解释方法。到了13世纪,还出现了《 圣经词语索引》,以作为人们学习与研究《圣经》的参考。
罗马“拉丁教父”的“经学”学风,被经院哲学家视为圭臬。经院学者对《圣经》的 解释,其意旨也是要证明“上帝”及其一切“神灵”事物的存在与权威,其解释的程序 大体有四个层次:字义、寓言、隐喻、神秘解释。字义保存着事实的记录,后三者则完 全不同,寓言启导人们应该相信什么,隐喻告诉人们该做什么,神秘解释则给人以盼望 。不过,与拉丁教父不同的是,经院哲学家一般都首先从《圣经》与拉丁教父的著作中 引经据典,并力图通过严格的概念界定与逻辑推理来证明其所要探寻的真谛。这样的“ 真谛”表面上看多聚焦在对“上帝”的存在作一“宇宙本体”的论证,但实际上是为罗 马教廷的大一统神权与封建统治秩序提供哲学上的理论依据,托马·阿奎那所证明的“ 宇宙等级秩序”论就是一个典型。经院哲学的主观臆断和烦琐论证,最终让《圣经》成 了玄虚的哲学命题与空洞的哲理思辨的注脚,使得这一基督教原典逐渐丧失了它在宗教 信仰与伦理上所蕴含的本义及其应有的文化原创性活力。
经院哲学家的“经学”活动受到了罗马教廷的大力支助,它以惟我是真、惟我独尊的 气势,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化专制主义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拉丁教父与经 院哲学家的有关解释与注疏《圣经》的著作,教会重要会议的许多规定和决议,罗马教 皇发布的教谕与教令也都成为绝对正确的真理。所有这些文件,再加上神职人员通过布 道书、口头传教等方式所传播的东西,被称之为“圣传”。教会强调,只有通过圣传, 才能正确地理解《圣经》。换言之,人们只能从《圣经》中获得与理解那些教会所传播 与作出解释、判断的内容。任何违背原则而自主地翻译与解释《圣经》都将被视为异端 而要受到惩罚。在“经学”热中兴起的经院哲学,最终将西欧基督教的“经学传统”推 上了学阀化与官方化的学术轨道,使之成为罗马教廷神权统治的精神支柱。
经院哲学所阐扬的“经学传统”尽管受到罗马教廷神权的呵护,但在当时仍然受到市 民、平民的异端理论的怀疑与挑战。在12世纪后期法国南部爆发的阿尔比“异端”运动 中,市民“异端”者的首领华尔多就组织人将正统的拉丁文本《圣经》弃而不用,代之 以翻译成为法国南部土鲁斯方言的《圣经》。13世纪后期,著名的“唯名”论者英国的 罗吉尔·培根在《哲学研究纲要》一书中,大胆抨击教会僧侣的愚昧无知与经院哲学空 洞繁琐的形而上学方法,认为神学研究也需要科学依据,提出研究《圣经》要以原本经 文结合历史、地理、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进行探讨。到了14世纪中期,英国的市民 “异端”思想家威克里夫在鼓吹建立英吉利民族教会时,力图打破罗马教会对《圣经》 版本与解释的垄断权。他将《圣经》由拉丁文译成英文,声称《圣经》是信仰的惟一权 威,每个人只要相信《圣经》,按《圣经》行事就行,根本就不需要专门的教会和神职 人员及相应的宗教教规及仪式。所有这些主张,成为日后人文主义学者批判教会“经学 传统”的理论先导。
三
14至16世纪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历史过渡,直接促使中古基督教“经学传 统”的衰落与人文主义“圣经学”的勃兴,进而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政 治的巨大变革。
其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勃兴与封建经济的瓦解,资本主义萌芽渐次在西欧各国破土成 长起来。与之相应,一方面,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愿望日益强烈,为争取建 立本阶级的“廉价教会”与实现其“自由平等”的理想而斗争;另一方面,在新的经济 态势下,西欧的民族国家逐渐兴起,有的还建立了君主与资产阶级政治联盟并实行政治 集权的“新君主制”,建立民族的或国家的教会的问题由此而凸现出来。同时,自“阿 维农之囚”后,罗马教廷就一蹶不振,权势如江河日下,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力大大减弱 。这样的社会大背景,酝酿出以“个体本位”为特征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人文主义者 批判教会在思想文化上的蒙昧主义立场与经院哲学家的僵化空疏的学风,颂扬个人的尊 严与自由。他们所树立的“思想自由”或“精神自由”的原则,构成了对正统神学思想 意识形态的强大挑战。随着人文主义思潮的不断流播,不少人文学者与反教廷的宗教改 革家将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焦点逐渐聚焦在基督教原典《圣经》上,开始与罗马教廷 展开了有关《圣经》版本使用权与经文解释权的激烈争夺,从而对积淀了数千年的神圣 至尊的“经学传统”以有力冲击。
逐渐兴起的人文主义“圣经学”,将“个体本位”人本观的“自由”原则贯穿在对《 圣经》的翻译、研讨与阐发之中。它反对教廷的拉丁文版本《圣经》的独尊地位,要求 实现《圣经》的民族语言化,由此而纷纷将《圣经》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它反对教会 人士对《圣经》阅读与宣讲的垄断权,要求实现《圣经》传播的平民化,由此而伸张人 人所应有的学习《圣经》的权利。它怀疑教会对《圣经》内容解释的权威性,由此而主 张在《圣经》解释与体悟上的自主化。这决不是一场单纯的学术之争,而实质上是一场 宗教—政治权力的斗争。新的“经学”热潮并没有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上,而是进一步向 纵深拓展,不仅主张以《圣经》的权威取代教皇的权威,而且返回到原版《圣经》的经 文中,去阐发新的伦理内涵与信仰真谛,由此而瓦解了罗马教廷神权统治的理论基石。
在对罗马教会“经学传统”的反叛潮流中,在15世纪中期的意大利,兴起了以瓦拉为 代表的“圣经人文主义”(Biblical humanism)学派。瓦拉学识渊博,曾撰文对所谓的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迁都时曾经将帝国西部的统治权赠给罗马大主教的论断,从史学、 法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揭露,最终考证出罗马教会的所谓“君士坦丁赐予”是 一件伪作。瓦拉等人还对《圣经》加以订正与注释。他们反对教会“经学传统”的那种 致力于发掘“微言大义”并从中导引出正统神学伦理的作法,“力图恢复其中每一个特 定教义或论点的精确历史内涵”[4](P209),为此而追溯到古希腊文与希伯莱文的原版 《圣经》中去探究。1449年,瓦拉发表了《新约全书注释》一书,在拉丁文与希腊原文 这两种版本之间进行鉴定性的比较考察,用其广博的语言知识纠正了拉丁文版本中的许 多谬误。例如,在“哥林多书”中,拉丁文译本中的有关圣保罗宣称的教义是,只有“ 靠上帝和我的慈悲”才能得救。而瓦拉通过对希腊语词汇的分析,断定这句经文的原文 是“靠上帝的伴随着我的慈悲”。瓦拉由此而得出结论:“保罗并未说他能够赐予什么 ,因为一切都必须被看作是属于上帝的”[5](P686)。此外,另一人文学者布兰多利尼 撰写了《希伯莱人宗教史》,旨在从《圣经》中和《约瑟亚书》中引出希人的宗教史概 要。他认为,经院哲学家对《圣经》的解释都是“琐碎无聊之举”,这只能使人们坠于 “荒谬的浓雾之中”[5](P601-609)。他还把《旧约全书》看做是编年史,从历史的角 度对它进行阐释与订正。在当时,除了瓦拉学派以外,15世纪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学 者曼内蒂、皮科等人都曾翻译或研究过《圣经》。曼内蒂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莱 语,在神学上颇有造诣,曾经阅读与研究了希腊文和希伯莱文版本的《圣经》,逐词通 读过希伯莱文注释者的注解,指出了他们的一些错误。而皮科为了取得成果,先后掌握 了拉丁语、希腊语、古犹太语与迦勒底语,并用译本名叫“卡巴拉”的犹太神学著作来 对《圣经》作一索隐探赜。
以瓦拉为代表的“圣经人文主义”学派为主体的人文学者在对以《圣经》原典及其他 教会神学文献的翻译、考证与探讨中,摒弃了经院哲学的那种先验与狭隘的解释方式, 逐步树立起求真证伪的怀疑主义与批判主义的学术精神,积累起一套新的知识结构与方 法体系,并恢复了《圣经》原文,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这些宝贵的知识财富,后来又 随着人文主义思潮一起传播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由此而推动了“北方文艺复兴”的兴起 。
在向意大利文艺复兴学习的过程中,不少“北方”人文学者特别钟情于它在复兴古典 文化上的学术成果。在英国,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三位皆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著名人文学 者W.克罗西恩、T.利纳克雷和J.科勒特在这方面堪称典型。从1488至1490年,克罗西恩 就在意大利师从于著名学者坡利扎诺等学习希腊文化,回国后成为英国最著名的古典学 者。有人认为“在他回到牛津大学后,他的英国同胞们不再为了学习希腊语而必须到意 大利去了”[6](P134)。从1486至1492年,利纳克雷在意大利的帕都瓦大学攻读医学博 士期间,也熟练地掌握了希腊文。回国后就职于亨利八世所建的皇家医学院,曾撰写了 语法、医学方面的著作,还翻译了盖伦的作品。科勒特的影响则更大。他多年在意大利 学习古典文化,深受瓦拉等人的影响。在1496年回国后,他就在牛津大学任教,开设了 一个有关《圣经》的“保罗的使徒书(Pauline Epistles)”讲座,以希腊语的《新约全 书》为依据,对基督教的历史进行引经据典的论证,由此“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像批评 李维或修昔底德的作品那样大胆地对《圣经》进行批评的武器”[6](P137)。此外,他 还抨击经院哲学家的僵化学风,否定教士对信徒的“赎罪”权。他的父亲是伦敦的尼绒 商,两次出任伦敦市长,借此,他在1504年被任命为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主祭后,就在 其中建立了圣保罗语言学校,教授学生希腊语与拉丁语。
在法国,著名的巴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J.利特维勒从1492年起就在意大利研究希腊古 典文化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东西。1507年回国后,就在圣日梅茵—德斯—普雷斯修道院 担任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组织研究《圣经》与教父著作等文献。他们摈弃了经院哲 学家的僵化学风,强调研究的深化必须依赖于手稿的发现并依据历史脉络而进行。1512 年,利特维勒出版了有关圣保罗之“使徒书”方面的著作,对“北方”人文学者产生较 大影响。[6](P134)
在德意志,15世纪后期产生了一个有许多僧侣参加的带有修道院色彩的团体“共生兄 弟会”(Brethern of the Common Life),其所属教堂、学校遍布各地,采用人文主义 的教学法则,传授希腊古典文化和人文主义的作品,敌视经院哲学。此团体培养了许多 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很多人都精通希腊文、拉丁文与希伯莱文,对有关《圣经》的 “新学”(new learning)特别感兴趣,并力图从中发掘适合于新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宗 教理念与伦理精神。这正如史家所云,在德意志,“人文主义运动却更密切地与基督教 文化的复兴联系起来,和向更精确的《圣经》原文与向教会内部的一种更纯洁生活的复 归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7](P48)。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了以勒克林为代表 的语言训练齐备并致力于“圣经学”的人文学者。勒克林精通希腊文和希伯莱文,在新 的“圣经学”上成就斐然。1506年,他出版了《希伯莱文基础》,其中将希伯莱文与拉 丁文这两种语言的字词加以对照,是一部颇有价值的语法书[8](P76)。他声称,他的研 究成果使得他“对《圣经》的译本极为怀疑”,特别是对教会钦定的《通俗拉丁文本圣 经》的精确程度深为怀疑[8](P72)。他还指出,由于是以对希伯莱文的元音系统误解为 基础的,《旧约全书》的希腊文版本本身有不少错误,这使得以其为蓝本而翻译出的《 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也充满着翻译错误,达到两百多种[8](P78)。勒克林的学术成就激 起人们对新的“圣经学”的兴趣,北方的一些大学纷纷建立了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与希 伯莱文的语言学院。同时,有这三种语言对照的《圣经》文本也开始问世。大约在1514 至1517年之间,阿尔卡拉(Alcala)大学出版了《旧约全书》,在此版本中,拉丁文译本 置于中间,希腊文译本在右边,希伯莱文本则放在左边。此书中的“摩西五经”的每一 页下部,还附有先知的释义[4](P211)。
在新的“经学热”中,“北方”著名人文学者伊拉斯谟的贡献尤为突出,故也被史家 称之为“圣经人文主义者”[6]。伊拉斯谟曾经在德文特的“共生兄弟会”学校学习9年 之久,又游历了意、英、法等国,深受瓦拉、科勒特与利特维勒等人的影响。他将批判 的矛头指向经院哲学家将《圣经》教条化与神秘化的做法上,极力地主张阐发《圣经》 原本中的伦理内涵,以之作为建立人文主义道德规范的价值源头。伊拉斯谟以现实生活 中的人的道德眼光来审视宗教问题,他鼓吹的基督教复兴运动,实际上是重振人的道德 运动,并由此而否定了教会教阶制度与礼仪制度存在的价值。伊拉斯谟强调恢复原始基 督教的道德精神。对他来说,基督并不仅仅是“上帝”派往人间的“救世主”,更是一 位伟大的神学真理的宣讲者与传播者,一位集各种美德于一身而应当被每个人敬仰与效 法的道德上的“唯一原型”。他指出,“任何人如果偏离了这个原型哪怕只有一颗钉子 的距离,他也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9](P36)。他还指出,基督的“哲学”除了体现 基督本身及其教诲的朴实、仁爱、忍耐与虔诚外,并没有其他的任何含义;而基督之教 义的核心则是博爱,即将所有的人“全都看成是基督的信徒,将上帝赐予你的同胞的爱 高兴地看作是赐予你的好运,解除他们的灾难,善意地纠正他们的过失,启迪愚昧者, 超度阵亡者,慰问苦闷者,帮助辛苦劳作者,救济需要者……”[9](P39)从此出发,伊 氏提倡革新基督教,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反对教会中流行的繁文缛节,否定圣礼的玄 秘与功效。他说:“去遵守这些礼仪是有益的,但依赖它们却是有害的。保罗没有禁止 你去使用礼拜式和教会礼仪,但他不希望自由信仰基督的人被这些东西束缚住……没有 这些礼仪你不会虔诚,但它们不会使你虔诚”[9](P36)。从此出发,伊拉斯莫呼吁每个 基督徒都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圣经》,建立一个以基督为最高伦理典范、以基督作为 人与“上帝”联系之媒介的社会。在1516年发表的《新约·导论》中,伊拉斯莫指出, 研究《圣经》“将带给你们活生生的基督的圣灵、话语、伤痛……它们如此丰富地呈现 基督,只要你睁眼凝望就能看见”[10](P92)。在他看来,塑造完美人生、符合人性的 的基督教道德哲学深蕴在《圣经》之中,《圣经》是知识的源头,“《圣经》是万事万 物的最后权威”[11](P155)。为此,他主张将《圣经》普及化,人人都应阅读《圣经》 ,也应当将《圣经》翻译成民间俗语。对此,他在《基督教战士手册》一书中写道:
我强烈反对那些不愿让俗人阅读《圣经》的人和那些不愿让《圣经》被翻译成通俗语 言的人,好像基督让《圣经》教义晦涩以至于只有少数神学家才能理解它,或者好像是 基督教的安全寓于对它的无知之中……基督希望他自己的秘密尽可能被广泛地宣传出去 。我希望所有即便是最卑微的女子也能读到福音书和保罗书,我希望它们被译成各种语 言,以至于不仅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而且也被土耳其人和撒拉森人诵读与领悟。由 此,农民在耕田时便能吟颂《圣经》的词句,织工们就能在机梭的伴奏下哼唱《圣经》 的段落,旅行者就会用《圣经》来减轻旅途的疲劳[10](P97)。
正是为了深入发掘基督教原始经典中的道德精神来与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相对抗,伊 拉斯莫积极展开新的“经学”研究。在《新约全书》方面,他将罗马教廷官方钦定的哲 罗姆通俗文本与一些希腊文原文的《圣经》手稿进行对照,修正了前者的许多讹误。在 评注方法上,他运用了瓦拉等“圣经人文主义”者的方法,在对《圣经》中的历史意义 、寓言、词语的比喻等进行注释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圣经》进行历史主义的探讨,即 结合历史背景来寻找其经文的真实内涵。他特别强调将语言知识与自然、历史知识结合 起来对《圣经》研究的重要意义,主张出版不同的版本来让读者加以对比和判断。通过 考订、增删、校对与翻译,伊拉斯莫终于在1516年出版了较为精确的希腊文的《新约全 书》,并附有自己所翻译的拉丁文译本。他所作的批判性附注,与罗马教廷的正统的评 注大为相左,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英王亨利、法王法兰西斯、西班牙国王查理等君 主,都得到了他所赠送的四部《福音书》的评注。
“北方”人文学者的“新经学”活动,从对《圣经》的翻译、订正与注释出发,以阐 发其中的伦理精神与纯洁基督教道德为主旨,形成了对中世纪经学传统与罗马教会教阶 、礼仪制度的巨大冲击,由此而激起人们在传统宗教信仰上的裂变,为马丁·路德宗教 改革思潮的勃发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土壤。①
马丁·路德是一位学识广博的神学家,通晓希伯莱文、希腊文与拉丁文。从1515年开 始,他就在维登堡大学主讲《圣经》,并为之作注。在研讨的过程中,他对教廷神学家 对《圣经》版本与解释的垄断深为不满,发愤要翻译出一本既通俗、又准确的德文版《 圣经》。在翻译时,路德参考了伊拉斯谟1516年出版的《新约全书》,其中包含了希腊 文原本与伊拉斯谟完成的拉丁译本。同时,他选择了具有规范化趋势的萨克森—图林吉 亚语(“新高地德语”之母)。在此之前,实际上大约已经有18种德文《圣经》译本问世 ,其中包括高地德语版本14种,低地德语版本4种。然而,它们依据的是罗马教廷官方 钦定的、被加工了的拉丁文《圣经》;此外,它们采用的是地区性的土语方言,粗陋呆 板,谬误很多。而路德的故乡萨克森—图林吉亚地区,由于商路在这里四通八达,各地 来的移民较多,萨克森—图林吉亚语在吸纳了德意志各地方言的过程中逐渐成熟,成为 一种适用范围较广的语言。此外,为使《圣经》传播的普及化与大众化,他还在民间语 言中吸取营养。他曾经说道,“我的老师是家庭的主妇,是做游戏的孩子与城市广场中 的商人。我努力地去从他们那里学习如何去表达与解释《圣经》”[9](P70)。正因为如 此,当他将《新约全书》的新译本在1522年9月出版时,普遍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第1版3000册在3个月内就被销售一空[9](P70)。此后花费了近20年时间,将《旧约全书 》翻译出,分4个部分出版。到他逝世时,仅在维登堡一城就出版了10多万册。
在如何理解《圣经》的问题上,路德反对旧的经学传统的禁锢,强调个人自由解释《 圣经》的权利,以求实求真的批判视野来解读《圣经》。因此,他不畏触犯先知、使徒 、圣徒与教父乃至罗马教廷的神圣权威,不受种种迷信、愚昧与荒诞的束缚,他对有关 《圣经》作者、内容与价值等方面的许多问题,都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在对《圣经 》的各种手稿、版本进行对比与研判的过程中,路德发现多年来《圣经》不断遭到教父 与教士们的“加工”与篡改。他将此公诸于众并告戒说,“要想通过教士们的判断来学 习《圣经》,实在是愚蠢的”[12](P92)。
对《圣经》的神学内涵的深层次发掘与创造性诠释,构成了路德之新教思想的理论源 泉。他不仅力倡以《圣经》为最高的信仰权威,而且从中确立出以“因信称义”为轴心 的新的“救赎”学说。这样,由“圣经人文主义”开启的自由主义的学术批判思潮,最 终通过路德而完成了基督教“经学传统”的历史性转换,进而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思想文 化与社会政治的变革。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下,罗马教会正统的神学思想与其大一统 神权对西欧的统治局面土崩瓦解,西欧思想文化乃至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的历史转型又 向前迈进了关键的一大步。
注释:
①西方学者对“圣经人文主义”学派、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贡献评价很高。有人指出, 瓦拉等人的学术活动,“不仅复兴了古典文化,鼓励了文化批判主义,而且也恢复了《 圣经》原文,促进了神学批判主义”。“如果没有意大利人的怀疑和批判工作,与其在 哲学、神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中的勇敢探索,如果没有他们在人类知识的基础上的发掘和 对中世纪先验论的直接否定,德国的宗教改革是不可能产生的”(J.A.西蒙兹:《意大 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 in Italy),伦敦,1900年版,第5卷,第462页)。还有人 指出,由瓦拉开启的“圣经人文主义的方法技巧”在德意志宗教改革中“扮演了特洛伊 木马的角色”(Q.斯金勒:《近代政治思想基础》第1卷《文艺复兴》,第212页)。更有 人强调,圣经人文主义的精神、成果与方法,是促使宗教改革爆发的最强大的“一种主 要因素”(B.M.G.雷尔顿:《宗教改革中的宗教思想》,序言,第6页)。
标签:基督教论文; 人文主义论文; 圣经论文; 经学论文; 上帝的教会论文; 文化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旧约全书论文; 经院哲学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新约全书论文; 希伯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