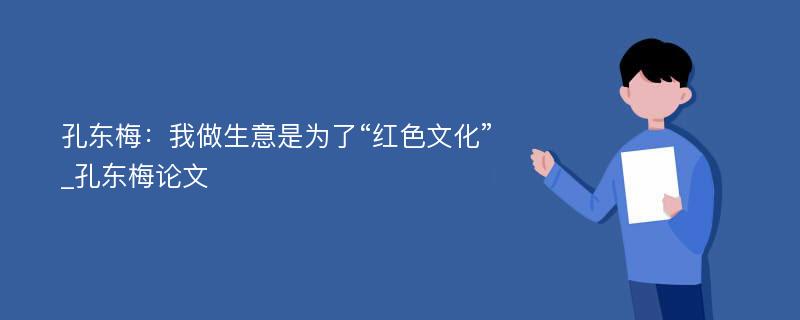
孔东梅:我从商是为了“红色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为了论文,红色论文,文化论文,孔东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初见孔东梅,是在广州市购书中心,短发淡妆的她挂着微笑,在这里进行她的新书《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的签售。
毛泽东唯一的外孙女,毛氏孙辈中唯一的女性——任何场合对孔东梅的介绍都离不开这两句话;而下巴一颗带着明显毛氏特征的“痣”,也使孔东梅与毛泽东增添了几分神似。
于是,毫不意外地,购书中心现场预备的150本新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只听到场内的随行人员扯着嗓门向电话里吆喝:“马上加运200本以满足现场需要。”——而坐在一旁的孔东梅,仍是不动声色,优雅地微笑着,保持着她伟人之后的风度与气质。
《改变世界的日子》并不是孔东梅的第一本书,此前还有《翻开我家的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及《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毛泽东与贺子珍》,每本书的标题都离不开毛泽东。而很显然,吸引众多读者追捧孔东梅的书的首要因素,应该是她的特殊身份,其次才是书的内容。
记者:作为毛主席的外孙女,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份的特殊性的?
孔东梅: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因为家庭环境原因,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因为我在离家很近的武康路小学上学,放了学就直接回家,而小朋友也进不来我家。
记得那时候外婆身体不好,很多时间都在医院,妈妈又远在北京,心里觉得比较孤单,很想跟小朋友一起玩,也特别想妈妈。
当然,除了孤独之外。工作人员把我生活各方面都照顾得很好,不但不愁吃和穿,而且在家就能看到很多电影——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普通孩子无法想象的优越。
不过我仍然羡慕他们有父母陪,我的童年应该是因孤寂而比较内向的。
记者:看来伟人之后的身份给你的童年带来的并不是优越感而是寂寞和孤单。这是你在求学阶段刻意隐瞒自己身份的原因之一吗?
孔东梅:主要原因其实跟家庭教育更有关系。我的妈妈李敏在前苏联长大,外婆一直都没有告诉过她的真实身份,她在12岁前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妈妈12岁那年,毛岸青舅舅指着外公的照片问妈妈“你知道他是谁吗?”妈妈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舅舅说,“他是我们的爸爸”,但母亲并不相信,还说“我没有爸爸”。
后来,母亲写了封信问外公:毛主席,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
外公马上回了一封电报,说: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吧——这个时候妈妈才知道自己的身世。
受外婆这种态度的影响,我的母亲从小也常常告诫我们,不要老记住自己是谁的孩子,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我觉得我们甚至有“夹着尾巴做人”的意思。所以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期间,除了向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报告外,并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身份,就连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都不知道我是毛泽东的外孙女。
也许求学时代的孔东梅确实谨遵母训,有那么一段“夹着尾巴做人”的日子。但自从出版第一本与毛泽东有关的书籍开始,亦即孔东梅从开始创业,由一个单纯的学子或工薪一族,转变为一个“商人”起,就跟“低调”沾不上边了。频频地签名售书,接受媒体专访,使她头上聚起了越来越多的光环,而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备受瞩目。
记者:听说你现在在从事出版传媒事业,已经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董事长。
孔东梅:是的。我创立了一家文化公司——北京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我自己任董事长。这个公司是以外公在中南海的办公地点名称“菊香书屋”来命名的。公司业务是以研究、宣传、出版、传媒为主,从文化角度研究百年毛家以及中国“红色文化”代表人物。因为我觉得现在国内这方面做得还不够深。
当然,我们的“红色文化”是有别于过去二三十年间兴起的“红色文化热”的。我希望能用现代人的角度、观点去诠释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政治家、历史学家用他们的角度讲,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层面去剖析。
很多人跟我说现在是网络时代,不流行这些革命的东西了,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年轻人都会经常去参观越战纪念碑,都很景仰华盛顿等革命先辈。我心目中的“新红色”应该是时尚中的时尚,能够吸引年轻一代了解红色历史。
记者: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你一直强调外婆与母亲灌输给你的“低调”思想,在求学阶段你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最近你频频出书、露面、接受采访,已经打破了“低调”的惯例,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转变?
孔东梅:频繁吗?我自己也不觉得非常频繁呀。可能以前一直在求学,也没有从事这方面的业务(指出版、传媒),也没有必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或者以这个身份与外界见面吧。
记者:就是说现在打破低调惯例与公众见面及出书,是与你的创业经历和公司发展有密切关系了?
孔东梅:也有这个原因吧。
记者:那么公开了身份后,对你的事业发展有什么帮助呢?
孔东梅:要说有什么好处,可能就是人们非常关注我们这个家族,希望知道我们这些后人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从而令我的公司也受到一些关注。但是你要说什么实质性的利益,例如谁给你投资个几百万、几千万,或者能随便拿到些什么批文,还真没有过——市场是公平的。
孔东梅与毛新宇,是毛氏孙辈中学历最高的两位,也是最爱出书的两位。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没有见过外公,但书的内容却全部都离不开外公……
记者:你已经出了三本书,都是关于你外公的,但听说你其实根本没有见过他。
孔东梅:我在照片上与外公“见过面”。那时候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外公看,再把外公的照片带回给我看。我的名字就是外公看着照片取的,用了他名字里的一个“东”字,又用了他平生最爱的“梅”字。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外公既熟悉又陌生,既远又近,我真心地从心底里尊敬他。
记者:你曾经强调你写书特别强调真实性,不会像市面某些书那样采用一些没有经过考证的资料生拼硬凑。但你既然没有见过你的外公,又如何保证你所著的书比其他作者更具真实性呢?你考证资料的方式与其他人有何不同?
孔东梅:无可否认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写伟人的书用的都是第三四手的资料。而虽然我本人没有见过外公,没有在他老人家身边生活过,但我写书时一直坚持一点,就是要拿到第一手的采访资料,即一定要采访到当事人。尤其是写我外公这么伟大的领袖,更要保持真实性。
至于资料的运用,我一定会反复考证核实。其实方式跟其他作者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因为我的身份,所以很多人知道我要做这个事情时,都会比较愿意帮助我,跟我说很多平常不会说出口的,鲜为人知的事情。这就是我的优势。
写书于我不仅仅是卖书,还是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例如我心中从小就有很多解不开的谜:为什么外婆想见外公一面竟那么难;外婆这个井冈山上资格最老的女红军,居然在外公去世三年以后才第一次到北京……这些疑问我都在写书的过程中寻找答案。
记者:例如这次王海容就是因为你的特殊身份才开口谈往事的?
孔东梅:是的。王海容是我外公身边非常核心的工作人员,她事业最顶峰时期就是中美建交时期,而中美外交对今天的世界格局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选取了这一点来下笔。王海容平时很低调,几乎不肯接受任何采访,但她是我们的家族成员,与我是同辈,她也叫我外公做公公。
记者:很多人这次都是冲着王海容来买这本书的,因为她在“文革”的后半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凡有毛主席外交活动见于报端的,就有王海容。而这些年她不但从不发表任何文字,而且从未说过一个字。按理说这本书应该是很有价值的,但我翻看了一下发现,书里真正引用王海容的讲话只有只言片语,而更多的是其他中外人士的回忆片断,而且很多都已经公布于世。
孔东梅:王海容能开口,就是最大的亮点。她甚至跟我谈到我外公的初恋,如果不是她说出来,又有谁会知道呢?而且历史总是有一些不宜公开,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社都要审。书稿在2006年年初就出来了,但现在才出版,中间经历了很多环节,比原稿删掉了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