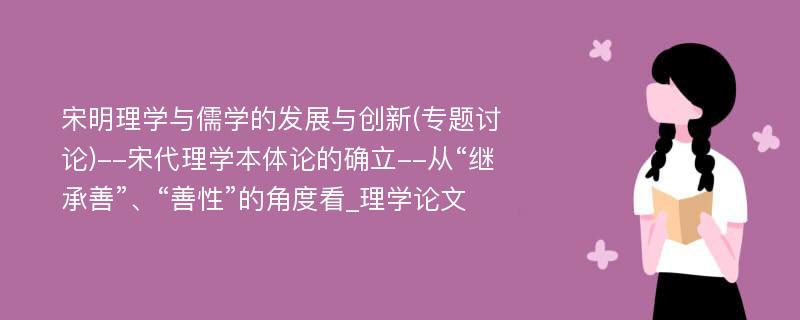
宋明理学与儒学的发展和创新(专题讨论)——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从“继善成性”和“性善”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本体论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儒学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学的发展在经历了长期的不景气之后,自宋代开始复兴,传统儒学也相应变型为新儒学。新儒学的理论创新,通常以天理论、心性论、道统论等为标志,但所有这些理论却可以用一条主线——复性论来贯穿。儒学复兴的关键在于复性。理学家通过“继绝学”的理论变革,重新接续起先秦时期“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并进一步发扬推进。正是有赖于新儒家的这些努力,曾在汉代短时期推行而又长期名不副实的儒家“独尊儒术”的理想,在宋代以后以新的形式得以实现,理学的理论创造同社会对理学的选择这种“内外交相合”的结果,最终造就了宋明新儒学——理学在整个中国学术领域的中心地位。
那么,如何才能复性?复性并不是简单地回复到先秦性与天道论“不可得而闻”的旧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从内在性的角度阐明性体、道体如何奠定,人在自觉的层面如何“成性”。也就是说,在理学家那里,“复性”的实质其实是“成性”。他们号称自己的理论创造或者是“自家体贴”,或者是“自得”于先秦孔孟,都是在倒转“性与天道”论的指向而使其“得而可闻”。这种强化自身理论创造的“成性”说,是儒学复兴最重要的理论标志。
但是,“成性”在文本和思想史上都是与“继善”相联系的,性和善如何发生关系是“性与天道”论的思辨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中国哲学对于善与性关系的思考,主要有两大思想来源:一是以《易传》为代表的“继善成性”的观点;一是以思孟学派尤其是《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的观点。双方虽然都是既讲性又说善,但在性与善的先后顺序及关联程度上却是大相径庭的。《易传》是善在性先,善与性在发生论上是两个前后跟进而又相互独立的阶段;《孟子》则是性在善先,而且“孟子道性善”突出的是性与善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讲性是为了彰显善;讲善正是在说性。那么,“继善成性”与“性善”虽都出于儒家的经典文本,但引出的却是不同的义理间架和理论走向。
就“继善成性”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哲学家并未有意识地对它们进行思考。韩康伯续王弼注《周易》,对“继善成性”完全没有解释;对于同为本体论思辨源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亦只是无关涉性理地一语带过。
与此有别,从孟子之后到整个汉唐时期,围绕“性善”却一直是争议不断且新说迭出,如性恶、性善恶混、性三品等。但不论将性划分为几品,都只是在道德论上谈问题,即在价值评价上做文章。韩愈虽然具有了“原性”、“原道”的形而上的追寻意识,但最终还是止步于道德论层面讨论人性三品,未能提高到华严五祖宗密所说的“本源”即本体的水平。这说明,儒学要想真正实现创新,使“性与天道”论的意蕴真正得以发掘,必须突破将性与善捆绑在一起而仅限于从道德论上说性的束缚,以此才有可能将儒家的理论水准推进一步。
然而,“善”作为儒家哲学的价值基准又不能不讲。这样一来,既讲善又使善与性相对分离的另一思想资源,即“继善成性”说便开始为人们所注重。从韩愈的“原性”、李翱的“复性”,再到宋儒的“成性”,说明理学家是将与善相区分的本性观的建立作为儒学复兴的中心内容的。事实上,佛学在这一方面已经为儒学的新生提供了直接的样板。慧能禅宗倡导“佛性清净”、“人性本净”,使清净的本性不再与善恶评价相关联,从而廓清了明心见性以觉悟清静本体的问题。
当然,先天本性在人如何成立,这不是出世的佛学而是入世的儒学所关心的问题。但儒学的本性观要成立,不可避免地要借鉴佛学的理路。如此一来,“性与天道”论的重心必然要落在客观天道如何成就人的本性上,“继善成性”的理论构架则正好适应了这一理论需要。从另一方面说,理学时代的到来,通常是以二程“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论为标志。但天理的一般本体,表现在人则各有其性,即所谓“性即理”的模式,“所谓理,性是也”。这与从天道生生到本性建立的“继善成性”说所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继善成性”说的优长,是其由天至人体现为一个以天道为本而构筑本性的思辨逻辑。这一逻辑的前提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按照《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的规定,天道就是阴阳之道。那么,从道经善到性的序列,则为本性观的成立提供了天道的客观基础,而善则处于中介的环节。作为天道流注的产物,善在这里体现的是天道生生的普遍原则,《易·文言》之“元者,善之长”一句已说得非常清楚。由此而将传统儒学论善只限于人性善恶领域的狭小眼界,拓展到整个宇宙,“六合之外”的世界不再是佛老哲学之专长。
但是,放眼六合之外,又必须落脚于人性之内,只讲善的普遍性而不讲特殊性,此善对立足于人生世道的儒家来说便没有意义。“继善成性”的意义在于说明,万物通过自身的生长化育使天理(生理)获得实现。对于天地间的每一生物主要是人而言,这一过程是以具备此道、此善而成就自身的本性并与他物相区别为结果的,所以说是“成之者性也”。如此普遍之善与个体之性的顺序过渡,从根本上说明了个体之性成就的合理性和价值的肯定性。那么,天道化生万物就不仅仅体现的是宇宙秩序的合理,而且是为人的本性在价值层面值得肯定和推尊打下的最根本的基石。在一定意义上,只有讲到“继善成性”,乾卦《彖辞》所说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才真正得到了落实。可以说,传统儒学对于自我能否确立起心性本体,基本上没有意识。禅宗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给儒学的启发,就是心性本体的挺立,只能是“各正性命”,即“成性”不是成普遍性,而是成特殊性,即在自我的形而上的本性的奠定。
在一般意义上,天道生生在人生就是“成性存存”,这在《易传》已讲得非常清楚,二程和张载也都是这样来论述的。而“成性存存”作为“道义之门”,说明“继道”之善是在“存而又存”的“成性”实践中不断积累而成的。所以,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张载和二程等人讨论性与善关系的基点,不论在文本还是诠释上,都主要是《易传》的“继善成性”而非孟子的性善论。这说明,北宋新儒家的理论兴趣,重点在利用天道性命流注的生成论基础去阐释和看待个体的道德创造,解决个体心性修养在天道生生中的合理性问题。孟子讲究道德价值自我实现的性善论模式,自然就受到了人们的轻视。
事实上,通常不归入理学阵营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对孟子性善的批评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譬如,苏轼就是按照他所理解的“继善成性”模式去反驳孟子性善论的“以善为性”的,认为孟子是“不及见性而见乎性之效”(《苏轼易传·系辞上》),将性之效用(善)混同于性本身,所以根本是错误的。
当然,这并不等于讲“性善”就没有了地位。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既会产生对现实背后的本性的追求,也会考虑这个本性在现实世界的意义,而后者就是“性善”所要回答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顺“继善”与“性善”间的关系,以适应本性观建构的理论需要。程颢讲过,“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遗书》卷一)。这说明,以“继善”说性已成为当时流行的风气。但此种讲法只是说了继天道普遍之善而布洒在人性上的结果,也就是孟子的“人性善”;或者说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模式,天降性于下而万物“各正性命”。但实际上,“各正性命”或“成性”又离不开主观自觉,用张载的模式说,就是要“变化气质”而“善反”之,天地之性方能存(成)。否则,人性则不必然为善也。同时,“凡人”的讲法也无助于揭示理学理论建构所需要的先天本性。因为“‘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遗书》卷一)。以“善”说性已不是先天本性——先天本性不可得而说也。
但是,如果因为“不容说”就不说,也是有问题的。这就如同“道可道非常道”却又不得不“道”、“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又必须要“闻”一样。“不容说”则仍然要说。这就需要对“不可得而闻”和“性善”的观点作出新的解释,以适应本性观建构的理论需要。在前者,程颐的解释是子贡实际上已“亲达其理”,之所以还要说“不可得而闻”,不过是“叹美之辞”(《外书》卷六),因为众人很难达到这样的本体境界。
“叹美之辞”概念的提出,对于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至关紧要。它说明,北宋新儒学已经找到了一条将“不容说”与“可容说”结合起来以论证本体的道路。这在实质上可以说是虚实相应,如张载的“太虚即气”和程颢的“性气相即”;而在形式上就是“叹美之辞”。
“叹美之辞”的概念,不仅可用于解释“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而且可以解释“性善”;这既保证了性体对人生的善的价值,又不会使它仅仅局限于道德论的层次。譬如,程颐讲:“称性之善谓之道,道与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谓之性善。”(《遗书》卷二十五)比较孟子的“性善”,显然已有了重大区别:“善”在这里并不意味实际的道德价值,而只是形容美好的词语,因称赞性之美好如此(道),所以才要说“性善”。换句话说,“性”实而“善”虚,中心是“性”而不是“善”。程颢在分析“德性”的概念时,也强调说:“‘德性’者,言性之可贵,与言性善,其实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韫也。”(《遗书》卷十一)“德性”与“性之德”不同,它只是在突出性的珍贵,而不是像某卦具有某德那样是所有关系;与此相应,“性善”也就与“性之善”不同,它强调的只是性之美好珍贵,而并非是说性“所有”善。
如此以“性善”为虚指而为叹美之意,在作为程学后劲的湖湘学那里得到继续,所谓“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也,不与恶对”(《知言疑义》)。性作为“天地之所以立”的根据和哲学本体,是超善恶的,即性在善恶之“上”,不然,也就做不得本体。一方面,性作为最高范畴,除了赞叹其美好而外,不能也无法以别的什么范畴去规定它;另一方面,以性善为叹美之辞,可以方便地解决本性观创立的重大理论困境:性体“难名”又不得不名的问题。这里,即是利用“善”的名号去补充“性不容说”之缺失。张栻总结说:“大抵性固难名,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为有根柢也。但所谓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难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说’而遂不可说,却恐渺茫而无所止也。”(《南轩文集·答胡伯逢》)性虽难言但不是不能言,性“善”便是形容性体的最恰当的名言。那么,近看从程颢到张栻,远看从老子到理学,本体难言又不得不言的困惑,在理学家那里已获得了基本解决。尽管不同理学派别的最高范畴有所不同,但不论是天理、太虚还是心性,如同老子的道一样,遇到的理论窘境是同一的,张栻的阐释具有一般的性质,从而能使理学的本体范畴得以顺利奠定,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
标签:理学论文; 孟子论文; 儒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宋代理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国学论文; 天道论文; 遗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