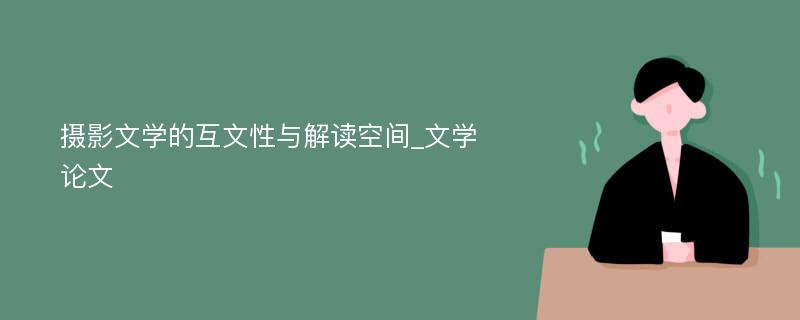
摄影文学的互文性与阐释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空间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体验激起的理论兴趣与后设视角
“除了体验所得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知识”,(注:(美)林赛-沃特斯:《美学权威主义批判》,《前言》,昂智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体验诗学这样说。在体验诗学看来,文学乃至一切艺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文本内部的东西,它发生在人与物之间。只有在你获得某种体验之后,你才开始意识到你所接触的是艺术。只有当体验是如此的强烈而不可忽视,而且自我意识作为一种副产品涌现出来时,艺术才可能获得确认。我对摄影文学的理论兴趣,来自这样一种艺术的体验。我发现在“看”和“读”了一些摄影文学作品之后,我深深地被吸引住了,似乎是小时侯看连环画时的体验,又似乎超出了那样的体验。是什么呢?体验的是诗意和形式美,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摄影文学当属文学。它的主要性质取决于摄影图象的加入。是以图象为主要欣赏对象、以文学话语为意蕴支撑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样式。它在接受方式上改变了文学阅读中单纯的文字信息进入阅读者大脑之后转换为形象的接受方式,而变为双重符号系统在互相交织、互补的机制中被接受的方式。读图是对读文的辅助,读文也是对读图的辅助,两者互为阐释。言不尽,立象以尽意,曾经是中国人的选择,这是出于文体的思考,也就是说是立在文学的立场上力求达到尽意的期望而产生的苦恼和选择。以此推理,任何文本形式都有不能完全尽意的遗憾,图象依然。在摄影文学中,既是言不尽立象以尽意,同时也是象不尽,立言以尽意。这是人类意识到表达有限度而采用补充方法的智慧表现(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在他的《在言象结合中拓展意义空间》所言)。摄影文学的言与象的这样关系,以理推之,当会产生互文性。所谓“互文性”,是朱力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表示任何一部文学文本“应和”其他的文本,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种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是公开的或隐秘的引证和隐喻;较晚的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对文学的代码和惯例的一种共同积累的参与等。(注: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页)
既然摄影文学采用的是双重符号体系,并且产生互文性,那么采用现代符号学,来分析摄影文学就是可行的。自索绪尔倡导和发展现代语言学以来,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将之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拉康将之运用于精神分析学研究;福柯则扩展性地运用到对于不断变化着的事物的辨认、分类和对精神病治疗的分析上;罗兰-巴尔特将之用来评论和分析许多关于世界的“资产阶级的神话”的组成因素和代码,比如对著名的艾菲尔铁塔的分析等,都取得了另人瞩目的成就。在运用符号学的同时,我还将始终站在摄影文学之外来看摄影文学,保持后设性,即元文学的视角。
二、摄影文学中言辞文本的符号系统特征
我将摄影文学的文字部分称为“言辞文本”,之所以不称为“文学文本”,是因为摄影文学也可以被称为“文学文本”,为了与之相区别,我在后面始终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词,而将摄影图片称为“图象文本”。
言辞文本的规律已经基本获得共识。在索绪尔看来,言辞符号是任意的,除了很少一部分的“拟声词”以外,在言辞的“意符”和“表意”之间没有固定的或自然的联系。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并不能重合。依据着不同的语境,能指可能有许多种所指。在语言学转向之后,人们已经认同了:文本和现实是两回事。正如杰姆逊所认为的那样,关于世界的语言只不过是语言,而不等于世界。这给予我们一种警觉:不能轻易地相信所谓“真实”。
与这样的警觉相关的另一个语言事实,即现代修辞学的成就所表明的事实是,人基本上是语言建构的产物,我们的文化、我们个人与他人的日常对应关系,都凭借着语言而存在,当社会发生变化,朝代更迭之后,语言及刻铸在语言上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甚至我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完全变换。比如我国五四运动,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的语言,但是文言里的修辞格,大部分依然保留在白话里。在默默地传递着文化传统。现代修辞观还认为,语言是先有比喻义,后有本义。依此,文学里的语言在本质上是隐喻的。摄影小说《将军泪》是篇优秀之作。它依然没有逃脱语言中的这种比喻义先于本义的规律,而且这种比喻义也在发挥着它的诗性作用。《将军泪》中图19的言辞文本为“孙二勇大口大口地喝酒,他微醉了。突然他一把扯开自己的衣服。伤痕斑斑,每一道伤疤都有一个流血的故事。这些伤疤大多是为张自忠留下的”。图20的文学语言为“张自忠也哗啦一下撕开自己的军装,这些伤疤是为中国留下的”。这两段文字构成一种可叫做“联锁”或者“偏重”格。这种修辞本身就有“意味”,因为其中携带着引申义,“为张自忠留下的”和“为中国留下的”,都不是本义,而可以引申为为张自忠的爱国事业为忠于张自盅而留下的;为保卫祖国不被外族侵略,为了祖国的神圣而留下的。其中渗透着身/家/国的递进并被包容的关系,这是一种出于意识形态认可和想象的结果(我只是从学理上说,而不含任何价值评价)。可作为这个现象旁证的是加拿大阿尔伯达大学教授高辛勇在《修辞学与文学阅读》中所举的我国《大学》中的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段子: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先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致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高辛勇指出,天下,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不仅是层次的关系,也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在概念上它们有“偏全”格的关系,从天下讲起,确有其修辞效用。但更有传统观念里家国一体,个人只是家、主要是国的一部分的意味在其中。从“修身”到“致知在格物”,因为层递格的关系而形成了“全体”与“部分”,同时又是“内”与“外”的关系。高辛勇的论述告诉我们,修辞常被逻辑所遮蔽。让我们再来看《将军泪》的图19、20的文学语言,确有逻辑上的承续关系,但也有修辞关系,而这种修辞关系本身就是传统给予我们的。因此,语言,指明那些自称为真实的东西原来仅仅是一种比喻。《将军泪》的爱国情怀、爱自己部下而又严守军规的矛盾给予张自忠将军的心灵痛苦,这一切的艺术魅力,也来自这样的修辞所夹带的传统文化。指认出语言中自身携带的修辞作用,在提起我们警觉(后设性)的同时,也能提高我们以此增加文学诗性的自觉性。
三、摄影文学中图象文本的符号系统特征
第一,在语言符号系统中,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关系,而图象符号系统中的能指与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则不是任意的。也就是说,总是和一个能指相对应的所指存在于那里。我的意图却是,超越能指与所指的非任意关系,而认识到摄影符号的喻说性质。这一点进入摄影文学时,很有意思。表面看,摄影文学图象的画面是真实的(不就是因为现实中有这样一些事物和人,才为拍摄提供了物质性的存在依据吗?)而且,我们一贯认为,因为用标准镜头,不设计演员的摆拍,就可以还原“真实”,这只能是误解。这对我们认识摄影纪实文学非常重要。大千世界,永远是拍摄不完,纪实不完的,我们所看到的摄影纪实文学(包括摄影报告文学)等,为什么拍摄这些,而不拍摄哪些?图象依然是符号,有一双眼睛在摄影机后面操纵着这些符号。这里我们借用喻说理论来认识图象符号的喻说性质。雅格布逊将比喻分为隐喻和换喻两种。而维柯则分为四种:隐喻、换喻、提喻、讽喻。其中的提喻,是就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整体的意义在部分中得到体现。摄影机的取景框中摄入的事物和人,就是从大千世界中提取出来的那么一部分,摄影作者认为这是最能表达他对现实的理解,最能代表整体本质的,这一部分可以喻说整个世界,因此,正如臧策先生所认为的,摄影也可被看作是一门提喻的艺术(注:关于摄影是一门提喻艺术,这个提法来自臧策先生题为《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的系列论文,臧策在系列论文之二的《围剿“观念”的背后》(载于《中国摄影报》2001年3月2日)中有“我个人认为:摄影中快门瞬间的把握,既是一种‘提喻’。也是摄影区别于电影、电视的根本特征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影又可视为是一门‘提喻’的艺术”。笔者曾就这组论文发表过文章《冰山理论:海平面上、下—读臧策的《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论文》认为:把摄影看作是一门提喻的艺术,“这是臧策这一组论文在摄影理论上的重要突破,即便是放在国外的有关摄影理论中,也是处于前沿位置的。将摄影纳入语言、修辞系统,纳入编码程序之中来看待,是现代摄影理论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一转换又是十分困难的,而臧策的系列论文在这方面做了有意义的突破。”(发表于《中国摄影报》2001年6月29日))。摄影报告文学《躺着的铁匠和他的女人》,摄影者显然是将镜头直插那个“位于湘、浙、皖的交界处,被重重的大山四周围困着”的江西省婺源县浙源乡,在浩大的中国农民人群中提取出余根源和他的一家,这也是一种理解的提喻:人生是各种各样的,人的一生都在路上,路,坐着汽车,坐着大车,迈着双腿走过的路。这是各种走法所共同构成的整体。而余根源却躺在床上,余根源一旦离开了床,就只能趴在妻子的背上。这是从整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人走路的人生状态。其他如摄影纪实文学《一只铝盆的制作过程》《农家饭场纪实》《巴山“背二哥”》等都可以证实摄影的喻说性质。
第二,与言辞符号相区别的另一点是,语言是历时性的,而图象符号是共时性的(就单独一幅图象而言是共时性的,但在摄影小说等叙事体摄影文学中,图象成为系列,已经具有历时性)。图象的字面意义,也就是“能指”,相对于事实存在的所指,有没有可“阐释”,可“赋义”的可能?有没有“转义”?这里我们进入“构图”的修辞学性质,进入取景框,已然是一种提取,而如何构图,则已经是对现实“真实”的改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修辞。或者说,从“构图”始,就有了“想法”,而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而没有那样的“想法”?可见有“想法”的同时就在“赋义”。这点很重要。后面我们论及到的“互文性”时会用到这一点(越是有“想法”的构图,就越为言辞文本提供广阔的再创造的空间)。我举一幅没有配以文学文字的摄影作品为例。笔者在《中国摄影报》2001年3月2日《作品》版刊登的“读者园地”栏目,看到一幅题为《农家女学童》,画面的主要部分是晾晒的玉米,玉米旁边有聚拢玉米用的耙子,在玉米边,有一个女孩在学习,似乎在写作业。点评人写到:“晾晒玉米的女孩,忙中不忘看书学习,很感人。金黄色的玉米,展示出丰收景象,孩子认真学习也预示一定取得好成绩。如果把人物拍得大些,效果更好。”把女孩子和晾晒的玉米框在一幅画面中,这构思本身就是有“想法”的,晾晒的玉米是已经的丰收,而丰收前曾有过辛勤的劳动,而女孩现在的认真学习,也将会得到学习上的大丰收,玉米的丰收,隐喻着女孩学习上的丰收。如此分析这幅摄影作品,其实已经是开始在进行文学创作,也能给我们“除魅”:不存在与事实相符的“纯摄影”,构图之时“转义”便不期而至。臧策先生提出,图象在转换成话语之前是否可读?是否具有意义?(注:臧策:《关于《摄影-批评-文化研究》……兼答高恒文先生》,近期将在《中国摄影报》发表)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能转换成话语就表明是可读的,可读的,就是有意义的。前面所分析的《农家女学童》就是证明。
第三,图象符号的阐释空间。阐释空间有方向性,在摄影文学中,是向文学方向的阐释。是“画中有诗”的问题,“画中有诗”是指有“诗意”。与言辞符号相比,图象符号的阐释空间要相对小一些。这与如前所说的能指和所指不是任意的关系有关。但依然是可阐释的。阐释什么?阐释有文学性的东西。形式主义美学认为,文学是语言的一种类型。关于这种类型的语言法则产生了文学性(literariness)的独特因素。罗曼-雅格布逊在1921年写到:“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是使一部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因素”(注:M.H.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雅格布逊就文学性产生的条件说的“独特因素”面有点窄。仅就语言自身的法则运作的结果而言的(此处不就这个问题详述)。
图象符号的阐释可以有如下一些方式。
其一,图象字面义的解说。解说不是纯客观的,而是调动作家的记忆表象,凝聚在对这幅图象的阅读中。在向历时性的方向掘进中,赋予图象以历史时光,意义在时光的回溯中产生。这是仅仅读“图”所无法获得的。比如摄影散文《心中的东溪》三幅照片。散文的前半部分是平面的描绘故乡的东溪景色,所依的是一天中的时间顺序:“清晨……”“中午时分……..”“当太阳向西边的杨梅山靠近…….”“月亮徐徐升起…….”这些言辞符号已经超出了图象符号的所指。后半部分则笔锋一转,追溯时光:“最使人难忘的,是那个古渡口。我不知这个渡口已有多大年龄,只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和哥哥一起搭渡到对岸的山坡上去采集过松树籽;也常和小伙伴从这里下水,嬉嬉闹闹游得痛快。……..每次回乡,我必定要去一趟渡口,特别是在黄昏之际,在那磨得发亮的石头上静静地坐着,看渡船和满船的人,溶进金色的波光里,目送他们上了岸,带着一天的收获,踏上回家的路。”沿着回忆的隧道,走到以往时光中的某一个空间中,拓展了另一幅画面。这样的回溯时光,是两维的图象符号所无能为力的。而言辞符号的阐释给予了时间感,共时性中产生出历时性。
其二,将图象符号纳入文化传统的诗性视野中,使之同化于言辞符号所展示的意蕴中,从而发生隐喻意义。在以景物或大自然为主要字面义的图象符号中,这样的阐释特点最为显明。话语本身所先天夹带的引申义起了重要的修辞作用。尤其是一些“典”,给图象赋予了诗意。比如题为《菊影》的摄影散文,伸发的是“菊”的“圣洁与高雅,争气与大度,悄然而生”“菊的精神观照过的生命,是淡远的,是无愧的,是辉煌的”“爱菊花吧,菊的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菊的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这样的阐释,显然得益于中国文化中的松柏梅菊等意象的诗性传统,如“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等。再如摄影散文诗《鱼的自白》,用鱼的口气,吐露了它戏之于莲叶之间时候他人不知的快乐、自如。有这样的文字:“你可曾听过千年的传说?你又不是我,你又不在我的肚里,你怎么知道我不在想什么?”《庄子》外杂篇中的《秋水》所载的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与“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典”,给予了这段阐释以情趣。这类阐释,运用的是“互文性”中“较晚的文本(言辞文本)对较早的文本特征(图象文本)的同化”的方法。
其三,在图象文本中的各个事物之间通过联想而产生意义。可以用隐喻,也可以用转喻,来处理此事物与彼事物的关系,这是在一个图象中的互文性。比如摄影诗《果实》,厦门大学教授黄鸣奋已有分析,他是从诗与图象的互文性来说的。而我则从图象文本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产生意义的角度来分析的。大树枝桠的投影上,坐着几个女孩身着红衣,还有身着绿衣的男孩,孩子们象是树上结的果实,红的,绿的,是植物的果实,可又毕竟是孩子们,他们也是即将成熟的社会的果实。大树枝桠的阴影与孩子们又构成隐喻:树可以理解成根深的“传统”,果实和大树互相映衬。
应该指出的是,如上所列的三种方式在实际的阐释中,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可以相互匹配使用的。
四、言辞文本与图象文本之间产生互文性的几个问题
我们已经分别就摄影文学中的言辞文本和图象文本各自的符号系统特征作了分析,尤其就图象符号的阐释方式作了分析。而且我们的分析主要是就先有图象文本,而后进行言辞文本创作的程序来分析的。下面我们就互文性深入地探讨几个问题:
第一,图象的排列与言辞叙述的结合。在摄影小说等连续性图象系列中,若干幅图象之间构成的是图象符号系统。选择哪些图象,如何编排这些图象,这依然是一种“提喻”,也就是“喻说化”“故事化”的过程,更是一种叙事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与言辞文本相匹配。如果我们认为摄影小说是先有话语文本,而后再有图象文本,那么,话语文本的叙述与传统的纯文字式小说的不同,就是叙述的选择和空白,叙述什么不叙述什么的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作者面前。叙述是对事件的见证,事件是绝对的,而叙述则是相对的。叙述是事件的展示方式,叙述给出了如伽达默尔所说的作者观看那事件的“观点的透镜”,这透镜标示出一个角度和一种观看方式的选择。所以叙述不可避免地会留下空白,这是必然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同时也是一种策略的显现:叙述什么,留下哪些空白,都依作者的理解而定。即便在叙述出来的文字中,其编排本身就是一种修辞,文字叙述又影响到图象的编排和修辞手段。提喻的意义始终在显现:将那相对来说比较长均速行进的故事作为整体,而将最具有隐喻作用的事件叙述出来。这已经是一重创造,而另一重创造,既图象的编排在此基础上,还有一次创造。也就是,如何根据文字叙述,分解那若干个镜头,如何利用蒙太奇手法编排图象,这是一种修辞,也是来自于特定的理解。不同的摄影艺术家、改编者、策划和导演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些人,是文学文本的重要的具有转折意义的读者(他们承担着用镜头所获得的若干图象编排起来,向观众讲述这个文本的任务)。已有学者在探讨摄影小说的叙事时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而我想指出的是,在这一切之后的那双“眼睛”。互文性与那双眼睛分不开。其实,已经有人意识到在这个转折的关头,影象遇着文字后,背后那双无所不在的“眼睛”的重要。比如,《摄影文学导刊》28期李晓红就写到:“当影象遇见文字,你认为会怎样?”李晓红说,她很遗憾电影《廊桥遗梦》有些镜头处理,她说:“我常常想,也许我应该作一部李氏版本的《廊桥遗梦》。”因为,“心里一直对几年前的一部美国电影《廊桥遗梦》耿耿于怀,因为它不能用影象说出文字背后的东西”,“对于小说《廊桥遗梦》,如果我能够,我要拍摄这样的一幅画面:我要浓墨重彩地表现最能体现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却被电影导演轻轻带过的重要细节:……”“当影象遇见文字,你认为会怎样?我想,一定有许多罗曼蒂克的事情发生”。她认为,摄影文学,这种相对于电影来说非常平民化的艺术,也许可以实现她的重新诠释小说《廊桥遗梦》的梦想。李晓红的潜台词是当影象遇见文字,影象在自己的组合中可以重新诠释文字。王岳川在《信息化中的图文时代》一文中这样评价摄影文学:“传媒时代中的‘摄影文学’,是在后现代平面化传媒时代中一种重造精神深度的努力”。(注:王岳川:《信息化中的图文时代》,载《摄影文学导刊》第七期,2001年2月23日)我以为,图象编排与叙述后面的那双眼睛,正是创造精神深度的通道。这为摄影文学的作者、编导提出了高的要求。
第二,提问与回答:互文性的基础。摄影文学的图象文本与言辞文本,因为要互相匹配而组成共同的艺术,它们之间的互文性,建立于不断地互相提问和互相回答的关系中。无论图象文本在先,还是言辞文本在先,较早的文本总是对较晚的文本提出问题,而较晚的文本总得对较早的文本加以理解。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某个流传下来的本文成为解释的对象,这已经意味着该本文对解释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解释者必须设想本文讲述的一切是对某个问题的回答,因此解释者将文本作为对此提问的回答时才能理解文本,也只有理解了文本才能回答文本的提问。因此,“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问题提出问题,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75页,第482页)提问越多,回答也就会越多。在摄影文学中,两种文本形式的互相阅读,是多次的行为。我们以摄影纪实文学为例,因为这类作品的图象,都没有演员的表演,而是生活中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固然摄影者选取这些人和他们的生活,如前面说的,是“提喻”,是对判断和评价,但是,当配以文字的时候,依然存在从这些所谓“纪实”图象中发现什么,如何解释的问题。《躺着的铁匠和他的女人》、《山那边的世界》《农家饭场纪实》《巴山“背二哥”》《一只铝盆的制作过程》《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等一批作品。作者和编导向所获得的系列图象中,询问的是作为“最后”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中的人们,作为边远的几乎被社会所遗忘的人们,他们那份自足、怡然。感受和看重的是怀旧和对平凡的底层人生的认同与关注,(当然,能够获得这些照片,也恰恰是这些感受和关注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对这些图象提出的问题更丰富于上面所说,更复杂些,这些图象所展示的意义可能会更多。
标签:文学论文; 互文性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摄影论文; 中国摄影报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廊桥遗梦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