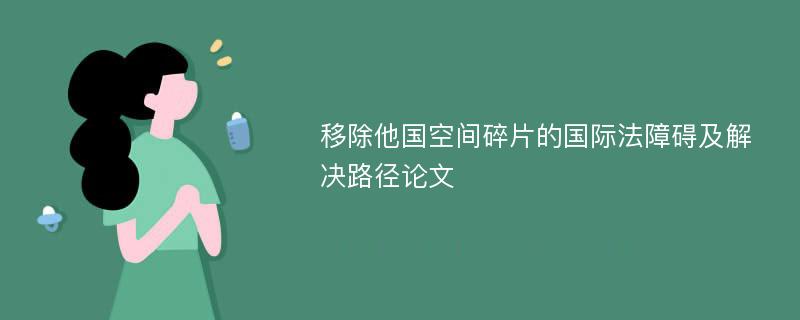
移除他国空间碎片的国际法障碍及解决路径
赵 青*
[摘 要] 空间碎片是丧失功能和可控制性能的空间物体,其按照登记状态可分为可辨明登记国的空间碎片和不可辨明登记国的空间碎片。随着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空间商业化的发展,空间碎片的移除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即使对于拥有经济实力、技术能力和移除意愿的空间活动参与者而言,移除他国登记的空间碎片仍然会受到国际法赋予登记国的管辖控制权的限制。此时,如何依靠国际法保护各国进行外空活动的自由、促进主动移除外空碎片活动的发展是空间碎片移除法律制度完善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保护非登记国正常的空间活动,促进空间碎片残留问题的解决,应当取消登记国对空间碎片的专属管辖权,规定各国均享有一定程度的移除权。当第三方机构认定某一空间物体为空间碎片后,各国均具有移除碎片的权利,只是登记国拥有优先移除的权利。
[关键词] 空间碎片 移除 管辖权 移除权
引 言
空间碎片是存在于地球轨道或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没有功能的人造物体。目前,大量的空间碎片残留在外空中。空间碎片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具有功能的空间物体的数量。根据ESA的统计,截至2019年1月,直径大于10厘米的空间碎片有3万4千个,直径大于1厘米小于等于10厘米的碎片有90万个,直径大于1毫米小于等于1厘米的碎片有12.8亿个。(1) See ESA,Space Debris by the Numbers , available at: http://www.esa.int/Our_Activities/Operations/Space_Debris/Space_debris_by_the_numbers. last accessed on July 15 2019.这些失去功能的空间碎片占据了外空有限的轨道位置,对于其他空间物体的正常运行带来了威胁。而且,随着空间活动的发展,空间碎片将继续增加,空间碎片减缓措施和空间碎片的自然返回都无法阻挡这一趋势。大量的空间碎片占据了有限的空间轨道,对工作中的空间物体带来了碰撞风险,其威胁不可小觑。空间碎片在轨道上高速运行,所以即使很小的碎片,在与工作中的卫星碰撞后,也会给后者带来致命的影响。另外,外空中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大量失去功能的空间物体长期占据轨道,无异于对轨道资源的浪费。空间碎片在失去功能前是可以被登记的。虽然空间碎片不再具有外空物体的功能,但是外空物体曾经被登记的证据仍然可能留存于空间碎片。而这种登记状态是否能够辨明则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变化。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国开始讨论空间碎片的应对之策,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空间碎片的减缓,即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防止空间物体在任务结束时变为空间碎片。出于安全考虑,空间活动的主要参与国或多或少地采取了一些减缓措施。客观地说,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空间碎片的增速有所缓解。但人类逐渐发现,缓减措施并非长久之道。因为减缓措施无法使业已存在的空间碎片自动消除。即使假定各国可以自觉地、有效地落实空间碎片缓建措施,层层包裹地球的空间碎片依然可以使外空活动被“凯斯勒”现象——空间碎片间的多米诺骨牌式碰撞——的威胁所笼罩。所以,移除是彻底解决空间碎片问题的必要措施。
但是,移除技术的推广面临着强大的阻碍。除了资金和技术的掣肘,移除空间碎片遭遇了空间法的挑战。因为,自国际外层空间法律制度创立伊始,国家为了保护外空活动的自由,实现外空活动的有序化发展,确立了各国对其登记的空间物体的管辖控制权。这一权利的存在引发了与移除空间碎片相关的法律问题:在已有法层面,登记国对保有其登记标志的空间碎片是否享有同样的管辖控制权?空间碎片的登记国是否有相应的移除空间碎片的义务?非登记国可否移除他国的空间碎片?在应有法层面,国家移除他国空间碎片的权利是否是正当的?这一权利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应当设置对这种权利的限制?对于以上问题,本文将以非登记国移除对他国登记的空间碎片为切入点,分析国际法对移除他国空间碎片的限制,并提出障碍消除后的解决路径。
一、国际法障碍:登记国管辖控制权
空间碎片属于“被射入外层空间并留置于外层空间或天体的实体”。对于可辨明登记状态的空间碎片而言,登记国对空间碎片享有管辖控制权,包括立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以及技术角度的控制权。管辖控制权的存在使得任何移除活动必须以登记国同意为前提:其他国家不得对空间碎片采取移除措施,而任何私主体的移除活动必须事先经登记国批准;登记国的同意仅在紧急状态发生时存在有限例外。当发射国间约定共同行使管辖控制权或登记国将管辖控制权移转给非登记国时,登记国对其所登记的空间碎片没有管辖控制权,此时,他国的移除也无需经登记国同意。但事实上,权利的转移也是因登记国同意移转而产生,而且,此时的移除还需要经权利继受国同意。
(一) 登记国管辖控制权可适用性
登记国管辖控制权的依据是《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以下简称《外空条约》)第8条。管辖控制权的权利主体是各缔约国,客体是被射入外层空间并留置于外层空间或天体的实体,以及实体所载人员。主体与客体的连接点是登记,即缔约国必须登记了上述客体,才享有本条所规定的权利。
空间碎片可以是形态完整的空间物体,也可以是从空间物体上分离的残块。当空间碎片是形态完整,但失去功能的空间物体时,其必然属于被射入外层空间并留置其中的实体。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当空间碎片是从空间物体上分离的残块时,空间碎片是否属于管辖权客体。当组成部分未脱离空间物体时,第8条的管辖控制权延及组成部分。因为,当国家对空间物体整体享有管辖控制权时,其必须可以管辖和控制空间物体的每一部分,“有权控制整体但无权控制其组成部分”的解释是不符合逻辑的。所以,国家对从空间物体上分离出的组成部分依然享有管辖控制权。第8条中没有任何语词暗示了组成部分的分离可以使附着在其上的管辖控制权消失。相反,第8条对实体所载人员的规定还可以为我们所面临的解释问题提供参考。第8条规定,在外层空间中,即使实体所载人员离开该实体,登记国对其登记实体所载人员的管辖控制权依然存在。(2) See Legal Sub-Committee, UNCOPUOS, Summary Record of the Sixty -Sixth Meeting ,Fifth Session , A/AC.105/C.2/SR.66, 1966, p. 11.由此可见,因登记产生的对人管辖控制权不以人脱离被登记物而消灭。那么,同样作为第8条规定的管辖控制权的一种,因登记产生的对物的管辖控制权也不应因组成部分脱离被登记物而消灭。
(二)管辖控制权的内容
《外空条约》第8条规定了管辖和控制权,但是对于这一权利的内容却没有说明。理论界认为,该条中管辖权的内容应当从一般国际法上管辖权的表现来理解,(3) See Bernhard Scbmidt-Tedd and Stephan Mick, Article VIII, in Stephan Hobe, Bernhard Schmidt-Tedd and Kai-Uwe Schrogl (eds.), Cologne Commentary on Space Law, vol. I, Heymanns, 2009, p. 157; See also Bin Cheng,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pace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13.阿根廷在条约缔结过程中同样支持该观点。(4) See Legal Sub-Committee, UNCOPUOS, Summary Record of the Sixty Meeting ,Fifth Session , A/AC.105/C.2/SR.60, 1966, p. 4.根据一般国际法,管辖权可分为立法管辖权(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jurisfaction)和执行管辖权(enforcement jurisdiction/jurisaction)。 (5) See Bin Cheng,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pace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480; Also Cedric Ryngaert,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 James Crawford, Brownlie '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it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456; Malcolm.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6th edi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645-646.控制权是外空条约相对于一般国际法而言的特别规定,一国的控制权包括采取与执行法律无关的技术性措施的权利。
1. 管辖权
在一般国际法上,立法管辖权针对的是一国法律适用的地域范围问题。(6) See Cedric Ryngaert,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it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9. 在实践中,有些国家已经将其国内法适用于管理其所登记的空间物体上的活动和空间物体的权利状态:美国将其所登记的空间物体纳入刑法上的“特别的海事和属地管辖权(Special maritime and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7) 18 USCS, sec. 7 (6). 俄罗斯规定其法律适用于其所登记的空间物体上的一切人员,不论这些人是俄罗斯人还是外国人。(8) Law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bout Space Activity ”, Decree No. 5663-1 of the Russian House of Soviets, art 20.5 “Citizens of foreign states who take a space flight training course in Russian Federation or are involved in a flight on a piloted space object of Russian Federation [space object registered by Russian Federation, according to art.17.1—noted by the author] shall be obliged to observe the legislation of Russian Federation,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i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f Russian Federation.”哈萨克斯坦规定,登记于哈萨克斯坦、并由该国自然人或法人所有的、空间物体上的权利的产生、变更或灭失应适用哈萨克斯坦民法。(9) Law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on Space Activities , art.17.2 “State registration of space objects and the rights for them specified in subclause 1)of clause 1[space objects that belong to the individuals or to legal entites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as well as the rights to the given space objects] of the present article, is a record of space objects, the certificate of acknowledgement and confirmation by the state of occurrence, amendment or termination of the rights(the encumbrance of rights) for space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civil legisl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空间碎片属于第8条中的射入外层空间的实体,因此,理论上国家有权将其法律适用于空间碎片。实际上,我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在国内法中规定空间物体包括其组成部分。(10) 参见《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第2条;See also Space Activities Act 1998, art.8; Authorization of Space Activities and the Estabishment of a National Space Registry (Austrian Outer Space Act ), sec.2.其实,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对空间碎片的法律性质、移除方式以及移除程序等内容进行规定。目前,还没有国家对已形成的空间碎片的法律性质或处理方式进行立法,尽管如此,这一事实并不影响登记国将其现有法律适用于其登记的空间碎片,以及对其所登记的碎片制定新法的权利。
国家的立法管辖权并不能决定国家可以在何处采取实际行动。常设国际法院在“荷花号”案中指出:“国际法对国家最重要的限制是:除非存在授权性规则,否则,国家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他国领土上行使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辖权是属地性的。除非条约或国际习惯中有授权性规则,一国不得在其领土外执行管辖权。”(11) PCIJ, SS Lotus (French v. Turkey), PCIJ Reports, Series A, No. 10, 1927, p. 19. 另外,执法管辖权行使的前提是存在有效的、可被执行的国内法律。(12) See F. A. Mann, The Doctrine of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 111 Recuei des Cours,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1964), p. 128.
虽然空间碎片丧失了原本具有的功能,不能继续执行空间活动任务,但是,空间碎片仍然具有经济价值。 据统计,仅仅是轨道上的发射设备残片就含有约1000吨的铝。如果国家在轨道上将这些材料回收利用,则可节约50—100亿美元的发射新空间物体的费用。 (28) See Alexander William Salter, Space Debris :A Law and Economics Analaysis of the Orbital Commons , 19 Stan. Tech. L. Rev (2016), p. 234. 另外,登记国在碎片上还具有信息利益。空间碎片是空间物体整体或部分,其可能携带有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可包括技术信息、军事信息和国家安全信息。 例如,在联合国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讨论中,一些国家提出可以考虑对空间碎片的移除,但是在移除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国家对空间物体知识产权; (29) 参见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2016 年 4 月 4 日至 1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报告》,A/AC.105/1113,2016年,第22页。 美国将空间物体及其组成部分列入其国内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S)清单,对其进行重点保护。(30) 参见朱鲁青,关丹:“空间碎片天基主动清除技术相关法律、政治及经济问题分析”,载《国际太空》2016年第7期,第63页。
其一,对个人己经获得的知识进行管理;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新知识,吸取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优点和长处,弥补自身思维和知识缺陷,不断建构自己的知识特色;其三,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再加上别人的思想精华,去伪存真,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激发创造出新的知识。
2. 控制权
受控核聚变的研究之所以如此艰难,原因在于所有原子核都带正电。当2个带正电的原子核互相接近时,二者之间的静电斥力也越来越大。只有当它们之间的距离达到约3×10-8mm时,核力方可起作用。这时,由于核力大于静电斥力,2个原子核才能聚合到一起,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由于2个原子核聚合前首先要克服强大的静电斥力。因此核聚变反应在地球上的自然条件下很难发生。
理论界普遍赞同《外空条约》第8条中的管辖权是控制权的基础,但对于控制权的内容有不同认识。(13) See Bernhard Scbmidt-Tedd and Stephan Mick, Article VIII , in Stephan Hobe, Bernhard Schmidt-Tedd and Kai-Uwe Schrogl (eds.), Cologne Commentary on Space Law , I Heymanns (2009), p. 157; See also Bin Cheng,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pace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13.一种观点认为,控制权既包括管辖权中执行法律的权利,也包括与法律无关的、对空间物体进行的技术控制。(14) 参见尹玉海:《国际空间法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See also Manfred Lachs, The Law of Outer Space :An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Law -Making , Tanja Masson-Zwaan and Stephan Hobe(eds.), Nijhoff, 2010, p. 66.例如,拉赫斯法官认为,“控制”一词对于认定登记国的专属管辖权至关重要,登记国根据此条有权要求其他国家不得对其引导(direction)监督空间物体进行干扰。(15) See Manfred Lachs, The Law of Outer Space :An Experience in Contemporary Law -Making , Tanja Masson-Zwaan and Stephan Hobe(eds.), Nijhoff, 2010, p. 66.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控制权与执行法律无关,只是指采取技术手段的权利。这些手段包括登记国制定的,以确保空间活动顺利开展为目的的技术规则;也包括登记国采取的,引导、停止、更改空间物体运行的措施。(16) See Gabriel Lafferranderie, Jurisdiction and Control of Space Objects and the Case of an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ESA ), 54 ZLW (2005), p. 230.
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登记国的控制权包括采取与执行法律无关的技术性措施的权利。例如,登记国有权在地面控制中心,通过技术手段,控制空间物体的发射次序、空间物体的在轨位置、空间物体返回地面、向空间物体发送数据以及接收空间物体发回的数据等活动。(17) See Gabriel Lafferranderie, Jurisdiction and Control of Space Objects and the Case of an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ESA ), 54 ZLW (2005), p. 231.国家对空间活动的控制包括对发射空间物体的载体的控制和对空间物体在轨运行的控制。(18) See Gabriel Lafferranderie, Jurisdiction and Control of Space Objects and the Case of an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ESA ), 54 ZLW (2005), p. 231.
登记国对空间碎片的控制属于登记国对空间物体在轨运行的控制。登记国的控制权使其可以在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基于技术考量,决定空间碎片是否应继续在轨运行、何时移除以及如何移除;而且,其可以运用移除技术,移除空间碎片。
(三) 管辖控制权对非登记国的法律效果
在外空中,登记国是唯一对其所登记的空间物体享有执行管辖权和控制权国家。在空间物体上,非登记国并无以上两项权利。因此,登记国的权利限制了非登记国的移除。登记国的同意是非登记国移除行为合法的必要条件,而且,登记国同意的范围构成了非登记国进行移除的条件。另外,任何私主体移除空间碎片的活动也需要登记国的同意。此时,登记国的同意表现为:登记国的法律适用于其所登记的空间碎片,外国私主体的移除需要遵守登记国法律。当然,理论上存在非登记国援引紧急情况进行合法的单方移除的可能。但是,援引紧急情况有很严格的要求,此种例外成功的可能性因此降低。
1. 移除空间碎片需登记国同意
2. 紧急情况例外
《外空条约》第6条规定,非政府团体在外层空间的活动,应由有关的缔约国批准,并连续加以监督。私主体的移除行为发生在登记国立法管辖权的范围内,登记国是本条中所指的有关缔约国。所以,私主体的移除应当受登记国相关立法的约束。具体而言,私主体的移除是否合法要依照登记国的法律进行判断,其移除行为要遵守登记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如果其行为违反了登记国的相关法律,登记国有权在其有管辖权的地方(领土和登记的外空物体上),对其采取执法措施。需要说明的是,空间碎片上可以存在多个国家的立法管辖权,除非登记国与相关的非登记国就法律的适用达成特别协定,这种管辖权的竞合不影响非登记国私主体对登记国法律的遵守。立法管辖权竞合对私主体产生的法律效果是:私主体的移除需要同时遵守所有有立法管辖权的国家的法律。
如果一国没有援引授权性规则作为其执行管辖权和控制权的依据,其执行管辖权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外空条约》第8条是唯一允许国家行使执行管辖权的授权性条款。的确,空间物体上存在其他的管辖权连接点,比如,空间物体上的人员的国籍国对这些人享有属人管辖权。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他管辖权连接点只是国家主张立法管辖权的依据,而非执行管辖权的依据。在只有登记国对空间碎片享有执行管辖权和控制权的情况下,他国单方移除空间碎片的行为是非法的。这意味着,任何非登记国的移除行为必须经登记国同意而合法。非登记国若想移除空间碎片,必须在移除前或移除开始时得到登记国对移除行为的同意。非登记国必须按照登记国的国内法,确定其需要经过登记国的哪些机构或人员同意,或者其有证据证明同意其移除行为的机构或人员得到了登记国的授权。登记国是否同意要根据具体事件中登记国的表示及行为判断。登记国是否同意移除、同意采取的移除方式、移除的对象和时间等都需要非登记国注意,以确保其登记行为的合法性。
当登记国不同意移除空间碎片时,非登记国如果想合法地移除空间碎片,就必须证明空间碎片的存在属于一般国际法上的紧急情况。紧急情况是适用于国家移除的例外。
紧急情况(necessity)是习惯国际法上排除国家行为不法性的条件之一。非登记国援引紧急情况存在多重障碍。首先,其必须要证明空间碎片威胁的利益是关系该国生死存亡的利益或国际社会的利益,比如,该空间碎片可能与该国负责全国通信或定位的卫星发生碰撞,或者,某一空间碎片与全球或洲际定位卫星发生碰撞;而且,其需要证明这种威胁是紧迫的,必须要援引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某一空间碎片确实会在短期内带来危险;其次,其需要证明移除行为的唯一性,而这也是最为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其至少要证明登记国同意移除和移动本国遭受威胁的空间物体这两种替代性手段不可能实现的。显而易见,这种证明是很难成功的;再次,其需保证移除行为不会同时损害登记国的核心利益,比如,避免在移除过程中损害登记国的军事、全国通信、全国定位卫星等;另外,当移除国是空间碎片的发射国时,登记国可主张移除国对碎片的产生负有责任而导致紧急情况的发生,从而,排除该发射国援引紧急情况的可能。
(四) 阻碍的例外:登记国无专属管辖控制权的情形
在两种情况下,登记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可获得管辖控制权,从而可以合法地自主移除空间碎片。这种不受登记国管辖控制的移除构成了登记国管辖控制权阻碍的例外。《登记公约》第2条规定,共同发射国可通过协议约定《外空条约》第8条中管辖控制权的行使。登记国无专属管辖控制权的另一种情况是:登记国通过双边协定,将管辖权移转给非发射国,例如:在空间物体所有权转让的同时,登记国将管辖权转移给继受所有权的非发射国。
1. 发射国间约定共同行使管辖权
在国家实践中,共同发射国依据《登记公约》第2条,通过协定共同行使管辖和控制权。例如,我国与巴西缔结的关于资源卫星合作的议定书规定:“双方将依据在工作报告中所描述的特定责任,平等分享资源卫星03、04星的操作和控制权。”(19)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科学技术合作框架协定〉的关于继续合作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补充议定书》,第14条。 在协议共同行使管辖控制权的情况下,如果协议授予了登记国以外的其他共同发射国以执行管辖或控制权,这些共同发射国有权移除空间碎片而不受登记国管辖控制权阻碍。
2. 登记国移转管辖权至非发射国
国际空间法没有禁止登记国移转管辖权至非发射国。例如,联合国大会于2008年通过的62/101决议中,没有任何关于限制管辖权转移对象的规定。(20) See General Assembly, Recommendations on enhancing the practice of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registering space objects , A/RES/62/101, 2008, p. 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对移转管辖权至非发射国的默认态度。事实上,随着空间活动商业化的发展,管辖权移转更为普遍。例如,荷兰公司New Skies NV通过所有权转移的方式取得了国际通讯卫星组织的NSS 6和NSS 7的所有权。荷兰政府声明自己不是这两颗卫星的登记国,但却拥有对两颗卫星的管辖权; (21) See UNCOPUOS,Note verbale dated 29July 2003from th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Netherlands to the United Nations (Vienna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 , A/AC.105/806, 2003, pp. 1-2; also see Lyall, Francis, and Paul B. Larsen, Space law :a treatise ,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pp. 92-93.管辖控制权的移转和登记国对他国移除的同意的法律效果不同:管辖控制权的移转使他国移除具有国际法基础,移转生效后,他国移除自始且始终是合法行为,没有国际法障碍;而在登记国同意的情形中,他国移除是不法行为,只是个别移除因登记国的同意而解除不法性。
二、国际法障碍消除的必要性
(一) 登记国管辖控制权法益消除的必要性
登记国的管辖控制权保护的法益有二:一是登记国对外空自由利用的权利,二是外空整体上的法律秩序及外空的稳定性。因为空间碎片是已经脱离登记国控制的物体,所以,登记国对外空的利用事实上不能通过操控空间碎片来实现。另一方面,登记国无法在空间碎片上执行其法律,所以,登记国无法通过继续管理其空间碎片以实现保障外空法律秩序的目的。因此,当外空物体变为空间碎片后,登记国管辖控制权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消除。而且,登记国在空间碎片上存在的剩余利益可以通过其他非管辖控制权的方式得到保护。
4.中国的明治文学本质研究,在文学研究方法、研究内容重心选择甚至结论的获得等方面,受日本影响较大,能找出与日本的一一对应关系,原创研究较少。
1. 管辖控制权意在保护的法益
设立登记国的管辖控制权,既是一般国际法上国家权利的域外延伸,也是《外空条约》第1条和第2条规定的必然要求。(22) See Gabriel Lafferranderie, Jurisdiction and Control of Space Objects and the Case of an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ESA ), 54 ZLW (2005), p. 229.《外空条约》第1条确立了缔约国探索利用外空的自由,但是,在《外空条约》第2条规定的外空不得据为己有原则的约束下,国家不得通过将外空占有为自己领土的方式利用外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外空的探索和利用必须要依托空间物体实现。为了实现国家探索外空的自由,国家对探索外空的载体享有管辖控制权的制度应运而生。虽然,国家不能自由地占有外层空间、决定外层空间资源的属性,但是,其可以自由地决定利用何种载体来探索利用外空,并按照其意愿规制载体上的人类活动。从这个层面来看,管辖控制权的目的是保护登记国探索利用外空的自由。
通过收集“今日推广”近一周的课程名称及对应的播放量,对上述四个方面的课程分别进行了播放量排名前十的统计,发现语言方面的课占据大多数,约为82%,其次为社会文化约为15%,翻译约3%,而关于文学方面的课程几乎没有。
就外空整体而言,登记国管辖权保障了外空内的法律秩序。《外空条约》第2条确立的不能据为己有原则,使外空中不存在任何国家的属地管辖权。但是,外空的良性发展要求法律的存在以规制外空活动,而仅靠国际法来维护外空的法律秩序是不够的。因此,登记国管辖权就产生了第二个作用,即保障外空中的法律秩序,确保外空的稳定发展。(23) See Imre Anthony Csabafi, The Concept of State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Space Law :A Study in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Space Law in The United Nations , Nijhoff, 1971, p. XVII.管辖控制权给登记国带来了相应的管理其登记的空间物体上的活动的义务,对这些义务的履行促进了对外空秩序的保障。根据《外空条约》第6条的规定,有关国家应对其非政府团体的空间活动进行批准和持续性的监督,学者认为,这个义务应该被理解为:国家对其管辖权范围内的活动,应当进行批准和持续性的监督。(24) See Bin Cheng,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38-239; see also Bernhard Scbmidt-Tedd and Stephan Mick, Article VIII , in Stephan Hobe, Bernhard Schmidt-Tedd, and Kai-Uwe Schrogl (eds.), Cologne Commentary on Space Law , vol. I, Heymanns, 2009, p. 158.另外,第8条中“应当”一词,也被学者解读为赋予了第8条义务的属性。(25) See Bernhard Scbmidt-Tedd and Stephan Mick, Article VIII, in Stephan Hobe, Bernhard Schmidt-Tedd, and Kai-Uwe Schrogl (eds.), Cologne Commentary on Space Law, vol. I, Heymanns, 2009, p. 158.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因其享有管辖控制权,而同时负担了法律赋予其的监督空间物体运行的义务。管辖权使空间物体登记国的法律适用至空间物体以及其上的人员活动,并要求登记国实际执行该法律,从而,实现其维护外空法律秩序稳定的目的。
总体而言,管辖和控制权保护的法益是登记国对外空物体以及其所载人员活动的控制,实现各国在外空中活动的自由,而且保障一个稳定的法律秩序存在于外空,使得各国的活动不妨碍其他国家的自由。应当说,设置登记国管辖控制权同在公海上授予船旗国专属管辖权的原理是一致的。(26) See Imre Anthony Csabafi, The Concept of State Jurisdiction in International Space Law :A Study in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Space Law in The United Nations , Nijhoff, 1971, p. 122.
1.2.2 联合干预组、康复治疗组的治疗及发育商数 将0~2岁组、2~3岁组、3~6岁组各50例精神发育迟滞患儿随机分为2个亚组,每亚组25人(轻度异常19人,重度异常6人),对每亚组进行不同干预措施,其中康复治疗配合家庭康复的为联合干预组,常规康复治疗的为康复治疗组,治疗3个月,观察6组患儿治疗前后症状变化程度及发育商分数改变。
2. 管辖控制权意在保护的法益无法实现
事实上,针对于空间碎片,第8条规定的登记国管辖控制权所保护的法益并不能实现。首先,登记国在空间碎片上的管辖控制权已不能起到保障其外空探索利用自由的作用。空间碎片是脱离控制的外空物体,其已经不能作为探索利用空间的载体。此时,登记国享有权利只是一纸空文。在实践中,国家也没有选择对空间碎片保持控制,而是选择暂时或永久性结束对空间碎片的使用,例如,当envisat成为空间碎片后,欧空局公开宣布envisat任务结束,并暗示宣布结束任务的两个月后,将不再尝试恢复对envisat的控制。(27) See ESA,ESA declares end of mission for Envisat , available at: http://www.esa.int/Our_Activities/Observing_the_Earth/Envisat/ESA_declares_end_of_mission_for_Envisat, last accessed on 2019.7.15.
其次,登记国对空间碎片的管辖权的放弃不能带来免除其对空间碎片监督义务的法律效果。但实际上,登记国又无法履行这种义务。就这个层面而言,管辖控制权保障空间法律秩序的目的无法实现。空间碎片此时的状态犹如无国籍的船舶,二者的相似之处在于脱离了任何国家的有效控制。此时,要求无法执行的登记国法律适用于空间碎片,无助于实现对空间碎片的法律规制。对于空间碎片而言,此时登记国的管辖权和监督义务无法保障其上有稳定的、可落实的法律秩序。因此,管辖控制权所保护的空间法律秩序利益此时应当消除。最后,法律要求登记国持续保有管辖控制权,不符合“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一基本的一般法律原则。登记国既无法实现其权利,又碍于义务无法放弃权利,且无法履行义务。法律如果继续以保护登记国无法实现的权利为由,继续要求其履行义务,实属强登记国所难。
综上,本文选用基于C0复杂度的端点检测算法对接收到的语音信号进行端点检测,然后其进行10阶线性预测,去掉了传播中声道的影响,选择语音浊音段的激励信号使用广义互相关算法进行时延估计,对得到的时延进行一阶自回归滤波得到最终时延。完整的算法框图如图2所示。
3. 无需通过管辖控制权保护的利益
外层空间不是任何国家的领土,国家在外空行使执行管辖权必须依据明确的授权性规则。登记国享有执行管辖权的依据是《外空条约》第8条。登记国对于空间物体享有执行管辖权意味着:无论其登记的空间物体处于何地,登记国均有权对那些空间物体采取相应措施以执行其适用于那些空间物体的法律。对于空间碎片而言,这意味着登记国有权根据其国内法律法规,移除本国登记的空间碎片。例如,当一国规定其登记的空间物体在成为碎片后应当被移除时,登记国后续的移除行为就是在行使执行管辖权。
综上,空间碎片上的经济和信息利益并不属于管辖控制权意在保护的法益。从性质上看,其属于所有权保护的法益。因为,所有权强调的是对物、以及物上利益的占有和排除他人的占有;而管辖控制权强调的是将一国法律适用于物以及决定物的运行。应当承认,在物上适用法律以及控制物的运行是一种保障对物占有的方法,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方法。换言之,如果允许非登记国移除他国空间碎片,可以通过对移除权的限制来合理解决对空间碎片上经济和信息利益的保护问题。为了保护剩余利益而继续保持管辖控制权规定的做法难免顾此失彼,因小失大。
(二)非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3]美好生活需要除了物质和精神需要,也包含对美好环境的需要。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人们对于健康的饮食、新鲜的空气、蔚蓝的天空必然更加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人类的永续发展,伟大复兴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4]
1. 空间碎片对非登记国利益的损害
表现形式多样化 基于学习者的阅读习惯,多采用可视化的信息呈现方式,便于知识的理解、掌握和拓展,增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非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的一个重要考虑是自身的空间活动安全。空间碎片对空间活动带来的安全隐患是碰撞威胁。其可能引发的碰撞有两种:一是碎片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会产生大量新的碎片,当近地球轨道上的空间物体达到一定密度时,空间碎片带来的一次碰撞很可能引发链式效应——即“凯斯勒现象”;第二类是空间碎片和正在运行的空间物体的碰撞,这是空间碎片所主要导致的危险。在低地球轨道上,第二类碰撞平均5-10年就会发生一次。(31) See UNCOPUOS, Working report of expert group B: Space Debris, Space Operations and Tools to Support Collaborative Space Situational Awareness, A/AC.105/2014/CRP.14, 2014, p. 9.因为空间碎片在轨道上高速运行,所以即使是很小的碎片,在与工作中的卫星碰撞后,也会给后者带来致命的影响。1984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射了一个轿车大小的长期暴露装置。 此装置1990年由航天飞机收回,在轨道上停留近6年。检查结果显示,在其表面有3万多个被空间碎片撞击的痕迹,其中5000多个撞击坑直径大于0.5毫米,最大的直径达5毫米。 (32) 参见李春来、欧阳自远、都亨:“空间碎片与空间环境”,载《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6期,第544页。 空间碎片所带来的碰撞还可危及宇航员人身安全。仅在2016年,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已经4次进入避风港以躲避空间碎片可能带来的碰撞。(33) See Bryan Corley,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Debris Avoidance Process , 20(4) Orbital Debris Quarterly News, 2016, p. 7.
而且,碰撞会使国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据统计,制造一个卫星平均需耗2亿美元,(34) See Jared.B.Taylor,Tragedy of the Space Commons :A Market Mechanism Solution to the Space Debris Problem , 50 Colum . J. Transnat'l L (2011), p. 261.而碰撞会减少包括卫星在内的空间物体的财产价值,甚至可能将其损毁。另外, 一些具有重要功能的卫星(例如覆盖全国的定位和通讯卫星)如果停止服务,会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带来威胁。事实上,俄罗斯代表在联合国外空委科技小组委员会第52次会议上,将空间碎片的清除同限制外空自卫权、禁止外空领域网络攻击一起,作为安全利用外空的建议指南提交至会议讨论。 (35) 参见王国语:“空间碎片国际机制发展趋势分析”,载《航天器环境工程》2015年第2期,第151页。
沙盘模拟实训课程属于综合实训,内容涉及到战略管理、生产管理、销售管理、财务管理等等多门课程的知识。同时,经营过程中,又需要进行好团队建设与管理,竞争策略的制定与实施等等,因此,沙盘实训课程既具有知识性,又具有实战性。
4.在班风建设中创设主动学习的班级氛围,让留守儿童在这个氛围中受到大家的感染,能够主动地、自主地学习,培养学习的兴趣。
目前,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搭建“民心相通”的桥梁,必然要求推进志愿服务国际化。目前志愿服务国际化有三种形式载体:政府间交往、企业志愿服务、个人志愿服务,志愿者们通过这三种形式为各国家地区的交流活动、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等提供国际化的志愿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助推器,助推了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的广泛合作,为中国志愿服务国际化发展赢得新机遇。
此外,大量的空间碎片占据了有限的轨道资源,将引发轨道资源利用紧张。从总体上看,空间碎片的数量庞大,远远超过了具有功能的空间物体,而且,这些碎片自我销毁需要漫长的时间,大量漂浮在外空中的空间碎片占据了本可由具有功能的空间物体利用的轨道位置。从空间碎片的具体分布来看,空间碎片集中于低地球轨道。据统计,约90%的空间碎片分布在低地球轨道区域内,(36) 参见李怡勇、王卫杰、李智、陈勇编著:《空间碎片清除》,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而低地球轨道同时是人类空间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从轨道分布的角度而言,空间碎片对正常空间活动的影响尤为显著。所以,移除空间碎片保护了非登记国正常运行的空间物体对轨道的利用,也减少了人类进一步增加对外空利用的阻碍。
2. 登记国移除其空间碎片的非强制性
根据目前的国际法,只有登记国可以对外空中的空间碎片进行移除。但是这种移除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登记国可以选择自己是否移除以及如何移除空间碎片。一方面,《外空条约》第9条没有对登记国施加移除义务;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形成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义务的国际习惯。
(1)《外空条约》第9条的角度
《外空条约》第9条规定了两种可能与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相关的义务。第一是避免有害污染的义务。第9条规定:“各缔约国从事研究、探索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时,应避免使其遭受有害的污染。”在缔结《外空条约》的过程中,国家并没有确定“有害污染”的范围。美国缔约代表指出,对外空造成有害污染的活动类型还需要通过科学研究进行进一步了解,目前不应建立过于严格的制度,以致阻挠空间研究的发展;(37) See Legal Sub-Committee, UNCOPUOS, Summary Record of its Sixty -Eighth Meeting , A/AC.105/C.2/SR.68, 1966, p. 4.法国缔约代表也认为,应当进一步讨论哪些活动可能对外空带来危害,而在未来依此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38) See Legal Sub-Committee, UNCOPUOS, Summary Record of its Seventieth Meeting , A/AC.105/C.2/SR.70, 1966, p. 8.目前为止,无论是从国家实践还是国家意见的层面上,各国并未就有害污染的解释达成一致:(39) 参见李居迁:“合法性、合理性与后续问题——反卫星实验的法律问题”,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48页。 在联合国法律小组讨论空间碎片的过程中,各国未就碎片是否属于有害污染达成一致,实践中也没有国家援引第9条要求制造空间碎片的国家移除空间碎片。从这个意义上讲,“避免有害污染”目前不能被解释为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的义务。
第一个问题是对“没有功能(non-functional)”的界定。首先要考虑的是暂时失去功能和永久失去功能的区分。应当说,要求登记国放弃其对暂时失去功能的空间物体的管辖权是不合理且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功能应当指永久失去功能。而对于永久失去功能的标准,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的定义值得我们借鉴。国际法协会对空间碎片的定义是:“外空中不活动或无用的空间物体,而且,根据理性估计,这种不活动或无用的状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改变(man-made objects in outer space, other than active or otherwise useful satellites, when no change can reasonably be expected in these condition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44)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port of the Sixty -Sixth Conference , 1994, p. 317; also Carl Q. Christol, Protection against Space Debris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 43 Proc. on L. Outer Space (2000), p. 350. 据此,永久失去功能是指,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根据理性估计,空间碎片无法改变丧失功能的状态。其中,“可预见”、“理性估计”等标准赋予了根据个案判定的灵活性。其次,要考虑“功能”的定义。任何一个空间物体被发射时均具有其目标功能,但空间物体不能完成目标功能并不代表其已经失去全部功能。在“失去目标功能”与“失去全部功能”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失去全部功能”这一标准更为合理。首先,移除者无法准确判定空间物体发射的目标功能,其根据目标功能丧失而进行移除很可能与登记国发生争端;另外,以“失去全部功能”作为失去功能的标准,有助于使登记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自己的管辖权、尽力恢复空间碎片的功能。因此,判定空间物体是否没有作用要以控制者是否能够控制空间物体为标准。如果空间物体脱离了控制,则可被认为失去了功能。空间物体失去控制的情况包括卫星无法接受任务指令、卫星无法传回特定位置信息等。
(2)国际习惯的角度
综上,笔者认为,可被各国自由移除的空间碎片是存在于地球轨道或重返大气层的,脱离控制者控制的人造物体。根据理性估计,这种脱离控制的状态在可预见的期间内不可改变。空间碎片不仅包括失去控制的空间物体本身,还包括其组成部分及残块。
三、解决路径:移除他国空间碎片权的设立
(一) 空间碎片的判定
建立各国对空间碎片的移除权的前提是确定移除权客体的范围,具体而言,即确立法律上判定空间碎片的规则。这一规则应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实体规则。实体规则应规定空间碎片的法律定义,其目的是明确哪些物体可以纳入移除权的范畴。其次,为防止移除权的滥用,防止正常的空间活动被滥用移除权干扰,我们也有必要建立判定空间碎片的程序规则。程序规则的目的是确定实践中具体落实空间碎片的判定标准。程序规则包括判定空间碎片的主体和判定过程中的证明责任分配。
1. 空间碎片的法律定义
如前所述,空间碎片是一类特殊的空间物体。目前,对于空间碎片的特征,外空活动的主要参与国已经形成了统一认识:空间碎片是存在于地球轨道或重返地球大气层的、没有功能的人造物体;它既包括丧失功能的空间物体的整体也包括其组成部分或残块。(43) 参见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联合国关于外层空间的条约和原则、大会有关决议以及其他文件》, ST/SPACE/61,2013年,第57页。 这一定义符合空间活动参与者在科学技术领域对空间碎片的认知,但若想使其符合各国对上权利义务的考量,则必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9条中另外一个与空间碎片产生联系的规定是避免对他国空间活动产生有害干扰的义务。但同样的问题是,空间碎片是否属于有害干扰是由制造空间碎片的国家或受到危害的国家在个案中进行认定的,即使我们将空间碎片解释为有害干扰,制造空间碎片的国家也只有和对方开启磋商程序的程序性义务。进行磋商既不能被解释为移除,也不能被解释为一定与对方达成有拘束力的移除决定。所以,“避免有害干扰”的义务也不能被解释为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的义务。
目前,外层空间中存有大量空间碎片,更为严重的是,碎片的数量持续性增长,使得空间碎片对空间活动的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并且,大量的空间碎片占据了外空中有限的轨道位置,这对于轨道资源是极大的浪费。由此观之,空间碎片对非登记国的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损害的潜在的对象是全体国家。空间碎片带来的危害不能通过登记国解决,因为,依照目前的国际法,登记国没有移除空间碎片的义务。允许非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符合保护非登记国的利益的要求,而且,这是一种有效解决空间碎片残留问题的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移除的客体是否具有特殊性,即,是否所有的空间碎片都应被设置为各国均可自由移除的对象。一些国家在外空委法律小组委员会的讨论中指出,移除体积较大(large pieces)的空间碎片是必要的。 (45) See Legal Sub-Committee, UNCOPUOS, Report of the Legal Subcommittee on its fifty -fifth session , held in Vienna from 4 to 15 April 2016, A/AC.105/1113, 2016, p. 27.从技术上讲,仅移除体积较大的空间碎片可以达到保护外层空间安全的需要。那么,是否有必要从体积的角度,对可移除的空间碎片进行限制呢?应当说,这种限制是没有必要的。即使是很小的空间碎片,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下依然会对其他空间物体带来较大的威胁。而且,登记国对碎片的利用价值主要存在于大体积碎片上,移除小体积碎片并不会受到登记国的强烈反对。另外,在外空物体监测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准确检测空间碎片的体积也并不可行。
如前所述,移除空间碎片的技术尚未被投入实践,因此,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义务不可能是一项已经形成的国际习惯。另一方面,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义务在可预见的未来成为国际习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与移除空间碎片目的相同、只是对象不同的“任务后处理措施”没能发展成为国际习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空间碎片减缓准则》规定了“任务后处理措施”的具体内容。准则六要求:“对于已经结束轨道操作阶段而穿越低地轨道区域的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应当在控制下将其从轨道中清除。如果这不可能,则应在轨道中对其进行处置,以避免它们在低地轨道区域长期存在。”;准则七要求:“对于已经结束轨道操作阶段而穿越地球同步区域的航天器和运载火箭轨道级,应当将其留在轨道内,以避免它们对地球同步区域的长期干扰。对于地球同步区域内或附近的物体,可以通过将任务结束后的物体留在地球同步区域上空的轨道来减少来碰撞的可能性,从而使之不会干扰或返回地球同步区域。”(40)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联合国关于外层空间的条约和原则、大会有关决议以及其他文件》,ST/SPACE/61,2013年,第59页。See also IADC, IADC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Guidelines , IADC-02-01, Revision 1, 2007, p. 5; ASI, BNSC, CNES, DLR, and ESA,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 Issue 1.0, 2004, p. 2; ISO, Space Systems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Requirements , ISO 24113:2011, 2011, p. 1, https://www.iso.org/obp/ui/#iso:std:iso:24113:ed-2:v1:en, last accessed on July.15, 2019; ESA Director General's Office,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Policy for Agency Projects , ESA/ADMIN/IPOL(2014)2, 2014, p. 1; NASA, Procedural Requirements for Limiting Orbital Debris , NPR 8715.6A, 2009, sec. 1.2.1.由此可见,“任务后处理措施”要求国家在空间物体变为空间碎片之前,移动低地球轨道和地球同步轨道中寿命即将终结的空间物体。但是,国家并没有在实践中对这两条进行有效的执行。根据ESA 的统计,从1990年到2015年,低地球轨道上的碎片被移动的比率极低。 (41) See ESA,ESA ’s Annual Space Environment Report , GEN-DB-LOG-00208-OPS-GR, 2017, p.49.而且,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各国普遍把移除寿命即将终结的空间物体作为法律义务。目前,只有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法国、日本、尼日利亚、乌克兰和美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参与空间活动的主体进行任务后处理的义务。(42) See UNCOPUOS,Compendium :Space Debris Mitigation Standards Adopted by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 2017.所以,目前移动寿命末期的航天器离开特定轨道的义务尚未成为国际习惯,可以想见,移除已经产生的空间碎片能够成为国际习惯的前景同样渺茫。
2. 判定程序
相较于请求移除国自主判定,空间碎片的判定交由第三方机构确认会更为合理。请求移除国的判定虽然简便易行,但会增加国家间对空间碎片的认定纠纷,引发空间活动领域的冲突。因为,无论如何对空间碎片进行细致定义,空间碎片的认定不可避免地会包括主观要素,(46) See Christopher Lehnert, Space Debris Removal for a Sustainable Space Environment , European Space Policy Institute Perspectives No. 52, 2011, p.4.在主观认定的过程中,各国不免会对同一空间物体的认定各执一词,依靠请求移除国的单方认定显失公平。而且,当空间碎片涉及军事等登记国认为敏感的信息时,由第三方进行认定也有利于对登记国的信息保护。而且,移除国单方认定空间碎片会给移除国带来很重的负担。移除国和登记国对于特定空间物体的状态信息并不对称,移除国获取认定所需的信息难度大,但是,移除国一旦认定错误,却需要为登记国的损失承担责任,这要求移除国尽可能确保认定的准确性,这与其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是矛盾的。因此,第三方机构认定也是对请求移除国的一种保护。第三方机构应当中立,并由空间技术领域专家组成。在确定第三方机构时,我们应尽量考虑选择现有的国际组织或机构,以减少新设机构带来的人员、场地等经济成本和各国商讨成立新机构的时间成本。(47) See Agatha Akers, To Infinity and beyond :Orbital Space Debris and How to Clean It Up , 33 U. La Verne L. Rev (2012), p. 315; Also see Christopher Lehnert, Space Debris Removal for a Sustainable Space Environment , 52 European Space Policy Institute Perspectives, 2011, p.5.第三方机构没有主动认定权,只能依请求移除国的申请开始认定。
奥利司他对比二甲双胍降低超体质量或肥胖患者体质量疗效和安全性的Meta分析 ……………………… 刘永健等(5):690
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请求移除国应举出初步证据,证明其有依据认定某一空间物体为失去功能的空间碎片。根据证明的一般原理,证明“无”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不能完全将证明空间物体失去功能的责任施加于请求移除国。反之,登记国应当承担证明其空间物体仍具有功能的责任。这种安排也与双方掌握的空间碎片活动信息一致。第三方应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最终认定,并对涉及军事等敏感信息进行保密。
(二)移除权的形态
当中立机构判定空间物体为空间碎片后,空间碎片就不再是登记国管辖控制权的客体,移除他国空间碎片的权利应当被规定为登记国对外空物体管辖控制权的例外。具体而言,该规定应当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各国均有移除碎片的权利。该权利的本质是各国均有对空间碎片的管辖权和控制权。第二,各国行使移除权要遵循一定的顺序,登记国享有优先的移除权。
1. 各国均有移除空间碎片的权利
国际法上有对船舶和航空器的专属管辖权限制的先例,考虑到空间物体上管辖权的性质与之类似,所以,在设计限制空间物体管辖权的法律规则时,我们可以适当参考这些先例。国际法限制船舶和航空器上专属管辖权的方法是授予其他国家以管辖权。国际法对这种限制的规定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所有国家均有管辖控制权:例如,根据国际习惯法,任何国家都有权对海盗船舶、飞机以及海盗本身行使管辖权;(48) 参见马呈元:“论普遍管辖权的意义”,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29页。 第二种是能够证明自己利益遭受严重损害的国家: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21条规定能够证明自己国家的有关利益会遭受海难带来的重大环境污染的国家,有权在公海上对他国船舶行使适当的管辖权;第三种是与所管辖事件具有特定联系的国家。这种情况与第二种情况的不同在于,第三种情况中,哪些国家因利益受损而可以行使管辖权是由条约明确规定的,而在第二种情况中,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主张利益受损而行使管辖权。此种情况的一个实例是《关于在航空器内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第4条中的非登记国管辖权。
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应适用以上哪一种模式授予非登记国移除权。笔者认为,应当允许所有国家对空间碎片行使管辖控制权。这种选择的合理性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所有国家”一词应当根据国家未来可能设立移除权的不同模式来理解。如果国家通过缔结多边条约建立移除权,则各国应当被理解为各缔约国;如果国家能够形成有关移除权的国际习惯,则各国应当被理解为除一贯反对者外的所有国家。首先,空间碎片的存在威胁了全人类的利益,理应赋予各国清除这一威胁的权利。就比如,国际法赋予各国对威胁全人类的犯罪行为的普遍管辖权,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49) 参见马呈元:《国际刑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248页。 其次,空间碎片是脱离任何国家控制的物体,其上没有所载人员,外空目前也并不像海洋一样存在专属经济区、毗连区等法定特别区域。因此,通过设置连接点为非登记国行使管辖权建立依据是很困难的,即,上述第三种模式对于空间碎片而言是不可行的。另外,考虑到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移除碎片能力的国家是有限的。此时,不适宜要求移除的主体通过证明自己的特定利益损失作为移除的前提。因为,这样可以尽可能减少有能力、有意愿的移除主体进行移除的制度成本,从而促进移除活动的进行,而且,也有助于使该规定得到这些国家的同意。当然,为了防止移除权的滥用,我们也有必要通过其他规定对移除权进行限制:例如,空间碎片的判定经过了第三方机构,对其的认定具有中立性;以及,登记国享有优先移除的权利。笔者认为,通过这些限制也可以达到平衡登记国与非登记国利益、防止权利滥用的效果,而无需对主体进行特殊限制。
当然,将移除权的主体定位为各国并不代表私主体移除是非法的。根据《外空条约》第6条,私主体有权从事一切外空活动,只要其得到有关国家的批准。需要注意的是,私主体对空间碎片的移除无需得到原登记国的批准,因为登记国此时已不再享有专属的管辖权。私主体可经任何一国的批准而进行移除,但是,批准国应当对其承担责任。
2. 登记国移除权优先
在允许各国均享有移除空间碎片权利的同时,应当对权利的行使设置顺序,这一顺序便是给予登记国移除优先权。基于登记国的利益、移除的便利性和制度可行性的考虑,这一安排是合理的。登记国的优先权需要受到期间的限制,到期后优先权自动消灭。登记国权利的优先性体现在权利的行使期间。从内容上看,其与所有国家均可行使的移除权没有差别。在第三方机构判定某一外空物体为空间碎片后,登记国即享有行使移除权的优先期间。在此期间内,登记国须作出积极的意思表示,表示自己愿意移除空间碎片。如果权利的期间经过,登记国没有作出积极的意思表示,则登记国丧失优先移除权,所有国家均可移除碎片。在登记国移除碎片的优先期间内,其他国家移除碎片仍需经登记国同意。如果登记国决定行使优先权,其他国家也有意愿移除的,双方应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确定移除权的行使方式。登记国作出的移除的意思表示应当是明示且成文的,并应当向所有国家公开。
结 论
登记国对空间物体的管辖控制权本没有争议,但是这一管辖权却构成了非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的法律障碍。在现行的制度下,即使外空物体失去功能变为碎片,登记国依然对其享有专属的执行管辖权和控制权,这一权利的存在,使得非登记国移除空间碎片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因此,移除他国空间碎片必须得到登记国的同意,移除行动也必须按照登记国的要求执行。即使非登记国实际受到了空间碎片带来的碰撞威胁,其也不能单方移除以保护自己的权利,除非这种情况能够满足国际法上“紧急情况”的严格要求。
为了实际保护非登记国的利益,促进空间碎片问题的解决,有必要对登记国的专属管辖权加以限制,赋予所有国家对空间碎片的移除权。空间碎片是存在于地球轨道或重返大气层的,脱离控制者控制的人造物体。根据理性估计,这种脱离控制的状态在可预见的期间内不可改变。空间碎片不仅包括失去控制的空间物体本身,还包括其组成部分及残块。对空间碎片的认定应当由第三方中立机构进行,由申请移除的国家提出表面证据,而由登记国承担证明空间碎片仍然在其控制之下的责任。空间碎片一经认定,每个国家都有移除空间碎片的权利,当然,这不代表其可获取空间碎片及其上的信息。在认定之后,还应当设立一个特殊的期间,在此期间内,登记国可优先决定其是否移除空间碎片,其他国家不可进行移除活动。当期间届满时,登记国的优先权消灭,如果其想参与移除,则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平等协商。
式中:μm为混合油黏度,m Pa·s;μi为组分油i的黏度,mPa·s;X i为组分油i的质量分数,ΣX i=1,i=1~n;B jk、Cjk为考虑组分油间相互关系的常数。
空间碎片的移除涉及到对各国在外空中管辖权的调整。各国在外空中的活动须通过相应的载体实现,而活动自由的保证则是对其登记空间物体的管辖权。但是,这一自由应当受到其他国家权利的限制。当空间物体失去功能后,其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安全隐患和活动障碍,此时理应对登记国的管辖权加以限制。更重要的是,移除权的设置在客观上是一种有效的解决空间碎片问题的思路。登记国很难接受移除空间碎片的义务,事实上,受制于技术和资金,要求登记国承担这种义务也不甚合理。那么,我们应考虑让有能力、有意愿的国家参与到空间碎片的移除过程中。毕竟,毫无限制的管辖权最终可能导致受害国乃至全体空间活动参与国利益的损失,对权利的限制和重新界定才是使每个国家能充分享有探索外空活动自由的长久之策。
* 赵青,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100088)。
标签:空间碎片论文; 移除论文; 管辖权论文; 移除权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