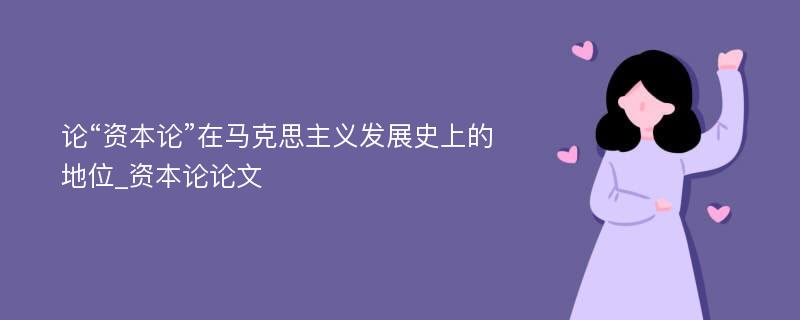
再论《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发展史上论文,地位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5-0001-06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的心血写成的一部光辉巨著,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中一部博大精深、流光溢彩的百科全书。《资本论》以其完备而科学的知识体系与完美而严密的逻辑结构,在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及其内在矛盾,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客观必然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它虽命运多舛,经历了资产阶级学者非难和攻击的考验,经受了风雨的冲刷和洗礼,但它所具有的严谨的科学性、严密的逻辑性,以及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却使它具有任何其他著作都无可比拟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具有震撼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
一、《资本论》是马克思实现经济科学革命的理论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资本论》是马克思实现经济科学革命的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从《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来看,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资本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彻底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是在确立科学的世界观过程中,通过阅读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参与当时的经济问题的争论之后,逐步丰富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提出自己的经济学新见解,并建立起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的。1843年底开始,马克思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的崎岖道路。从1843年到1848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经过近5年的潜心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首先,马克思运用由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得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重要结论。他从社会总体结构中,分离出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特定的研究层次,认为构成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此,“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
其次,马克思对商品、货币范畴作了初步论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指出,在私有制经济中,商品、货币这些范畴只不过是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的表现形式。商品交换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产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只是商品私有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反映。在货币中,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的颠倒和混淆,实质上是由人的“异化”、“外化”和“外在化的类本质”所决定的。在对商品、货币范畴的初步研究中,马克思摒弃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忽视商品、货币范畴社会关系性质的错误观点。他还认为,在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成为“廉价的商品”是由于“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是由于“感性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2]。这一论述显露了劳动力商品理论的思想萌芽。从商品范畴到劳动力商品范畴,再到剩余价值、利润范畴思想线索得到初步反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内在联系已初露端倪。
再次,马克思对反映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本质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利润和工资范畴作了初步分析。马克思区分了资本和资金,他认为“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3]。马克思还证明,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工资和利润的对立是资本对工人劳动占有、奴役和剥夺的结果。资本是以雇佣劳动的存在为前提的,是通过对工人劳动的占有和剥削而积累起来的。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他还初步揭示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他认为,生产资本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统治力量的增加;随着资本的增加和资产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另一方面又使大批较高的社会阶层中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因此,“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4]。
从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下了一系列的经济学手稿,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了一场革命。这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现在被称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以后的15年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光辉结晶。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问题作了科学论述。手稿中的这些论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形成。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的理论体系设计了著名的“五篇结构计划”。这就是:“(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5]
1859年6月,马克思公开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序言”中,马克思提出了更为清晰的“六册计划”,即“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六册计划”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所有者的角度来看,资本家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三个基本的条件和主要的经济关系,或者说反映当时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对这三方面内容分别作出详尽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国家问题,即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之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国家的对外贸易,或者说国家对外的问题;最后再研究涵盖了各国经济关系在内的世界市场问题。“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主要研究四大问题:“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马克思把“资本一般”又分作三章:商品、货币和资本本身。其中第三章又分作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三项内容。这也就是说,商品是资本的最抽象的要素和范畴,研究了商品范畴才能理解货币的本质,研究了货币范畴才能理解资本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后来就是以商品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始基范畴的。从最抽象的、最简单的商品范畴开始,一直到最具体的、最复杂的世界市场范畴,这之间存在着一步一步上升的逻辑关系,同时,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规律也得到了一步一步的展开和深化。
显然,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是按“六册计划”来撰写的。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就是“六册计划”的开头部分,即第一册《资本》第一部分“资本一般”的起首两章。按照原先计划,《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主要论述第一册《资本》第一部分“资本一般”的第三章资本。后来,在对资本的深入论述中,大约在1862年底,马克思对原先的写作计划作了调整,把他正在写作的经济学著作正式定名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标题最显著地证明:资本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理论史批判之间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之后在写作手稿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四卷结构”的计划,即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卷理论史。马克思对原先写作计划所作的调整,并没有改变他的“六册计划”。马克思似乎感到,他的有生之年是难以按“六册计划”完成全部经济学著作,而只能完成属于“基本原理”的第一册《资本》。马克思一直认为,这些属于“基本原理”的内容,是他整个著作的最难论述的部分,也是他整个著作的“精髓”。这一部分论述清楚了,其余部分后人就可能较为容易作进一步的论述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论》的前三卷,论及的其实只是相当于“六册计划”第一册《资本》的第一部分资本一般(商品、货币、资本)的内容。
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在汉堡出版。从“五篇结构计划”到“六册计划”,再到“四卷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也是《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反映了《资本论》是马克思实现经济科学革命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它不仅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经济学理论优秀成果,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经济学家的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要对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作出一个总体性的研究,而这种总体性的研究是要从本质上、从规律上探讨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貌,而且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资本论》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这一恢弘体系的一个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不是脱离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大道形成的,更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形成的,而是随着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是人类思想史和文明史上的光辉结晶。
二、《资本论》是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的典范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资本论》是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的典范,它不仅使剩余价值理论成为唯物史观的逻辑展开,而且也在论证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同时,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资本论》的创作过程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并论证其科学性的过程。马克思步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过程是《资本论》创作过程的重要前奏。1843年,马克思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中搞清楚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当时已经认识到,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理解“市民社会”,进而理解包括国家和法的关系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出发点,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出发点。马克思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正确分析,以及打算进一步去解剖市民社会的想法,是他能够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它既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后所写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最初理论探索,因而它体现了马克思把哲学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进行了研究[7]。这一分析意味着他已将研究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本质中,并以人的本质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批判。但是,马克思当时还正处于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对劳动价值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写作到《哲学的贫困》的完成,是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到赞同劳动价值论的过程,其间经历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完成的著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果说1844年9—11月完成的《神圣家族》对唯物史观的阐述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唯物史观还处于形成的前夜,那么,在1846年5月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已通过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批判和清算,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运用这些原理对国家的阶级性质、社会的意识形态性质、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作了分析。可以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点,使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视野,唯物史观成为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基础。
在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写成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12月完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1848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和发挥。《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态度发生转变的标志。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强调了经济范畴抽象性、客观性、历史性,第一次公开了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不仅如此,马克思也明确地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通过《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已经实现了劳动价值论与唯物史观的结合。《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直接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本质的剖析、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露、对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对工资本质的揭示,等等,不仅体现了劳动价值论的运用,而且也是剩余价值理论确立的基础。《共产党宣言》关于资产阶级历史地位、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个必然”等的论述更是贯穿和渗透着唯物史观的思想。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中,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范畴的首次提出和对剩余价值来源、生产、实现等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方面为之后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形成,标志着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结合。这一探讨使马克思对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有了更加深刻而丰富的发展。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马克思通过阐述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应该说,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这一经典的阐述中达到了高度统一。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作了考察,还引入了超额剩余价值的概念来分析问题。在阐明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两种基本形式的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第一次对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润到平均利润的“两种转化”过程作了系统的探讨。所有这些分析使剩余价值理论更加丰满,从而以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进一步完善了唯物史观。
第二,《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确定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并论证其科学性的过程。19世纪40年代后期,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逐步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明确认识到社会关系实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到19世纪50年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研究对象主要作了两个方面的探讨。一是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入分析,强调“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9]。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10]。二是对社会运动整体的系统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作了阐述,认为在社会运动整体的系统关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原生”关系,国家形式、法的关系和家庭关系等是“非原生”,或者“第二级和第三级”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为基础。
19世纪60年代以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涵日益清晰。1865年初,马克思在写作《论蒲鲁东》一文中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的论述,政治经济学“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11]。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分析最后在《资本论》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2]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实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社会结构必然被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资本论》是以劳动者和它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为既定出发点,来研究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怎样结合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的问题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形式相结合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资本论》所研究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一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特殊结合的性质。因此,《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就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全过程的生产关系。
第三,《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剩余价值理论,不仅丰富了唯物史观,而且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生产及生产过程、剩余价值实现和分配等问题的探讨,不仅运用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如唯物辩证法、抽象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且也以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分析,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使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中得到了逻辑展开。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3]
恩格斯曾说过,《资本论》“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4]。唯物辩证法作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它强调的是从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过程出发,研究一种关系所包含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即矛盾的方面。《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对商品内部矛盾的分析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进而揭示出这些矛盾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它的精髓在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质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运用唯物辩证法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肯定的理解中,也同时包含着对它否定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必然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在《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理论的逻辑结构中再现了现实的经济运动。通过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15],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方方面面。《资本论》从商品上升到货币、从货币上升到资本、从资本上升到剩余价值,从资本循环上升到资本周转、从单个资本上升到社会资本,再从剩余价值上升到利润、从利润上升到平均利润、从价值上升到生产价格,再从剩余价值分割为企业主收入、银行利润、借贷利息、地租等逻辑过程,说明了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反映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关系,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经济运动。
《资本论》的研究和叙述过程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运用过程,亦即在占有大量的经济生活实际资料基础上,运用人脑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抽象力,排除各种外在的、非本质的东西,抽取某种共同的、本质的东西,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揭示出经济过程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然后通过抽象的规定去把握思维中的具体。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6]。“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7]因此,叙述是把研究的结果用一定的方法在理论上再现出来。马克思对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以及以《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形式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揭示,正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
《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进一步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提供了经济学的证明。唯物史观创立之前,马克思是从哲学原则出发,把共产主义看做是某种哲学原则的实现,并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唯物史观创立后,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18]。马克思不再从哲学的原则出发来理解共产主义问题,而是通过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深刻分析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唯物史观的创立使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有了科学的理解,那么剩余价值的发现则使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揭露,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尖锐的对抗矛盾的论证,说明了“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9],未来社会则是“全面的自由个性的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仅是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肩负着改变世界这一特殊的实践任务。
三、《资本论》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资本论》的问世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和革命性的影响。如恩格斯所说:“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20]《资本论》为无产阶级铸造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这无疑是向资产者(包括土地所有者在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21]。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无疑“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22]。最初,资产阶级学者以“缄默抵制”的态度对待《资本论》及其传播,他们不评论、不介绍、不攻击,企图用沉默的方式将《资本论》置于死地。但是,马克思逝世以后,随着《资本论》二、三两卷问世,第一卷的各种文字版本的相继出版,以及《资本论》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为了诋毁《资本论》的影响,资产阶级学者转而对《资本论》进行了“非难”和“攻击”,他们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妄图通过“釜底抽薪”来摧毁《资本论》这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大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开始向垄断过渡。面对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冯·庞巴维克首先发起了对《资本论》中阐述的劳动价值论的攻击。他一方面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与第3卷之间存在矛盾,马克思用第3卷的劳动价值论否定了第1卷的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认为在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中,复杂劳动是无法还原为简单劳动的。庞巴维克攻击和非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在于用边际效用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以庞巴维克的观点为依据,对《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也提出了一系列“修正”和否定的主张。一时间,宣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的论调、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颠覆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在事关马克思《资本论》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一些理论家如奥地利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罗莎·卢森堡等旗帜鲜明地对庞巴维克、伯恩施坦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为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
随后,《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不休的争论。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英国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以其所建立的“均衡价格论”,集供求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生产费用论等各种学说为一体,试图用这种折衷主义的庸俗的价值论来对抗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继马歇尔之后的凯恩斯,把《资本论》诬蔑为“只是一册陈腐的经济学教本”,认为“这本书不但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已经没有关系或不相适应”[23]。但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之后,西方学者为了找到反危机的出路,回过头来想从马克思《资本论》中寻找医治资本主义痼疾的良方。因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谩骂少了、全盘否定不多见了,他们摆出和解的姿态,要在马克思理论和凯恩斯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融合”的桥梁,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英国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提出了“重新学习”、“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于是,《资本论》走进了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课堂和研究场所。马克思《资本论》在西方显现了强大的理论威力。
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深入发展,信息产业崛起,高新技术出现,生产自动化极大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使马克思的《资本论》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些西方学者如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又提出要用知识价值论、信息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然而,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又重现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价值。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理论的研究处于高潮,人们意识到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结果。在西方,“马克思引起了轰动”、“马克思没有死”、“马克思的幽灵又回来了”的看法层出不穷。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产生了“《资本论》热”、“马克思热”、“马克思的复兴”、“马克思的回归”。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有更大的兴趣开始了解这位一百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了解他在一百多年前所阐述的思想。由此可见,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理论在提出“重新学习”、“重新研究”以后,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经历了经济全球化浪潮和苏东剧变的考验,开始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出了肯定、呼唤、向往和重新评价。
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攻击和非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疑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反对马克思《资本论》、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但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力量、科学精神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又不断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所探讨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对当代人来说,马克思有着让人无法绕开的巨大身影。马克思的《资本论》穿过历史的长河,已经充分地显示出了它的强大的感召力和生命力。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20世纪作为人类最伟大的世纪之一,就在于在这个世纪中,在马克思《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引下,社会主义从理论发展为实践,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并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开创了人类社会最伟大变革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以它在革命、战争、建设、改革中经受的考验和磨炼,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魅力和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创造力。
《资本论》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规律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折服,就连一直对马克思持反对态度的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熊彼特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学说是把伟大和生命力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事实不仅证实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还证实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世界上一大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不是马克思《资本论》理论的胜利和证实,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经济危机的爆发相伴随无不显示出马克思《资本论》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发生了解体、东欧发生了剧变,但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深远意义是永存的,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意义是永存的,《资本论》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的、正确的。
考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我们看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一个随着历史条件变化,低潮和高潮交替发展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显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小小的旋涡、一股小小的逆流。尽管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了低潮,世界上许多国家改旗易帜转信民主社会主义,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目标,但是,它使各种矛盾得以最充分、最清晰的暴露,从而最有利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最全面、最冷静的思考,对马克思的理论作出最系统、最深刻的研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作为高于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的新生事物,必定要经历一个初期的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在不成熟、不发达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败是在所难免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很不完善,还会受到资本主义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进攻和渗透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在发展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局部的暂时的倒退,出现低潮,是合乎规律的。苏东剧变不仅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相反,它却给社会主义实现新的飞跃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经验材料。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们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4]
标签:资本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剩余价值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抽象劳动论文;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剩余价值规律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商品货币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