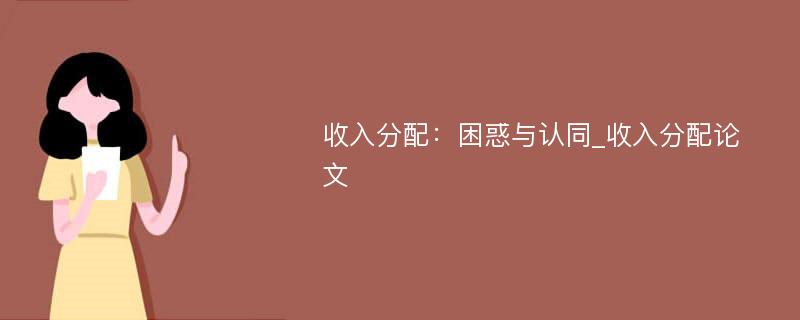
收入分配:困惑与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4)04-0031-06
党的十六大以来,按要素分配成为理论研究和现实探索的一个重点,但歧见也日趋增多。有的认为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分配,也有的认为是按要素的购买价格分配。(注:孙永梅.“要素所有权”与“要素贡献”[J].经济学家,2003,(3):33—38.)而郑志国则似乎认识到了其中的矛盾。(注:郑志国.效用价值论的四个矛盾[J].经济学家,2003,(3):39—43.)尽管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争议发现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反差,但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本文以回顾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为切入点指出其缺陷,以经济学家对剩余的认识的变化来展示收入分配理论的演化,目标是使我们对经济世界中的分配如何运转有比较充分的理解。
一、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并不能解决实际中的分配问题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宣称,如何在两个或更多的相互作用的要素之间分配它们共同生产的总产品,可以用边际产品的概念得到解决。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等人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著作,他们提出了以主观效用为基础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分配是按相同规律解决的,那就是它们的效用。从此以后,边际分析对于理论上的“具体”是必不可少的,离开这一分析工具经济学家好像对分配问题一筹莫展。
边际学派所主张的效用,只是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主观评价。他们用数学方法来分析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认为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价格等于它们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等于最后一单位劳动的产量,利息等于最后一单位资本的产量,利润是企业家的贡献收入。这样,边际学派就把收入分配问题转化成了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问题。
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的总和等于总产量,没有剩余。这一理论在当时有为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辩护的功能,也是为了调和各生产要素间的矛盾,并不是解决分配问题的有效方法。事实上,即使用最先进的计量手段也不可能准确地测出动态经济中最后一单位要素的贡献是多少。退一步说,即使我们能够测量出最后一单位要素的边际贡献,也只是能够说明通过边际产品可以决定“某一类”要素价格,而不能识别“某一个”要素的贡献。这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能说某一种投入独自创造了产出,而应该说产出是由不同要素的相互作用所致。
正是由于土地、劳动和资本品在生产中的相互依赖性,才使得收入的分配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假设我们不得不同时分配一个国家的所有产出,如果我们能够判定“土地”独立生产这么多,“劳动”独立生产那么多,而“机器”又单独生产了其余部分,那么分配就会很容易。而这样的情况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注:[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187.)萨缪尔森作为“新古典综合”的代表人物是边际分析的拥护者,对用边际生产力解决分配问题的局限性却有着清醒的认识。而这一点,我们在引进这些理论时忽略了。
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也是有其假设的前提条件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包含了在有限交换市场范围内的要素定价和分配份额。它依赖于竞争性市场结构内部的个人利润和效用最大化,也依赖于生产函数和统一的均衡概念,从而使分配局限于这个分析框架之中。
德姆塞茨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指出了新古典分配理论的缺陷。他认为,新古典分析方法考虑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非制度因素或资源禀赋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这一框架,经济学家创建了抽象的理论来解释一个成熟的价格体系如何确定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根本兴趣不在于实际经济变化,而在于加深我们对成熟的价格体系分配要素和收入的规则的理解。他们未能将制度和其他资源禀赋考虑进去。(注:[美]科思,诺思,威廉姆森等.制度、契约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85.)
超越时间之上,在理解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并且更有效率地解决它的问题的努力中,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市场不完善、外在性、制度结构、新的均衡概念、调节过程、制约选择的目标、谈判力量、社会关系、国家优先等所强加的限制的重要性。随着历史的变化,越来越多地受到动态非均衡的非竞争市场所控制的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新古典的世界。新古典的分析方法不能用来解释每一件事,为了使新古典经济学变得有用,它们必须适应于应付这个变化的世界。(注:阿西马科普洛斯.收入分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11.)
针对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存在的缺陷,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反边际主义。反边际主义批评的主要目标是新古典企业理论;而边际分析是新古典企业理论的主要部分。在该理论中,一般假定,被认为是独立决定企业行为的企业家,是利润最大化者。如果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利润就实现了最大化。如果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那么我们就可以多生产一个单位来获得超额利润。在边际收益曲线是负向倾斜的和边际成本曲线是U形的通常假设条件下,利润最大化假设暗示,企业家的价格和产出政策是,将产出扩张到直至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这一点。反边际主义受到经验发现的启示而提出质疑。因为经验发现显示,企业在实践中并未采取基于边际主义深思熟虑的价格和产出政策,而都遵循了一种“全成本”的价格规则。这种规则是以每单位的主要(或间接)成本作为基础加上一个百分比来覆盖一般的管理费用(或间接成本),然后再加上一个惯例的增加额(通常是10%)作为利润。(注:[荷]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7.)企业家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在生产中经常缺乏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信息,或者说,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是多少。这样,反边际主义者就从实践上否定了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
实际上,按劳分配或者按要素分配都存在无法计量的问题。正如诺思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的产出,这样的话,人们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的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注:[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J].改革,1995,(3):54.)
尽管存在着争议,但世界上也并不存在无法分配的资源、产品和劳务;尽管分配的结果受着来自经济、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审视或诘难,但分配一刻也不能停止。因为作为生产背面的分配一旦停止,生产也就不能延续下去。为了使生产能够进行,人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分配理论和分配形式,这些形式有时是单独使用,有时是混合使用。
从已有的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看,按劳分配可能是一种接近按贡献大小进行的功能性收入分配。但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按劳分配所需要的条件很苛刻,尤其是不能有效解决搭便车问题,这就在实践中演化为平均主义。列宁似乎认识到了按劳分配的难处,因此要求对劳动进行严格计量。他说:“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就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而做不到这一点,便谈不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注: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9~480.)
按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分配方式,但在一般情况下按要素分配是一种事先分配而不是按贡献分配。这种分配理论和方式与生产要素的价格制定密切相关,生产要素的价格是由其稀缺性决定的,仅仅因为相对稀缺性的不同而使市价不同;这并不是由他(它)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决定的。长期以来,古典或新古典的分配理论把要素参与分配演化为按要素的贡献分配,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贡献小的得到较低的收入,贡献大的应该得到更高的报酬。由于无法衡量贡献的大小,我们就误以为收入高的人贡献大,出现了像赵磊先生所指出的“倒推”现象。(注:赵磊.经济学谬误三题[J].江汉论坛,2003,(4):39.)可见,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并不能科学地解释和解决实际中的收入分配问题,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的需要和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来寻求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新思路。
二、从新制度经济学中寻求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把产权和交易费用引入微观经济分析,可以说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发展。他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企业的效率问题,但对剩余进行深入而又有趣味的研究为我们如何解决分配问题提供了方法和思路。
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通过经济计划,节约了交易费用,从而生产出低于市场价格的剩余。围绕着效率新制度经济学对剩余的控制和分割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
1.对剩余研究的简要回顾。经济学家对剩余是如何产生的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研究剩余的来源或源泉都是为了给剩余的归属即剩余的占有找到更“合理”的出路。
在经济史上,较早发现剩余的是魁奈。1758年,魁奈发表《经济表》,提出了“纯产品”学说。他认为,农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农业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农业资本家的生活资料外,还有剩余的产品,这就是“纯产品”,也是增加的财富。魁奈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一是生产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生产“纯产品”;二是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地主、国王和官吏、教会等,他们通过收取地租和租税从生产阶级那里获得“纯产品”;三是不生产阶级,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他们不生产“纯产品”。
1817年,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自己的分配理论。他认为,土地产品要在土地所有者、耕种者所需的资本的所有者及进行耕种工作的劳动者这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地租是为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劳动的自然价格(工资)取决于劳动者维持其自身与其家庭所需要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资本利润则是全部商品价值中扣除劳动工资的剩余部分,即资本利润是劳动的剩余价值。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马克思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理论对剩余的来源作了更为清晰的说明,剩余的合理、合乎道义的分配成为马克思分配理论的主题。马克思利用剥削概念有力地论证了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理应归于它的创造者。可见,马克思的理论是多数人分享剩余的理论。
1912年,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发表,他把剩余归于企业家的创新。他认为,企业家利润是一种超过成本的剩余。他们(企业家)并未积累任何种类的商品,他们并未首创任何独特的生产手段,而是与众不同地,更适当地,更有利地运用了现存的生产手段。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他们就是企业家。他们的利润,即我们所谈到的剩余,就是企业家利润。(注:[美]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47.)这样,熊彼特构建了一个少数人分享剩余的理论。
2.剩余索取权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新制度经济学抛开经济史上剩余来源的争议,把谁来获取剩余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来研究,取得了与实践比较一致的看法,因而对我们理解现实世界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很有帮助。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剩余与效率密切相关,与激励完全相容。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在队生产(Team Production)中,参与合作的成员的边际产品并不是可以直接地(即廉价地)观察得到的。当两个人联合将一重物运上卡车时,我们只能观察到他们每天装载的总重量,却无法确定每个人的生产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报酬的支付是随机的,也不考虑生产者的努力,这种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负相关,这种组织就是具有破坏性的。为了确定个体的努力,不得不发生监督成本。这就需要有监督者,但是,由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如果监督者是“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s)就可能对监督者产生激励。
在企业中,对剩余(或残余)的分享只能是少数人,而不是普遍地分享。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看来,“对残余的普遍分享会导致由监督者增加偷懒所带来的损失超过分享残余的雇员的偷懒减少所带来的收益”。(注:[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61—76.)由此可见,企业制度在创立时,并没有也不会产生一个大多数人分享剩余的机制。发达国家企业中越来越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似乎提供了佐证,一个“胜者全得”的分配格局正在形成。少数人对剩余的分享虽然可以减少搭便车行为,但也造成了收入分配悬殊的后果。
这样,新制度经济学的分配理论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的轨道上,并且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接。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家在进行生产之前,到市场上购买各种生产要素,然后在企业中进行生产。生产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高于市场购买价格的剩余。在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中,企业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能够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内部的协调更像经济计划而不是市场治理。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是不是市场价格的既定接受者,是不是完全“让人家来鞣”有着不同的情形。
那些技能单一且容易被替代工作岗位的劳动者成为价格的既定接受者。由于激烈的竞争,他们不得不接受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剥削,但现代国家制度文明的演进使其剥削程度大大受到限制,许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护市场竞争中的弱者。而那些在生产中处于关键地位的技术人员可以通过“跳槽”的方式找到更合适的报酬。其行为就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博弈的结果是,拥有先进技术手段的群体会获得更多的收益。
以上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理论观点的分析可以对目前的争议进行整合:一般生产要素或者可替代性的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其市场的竞争价格决定,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之前其报酬就已经决定了;特殊的要素或者垄断性生产要素的报酬既由市场决定,也由其在生产中的业绩和博弈决定。
由此可见,收入分配问题部分地可以从现代企业理论中得到破解: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靠有效率的激励来维系,而激励的后果也带来了过大甚至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弥合这种差距,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培育每一个劳动者的人力资本,为每一个人提供自由而又全面发展的机会。这可能是国家调控收入分配最重要的手段。
三、需要构建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来统一对收入分配的认识
真实世界里的收入分配结果并不像要素分配论者所鼓吹的那样简单,那样被人心服口服地接受。如果真是劳动者得到与其投入相一致的工资,资本持有者得到市场认可的利润,土地所有者得到正常的地租,那么就不会出现工人罢工这种现象,工会存在也就是多余的了;更进一步地,那些研究如何通过分配这个导向来激励生产及技术上的创新的经济学家就会失去市场,那些研究如何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的现状来实现社会公平或平等的社会学家更无存在的必要了。
收入分配是经济学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它与每个人的利益密切相关。各种分配理论都试图给人们以“合理”的解释,但分歧一直难以弥合。
现行的收入分配方式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上通行的方式?弗里德曼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全来说,有一套信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毫无疑问的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地接受,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个人的判断而言,这一命题就是或已经是我们社会上的这类信条之一,而事实上它也的确如此,这就是社会为什么接受了市场体制和与之相关的报酬方式的部分原因。依据边际产量进行支付的功能也许‘实际’是为了获得资源配置效益,或许也是错误地认为它导致了分配上的公正。”(注:[美]弗里德曼.价格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59—260.)
一种分配方式,只有当人们认为它是“公平”的时候,才能使人们对分配的结果感到满意。所以,理论上的缺陷需要我们通过意识形态来弥补,而对收入分配的“恰当”评价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委托代理关系中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以及人们的搭便车行为也会使收入分配的结果出现扭曲,也需要意识形态来矫正。
收入分配的结果,作为特定阶段生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一方面,它要受制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供给与需求的巨大缺口使人们不断产生出“公平”和“不公平”的感觉和认识,这种感觉和认识的系统的理论形态就是关于收入分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去引导人们对收入分配结果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看法,而是统治人、支配人的观念性的力量。就我国而言,正确地把握这种力量,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就需要我们在构建意识形态时,使其具有以下功能:
一是认同功能。认同现存的分配制度可以产生一个“双赢”的分配格局。新的分配制度造就了百万元、千万元乃至亿万元的少数富有家庭,发挥了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造就更多的富有家庭,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这就需要我们承认富人作为建设者应有的地位。因为,“虽然在竞争制度下,穷人致富的可能性比拥有遗产的人致富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前者不但是可能致富,而且他们只有在竞争制度之下,才能够单靠自由而不靠有势力者的恩惠获得成功,只有在竞争制度下,才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挠他谋求致富的努力。”(注:[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00.)
二是稳定的功能。中国由共同贫穷到走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继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发挥意识形态稳定功能的一个重要内容。收入差距的扩大使一些经济学家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产生了怀疑并主张公平优先。这种主张在当前还难以实施,因为现阶段如果采用公平优先的原则不但不能实现公平,反而会产生普遍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丧失效率。历史经验表明,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只能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
三是兼容整合功能。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够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注: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8.)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明显地把人群分为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出现了利益获得者和利益相对剥夺者。这就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兼容整合功能,在继续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提倡先富帮后富,并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四是节约的功能。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具有辅助正式制度的功能,并且在正式制度无法实施或实施成本过高的领域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这样的意识形态能够对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搭便车等行为起到抑制作用。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是要使人们认识到,既然我们选择了市场制度,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我们只有弘扬实施这一制度所需要的契约观念、诚实守信品德以及探索创新精神,才能降低交易费用并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从而使每个人获得不断增加的收益。
标签:收入分配论文; 边际收益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边际收入论文; 边际分析方法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功能分析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