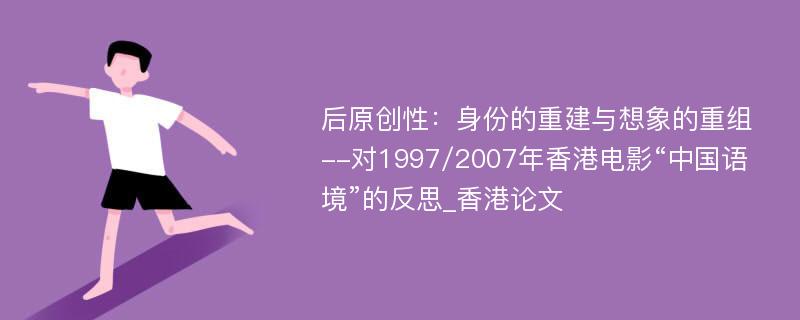
后原初性:认同的再造和想象的重组——反思1997-2007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中国论文,香港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11-0039-06
1
探讨香港电影最近十年来的发展和演变,我们会发现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的同时,香港电影的内在风格和气质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的轨迹其实正是香港电影新面貌的展开。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关系的改变,许许多多对香港文化和电影有兴趣的人们在1997年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变化的走向,也就是说,今天变化的走向是当时的主流预言所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在一个新的“后殖民”情境中,香港本身的命运和香港电影的命运完全脱离当时的“预设”,被视为“宿命”的东西烟消云散,人们无法想象的新的历史景观悄然浮现。今天看来,香港电影正是这一变化的结果,也最好地投射了这些变化所交织互映的诸多关键的侧面。我试图通过对于香港电影“中国脉络”中的“原初性”向“后原初性”的转化,探讨1997-2007的十年中香港电影变化的关键之点。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在“九七”后的新的文化经验中,香港电影如何想象香港?如何想象中国?
2
香港电影中所谓的“中国脉络”是香港影评人李焯桃1990年在编辑第十四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特刊《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时提出的概念。他当时点明:“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范围本来十分庞大。正如绝大多数香港人也是中国人,从来没人怀疑香港电影也是中国电影的一部分,但香港特别在1949年大陆解放后,与中国有相对上独立的发展,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而香港电影就和这个城市一样,华洋夹杂,除了中国传统的脉络之外,更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①同时,他也强调这本专辑探讨的“中国脉络”问题主要集中于80年代以来的香港电影中:“无论如何,80年代的香港电影是从土生土长的一代的角度,以香港为立足点,检讨中港两地的微妙关系和历史渊源。那种纠缠不清的中国情结,又与 40、50年代南来影人的过客(不久就回归中国)或流亡(始终根在故乡)心态迥然不同。”②这里所说的“中国脉络”其实有双重含义:首先,它是一个较为抽象、在文化领域内展开的概念,意味着“中国传统”在香港电影中的作用;其次,它是一个异常具体、在现实的生存中展开的概念,意味着中国的现实和由此产生的“中国情结”在香港电影中的作用。
我以为,在20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的现实中,这种“中国脉络”的作用其实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内地的“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和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在迅速地层开,中国开始进入“新时期”③。而在“新时期”的发展进程中,香港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窗口作用。它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又是内部“改革”的窗口。无论是外部“向内看”的对于中国的观察,还是中国“向外看”的对于外部世界和西方的观察,都不同程度地经过“香港”这一“窗口”的反射,所以,香港乃是一个独特的“中介”。正是依赖这个中介,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话语获得了重要的资源。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中英谈判将香港“回归”的时间表明确化,香港回归进程开始,近现代以来作为中国屈辱象征的香港的“殖民”历史即将终结。“中国脉络”其实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情境所产生的历史结果。
可以想见,“中国脉络”包含一个具有悖论意味的情境存在:一方面,回归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中国“现代性”内在的历史要求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没有任何疑问,这一历史事件必然发生的确定性不容置疑,而“中国”这一主题也是任何香港文化想象难以逃避的前提;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既曾经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中,又有远比内地发达的经济和与西方更为深入的联系,所以,内地在经济上的“落后”和文化上的“封闭”也变成香港对于中国内地的文化想象的重要部分,这种复杂交错的经验是过去的一般性的“后殖民”理论所难以涵盖和探究的。香港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殖民/被殖民的二元对立关系,还是一个殖民/被殖民/将回归民族国家三者之间的三重关系。这一关系犬牙交错,互相纠结,使得香港的新文化经验变得异常独特,具有异常性的阐释空间。一般的“殖民”历史都是一个在第三世界尚未建立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刻,殖民主义将文化空间变为“殖民空间”,而本地人民对于自己文化的要求正是和“民族国家”的建构相联系的。而香港的状况是一个特别的例证,它的殖民问题的解决和后殖民状况的来临必然地与回归中国联系在一起。香港的“现代性”是在殖民统治下演化的,而中国内地的“现代性”则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完成的过程。由此,“中国脉络”使得香港的“后殖民”演化呈现出不可多得的文化想象的独特性。
我想借用周蕾在探讨中国电影发展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来说明“中国脉络”的特征。周蕾在她的重要著作《原初的激情》④中分析中国电影时使用了一个关键性概念——“原初性”。她对“原初性”概念做了比较复杂的阐发,其关键的意义是指:
在一个纠缠于“第一世界”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力量之间的文化,如20世纪的中国文化,原初性正是矛盾所在,是两种指涉方式即“自然”和“文化”的混合。如果中国文化的“原初”在与西方比较时带有贬低的“落后”之意(身陷文化的早期阶段,因而更接近“自然”),那么该“原初”就好的一面而言乃是古老的文化(它出现在许多西方国家之前)。因此,一种原初的、乡村的强烈的根基感与另一种同样不容置疑的确信并联在一起,这一确信肯定中国的原初性,肯定中国有成为具有耀眼文明的现代首要国家的潜力。这种视中国为受害者同时又是帝国的原初主义悖论正是使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朝向他们所称的为中国所困扰的原因。⑤
其实,“原初性”是“落后”与“天真”、“压抑”与“力量”之间悖论的一个结果。前者更多地体现于文化,后者更多地体现于政治。这一文化/政治“悖论”是“原初性”存在的基础。由于“落后”和“天真”,中国大陆主要显示了贫穷和传统的一面,而由于“压抑”和“力量”,中国大陆又显示了强大和能量。这一悖论其实是现代中国想象的关键。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也是这种“原初性”想象的一个特殊部分——以香港为中介的“原初性”想象。这一想象的前提与周蕾所主要论述的中国大陆的“第五代”电影的自我的“原初性”想象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自我民族志化的结果⑥,而是一个在殖民力量和将要回归民族国家之间的独特身份的展开和来自这种身份的对于中国大陆的想象。在 80年代以来的香港电影中,中国内地一方面被表现为一个“落后”的地域,大量的“阿灿”、“表姐”等渲染着内地的落后和贫穷,这种渲染又时刻与香港的发达和丰裕尖锐对照。“土气”的内地人往往被表现出对香港的生活和文化异常渴望,充满惊奇感,让香港人感到不堪,并成为某种“笑料”;另一方面,内地人的朴素和来自乡间的淳厚人情又让香港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所表现的某种“原初”的、未经现代洗礼的力量又让香港人感到惊奇。与此同时,内地计划经济的刻板和压抑被刻意地渲染,而内地所具有的强大的来自“民族国家”的与西方不同的现代力量又被强化表述。这种“原初性”,其实也就是丘静美在论述80年代著名香港电影《省港旗兵》和《似水流年》时所指出的一种“混成认同”。丘认为:“这种混成认同包括殖民地/资本主义/西化等元素,使香港将大陆视为‘他者’;它同时又包括民族/国家/种族等元素,使得香港和大陆分享某些对于殖民者的反对立场。香港电影表达出它对后殖民未来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可以归纳为香港文化认同本身的混成本质。”⑦
8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对于中国内地的“原初性”想象,其实导致了一个复杂性的文化后果,它变成香港电影所强调的文化认同焦虑的中心。正是由于“原初性”的存在,使得香港电影具有了某种对于中国内地的“凝视”优势。无论是内地所显示的“落后”和“天真”、“压抑”和“力量”,原来都在一个中西之间的“香港”视野之内,香港独特的“窗口”位置为这种“凝视”提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础。担心回归造成这一优势的消失则是许多电影乃至文化研究的基础。这里所表现的对于“九七”以后的忧郁其实来自于一种对于回归的“合法性”的无法否定和对于内地的力量可能经由“政治”方面对于香港的自由进行压抑的焦虑,而香港电影特殊的对于中国内地的“原初性”想象的基础其实正是基于这种焦虑状态。
所以,80年代以来香港的“文化认同”所强化的电影潮流,其背景正是担心内地独特的社会状态对香港文化产生压抑,所以,这种“原初性”往往表现为一种大限将至、香港文化认同的独特性会由于政治因素而消失的心态。阿克巴·阿巴斯通过王家卫等人的电影研究提出的关于香港“消失文化”的论述,其实正显示了这一对于“原初性”想象的焦虑感;周蕾有关香港文化的著作《写在家国以外》,通过分析香港的诸多文化现象所提出的观点也是如此。这里其实隐含着一种根本性的意识形态想象,认为回归的进程尽管是历史的必然,但这一必然包含的却是一种“政治”压抑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取代”。香港电影通过对内地的“原初性”想象提供了某种对于未来的判断和预言。我们前面所说的两个方向上的“原初性”——“落后”和“天真”、“压抑”与“力量”之间,会出现有关政治的“原初性”吞没有关“文化”的“原初性”的后果。这种预言其实相当程度上主导了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发展,而“九七”后的历史正是对这一预言的大扭转和大超越。历史超出了预言的魔力,而电影也必然展开某种完全不同的形态。
3
我想从陈果有关“北姑”的两部重要的电影开始关于“后原初性”的讨论,一部是《榴莲飘飘》,另一部是《香港有个好莱坞》。这两部电影的重要性在于它们通过同一题材表现了不同的对于“原初性”的“凝视”的感受。
《榴莲飘飘》所表现的依然是一种“原初性”想象的延续。一个大陆来的性工作者秦燕(秦海璐饰演)在香港从事性工作赚钱,她原来是一个演员,却失掉了“天真”,在返回东北故乡时充满了感伤和忧郁。这里所延续的仍然是“落后”和“天真”的二元对立。在香港,她被侮辱和损害,却得到经济上的好处,内地是这个女性的精神皈依,却不足以提供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生活形态。内地的淳朴而“静止”的生活被刻意地强调,历经沧桑的主人公和她的那些仍然希望到香港寻找机会的学妹之间的关系蕴含了充分的“原初性”。通过“返乡者”的已经失掉“天真”的优势,电影直接走进内地的生活,将这一生活建构在一种“原初性”想象之下。这里所出现的想象来自于香港回归初期的形态,也就是发现“回归”并没有带来文化上的根本改变,香港原来所具有的优势“位置”仍然得以保持,香港电影对于内地的“凝视”目光仍然得以延续。摄影机在这里所展现的观看视点仍然具有高度的自信,观看着内地的“落后”和“天真”。这样的主题居然意外地应和了80年代严浩的(似水流年)的主题,只是这里人物的职业和生活更具有暧昧性。
随后,在陈果的电影《香港有个好莱坞》里却发现一种新的“后原初性”景观。这部电影里同样出现了一个性工作者东东(周迅饰演),她住在香港的一座名叫“好莱坞”的公寓中,有一种脱离原有界限的暗示,出现了“原初性”瓦解的新状态。这个东东没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痛苦,反而通过自己的能力利用香港,后来她到了真正的好莱坞,寄回香港的是以位于美国加州好莱坞为背景的照片。这里的东东是脱离香港原有的“原初性”视角的内地人,她虽然生活并不光彩,却意外地获得了一种完全在政治之外的新的力量,她可以自己掌控命运,可以有机会跳过香港直接到达美国,她对于香港居然采取了一种利用的姿态。在摄影机下,她闪闪发亮的眼睛闪耀着诱惑和梦想的力量。虽然她是一个不遵守道德的人,却具有某种“超溢”“原初性”的新的可能性。这里的“好莱坞”既是一个空间的实体,又是一个空间的隐喻。香港的“好莱坞”其实具有赝品的味道,它是真正的美国“好莱坞”的某种模仿,这似乎是对于香港在新一波全球化中介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位置”表现出某种不安。一种“不确定”的特质突然出现,而这种“不确定”的无力感并不是来自于某种政治力量的压抑,反而是来自于一种新的中国内地的发展所带来的直接在中国/西方之间建立新的想象性关系的结构。赵卫防的分析点出了这部电影的特征:“影片……表现转变中的香港,透出了香港人面对内地发展和香港经济困顿的迷茫心理,以及对香港主体优势缺失的一种矛盾心情。”⑧东东这样的人都已经可以掌控自己,原有的“原初性”的确定性表述显然面临危机,“后原初性”的出现就成为“中国脉络”的新的关键点。
“后原初性”其实是对“原初性”在“中国脉络”表述失灵状态的一种反应,也是一种香港的新位置正在生成的表征。这成为香港电影新的可能性的来源。
这里的“后原初性”其实来自于多重原因。中国内地通过“改革开放”而导致的内部市场化和外部全球化,使其直接进入了全球的生产和消费的体系。从90年代后期直到21世纪初,一方面中国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上海、北京等地已经成为和香港的功能、风格相近的“全球都市”,内地的闭塞和压抑状况一去不返;另一方面,香港经济却面临更多的挑战和转轨的困难。内地的开放不但没有带来香港政治的压抑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反而通过许多经济和社会政策支持使香港获得了新的发展,香港的国际优势仍然存在。当然,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分量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一个“新中国”的生成超越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悲情和屈辱的“现代性”历史,形成新的历史形态。这种变化带来香港的“原初性”的中国想象的终结和新的“中国脉络”的寻找。首先,这是电影业内部的强烈需求,因为香港电影业在90年代中后期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⑨,所以,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在一个新的“华语”市场的统一运作中谋求共同发展的要求已经非常强烈。香港电影在内地找到了发展市场,而合拍和资金、人员、制作等方面的全面整合已经成为趋势⑩。其次,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融合的趋势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的强烈要求,使香港认同和中国认同的同构性被进一步认知,这并不意味着香港认同的消失,反而是香港在中国全球化进程中谋求强势的机会,这也是一种文化再认知的开始和文化认同的新发展趋向的展开。
香港电影在回归后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正是如何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内地。这个中国“超溢”于我们的想象之外,也“超溢”于 1997年之前的种种历史预言。这种“超溢”其实是一种意料不到的结果。中国变成一个“意外”之地。它的意外乃是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入全球化进程,中国不再脱离世界而孤立地发展,没有变成对抗世界的自外之地,而是越来越变成世界的重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它通过巨大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突破众人想象的新空间。中国最近的发展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的讽刺”,其实是对于香港和中国前途许多想象模式的“超溢”。它“超溢”自己的过去,也“超溢”它的过去对现在和未来的限定。我们的种种依据常规和经验所进行的分析或预言总是被现实所覆盖。香港今天的问题在于,如何提供给全球和中国新的可能性经验,如何在中国崛起的大历史进程中在场。“消失文化”的危险其实根本不在政治压抑中,而在香港难以提供有力的新的可能性的空间上。不是有人压抑香港,而是大家需要香港给我们提供新的可能性。所以,“后原初性”的不确定就在香港当下电影的选择之中。
香港电影通过对于“原初性”的“超溢”获得一种新的“后原初性”的生成。这种“后原初性”是对于原有的中国大陆“落后”与“天真”的文化方面的认知和“压抑”与“力量”的政治方面的认知的全面“超溢”。首先,内地在许多电影中已经被一种新的形象所表述,如在《无间道》(三)、《终极无间》中出现的陈道明所扮演的内地警察,已经不再是90年代初刻板的“公安”形象,而是一个几乎和香港人没有多少差别的同事。一种“超溢”过去的“平视”目光已经出现。内地在文化上所呈现的是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新的力量区域。中国内地既是国家认同所在,也是经济的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动能之一。其次,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也被表现为一种现实力量和全球化存在。这里所出现的许多新电影都开始以新形态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因为过去的“中国脉络”虽然还在起作用,但“新新中国”形象“超溢”这一状态已经清晰。
从这个角度观察香港电影,我们会发现通过“后原初性”,一个新的未来正在展开。
4
我想提出两部同样由黄秋生出演的电影来结束我的讨论。一部是许鞍华的《千言万语》,一部是最近上映的赵良骏的《老港正传》。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后原初性”是如何展开的,以及香港的“中国脉络”的历史演化。
在拍摄于1998年的《千言万语》中,一个由黄秋生扮演的从事“左翼”运动的甘神父和一位从内地到香港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妓女与母亲双重身份的女性有一段谈话。这个女性向他倾诉自己的痛苦生活,神父给她一本毛主席著作,希望她看看,她却惊讶地说:“我是从内地来的呀!”神父只有苦笑。许鞍华对于历史的发展和“中国脉络”仍然有一份深刻的迷茫。
但最近上映的赵良骏的《老港正传》却是一部对于历史再度想象的作品。其中的那个普通的香港市民、电影放映员、“左翼”信仰者左向港,仍然由黄秋生扮演。在1967年以来的历史中,由于他的执著和信念错过了所有的机会,他失掉妻子,生活艰难,儿子也不了解他的信念,但他对于祖国的信仰从来没有改变。他可以说是一个屡败屡战的人物,坚守自己的信念,却时运不济。如果我们把历史比作棋局的话,他好像输掉了每一局,连希望看看天安门的梦想都没有实现,但他终于赢在了最后,他所相信的中国有了他所期望的命运。历史好像曾经在每一个时刻都嘲笑他的信念,但最后他是胜利者,因为他所热爱的这个国家确实迎来了自己的新命运。他想象的过程可能和现实发生的过程有距离,但他所想象的结果确实是那些在过程中成功的人们没有机会想到的。赵良骏有了比许鞍华更强的自信,因为他今天看到的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面貌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注释:
①②《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香港:香港市政局1997年修订版,第7页。
③有关中国内地“改革开放”给世界带来的影响的分析,参见郑必坚《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2日)。他在此文章中认为,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其实关键之点在1979年中国和苏联的不同选择。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在1979年的不同作为说起,同样都叫共产党,在同一个1979年,各自作出了性命攸关的重大战略决策:勃列日涅夫的苏共在这一年决定出兵阿富汗,进一步走上了打着‘世界革命’旗号实行军事争霸谋求世界霸权的自取灭亡之路;而中国共产党则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④⑤周蕾的这部著作已经由孙绍谊译为中文。为行文方便,本文直接引用此中译本。《原初的激情》,台北:远流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译文稍有改订。
⑥有关“第五代”电影的自我民族志化问题是“原初性”概念的重要支柱。参见周蕾《原初的激情》第二部分的论述以及拙作《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丘静美:《跨越边界:香港电影中的大陆显影》,《当代华语电影论述》,台北:时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73页。
⑧⑨赵卫防:《香港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年版,第395页,第346-361页。这里对于香港电影困境有详细的探讨,可以参阅。
⑩傅葆石《中国全球:1997后的香港电影》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载《当代电影》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