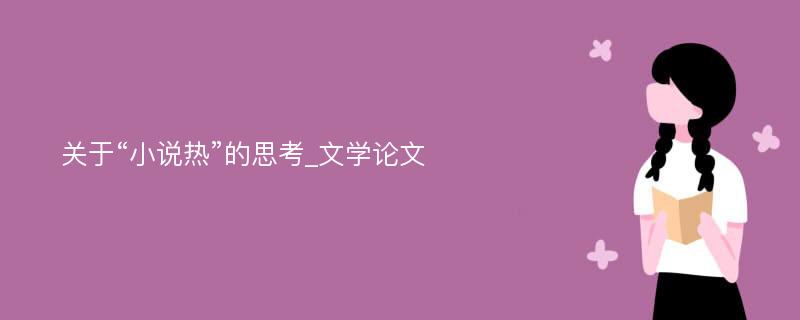
“长篇小说热”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历来被认定为一个时期文学成就的重要标志,被看作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学旗帜。进入创作旺盛期、充满艺术表现力的小说家,更是把长篇创作视为自己艺术生命的里程碑。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自80年代中期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遇到种种障碍,呈现逐年消退之势。在文学圈子里,人们报怨“出书难”、“纯文学创作不尽人意”、“文艺图书市场萎缩”,很大程度是指纯文学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不景气。曾经有专家作过悲观的预测:到本世纪末难以见到长篇小说创作和出版的旺势。
然而,1993年夏秋开始,由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凶奴》等一批长篇小说掀动的“陕军东征”、“长篇复苏”浪潮,骤然间将多少年倍受冷落、处境凄凉的一批长篇小说作家从幕后邀到台前,也使“运交华盖”难有出头之日的长篇小说出版,一夜之间身价倍增、炙手可热。惯由中短篇小说、纪实性作品和散文随笔卓领风骚的国内文坛,转瞬间即被长篇小说取而代之。接二连三登场问世的长篇小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了文学图书的主要市场,一个曾被专家们哀叹“在本世纪末也难以见到的旺势”居然活生生出现在我们眼前。
长篇小说由门庭冷落到畅销于市,从文学创作文艺出版的总体上讲当然是一件幸事;但我们认真检视其冷热缘由,考察其盛衰因果,特别是在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深远背景下作深入的反思,便会发现,由于创作中的良莠参差和出版中的追波逐流,时下的“长篇小说热”,荣中有虚,喜中堪忧,许多隐伏较深的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
一
长篇小说在备尝寂寞之后由冷趋热,渐成潮流,直接动因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多年来纯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出版难,一些作家早已完成的长篇小说书稿在出书过程中搁浅,形成相当大的文稿库存。据笔者了解的情况,国内30余家文艺出版社都程度不同地积压着长篇小说书稿,少的几十部,多的逾百部,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一批长篇小说书稿三审通过,发稿排版,只因为销路不畅,订数萎缩,已经制作成纸型、胶片而无法付梓。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中年作家,他们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精进不懈,历经短篇、中篇、影视剧、纪实性作品的不同创作实践,进入创作盛期,渐渐蓄积起长篇小说的创作实力;而这一批作家又为相当多的读者熟悉喜爱,具有颇为广泛的受众层面。这样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上,形成微妙的供求网络,几成默契的授受呼应。第二,读者的文学欣赏趋向明晰,求雅求俗取向分明,那种盲目追随阅读热点,从众消费购买图书的状况正在被清醒、独立、雅俗由己的阅读选择所代替。应该说,这是广大读者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显著标志。我们不妨回顾往事:70年代末,当“十年浩劫”以至更长久的左的思想禁锢被打碎之后,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热潮--“侦探小说热”、“武侠小说热”、“言情小说热”、“纪实文学热”、“三毛热”、“琼瑶热”、“汪国真热”、“王朔热”、“明清艳情小说热”、“散文随笔热”……当读者什么都看看,什么都想想之后,有了比较就会有取舍。到如今那些生活容量大、时代特色浓、现实感强的长篇小说作品终于渐渐受到读者欢迎。在多次读者调查中,笔者听到这样的反映:“港台小说都一个味儿,几个男人爱一个女人,几个女人争一个男人,再加上情杀、暴力、床上戏,看多了败胃”。还有的读者,阅尽“时髦小说”之后顿悟一般发觉:“最好的小说家不在港台在大陆。”由此可见,方兴未艾的“长篇小说热”依托着一个多么广阔的读者市场。第三,长篇小说被当作商品推入市场,商业化手段日益介入纯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长篇小说的出版过程。分析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过去很长一个时期长篇小说出版后的促销手段单一,这就是文艺评论。几乎完全依靠文艺评论家的褒贬毁誉来决定一部小说的命运,因此报刊媒体的舆论引导掌握了一部小说能否营销的生死予夺大权。而眼下长篇小说的畅销走红靠什么?靠广告,靠营销运筹,靠商业包装。图书市场调查表明,读者是否掏钱买一本书,52%靠广告宣传(当然,这种宣传包括该作品是否改编成影视节目,也包括新闻媒体的新书介绍、市场分析、作家访谈等等);30%靠图书封面(具体到一本书的装帧风格、印刷质量、丛书规模);12%看购买途径是否便捷、迅速(这证实畅销书为什么总是从遍布城乡的报亭书摊开始走红,继而推向全社会,新华书店的官商门市部几十年一贯制“守株待兔”,几乎与畅销书无缘);最后的6%才是报刊杂志的“畅销书榜”和文艺评论等宣传方式的综合影响。
由此看来,当前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既遇到了以前少有的发展机遇,也同时存在向不同方向拓展分化的诸多可能。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因长篇小说作者知名度、作品题材、艺术风格、营销策略、舆论引导和读者层面等原因,“长篇小说热”从发韧开始即呈现出求雅与趋俗、高攀与低走的不同取向,因而既显示健康的繁荣,又呈现令人忧虑的畸态。
二
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沉闷多年一炮打响,除了不同文学体裁“轮番走红”,循序渐进,“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受众规律”之外,一批当代作家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内容上确有分量,艺术上确有特色,主旨上确有拓展,不愧为久酿于心,厚积薄发的佳作,因而赢得了读者。譬如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00多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就是一部以丰富思想内蕴和独特艺术魅力取胜的佳作。作者唐浩明先生原为岳麓书社资深编辑,以编辑卷帙浩繁的《曾国藩文集》时精心研究史料,认真思索历史进而萌发了以曾国藩为主要人物创作多卷本历史小说的念头。长达十余年间孤灯寒窗,呕心沥血,甚至辞去出版社副社长的职务潜心于创作,终于使这部艺术品格出众的作品与读者见面。这本书的营销平淡无奇,既不大哄大嗡,更不哗众取宠,甚至连图书的封面设计、装帧风格都极其普通,但是小说却不胫而走,读者竞相传阅,迄今已重印数次总印数逾10万套。许多读者不仅阅读、珍藏《曾国藩》,而且还以此作为赠送亲友的礼物。笔者认识一位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曾担任中央部委的领导职务,离休后他闭门读书尤其博览当代长篇小说,他对《曾国藩》评价极高,认定是“安身立命、持家建国之辅佐”。他自费购买若干套,分赠同事、战友、亲朋。一部小说引起如此深刻的受众反响,令人深思。
陕西作家素来以吃苦耐劳、执著不懈闻名于世,近年来有相当一批优秀的长篇小说出自陕西作家之手。例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商州》,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陈忠实不满足于过去的文学成就,更不眷恋省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他发誓:50岁之前一定要写出一部死了可以垫枕头的书!于是,他出走长安,隐居故乡,“三更灯火五更鸡”,孜孜以求,10年创作出“一部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全书以厚重深邃的思想内容,复杂多变的人物性格,跌宕曲折的故事情节,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形成作品鲜明的艺术特色和震撼人心的真实感,被誉为“近年不可多得的长篇力作”。陈忠实成功了,他的人生夙愿、他的艺术追求果真在他知天命之年得以实现。而令人痛惜的,像路遥、邹志安这样孜孜不倦埋头长篇创作的作家,却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面对他们的心血之作、生命之作,读者给以厚爱理所当然。
此外,春风文艺出版社有组织、有策划地推出了“布老虎丛书”,接二连三让国内有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作家洪峰、铁凝、赵玫、梁晓声、崔京生等创作的长篇新作“闪亮登场”。立足于“纯文学作家写通俗故事,长篇小说进入大众阅读”的新颖创意,“布老虎”的图书商标紧随《苦界》、《朗园》、《无雨之城》、《纸项链》、《泯灭》等作品进入千家万户。如果说,60年代的《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主要凭借政治宣传广为传播的话,那么,90年代的“布老虎”则赖于有效的营销手段和明显商业化的出版运作,使纯文学作品进入流行行列,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只既雅又俗的“布老虎”啸叫一声,窜出文学的大林莽,改变了长时期来以长篇小说为代表的纯文学作品脱离大众阅读兴趣,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尴尬与迷惘,从而将长篇小说领出文人的小圈子,走向广阔的大社会。
三
长篇小说的行销热潮中,有一类在作品内容和写作上以猎奇为诱饵、靠趋俗媚俗而迎合读者的所谓“畅销书”,为眼下“长篇小说热”推波助澜,火上浇油。街头巷尾花花绿绿的新书广告,耸人听闻的故事梗概,自吹自擂的行销宣传,绝大部分是这种货色。它们也冠以“长篇小说力作”,“写实主义大手笔”、“投入当代文坛的一块巨石”等眩目冠冕招摇问世。书前书后的内容提要,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性爱为幡,盅惑人心--
“一个70多岁的老头日夜淫乐,终于累死在女人的大腿之下。”
“一个色艺双绝的女演员与12个身份不同的男子发生关系”,“五花八门的男欢女爱,生生不息的情场恩怨。”
“豹房是明武宗淫乱的舞台,人与虎斗,人与兽交。”
……
诸如此类广告招贴,赤裸裸地让泛情主义、泛性主义滋生蔓延,并像鼠疫一样在大众阅读中流行。有统计资料显示:长时期来全国每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仅有三四百种,约占全年图书品种的2%,而1993年夏秋“长篇小说热”席卷而来,各式各样的文稿拍卖会、选题策划所、信息咨询部以及大大小小的书商发行人,全都将贪婪的目光盯住长篇小说书稿,不管良莠优劣,不问青红皂白统统“策划”出版。据悉,1993年下半年一些出版社增补的长篇小说选题比年度计划还要多,并由此波及1994年全国出版计划。权威人士称:30家文艺类出版社报来的长篇小说选题有600多种,占整个文学类选题的18%,比1993年增加了10%以上,而实际运作中实现的选题至少又增加了一二百种。如此浩大的长篇小说冲击波,给图书市场带来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潮汐,一时间《混血》、《妻命》、《老村》、《骚土》蜂拥而来,《新镇》、《错乱》、《情殇》、《畸病》接踵而至,《天猎》、《地猎》、《人猎》成系列成套路,《床》、《帝京》、《恶德的根源》暗藏机关。这类小说并非文学创作的杰作佳构,然而处心积虑的通俗化包装和商业性推销,使其销量惊人,动辄数万册,乃至十多万册。广告的浮华热闹与小说内容的虚假丑陋互为表里,严重败坏了长篇小说的信誉与尊严,受广告蛊惑买了书的读者惊呼上当!这些书的畅销走红,与其说是作者的胜利,不如说是出版商、发行人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本身,即对文学构成强烈的反讽。因为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在这里成了一些人赚钱的旗幡和盈利的工具。
某畅销小说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忌讳地宣称:与别的长篇小说不同,“畅销书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制作之书”。“它在制作过程中基本上拒绝了创作最主要的动力,即灵感与激情,严格意义与精典精神”。“畅销书的基本特征就是发行量大,影响面广,主要审美功能就是娱乐。写作畅销书已经成为许多作家的内心期望……自1993年‘陕军东征’以来突然一下子冒出那么多长篇小说,这说明文学的制作时代已经到来”。而与此论针锋相对的观点,则是新近刊发的德国著名学者汉斯·迈耶(Hans Mayer)题为《我们已不再有文化》的长篇访谈,汉斯先生在深入分析战后半个世纪西方文化状况时指出:“资本主义从来就只与利润结婚”,“一切都成为消费的对象”,而使“真正的精粹的文化愈来愈被推到寂寞之中,排挤到怪僻的角落里”。那末,“长篇小说热”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学思考是什么呢?
四
已经无需考据揣测,只要推开门窗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我们已经被抛入一个物化的时代。而且清醒的人们看得更清楚,这无情的抛掷才刚刚开始。
有识之士告诫人们,这样的时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古代中国人并不曾像中世纪欧洲人那样拒绝物的引诱和享受而将灵魂皈依于上帝,尽管唐宋明三代东方古国的商品经济也曾一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与当今的整整一个时代的物化相比,人们对物的崇拜与追逐、对金钱的渴望与占有从来没有占据文化的中心,物的力量也从来没有使心的力量屈服。否则,不会有罗贯中、吴承恩、曹雪芹这样伟大的小说家,不会有那么多注定寂寞孤独却又光华灿烂、千秋永存的文学精典被前人创造出来,又穿过漫长岁月而保存至今。不可否认,长篇小说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旗帜,优秀的足以传世的长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然而,我们不幸置身于物化透彻的生存现实,不知道将何以寄托我们的文学理想,实现我们的文学抱负。只要稍稍俯下身来你就会看到:眼下相当多的一批作家欣赏物化、追逐物化,灵魂浮躁以至寝食难安,他们越来越自觉地把文稿当作商品,使写作成为谋生赚钱的手段。而更多的出版商、发行人和文化掮客,更是被物化的魔圈死死套住,往往以利润为半径规划成败,谋求得失,这在“长篇小说热”的潮涨潮落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事情的发展已经渐渐清晰,由于时代的局限,由于社会生活的局限,由于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现状的局限,由于作家们、出版者们以及万千读者的心灵局限,尽管操笔为伍者人数众多,长篇文稿库存不薄,出版商、发行人云集成阵,但是我们仍然要承认:一时间尚不会有大作问世,数年内还难以见到文学大师。上帝无言,或许这已是命中注定的结果。
在20世纪最后的几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有钱人;长期贫穷落后的东方古国,会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阔佬、富翁和小康殷实人家。然而祖祖辈辈就窘迫困苦的人们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可能会玩起“奢侈魔方”,变着花样地开销享受,却偏偏难以惦记文学才子,难以善待高人韵士。过去,我们无情地批判“精神贵族”,自然也将贵族的精神弃之若粪土。其实依今天的眼光来看,“精神贵族”应该是衣食丰足,精神朗照,怀抱巨大创作热情的人;他们不必为衣食温饱碌碌终生,也无需直面通货膨胀处心积虑,更不会为了将文稿仓库的陈货翻新而欺世盗名……他们忽略不计这一切,他们全身心潜入人类的精神世界,倾其毕生精力去构筑自己的文学殿堂。可以设想,19世纪文学泰斗托尔斯泰倘若没有庄园里宁静的书房,没有丰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恐怕难以从容不迫地写成《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家境若是温饱有虞,跌在贫困线之下,那么天才般的著作《烟》、《罗亭》、《贵族之家》的构思只有烂在肚子里。期待民族的文学成就,首先要期待作家个人的创作成就;期待作家个人的创作成就,首先要期待作家的精典精神。如今,荣膺最近一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早已将目光盯着核与地球环保等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的时候,为数不少的中国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们才如梦方醒般地忙着赚钱!无需讳言,一些人钱袋早已饱满,家境也开始发福,但是他们匍匐在钱眼里边就绝不抬头--他们的生活终究是物质的;而更多的极有天赋、极富创造力的作家们,又不甘清苦、不甘贫困如洗,为养家活命去挣钱--他们的生活又只能是物质的。
那位以《黑骏马》、《北方的河》等著名小说蜚声文坛,又以《心灵史》来命名自己的长篇小说的作家张承志,曾宣布挂笔退阵,离开文坛。但在新一轮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严肃文学刊物纷纷卸甲转向,文稿拍卖众说纷纭,作家签约卖身赚了时髦,调侃风气充斥屏幕,“五书闹京华”惹得长篇小说得运走红……的时候,张承志又放弃了自己的“约言”,以笔为旗,痛心疾首道:“我不承认这些人是什么作家,他们本质上都不过是一些名利之徒。他们抗拒不了金钱和名声的诱惑,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抗拒这一切的愿望和要求……”
人生总是要抗拒什么才会拥有什么,文学更是应该抗拒什么才会拥有什么。
事实就是这样无情而冷峻:物化的生活日益物化着,我们却凭空希望那几乎构筑在物化基础上的一次两次“热潮”会带给我们宏篇巨制的大作和惊世骇俗的大家,可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