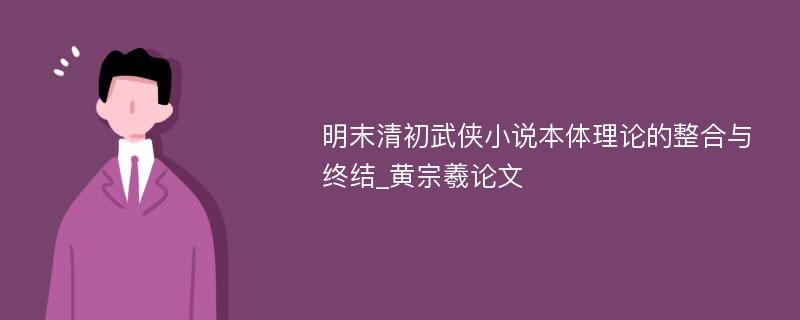
明末清初本体功夫论的融合与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末清初论文,本体论文,功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阳明后学的本体和功夫两大系统代表着明朝后期学术思想的两大发展趋势,这是在王阳明的核心理论——“良知”和“致良知”学说及其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发展衍化出来的。这两大发展趋势,到了晚明,则有了融合的动向。这种融合的动向,随着李贽和黄宗羲的集大成,而意味着本体功夫论的终结。
一、本体系统与功夫系统的融合
明朝晚期,阳明后学的本体系统和功夫系统这两大发展趋势出现的融合动向,既表现在本体系统和功夫系统的各自内部,也表现在本体系统和功夫系统之间。
1.本体系统内部的融合动向
首先,本体系统内部的绝对、虚无和日用三派,特别是虚无、日用两派从本质上来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尤其两派在“良知现成”、“不离乎日用”这一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例如,心境“高亢”的王艮,从王阳明的“良知现成”说和“心物一体”说出发,推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的论断,主张在“百姓日用”或“家常事”中体现良知。而处世“圆融”的王畿则从另一角度得出了本体“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的结论,认为“古人理会心性,只家常事”。
其次,虚无和日用两派彼此之间往往交叉从学,而且,两派相互之间平时也很少发生磨擦。这就为虚无和日用两派的融合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第三,虚无和日用两派发展到后期,理论上有相互汲取、融合的趋势。例如,日用派的王襞就深受虚无派的王畿的思想影响。他以王畿的“四无”说为出发点,结合佛、道的“空”、“无”,把日用派创始人王艮的思想向着更彻底的方向发展。
2.功夫系统内部的融合动向
功夫系统内部主意、主敬、主静、主事四派相融合的动向,集中地表现在刘宗周的学术思想中。
刘宗周提倡诚意、慎独,是主意派的代表。但“慎独”不过是“主敬”的代名词。黄宗羲说过:“先生(刘宗周)宗旨为慎独,始从主敬入门,中年专用慎独工夫。慎则敬,敬则诚。”(《刘子全书》卷三九《子刘子行状》)刘宗周确也说过:“入道莫如敬,从整齐严肃入。”(《刘子年谱》上“万历三十一年”条)
对于主静派,刘宗周曾作《圣统》,把主静派代表人物罗洪先视为接王阳明之后的“先儒”;31岁后又“专事静养”,“析主静之学”(《刘子年谱》上“万历十年”条),后来又把它融入“慎独”说之中,认为“独只在静存,静时不得力,动时如何用工夫?”(同上书,“天启六年”条)
至于主事派,刘宗周在坚持“诚意”、“居敬”、“静养”和“慎独”的同时,大量地吸收了主事派的“事上工夫”说,强调“吾儒学问在事上磨练,不在事上做功夫,总然面壁九年,终无些子得力”(《刘子全书》卷一三《会录》)。这便为经世致用之学的建立奠定了哲学认识论的基础。
3.本体系统与功夫系统之间的融合动向
应该说,阳明后学的本体系统和功夫系统是有着尖锐的矛盾的。首先,是“无善无恶”和“有善有恶”的矛盾。王畿遵循王阳明“体用一源,有是体即有是用”的原则,从心体的“无善无恶”,悟出意、知、物的“无善无恶”,主张“四无说”,并以此与钱德洪争辩。(参见《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一《天泉证道记》)与王畿相对,钱德洪则以“四句教言”“为定本”,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同上)实际上是主张“四有说”。
其次,是“流行”与“收敛”的矛盾。所谓“流行”,就是“发用”,而“收敛”则是“戒惧”。所以,如果信任良知,就必以“流行”为主,而轻视修养功夫,因为“乐(即:“活泼”)是心之本体,“流行”是“活泼”良知的本质属性。只要“依此良知流行”,便可“当下具足”,“人人见在”。反之,如果重视功夫,就必以“收敛”为主,因为无论什么形式的功夫,都是为了销欲去蔽,因而都需保持高度的“戒惧之心”,以防止心之体被外物玷污。
第三,“自然”与“主宰”的矛盾。在王阳明那里,“主宰”强调的是“心体”,“自然”注重的是“发用”。“主宰”要求“心”对“意、知、物”的统摄,“自然”则需要“心”对“意、知、物”的松绑。强化“主宰”作用,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心体对外物善恶是非的分辨,进而通过收敛功夫复归纯善的良知本体;而强化“自然”本能,则必然得出“制欲非体仁”和“物欲合理”的逻辑结论,从而取消禁欲主义的道德修养功夫。
总之,从王阳明“四句教言”的首句和“流行”、“自然”说出发,可以产生本体系统;而从王阳明“四句教言”的后三句和“收敛”、“主宰”说出发,又可以引出功夫系统。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然而,这“四句教言”的首句和后三句,“流行”、“自然”和“收敛”、“主宰”,在王阳明那里原又有相统一的一面:①在“无善无恶”的问题上,王阳明的“四句教言”中,第一句讲本体虚无是为了明莹无滞,后三句讲实有的道德修养功夫,是重点所在。可见,“四句教言”是无与有之结合,实际上是“四无”与“四有”之统一,而其重点放在实有上。②在“流行”和“收敛”问题上,王阳明既强调“流行”,说:“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认为只要“依此良知流行”,便可“当下具足”,“人人见在”。同时,王阳明又注重“收敛”,说:“精神道德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③在“自然”和“主宰”问题上,王阳明认为两者都不能偏废。他说:“我只是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又说:“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
正因为如此,在本体系统和功夫系统进一步发展以后,两者之间也开始出现融合动向。例如,主事派从现成功夫出发而推出“离却天地人物……亦无所谓良知”,这与日用派从现成良知出发而得出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王心斋先生遗集·语录》)是何等地相似。这说明,本体系统和功夫系统实在是殊途同归的。
二、李贽和黄宗羲的集大成
李贽和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本体功夫论的集大成者。其中,李贽是本体功夫论,特别是本体系统的本体功夫论的集大成者;而黄宗羲则是本体功夫论,特别是功夫系统的本体功夫论的集大成者。
1.李贽的集大成
李贽是在王阳明本体功夫论基础上,主要综合本体系统内部虚无、日用两派的本体功夫理论,同时吸收功夫系统的观点并加以发展,提出自己的本体功夫论的。
(1)对王阳明本体功夫论的继承
李贽的本体功夫理论,首先是从王阳明那里来的。王阳明曾说:“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噎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年谱》)为此,李贽也讲天地万物“皆是吾妙明真心中一点物相耳”(《焚书》卷四《解经文》)。同时,他又说:“若无山河大地,不成清净本原矣,故谓山河大地即清净本原可也。”(同上书,《观音洞》)这与王阳明的说法是一致的。特别是李贽在叙述王阳明《与顾东桥》书信中所阐明的良知本体论时,把“良知”改写成“太虚”,把“知”改写为“虚”,把“致知”改写成“悟虚”,更能说明这一事实。
(2)对本体系统虚无、日用两派理论的综合
李贽的本体功夫理论也是综合本体系统虚无、日用两派的思想而成的。李贽以道为虚空,这是虚无派的观点。但李贽又是一个日用派的人物,他把虚空全部归到“活泼泼”的民众的生活中去。他说:“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焚书》卷一《答邓石阳》)然而,因为李贽以虚空为道,所以他又追求不执著于伦物的达人宏识,认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这充分说明李贽对虚无、日用两派的综合。
(3)对功夫系统各派功夫观点的吸收
李贽不仅综合本体系统的虚无、日用两派,而且还吸收功夫系统的观点,提出所谓“当然功夫”,认为只有基于“当然功夫”,才能自然而然生出礼义,才能不因人为安排而使礼义歪曲。(见《焚书》卷三《四勿说》、《读律肤说》)李贽也强调功夫的重要性,这一点从他的艺术论更可以看得明白。李贽认为,技艺(功夫)和心(本体)必须相即而浑一,心通过技艺才始得成为“神”。(见《焚书》卷五《樊敏碑石》、《诗画》、《琴赋》)所以,他当时不作当下即是、当下即现成的顿悟之论,反而强调渐修的重要性。这表明他不仅兼采虚无、日用两派,而且融合本体、功夫两系统,预示着本体功夫理论的统一和终结。
2.黄宗羲的集大成
黄宗羲是上宗王阳明,并以其师刘宗周为中介着重对功夫系统的本体功夫论加以综合,且在此基础上,去融合本体系统的观点,从而提出自己的本体功夫论以至全部学术思想的。
(1)承其师说,肯定本体与功夫的合一
黄宗羲首先是继承其师刘宗周的学说,肯定本体与功夫的合一的。他说:“先生(刘宗周)宗旨为慎独,始从主敬入门,中年专用慎独功夫,慎则敬,敬则诚,晚年愈精密愈平实,本体只是这些子,功夫只是这些子。仍不分此为本体,彼为功夫。”(《子刘子行状》)在这里,黄宗羲通过刘宗周所主张的慎、敬、诚,论证了“不分此为本体,彼为功夫”。所谓慎、敬、诚,即思想意识和言论行动上自觉地合乎道德原则;若能在慎、敬、诚上做功夫,慎、敬、诚就在这种功夫中,即在道德修养中。这是通向“天地完人”的途径。黄宗羲据此批评了本体系统无视功夫的做法,他说:“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南雷文案》前集一《留别海昌同学序》)
(2)在本体与功夫的合一论中加重功夫的分量
黄宗羲在肯定了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之后,便努力加重功夫的分量。他强调本体就是随“功夫积久”而展开的过程,提出了“心无本体,功夫所至即其本体”(《明儒学案·序》)的新命题。在此,黄宗羲认为,本体并非超越于功夫之上的绝对理念,而是在“吾人应物处事”、“竭其心之万殊”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吾心之物”。这种“万殊”形态的“吾心之物”,尽管是“心”变化所致,其实正是各种各样的具体事物。因此,功夫亦应“只是一个行字”(《明儒学案》卷十),即“力行实际去做”(同上),切不可使行“滞于方隅”(同上书《师说》),亦“不得专以经义为主”(《破邪论·科举》),更不能“以空疏应世”(同上)。功夫的目的就是为了“通今致用”(同上),故功夫必须“致之于事物”(《明儒学案》卷十)。这样,黄宗羲就不仅以功夫代替了本体,而且赋予功夫以新的内容。
(3)用“功夫所至,即是本体”的观点来说明人类认识的历史过程
黄宗羲最后把他所提出的“功夫所至,即是本体”的新命题拿来说明人类认识的历史过程。他认为“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于是就表现为“殊途百虑之学”。他说:“诸先生深浅各得,醇疵互见,要皆功力所至,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未尝以懵懂精神冒人糟粕。”(《明儒学案·序》)所以,真理正是在“深浅各得,醇疵互见”的学派纷争中展开的。他说:“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同上)在这里,他认为学派纷争的历史正体现了“本体”随“功夫”而展开的运动,并认为通过历史的考察可以把握其一本而万殊的脉络;而把握一贯的学脉,正是为了引导人们去做切实的功夫。
总之,黄宗羲继承、发展了其师刘宗周的学术思想,把刘宗周的“本体即功夫”的命题,改成“功夫即本体”的命题。这既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必然,也是锻铸新理论之时代需求。因为适应处于激变中的社会发展,迫切需要新理论的指导。为此,惟一的出路,便是通过对现实活动的理论概括来确立建构新理论的支点,这就促使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把传统的“功夫”范畴当作本体范畴,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给予充分的重视,藉此挽救王学,改造理学,组建新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功夫即本体”是一个时代的命题,也是一个意蕴极为丰富的哲学命题。黄宗羲不仅运用这一命题,总结了宋明以来的本体功夫论,而且用来铸造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三、本体功夫论的终结
明清之际,以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为契机,随着对封建礼教和纲常伦理的批判,随着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高涨,同时也由于本体功夫论的充分展开和全面总结,本体功夫论便终结了。
1.对封建礼教和纲常伦理的批判,动摇了本体功夫论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政治基础
我们知道,本体功夫论,是为了适应自宋朝开始的封建社会后期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把体用范畴运用到认识论和道德修养领域,与心性学说相结合的产物。随着封建礼教和纲常伦理遭到越来越猛烈的批判,这种本体功夫论便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而李贽和黄宗羲恰恰是这个时期批判封建礼教和纲常伦理的杰出代表。
李贽首先是用“是非无定”论破除圣人迷信。他说:“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亦无定论。”(《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他从这样的“是非无定”论出发,认为真理是多方面的:“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焚书·答耿中丞》)同时,真理也是发展的:“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因此,应该造成“不执一说,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藏书·孟轲传》)的局面。这种求“通”搞“活”的开放思想,在打破“圣人迷信”方面起了难能可贵的积极作用。接着,李贽又进一步用“物各付物”论反对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尖锐地指出,封建礼教通过社会习染形成的“闻见”和哲学加工编造的“道理”,不仅束缚人的“视听言动”,而且绞杀“童心”,使人们“失却真心”,变成了“假人”。(参见《焚书·童心说》)为此,他要求“有德之主”应根据“物各付物”的原则,实行“因材”开发而又使之“并育而不相害”的开明政策,来满足“千万人之心”、“千万人之欲”。(《明灯道古录》)这种观点鲜明地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罗网、发展“自由私产”的愿望。
黄宗羲则首先是在对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给予高度重视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王阳明及其本体系统各派弟子的“自证”、“自悟”、“自得”的人格独立精神。本着这种精神,他不仅肯定了阳明学派关于人人皆能成圣作圣的观点,而且主张对任何东西都抱“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南雷文案·答黄吴仲论学书》)的怀疑批判态度。由此,黄宗羲专门就君臣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伦理思考和深刻的政治批判。他认为,君臣不是主奴关系,不应有尊卑之分,而应是平等的互为师友关系。他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明夷待访录·原臣》)的君臣平等原则。以此为前提,他猛烈地抨击了独断专行的君主制度,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2.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高涨,进一步冲击了本体功夫论的思想基础
在明清之际日益高涨的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的冲击下,陆王心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从而导致本体功夫论濒于崩溃。
被称为“经世致用”的实学新思潮,是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它形成于明代中叶,在明清之际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高潮,成了实学思潮的极盛时期。“经世致用”实学大致可分为三类:①“明体实学”。这与明朝中后期的“明道实学”有相似之处。它强调致用的重点,在于“明体”;把心性视为本体,把应用视为心性的体现;认为“体用一源”,以用为统一体用关系的基础,把“明道”局限于“明体”,以求“明体适用”。这类观点以王夫之为主要代表。②“质测实学”。这是明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反映。它强调致用的重点,在于“辨物则”,认为只有通过明事物客观规律,才能行之有效。这以方以智为主要代表。③“济世实学”。这是“实学”发展的最高峰。它既注重于“明道”,也注重于“明体”和“质测”实学,但特别注重济世、济时。他们反对过时之学和无用之学,以行道济时为意,用世之心最殷,认为学问就只能是有用的、济世的。这是我国近代实用主义思想的萌芽。这以黄宗羲、傅山、颜元为代表。这三类实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专讲实用之道和实用之功,并且以此为指导,以总结明亡的经验教训为契机,实行儒家价值观由“内圣”向“外王”的转移,从而对明以来空谈性理、不务实际之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使本体功夫论失去了得以维持的思想基础。
3.本体功夫论的充分展开和全面总结,使本体功夫论逻辑地走向终点
称为宋初五子的周敦颐、邵雍、张载和程颢、程颐,在继承了唐代中叶以后产生的复兴儒学的思潮之后,进一步考察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探索了人类存在的本源。虽然具体观点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宇宙的本体(太极、无极、太虚、理)是形而上的、无限定的、绝对的存在,它与阴阳五行相结合而生成万物。因为万物中只有人类禀有秀气,所以人也就成了万物之灵长。宇宙本体内存于人类,构成了人类的本性,这人类的本性也就是道德的根源。通过道德修养的功夫,就是为要认知内存于人类的宇宙本体,或恢复人性之本然。这样一种观点,也就是本体功夫论。程颢的学说发展到陆九渊明确称为心学,而程颐的学说发展到朱熹完全被其继承而成为理学。陆学长于实践的、一体的思考;朱学则长于唯理的、对立的思考。
自宋学向明学的展开,是理学向心学的展开,因而是从持复杂的构造的唯理主义向着持单纯的构造的实践主义的展开。其中,王阳明的心学继承了陆九渊的动的心学,陈白沙则背于陆九渊而与趋向于静虚之学的杨慈湖的心学相通。此外,朱子学发展到明朝中期带有心学的倾向。它虽仍提倡格物穷理,但已有更重视理的体认存养的倾向,而归根到底趋向实践化、单纯化。这样,明代的朱子学便接近于陆王心学,然而与陆王心学是划一界线的。单就本体功夫论而言,程朱理学是自功夫趋向于本体,而陆王心学则自本体趋向于功夫,即前者取功夫即本体的立场,而后者则取本体即功夫的立场。
这里,特别是王阳明,他把三纲领、八条目归于致良知,认为在致良知之外无致知,在致知之外无学问,而以浑一的功夫为学之要。即使关于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他也是把心、意、知、物作为是一物,把正、诚、格、致作为是一事,而认为归根到底本体功夫只是一个。所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是本体功夫一体之学。
不过,王阳明虽然用致良知之学教导门人,但却是应于门人的机根,既有强调本体之事,又有强调功夫之事。而且,既说以本体为功夫,也说以功夫为本体。为此,其门下便分成本体、功夫两大系统和本体系统的绝对、虚无、日用以及功夫系统的主静、主敬、主事、主意七派。这两大系统七个派别,各自对本体功夫论作了充分的发展,并最后由李贽和黄宗羲等人作了全面的总结。由此,本体功夫论,便朝着实践化、单纯化,亦即一体的思考的方向,走到了逻辑的终点。从而宣告了本体功夫论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