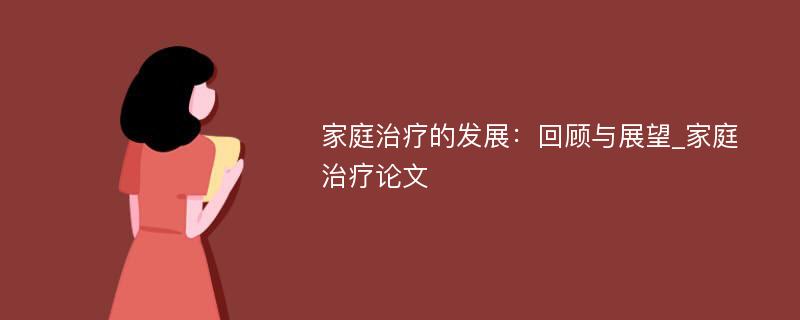
家庭治疗的发展: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庭治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0)03-0093-06 收稿日期:2009-11-16
家庭治疗是心理治疗的一种形式,它将所存在的问题或症状从个体转向了关系[1]12-30,通过促使家庭或更大的机构在内的系统的改变,进而处理和消除个体所存在的问题或症状。家庭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人类行为的框架,代表了一个新的领域和方向。斯路齐(Sluzki)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家庭治疗是行为科学上主要的认识论革命。[2]366积极心理治疗大师佩塞施基安也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家庭治疗看成一种特殊的治疗安排,而是把它解释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方法,一种公正地对待人的社会性方法。[3]7
一、家庭治疗的产生:将心理问题的成因从“内心冲突”扩展到了家庭层面
大多数研究家庭治疗历史的人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年是家庭治疗的形成时期。
与家庭治疗产生直接相关的两个主要方法论是系统论和控制论。系统论将家庭看成一个有机体,自成一个系统,有许多次系统,每个次系统间既有联系又有制约,形成家庭系统有序的运转,以此实现家庭的功能。系统论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而非个人的特性上,认识到家庭系统内的关系模式大于各组成部分的本质,强调分析问题时从家庭整体入手,研究的是组成家庭整体的各部分因持续互动而产生的相互关系。
控制论为家庭治疗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模式:即家庭规则是家庭用以掌管家庭系统所能容忍的行为范畴。罪恶感、双重信息、症状是家庭用以强化家庭规则的负向回馈机制。面对问题时家庭所反应的行为序列显示了家庭系统如何面对问题。
除了方法论,学者们还进行大量的理论准备工作。当时,在美国有三支独立的研究队伍,一支是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加利福尼亚心理研究所领导的研究队伍;一支是利兹(Ted Lidz)在耶鲁领导的研究队伍;还有一支是的鲍文(Murray Bowen)和文尼(Lyman Wynne)在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领导的研究队伍。三支队伍的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家庭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的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贝特森研究小组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家庭沟通系统失败的结果;利兹研究小组的结论是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家庭“营养失调症”,这样的家庭无法提供完整人格发展的必要要素;而鲍文和文尼的研究显示心理障碍和偏差行为的出现是家庭成员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研究后来发表在一本论文集——《密集性家庭治疗》(Intensive Family Therapy)中,他们以科学研究的方法,将心理问题的成因从“内心冲突”扩展到了家庭层面,为家庭治疗的产生打开了大门。[4]12-56
此外,二次大战之后,在战前主要是由精神科医生提供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服务,开始由许多经过不同训练的实务工作者来承担,临床心理师、精神科社会工作者、婚姻咨询师等开始加入心理治疗行业。这些不同训练背景的临床工作者,在治疗过程中虽然仍以个体治疗为主,极力寻找操控个人外在行为的一种看不见的内在动力,寄希望从人们的早期记忆中去挖掘攻击、害怕和焦虑行为的根源。但他们逐渐发现,根本无法确定人们行为的开端在哪里,因为个体的行为常常是家庭成员互动的结果,家庭成员的某些行为和感受是对其他家庭成员行为和感受的反应,然后其它行为又是针对这个反应的再反应,如此循环往复下去。[5]45因此,大多数的人类行为都是互动性的,有些问题存在于个人的心理状态,却展现于与他人的互动之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帮助人们改变他与其他人的互动方式,而影响人们的最主要的互动方式出现在家庭中。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家庭在心理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开始尝试从家庭的角度来对人类的心理行为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时至今日再去回顾,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六个看似不相干的理论及临床的发展,共同为家庭治疗的兴起铺路,它们是:(1)精神分析治疗范围的扩展,将精神分析的治疗范围扩展到处理全面性的情绪困扰问题,包括家庭问题;(2)一般系统理论的引入,强调部分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交互影响的整体;(3)家庭动力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的探索;(4)儿童辅导运动的发展;(5)婚姻辅导的发展;(6)团体治疗技术的发展。[6]27-66
二、家庭治疗的发展:各家庭治疗流派的创造性竞争
家庭治疗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家庭治疗的探索期;二是家庭治疗发展的黄金期;三是后现代家庭治疗发展期。
1.家庭治疗的探索期
20世纪50年至60年代初是家庭治疗的探索期,也有学者指出,这10年是家庭治疗运动奠定基础的10年。[7]8-30这一时期家庭治疗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将之前的关于家庭的研究逐步运用于临床实践,通过家庭观察而获得的理论与方法开始逐步走向融合。
当时,这种探索在美国四个地方独立展开[8]35:杰克逊(Don Jackson)在加里福尼亚的帕罗·阿尔托(Palo Alto)成立了一个心智治疗中心(Mental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MRI),致力于将社会和行为科学的理念应用于临床,开创了联合治疗,在治疗过程中尤其关注人们互换信息的过程;贝尔(John Bell)在克拉克大学定期接待整个家庭,思考会见整个家庭的技术,将家庭治疗分解成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都集中在家庭特定的问题上;阿克曼(Nathan Acherman)在纽约创办了家庭研究所,发展出对于家庭动力研究的兴趣,通过家庭访视研究家庭的互动模式[9]82;鲍文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MH)发展了一个研究课题,让有精神分裂症成员的家庭一起入院治疗,观察这类家庭中母子间的共生关系。[8]25
这四个研究与实践是独立展开的,之间没有任何沟通与交流,直到1957年,美国精神卫生学家联合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召开家庭治疗会议,全美的家庭治疗及研究者才首次产生联结,家庭治疗运动在全美范围内显露出来。[10]601961年,哈利(Jay Haley)与阿克曼共同创办了《家庭过程》杂志,标志着家庭治疗真正全面地发展起来。
2.家庭治疗发展的黄金期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是家庭治疗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也是家庭治疗各主要流派的发展与成熟期。家庭治疗的先驱们致力于发展自己流派的理论与技术,建立自己的工作坊和培训中心,并努力将自己的治疗理论运用于实践,整个家庭治疗领域一派欣欣向荣,30年出现了三个主要的经典流派。
1960年代以帕罗·阿尔托小组创立的沟通模式为代表,代表性书籍是《人类沟通的语言学》(Pragmatics of Human Communication)和《联合家庭治疗》(Conjoint Family Therapy),这是两本系统介绍家庭治疗的教科书,对家庭运动的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沟通是帕罗·阿尔托小组家庭治疗师主要的分析工具。他们提出家庭中每一个信息都受到另一个信息的高度限制,内隐信息在争夺控制权的斗争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症状本身反映了家庭沟通水平的不协调。治疗的目标是输入正向回馈以松动家庭原有的互动模式,重建家庭的稳定与平衡。帕罗·阿尔托小组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杰克逊、哈利和维琴尼亚(Virginia Satir),帕罗·阿尔托成为了早期家庭治疗发展的中心。
1970年代属于米纽钦(Salvador Minuchin),他所创建的结构式家庭治疗支配这10年的治疗倾向。1974年,米纽钦出版了他的《家庭与家庭治疗》(Family and Family Therapy)一书,详细地阐述了通过结构式家庭治疗而带来改变的理念,这本书后来成为了家庭治疗史上一部经典著作,影响深远。这10年,由米纽钦领导的费城儿童辅导中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家庭治疗运动的中心,吸引了全世界的人们蜂拥而至。结构式家庭治疗视家庭为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运作的结构功能系统,个体的症状来源于家庭结构的不平衡,干预的方式是增加家庭系统的压力,促使家庭结构开放,产生改变,进而重新达至平衡。[11]74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米纽钦、阿彭特(Harry Aponte)、乌姆巴格(Caner Umbarger)、沃尔特斯(Marianne Walters)、费施曼(Charles Fishman)、曼登尼斯(Cloe Madanes)等人。
1980年代的家庭治疗发展则以策略式家庭治疗的发展为代表。有三本书系统地描写了该流派的主要方法:《改变》(Change)、《问题解决治疗》(Problem-Solving Therapy)、《矛盾与反矛盾》(Paradox and Counterparadox)。策略式家庭治疗主要关注的是家庭系统如何被负性回馈所控制,他们认为家庭对于问题的出现采取了错误的解决方式,症状是不断重复出现的错误的行为模式的结果。治疗的目标主要是提出干预策略,寻找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兹沃克(Watzlawwick,P.)、维克兰德(Weakland,J.)、鲍斯考勒(Luigi Boscolo)。
除了这些经典流派,同一时期家庭治疗还出现了鲍文家庭系统治疗、精神分析家庭治疗、认知—行为家庭治疗等,虽然这些流派没有像经典流派那样盛极一时,但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家庭和有关家庭问题的解决之道,为家庭治疗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家庭治疗终于挑战了个体治疗的霸权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推广开来。这一时期家庭治疗的重要发展也发生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在英国,罗博(Robin Skynner)在伦敦家庭治疗研究所开展心理动力家庭治疗,约翰(John Howells)发展出一套系统性的家庭诊断方法作为治疗干预计划的必要步骤;在德国,海宁(Helm Stierlin)将精神动力学和系统观进行整合,发展出了系统式家庭治疗;[6]96在意大利,赛文尼—帕拉佐莉(Mara Selvini Palazzoli)在米兰成立了家庭学习研究会,创建了影响深远的家庭治疗米兰学派。此外,家庭治疗也在专业上日益受到尊重,成为大多数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会议公认的主题,并很快渗透到了成人精神分裂症、心身症状、成瘾、抑郁、焦虑、婚姻压力、性功能障碍等许多领域,成为心理治疗领域的“第四势力”。
3.后现代家庭治疗发展期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强调心理现象的建构性和心理学知识的相对性,这一取向贯彻到家庭治疗领域,对家庭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其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化。
首先是建构主义对家庭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尼古拉斯和斯克瓦(Michael P.Nichols & Richard C.Schwartz)认为,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家庭治疗的新变化表现在:(1)提升意义的位置,至少将它和行为改变放在了同一位置上;(2)对不同理论取向保持谦逊的态度;(3)增加对假设背后价值的注意;(4)减少强迫他人改变或对人的控制,增加对人自身资源的信任等[12]。建构主义质疑了家庭治疗试图寻找症状背后原因的努力,认为所谓的家庭的真实,实际上是治疗师的一种心理建构,寻找“症状”背后本质原因的过程,实际上是将他们自己的框架或解决方法强加于家庭。[13]31-47建构主义还质疑了家庭治疗认为治疗师是专家,可以在治疗过程中“加入”家庭,指导家庭改变的治疗理念。建构主义认为,治疗师所用的沟通和思考都是用来协助他发展出可能有用的想法,然而这些想法无论怎样被运用,家庭故事最终仍是不可预测和神秘的。[14]149-173
其次是女性主义对家庭治疗的质疑。女性主义对家庭治疗的质疑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马斯汀(Rachel Hare-Mustin)首先撰文指出,现存的家庭治疗模式中先天具有性别的偏见。此后,女性主义家庭治疗的文章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他们指出在家庭治疗领域,一直都假设家庭的常态性功能以及男性与女性是分离而平等的事实,好像家庭成员对家庭内部的互动结果具有同等的控制力,这是不符合社会现实的。[9]40-45女性主义挑战了家庭治疗师性别歧视的价值与态度,认为他们的理论与实务助长了这些价值与态度的产生,以性别定义的家庭功能蓝图,完全忽视了社会因素对家庭中角色预期的影响,忽视了男性与女性在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的差异与权力不平等,是对女性的一种潜意识的偏见,当治疗师带着这样的刻板印象进入治疗系统时,会对家庭产生影响,使家庭按照治疗师预期的性别角色刻板印象行动,不但会限制家庭做出积极改变的能力,还会增强现状并协助继续促成女性的被驯服。[15]56
第三,家庭治疗受到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人的行为不仅受到个体内部因素的调节,也为社会的文化因素所制约,从根本上讲,行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行为的研究不能脱离制约行为的特定文化背景。家庭治疗就其本质来说是西方主流文化的产物,因此具有文化的局限性,并不具有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普遍意义。家庭身在其中的文化背景,包括民族、种族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宗教、教育水平、社会阶层、性取向以及家庭赖以生活的文化规范,这些因素以多种方式影响家庭,有时这些影响是微不足道的,有时则对家庭功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多元文化主义质疑家庭治疗似乎在寻找一种适合所有家庭的单一的家庭结构理论,这样会忽视家庭所处特定文化对家庭的影响,有可能将一个不熟悉的家庭模式贴上功能失调的卷标,而这个被贴上异常标签的行为可能与该家庭所属群体的文化是相适应的。
受后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挑战,20世纪80年代后,家庭治疗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综合起来说,这些新变化包括:(1)不仅关注家庭成员行为本身,而且关注对行为背后的意义;(2)避免专家性以及透过治疗过程的影响力来控制家庭,尤其避免用一个既有的理论框架去套用不同的家庭;(3)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与态度,越来越注意从性别的角度看待家庭中呈现的问题;(4)强调治疗师与家庭之间合作关系,重视挖掘和运用求助家庭本身的改变能力和资源;(5)从家庭所在社会结构背景的角度了解家庭,审视家庭与所在文化背景相适应的结构,看到家庭内在成员相互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它背后的社会结构的影响。
在这些新变化的基础上,1980年代后家庭治疗领域产生了一些新的流派,如聚焦问题解决家庭治疗、叙事家庭治疗等,代表人物分别是史迪文(Steve de Shazer)、博格(Insoo Kim Berg)和怀特(Michael White)等。
三、家庭治疗的未来:整合以及对特定情境下特定家庭问题的最有效治疗
进入新世纪,经典家庭治疗流派的主要领导人要么已经离开人世,要么年事已高,他们的影响力日渐消退,加之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家庭治疗不得不寻求新的机遇与发展方向。
首先,整合成为家庭治疗发展的主要趋势。1990年代之前,关于家庭以及如何改变家庭,每个流派都形成了一套理念、理论与技巧,以至于在家庭治疗领域内部出现了流派林立的局面,所有流派都致力于使自己和其他流派不同,认为吸收别派的观点是对自己已有治疗模式的削弱。但正如休(D.W.Sue)所指出的,这些流派的一个弱点就在于:它们只着眼于人类情况的一个方面[16]7-14。
进入1990年代后,家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人们也渐渐意识到家庭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统一体,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保证对所有的临床案例都有用,也没有一种方法被证明是明显优于其他方法的,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完全打破了各流派之间的界限,整个家庭治疗领域出现一股整合的潮流。很多的研究也证明,如果治疗者使用了多种形式的治疗法,所确定的治疗目标又与患者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价值观相一致的话,治疗的效果将会提高。[17]67因此,尼古拉斯和斯克瓦兹指出:“在我们迈进21世纪的时候,整合模式看来就是家庭治疗的未来。”[18]476
这种整合出现了三个方向[19]476:(1)是折衷模式的出现,将两个或几个模式的理论和技巧结合到一起,如结构和策略模式的折衷、鲍文的系统模式与认知——行为模式的折衷等;(2)拿来主义,仍然强调原先持有的理论是治疗的基础与核心,但偶尔也会使用其它模式的理论与技术。例如,一个结构式的家庭治疗师,会借鉴了叙事家庭治疗的技术,强调语言的作用。而系统式家庭治疗中的循环提问技术、策略式家庭治疗中的矛盾处置法、萨提尔家庭治疗中的家庭雕塑技术也会运用于其它任何家庭治疗流派中;(3)新的整合模式的产生。这是将一些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有机”地综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的模式。如内部家庭系统模式,由斯克瓦兹、巴内特(Barrett)创立,他们将系统思考延伸至家庭范围之外,从最初人们的精神生活开始,到后来较广泛的文化问题,包含了很多后现代的元素,也保留了许多现代性的特征。再比如元架构家庭治疗模式,由布瑞林(Douslas Breunlin)、斯克瓦兹和麦克恩—卡瑞尔(Betty Mackune-Karrer)三位家庭治疗师共同创立,从人类经验的六个核心领域——组织、序列、发展、文化、性别和内在历程介入。[20]50-120这些领域沟通了结构(组织)、策略(序列),结合了个体内在心理(内在过程),并且处理了这些范畴中的新要素,如性别和多元文化的主题,超越了家庭治疗的任何个别流派。
整合使治疗师不需要把实践限定在某一个特定的流派之内,而可以从众多的流派中寻找有益的东西,从今天的眼光看,不论是折衷、拿来主义,还是新的整合模式的产生都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方向。因为缺乏统一的概念,所谓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只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有更多的干预方法可供选择而已。[20]195但是,不管怎么说,整合仍然显示出了未来家庭治疗发展的方向,在整合的过程中,治疗师的眼界越来越开阔,对家庭的洞察也开始不断扩大和深入,家庭治疗的知识以一种新的方法汇集在一起,这也给家庭治疗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家庭治疗过程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更加系统和综合的过程。人类是复杂的,其认知、情感和行为存在于一个受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复杂系统中,对个体心理行为的干预也就必然会需要多方面力量的综合。家庭治疗的发展会更多地采用生物—心理—社会倾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紧密。如,家庭治疗师花了很多年才完成了对心理动力学的否定,而特别地强调家庭关系的重要性,但现在,人们又重新认识到家庭关系背后的个体心理内在过程的重要性,所以,一些治疗师又开始将心理动力学重新带回家庭治疗的实践中。这也提醒家庭治疗师注意,在看到家庭中关系和结构的同时,也要看到家庭中的个人,呈现家庭关系的同时,也呈现出个人的内在自我,改变时既要评估整个家庭结构的改变,也评估家庭成员自我的改变。另外,今天的家庭治疗正在走向综合的个案管理的模式,在治疗的过程中,选择从个体、家庭、社会三个层面同时进行介入。1989年,米纽钦在《制度化的疯狂》(Institutionalizing Madness)一书中指出,很多家庭问题的出现是超越家庭的,家庭治疗如果只将注意力集中于核心家庭内,他的解决方法只能是短视且低效果的。例如,对于一个低收入的黑人家庭,不仅要战胜因障碍而产生的焦虑、沮丧和绝望,还必须克服障碍本身。
第三,家庭治疗越来越强调对特定家庭问题的研究。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治疗方法的临床治疗师都面临着一种新的需求,那就是有义务使治疗更加有效果。过去,人们过于强调了某一派别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似乎一种理论与技术可以运用于所有类型的家庭,但这显然脱离了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所面对的事实。比如,结构式家庭治疗对一些家庭形态,如有身心症症状的家庭、成员间界限不明的家庭等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对另一些家庭,如跨代家庭、再婚家庭,在运用结构式家庭治疗时效果就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家庭治疗的发展将会越来越重视对特定家庭问题的研究,侧重于强调对什么情境下的什么问题进行什么样的治疗才是最有效,并发展出针对这些特定家庭问题的家庭治疗理论与技术,如针对儿童期和青春期行为障碍、药物滥用、网络成瘾、进食障碍、夫妻性功能障碍、同性恋、抑郁症等问题发展出更具适应性的治疗方法与技术。
第四,家庭治疗将特别强调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看到家庭的发展与变化,并顺应这一发展与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比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期待也在提高,期待生活提供更多的快乐与满足;教育水平的提升,休闲时间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加注意内在的经验,更重视关系中的情绪质量;工业化的发展,家庭子女数的减少,人们对子女的关注程度加大,对子女的期待也在不断地提高;老年社会来临,人们活得越来越长,使得家庭在完成教养子女的责任后,还要承担繁重的赡养老人的任务;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人们观念的变化,使得婚外情、婚前同居、离婚等社会现象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以及工作的压力过大,实际的家庭关系反而越来越疏离等。家庭问题在不断地增加、而且不断地出现新的变化,家庭治疗师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了解社会与家庭的特点,体验到时代与文化的建构对家庭的影响,而发展出不同的应对策略,使治疗更加针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