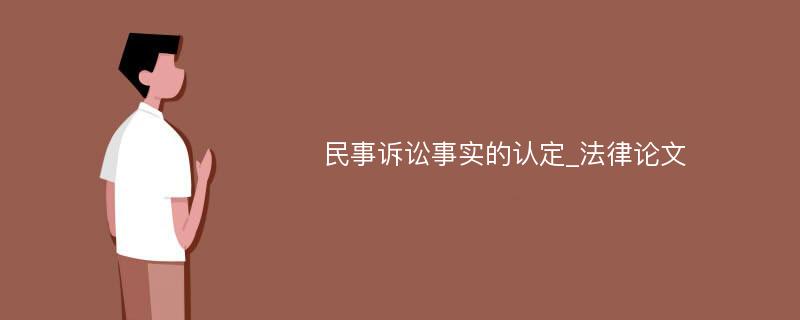
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事诉讼论文,案件论文,事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事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是裁判者作出正当的民事裁判,而正当的民事裁判又是以科学的事实认定、正确的法律适用以及事实与规范之间的符合逻辑的推理方法为表征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案件事实的认定是裁判者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第一个步骤,①是构成正当性裁判的前提和基础,是整个民事诉讼活动的核心和灵魂。失却了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必将会导致错误民事裁判的形成,故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实现民事诉讼目的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实现阿列克西法律论证外部证立的必由之路。②在实践中,多数民事案件之所以发生纠纷,根源于事实问题上的对立,“形象地,实践当中如果有一千个事实问题,那么真正的法律问题还不到事实问题的千分之一”。③可见,民事诉讼的中心在于事实认定,若此种认定流于恣意,则民事审判的正义根基将会荡然无存。
明晰了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中心地位后,如何正确认定该案件事实便成为了核心中的核心。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指民事诉讼中裁判者如何从听取当事人向法庭陈述的主张事实到最终作出据以裁判的案件事实的全过程。当下我国学界对于该过程的研究大量集中在如何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上,即将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作为一个理所当然或显而易见的问题。然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并非一望即知而是内含着非常复杂的逻辑推演。关于民事诉讼案件事实的认定全过程,笔者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当事人双方陈述的主张事实到裁判者需要确认的待证事实的过程,二是从裁判者需要确认的待证事实到最终作出据以裁判的案件事实的过程。④鉴于多数学者对第二阶段的研究已经非常翔实和深入,笔者在此仅将第一个阶段即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过程作为研究对象。
一、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概念及相关概念的引入
(一)待证事实的概念
待证事实,又称证明对象,是指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且需要通过证据予以证明的能够产生法律效果的具体事实。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中有些需要通过证据予以证明,而另一些则无需证明,前者为待证事实,后者则为无需证明的事实。因此,待证事实是相对于无需证明的事实而言的。在民事诉讼中,笔者认为,待证事实是指当事人的主张事实经要件事实的涵摄反映在程序上的具体事实——主要事实和推导出主要事实的间接事实。既包括积极要件事实反映在程序中的具体事实,也包括消极要件事实表现在程序中的具体事实。待证事实作为裁判者认定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过程中的认识对象,理论上应是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客观真相,但在具体案件中,不论对于经历者还是裁判者而言,在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中间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时间流动之河。真正作为裁判者认识对象的“事实”,已经不是当事人主张的生活意义上的具体纠纷事实,而是经过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格式化”之后的案件具体事实,是在实体法律规范要件事实涵摄下形成的当事人主张的案件相关事实的法律命题表现形式。
(二)待证事实相关概念
在对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概念论述中可以看出其与主张事实、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等相关概念密切相关,下文笔者将对这些相关概念予以厘清。
1.主张事实
主张事实,又称为叙述事实,是指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为支持自己在诉讼中的主张或反驳对方的主张而向法院叙述的一系列事实。主张事实一般情况下不是一个单数概念而是一个复数概念,其数量很多且繁杂无序。当事人在诉讼中陈述的事实是当事人对客观发生或存在的行为、现象或过程的一种陈述和判断。基于事实概念的主观性特征,当事人对民事纠纷的事实叙述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经过主观认知和剪辑过的事实,其可能为真,可能为假,也可能真假参半。⑤民事诉讼案件中当事人的主张事实有些是对纯粹生活事实或自然事实的陈述,有些是对渗透了一定程度法律规范的事实的叙述;因此,主张事实本身不等同于裁判者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但又与案件事实有着重要关系。一方面,主张事实划定了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范围和界限;另一方面,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主张事实需要经过民事实体法律规范要件事实的涵摄并经程序法上的主要事实转化为待证事实,再由裁判者通过证据对待证事实形成内心确信而最终认定案件事实。
主张事实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其指涉的却首先是案件的实际事件或状态,即案件的客观真相。它告诉我们:在某时某处有此事或彼事发生。主张事实的作出通常以感知为基础,判断者以自己的感知或者告知此事之人的感知为基础,当然,个别的感知也会以日常经验为据而连接成一些观念形象。因此,笔者此处的主张事实可以理解为卡尔·拉伦茨先生所称的“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⑥
2.要件事实
要件事实,又称为规范事实,是指民事实体法律规范中规定的可以引起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变更和终止的构成要件事实。要件事实在司法三段论推理中是连接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的关键词语。要件事实一词来源于日语,其在德语中的对应词语是tatbestand,包含了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和与构成要件相对应的具体事实的双重含义。⑦然而,根据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的论断,笔者认为,实践中要件事实更多是指作为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能够引起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变更和终止的事实。例如,《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的“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的“过错”是公民、法人承担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故是要件事实。在目前我国的民事法律条文中,要件事实既有具体的事实如产品存在缺陷,也有相对抽象的不确定概念如过错和具有价值评价性的一般条款如诚实信用。要件事实分为积极要件事实和消极要件事实。前者如《合同法》第196条借贷合同中规定的请求偿还借款应证明的两个要件事实:一是金钱的给付;二是返还的约定。后者如《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的不当得利的一个要件事实即一方获利没有合法根据。
需要指出的是,要件事实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使用的法律术语,在英美法系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争点事实,包括诉讼原因的构成事实和诉讼抗辩的构成事实两项内容。诉讼原因和抗辩构成事实都是当事人必须予以证明的事实,并且是有可能发生争议的事实,英美法学者将两者合一称作争点事实或结局事实。⑧
3.主要事实
主要事实是程序法上的一个术语,是指能够直接引起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变更或终止的具体事实。案件的主张事实在程序法上被分为主要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⑨有人认为,主要事实是要件事实在程序法上的反映或体现。笔者不予认同,而是认为主要事实是由民事实体法律规范中的要件事实引发而来的具体事实,其来源于要件事实但不同于要件事实。如前所述,要件事实既可以是具体事实又可以是抽象性的不确定概念或者是一般条款,而主要事实则必须是在诉讼中能够产生法效果的具体事实。例如,民法上的“过失”是一般侵权行为的要件事实,但却不是主要事实,主要事实是体现“过失”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如汽车肇事侵权中肇事司机出车前没有检修好汽车或者是行车过程中打瞌睡等具体事实。在民事诉讼法上,与主要事实相对应的是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间接事实又被称为凭证(证据),是指借助于经验法则或逻辑规则的作用在推定主要事实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事实。例如,“突然资金周转不灵”之事实是可以用于推定“金钱的授受”这一主要事实的间接事实。而辅助事实则是指用于明确证据能力或证据力(证明能力)的事实。例如,当存在某证人经常说谎、证人是当事人的朋友或亲戚之事实时,该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就必然会降低,而这些事实就是典型的辅助事实。⑩在民事诉讼理论上,主要事实和要件事实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可以说是经常被混淆。最初要件事实理论不仅包括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还包括构成该要件的主要事实,后来日本学界通说经历了要件事实所指从主要事实说到构成要件说的转变。诚如著名民事诉讼学者谷口安平先生所言,“所谓的‘事实’本身也存在几个层次,首先要使用一定的法律规范,则成为该规定主要部分的要件必须作为事实而存在,这样的事实成为‘要件事实’,常以如‘过失’等抽象的法律概念来表达。法官使用法律意味着必须判断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定的具体事实是否合乎这种要件,或者是否相当于要件事实。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实因为能够确定要件事实是否存在,所以被称为‘主要事实’或‘直接事实’。……直到不久之前,法学界对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并未加以区分,而是作为同样的概念使用。但随着研究的进展,学者们才意识到有必要将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一般而言,主要事实必须通过证据才能认定,也就是需要证明的事实。”(11)
综上,民事诉讼开始后,裁判者首先需要根据当事人双方所主张的事实确定本案的待证事实。唯如此,才会使第二阶段案件事实的全面认定成为可能。故笔者将裁判者从当事人的主张事实到待证事实的推演过程称为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前提。那么,裁判者是如何完成这一过程的呢?从主张事实和待证事实的概念可以看出,在民事诉讼中,裁判者从当事人的主张事实到待证事实的认知不是一蹴而就、直接得出的,主张事实需经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所内含的要件事实的涵摄形成主要事实并再经是否存有争议的筛选而最终形成待证事实。
二、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形成的第一阶段:主张事实经要件事实的涵摄形成主要事实
主张事实经要件事实的涵摄形成主要事实是实现从主张事实到待证事实的首要环节,也是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与裁判者的审理对象发生关联的初次对撞。
(一)当事人的主张事实和内含要件事实的民事实体法律规范的选择
要件事实是指民事实体法律规范规定的可以引起民事法律效果发生、变更和终止的构成要件事实。从要件事实的概念可以看出,要件事实指陈的实质是民事实体法律规范。从形式逻辑的结构角度而言,民事实体法律规范由主项、谓项和模态词构成:主项给出了谓项条件,是为法律构成要件;谓项描述主项所引起的效果,是为法律效果;模态词把主项和谓项联系起来,把法律效果归属于法律构成要件。可见,要件事实是民事实体法律规范的主项,两者之间是“毛”与“皮”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内含,后者是前者的载体。之于民事诉讼,当事人双方的主张事实因符合实体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要件事实)而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即内含要件事实的实体法律规范的确定是从当事人的主张事实推演出待证事实的前提条件。只有正确地选择该实体法律规范,才能明确获知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的内容,也才能准确归纳案件的待证事实。
大部分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活动是一个发现事实、寻找法律并将所寻找法律适用于所发现事实并最终作出裁判的过程,其中,发现事实和寻找法律是先后并行不相交叉的活动。笔者认为,这是对于具体民事裁判活动的一种误解,实际上,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规范的找寻在诉讼中是交互进行、须臾不可分离的。当事人尤其是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主张事实就是当事人(或在其律师帮助下)初步运用要件事实所指向的实体法律规范进行涵摄的结果,即在民事诉讼案件事实认定的最初阶段就涉及实体法律规范的选择与适用。具体而言,在民事诉讼实务中,发现事实和寻找法律的关系大致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先寻找法律后发现事实;二是发现事实和寻找法律交错进行;三是先发现事实后寻找法律。而适用情形最多的是前两种。
1.先寻找法律后发现事实时,当事人的主张事实和实体法律规范的选择
先寻找法律后发现事实的裁判方法是裁判者裁判活动的常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四个要件,其中之一就是当事人起诉时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12)这里的“理由”二字,既然和“事实”二字并列表述,就说明“理由”并非“事实”的同义词。那么,“理由”到底是指什么呢?笔者认为,理由应当是连接事实与诉讼请求的桥梁,这个桥梁只能是法律依据,也就是当事人之所以基于其所主张的事实可以提出特定的诉讼请求是因为该主张事实符合相关实体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根据上述分析,当事人在起诉之前,至少应当完成初步实体法律规范的寻找。当然,他所寻找到的法律不一定是非常具体的法条,但至少应当是一个比较具体的范围,以便使裁判者可以据此在案件审理之初很快确定应当适用的具体实体法律规范。通常情况下,当事人在诉状中只要表明他们所争议的事实属于何种法律关系即可,如请求归还借款表明是债权债务纠纷,请求离婚表明是婚姻关系纠纷。裁判者据此可以很快寻找到相关的实体法律规范,并进一步解析出其内含的要件事实,然后再从当事人的主张事实中进行要件事实的发现,如果逐一发现了要件事实,即可裁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否则将予驳回。由此可见,当事人的主张事实本身就蕴涵了内含有要件事实的实体法律规范。
为什么要求当事人在起诉时就必须初步完成实体法律规范的寻找,而不是仅仅提供诉讼请求和事实而将寻找法律的工作交于裁判者进行呢?这就需要从大陆法系的诉讼标的理论和英美法系的诉因制度谈起。在大陆法系,诉讼标的理论是民事诉讼中一个基础性理论。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并要求法院进行裁判的对象。既然诉讼标的首先是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对象,当事人将其提交到法院后才会成为法院的裁判对象,那么,当事人在起诉时当然应当先弄清楚其争议的对象是什么。如此一来,当事人在起诉之前就必须根据双方争议的事实进行实体法律规范的寻找,然后总结出其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为何,再提交法院请求裁判。因此,寻找法律的工作应当在诉讼开始前就完成,至少是初步完成;而在诉讼尚未开始之前,法官尚未介入诉讼,因此,寻找法律的工作又主要由当事人来完成。在实务中,诉讼开始后也可能会出现因诉讼标的不明确而导致其后的诉讼活动难以展开的情形,此时,裁判者一般通过行使阐明权来协助当事人明确诉讼标的。此种情形下,法官在诉讼开始时就参与到当事人寻找法律的活动中。我国司法实务中,由于各审判庭分工不同,故在立案之时立案庭的法官就要和当事人一起确定案由,并根据案由将案件分配到不同审判庭。当事人和立案庭的法官在确定案由时,也就初步确定了案件应当适用的实体法律规范(或实体法律规范群),完成了初步的法律寻找。在英美法系有着类似大陆法系的诉因制度。所谓诉因是指法律所承认的当事人可以请求启动诉讼程序的诉请。诉因一般是类型化的,具有制定法或者判例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具备法定的要件事实即构成法定的诉因,如违约、侵权、欺诈和诽谤。在诉因制度下,当事人起诉之前必须根据有关事实来寻找法律,只有在确定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具体法律规定的义务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某种诉因构成要件时,其起诉才会被法院受理。可见,此时寻找法律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由当事人来完成的。诉讼开始后,裁判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发现事实,具体表现为对当事人主张的诉因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
2.发现事实和寻找法律交错时当事人的主张事实和实体法律规范的选择
当事人通过寻找法律提出诉讼请求和主张事实后,其对于实体法律规范的选择可能与裁判者的认识不相一致,故诉讼开始后,可能会出现如下三种情形:
其一,裁判者认为当事人的主张事实因欠缺要件事实而驳回其诉讼请求。该情形非常容易理解,笔者在此无须赘言。
其二,裁判者认为当事人的主张事实不能支持其诉讼标的中内含的要件事实,但当事人可以主张其他诉讼标的,此时裁判者是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还是允许其更换诉讼标的呢?对此,笔者从民事纠纷的一次性解决角度考虑赞成后者。也就是说,裁判者根据当事人主张的诉讼标的提取要件事实时,发现该要件事实与其主张事实不相吻合,并且裁判者已经寻找到更符合当事人主张事实的其他实体法律规范,此时,法官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标的,重新选择民事实体法律规范。具体到我国,具体做法是,法官通过行使阐明权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即在同一个审理程序中直接变更案件的诉讼标的,起诉之时是此案裁判之时已经变成彼案了。在有些情况下,法官甚至可以不待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而直接依据自己所寻找到的实体法律规范进行裁判。例如,当事人主张的可能是合同履行请求权,而裁判者在发现存在合同无效情形后可能无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直接根据合同无效的法律规范判决合同无效。再如,当事人主张的是离婚请求,而裁判者在发现存在婚姻无效情形后,直接根据无效婚姻的法律规范判决婚姻无效,等等。
其三,请求权竞合时裁判者应告知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对应不同实体法律规范的选择。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尤其是原告基于其主张事实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对于本案待证事实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诉讼请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实体法律规范的选择和适用,而不同的实体法律规范又内含不同的要件事实,故在其涵摄下所形成的主要事实以及后面的待证事实也会大相径庭,该情形在当事人请求权竞合时尤为明显。例如,某甲购买的电视机爆炸,其既可以根据合同向电视机销售商提出违约之诉,也可以根据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损害向电视机销售商或生产商提出侵权之诉,两种不同的诉讼请求所对应的实体法律规范便分别是合同法中的违约责任法律规范和侵权法中的产品侵权法律规范,其要件事实亦不同,表现在诉讼活动中便是案件的主要事实不同,最终便表现为待证事实的不同。
在我国的民事司法实务中,实体法律规范的选择一般依赖于民事诉讼案件案由的确定。所谓民事案件案由,是指民事诉讼案件的名称,反映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是人民法院对诉讼争议所包含的法律关系进行的概括。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2007年10月29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38次会议讨论通过《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该《案由规定》在坚持以法律关系性质作为案由确定标准的同时,对少部分案由也依据请求权、形成权或者确认之诉、形成之诉的标准进行了确定,共规定了361种案由。笔者认为,该《案由规定》中建立了相对科学和完善的民事案件案由体系,这有利于当事人准确选择实体民事法律规范作为诉由,有利于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和审判中准确确定案件的要件事实、主要事实、待证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13)例如,《案由规定》对物权纠纷案由和合同纠纷案由做了界分,规定按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对于因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即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应适用债权纠纷部分的案由,直接指向具体的合同法律规范,如物权设立原因关系方面的担保合同纠纷指向担保合同法律规范,物权转移原因关系方面的买卖合同纠纷指向买卖合同法律规范;对于因物权成立、归属、效力、使用、收益等物权关系产生的纠纷则应适用物权纠纷部分的案由,直接指向相应的物权法律规范,如担保物权纠纷指向担保物权法律规范。在具体的民事案件诉讼流程中,民事案由一般由立案庭来确定,但其只是初步确定,目的是将民事案件进行初步的简单分类。接下来在审判庭中有可能会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事实来重新确定案由。其具体思维过程是,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去追寻其请求权的基础,并找出相应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以此来确定具体案由,以便进一步确定本案的主要事实、待证事实是什么,同时也为下一步举证责任的分配奠定基础。换言之,内含请求权基础的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是连接民事诉讼程序第一阶段待证事实和第二阶段举证责任分配的桥梁和纽带,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和内在的核心支柱。笔者通过对民事审判实务的相关调研认为,人民法院在根据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确定案件案由时应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属于主从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以主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但当事人仅以从法律关系起诉的,则以从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不属于主从关系的,则以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二是,请求权竞合时,人民法院应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三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导致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人民法院应当相应变更案件案由。
当然,民事诉讼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公众参与的“表演”,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民众获得一种关于民事实体法律规范构成要件的信息,进而去指导其日后诉讼中对于实体法律规范的正确选择,并最终达到既利于当事人自身合法实体权益的保护又利于民事诉讼程序的顺畅有效进行的目的。
(二)要件事实对主张事实涵摄后形成主要事实
主张事实是当事人双方对案件客观真相的一种主观认知和陈述,是当事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所做的一种描绘和讲述,内容庞大众多。在众多的主张事实中,有些与案件关系密切,能够为实体法律规范内含的要件事实所涵摄,成为能够影响案件法律效果的具体事实;有些则与案件关系相对较远,只起着一定证据材料作用的事实;有些则与案件没有或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关系。相对于主张事实而言,民事实体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事实则犹如一个可以过滤掉与案件无关事实的筛子,经过其涵摄或者筛选,当事人向法庭陈述的众多主张事实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纯化和沉淀,为其后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以及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法院的认证提供范围和方向。当然,要件事实在涵摄主张事实形成主要事实并进而确定待证事实的过程中,其自身的确定又反过来依赖于当事人对于案件客观真相的主张,要件事实确定的本质在于诉讼中实体法律规范的确定,而实体法律规范的适用又受制于当事人尤其是原告的诉讼请求和主张。
主张事实在经过要件事实涵摄后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事实,笔者称其为主要事实。如前所述,主要事实是指能够直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终止的具体事实。需要强调的是,主要事实是一系列具体而非抽象的事实,这也是主要事实与要件事实的本质区别。要件事实作为民事实体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事实,其既可能是具体事实如产品存在缺陷,也可能是抽象事实如过错。因此,程序法上的主要事实和实体法律规范内含的要件事实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分离性:多数情况下因要件事实表现为具体事实而体现两者的一致性;但当要件事实为抽象概念时主要事实则表现为其具体化事实。例如,“过错”这一抽象概念是一般侵权行为的要件事实,但却不是主要事实,主要事实是体现“过错”的各种具体事实表现形式:或者是汽车肇事侵权中的肇事司机出车前没有检修好汽车或者是行车过程中打瞌睡等。
在具体民事诉讼中,一般情况下,原告在起诉状中通过记载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而明确实体法律规范内含的要件事实及作为其具体化的主要事实,即起诉状原则上应当记载满足发生特定法律效果所需构成要件的具体事实。但在我国当下的民事案件中,若没有律师的帮助,要求原告在诉讼开始时就对案件纠纷做出正确的法律评价几乎不可能。因此,民事起诉状只要包含大体的诉讼主张就可以了,其进一步的细化有待于法庭审理时完成。此外,关于原告应当提出的主张事实的范围,因为民事诉讼是以原告请求的法律效果为指向的,故在事实主张的范围问题上,一般而言,原告至少应当提出足以支撑所请求法律效果的基本构成要件的事实主张;(14)否则,根本无法确定本案的主要事实,进而无法明确案件的待证事实并最终影响对整个案件事实的全面认定。
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民事诉讼中被告的答辩可能会导致案件主要事实发生实质性转向。因为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承认对事实认定具有拘束力,故当被告全部承认原告的主张事实却提出相应抗辩事实时,案件的主要事实也随之变化。例如,在返还借款诉讼中,被告承认确实曾从原告处借过钱,但却提出偿还抗辩,此时,本案之主要事实便从原告主张的借款事实转向为被告是否偿还的事实。可见,在原告提出诉讼主张到诉讼进行的过程中,案件的主要事实(包括紧随其后的待证事实)是随着原被告之间不断提出诉讼主张和诉讼请求而发生增补和调整的。
三、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形成的第二阶段:主要事实经是否存有争议的筛选形成待证事实
当事人的主张事实经要件事实涵摄后表现为一系列具体的主要事实。当事人对于这些主要事实有些存在争议有些不存在争议。其中,不存在争议的主要事实将会被裁判者直接认定为据以裁判的案件事实,而存在争议的主要事实则会成为本案的待证事实需要通过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从主要事实到待证事实的过程,笔者称之为待证事实对主要事实的筛选,而筛选的关键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争议。根据该标准,笔者将主要事实分为不需通过证据证明的事实(即法官可以直接认定的事实)和需要通过证据证明的待证事实两大类,这也是与我国学界将案件事实认定的方法分为通过证据认定事实的一般方法以及通过司法认知、自认、推定和法律文书预决等认定事实的特殊方法相契合的。
(一)当事人存有争议的主要事实和间接事实成为待证事实
待证事实是指当事人双方争议的且需要通过证据予以证明的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主要事实以及推导出主要事实的间接事实,待证事实通过相应证据证明后被裁判者认定为裁判事实。
为深化对待证事实的理解,笔者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与其相关的概念,即案件争议焦点(简称争点)。所谓民事诉讼中的案件争点,是指当事人双方在特定案件中争议的焦点,也是当事人诉请裁判者审理的对象。关于争点之范围,理论上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学说:狭义说主张争点仅指事实而不包括法律争点;广义说则认为事实、证据和法律等都可以成为争点。比如,在日本,有学者认为,争点就是对于法律适用有意义的事实主张不一致者。(15)有学者认为,与诉讼标的有关的主要事实、与主要事实有关的间接事实以及有助于和解的背景情况,均因争执而成为争点。(16)还有学者认为,有关法律问题、经验法则、主要事实或者间接事实的争执,都属于争点。(17)从各国民事诉讼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案件的法律适用即法的观点问题属于法官职权范畴,而争点更多是从事实层面考虑的,故笔者主张争点范围应采狭义说。关于案件争点的确定问题,日本井上治典教授采争点浮动说,主张争点为流动可变的,浮动于当事人的纷争交涉过程。(18)加藤新太郎法官则认为,当事人若能充分地把握事实关系,通过双方当事人间对主张的事实关系的对质,有争执的事实自然地能够浮现出来。(19)例如,原告主张请求的原因事实,被告虽承认但另外主张抗辩事实,原告承认被告的抗辩事实而主张再抗辩事实,被告承认而为再再抗辩事实,这时,争点虽随着原告及被告的主张、抗辩、再抗辩和再再抗辩而一再变动,但其仅是争点整理的中间阶段,最终再再抗辩的争执才是真正的争点。由此可见,争点概念是服务于争点整理程序的。为了进一步强化对于争点的认识,笔者认为,可以从通说对于争点整理的界定上来观察。所谓争点整理,是指为确定当事人是否主张与诉讼标的相关联的主要事实(要件事实)、与该主要事实相关联的间接事实为何、有助于和解之背景事实为何、与这些事实相关联之证据为何、区别对造当事人所争执的事实与不争执的事实,限定证据调查对象及范围的程序。(20)依此界定,争点整理程序中所确认的争点是指事实关系上的争点,既包括实体法上的事实(如主要事实、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争点,也包括程序法上的事实(如证据能力事实和举证责任事实)争点。
在介绍了民事诉讼案件争点概念之后,大家可能会问其与待证事实关系如何?笔者认为两者的范围不尽相同。案件争点既包括实体上的事实争点,也包括程序上的事实争点;而待证事实仅为实体上而非程序上的事实。(21)可见,案件争点的范围大于待证事实的范围,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种属关系。而在特定民事案件中,有关程序事实、证据事实的证明活动又与有关实体事实的证明活动之间是一种“枝干关系”:一方面,有关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活动是基础,是主干,正是该证明活动的存在和展开才可能引发有关程序法事实、证据事实的证明活动;另一方面,关于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活动总是在一定程序下借助一个个证据来完成的,因此,有关程序法事实、证据事实的证明活动又是为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活动服务的,其目的在于保障后者的正当性与真理性。(22)
(二)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被直接认定为案件事实
笔者认为,当事人不存在争议的事实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事人双方积极意义上的不存在争议,如当事人双方都主张的事实和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另一类是当事人双方消极意义上的不存在争议,如司法认知的事实或者一方提出的事实主张因有了司法机关、仲裁机关和公证机关在先的生效法律文书故另一方不得提出争议(尽管另一方可能内心仍有异议)。当事人不存在争议的事实不需要通过证据予以证明。各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大致都规定了免证事实的范围,我国也不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二)自然规律及定理;(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该条,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需举证证明的事实包括两类:一类是常理性的事实,另一类是有权机关(如司法机关、仲裁机关和公证机关)认定的事实。笔者认为,第二类事实免于证明的原因非常清楚,而第一类事实是否应当免于证明及在何种情形下才能免于证明在学界和实务界有不同声音。
各国大多将根据社会常理能推出的事实归于免证事实的范围。笔者认为,社会常理有三种:一是形式的、永远不变的常理即逻辑,二是大部分已经内化到法律之中的规范性常理,三是事实性常理。该三种常理在判决中的地位各不相同。逻辑是永远不变的,任何时候认定案件事实都必须遵守逻辑规则;规范性常理应视情况而定;事实性常理则更应当谨慎。关于规范性常理,因为其绝大多数已经内化到法律之中,为了维护法律权威,常态下裁判者没有权力不顾法律规范而依规范性常理断案:只有在法律规范空缺时才可依规范性常理断案;裁判者在对法律进行解释时引用学理,但是变种对常理的引用必须在法律整体的意义之内;当然,也不排除极端情况下裁判者依常理推翻法律的可能,如美国的帕尔默案。事实性常理是指事实之间高概率关联的常理。例如,按常理,人们去银行会办理某种金融业务,刹车失灵会产生车祸。此类所谓事实性常理具有概然性不是必然的,故将其作为前提推断法律事实时应当特别慎重,只有得到整个证据链支撑的“常理”才有辅助性意义,才能作为裁判者采信证据与否的理由之一。质言之,对于上述三类常理,第一类法律逻辑是裁判者在推理论证中必须遵守的不得违背的常理,如传统逻辑三段论规则;第二类规范性常理是实体法上的具体法律规范,其适用问题实质上是民事司法中的法律解释问题;第三类事实性常理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所言的社会常理或日常生活经验。至于事实性常理如何在案件事实认定中适用,法官在南京彭宇案中给出了一个反面的例子,(23)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深思的问题,即事实性常理在何时才可以被适用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仅仅需要法官认为是“常理”即可还是需要具备其他一些条件?对此,笔者认为,事实性常理的事实应当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常理必须是真正的常理,而“真正”的判断必须得基于共识,必须有经验性的高概率支撑,没有共识为依据、没有高概率支撑的“断言”不能作为常理。二是事实性常理必须让位于事实本身,即依据常理,出现了A,B出现的概率很高,但事实上B并没有出现,我们就必放弃常理。三是常理必须在证据链条中才能起作用,即常理必须有其他证据支持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之一,决不能仅凭常理断案。(24)
综上,在民事诉讼中,从当事人向裁判者陈述主张事实到裁判者确定待证事实是案件事实认定内在思维进程的第一阶段,也是前提阶段。该过程明确了裁判者进行案件事实认定最重要也是最困难最复杂的审理对象,也使第二阶段的诉讼证明活动得以有的放矢地进行。
注释:
①德国著名法理学家伯恩·魏德士在《法理学》一书中提出:“法律适用可以分为四个步骤:认定事实,寻找相关的(一个或若干)法律规范,以整个法律秩序为准进行涵摄,宣布法律后果。”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297页。
②罗伯特·阿列克西(Robert Alexy)是德国著名法哲学家,其在《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一文中提出了关于法律论证的内部证立和外部证立的理论。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页。荷兰学者伊芙琳·T·菲特丽丝指出,依照阿列克西的程序性法律论证理论,“整体上证立的合理性依赖于前提的合理性。最后判断之合理性的裁定因而依赖于外部证立。”参见[荷]伊芙琳·T·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张其山、焦宝乾、夏贞鹏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9页。
③[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④本文的“案件事实”是指裁判事实,具体内容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有一套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专门术语,前者如要件事实、主要事实、间接事实、辅助事实,后者如争点事实(facts in issue)、争点相关事实(relevant facts)和次争点事实(collateral facts)。然而,基于争点事实与要件事实、争点相关事实与间接事实以及次争点事实与辅助事实的同质性,笔者在下文的内在思维路径的阐述中仅适用大陆法系的这一套术语。
⑤Robert P.Burns,a Theory of the Tria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p.221.
⑥当然,笔者论文中的“案件事实”和拉伦茨先生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案件事实”的适用语境是不同的。
⑦章恒筑:《要件事实原论——一种民事诉讼思维的展开》,四川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8页。
⑧沈达明:《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1~73页。
⑨如果说英美法系国家的争点事实(facts in issue)对应大陆法系国家的要件事实的话,则英美法系国家的争点相关事实(facts relevant to issue)和次争点相关事实(collateral,subordinate facts)则分别对应于大陆法系国家的间接事实和辅助事实。参见沈达明:《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4页;又见史优:《事实认定问题之探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⑩[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11)[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12)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13)当然,科学完善的民事案由体系的设立,也有利于提高民事案件司法统计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利于对受理案件进行分类管理,从而更好地为审判规范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法院司法决策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
(14)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15)[日]加藤新太郎:《爭點整理手續構想》,判例ㄆイ厶ズ,八二三號,1993年10月,第10頁。
(16)[日]伊藤真:《民事诉讼におけゐ爭點整理手續》,载《法曹时报》1991,43(9),4。
(17)[日]山本和彦:《爭點整理手續について》,载《民商法杂志》1994,110(45),106。
(18)[日]井上治典:《弁論の條件—和解兼弁論の位置と評價》,民事手續論,有斐閣,平成五年,第103~104頁。
(19)[日]加藤新太郎:《爭點整理手續構想》,判例ㄆイ厶ズ,八二三號,1993年10月,第9頁。
(20)邱联恭:《民事诉讼法第一审程序修正草案之走向(四)》,载《军法专刊》(第40卷),1994年4月;邱联恭:《争点整理方法绪论》,载《争点整理方法论》,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24页。
(21)江伟教授主编的《民事诉讼法》一书在界定“对事实的认定”概念时,主张“对事实的认定是指审判人员在法庭评议阶段,综合本案全部证据的证明力,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法上的事实存在与否作出判断”。由此可以推出,该书主张案件待证事实是民事实体法上而非程序法上的事实。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22)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2页。
(23)详情请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决书(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号。
(24)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国民法学者梁慧星教授在《怎样进行法律思维》的演讲中提到,与日常生活经验相联系的不需证明的事实有两类:一类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医生将手术钳遗留在患者体内后被取出能够推出医生或医院方是有过错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另一类是“难以举证的事实”,这类事实很难甚至不可能通过证据加以证明,最典型的就是精神损害的事实,精神损害之是否存在及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当事人很难举证甚至不可能举证,属于难以举证的事实,应当由审理案件的法官直接根据社会生活经验予以认定。梁老师并以台湾地区台北地方法院1999年的一个消费者权益诉讼案例进行了例证。案件事实如下:原告到一个高级餐厅用餐,餐后上甜点每人一杯冰淇淋,原告在吃冰淇淋的时候咬到玻璃碎片,把口腔内侧的粘膜划破流血,于是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被告餐厅赔偿50万元新台币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这个案件中有两个事实需要认定,一个是人身伤害的存在和严重程度,一个是精神损害的存在和严重程度。本案中,法官严格按照证据规则认定了人身伤害的存在及其严重程度,但精神损害的存在和严重程度则难以通过证据予以证明。最终,法官的判决书如此认定,“甲主张因此事件,连续数日惶惶不安,担心是否已吞入玻璃碎片,是否造成穿肠破肚、内脏损坏,是否须开刀取出,亦符合一般经验法则”。判决被告支付原告10万元新台币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具体参见梁慧星教授2008年12月9日在河南法官学院关于《怎样进行法律思维》的演讲稿。笔者认为梁教授的这一观点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具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标签:法律论文; 诉讼标的论文; 诉讼请求论文; 民事法律事实论文; 民事案由论文; 民事诉讼主体论文; 民事诉讼当事人论文; 法制论文; 实体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