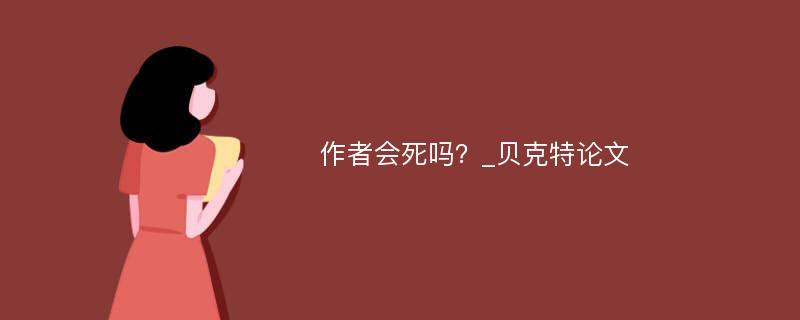
作者能不能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与文本的关系,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原点性问题。在当代西方文艺学和阐释学理论中,从20世纪初俄国的形式主义兴起,经过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传统的作者与文本关系的定位被彻底颠覆。新批评的“意图谬误”,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福柯的“什么是作者”,一条线索下来,疏离和否定作者,隔绝和阻断作者与文本的关系,视文本为纯粹的、悬浮的词与物,成为主流观点和基本主张。在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笔者总是感到疑惑,文本是书写者的创造物,书写者与文本的关系可以被人为地消抹、被阐释者蔑视为无吗?笔者认为,无论怎样辩解,无论多深奥的学说,作者或者说文本的书写者都是一种“存在”,是一种“有”,在文本生成及后来的阐释中“在场”,无论你喜不喜欢,其客观影响和作用永远都是“在”的。 一、文本是书写者的文本 文本是书写者的创造物,无论从什么基点出发,都不能否认这个客观事实。一个确定的文本,有一个确定的书写者,是这一个书写者生产了这个文本,从而使文本以“有”和“存在”的方式呈现于我们面前。没有书写者的创造,文本就不会存在。这个刻在羊皮纸上的存在,是可以触摸、翻阅、留存的,是一个不能否认的物质存在。我们以这个存在为基点,展开全部理解和阐释。从历史传承的意义上说,文本为书写者所有,这是既定的事实。《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个人创造物,这是无可争议的,不允许他人分割。而且正是因为它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哈姆雷特》才有确定的经典意义。除非有切实的考古证据,否则,把它说成是别人的作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从现代版权的意义上说,文本的作者决然不能被忽视,社会必须承认作者对文本的所有权,说作者死了,文本归属于他人,有可能构成一种违法行为。对此有人诘难:一个流传古老的民族史诗和神话文本,它的作者是谁?比如著名的希腊神话故事,就没有确定的作者。这就证明,对一部作品而言,作者的有与无,并没有多少意义。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希腊神话,作为历史流传的精神文本,是民族集体的创作。无数的个体说唱者,在诸多时代的大事件中,创造出自己的故事,经过历史和民族的检验,不断地淘洗和加工,符合民族物质与精神诉求的因素被整合放大,背离民族利益与传统的因素被淘汰和修正,从而才有了今天能够读到的经典文本。文本的作者是谁?就是古希腊时代各民族集体(或者说是民族个体,或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多民族的个体)。时代和民族创造了希腊神话,通过神话表达民族意志,锻造民族精神。后人阐释文本,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认识和欣赏文本自身,而是要以文本为桥梁和导引,认识和体察那个时代和民族的演进与成长。这就是作者存在的意义,也是难以消解和去除作者的根据。 以传统的理论看,书写者之所以书写,是为了表达,是要表达他自己的感受和思想,表达某个或某几个社会群体的感受和思想。这些感受和思想,通过文字构建为文本,使主观的精神现象物化为客观的存在,书写者的思想和情感定格于此,以文本的状态留传于后人。这是一个贯注与播撒的过程。书写者的精神诉求都倾注在文本里。文本是作者的对象化,是物化的作者,是作者实现自己、留存自己的方式和手段。他以此文本与后人对话,无穷地再现自己和延展自己的思想。作者可以物质性地死亡,而精神却在,文本扎根于作者的精神之中,或者说文本因为精神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笔者更赞成意大利哲学家贝蒂的观点:文本或者说作品,是作者“精神的客观化物”。对此,曾有中国学者给予精准阐释。潘德荣先生指出:何为“精神的客观化物”?“诸如文字、密码数字、艺术的象征、语言与音乐表象、面部表情、行为举止方式等,均为富有意义的形式,亦即精神显(现)自身、从而成为能得以被辨认的客观化物。”当然,这种客观化物与其自身所负载的意义内容是不同的,它们之间的区分在于:“客观化物是属于‘物理层次’的,它所携带的意义内容属于精神性的。所谓精神现象的认识,就是通过客观化物而把握精神、亦即客观化物所承载的意义内容。”(潘德荣,第374页)这些论述证明,在贝蒂的立场上,无论其意义如何,文本首先是作者的创造物,也就是作者精神的客观化产物。富有思想和精神力量的作者,向我们提供极具个性化的精神产物,而这个精神产物是别人无法复制、再造和替代的。正是在这样个性化的产物之中,作者与文本融合炼化,作者赋予文本以思想和精神,文本承载它们而化身为物质的作者。否认作者就否认了文本,文本的存在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和价值。 按照福柯的说法,书写已经不是表达,以他的期望和判断说,“当AI写作作已经使自身从表达的范围中解放了出来”,不再指涉书写者的思想感情与价值观念,它只是一种词语的游戏和操练,符号的无声积累和繁衍,词语的书写游戏,既无能指也无所指,更与书写者无关。在书写中,“关键不是表现和抬高书写的行为,也不是使一个主体固定在语言之中,而是创造一个可供书写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福科,第288页)我们不评论这个判断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仅就福柯的表述看,有三点值得讨论。其一,如果说书写只是一种词语游戏,而不是书写者的意图表达,那么游戏本身是不是一种表达?如果是,那么是谁在表达?福柯自己的话已经确证,游戏者就是书写的主体,是游戏者这个主体在游戏。据此,我们清楚地看见,书写者或者说游戏者是“在”的,所谓“创造一个可供书写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其中明确出现书写主体的概念就是明证。其二,如果说不表达主体思想,书写是纯粹的词语游戏,那么这个游戏出的产品,其符号的选择与排列、词语的结构与解构,是不是游戏者的自主书写?这个行为是不是自觉的有意义的行为?他这样“游戏”,而不是那样“游戏”,这其中渗透的是作者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毫无歧义地表达着书写者的存在,显示了这一个词语“游戏”绝对不同于另外一个词语“游戏”,隐含和彰显书写者的意志,抹是抹不掉的,更无法彻底消解。其三,“创造一个可供书写主体永远消失的空间”,本身也要留下书写者作为主体的痕迹。且不说“书写主体”的精确表达,退一步讲,如果说书写主体真的要消失,那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在词语的“游戏”中逐步“消失”,“消失”的方式及路径也因主体不同而差异明显。一个文本中的主体消失与另一个文本中的主体消失方式截然不同,否则,文本将因模仿、抄袭、类同而失去存在价值。就是对作者到底有与没有的问题,福柯也是有不同提法的。在《什么是作者?》一文里,在用作者功能替代作者,并指出作者功能的四个表现后,福柯又出人意料地举出一个新的概念——“话语创始人”。他说:“此外,在十九世纪里,欧洲曾出现过另一类更与众不同的、既不应与‘伟大的’文学作者、宗教本文的作者相混同,也不应与科学的创立者们相混淆的作者。我们将武断地把那些属于后一类的人称之为‘话语的创始人’。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他们不只是他们自己著作的作者。他们已经创造了某种别的东西:其他本文构成的可能性与规则。比如,在这点上他们就与实际上不过是他自己本文的作者的小说家迥然不同。弗洛伊德不仅是《释梦》或《玩笑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也不只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作者。他们都奠定了话语无穷无尽的可能性。”(福科,第299页)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总体上说,福柯是主张消灭作者的,但在这里,无论是什么文本的制造者,福柯都要称之为“作者”。这个事实本身说明,文本的制造者只能是作者,除了作者,没有其他的称谓。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马克思,不仅是其重要著作的作者,而且又被称为“话语的创始人”,那么,这个“话语的创始人”是不是话语的作者?福柯认为:“当我称马克思或弗洛伊德是话语的创始人时,我指的是他们不但使某些类同成为可能,而且还(同样重要)使某些差别成为可能。他们远不止为他们的话语,而且为某种属于他们所创立的东西创造了可能性。”(同上,第300页)这赋予“话语创始人”以很重要的功能负载,同时也说明,这些话语创始人,也就是自己著作的书写者,不仅在其本人的著作中有深刻永久的影响,而且在以此为基础的话语扩张和繁衍中继续发挥方向性的影响。作者不可能虚无。在“话语创始人”的作用下,作者永远不死。 二、书写者的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当代文化和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我的存在与消失,主体的肯定与否定,“我是谁”“你又是谁”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自我和主体的式微,而实际上,正是自我的感觉暗淡和由此而生起的焦虑,才有了人们奋力寻找自我、叩问自我、突出地强化自我的思想和理论行为。没有人愿意放弃自我。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一些哲学流派企图消灭和拆解主体,注定难以实现其目的。那么书写者呢?书写者如何面对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关于书写者与文本的关系,有三种情况需要讨论:作品就是自传或半自传;作家的经历深刻影响写作,文本是作家经历的折射;与作家本人经历毫无关系,号称完全虚构的文本。前两种情况不需要讨论,因为作家就是要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在作品中,作家论证自己,也要读者印证自己。此类文本,在文学史上占有极大比重。核心是第三种情况,看起来文本与作者的经历没有任何关系,作者本人也要宣称所谓“零度写作”,绝不投射书写者本人的任何思想情感和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文本似乎好一些,特别是以虚构为天职的小说类文本,但即便是这类文本,也可以从中找到作者无处不在的幽灵。更难考证的,也许是哲学和历史文本,比如福柯的《什么是作者?》,福柯本人的影响,他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追求,他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难道毫无症候和征兆,福柯可以不在文本之中,人们可以不计较是福柯在说吗? 先说经典中的作者。福柯是以贝克特的话为起点开始这个话题讨论的——“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就看贝克特如何面对文本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或者说他如何认识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他如何在文本中验证自己。贝克特是法国荒诞派戏剧大师。他的戏剧理念及实践,以实验的、抽象的、荒诞不经的面目呈现于世人,简洁、抽象、梦呓般的风格给人以震撼。那里面似乎完全没有作者的印记,似乎给阐释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这种理解有些浮浅。深入地考察和体味,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文本的书写者,贝克特从来没有离开自己的作品,他的记忆和思考、他的情感和语言,以至他真诚皈依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原点,幽灵般地潜没于字里行间。直接一点的事实是,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对他自己童年、青年、爱情、家人和身体体验的指涉。最突出的是,贝克特的儿时记忆在其文本中随处可见,以鲜明的自我的方式存在和表白着。贝克特曾经强调和赞赏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但是,他无法否认,大量的意象与细节,把他自己的人生经历熔铸于文本之中,使文本成为经历的认证:“一个男人和他的儿子手拉手走过一座座山”“有一棵落叶松每年总是比其他的树提早一周变绿”“采石的铿锵声响彻他家上方的山间”。对此,贝克特如何对待?他只能由衷地认可:“它们都是挥之不去的。”(Knowlson,p.20)它们必然出现在文本中,成为文本深处最活跃的幽灵。间接的证明则是语言的使用。文本中经常出现的都柏林民间语言,那种缓慢且不时停顿的节奏,让我们瞬即认证书写者的爱尔兰身份。“在《瓦特》中,贝克特这里首次实现了他的独特风格:一种富于保留性和不确定性的句法,否认又承认其他可能的情况,逗号的非凡运用”。(Cronin,p.337)这种语言风格在《终局》中体现得更加典型:“克劳夫:(目光呆滞,语调平直)终局,这是终局,将要终局,可能将要终局。(略停)谷粒加到谷粒上,一颗接着一颗,有一天,突然地,成了一堆,一小堆,讨厌的一堆。(略停)他没法再惩罚我。”(《贝克特选集》第4卷,第6-7页)有人指出,这种重复、停顿和不确定性的语言表达,不仅是都柏林人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是贝克特母亲的言语方式。作为没落贵族的后裔,贝克特的母亲以虔敬新教闻名,她对儿子耳提面授,引导他走向理解圣经、理解新教和理解语言的道路。而贝克特又把这些一般的文化要素凝结成为独特的自我形象驻留于文本之中,成为与读者交往的主体。 关于作者的在场与缺席,贝克特曾经迷惑过:“如果我可以,我要去哪里?如果我可以,我会去当谁?如果我有声音,我要说什么?谁说的这个,说是我说的?”“我不在他的脑子里。我不在他的旧躯体里。然而我还是在那里,因为他而在那里,和他在一起。一切都乱了。”“本来有他就够了,本来我该不在场。但不是这样的,他想要我在那里,有外形,有世界,和他一样,管他什么样,我是一切,就像他是虚无。”“然后故事开始,一切开始,我又站得远远的。我远远地站在我的故事之外,等它开始,等它结束,这声音不可能是我的。”(Beckett,p.91-92) 贝克特以诗性的语言,表达他和漂浮于其作品之上的“他”的关系。在这里,贝克特以“我”和“他”的关系,展现出一种精神上的分裂:“我”是生活中的我,“他”是作者的我;“他”不停地胁迫“我”说话,代替“我”说话;“他”指责“我”词不达意(he would like it to be my fault that words fail him);“我”要和“他”分离。然而,可以分离吗?能够分离吗?恰恰是因为“我”和“他”无法分离,“我”才如此强调分离。因为“我”就是“他”,“他”就是“我”,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我的死亡就是他的死亡,所以我要站得远远的,与作品保持距离,以消解记忆的疼痛。贝克特远离作者身份的姿态,恰恰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和他作品之间的关联如何深刻又难以勾销。有材料证明,作为荒诞派大师,贝克特却十分在意“作者意图”。他的电视剧《游走四方形》(Quad)中有四个人像疯子一样从广场的四个角落出发匆忙穿越广场,看上去小心翼翼,又好像刻意避开广场的中心。詹姆斯·诺尔森请教贝克特:广场中心那个危险地带是否是道教中的“安静的中心”?贝克特否定说:“不是,至少,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他想强调的是“人类‘存在’中不断出现的烦躁情绪”。(海恩斯、诺尔森,第13页)令人烦恼的“作者意图”,没有那么容易被消解,这是作者和读者都必须寻找和证明的身份认同。 再说福柯本人。福柯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一个根本特点,是他的著作总是鲜明地与他自己生动的人生实践紧密联系,更确切地说,一些重要著作就是他浸入生活,用深入观察以至切身体验凝聚起来的,是他实践自我、实现自我的纪录。他撰写《疯癫与文明》的生活动因是,他应朋友的邀请,到圣安娜医院协助工作,也到巴黎的监狱接触犯人,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观察。福柯说:“我感到自己同病人非常接近,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段经历促成他后来用“历史批判或结构分析的方式来写精神病学史。”(参见刘北成,第36页)据记载,1952年,福柯同朋友在瑞士“目睹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场面”,这个场面是当地精神病院的病人参与当地的狂欢节的活动。福柯自己描述:“狂欢节这天,疯人——显然不是那些病情严重的疯人——经过梳妆打扮后进入小镇。他们是在狂欢,而居民们则站在远处十分紧张地观看。归根到底,这是极其可怕的。因为只有这一天他们可以全体出去,而这一天他们必须实实在在装扮疯人。”刘北成先生指出:“在福柯后来的著作中,尤其是《疯癫与文明》对愚人节的描绘中,可以看到这一记忆的痕迹。”(同上,第35-36页)《规训与惩罚》写于1972年至1974年。在这时期前后,从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后,女权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监狱改革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反精神病学运动,等等,各种政治性抗议活动风起云涌。福柯是这些运动特别是监狱改革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同时他也展开了其政治领域里的“极限体验”:1971年,福柯领衔创立了“监狱情况协会”,收集和公布监狱情况;同年的5月1日,福柯到监狱门口组织集会,声援犯人运动,遭到警察击打并被拘审;1972年1月18日,福柯和萨特、德勒兹夫妇,带领支持者在卡斯蒂格利昂大街聚集,并到司法部前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被防暴警察驱赶到街上,“福柯站在最前列,满脸涨红,青筋暴露,竭尽全力抗拒”;“1972年12月,又一名阿尔及利亚人死在警察局。有几十个人举行哀悼和抗议的游行。警察驱散人群,逮捕示威者……福柯、莫里亚克和热奈为抢回被捕者而同警察搏斗。他们也遭到殴打”;1973年3月31日的数千人的游行中,福柯和莫里亚克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同上,第186-188页)对此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深为吃惊和不满,但是福柯并没有停止他的学术研究和创造,“尽管社会政治斗争占用了不少时间,但这对于福柯的思想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这是福柯对尼采所说的‘破坏愉悦’的体验,是福柯本人所说的一种‘极限体验’”。(同上,第195页)这些行动告诉我们,福柯此时正在投入书写的《规训与惩罚》是怎样写成的,他在这个书写中投入怎样的体验。作为书写者,他要在文本中得到身份认同,用文本表达自己,用书写证明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满怀敬畏地说:“于是,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一个福柯——那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毁灭又自我发现的令人迷惑的形象,一个‘退入他的作品的表现形式之中的’形象”,福柯“把自己的各种最疯狂的冲动注入自己的著作,力图理解之,同时阐释并表达之”,“毋宁说,他的oeuvre(作品)似乎是他的书和他的生活的共同体现”。(米勒,第212、530、525页)这就是身份认同,是一个负责任的书写者的应为之举,是以自己的实践和思想、行动和书写的共进行为,去寻找和实现的身份认同。对此,我们可以说“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吗?不是福柯在说话,就没有这些文本;文本里没有了福柯,文本就失去意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福柯就是文本,文本就是福柯。文本不死,福柯不死。 三、作者为什么要死 作者死了,文本不是作者的文本,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似乎是荒谬的话题,怎样成为了哲学和阐释学的重大主题?这是值得深思的。很明显,这也是一种话语霸权。作者明明在,作者的思想明明也在,从形式主义到巴特再到福柯,为什么要作者去死呢? 形式主义的目的是单纯的。它要摆脱以至决绝19世纪以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反叛,也是一种进步。在持续多年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影响下,文学背离了文学,用社会学、历史学以及作家的生平和轶事考证文本,文学失去了独立和自由,文学批评成为社会历史主张的附庸。文学应该回到文学本身,这个主张单纯却极富魅力。罗兰·巴特的诉求就更为深刻和复杂。“作者之死”只是一种隐喻,是一个问题的提起。在“作者之死”的背后,是解构主义的反主体、反中心、反理性的主张,是解构主义在文艺理论和阐释学领域的强暴扩张。福柯的《什么是作者?》更为深刻和系统。福柯以“人之死”为起点,论证“作者之死”的必然性,分析了作者的话语功能和话语实践条件,把“作者死了”的华丽口号变成严整的理论。抛开这些深奥的哲学思辨和政治社会诉求,从阐释学的意义上看,这些口号和学说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判断,问题的核心是关于文本解读的话语权及其标准。从阐释的权力来说,作者死了,读者成为最高阐释者和文本的创造者。在文本意义的多维空间中,任何阐释都可以生成,批评家和普通读者一样,随意衍生自己的结论。从阐释的标准来说,文本没有了作者,意义不再有源头,阐释就不再受单一意义的支配,各种想象和体验相互对话竞争,任何阐释都是正确的。试想,当人们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地阐释文本的时候,文本的作者跳出来说他的本意是什么,阐释还会继续下去吗?更何况作者本人未必就是文本的最后评判者,他的书写常常背离自己的本来意图,甚至就没有意图。“当我们认为作者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时,我们的阅读和批评实践却使他或她进入了一个将意义和意味限制到单一的无歧义状态的语言的泥沼。因此,福柯总结说:‘作者是一个由于我们害怕意义增生而构想出来的意识形态形象。’我们希望文本有一个统一的作者,因为统一的作者会以文本存在具体意义的观念来取悦我们。”(本尼特、罗伊尔,第24页)巴特说得更加直接:“我们现在知道文本不是一行释放单一的‘神学’意义(从作者—上帝那里来的‘信息’)的词,而是一个多维的空间,各种各样的写作在其中交织着、冲突着,没有一种是起源性的。文本是来自文化的无数中心的引语构成的交织物……作者一旦被驱逐,解释一个文本的主张就变得毫无益处。给文本一个作者,是给文本横加限制,是给文本以最后的所指,是封闭了写作。”(同上,第22-23页)正是这种阐释思想和作者理论,使得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论中的“强制阐释”成为潮流。阐释成为各种理论任意发挥和竞争的试验场。“强制阐释是指,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的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张江)强制阐释之所以风行,其主要动力就在从形式主义开始的作者理论。 2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几经曲折和发展,三种类型的理论转换,其线索大致清楚。从时间顺序上说,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三个历史段落起伏有致,后者否定前者,中心替代中心。传统的社会学批评衰落以后,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虽然独到新颖,但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以作者为中心;以雅格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兰塞姆倡导的“新批评”,以及罗兰·巴特等人引领的“结构主义”,则彻底转向以文本为中心;英伽登的“阅读现象学”,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姚斯、伊瑟尔创立的接受美学,成为以读者为中心的骨干代表。应该说,这个纵向分类是有道理的。一个时期当中,哪种理论更新潮、更具影响力,中心自然形成。但深入考察下去,我们能够发现,在这些表象背后,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在起作用,这个力量以各种策略和方法表现自己,推动20世纪的文论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形成了新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理论。以理论为中心,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走向和态势。其基本表现是,理论是全部活动的最高标准和目的。所有阐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理论自身。理论标准是刚性标准,理论修正事实,事实服从理论。理论的自我生产,是理论无限膨胀的唯一方式。理论的自我检验,是理论自称真理的标准。在文艺学领地,作者之后、文本之后、读者之后,理论成为中心,一切文本阐释都以理论为中心,理论成为文本阐释的唯一根据。但是,文本不是为理论而生的,文本只为自己发出或隐藏声韵,理论要达到目的,只有强制阐释文本,让理论的作者成为文本的作者。我们可以梳理一下,西方当代诸多思潮和主义,有几个能够脱离这一窠臼?这恰恰是要作者去死的核心动因。詹姆逊在阐释海德格尔有关艺术作品起源的一段话时曾这样说过:“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后期总带有点神秘主义的色彩,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解释是很出格的,但既然海德格尔已经死了,我们也就有进行各种解释的权利。”(詹姆逊,第183页)从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些活着的人却要作者去死的隐秘动机?作者真死假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阐释的话语权和标准在谁手里。消灭了历史,消灭了作者,强制阐释就有了借口和自由,理论才有了暴力和强权。 当然,放眼历史纵深,“作者之死”不过是“上帝之死”的延伸。“上帝死了”是尼采的著名口号,提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要表达他彻底否定人类的理性、传统形而上学体系的决心和意志。从某种意义上讲,“上帝死了”和“重估一切价值”,开启了当代西方哲学以至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取向。特别是以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更是滥觞于此。上帝死了,任人重新开启对一切事物的一切认识;“作者死了”,任人重新开启对一切文本的一切解读。认识和解读的根据是什么?不是事物和文本本身,也不是理性和规则,而是生命的冲动和权力意志,是“陶铸的意志”,是“同化的意志”。据此,才有今天我们碰撞的所有需要辨析与解释的诸多理念和价值,包括本文正在讨论的“作者能不能死”。这是一个内容广阔的论题,本文无力承担,相信理论界会有更加深入和切实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