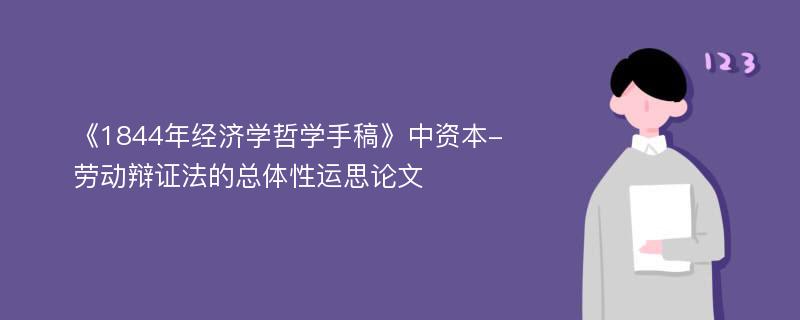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资本-劳动辩证法的总体性运思
张海燕
(内蒙古大学 哲学学院,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一节对“资本-劳动”内在矛盾的揭示,绝不是对《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的简单摹写,而是对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结构性剖析,典范性地展示了以“具体的总体”为核心的辩证法的总体性运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历史辩证法的现实主题是以“资本-劳动”的矛盾运动这个“具体的总体”为核心问题对现代社会进行总体性批判和重构,在思维方法上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经验实证性范式的尝试性融合,开启了走出德国观念论辩证法、创建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科学抽象法”之思想征程。而在走出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过程中,费尔巴哈所开创的感性原则和具有经验论传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颇有启示。在此意义上,只有将“资本-劳动”辩证法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辩证法的“具体的总体”,才能深度把握其辩证法的肇始性思想史地位和方法论价值。
[关键词]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劳动辩证法;具体的总体
《资本论》的研究和阐释者不会忽略马克思在其中对资本的“普照光”作用所做的具体的总体性论述,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也体现了一种“具体的总体”的运思。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藩篱中画地为牢,尤其是过于纠结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到底是谁在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中起到更大作用的还原论式解读,致使《手稿》的“具体的总体”——资本-劳动辩证法明珠蒙尘,本文试图以“资本-劳动”的内在矛盾为核心阐述《手稿》辩证法的革命性变革,并在此基础上揭示《手稿》与《资本论》辩证法的差异一体。
一、《手稿》对“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观念论辩证法双向批判的总体性运思
(一)黑格尔辩证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
“且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这句话提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在结构,提示了黑格尔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深层关系,是具有提纲挈领式作用的关键句,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研究者要么对此忽略,要么仅仅将其看作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的一个评语。而回到《手稿》,我们就会发现这既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内在关联的思想史评判,也是《手稿》时期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总体性运思结构之提示语。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卢卡奇发现了黑格尔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思想关联,并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对二者关系展开了一个马克思式的解读。德国哲学具有浓厚的观念论传统,这使得德国哲学家很少直面考察社会生活。根据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考察,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唯一对英法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认真考察的是黑格尔,黑格尔对斯密等英法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较为熟悉。在黑格尔之前,劳动在哲学中一直处于较为低等的地位,正是从英法政治经济学那里,黑格尔意识到劳动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性,进而认识到了劳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劳动的重要性在《精神现象学》中才得以凸显,并得到了本体论意义上的阐述。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结构的考察更是直接彰显了政治经济学对其法哲学的影响,劳动也被称为市民社会中实现需要的环节。黑格尔不仅认同对劳动和满足劳动的需要体系,甚至仅仅从市民社会的阶段上来看,黑格尔也基本认同政治经济学家的原子式社会结构分析。
1.2 观察指标 在观察期间的每年12月,抽取患者透析前空腹静脉血,检测血红蛋白(HGB)、血浆白蛋白(Alb)及甲状旁腺素(PTH);按照Daugirdas尿素单室模型公式计算尿素清除指数(KT/V)。比较导管组与内瘘组透析患者的HGB、Alb、KT/V及PTH差异;比较观察期间两组患者HGB、Alb、KT/V及PTH的变化情况。
黑格尔是当时唯一对国民经济学有过深入研究的德国哲学家,他的辩证法包含着对国民经济学的思辨考察,并在时代立场上与国民经济学具有内在一致性。但是,黑格尔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纯粹德国观念论的传统中是很难被辨识出来的。在《手稿》之前的马克思,对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无从了解。《莱茵报》被查封对马克思而言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只有离家出走接触到差异性的思想,才能真正促使思想者对自己曾长期浸润其中的思辨哲学进行前提性反思。漂泊在巴黎的马克思开始大量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历史学著作,并真正接触到德国之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现实,正是这第一次亲密接触,才使得马克思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
(二)马克思批判黑格尔观念论辩证法的“他山之石”
依据劳动又反对劳动,依据人而又反对人,充分体现了国民经济学的伪人道主义和伪科学性,但是国民经济学中犬儒主义因素的增加决不能归结为国民经济学自身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国民经济学家之所以越来越敌视劳动,究其根源而言,是由于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其根源在于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现实中人的劳动的抽象程度越来越高。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发展史的考察,马克思凭借其历史性思维,逐渐认识到国民经济学的内在矛盾绝不仅仅是理论形式的,而是历史的必然。资本同一化的现实运动,在理论上表现为国民经济学的演变过程。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以斯密为代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作为主体本质的劳动逐步显现出来。换言之,财富的同一的主体本质逐渐从各种差异性的外在物中被解蔽出来,财富的主体本质演化的历史过程,就是各种各样的特殊劳动逐渐通约化,被同一理解为一般劳动的过程,是劳动范畴逐步抽象化、纯粹化的过程。“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2、77页。 这种国民经济学的演化过程,是与历史的发展同步、并以历史的存在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的演化过程不过是历史的过程的重演。因此,对国民经济学的扬弃,就不能再采用伦理批判的立场,而是要走入其问题的深处,探讨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演变的历史必然性就成为马克思终其一生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赞赏主要是后者基于感性原则的感性自然观和感性人本学。费尔巴哈是以宗教批判者的身份出场的,在宗教批判的意义上将黑格尔思辨哲学确认为理性神学,并将与黑格尔的绝对理性相对立的感性确立为新哲学的原则。当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6页。 ,他主要指的就是费尔巴哈是第一个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进行了前提性批判的人。采取了一种机智的“颠倒法”,费尔巴哈扛着感性的大旗反叛了黑格尔,成为反对理念形而上学的先锋。与黑格尔对思维的极端推崇相反,费尔巴哈站到了感性自然的立场上,并将人也理解为感性存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挑战迫使人们关注到一直被德国观念论所忽视的感性存在,启示后来者超越德国观念论来思考人的存在。感性原则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环节,最终经过马克思的批判性改造开花结果。费尔巴哈确立了与德国观念论异质的感性原则,这一点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他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是从总体上来说,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性地克服。对于1844年写作《手稿》的马克思来说,不仅斯特劳斯和鲍威尔没有真正解决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就连最激进的费尔巴哈也落入俗套。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所借助的第二个因素是具有经验论传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由于黑格尔的最终目的是希望真理与特定的社会或政治的秩序达到现实的统一,他最终让现实服从于理论。“在黑格尔最终为现实设定的形式中,理论,即真理的适当的储藏地,似乎很欢迎过去的事实并渴望他们服从理性。”[注] 〔美〕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思辨最终吞没了经济学的路径,使经济学成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环节,也就阻断了黑格尔走出思辨牢笼的可能性。德国观念论的传统曾经在马克思身上长期驻留,直到在巴黎生活并阅读了大量历史学,尤其是以英国为主的政治经济学的资料之后,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和所思考的问题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观念论辩证法才成为马克思的批判重点。英国有着深厚的经验论传统,就算是最思辨的哲学也是以经验论见长,更何况是与现实生活最为贴近,致力于提高国民财富的政治经济学。“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页。 这段话表明以经验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手稿》初步确立了经济领域对思想领域的决定性作用。英国经验论与德国观念论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思想探索之路上产生了影响,形成了很大的张力,至此马克思与黑格尔对何谓现实的认识分歧已经暴露。从本质上来说,黑格尔最终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其思辨的历史辩证法的材料或因素;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才是社会现实的最重要反映。正如卢卡奇所说,“黑格尔和马克思是在现实本身上分道扬镳的。黑格尔不能深入理解历史的真正的动力。”[注]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8页。 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现状和政治经济学的考察,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确认辩证法的现实基础不是自我意识在哲学家思想中的历史演绎,而是只有在以现实的经济运动为基础的社会整体的历史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辩证法的现实基础及其价值所在。
(三)马克思对哲学思辨和经验实证的初步创造性融合
不仅黑格尔的观念论辩证法的批判,而且与之有着内在关联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同样采取了“非批判的实证性”。所谓非批判的实证性,主要是指政治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和劳动的分离看作一切社会的前提,把私有财产当作一种永恒的自然状态,一个无需申辩的前提,直到今天这种研究倾向依然存在。埃伦·伍德指出,有些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者将资本主义视作自然之物,“假定它从历史起点就已经存在,并通过描述阻碍其自然演进的障碍物如何以不同方式被移出这一现象‘解释’它的发展进程。”[注] 〔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域下的长篇综述》,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和共同缺陷的发现,马克思开启了一种融贯二者并致力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辩证法。在此视域下,哲学思考和政治经济学思考既存在区别,又处于一种相互审视、相互批判的位置上。一方面,只有对最能反映人的现实存在的政治经济学进行考察,才能揭示出人的存在的现实、历史维度,因此真正的哲学必须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之中。另一方面,经济学作为考察人的现实生活的一门科学,又需要哲学尤其是历史辩证法提供前提性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之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的考察始终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的、历史的批判。至此,以人为焦点,经济学和哲学走到一起,经济学将成为哲学经济学,哲学将成为经济学哲学,马克思在此所开创的哲学与经济学联盟的道路和方法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学科交叉、整体思考的方法论在马克思著作中一直延续,雷蒙·阿隆颇有见地地指出:“《资本论》是一部经济学著作,又是一门资本主义社会学,也是一部在史前时期一直受到自身冲突麻烦的人类的哲学史”。[注]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考察从来不仅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部延续,而是与哲学尤其是其历史辩证法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辩证法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种总体性方向和方法,构成了其批判资本主义的总体性维度,而具体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则最终使得马克思掌握了社会自身的逻辑,并因而真正超越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成为一种融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一体的社会哲学。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哲学是一种既源于现实又超出现实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他那里,辩证法绝非仅仅是纯粹观念体系的逻辑展开,而是必须要与具体的经验科学研究相结合,凝炼成一种以历史性的批判为基本特征的科学方法论。
夜晚的布莱德湖在灯光和烛光的点缀下,显得十分绚丽多彩。欣赏完湖景,不妨品尝一下颇具当地特色的布莱德奶油蛋糕。薄薄的糖霜下是层层酥皮,酥皮之下是甜而不腻的奶油和滑爽的芝士蛋糕,蛋糕的口感一层比一层香醇,是很受欢迎的传统点心。
噢,妈的。等我知道身子疼痛的时候,那已经是三天以后了。但,我依然清晰地记着,小六子手中的那根榆木镐柄在即将砸向我头顶的时候,他的面庞仍然是笑容可掬。
二、私有财产批判:《手稿》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维
想要走出对《手稿》时期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研究的“德国古典哲学化”藩篱,需要迈出的重要一步就是要确认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手稿》时期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建构的重要意义。私有财产问题与劳动异化在历史上是相伴而生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手稿》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正是私有财产制度阻碍了自由自觉的劳动,因此,致力于扬弃劳动异化的《手稿》辩证法考察离不开对私有财产的考察。正是由于对二者内在关系的历史性探讨,才使得马克思走出德国观念论的视野,着力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经验传统与德国观念论尤其是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融合。而对二者的融合同时开创了一种双向批判的方法论,也成为马克思以劳动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初次出场。
(一)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原初设定的批判
资本同一性的历史演变过程是在两个方向上同时展开的:一方面体现在工商业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的斗争;另一方面则是将劳动力商品化。正是在工商业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的斗争中,不动产取得了对动产的胜利,成为现代的、合法的嫡子;同时地产转化为一般资本。至此,“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7页。 一般资本的出现,是资本同一化过程的标志,一般资本的功能及其对社会和人的生存方式所产生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资本同一化进程深浅的标志。当所有资本都成为一般资本,资本的同一化进程才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彰显。当然表征一般资本的特殊资本依然会变化,比如过去是工商资本,后来演化为金融资本,国家资本等等。但是资本的一般性或者说资本的同一化趋势确实是在加强。
随着私有财产形态的历史演变,作为私有财产之理论反映的政治经济学也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再到斯密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更替。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人们的财富观还处于较为感性的阶段,把财富主要等同于金银等贵金属。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照得眼花缭乱,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35、45、46、127页。 重农学派的兴起标志着人们对财富的认识逐渐超越了对贵金属的感性拜物教阶段,但重农主义的缺陷在于它仅仅在某一种劳动形式即农业劳动中发现了财富的主体本质。而此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则充分认识到了财富的一般本质。劳动主体性的凸显,是国民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但是国民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敌视劳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并没有仅仅采取伦理批判的态度,从《手稿》第二部分起,历史性批判就逐渐取代纯粹伦理的批判,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后来的国民经济学之所以表现得敌视劳动,并不是因为其理论水平的问题,而是资本逻辑扩张的必然。国民经济学家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国民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社会的不幸”,“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每当我们谈到国民经济学家,我们一般总是指经验的生意人,国民经济学家是他们的科学的自白和存在。)”[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2、77页。
对国民经济学所预设的“资本、土地和劳动”的三要素说及其相应的财富三形态的质疑和反思,从历史的角度对国民经济学的方法论展开了批判。马克思给自己的任务则是揭露资本和劳动分离的历史根源,揭示私有财产充满矛盾的本质及其发展结局。并由此明确提出了与国民经济学无批判、非历史的实证方法相反的“实证的批判”或批判性的实证的方法。这种批判不是简单的外在伦理批判,而是审慎的、内在的反思。从方法论上来说,这就是“批判的实证主义”。
在其受贿四年间,对连卓钊暗度陈仓、跨境接送赌客的行为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且,他任内的广东两次查赌风暴,均从连卓钊的通风报信中获得官员赌博信息并实施查处。
从主体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政治经济学可以说是德国思维的特征,这一点显示了德国古典哲学在马克思身上所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显示了他与英法政治经济学家的不同。黑格尔最终将主体性囚禁在精神劳动之中,但马克思却从主体哲学的角度揭示了财富的主体本质就在于它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考察政治经济学思想发展史时,马克思明确指出,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将劳动凸显为财富的主体本质,将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因此,发现财富的主体本质对象化思维是一种与政治经济学仅仅将劳动视作财富生产要素的物化思维不同的新思维。因此,马克思说把私有财产问题转换为异化劳动问题,本身就是探索私有财产问题的新思维。
与国民经济学的事实假定不同,马克思把国民经济学当作前提的东西放入历史当中,采取了历史分析的方法,并以此来破除国民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迷误。从历史来考察,就会发现,不论是社会发展的现实历史还是国民经济学自己的学术史,都说明了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绝不是一种“自然状态”。通过萨伊,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指出“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35、45、46、127页。 而资本在现代社会的主导地位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资本家不过是土地所有者的翻身了的“昔日的奴隶”;而土地所有者则不过是资本家眼中不学无术的“昔日的主人”。这通过不同阶段分别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家的对骂得到了反映。这样,通过历史性的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原罪就被暴露出来。
(二)土地资本化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更替
当国民经济学家将资本、劳动和土地的分离当作其理论的前提,将私有财产当作一种亘古如一的自然状态时,他们自然不可能探索私有财产的起源及历史演变问题。但是对于马克思,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资本并非自然产物,而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探索资本的起源、演变问题是必须面对的理论任务。
因为刘必芒是个瞎子,而且平时不关心娱乐圈,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领班,这个饭馆的领班和服务员都是当地人,但因为自己的家里房子都被外来务工人员租满,所以同住的时间一长,耳听目染,深得要领。老板一吩咐要找明星的大照片贴墙,都兴致昂然,这比抄菜谱有意思多了。
土地资本化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资本逻辑扩张的过程,但资本逻辑的扩张却不会止步于土地的资本化,资本的统治在覆盖土地的同时将劳动者作为商品纳入了其私有财产体系之中。在这种新的类型的私有财产制度中,“死的物质”越来越表现出与人的对立和对人的统治。资本这种死物质对人的统治首先、也最集中地体现在工人阶级身上。这个阶级通过劳动不仅生产出了财物,还生产出了自己的统治者——资本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统治的普遍性又强化了异化劳动,导致了无产阶级的出现。这个阶级最为极端地体现了“非人”的存在状态,成为整个社会的“非存在”链条上的一环。
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观察社会现实的重要维度,但是它却只提供了现存社会的静态横切面,长期浸润于黑格尔历史思维的马克思,在《手稿》时期初次考察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其致命的弊端,那就是其“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马克思洞察到从理论上看来和谐相处的三一式社会结构不过是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虚构,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财富的三个要素及其所有者的利益却时刻处于冲突和斗争之中,这甚至可以从政治经济学家自己的著作中找到鲜明的证据。“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7、37、50页。 首先,土地所有者与社会其他阶级处于对立之中。在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土地所有者所获取的地租绝不是自然产物,而是从社会榨取而来。“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7、37、50页。 二者收入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争利状态之中。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接着从国民经济学中引申出租地农场主与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也相敌对的结论。而且地产与地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竞争和斗争。其次,土地所有者之间也存在竞争,而在竞争的过程中,无孔不入的资本家自然见缝插针,时刻准备分一杯羹。
随着我国公务员需求量增加,编制又越来越少,因此,出现了合同工、派遣工等多种的用工形式,其薪酬差异十分巨大,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都对同工同酬做了相关表述,但在司法实践中,对政府部门编制内外用工同工同酬的诉求,却极少得到法律的支持,其理由均为在编员工适用《公务员法》,而编制外员工关系受《劳动法》调整,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显然违背了《宪法》的精神,违背了人人平等的最基本现代价值理念。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四十年的今天,在我国即将进入发达国家的今天,这种由于身份导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这是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是极不相称的。
走出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严密体系,《手稿》时期的马克思主要借助了两个“他山之石”:一是费尔巴哈所开创的感性原则,另一个则是具有经验论传统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土地作为最初形态的资本,在历史中是不可能保持原初形态的,按照历史趋势,必然被资本化。随着工商业的出现,土地所有者再也不能坐享其成,而要忙碌于交易,“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35、45、46、127页。 地产作为商品进入了竞争领域,而一旦进入竞争,地产就必须和受竞争规律支配的其他商品一样,最终被资本化。这样昔日的奴隶就战胜了其懒惰的主人,资本就取代地产成为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而随着土地的资本化,“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35、45、46、127页。 随着经济上资本取代土地成为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政治上的资本主义革命也逐渐确立了现代政治制度。
三、资本-劳动辩证法:《手稿》辩证法的“具体的总体”
“辩证地研究客观现实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具体总体的观点。这意味着每个现象都可以被看成整体的一个环节。一个社会现象在什么程度上作为特定总体的一个环节来研究,也就是说,它在什么程度上发挥着使其首先成为一个历史事实的双重作用,该现象就在这一程度上是一个历史事实。”[注] 〔捷〕科西科:《具体的辩证法》,刘玉贤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 辩证法是具体的辩证逻辑,历史辩证法的具体形态与现实历史的演进历程是密切相关的,资本-劳动辩证法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具体的总体”。正是在考察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资本以其历史性的运动取得了对地产的胜利,并形成了它的结构性统治,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成为一种结构性的对立。因此,现代社会的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内在矛盾,其最高端的表现形式就是资本-劳动的内在矛盾。对于马克思而言,辩证法绝非一种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力求从内容本身出发的具体的辩证逻辑。《手稿》时期的马克思转向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就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提出的“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的继续探索。这种接续关系同时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对辩证法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域,那就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考察,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作出理论论证,并探寻实际的、可能的解放道路,而这个基本问题域决定了资本-劳动辩证法成为《手稿》的“具体的总体”。
(一)作为财富本质的劳动
政治经济学的巨大贡献在于看到了财富的主体性质,将财富的本质归结为劳动,这一点得到了马克思的肯定,但是政治经济学家在将劳动指认为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同时,也对劳动做出了越来越抽象化的理解,只看到了作为财富本质的劳动,而没有看到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在这一点上,考察过政治经济学的黑格尔对劳动肯定性作用作出了哲学上的肯定,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的黑格尔”也同国民经济学一样,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虽然黑格尔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分工所导致的机械化、抽象化劳动进行了批判,但是他最终把这种状态看作是在市民社会领域内无法解决的,只能在绝对精神之实现的国家层面才能实现,而劳动最终也只是自我意识提升的一个环节,且低于“陶冶”。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家眼中财富生产的主体,也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劳动不仅仅具有财富生产的性质,而且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之彰显,异化劳动之扬弃只能在现实历史运动中进行,不能逃到纯思辨的领域。
近年来,炎症在NAFLD疾病进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其机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依赖于NLRPs炎症小体激活的细胞焦亡也是这些年的研究热点,其引起的炎症应答也被认为是疾病进展的推动者。各类NLRPs影响NAFLD疾病进展的不同的分子机制还需我们进一步的探究。
资本的实质在于它是抽象劳动的积累,相比于之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它的进步性首先在于抽象劳动对特殊劳动的胜利。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只有特殊的劳动尤其是农业、土地是最重要的,特殊劳动的主导地位使得地产具有个体性,所以中世纪有句俗语叫“没有无领主的土地”。从“没有无领主的土地”到“金钱没有主人”,不仅仅是俗语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了历史进步。资本的实质是人的主体力量的异化形式——抽象劳动的积累,现代资本的伟大作用在于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性是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的。
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的劳动问题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问题直接关联起来,将亚当·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称赞斯密劳动价值论相对于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历史进步。但是与斯密将劳动仅仅视作财富的增值手段不同,马克思更注重从人的主体维度和社会关系维度来分析劳动,并将关注点放到了资本逻辑下的现实劳动的异化形态之上,异化劳动是一种哲学的表达,但是它的内容却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的经验观察,那就是资本雇佣制度所造成的劳动的单向度,即劳动下降为因不合理的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简单机械劳动、谋生劳动。这种状态下的劳动,非但没有显示人的创造性,反而造成了抽象资本的统治,人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反而成为奴役人的王者。
把雇佣劳动和一般的普遍劳动混为一谈,将雇佣劳动设想为所有社会都普遍存在的一般劳动形式,是国民经济学的非历史性的症结所在。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首先就必须通过历史辩证法的思维来戳穿国民经济学的这个非历史性的前提性设定。从方法论上来讲,主要就是历史性反思,也就是强调辩证法的过程性和历史性。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制度视作自然天堂并将之永恒化,而马克思却将之视作“原罪”。这种原罪就突出表现在国民经济学把私有制作为前提,把资本与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当作一种亘古如一的自然状态。“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7、37、50页。 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不过是将他们想要的结论置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事物假定为事实。这反映了以斯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的根本性错误。这种设定把一种原本由劳动产生,需要从历史发展中来解释的社会现象当作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就像《圣经》设定了人的原罪一样,完全是一种未经考察的独断。马克思不无讥讽地说,“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注]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35、45、46、127页。
(二)作为私有财产完成形态的资本
如果说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那么资本则是现代社会财富的最典型形态。资本与其他财富形态相比较,其特质就是资本已经成为一种非人格的统治力量,将社会的所有财富包括地产和作为商品的劳动都尽收彀中。
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对财富三要素的分析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阶级结构模式的分析,是马克思考察国民经济学的出发点。从斯密开始,在代表工商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国民经济学家的眼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就构成了财富生产的三个要素和三种主要的财富形态,因这三种要素分别属于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其对应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就构成了国民的三大阶级。这种社会结构被国民经济学家设想为自然的、永恒的,甚至天堂般的。
资本同一化进程另外一个关键环节是将劳动力商品化。原始资本的形成过程,同时就是逼迫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过程,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商品化使得(雇工、工人)成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存活的商品,而且是最低贱的商品。劳动力的商品化是资本同一性推进的关键环节,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赞同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但是不同在于,马克思从未将劳动力仅仅看作财富积累的因素。劳动者在国民经济学那里仅仅是劳动者,而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者首先是人,劳动首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的价值因素在马克思这里从未消失。
私有财产绝不是一个定在物,而是一种历史形态的社会关系的表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再仅仅是财富或者是一般劳动的积累,而是“异化劳动的积累”。换句话说,资本只能在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条件下才能存在,资本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劳动积累。这种特殊形态的劳动与其私有制一样,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并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初状态”或者说国民经济学家所幻想的“永恒状态”。这种考察就使得马克思超越了一般国民经济学家的视野,对他们当作理所当然接受的东西进行了前提性批判。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采取了一个不同于黑格尔的态度,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正如他对于黑格尔“否定性辩证法”的态度一样,都是致力于对它的批判和改造。马克思所作的工作不同于一般实证经济学,而是具有真正历史性思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四种施工方法管片均整体向下位移,离区间隧道较近的底部管片变形略大于其他部位,台阶法施工管片最大变形为11.2 mm,CRD法施工为6.8 mm,临时仰拱台阶法和CD法施工结果较接近,分别为8.8 mm和9.1 mm。对临时仰拱台阶法施工盾构管片沿环向变形(见图11和图12)分析,结果表明,管片最大变形在地铁区间拱顶上方,而不是两隧道中心截面,且管片在地铁双区间截面中心±15 m范围内变形均较大,量值在8 mm~9.5 mm之间,因此为减小变形,可着重对这30 m段管片局部加固。
(三)资本与异化劳动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基本矛盾的确认
“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注] ②③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7、72、13-14、67页。 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已有的考察加以改造,将斯密的地租、资本和劳动三部分转化成两个因素:资本和劳动。这里最重要的是人被当作机器,资本和劳动两端对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转折。这说明,在《手稿》时期,马克思已经将社会的主要矛盾集中到了资本和劳动之间。马克思虽然借用的都是国民经济学的资料,但是却剖析了国民经济学内在的矛盾,得出了与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截然不同的结论。
私有财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在历史中通过三种形态表现出来。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资本和劳动之间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的关系;当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资本家和劳动者原来在反抗封建领主时期所形成的统一战线开始瓦解,二者之间的冲突开始呈现出来。“它们互相排斥;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②但资本家和工人的身份对立又不是永恒的,而是处于随时变换的可能性之中,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
国土资源信息是国民经济信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土地信息资源,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公益性、战略性和基础性作用。
在马克思之前已经有很多思想家比如社会主义者普鲁东就曾对劳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马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没有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仅仅看作是外在对立的,而是把它们视作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强调资本与劳动既具有历史的共生性,又具有现实的冲突性,是现代社会有机体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劳动异化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而以资本为主导的私有制导致和加剧了劳动异化,资本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两个内在因素。更加重要的是,二者的矛盾被看作是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动力,而不是偶然的、无关紧要的经济现象。“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③这个结论的得出是《手稿》第一部分的重要成果,这意味着异化劳动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不可能靠纯粹的伦理批判或者是普鲁东式的工资平等得以消除。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与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已经显示出了某种不同,意味着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的结构之中,以历史的思维来看待国民经济学所存在的问题。
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致,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④这段话表明马克思已经将资本-劳动的内在矛盾确认为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分别代表着私有财产的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犹如一枚银币的两面,虽然显示的图案有稍许差别,但是却共生共存。当马克思充分意识到资本-劳动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之后,他对私有财产与劳动关系的理解也就与普鲁东有了本质的区别。与“把工资的平等看作是社会革命的目标”的普鲁东不同,在考察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发现无论社会经济处于衰退、增长还是完满的状态中,工人所能得到的都是持续不变的贫困。工人阶级的贫困何以从现代劳动本身产生出来?这个问题的提出已经表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政治目标在于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论证无产阶级作为革命主题的合法性,并明确提出“有产和无产的对立只有被理解为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解决。
从此,马克思将自己理论的关注点锁定在资本-劳动辩证法之上,并终其一生都以资本-劳动辩证法作为其研究的主题。黑格尔辩证法是关于知识的辩证推演,而马克思本人的辩证法却要走出知识,走向行动。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精神通过外化、复归而确证为绝对体系的助手,而即将成为批判和改造社会的利器。这一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被明确表述为“以往的哲学都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句墓志铭式的格言,既是马克思思想的最恰当表述,也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最恰当表达。理论不再仅仅在纯思辨的领域转圈,而成为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通过政治性的社会运动来解决人类在政治解放之后的社会解放问题。
小 结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资本-劳动辩证法并非是对《精神现象学》的“主奴辩证法”的简单摹写,而是对整个现代社会基本矛盾的揭示。正如吉登斯所说,“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扎根于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中,这一社会的主要结构性特征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关系。”[注] 〔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资本-劳动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而这种由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导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是一般性的贫富对立,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结构性特征,这种结构性特征剖析就是《手稿》辩证法的“具体的总体”,也是此后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关注的问题。《手稿》辩证法思想运思的这种总体性思维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新起点。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不是借助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的“主谓颠倒”,而是以“资本-劳动”内在矛盾这个“具体的总体”为核心问题的总体性重构,是融贯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学科的总体性辩证思维的再造,立足于此才能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辩证法思想以真正重要的思想史位置和方法论价值。
总之,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为了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目标,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纪检监察派驻制度改革也要顺应时代要求,实现组织理论、组织形式、组织人员、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从而真正发挥“派”的权威,“驻”的优势。
The Total Thinking of Capital -Labor Dialectics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ZHANG Haiyan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70, China)
Abstract :The section on “alienation labor and private property” in the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by Karl Marx reveal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labor” and it is by no means a direct imitation of the “master-slave-dialectics” in theSpiritual Phenomenology , but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ich typically demonstrates the total thinking of the dialectic with the “concrete totality” as its core. In the manuscripts, the realistic theme of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s is the overall criticism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ety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labor” as the core issue. Meanwhil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peculative tradition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with the empirical positivist paradigm of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y provides an ideological basis for “scientific abstract method” in creating materialist historical dialectics beyond the dialectic of German conceptualism.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beyond Hegel's speculative dialectics, Marx was enlightened by the sensibility principle initiated by Feuerbach and the positivist research method of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y with empiricism tradition, and therefore, it may be argued that only by regarding the dialectics of “capital-labor” as the “concrete totality” of the dialectics in the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an we grasp deeply its initiative historical status and methodological value.
Keywords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 capital-labor dialectics; concrete totality
[中图分类号] A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9)03-0089-09
[收稿日期] 2018-10-16
[基金项目] 内蒙古社科规划项目“‘互联网+’内蒙古意识形态建设研究”(2015B036),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理论传承关系研究”(15CZX004)。
(责任编辑 胡敏中 责任校对 胡敏中 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