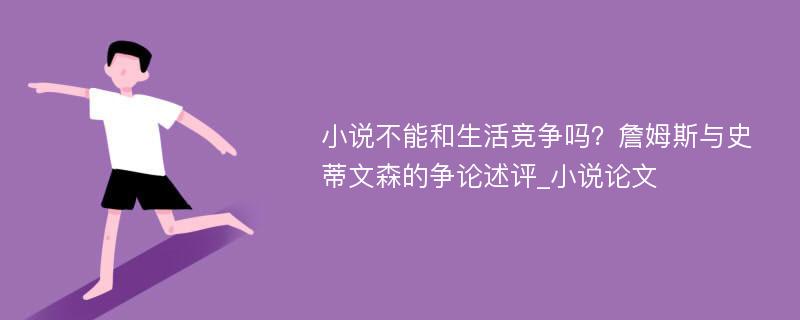
小说不能与生活竞争吗?——评詹姆斯和史蒂文生的一场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詹姆斯论文,竞争论文,小说论文,史蒂文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英国小说理论史而言, 1884 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于该年9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小说艺术》(The Art of Fiction)的文章;3个月之后,史蒂文生(Robert LouisStevenson ,1850 —1904 )发表《谦恭的争辩》(A HumbleRemonstrance)一文,以此向詹姆斯提出挑战。关于《小说艺术》的介绍频频见于我国的几家刊物,可是《谦恭的争辩》却很少有人提及。针对这一不足,本文拟对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进行追溯,并对它的意义以及詹史二人的小说观试作分析。
一、争论的焦点
詹史之争的焦点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小说是否能与生活竞争?换言之,小说能否以艺术的真实取胜于生活的真实?詹姆斯在《小说艺术》中明确提出:“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的确能够与生活竞争。”〔1 〕詹氏发表这一观点事出有因:当时名声显赫的小说家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 )经常在其作品中以旁白或插入语的形式坦言自己小说的虚构性,甚至再三提醒读者书中所述的事件并没有真正发生过。詹姆斯对这样的自白大为不满,称之为“对小说家神圣职责的背叛”:“恕我直言,这种对神圣职责的背叛是一种可怕的罪行……它意味着小说家在寻求真实方面不如历史学家执着,可是这样一来就完全褫夺了小说家的立足之地。”〔2〕詹姆斯认为, 小说的真实性丝毫不亚于史书,其原因是“小说的题材同样储存于文献和记录之中”〔3〕。詹姆斯还认为,小说家应该比史学家获得更多的荣誉, 因为他们“在搜集证据方面克服了更多的困难”〔4〕。 正是鉴于这些原因,詹姆斯提出了上述“小说能够与生活竞争”的观点。
然而,就在詹姆斯痛快淋漓地攻击了特罗洛普之后不久,他自己也成了别人的攻击目标——史蒂文生在精心准备了三个月以后推出《谦恭的争辩》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没有任何艺术能与生活竞争”的观点:“‘与生活竞争’好比爬云梯登天。生活中的太阳使人眼花缭乱,生活中的疾劳病苦使人消瘦乃至死亡,生活中的美酒芳香醉人,生活中的黎明美不胜收,生活中的烈火灼灼逼人,生活中的生离死别揪人心肺——这一切都是艺术无法与之竞争的……没有任何艺术能与生活竞争,就连史学也不例外;虽然史书由不容置辩的事实构建而成,但是这些事实一旦进入史书,就被剥夺了生动的灵魂和刺人的锋芒。”〔5 〕为了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史蒂文生把绘画和文学作了类比:“绘画中的阳光和雪花若是跟生活中的阳光和雪花相比,前者就会逊色许多。绘画不仅对描绘立体和显示运动无能为力,而且放弃了色彩的真实性——与其说绘画在与自然竞争,不如说它把一组色彩和谐地组织在了一起。同样,文学一旦面临生活的直接挑战,也只能逃之夭夭……”〔6 〕史蒂文生的意思是: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小说也不能例外。
那么,在史蒂文生眼里,小说还有没有存在的理由呢?如果按照詹姆斯的逻辑推论,史蒂文生的论述无疑是对小说存在的所有前提的釜底抽薪。然而,史蒂文生并不否认小说艺术的魅力和价值。恰恰相反,他认为小说的存在十分必要,无非他所提出的理由和詹姆斯的理由不同罢了。詹姆斯认为小说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逼真性,在于它和生活的相似,而史蒂文生则认为小说存在的理由恰恰在于它跟生活的差异。他说:“作为艺术品,小说的存在并不依赖于它跟生活之间的相似之处(硬要使小说跟生活相似,这就像硬要坚持鞋的原材料都必须是皮革那样,未免太牵强附会),而是依赖于它跟生活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表现出作者的匠心,并且构成了作品的意义。”〔7 〕史蒂文生这里所说的“差异”并非指小说与生活风马牛不相及,而是指小说对生活的艺术加工。用史氏的原话说,“小说不是生活原封不动的复本,而是对生活的某个方面或某个点的简化。”〔8〕当然, 这种对生活的简化必须建立在对生活本质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有了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小说家即使只凭生活中最隐蔽的暗示也能创造出一幅生动的图画,这就是史蒂文生真正想要说明的观点。换言之,史蒂文生比詹姆斯更多地强调小说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和小说家的主观能动性——虽然小说不可能完整地反映生活的复杂性、生动性和丰富性,但是它只要把生活“简化”(亦即艺术加工)得当,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魅力。
上述争论不仅涉及小说存在的理由,而且涉及小说创作的方法。确实,史蒂文生对詹姆斯的创作观也进行了攻讦。后者在《小说艺术》中曾经谈到史蒂文生的小说《宝岛》(Treasure Island,1883), 并称自己虽然想与作者争论一番,却苦于没有资格:“我有过童年,却没有探索宝藏的经历”〔9〕。 史蒂文生认为这段话反映了一种机械的文艺创作观和批评观,即一个人只能根据直接经验进行写作。在史氏看来,詹姆斯虽然没有孤岛探宝的直接经验,但是他有过孩提时代的种种冒险经历,至少有过这方面的梦想,因为这是儿童的共同特点。史蒂文生带着讥讽的口吻说:“如果他从来都没有探寻宝藏的经历,那么这只能证明他从来就没有当过孩子。任何孩子(除非詹姆斯大师是个例外)都探寻过金矿,当过海盗,做过军官,甚至一度占山为王;任何孩子都经历过枪林弹雨,遭受过船难,甚至使自己的小手沾上过血污;任何孩子都曾出生入死,在战斗中反败为胜,甚至有行侠仗义或英雄救美的壮举。”〔10〕史蒂文生在这里明显地强调了想象力的作用。他进一步推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小说家会抱着更大的热忱去描述他想要做而未做成的事情,而对那些他已经做过的事情却不那么热情,而且一旦两者都付诸笔墨,前者的效果也往往会超过后者。”〔11〕
需要指出的是,在如何根据经验写作的问题上,詹姆斯的看法其实和史蒂文生基本一致。就在《小说艺术》中,詹姆斯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表明他对“经验”的理解。 他首先对小说家兼历史学家贝赞特(Walter Besant,1836—1901)于1884年4月25日在伦敦王家学会上的一次演讲提出了异议。后者在那次演讲中主张“小说家必须根据经验写作”,并且这样阐发了这句话的具体含义:“人物必须是真实的,是实际生活中可能遇见的……如果一位年轻女子是在宁静的农村中长大的,她就应该避免描绘军营生活……如果一个作家及其朋友的经历都局限于中下阶层,他就应该小心地避免把笔下的人物引入上流社会。”〔12〕詹姆斯同意小说家必须根据经验写作,但是他不同意贝赞特对“经验”的机械理解以及上述僵硬的规矩。他用了一个真实的例子说明了自己对“经验”的理解:一位英国的天才女作家曾经十分出色地刻画过一个法国耶稣教青年的性格,可是她在这方面的直接经验仅仅是短暂的一瞥——有一次她在巴黎偶然经过一位牧师的家门,并且看到里面的餐桌前围坐着几位刚吃完饭的年轻耶稣教徒。詹姆斯认为这短短的一瞥已足以构成经验:“那一瞥产生了一幅图画;它只持续了一刹那,但是这一刹那就是经验。她获得了一个印象,并借此创造了一个典型人物。她了解青年的特点,也了解耶稣教义;她又有机会看到当法国人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她把这些概念熔合在一起,转化成一个具体的形象,创造出一个现实。然而,最重要的是,她得天独厚地具有得寸进尺的才能。这种才能跟居住地点或社会地位等偶然因素相比,是一种大得多的力量源泉。”〔13〕显然,詹姆斯在这里阐述的观点与史蒂文生的观点毫无二致。不过,如前文所示,詹氏有关《宝岛》的那段话确实有些自相矛盾,因此,被史蒂文生抓住破绽而进行攻击也就不足为怪了。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詹史二人在有关小说的存在理由以及创作方法的措辞上各执一端,但是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异中有同,虽貌离而神合。然而,这场争论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他俩有多少异同之处,而是在于他们的观点对整个英国小说理论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这也就是本文第二部分将要深入探讨的话题。
二、争论的意义
詹姆斯和史蒂文生的争论至少在一个方面对英国小说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它加深了人们对“真实性”内涵的认识。
在詹史二人的这场争论之前,关于小说的真实性的讨论已经相当广泛。早在1785年,英国女作家莉芙(Clara Reeve,1729—1807 )就在她的《传奇的进程》(The Progress of Romance) 中主张小说必须是“真实生活的图画”〔14〕。她认为传奇和小说的区别在于前者“描述从来没有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后者则用亲切的口吻“叙述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眼前的那些事情。”〔15〕在莉芙以前的费尔丁以及在她以后的司各特、萨克雷和斯蒂芬(Fitzjames Stephen,1829 —1894)等人都曾经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小说必须忠实地再现客观现实,其中以斯蒂芬的主张最为典型——他认为每部小说都应该“完美地再现生活”,而且认为“散文体小说根本不属于想象文学的范畴”〔16〕。这些理论主张不但在19世纪中叶前后的英国小说界完全占了上风,而且呈现出走向极端的趋势,如前文所述贝赞特关于真实经验的极为僵硬的解释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艺术》和《谦恭的争辩》的相继问世及时地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真实性”的深层内涵以及小说艺术和生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可以说,史蒂文生在这方面的贡献甚至超过了詹姆斯,因为前者用更为激烈的措辞,甚至用一连串引人注目的悖论向传统的模仿说——即艺术能像镜子那样反映现实——提出了挑战。前文提到,史氏大胆地断言“没有艺术能够与生活竞争”,这在当时确实是语出惊人,因为这似乎否定了小说艺术能够做到逼真的可能性。然而,如果我们结合上下文加以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史蒂文生只不过用了一句悖论:他真正要否定的不是小说艺术的真实性,而是真实性的表层含义,即小说真实地反映生活细节及其外部特征的可能性,而对于小说能真实地反映生活本质这一点,他从来就没有表示过怀疑。除了上文中已经提到的“简化论”之外,他还强调小说艺术犹如代数和几何,其特点是引导人们把目光投向“凭借想象从自然中抽象出来的某种东西”〔17〕。显然,史氏这里谈论的是对生活本质的抽象。此外,他虽然否定小说艺术以真实感为目的,但是把追求典型视为小说艺术的宗旨:“我们的艺术与其说在于使故事显示真实,不如说在于使其富有典型性;与其说在于捕捉每个事实的和特征,不如说在于按照一个共同的目标重新安排这些特征。”〔18〕史蒂文生这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不在乎表象的真实,而是着眼于深层意义上的真实,即具有典型意义的真实。
有意思的是,追求典型恰好也是詹姆斯的理想。他在《小说艺术》中有过这样一段话:“艺术在本质上就是选择,可是它是一种以典型性和全面性为主要目标的选择”〔19〕。可见,詹史二人各自的论述其实是殊途同归:他们从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即“小说能与生活竞争”以及“小说不能与生活竞争”——出发,最后却统一在了对真实性深层内涵的共同理解上。
还须强调指出的是,虽然史蒂文生的论述在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詹姆斯对真实性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更为全面和成熟。詹氏不仅深谙创造典型之道,而且熟知细节真实的重要。就典型的创造而论,他的论述虽然不如史蒂文生的那样妙语连珠,却有其独到之处。例如,他在解释上文谈到的小说家“得寸进尺”的能力时,仅用寥寥数语就把意思表述得非常明白透彻:“(这是一种)由所见之物揣测未见之物的能力,揭示事物内在含义的能力,根据模式判断整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全面感受生活的条件。有了这一条件,你就能够很好地了解生活中任何一个特殊的角落。”〔20〕
更为可贵的是,詹姆斯在强调典型的同时并没有偏废细节真实的重要性。相反,他把细节的精确性放在了首要位置:“我觉得真实感(细节刻画的实在性)是一部小说最重要的优点——所有其他优点……都无可奈何地、俯首听命地依附于这一优点。如果它不存在,其他的优点就全部等于零。换言之,后者的存在归功于作者在制造生活的幻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在我看来,小说家的艺术从头至尾都取决于这种成功的获取以及对这一精妙过程的研究。”〔21〕这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是关于“制造生活的幻觉”那一句,因为它从心理学和美学的角度点出了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即小说能够凭借制造艺术错觉来产生逼真的效果。
相形之下,史蒂文生对细节真实就显得不够重视。如前文所述,他强调小说艺术是对生活的一种简化,是对生活本质的一种想象性抽象,这无疑有其正确的一面。然而,他同时贬低了事物细节的作用,甚至主张艺术家“把目光从肉眼看得见的色彩和动作上移开”〔22〕,这就不免失之偏颇。让我们再回到他关于绘画和小说的类比上来:诚然,颜料和文字所表现的东西确实跟现实生活中的色彩、线条和物体运动不是一回事儿,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家只能放弃(史氏用语)追求色彩、立体感和动感的逼真效果。史氏的失误恰恰在于他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由于人类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小说家以及其他艺术家可以借助内模仿和观念联想等移情作用来制造艺术错觉;这种错觉能够使作品对象由物我两忘达到物我同一,亦即进入一个十分逼真的世界。为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妨借用谷鲁斯在其名著《动物的游戏》中的一段话:“一个人在看跑马,真正的模仿当然不能实现,他不但不肯放弃座位,而且有许多理由使他不能去跟着马跑,所以只心领神会地模仿马的跑动,去享受这种内模仿所产生的快感。这就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最纯粹的审美的观赏了。”〔23〕小说艺术的观赏也与此同理。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举不胜举,如西欧一度有不少青少年因读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模仿维特自杀——这种过分强烈的移情效果当然破坏了美感,但是却从反面说明小说家制造的幻觉的确能以假乱真。简而言之,小说确实能够与生活竞争。史蒂文生忽略了艺术错觉的作用,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综上所述,詹姆斯和史蒂文生之间的那场争论把有关小说艺术真实性的讨论推向了深入。尽管詹史二人(尤其是史蒂文生)的观点在不同程度上露出了破绽,但是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挖掘了“真实性”的丰富内涵。值得肯定的是,他俩对典型意义层次上的真实所作的阐述实际上确定了典型在小说艺术中的地位。同时,他们的争论还引起了人们对细节真实的空前重视。这一切都不容争辩地确立了詹史之争在英国小说理论史中的地位。注:
〔1〕〔9〕Henry James,“The Art of Fiction”,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o12,1979.p.483,p.496.
〔2〕〔3〕〔4〕Ibid.,P.484.
〔5〕〔10〕〔11〕〔17〕〔18〕〔22〕Robert Rouis Stevenson,“A Humble Remonstrance”,Victorian Criticism of the Novel,edited by Edwin M.Eigner and George J.Worth.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5,P.216,P.218,P.217.
〔6〕〔7〕Ibid.,P.217.
〔8〕Ibid.,P.222.
〔12〕〔13〕〔19〕〔20〕〔21〕Henry James,“The Art of Fiction”,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Vol.2,1927,P.489,P.493.
〔14〕〔15〕Clara Reeve,The Progress of Romance , the Fascimile Text Sociely,New York,1930,P.111,P.13.
〔16〕Fitzjames Stephen,“The Relation of Novels to Life”,Cambridge Essays,London,1855,P.181.
〔23〕转引自朱光潜:《谈美书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