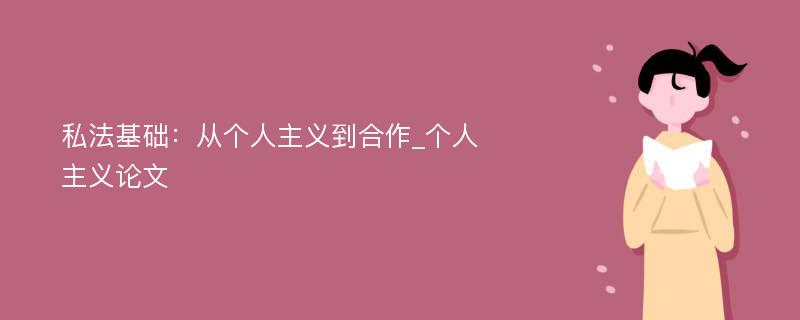
私法的基础: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法论文,个人主义论文,走向论文,主义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私法大规模继受外国私法,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零散地接受了来自两大法系私法学的个人主义哲学认识论。近来,个人主义认识论在中国私法学界得到集中表达并产生广泛影响。然而,中国当代私法学对个人主义的继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应急之需。受此影响,个人主义不仅难以对中国现有私法制度作出系统解释,而且将成为中国在两大法系传统智慧之外构想更优替代方案的绊脚石。中国私法学有必要重拾私人社会生活的合作面向,在哲学认识论上从个人主义走向合作主义。 个人主义是对“人与人之间应如何相处和组织”这一哲学问题的一种回答。在个人主义之前盛行的是整体主义:社会群体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整体,具有超越个体意志和利益的独立意义。社会成员的使命就是服务于那个客观目的的实现。而个人主义作为启蒙运动之后的一项思想资源,致力于将个人从诸种“整体目的”中救赎出来,宣扬人的主体性,并对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中国私法学而言,个人主义的影响表现为四大相互强化的命题。它们均将私法的功能限定在对既有私权的静态守护,却忽视私权的动态合作生成过程:一是认为个人是唯一真实的存在,社会整体只不过是虚构的概念体。在社会个体之外,社会群体是无所谓独立存在意义的。所谓公共利益,顶多是共同体成员的利益简单相加之和(1+1=2)。二是认为个人主观目的缺乏可知性和可比较性。主观目的源于内心世界,不具有物质世界那样强的可感知性和可评价性。无论是一般社会同伴还是立法者,在总体上对私人主观价值追求处于结构性无知状态。即便知晓也不存在判断优劣的客观标准。三是认为个人具有理性的自主决策能力,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这在私法上表现为私人自治原则,即通过维护私人自主决定的自由来实现私人利益的最大化。四是认为立法应当保持目的中立性,不要试图服务于所谓的社会共同目的和特殊个体或群体的特定目的。因为个人能够理性、自主安排自己的社会生活。 改革后的中国私法学接受个人主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私法的历史任务,特别是反映了我们对历史上“过分强调个人对社会集体的单方面服从、片面强调社会集体在个人之外的独立性,忽视公民个人的主体性”这一做法的深刻反省。在这层意义上,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倡导个人主义仍有必要。然而,个人主义将原本多元的现实社会生活简单化约,忽视了多样化的社会实践和组织方式: 首先,关于个人主观目的之可知性问题,只要个人需要通过与社会同伴的交往来实现自己主观目的,其通常就需要将源于内心世界的想法予以外在表达,进而使得我们对社会同伴的主观目的有了认识的可能。正是基于对同伴主观世界的认识和预期,我们才有可能较为准确地确定交往对象和内容。第二,关于个人主观目的之间的共同性问题,只要有机会去认识社会同伴的主观目的,自然就可能在我们之间发现相同或相似的主观追求,并思考能否通过相互合作来更好地实现它们。第三,关于个人的自主理性决策问题,如后文详述,即便在完美的市场条件下,正是个人的自利倾向使得一些人“理性地”选择搭便车或者敲竹杠,使得私人之间的合作前景难以实现或难以达到理想状态。第四,关于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组织问题,个人主义论者混淆了“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社会的必要性”和“国家权力介入私人社会的风险性”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二者同等重要,但需分别研究,不能混为一谈。 特别是,现实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在没有国家强制执行合同时,远期信用合同的发生概率大大降低;在缺乏政府组织时,旧村改造难以自发地实现集体谈判和规模开发;小区物业常常因缺乏有效管理而凌乱不堪,凡此等等。在这些“理性的个人、非理性的社会”现象面前,个人主义明显背离直觉和朴素经验。于是,不少人尝试用道德伦理、公共利益之类的模糊概念去解释国家强制力介入和组织私人社会生活的正当性,并努力对私法领域的个人主义零散地打小补丁,在意思自治原则之外零散地设置例外。但他们仍然是建立在对个人主义的总体承认基础之上的,未能思考个人主义私法学所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及其治理方案。 为更深刻地理解和应对“理性的个人、非理性的社会”,私法学在关注私有权利的静态保护同时,需主动去观察和思考私有权利的动态合作创造过程。当我们换一副眼镜看世界时,不仅有机会看到私人社会生活的合作面向,对既有私法制度作新的解读;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合作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社会合作面临的诸多障碍,思考治理社会合作障碍的替代性方案。如此,我们有可能形成一种关于哲学和法学的新认识论,本文称其为“合作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身就在告诉我们,历史发展是多元开放的,不是线性的。个人之间除了持有各种异质的主观目的外,总是在不同内容、范围和程度上分享着相同或相似的主观目的和利益。且它们通常需要经由共同合作来实现。在这些方面,对共同合作的强调非但不会损害个体之个性,反而会通过合作更好地满足个体主观目的,促进社会个性与共性的协同实现。该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婚姻、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单位、合伙、公司、行业协会、民族国家、国际联盟等各种大小不同的共同体都在向我们展示个体与共同体协同实现的可能性。在合同、财产、损害事故等传统私法领域,个体间同样具有明显的共同主观目的,需经相互合作来实现。合同本身就是一类普遍的社会合作实践,而信用合同则是有利于潜在当事人的重要合同类型。在财产领域,人们普遍希望有简明而权威的财产权公示方式、既有财产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和利用、潜在财产能够得以创造。在损害事故领域,人们都希望能够在合理成本内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害发生率。 关键问题在于,私人共同合作是如何实现的?对此,个人主义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简单地推定可以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引导下自发实现。的确,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不一定阻碍共同合作的实现。即使在完全没有国家立法和强制力的社会形态中,社会个体可自发地组建婚姻、家庭、部族和小规模经营;可以自发地组织小规模合作采集、生产和建筑活动;可以在陌生人之间从事即时合同交易、在熟人社会从事信用交易。即便是在国家强制力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之后,前述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自发的,并不依赖于国家立法和强制。 然而,当代社会的生产、交易和居住方式发生了结构性变迁。社会个体有必要与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在更多的内容上,开展更深入的合作,藉合作追求共同主观目的普遍实现。农地耕种由小块个人承包方式转向大规模合作生产;智力财产创造由单枪匹马的个人发明时代日益进入合作开发时代;社会金融从银号内的地域性交易变成了交易所的全球交易;契约实践从即时交易和熟人交易扩展到了陌生人之间的长期信用交易;居住房屋由原来的家庭自主施工建设变成了今天的规模开发和按揭交易;大量人口由原来的独门独院走进了人口稠密的小区,凡此等等。可是,理性的个人难以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引导下自发实现这些合作。那为什么呢? 中国有句古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一描述有些夸张但却道理深刻:当社会个体之间分享共同利益时,虽然个体间的集体行动将促进个体利益的实现,但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成员间的自发合作就越困难。而正是个人的“理性”自利心理,导致了非理性的社会。 在人数规模较小的共同体中,个体常常能自发开展共同合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如果一个人不积极参与共同合作并贡献投入,那么,其他成员不仅会发现其消极行为,而且极有可能也选择不作为,最终合作不会发生;或者将消极个体排除在共同体之外,其也无法得益于其他成员之间的合作收益。不过,即便小规模合作得以自发实现,其一般也不会达到最优水平。因为,在自发合作模式中,合作带来的部分收益可能被一些搭便车者分享。积极投入者对继续投入的收益就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可能在共同体最优水平到达之前就停止对共同体有利的投入。再加上,一些潜在共同体成员,尤其是所占份额较小的成员,因为能够从其他成员的投入中免费得到好处,其积极参与合作并支付成本的动力进一步降低。 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自发合作实现的共同体利益愈发远离最优水平。虽然这可能与信息不充分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仍然社会个体的理性自利行为:共同体越大,一定成员的投入所产生的共同体总收益将被越来越多的成员分享。而积极投入者自身实际分享的收益就越来越少。这就使得其投入的成本量越来越偏离对共同体整体来说最优的规模。尤其是,潜在共同体规模越大,搭便车行为被发现并被制裁的概率就越小。这将进一步影响合作的自发形成。如此,我们就能更系统地理解“理性的个人、非理性的社会”这一普遍现象了。 相应的,合作主义认识论也明确了应对此种现象的策略,即:对于那些难以自发实现的潜在共同体合作,或者自发合作水平较低的情形,要么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潜在共同体成员参与合作;要么为潜在共同体成员提供其它诱因,引导共同体成员“自发”地参加合作。这样,我们能更系统地解释私法中的立法强制现象:立法强制要求所有小区业主按照一定比例向业主委员会或者物业管理上缴纳物业费用,用于维护或改善小区公共环境;能够依法行政的政府可以通过征收权来应对旧村改造中的钉子户,实现村民居住环境的普遍提升;国家强制执行合同大大促进陌生人之间的信用合同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更积极更主动地思考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公权力组织来促进广泛的合作前景。 笔者亦深刻意识到,这将伴随着权力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公权滥用风险而径直否定国家对私人社会的组织功能。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从哪里给予肯定,从哪里开始怀疑。个人主义认识论希望通过塑造独立私法领地来防止国家强制对私人自由的侵害,这只不过是在逃避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国家强制力而已。与其如此,还不如正视私法中的国家强制,并主动思考如何在充分发挥公权力正面组织功能的同时克服其副作用,促进社会个体间的广泛合作与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