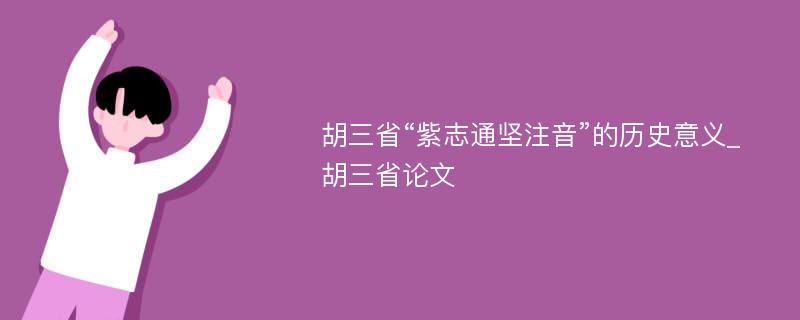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鉴论文,史学论文,意义论文,胡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三省从二十几岁开始,先后两次为《资治通鉴》作注。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冬,完成《音注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音注》),也称作《新注资治通鉴》,后人简称为《通鉴》胡注或胡注。胡三省的成就不仅仅是对《通鉴》在记事、地理、制度、音读等方面有疏通之功,更重要的他对“道”即历史发展法则有独特的认识,从而在史学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一、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实践中总结出民为国本的思想。管仲对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对“百姓”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管仲的话里多少包含了以民为国本的思想。汉初,贾谊在《新书·大政上》集中论述了民为国本的思想:“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危侮,吏以民为贵贼。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民为国本,是因为民能决定国家安危、君主危侮、官吏贵贱。胡三省对古代民本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他认为民既为国本,那么从民心向背就能看出天下形势,说观察“天下形势,但观人心向背如何耳”,看到政治形势和民心的关系。他对人民充满同情,提出“国家者果谁之国家”的疑问,似乎隐含了国家非君主一人之国家而是全体人民之国家的意思。这也就是他对“道”的认识。
论政治形势和民心向背的关系 民心向背在维持国家稳定、特别是在政权迭代之际具有一定的作用。古代政治家已经看到这一点,春秋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 年)晏婴就预见到姜姓的齐国将为陈姓(田氏)的齐国所代替,因为他看到齐国公室的不得人心和陈氏的得民心,说:“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鲁昭公三年)胡三省主要是更明确了民心向背在政治中作用的思想,说分析“天下形势,但观人心向背如何耳”(《音注》卷103)。 他认为民心向背决定国家政权的治乱兴亡。从曹魏到司马氏晋朝,从刘宋到萧齐,再到杨坚,他们取得政权都是靠篡夺而来,但他们之所以能篡夺,都是因为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前朝之虐政,简政宽民。他总结说:“贾谊曰‘寒者利短褐,饥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古之得天下,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虽奸雄挟数用术,不能外此也。”(《音注》174)当政事日非、人心背离之日,正是一姓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当中国境内有多个不同的政权或潜在政治力量存在时,人心就归向政治清明的政治力量或政权。这种情形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乃至五代十国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北齐文宣帝高洋暴戾,东方白额及沿江州郡都起兵投降南方的梁朝,“江淮之民,苦于齐之虐政,欲相率而归江南”(《音注》卷165)。南唐末年既无善政又有天灾,饥民渡淮而北归后周,因此,“观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矣”(《音注》卷192)。
民心向背,主要是取决于统治者能否满足人民的生产、生活。孔子认为政治的先后顺序应是庶、富、教,把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放在政治教化之前;使人民富庶的简单方法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足食足兵也有先后顺序。胡三省引孔子的话,来说明食在一切政治事物中是重要的因素,他说:“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已信之,足食足兵,当知所先后也。”(《音注》卷188)使民丰衣足食的简单办 法是不夺农时:“种艺之事,天有雨之不时,地有肥硗之不等,而人力又有至不至,故所收有厚薄之异也。若人君不夺农时,人得尽其力,则地无遗利矣。”(《音注》卷214)气候和土壤因素是客观的, 有了不夺农时和人得尽其力的条件,是可以有好的收成的。还要使人民安生乐业,重赋于民,使民不胜租赋而逃,是“不知稼穑之艰难”,“民逃则有不耕之土,何从得谷乎!”“民无安生乐业之心,安能亲其上而死其长乎!”。后晋恒州节度使杜重威厚敛于民,义武节度使马全义则说:“吾为观察使,取在养民,岂忍效彼所为乎!”胡三省说:“唐节度使率皆观察使,节度之职掌兵,观察之职掌民。马全义不效杜威,是矣。邻于善,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音注》卷283)在自然条件之外,胡三省注意到统治者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影响以及养民与得谷的关系,是难能可贵的。
历史上农民起义数不胜数,旧史往往称之为“贼”,胡三省的态度比较客观。他对每次农民起义,都能以简明扼要的评语指出起义的根源在统治者的政策失调、竭泽而渔。《通鉴》在唐僖宗乾符元年条下载:“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孚,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胡三省在此作注说:“是后王仙芝、黄巢遂为大盗。史先言唐末所以致盗之由。”(《音注》卷252)这样的注释,在《音注》中还有很多。 这表明胡三省看到农民起义和统治者政治作为、人心向背和皇朝统治的因果联系。
对人民充满同情 胡三省所说的“道”中,有“为国之道”,即治国之道。治国之道有很多内容,如他说:“国家多难而势诎。此时宜恤民之急,而举事反若有赢余者,失其所以为国之道矣。”(《音注》卷2)治国之道中,最基本就是要珍视民命。史言梁武帝“专精佛戒, 每断重囚,则终日不怿”。胡三省认为这不能说明梁武帝真正好生恶杀,关心人民,而是自欺欺天欺人作法。他说:“梁武帝断重囚则终日不怿,此好生恶杀之意也。夷考帝之终身,自襄阳举兵以至下建康,犹曰事关国家,伐罪救民。洛口之败,死者凡几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几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几何人?其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为死者,不可以数计也。至于侯景之乱,东极吴、会,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饥者,自典午南渡之后,未始见也。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乃终日不怿,吾谁欺, 欺天乎? ”(以上见《通鉴》及《音注》卷159)平心而论,当时的许多战争是南北分立形势所致, 不是梁武帝个人所能决定的;胡三省对战争的反感也是受他个人经历的影响的。但他指出由于梁朝政治的腐败,造成梁朝在南北战争中屡战屡败,由于梁武帝的决策失败召致侯景之乱,内乱外患给人民造成无数痛苦,是反映了他对人民的关心的。这也反映出他这样的思想,即君主应珍视民命。
“国家者果谁之国家”的质问 这种质问似乎具有国家非君主一人之国家而是全体民众的国家的意思。我们还以他对梁武帝时政治的评价来阐述他的思想。梁武帝在位四十多年,唐人魏征盛称当时为“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此之盛。”其实在当时,梁武帝的政治就不断受到时人的批评。在批评者中,有敌国之臣,有当朝之臣,更有平民百姓。天监十年(511), 秣陵老人批评梁武帝立法实质是“急于庶民,缓于权贵”。事实确实如此,史载梁武帝用法不一,权贵“有犯罪者,皆屈法伸之。百姓有罪,则案之如法,其缘作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举家质作”(《通鉴》卷147)。大同二年(536)尚书右丞江子四上书,“极言政治得失”(《通鉴》卷157)。大同十一年(545)散骑常侍贺琛上书言四事,其一认为南北通和,正是国家休养生聚教训之时,而户口减少,民不堪命,岂非牧守之过?其二认为天下官员务为贪婪,实由风俗侈靡使之然。宜严为禁制,导以节俭,移风易俗。其四认为当边境无事时,“宜省事、息费,事省则民养,费息则财聚”,“凡京师治、署、邸、肆及国容、戎备,四方屯、传、邸治,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兴造有非急者,征求有可缓者,皆宜停省,以息费休民。故畜其财者,所以大用之也。养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如此,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矣”(《通鉴》卷159)。太清二年(548)侯景至建康,在复宰相朱异并告城中士民书中,揭露梁朝廷百官的罪恶,说:“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通鉴》卷161)对这些批评的评价足以表明胡三省的观点。 他认为江子四的批评未敢指出梁武帝政治的真正失误,“江子四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释氏,而穷兵广地,适以毒民,用法宽于权贵,而急于细民等事,特毛举细故而论得失耳”(《音注》卷157)。贺琛的批评, 倒是抓住了梁朝政治的真正失误,“此亦确论也”(同上,卷159), 是千载不易之论。而侯景的批评更使梁朝当权者无辞以对,“(侯)景书至此,(朱)异等其何辞以对!”(同上卷161)从胡三省的简短评语中, 可以看出他确实反对统治者的“毒民”、“用法宽于权贵而急于细民”、“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夺百姓”等,而赞成省事、息费、休民。这些都是他具有民本思想的体现。
梁武帝对时人批评的反应,因政治形势不同而异。对江子四的毛举细务论得失,梁武帝马上抓住显示自己纳谏作风的机会,下诏说:“朕有过失,不能自觉。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书可时加检括,于民有蠹害者,宜速详启。”(《通鉴》卷157)对秣陵老人的批评, 梁武帝“思有以宽之”的办法,来年春天发布宽大诏书:“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同上,卷147)对贺琛的批评, 梁武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书以责(贺)琛”,这份敕书长达七千字,说:“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又辩解说他“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国匠”;并且指斥贺琛“何不分别显言,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减,何处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大有使贺琛谢过、不谈国事之势。可见,梁武帝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民众的重要。
胡三省批评了梁武帝的这种反应。他揭露梁武帝感于秣陵老人之言所下的宽大诏书的实质,“所谓宽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绳权贵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乱也”(《音注》卷147)。 针对梁武帝的“不食国家之食”,胡三省批评说:“帝奄有东南,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唯不出于公赋,遂以为不食国家之食。诚如此,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针对梁武帝的“营造不关材官及国匠”,胡三省说:“此自文其营造塔寺之过耳。材官将军属少府卿;国匠者,官给其俸廪以供国家之用者。大匠卿,掌土木之工。”(同上,卷159),这是说, 所食粮食不论出自公赋,还是出自园中之物,所营建的建筑物,不论是不是由国家官员所督造,既不是梁武帝所鼎礼膜拜的神、佛所营造,也不是从西天竺国来,都出自东南民力。如果确如梁武帝所说的“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那么国家是谁的国家?没有人民的劳动和赋税,还能有梁武帝和朝廷百官的衣食来源吗?如果国家依人民的劳动和赋税而存在,那么国家还能说是君主一人之国家吗?显然在胡三省对国家性质的怀疑中,是隐含了人民因素的。
胡三省赞扬贺琛的省事、息费、养民说是千载不易之“确论”,揭示江子四的论政治得失没有抓住梁朝政治的真正失误,揭露梁武帝的“宽民”诏和好生恶杀的虚伪性质,指出侯景的告宰相朱异书是对梁朝剥削实质的较深刻揭露。他提出“国家者果谁之国家”的质问,既是对国家性质产生怀疑,也是对国家统治和民力关系的一种间接论证。他论政治形势和民心向背的关系,他对人民的同情,都体现出他对古代民本思想的发展。
二、论人臣之事业和风节的关系
胡三省的“道”,还包括臣子事君治民谋身作事的法则,而尤以事君为主要内容。他对人臣节操和事业有自己的看法。
第一,他认为人臣既要有节操,又要有事业,唐朝诸将中只有段秀实堪称事业风节并著,“自高仙芝丧师于大食,段秀实始见于史。其后责李嗣业不赴难;滏水之溃,保河清以济归师;在彬州,诛郭唏暴横之卒;与马磷议论不阿,及治丧,曲防周虑,以安军府;最后笏击朱泚,以身徇国:其事业风节,卓然表出于唐诸将中”(《音注》卷225)。
第二,在事业不能有成时,要保持为臣的节操。当庙堂焦虑之时,正是忠臣毕命之秋。他赞扬董僧慧、陆超之之义烈、许远效死节以保国、颜杲卿之忠节照映千古等。他讽刺、批评和揭露失节者、徒有虚名者,认为他们是“详于身谋略于国事”。如汉末华歆、邴原、管宁很有名声,三人号称一龙,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腹、管宁为龙尾,但华歆成为曹氏篡汉的急先锋,邴原也接受曹操的封爵。胡三省说“高尚其事,独管宁耳。当时头尾之论,盖以名位言也”(卷67)。宋末,萧道成谋划篡位,谢腓、谢朓兄弟不闻不问,以“力饮此(酒), 勿豫人事”为戒,胡三省认为他们安享荣辱,不关心国家安危,徒有虚名,不可为忠臣。褚渊被时人评为“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大节”,“渊自谓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见宋明帝!”胡三省一再说褚渊有愧于为臣之大节,“褚渊之为人,人皆得而侮簿之”,“褚渊失节,人得以面斥之”。(《音注》卷133)。他对当时世家大族袁氏、王氏的评价, 是以他们与国家存亡安危的关系为准绳的。他认为袁氏自袁淑以来,尽忠帝室,“袁淑死于宋元凶之难,袁顗以死奉(刘)子勋,袁昂尽节于齐室,袁宪尽忠于陈后主”。袁粲才不堪于受托孤之命,但从人心之公是非来看“然粲虽不足,以死继之,无愧于为臣之大节”,“自是宋室忠臣”(《音注》卷133、137)。认为琅邪王氏虽奕世台鼎,而为历代佐命,“琅邪王氏股晋室,而王弘为宋室佐命,王俭为齐室佐命,梁室之兴,侯景之篡,王亮、王克(疑为王伟)为劝进之首”。其实,袁、王的高下在唐朝就有定论,如高宗时苏州刺史袁谊就耻与王氏为比,曾说“所贵于名家者,为其世笃忠贞,才行相继故也。彼鬻婚姻求利禄者,又乌足贵乎!”而袁谊的话受到时人的肯定。胡三省接受袁谊的说法,认为是有益于名教(《音注》卷202)。
第三,“臣子大节,则全其身以全国家”;在事业可能有成或必须有成时,可以不考虑臣节。梁武帝太清二年(548)侯景围建康, 梁世子萧方等入援建康,史载,“方等有俊才,善骑射,每战,亲犯矢石,以死节自任”。胡三省认为萧方等所作不符合“臣子大节”,“为人臣子,固当以身许国,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国也。…若论臣子大节,则全其身以全国家,斯得谓之忠孝矣”(《通鉴》及《胡注》卷161)。 以身许国是一种臣节,存身全身又是一种臣节,而以后一种为大“忠孝”,因为“存其身者,所以存国也”;“全其身以全国家”。国家和士人的家荣辱与共,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司马笠对殷浩说:“足下去就,即时之兴废,则家国不异,足下宜深思之。”胡三省很赞赏这话,说:“国兴则家亦与之俱兴,国废则家亦与之俱废也。”(《胡注》卷97)把国家存亡和个人得失、国家命运和个人作为联系起来,而不是用名节来衡量个人的价值。这种看法,表明胡三省更注重人臣在当时的建功立业,而不是死后的名声,这是古代价值观的一个变化。
胡三省对人臣在乱世的节操犹为重视,“世乱则人思自全,然求全而不能全者亦多矣。窦融、张轨之求出河西,此求全而得全者也;谢晦袁顗之求镇荆襄,此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也。盖窦融、张轨,始终一心,以奉汉晋,此固宜永终福禄,诒及子孙者。谢晦、袁顗,志在据地险以全身,其用心非矣,此天所不与也。然刘焉求牧益州,袁绍志图冀部,石敬塘心欲河东,皆以之潜望非规,至其成败久速,则有非智虑所及者”(《胡注》卷84)。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个人命运也和个人选择有关。但为什么选择相同,而命运却不同,胡用非智虑所及的“天”来回答。
对崔楷死节的评价,可代表胡三省对臣节的总看法。葛荣围广阿,魏殷州刺史崔楷在“强弱相悬,又无守御之具”的情况下,“抚勉将士以拒之,…连战不息,死者相枕,终无叛志。辛未,城陷,楷执节不屈,荣杀之”。胡氏说:“藩翰之任,保境安民,上也;全城却敌,次也;死于城郭,岂得己哉!崔楷合家并命,其志节有可怜矣。上之人实有罪焉。”(同上,卷151)这样看来,胡三省把臣节分为四等, 以全身保国保民为第一等,以全身而全国、事业节操并著为第二等,以死于城郭为第三等,无所作为、但不降不仕为第四等,至于屡降屡仕、永保富贵者,不在四等之内,人得而辱之。
三、论儒者与立国的关系
怎样处理好创业与守成阶段的不同问题,决定着封建皇朝能否长治久安,因此受到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重视。汉初和唐初,统治者对创业与守成,有过理论论争,并有独特的见解。陆贾对汉高祖提出“马上得天下,宁可以马上守之乎”的问题,引起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房玄龄认为创业维艰,魏征认为守成则难,唐太宗明辩创业与守成各有先后,守成是今后的为政重点:“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元统治者继承了这一传统,贵由汗时(1247)忽必烈就创业与守成问题,向封龙山三老之一的张德辉询问,张德辉告诉忽必烈守成的关键是“当求谨厚者司掌”,即选择人才。但对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则有不同的理解。元统治者从其统治需要出发,往往用西域人担当重任,而对有儒家思想文化的汉人、契丹人不甚重视。耶律楚材是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贵族,对成吉思汁的财税、文教等事多有贡献,也因此受到西域人的中伤。西夏人常八斤因会制造弓箭,曾傲慢地对耶律楚材说:“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有何用处”。楚材反驳说:“治弓尚须用弓匠,治天下岂可不用治天下匠”;以后又对窝阔台汗谈守成用儒的道理,“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累数十年不易成功”(《元史》本传)。但儒者在元朝一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胡三省提出“不有儒者,其能国乎”的论点,把儒者的地位、作用提高到维护皇朝统治长久的程度,是对陆贾等人观点的发展。
胡三省对创业与守成两个阶段的用人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武德九年(626)唐太宗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 姚思廉、欧阳洵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胡三省说:“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论议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然则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通鉴》、《音注》卷192)形势决定创业用武、 守成用儒。从选择人才方面讲,守成必须用德行才能兼备者。魏征对唐太宗讲创业与守成用人的不同,“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胡三省很同意这种说法,说:“观此,则天下已定之后,可不为官择人乎!”(同上,卷194)后唐天成三年(928),史馆修撰张昭远上书明宗,说:“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今卜嗣未定,臣未敢轻议。至于恩泽赐与之间,婚姻省侍之际,嫡庶长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绝其侥冀。”明宗“赏叹其言而不能用”。这受到胡三省的重视,说:“自梁开平(907)以来,至于天成,惟张昭远一疏能以所学论时事耳。 不有儒者,其能国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赏叹而不能用,呜呼!帝之赏叹者,亦由时人言张昭远儒学而赏叹之耳,岂知所言深有益于人之国哉!”(《通鉴》及《音注》卷276)这里胡三省提出“不有儒者, 其能国乎”的论断,将儒者和国家存亡联系起来,是把儒者置于很高的地位。儒者之重要,是因为儒者能“以所学论时事”,又因为儒者“所言深有益于人之国”。张昭远所言的重要,不仅是因为他提出选师傅以教皇子,分别嫡庶长幼以示等级威严;而且因为他认为师傅能为储君“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这些,恐怕都是胡三省看重张昭远言论的原因。
必须指出,胡三省的“不有儒者,其能国乎”的论断,是表示国家需要儒者,而不是儒者需要国家。这种思想表现在他对樊英的赞赏中。樊英是汉末名士,习《京氏易》,兼明《五经》,多次辞谢官府乃至朝廷的征聘,顺帝永建二年(127)“英不得已,到京,称疾不肯起, 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两年后,顺帝为樊英设坛席,待以师傅之礼,访问得失。“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俱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讲退无所据矣,”对樊英出处,《后汉书》作者范晔有过评论,说在后汉名士中“英名最高,毁最甚。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名,无益于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原其无用亦所以为用,则其有用或归于无用矣。”看后汉李、杜等人的事迹,可知范晔所言不虚。胡三省在张楷责备樊英的话后,具引《后汉书·樊英传》中的一段材料:
英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
这段材料因表现了强烈的轻君思想,司马光没有把它选入《通鉴》,但胡三省却全文照录,原因何在?陈援先生说是“以振逸民之气”(见《通鉴胡注表微》,270页), 其实这也表现了胡三省对樊英精神的赞赏。这种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士人和统治者在人格上处于同等地位,士人的一切也并不是由统治者所能决定的,因为士人不立暴君之朝,不受非礼之禄,不易万乘之尊,就是说士人不需要统治者。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欲,仕也需统治者的礼贤下士。
民心与政治形势的关系、民力与国家统治的关系、人臣之事业与风节的关系、儒者与国家的关系等,确实是能影响国家统治的重要关系,具有历史发展法则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论证,表现了胡三省对历史发展法则“道”的认识,是有史学方面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