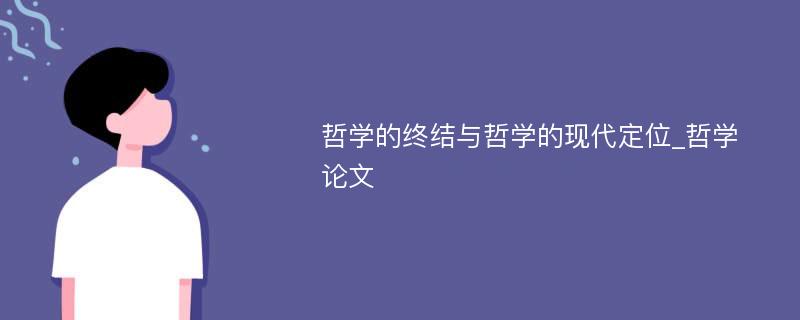
哲学的终结与哲学的现代位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位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在19世纪后半叶,已经揭示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恩格斯那里,所谓终结的含义有两重。其一,是指黑格尔所说的包罗万象的、作为科学的科学那种哲学,即黑格尔作为集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了。其二,是指黑格尔的形上学体系,是哲学史上最后一个这样的体系。这表明,恩格斯已经看到,随着原来襁褓在哲学中的未成熟的各门科学,纷纷成熟而独立出来,哲学史上原来意义的哲学已经解体。这样,正如他指出的,就原来意义上的哲学而言,剩下来的,就只有逻辑和辩证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把他们的哲学思想写出一个体系来,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批判和嘲笑了杜林创造体系的企图。马、恩没有构造哲学体系,是不是与此有关,就不得而知了。无论如何,恩格斯对于哲学发展所作的上述洞察和提出的问题,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对于哲学史上原来意义的哲学之解体,或者说,哲学之终结,应如何深入的理解,显然,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重要问题。
到20世纪后半叶,海德格尔对于哲学终结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在海德格尔看来,哲学的“终结”,不能作消极的理解。哲学的“终结”,在他看来,也是哲学的一种“完成”。原来襁褓在哲学中还未成熟的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这样的事情,就是哲学“完成”的表现,尽管这种“完成”,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因为,从古希腊开始,“就是科学在由哲学开启出来的视界内的发展”(《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60页)。就是说,所有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各门科学,不仅不是与哲学没有干系,而且其发展仍然是“在由哲学开启的视界内”。但是,由于各门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哲学本身还是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经过“终结”或“完成”的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它的使命又如何?对于这里提出的问题,海德格尔只是从否定方面做了回答。在他看来,如果不看到这种变化,还按照老路走下去,那么所谓哲学思维,就只能是老调重弹。用海氏的话来说就是:“无论说人们现在如何尝试哲学思维,这种思维只能达到一种模仿性的复兴及其变种而已”(同上)。在这里,他只说到不如此会如何,而对于这个问题的正面回答,似乎还在问题的清理之中。这就是指,他提出和思索了以下的问题:“哲学终结之际为思留下了何种任务?”海德格尔善于借助词源的分析,来阐发他的思想。他认为,“终结”一词的古老意义与“位置”相同。(同上书,59页)因此,所谓哲学的“终结”,不过是“位置”的改变。不管对于海氏整体思想作怎样的评价,他的这个哲学“位置”现代改变的观点,是极其深刻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位置”的现代改变?
二、哲学的现代位置
哲学的本质在于“思”或“哲思”,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接近于这种本质的表达。这种哲思,在哲学史上,虽然向外向内思之甚多,但是,对于“思”或“哲思”本身,却思之甚少。这就是海德格尔提出和思索上述问题的理论前提。就是说,如果哲学思维不想老调重弹,就不能不回到或面向“思”或“哲思”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在他之前,黑格尔和胡塞尔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这就是“面向事情本身”的问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是通过主体性的建立和思辨辩证法来实现的。所谓主体性的建立,是指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真理”,不仅应当被理解和表述为客体,而且同时应当被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而所谓“思辨辩证法”,就是指这种主体作为概念,其自身能自己运动和发展的辩证法。在一百年后,胡塞尔在其论文《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重新提出“面向事情本身”的追求。胡氏的追求,是“意向性”的意识道路。他之所以反对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就是因为这两种方法,阻碍着通向“意向性”和终极“原本的被给予性”的道路。在海德格尔看来,黑格尔与胡塞尔虽然角度不同,但是两者都把所面向的“事情”归结为“意识的主体性”,并且最后都归结为方法。也就是说,方法不仅不是外在的东西,而且方法就是“事情本身”。当然,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不同,胡塞尔所提出的“一切原则的原则”,乃是“现象学方法”。
海德格尔之所以比较具体地讨论黑格尔与胡塞尔,在于他把这两位大师所作的“面向事情本身”的研究,看作他继续前进的“路标”。不过,在海德格尔那里,已经把“面向事情本身”,变成“面向思的事情”。他认为,“事情本身”,应当就是“思的事情”。在这里,海德格尔强调“事情”(Sache )这个德文词所具有的“争执”意义和当下“关涉”意义。那么,海德格尔按照黑格尔与胡塞尔的“路标”,他走向了哪里?或者说,他所开辟的新路径又如何?他把哲学的“现代位置”摆在哪里?
现代人类社会所展现的,一方面是科学技术与物质生活层面,空前的发达和丰富。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同时也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可以说,这两方面在特定意义上,乃是一种因果关系。正是人类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上的失控,以及在物质生活追求上的贪婪,使人类陷入生存和精神的危机。海德格尔正是以他特有的敏感和深思的穿透力,试图从哲学上揭示和把握人类这种空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在《存在与时间》这部著作中,海德格尔着力揭示的是,以往哲学对于“存在”及其意义的忘却。人们只注意“存在者”,把“存在”与“存在者”混为一谈。通过这些抽象概念,海德格尔所显示的深意,就是人们在向外追求作为外物的“存在者”时,把人自身的“存在”或“生存”忘却了。相反,误把作为外物的“存在者”当作自身的“存在”或“生存”了。就是说,人被“物化”或“异化”了。这就是所谓“人生而被抛”或“无家可归”的理论说明。
可见,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位置”,就在“生存危机与精神危机”之中。那么,如何首先解决在这种危机中的哲学认识问题?中国学界在揭露认识缺点或错误时,现在有两个时髦用语,叫做“盲点”或“误区”。这两个用语,如果从海德格尔的眼光看,都带有“主体性意识”味道。海德格尔在揭示“忘却存在及其意义”时,他把这种“忘却”看作“遮蔽”。因此,他的思之“新路径”,可以说,就是如何解除“遮蔽”的途径。也许,这就是在哲学终结之后思所应当承担的新任务吧。
如果说黑格尔与胡塞尔为海德格尔所“思”提供了“路标”,那么,可以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方法就是事情本身”的思想。海德格尔对于“事情”(Sache)的词义解析,所谓“争执”、 当下“关涉”,已经透露出他也正是在把“事情”方法化。所谓“争执”,是指显现的方式不同,例如黑格尔与胡塞尔在方法上的不同。所谓当下“关涉”,则是指“事情”的根本或原初的前提,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本己的在场”,例如黑格尔与胡塞尔在这方面又是一样的。但是,“事情”的原初前提或“本己的在场”,即被忘却的“存在及其意义”,恰恰是以往哲学之思所未思,而且被长时期地“遮蔽”着。因此,海德格尔之思的“新路径”,确实就在于如何解除这种“遮蔽”。
海德格尔曾暗示,在人类早期或者人类思之童年,那时,人类曾有过没有被“遮蔽”的思。他指出:“在希腊语中,人们谈论的不是看的行为,不是谈论目睹(videre),而是谈论闪亮和显现的东西。”(同上书,第69页)那么,后来人类何以会陷入“遮蔽”而不能自拔的境地?海德格尔很多次都擦着这个问题的边缘,而走过去了。他急于探讨“解蔽”,却忽略了产生“遮蔽”的原因这个重要问题。实际止,“遮蔽”是人类自身发展的一种需要,因而是一种必然。例如从最初的原始人,像动物那样一丝不挂,到衣服的发明。再如,人类的思想从直接表现到隐喻表现的多样化和深刻化。所有这些“遮蔽”,直至今天仍在继续发展着。当然,问题在于,“遮蔽”原本出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但是,如果这种“遮蔽”导致忘却了人类自身,那么,海德格尔的“解蔽”就是极其必要的了。现今的事实,正是人类久已忘却了自身,可以说,已经到了不“解蔽”就不能恢复记忆的程度。不可否认,现代人知道的事情,确实比古人多得多,但是,惟独对于自身所知,却比古人少得多,以至几乎忘却了自身。即使在把大地当作自己保护神的“人神一体”的“整体观”中,古人对于自身的认识,也包含着现代人所无法比拟的深刻认识。可见,人类自身的发展,并不是只有前进,也包含有后退。海德格尔的“解蔽”研究,在特定意义上,就是要改变人类这种后退。
海德格尔从《存在与时间》到《时间与存在》,他在哲学理论上所要解决的问题,看去是那么抽象,但是,其内涵却是再生动具体不过了。在哲学理论上,他所要开启出的,或者是悟出并传达出的,就是那个“本己的在场”之境域。实际上,这就是对人生之“生”,寻求真正的领悟。这种“领悟”其所以需要,并且显得迫切,就在于人对于自己的人生之“生”,忘却得太久太久。甚至,不少的人,至死不悟。话也许越说越远,还是先打住在这里。不过,从上述亦可看到,就海德格尔所论而言,哲学的现代位置就是人的现代位置。反过来说,也一样,人的现代位置就是哲学的现代位置。
如果说,哲学显示着民族的时代精神,那么,对于个体人来讲,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种精神就是他的魂魄。因此,哲学在现代之被置弃,并不表明哲学的贬值。相反,哲学的被置弃,只能说明忘却或丧失自身的人,处于丧魂落魄的境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