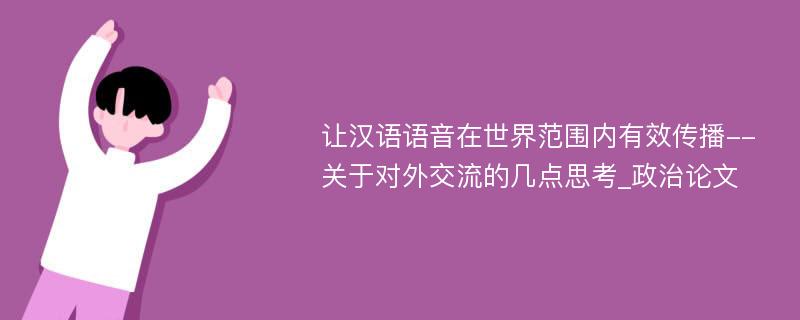
让中国声音在世界有效传播——关于对外传播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声音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让中国的声音在世界有效地传播?这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乏沉重的话题,甚至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话题,其艰难不仅在于理论,更在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求实态度。
一、我们为什么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缘起与模式的改变。
从一年前国内四行业协会联合商务部在CNN推出的“中国制造”广告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要与世界沟通的强烈意愿,而这种意愿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运行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显然,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的重新分配,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这种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市场份额和边界的调整过程其实是必然的,即使不是中国,也会由其他新兴经济体引发。但这种调整带来的相关国家国内产业调整、劳动力流动等问题,总会引起一些民众的对立情绪,为中国商品进入构成了很大的非关税阻力。并且,由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传统西方文化视野里,中国过去一直被边缘化,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国度,而这种神秘往往意指异类的、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当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异类的巨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商品在全球无所不在的时候,对方往往由于不清楚你将按什么规则出牌、是否是自己的潜在威胁而心生疑虑。
我们也需要反思自身的进入方式。中国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涌入世界各地,但中国的声音并没有实现全球化传播。缺少了文化的进入、对当地的社会人文环境没有贡献、对当地社会没有参与,而只是单纯的商品大量涌入,难免给人留下攫取利润的不良印象,很容易导致“中国制造”威胁论。隔阂产生偏见、偏见导致冲突,要真正改变“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对外沟通和文化输出首当其冲。
按照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虽然新闻中阐述的是事实,但往往是经过建构的、单一角度的事实。西方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往往只能为受众提供一个角度,并且是具有深厚西方文化底蕴和政治、社会背景的,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应当对建构自身形象有所作为,而不是只依靠西方媒体来塑造中国形象,这样不仅能改善西方主流人群对中国和中国制造的刻板印象,而且能帮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
同样明显的是,还要向世界说明,中国需要规则与模式的改变。
从商务部等有关国家形象的广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对外传播思路的一些积极调整。政府能够开展这种国家形象的营销行为,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而要向西方输出声音,就需要有他们可接受的媒体和方式来传达,这种通过西方主流媒体投放商务广告,使其听到中国第一手声音的做法,在现阶段是一种务实的表现。然而,国家形象广告不能成为唯一的推广模式,它与企业、社会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沟通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公民交往、学术交流、旅游都是很好的沟通方式,中国还可以推出政策、文化等多方面的整体形象广告,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是一个遵循人类共同价值和游戏规则的国家。如果能够通过多层次的综合传播,提供给西方主流人群解释中国的另一种角度并被其接受,在一定程度达到某种平衡、消除某些误解,就是非常成功的推广了。
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眼下的国家形象广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还有待商榷。对比与中国人通过整体概念把握具体事物的习惯,西方人更倾向于从具体的个案和场景来体验,更重要的是,沟通的第一步不是晓之以理,而是动之以情,让对方产生认同感才是传播成功的关键。目前这类广告的呈现形式还是略显东方化,并不符合西方人认识问题的角度和逻辑:整体上看这则广告是在讲概念、说道理,而不是感染人或以情动人,这种传达形式对于认同感的建立比较不明显。
这方面其实可以借鉴韩国的成功做法。中国人过去对韩国有多少了解和兴趣?但是韩国人通过韩风和韩剧中一些时尚元素的渗透和浪漫场景的营造,让许多受众对韩国文化产生了兴趣和好感,这种情感认同进一步带动了韩国的旅游业,乃至整个韩国文化的对外推广。
好的传播效果应当是一盏能够照亮全部阴影的无影灯,但这不可能由单一的传播行为完成。对于第一个国家形象广告而言,我们也不能苛求其涵盖各方各面的诉求,毕其功于一役。偏见的产生不是一时的,因此它的消除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该更加耐心和宽容,创造更宽松的交流方式和空间。希望在“中国制造”等国家广告之后能够有更多后续的推广和传播活动,真正达到对外沟通和文化输出的目标。
二、在造就传播的话语影响力方面,国力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第一位重要的因素。
“弱国无外交”,这话是有几分道理的——任何有作为的外交都是建立在一定实力基础上的,传播也是这样。有人把信息的流动比喻成一个连通器中的液体流动:只有当一端和另一端产生位差,流动才能够产生。换言之,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和国家的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微不足道的小国,即使你把报纸、电视、广播送到别人家门口,也不会对你产生多大的兴趣,只有当你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时,你的声音才有可能是人们“必听”的。
但是,国力并不决定一切,甚至它并不是决定传播影响力的第一位重要因素,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日本的经济实力早就位居世界第二了,但是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似乎和它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原因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缺少自身话语的独特核心价值——它和美国太一致了,用传播学的术语就是传播内容的同质重复,这样一来就缺少了人们选择和倾听它的话语的理由——与其听你说,不如听美国说,因为美国的表达更彻底、更鲜明、更到位。事实上,人们在对同一类事物做出选择时,多数情况下是只选第一,很少会选第二。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就其经济实力而言,它们所在的国家在世界的排名大约应该在几十名之后,但是它们在反恐和中东事务上的国际影响力甚至可以和CNN这样的大牌媒体叫板。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充分有效地利用了阿拉伯世界的资源,向世人展示了阿拉伯世界的视角,让人们看到了事实的另一面,为人们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提供了一个有独特价值的信息渠道。
显然,上述事实其实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影响力,或者当地发生了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重大事件,便有可能为其建立世界话语权创造契机。但是,这种可能能否变为现实,则取决于实力和事件以外的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传播内容与形式的价值因素。
从目前世界传播的格局上看,不但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基本上是由CNN、美联社和《纽约时报》等少数西方媒体所塑型的,而且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国际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上述媒体所塑型的。
为什么中国在世界传播舞台上的声音如此孱弱,以至于严重“失语”?是因为我们的国力孱弱吗?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缺少造就国际影响力的内在品质吗?是因为我们表达的声音不够独特吗?显然都不是。我国传媒的表达(从内容到形式)不可谓不独特,其旗帜鲜明的党派形象和不加掩饰的宣传腔,非常明显地是和西方媒介有着天壤之别的,但是这种“独特”似乎并没有构成吸引人们阅听的现实价值。显然,除了实力和独特性之外,传播话语影响力的造就还有着更加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那么这个因素是什么呢?
三、在国际传播领域,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主流媒介确立的,它塑型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这是我国传媒走向世界时必须正视和顺应的。
从最一般意义上来考察,价值是从物的有用性和主体需要的对应中产生的。在传播领域,政治、经济、文化的辐射力构成了传播产品物的有用性的基础,而打造与主体需要相对应的有用性,便成为传播产品真正具备价值的关键。
首先,传播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信息沟通和影响力的发生是建立在传授双方共同经验适度重合的基础上的。换言之,一切产生现实价值的传播产品必须与人们既有的信息消费经验、信息消费偏好和信息消费模式相切合,如果不切合,传播者就会沦落为“沙漠中的布道者”——再好的教义、再多的资金,也不会产生任何实际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国际传播领域,目前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由西方主流媒介所确立的,它塑型了人们信息消费的胃口,决定着传播致效的话语方式,这是我国传媒走向世界时必须正视和顺应的。譬如,客观、公正、平衡、独立,这是西方主流媒介主导下的国际传播市场的基本口味,是人们对于传播产品进行价值选择和鉴别时的基础性标准。所谓客观,就是要把事实报道与观点评论严格区分开,不在事实的报道中羼进主观的评论;所谓公正和平衡,就是要不偏不倚地对待争议双方,引述一方观点时,一定要同时引述与此不同或者对立方的观点;所谓独立,就是指媒介要不偏、不倚,体现社会良心和社会正义,持有不同于任何利益集团的独立视角,拉开距离报道事实和分析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成功,除去反恐形势凸显了阿拉伯世界的重要之外,一群受过BBC严格培训的新闻人对于西方主流媒体传播规则的熟知和利用,是其制胜的关键因素。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要高举旗帜,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话看上去正确,其实大谬不然。首先,我们的报道内容是给我们自己看的还是给别人看的?如果是自娱自乐,你尽管卡拉OK好了,但是如果你是要给别人看的,你就必须要和别人的需要方式以及偏好、口味相接轨。其次,从传播艺术的角度看,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天然去雕饰,最好的宣传是最没有宣传味的宣传。实际上,简单地保持口径上的一致是最容易做到的,但往往又是没有效果的。信息论告诉我们,顺向流动的信息价值是比较低的,只有错开一定的角度,信息的价值才有可能确立。
四、构建国际话语权的第一步:“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
曾经看到过一条报纸的宣传语:“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常常是有新闻的地方没有我们,我们媒体的国际报道往往只是西方跨国媒体报道的“二传手”。近来,加沙战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但是我们了解加沙战况的全部资讯却几乎都是来自于西方媒体的报道;再往前追溯,我们媒体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充其量也只是在西方媒体报道基础上的一种编辑。没有来自于新闻一线的第一手报道,没有我们站在新闻第一现场发出的声音,这意味着什么呢?往浅里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传媒软实力还不行,而往深里说,实质上是听由中国人的头脑被西方媒体格式化——至少在国际新闻认知方面是这样。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是媒介化了的社会。大约70多年前,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舆论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名著《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一书中指出:大众媒介时刻在向人们构建拟态环境。换言之,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而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的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大量的传播学研究表明,在这种由媒体构建起来的拟态环境基础上,媒体在决定人们关注什么问题(社会议程设置)、决定人们从哪种角度看待问题和用什么逻辑来分析问题(“诠释包裹”与“框架装置”),甚至于在塑造人们的态度和观点(“启动效应”)方面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1972年麦克斯韦·E·麦库姆斯(Maxwell E.McCombs)和唐纳德·肖恩(Donald Shaw)在《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指出:大众传媒对某些问题(议题)的特别报道倾向和力度(显著性和重要性)将影响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认知,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其后,心理学家凯尼曼(Kahneman)和特威尔斯基(Tversky)的决策研究发现,同样的讯息经由不同的表达方式会导致人们做出不同的决策选择,其不同的表达方式就是陈述的框架,不同的决策选择结果体现着传播策略所显现的框架效应。而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Owen Goffman)等人的研究表明,框架构建就是人们通过选择思考结构(框架)对事件进行主观解释并构建社会现实的过程。有学者因而认为,框架至少存在于新闻来源(因其可决定如何从自身组织的角度诠释事件真相)、新闻文本(如新闻中的关键字、语词、标题等)、新闻工作者、读者以及社会文化中(框架的真正起源)。
由上讨论可知,第一手新闻资讯的掌控,在形成社会议程和诠释框架方面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当我们缺失新闻来源第一手把控能力的时候,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社会议程设置的能力,失去了对于事件的解释权,并且最终让我们的人民无奈地接受西方媒体影响力的格式化。
问题的关键还不仅仅在于人们的认知层面。认知上的误导往往会进而导致自我实现预言的社会效应。研究显示,如果媒体在初始时构建了一个假环境,那么在特定条件下就足以引发基于这种情境状态的社会行动。社会学者默顿曾举例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一家银行倒闭来说明这一概念。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在某一天偶然聚集了较多的人提款,于是有人据此做出一个判断:这家银行的经营出了问题。这本是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却在储户中流传开来,结果大家争先恐后地提款,致使这家银行真的经营不下去了。这个结果,当然不能证明最早认为这家银行经营出了问题的那个人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是预言影响了储户的行动所致。
从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角度看,个人的决策总是会受到他人影响的,在变化较为迅速的社会中,人们会把媒体的报道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试想,当媒体所构建的拟态环境出现偏误的情况下,媒体的假定会成为许许多多社会成员的假定,这时自我实现预言就可能成为一种危机传导的机制。
处于崛起中的中国需要关于世界的真相和与世界沟通的能力,而真相和共同能力在认知上的本质就是信息对称以及由此造就的优势。信息对称的认知,必须由不同媒体多角度报道来共同构建,因此“有新闻的地方就有我们”是实现把握世界真相、与世界有效沟通的至为关键的第一步。
五、对内传播体制的改革是对外传播模式变革的前提和基础。
从中国社会言论尺度的宽松度和活跃程度看,30年来每十年中国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中西方的参照点不同,西方观察中国的参照点源自西方的价值标准和利益诉求,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进步很快时,西方还在批评中国太不民主、过于专制。中国社会现在并不缺少自由,抛开媒介的丰富程度,信息公开条例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但是在正式的媒介表达尤其是官方语言里,其表达还是有很大的限制。为什么我们总觉得自己进步很大,但是外国人并不认可这一点?恐怕我们自己也有某些根本性的不足。就像我们做社会调查一样,有些指标是反映社会深层的指标,有些指标是中介性的指标,还有些指标是显示性指标,显然我们在显示性指标方面的呈现做得不够,我们没有把自己具有本质意义的进步一面展示给别人,就像我这人很好心,但总是说些不那么让人爱听的话,这样双方就会产生误解,这恐怕是目前对外传播效果不够好的症结所在。
我个人并不觉得中国本身的自由程度有太大的问题,其实中国目前的自我决策、自由程度还是很充分的,而在政治表达、正规表达方面,我们的确还有很大的欠缺,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国内的传播体制对于传播空间的严重约束。常常有人提出对外报道和对内报道实行“双轨制”,我认为“双轨制”虽然可以给对外传播以某种相对宽松的行动空间,但这种宽松是极为有限的,国内的传播体制和传播模式不做深刻的变革,对外传播模式的变革及其传播效果的提升就缺少现实的基础。因此,解决国际话语权的问题,不能仅仅从对外传播的狭隘思路着手,必须与国内传播体制和传播模式的相应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