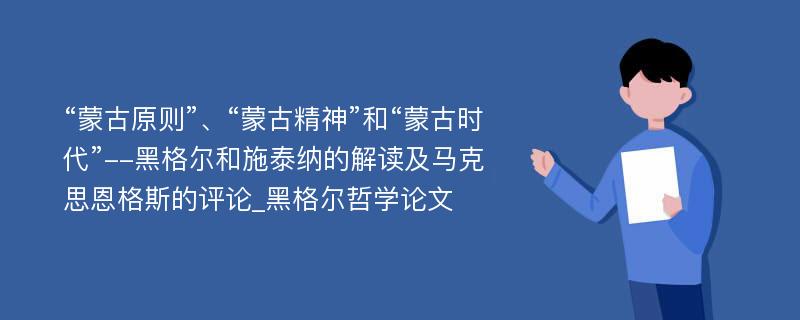
“蒙古原则”、“蒙古精神”和“蒙古人时代”:——黑格尔、施蒂纳的阐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蒙古论文,恩格斯论文,黑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蒙古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所鼓吹的历史观时写到:“当这些理论家们亲自从事编篡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匆匆忙忙地越过过去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蜕化为普遍争吵的历史”。[①]这里所说的“蒙古人时代”出自麦克斯·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该著作中,施蒂纳极力宣扬对精神力量的崇尚,使用了“蒙古精神”、“蒙古人时代”等术语,认为任何历史都是“精神”力量的一种体现。显然,这些观念承袭自黑格尔的学说,甚至“蒙古精神”这一术语也是施蒂纳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说的“蒙古原则”改造而来的。那么,“蒙古精神”、“蒙古人时代”究竟所指为何?马克思、恩格斯又是如何评论的,笔者愿就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施蒂纳是根据黑格尔所提出的“蒙古原则”而“造出了‘蒙古精神’这个概念”。[②]因此,若想揭示施蒂纳的“蒙古精神”这一概念,就要首先从黑格尔所说的“蒙古原则”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黑格尔哲学中始终都贯穿着历史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体现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哲学思考。正如恩格斯所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其著作“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③]然而,黑格尔的历史观、辩证法是建立在“绝对观念”的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其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性质。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都是“绝对观念”自我演化的结果,人类历史也不过是“绝对观念”“自我运动”“自我认识”的一个阶段或曰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历史总是表现为一种有内在必然性的合理的运动过程。他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理性’是万物的无限的内容,是万物的精华和真相”。[④]而“精神是自在自为的理性……世界历史是理性各环节光从精神的自由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⑤]世界既然是理性的产物,那么理性支配下的世界又是如何发展的呢?黑格尔认为,理性支配下的世界经历过许多阶段,呈现出各种形式,不断推陈出新,由不完善到完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精神’经历了这种发展阶段的行程,才取得它的真理和自觉。这些阶段的各种形态就是世界历史上各种的‘民族精神’,就是它们的道德生活、它们的政府、它们的艺术、宗教和科学的特殊性”。[⑥]这就是说,世界历史所经历过的每一阶段都体现着这一或那一民族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是“精神”在不同进展阶段中的特殊表现。世界历史便是以“民族精神”更替的形式来发展的。
黑格尔按照他自己所构想的“精神”发展的原则对历史的进程作了具体的阐释,宣称世界历史发展的顺序是: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这四类世界相应地代表着“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东方世界是历史的幼年时期,这包括中国、蒙古、印度和波斯;希腊世界是充满诗意和活动的历史的青年时代——已经开始涉足“精神”的园地,“表示着精神生命青春的新鲜、欢欣的状况”;罗马世界是人类的壮年时代,罗马对世界的贡献便在于抽象的普遍性——“一切‘神明’和一切‘精神’固结在世界统治的万神庙里”;日耳曼世界则是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标志着“精神”的成熟时代——“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⑦]
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开端赋予了东方,他认为东方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意识——“实体的精神性”,这时,“精神”还没有取得“内在性”,尚未脱离天然的精神状态,这也是为什么黑格尔在谈论东方民族时很少使用“民族精神”而较多地使用“民族原则”这一术语的原因所在。在黑格尔看来,东方人没有认出自己的意志,不知道精神的本质是什么,东方人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这个人就是专制君主,所以,“神权专制政体”便是东方世界的原则。东方世界虽有共同的原则,但每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东方民族在“民族原则”上又都拥有各自的特殊性。他说“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两者都把大家长宪法作为原则——在中国,这个原则经过修正,使一种有组织的世俗的国家生活得以发展;而在蒙古人方面,把这个原则集中起来,取得了一种精神的、宗教的主权的简单形式”。[⑧]在此,黑格尔特意指出,“蒙古原则”的特质在于“蒙古人的精神主权,他们的元首便是喇嘛,被尊敬如一个上帝。在这个精神的帝国里,任何世俗的国家生活都不能够发展起来”。[⑨]黑格尔还专门分析了地理环境对蒙古人的生活习俗、精神面貌的影响,认为高地和宽阔的草原上的人们的生活是“家长制的生活”,他们的财产不在于固定的土地,而在于随他们一同漂泊的畜群,这也决定了高原人的好客、冲动的民族性格,他说“蒙古人用马乳做饮料,所以马匹是他们作战的利器,也是他们营养的食品。他们大家长制的生活方式虽然如此,但是他们时常集合为大群人马,在任何一种冲动之下,便激发为对外的活动”。[⑩]应该说,黑格尔生活的时代,欧洲人对蒙古民族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这种对蒙古人的认识,不仅来自13、14世纪西方使者、方济各会的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撰写的《蒙古史》、法兰西路易九世使团首领威廉·鲁不鲁克撰写的《东游记》以及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等,也来自17、18世纪同样是用欧洲文字撰写和出版的《大鞑靼里亚》、《伟大的成吉思汗史》、德几涅的《通史》等多部有关蒙古民族的研究著作。而且,19世纪初,由于资产阶级历史学和东方学的普遍兴起,欧洲的蒙古学研究“获得了新的动力”(11),从而使西方人能够对蒙古人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无疑,黑格尔在谈及“蒙古原则”时所说的作为历史范畴的蒙古人不单指13、14世纪叱咤欧亚的蒙古大军,亦包括清代佛教化了的蒙古民族。黑格尔还特别强调佛教对蒙古人的影响,认为喇嘛教使得喇嘛教化了的民族能够把“精神”的普遍性放在心目之中,“这种‘精神’实体的‘统一’实现在喇嘛的身上,喇嘛乃是‘精神’自己所由表现的形式”。他说“蒙古人——满布亚细中部直到西伯利亚,受着俄罗斯人的统治——礼拜喇嘛;和这种礼拜方式相密切结合的,便是一种简单的政治状况、一种家长制的生活;因为他们根本是一个游牧民族,只偶然才发生骚动,那时候他们都仿佛发了狂,这巨大的部落就好象怒潮一样地向外冲决”。(12)接下去,黑格尔在谈论了达赖喇嘛、班禅以及喇嘛教与“精神”的关系之后,又写到“蒙古人主要信奉喇嘛教——佛教的一派,对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非常敬重,他们把蔬菜作主要食物,不肯宰杀任何动物,就是对于虫、虱也不忍加害。这种喇嘛教代替了萨满教,就是巫术左道的宗教。萨满——萨满教的巫师——饮醉烈酒后狂跳猛舞,同时口念咒语,仆卧地上,随后喃喃不绝地说出来许多话,就算是神鬼所授给的。自从佛教和喇嘛教占领了萨满教的地位以来,蒙古人的生活便变为简单、有定,而且通行着家长制度。他们在历史上有所表现时,他们引起的推动力量……成为历史发展的初步工作”。(13)这就是黑格尔眼中的蒙古人和蒙古原则。
无庸讳言,从历史发展的史实来看,古希腊、罗马的盛世在前,蒙古民族的崛起在后,而黑格尔却把蒙古民族放在古希腊、罗马之前,将整个东方民族置于历史发展的初始阶段的位置上,使各个民族变成“精神”发展的逻辑环节和工具,这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本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正象马克思所评价的,在黑格尔哲学中,“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整个复归,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想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14)恩格斯也指出,“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人类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5)这也正是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局限所在。
二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现代德国哲学”自居的德国哲学家麦克斯·施蒂纳便承袭了黑格尔的学说,撰写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等著作,利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圣经》中有关精神统治世界的观念,进一步宣扬对精神力量的信仰。麦克斯·施蒂纳是约翰·卡斯巴尔·施米特(1806—1856年)的笔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他时,除使用“麦克斯·施蒂纳”这一原有笔名外,还用了诸如“圣麦克斯”、“圣师”、“圣者”、“桑乔”、“柏林小市民”、“乡下佬雅各”、“堂吉诃德”等外号来讽刺他。
如前所述,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学说中将历史的进程图解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而麦克斯·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则将整个历史的发展简化为儿童、青年和成人三个阶段。儿童就是指“黑人”,“黑人般的人代表古代,对事物的依赖”,是唯心主义;青年是“蒙古人”,“蒙古人般的人代表依赖于思想的时代,基督教时代”,是唯心主义;而成人是“高加索人”,是唯实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否定的统一。(16)以此为框架,施蒂纳展开了他对“精神”和“历史”的理论论述,进行了一系列“历史命名”。他说“精神是精神世界的创造者”,“它的创造物就是它的世界”,而黑人是历史的童年时代,儿童——黑人时代就是指古代社会,塞索斯特雷斯远征、拿破仑远征埃及、天主教以及古希腊、斯多噶派的伦理学、怀疑论者和伊壁鸠鲁主义等都属于黑人时代。黑人——古代人力求洞察“事物世界”,他们不知道思想本身,“只能显示世俗的智慧”,因而属于唯实主义。(17)在施蒂纳的笔下,“蒙古人”是“近代人”、“青年”、“基督教”。近代人力求洞察什么呢?近化人力求洞察精神世界,他说“在古代人看来,世界是真理”,而“在近代人看来,精神是真理”,“这种真理就是近代人力求洞察它的非真理性而且最后的确洞察到了的真理”,是唯心主义。(18)在近代人的范畴内,施蒂纳又杜撰了“纯粹的诸精神史”,“不纯粹的诸精神史”,“教阶制”等抽象的概念,说什么处于蒙古人状态中的精神,就是精神中的精神,也就是基督教徒心目中的想象的本质。而天主教等同于中世纪,是黑人,新教则是近代范围内的近代,是蒙古人。新教内部又包括英国哲学和德国哲学,英国哲学本质上属于唯实主义,是儿童、黑人,德国哲学属于唯心主义,是青年、蒙古人。在“教阶制”内,黑人是“无教养者”、“利己主义者”,蒙古人是“有教养者”、“自我牺牲者”、“善人”;从“无教养者”中产生了非黑格尔主义,而从“有教养者”中产生了黑格尔主义。(19)可见,施蒂纳的历史理论是完全围绕着儿童(黑人)——青年(蒙古人)——成人(高加索人)这一三段式展开的,“蒙古人”不过是其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所谓“蒙古人时代”这一范畴所指范围很广,且前后相抵牾,概而言之,是指青年、对物质世界的否定、思想世界、新教徒、德国哲学、有教养者、唯心主义、黑格尔主义者等。(20)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理论论述,纯粹是一种“历史命名”,就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判的,“唯一者的全部历史是围绕着儿童、青年和成人这三个阶段兜圈子的,这三个阶段又具有‘各种转变’,兜着愈来愈大的圈子,最后直到事物的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历史被归结为‘儿童、青年和成人’为止”。(21)
在施蒂纳的“历史虚构和命名体系”(22)中,施蒂纳还进行了种种“历史的反思”,主要是“对于我们的蒙古精神的历史的反思”,他说:“匈奴和蒙古人一直到俄国人的远征都属于蒙古人时代”,蒙古人时代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同于“古代人”,“在我们的蒙古人时代,任何改变只是改良、改善,而不是破坏、毁灭或消灭。实体、客体依然存在着”,在此,施蒂纳修改了黑格尔的观点,他接着说“人靠习惯即可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并且建立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感到像在家乡和家里一样——也就是说,给自己创立天国。要知道‘天国’除了它是人真正故乡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在那里就不再有任何影响使他排斥自身了”。(23)经过一系列历史的反思之后,施蒂纳终于得出了“蒙古精神”的要旨——“努力为精神争取自由,这就是蒙古精神”。(24)
不难看出,施蒂纳的历史理论是从黑格尔那儿剽窃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施蒂纳的全部历史反思……是由黑格尔思想的片断拼凑起来的”,施蒂纳是“黑格尔的‘笨拙’的抄袭者”。(25)施蒂纳所阐述的“精神”、“民族精神”、历史进程等完全改编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但这种改编不是进步,而是一种思想倒退。如果说,黑格尔有关“民族原则”、“民族精神”的论述还能联系到各民族的宗教、伦理、立法、风俗、科学、艺术等具体内容的话,那么,施蒂纳所说的“民族精神”,包括“蒙古人的天国”则纯粹是一种与具体民族无关的抽象的思辨的东西了。黑格尔在谈论民族精神时非常强调一个民族的“整个的现实”,他说“民族宗教、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26)就是在论述蒙古人和蒙古原则时,黑格尔也没有脱离蒙古人所处的地理环境、游牧生活、历史影响、萨满教、喇嘛教等,并且将游牧生活的实质、萨满教和喇嘛教的影响等纳入“蒙古原则”的范畴之内,得出“神权专制政体”、“家长制的生活”是“蒙古原则”的实质所在。而施蒂纳在论述“蒙古人时代”、“蒙古精神”时,虽然引进了“天国”等被认为是来自蒙古民族本身所固有的思想观念,但经施蒂纳的阐释之后,“蒙古人的天国”连同“蒙古人时代”、“蒙古精神”等变成了与现实的蒙古民族毫无关联的抽象名词了。总之,施蒂纳把“思辨的观念变成了历史的动力因此历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哲学史。然而,就是这种哲学史也不是根据现有材料所载的真实面貌理解的,至于如何在现实的历史关系的影响下发展,则更不用说了……这样,历史便成为单纯的先入之见的历史,成为关于精神和怪影的神话,而构成这些神话的基础的真实的经验的历史,却仅仅被利用来赋予这些怪影的形体,从中借用一些必要的名称来把这些怪影装点得仿佛真有实在性似的”。(2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最后还不无讽刺地说,黑格尔在阐释其历史哲学时没有脱离“辩证法”,而“‘施蒂纳’所不同于黑格尔的地方是:他不靠辩证法而完成了同样的事”。(28)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46页。
②同上,18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21页。
④〔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47页。
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352页。
⑥同④,93——94页。
⑦同④,268,323,387页。
⑧同④,157页。
⑨同④,158页。
⑩同④,133页。
(11)〔苏〕马·伊·戈尔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49页。
(12)同④,214,213页。
(13)同④,21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6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43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08页。
(16)〔德〕Max Stir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verlag von Otto Wigad,1845.汉译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74页,133页。
(17)同上,155,133——136,151页。
(18)同上,151页。
(19)同上,133——135页。
(20)同上,209页。
(21)同①,131页。
(22)同①,174页。
(23)同①⑥,174,175,177页。
(24)同①⑥,181页。
(25)同①,182,183页。
(26)同④,104页。
(27)同①,131——132页。
(28)同①,211页。
标签: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哲学家论文; 恩格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