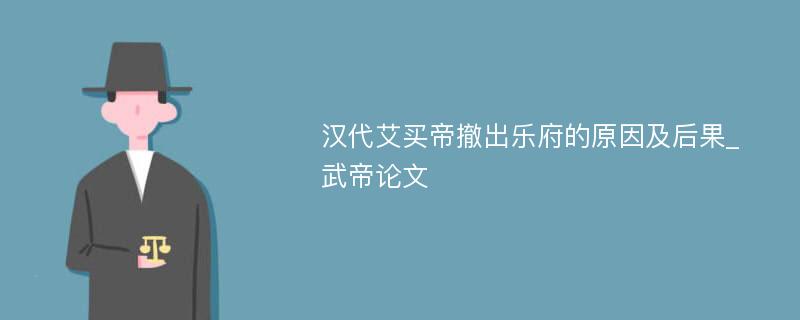
汉哀帝罢撤乐府的前因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哀帝论文,乐府论文,前因后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汉代乐府的发展中,武帝的扩建乐府机构和哀帝的罢撤乐府人员,是两件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事件。但综观历代乐府诗研究,前贤今哲往往将视点放在前者,努力考索其情况,挖掘其意义,而对于后者,却缺少必要的关注。为此,本文即试图通过对哀帝罢撤乐府情况的分析,来探讨其原因、它与当时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以期有助于汉乐府的系统研究。
一、哀帝罢撤乐府情况分析
汉和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六月, 刚刚即位才两个月的哀帝刘欣下诏“其罢乐府”(《汉书·哀帝纪》),诏书说:
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夫奢泰则下不孙而国贫,文巧则趋末而背本者众,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熟朴家给,独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
根据这一诏令,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等研究了罢撤乐官的具体内容,并立即奏可施行。分析孔、何当时的奏疏(见《汉书·礼乐志》),我们可以看出如下一些情况:
1.自武帝扩建乐府之后,宣、元、成诸帝虽都裁减过乐府人员(见《汉书》诸帝纪),但到成末哀初时,乐府所属人数仍达829 人(实为824人),该机构已成了当时国家机关中最为庞大的官署之一。
2.从当时乐府音乐的用途看,被哀帝保留人员除了刚、别、柎员、给《盛德》主调篪员、钟工员、罄工员、箫工员、听工、夜诵员、仆射共十五人外,其余的郊祭乐人员、大乐鼓员、《嘉至》鼓员、郊祭员、诸族乐人兼《云招》及兼给事雅乐、邯郸、江南、淮南、巴渝、楚严、梁皇、临淮、兹邡、骑吹、歌鼓员共二百七十六人,除了大乐鼓员六人外,余下的二百七十人全部用于祭祀南北郊,而被罢撤的沛吹、陈吹、商乐、东海、长乐、楚、缦乐、族歌鼓员以及楚四会员、巴四会员、铫四会员、齐四会员、秦倡员、诏随秦倡、蔡讴员、齐讴员、常从倡、常从象人、诏随常从倡、秦倡象人员、雅大人员、竽瑟钟罄员、治竽员共二百八十五人,则全部用于朝贺置酒为乐或朝贺置酒、陈前殿房中,都是不应经法的音乐。这种情况说明,哀帝罢撤乐府时是很注意乐府所管音乐的用途的,只要是用于祭祀的音乐,则全部保留,而用于朝会宴享的娱乐音乐则一概罢撤。哀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必须联系武帝当时扩建乐府的目的来理解。根据《史记·孝武本纪》、《史记·佞幸传》、《汉书·礼乐志》等书所记材料,我们可以肯定,武帝当时扩建乐府机构,并不像以前研究界所特别强调的那样,是为了“采诗以观风俗”,而是为郊祀之礼配乐,虽然因为武帝爱好新声,当时的乐府机关确实采集了一些诗歌,但是这些诗歌在当时却只是“重声不重义”。宋郑樵在《通志·乐略》中说:“武帝定郊祀,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则有赵、代、秦、楚之讴,莫不以声为主。”元吴莱在《论乐府主声》中也说:“及武帝定郊祀,立乐府,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作为诗赋,又采赵、代、秦、楚之讴,使李延年稍协律吕,以合八音之调。如以辞而已矣,何待协哉!必其声与乐家牴牾者多。”由此可见,哀帝罢撤乐府可能是想恢复武帝时的传统,并非完全像他诏书中所说的是要彻底恢复雅乐。
3.从当时乐府的乐种来看,被哀帝所保留的部分有两种,一是雅乐,一是地方乐种,而被罢撤的则全是地方乐种和俗乐,其中象楚四会员、巴四会员、铫四会员、齐四会员、蔡讴员、齐讴员、雅大人员、竽瑟钟罄员都属于郑声(参见吉联抗辑译《秦汉音乐史料》所列《乐府撤销时人员及处置情况表》。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由此可见,自武帝以后,乐府人员的增加,大概主要在于俗乐或称郑声。如果我们联系史籍所记载的宣、元、成诸帝及大臣对俗乐的爱好,则更能看出这一点。《汉书·霍光传》记昌邑王好乐说:“大行(昭帝)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会下还,上前殿,击钟罄,召内泰壹宗庙乐人辇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众乐。”《汉书·史丹传》载:“建昭之间,元帝被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聩铜丸以隤鼓,声严中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汉书·张禹传》载:“(张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戴)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子弟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汉书·元后传》载:“五侯群弟,争为奢侈……罗钟罄,舞郑女,作倡优。”“先帝弃天下,(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这就使得原来主要用于祭祀的音乐变成了“娱乐音乐”,这与哀帝时的社会状况已很不适应,而且还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武帝扩建乐府机关以后,历经昭、宣、元、成几代,乐府音乐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人数极度增加,连性质也有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已预示了乐府机关的改革。
二、哀帝罢撤乐府的思想背景
前人在解释哀帝为什么罢撤乐府的原因时,一般沿用班固的看法,认为是哀帝“性不好音”(《汉书·礼乐志》),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在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中,最高统治者的好恶在国家制度及其机构的变化中,必然发生巨大影响。但是,我们必须追问的是,为什么哀帝一上台,在其他诸事未办的情况下,就下诏罢乐,且规模如此巨大,速度如此之快,并能得到完全贯彻实施?我们认为,上面所作的分析是其中的内因,而自昭帝时起整个政治、思想领域掀起的对武帝朝诸政策的反思和批判思潮则是此次行动的外因,哀帝个人的性格至多只是一个契机。
众所周知,汉代发展到武帝时,整个国力已十分强大,但由于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大兴土木,巡行封禅,求仙问药,从而又严重削弱了国家基础。武帝之后,整个社会矛盾重重:经济凋蔽,皇权旁落,外戚专权,贵族豪门奢侈靡费,思想界复杂混乱,所有这些矛盾可以说已危及到汉王朝的生存。面对此种局面,一些正直朴实的思想家展开了连续的批判,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潮。这股思潮,以救治刘姓皇朝为旗帜,以反对贵族外戚奢泰专权为突破口,以经学复古为理论武器和思想成果,从昭帝时的“盐铁会议”一直持续到王莽秉权时的“托古改制”。
礼、乐乃教化之本。作为这股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武帝以后,思想领域也曾围绕着音乐的雅、俗问题展开过一些斗争。早在武帝时,就有河间献王试图以雅乐对抗武帝的新声。“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只是由于他们本身对雅乐也不明其意,加之武帝特好新声,故“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汉书·礼乐志》)到宣、元之际,以“明经洁行著闻”的大臣贡禹更是言辞激切地上书:“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于陛下,臣禹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论语》曰:‘君子乐节礼乐。’方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他还进一步建议:“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饰器物,三分去二。”(《汉书·贡禹传》)匡衡也上疏说:“宜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汉书·匡衡传》)在这些咄咄逼人的抨击下,宣、元帝都不得不裁减乐府人员。但这也不过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因此,到成帝年间,传承河间献王礼乐思想的谒者王禹及弟子宋晔等又一次上书推荐雅乐,大夫博士平当也帮腔说:“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今晔等守习孤学,大指归于兴教助化。衰微之学,兴废在人,宜领属雅乐,以断绝表微……诚非小功小美也。”(《汉书·礼乐志》)然而,这次主张仍因“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而最终未能施行。其时现实反而是“郑声尤盛,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汉书·礼乐志》)
哀帝就是在这种局面下登上皇位的。他眼见得西汉王朝日益贫弱,宫廷大权逐渐被王氏家族蚕食,于是决意整理朝政。而哀帝和他的前辈们的最大不同,在于他企图用改革前朝旧制的方法来重振汉室的雄风。他不但罢三公,罢州牧,临朝“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汉书·哀帝纪》赞),而且借助宦官打击外戚势力,利用政治权力压制阴阳灾异说,并扶植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以为改制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规模庞大且“郑声尤盛。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汉书·礼乐志》)的乐府机构就也了哀帝罢撤的目标。或许,这还是哀帝整个“改制”活动的先声和试验。因为,虽然“礼、乐为教化之本”,但相对于其他政治、经济大事来说,乐府的地位在封建国家的机构中毕竟轻小得多,它的罢撤所触及的利益者也毕竟只是一些地位低下的乐人,更何况,乐府发展到如此庞大、淫靡的地步,并成了外戚专权的一个标志,罢撤它不但不会激起反对势力的对抗,甚至还可能因在反外戚、除积弊这一点上得到各方势力的支持和赞同,阻力要比其他改制小得多。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哀帝才会在上台只两个月就下诏对乐府机关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撤减整顿,其施行起来也能如此顺利。
三、哀帝罢撤乐府的影响
由于乐府本身的“变质”这种内在特点和西汉后期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共同作用,盛极百年的乐府机关发展到哀帝时,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么,作为一种文化措施,这种变化又蕴涵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呢?换句话说,哀帝这种大规模的裁减乐府人员和乐种,对于其后的文化建设发生了哪些影响呢?我们认为,这种变化自然首先表现在音乐和文学两个方面。
其一,因为哀帝罢撤乐府的主要内容是所谓“淫靡”的郑声俗乐,并将一些可能不太“淫靡”的地方乐种归入了雅乐系统,这就不但造成了这些民间音乐(即所谓的郑声俗乐)的散失消亡,而且影响了其时音乐的发展方向。本来,民间俗乐来自于社会下层,发乎下层人民,不管封建统治者如何理解、看待、使用它们,甚或作某种程度的加工改造,但其核心却仍是反映人民的心声的,客观上是可以“观风俗,知厚薄”的,它们与那些刻板枯燥的“庙堂音乐”、“祭祀音乐”相比,也是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音乐。哀帝的罢撤无疑割断了这一传统,使活生生的人民音乐可能因得不到保存而逐渐散失。虽然由于整个社会“湛沔日久”,它在下层人民中一定还在流传,但在古代那种官府垄断式的文化传播方式之下,这些音乐的保存自然只能走自生自灭的道路,这显然是中国音乐的一大损失。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辩证的看问题,就会看到这种损失也有其正面的价值。因为从文学的角度看,哀帝罢撤乐府,虽然阻碍了音乐的发展,但却又促使了诗与音乐的分离,为诗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前面我们曾经指出过,乐府在武帝时就带有严重的“重声”性,之后,随着乐府音乐娱乐性的增强,这一特点则更趋明显。这就使诗逐渐成了音乐的附庸,对诗歌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在我国诗歌的发生期,它们往往与音乐结合在一起,但当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诗又必须摆脱音乐的束缚(一般是转而通过声律来实现它们脱离音乐之后诗本身的节奏性乐感)。古代诗、词、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特点。当然,这种分离有时是渐进的,有时是突发性的,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则是不自觉的。哀帝罢撤乐府属于后者,是非目的性的,但却在客观上将武帝以来逐渐走向程式化的音乐系统割断,从而使创作者和接受者都将注意重点由声转向义,也就使诗逐渐地获得了意义上的明确性。东汉时民歌的音乐性减弱、政治性加强的特点实际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实现的。
对于乐府的这种“声失而义起”的现象,前人也曾进行过研究。郑樵在《通志·乐府总序》里说:“今乐府之行于世者,章句虽存,声乐无闻,崔豹之徒以义说名,吴兢之徒以事解目,盖声失而义起,其与齐、鲁、韩、毛之言诗,无以异也。乐府之道,或几乎息矣。”他甚至说:“武帝定郊祀,立乐府,采诗夜诵,则有赵、代、秦、楚之讴,莫不以声为主,是时去三代未远,犹有《雅》、《颂》之遗风。及后人混于名义,是以失其传……然使得其声,则义之同异,又何足道也。”吴莱在《论乐府主声》中也说:“古者乐府之说,乐家未必专取其辞……辞者特声之寓耳,故虽不究其义,独存其声也……奈何后世拟古之作,曾不能倚其声以造辞而徒欲以其辞胜,齐、梁之际,一切见之新辞,无复古意。至于唐世,有以古体为今体,《宫中乐》、《何满子》,特五言而四句耳,岂果论声耶?他若《朱鹭》、《雉子班》等曲,古者以为标题,下则皆述别事,今仅形容二禽之美以为辞,果论其声,则已不及汉世儿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乐府为哉?”郑、吴二人指出乐府古朴而后世拟作有时往往专事斗辞营巧的情况,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却不知道,“文不新变,不能代雄”,文学的发展必须不断的创新,才能逐渐进步。乐府的发展自然也不能例外。东汉以后,古诗的出现和成熟,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其二,乐府机关从武帝时起,虽然主要的目的在于为郊祀之礼配乐,但因为武帝特好新声,而这些“新声”主要来自民间的俗乐,故而在求乐的同时也就自然的采集了许多文字式的诗。这些文字式的诗,同样反映了人民的思想、生活状况。但经哀帝罢乐之后,这些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也就随之散失(这是乐府重声的特点所决定的)。萧涤非先生在三十年代就曾痛切于此,他说:“《相和歌辞》外,《杂曲》中亦有民间之作,综计约三十余篇,当为汉乐府之精英,以其价值不仅在文学,且足补史传之阙文,而使吾人灼见当日社会各方之状况也,然在当时,则此种作品,地位似甚低,缙绅之士,悉狃于雅、郑之谬见,以义归廊庙者为雅,以事出闾阎者为郑,故班固著《汉书》,于《安世》、《郊祀》二歌,一字靡遗,而于此种民歌,则惟录其总目,本文竟一字不载。”(《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萧先生将西汉民歌的散失归咎于班固,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推本溯源,恐怕还应归因于哀帝的罢乐。
然而,问题同样存在着另一方面。虽然哀帝的罢乐,并不是彻底地取消乐府机构,而是裁减人员,但毕竟促使了乐府机构的萎缩。哀帝之后,是否仍然存在乐府机关,史无明文,近代以来,有人根据史籍中的一些材料推断,其后仍有乐府机构(参见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二编第三章)。但是,正如聂石樵师所指出的那样,哀帝之后,尤其是东汉时期,乐府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变化。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中概括说:“西汉采诗乃为音乐之要求,东汉则全为政治之需要。”(《两汉卷》第36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说,此时采诗已不为乐,而是将之与朝政制定和官吏升黜结合起来。这种由音乐向政治的转变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这样一来,真正反映人民心声、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街陌谣讴”就有了上达和保存的可能。当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自然有许多变样,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弄虚作假的现象,如《汉书·王莽传》所记载的,平帝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司直陈崇等八人分行天下,观览风俗,但他们却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又如《后汉书·刘陶传》记载,灵帝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但这些公卿对于贪污秽浊、又与宦官有密切关系的太尉许戫、司空张济等人却不敢问。但有时候这种措施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后汉书·雷义传》所载,顺帝时使使者行风俗,就一下子黜免太守令长七十人。这些“风俗”、“谣言”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说明它们确实是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的。从现存的东汉乐府民歌的内容来看,绝大多数乃是真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饥者、劳者之歌,自然是这种情况的记录。这些作品不但绘成了一幅形象的汉代社会生活史,而且使由《诗经》民歌发端的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绍继并进一步发扬光大。当然,乐府裁撤之后的这种积极影响,自然是哀帝没有预料到的,也是他所无法预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