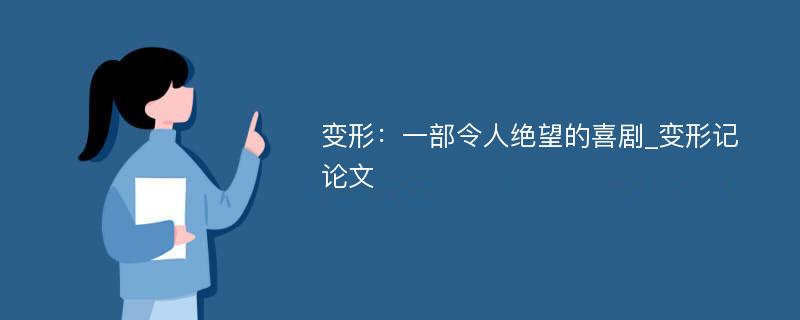
《变形记》——绝望的喜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喜剧论文,绝望论文,变形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卡夫卡,人们已经说得够多了。现代派引他为同调,后现代视他为先辈。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主义看到了一个充满灾难性预感的动荡世界;超现实主义品味出一个扑朔迷离,亦真亦幻的梦魇世界;宗教主义感受到一个体现惩罚与仁慈的信仰世界;存在主义发现了一个交织着自由,迷调与希望的荒诞世界;举凡种种,不一而足。因而,我们这里试图探讨的有关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主人公变形一题,自然未出各位论家早经涉略的畛域。但毕竟思考问题的角度往往因人而异,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本文就是本着这种态度一抒己见,以冀能从一个多少不同的视点昭示出卡夫卡笔下艺术形象所具有的二十世纪文学的现代性特点。
表面看来,《变形记》大体恪守着传统文学的表现方式。这部作品情节单纯,细节真实,语言质朴,在技巧上没有任何故弄玄虚之笔,但它还是在在显示着现代作家的崭新风貌——这主要得力于卡夫卡对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的独特处理——变形。
《变形记》的主人公是卡夫卡笔下一个不同凡响的特殊人种:“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①小说以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事件,开始了它平静而略带嘲弄的叙述。就是这开卷伊始的神来之笔,为小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深刻内蕴,也为后世凭添了许多笔墨之争。这一变形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类比?抑或寓言?是表现了“反抗”的主题?还是传达了受难的涵义?——可谓见仁见智,言人人殊。在此,笔者不揣愚鲁,也拟对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问题一陈鄙见。
我们认为,在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千百年来一直奉行着一条可以称之为“类型化”的艺术创作准则。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经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而拉辛而莫里哀,直至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作家,艺术形象的塑造一般都依据着人物身份、地位、年龄、职业等等的不同,或勇武,或机诈、或高尚、或虚伪、或豪侠、或悭吝。人们不难对他们一个个地进行认同归类。只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在十九世纪的一批优秀作家那里,艺术形象的创造才获得了新的突破。作家们在继承“类型化”的表现传统之外,又格外注意赋与艺术形象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可以说,“一个人的遭遇,”往往成为十九世纪大多数作家关注的中心。及至十九世纪末期,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许多令人眼花瞭乱的变更和动荡;科技飞跃,经济恐慌,劳资冲突,战争革命。特别是在卡夫卡生活的欧洲,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似乎急剧膨胀,危机一个个纷至沓来。就文学而言,“一个人的遭遇”已远远不能将这一切解说明白,传统艺术创作中的那些有关勇武、机诈、高尚、虚伪、豪侠、悭吝的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在现实生活面前显得尤其苍白无力。时代呼唤新的作家,作家也需要表述迥异以往的时代。卡夫卡的创作就是在这种契机下应运而生的。他敏感而准确地捕捉到时代的困惑,在对它们的艺术表现中再次突破了十九世纪以前的传统文学写作方法的樊篱。《变形记》的主人公既不同于果戈里笔下那个一心一念担忧开罪了上司的小职员,也有别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刻划的那个充满思想激情的地下室人。如果没有变形,他简直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而且即便是在变成甲虫之后,他的思想意识也没有一丁点儿超出常人的思想范畴。某种意义上,他正象卡夫卡所认识的自己:“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和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了进来,这个时代与我可贴近呢,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②格里高尔·萨姆沙也是这样,相对而言,他身上缺乏一种标志着个人独特品格的规定性,他是他这个时代人类最一般的代表。对这样一个人物,人们既不会特别厌恶,也不会特别喜欢,只除了一点,这就是在一天清晨的梦醒之后,他居然能躺在床上,化身而为一只巨大的甲虫。由人到虫的变化已足令人震惊,但更令人惊讶不已的却是主人公的反应。格里高尔·萨姆沙除了为变形可能给他的差事带来的麻烦而苦恼外,对自己一夜之间由人到虫的兑变反倒颇能处之泰然——这倒不能不引人深思。试想,如果你不是对某一桩十分超常的事物业经习已为常、见惯不惊的话,你怎么可能不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性巨变吓得魂飞魄散、痛不欲生呢?换言之,如果格里高尔·萨姆沙不是早已对这只悄悄盘距自己体内的大甲虫业已十分稔熟的话,他怎么可能面对变形的突然打击而依然镇定若素呢?这里,如果我们参阅一下卡夫卡早些年写下的另外一篇作品《乡村婚事》,或许可以找到有关这只大甲虫的最好注脚。
在《乡村婚事》中,主人公拉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人们在公务机关中操劳得这样过分,但并没有因为做了所有的工作而获得被大家爱戴的权利,反而孤孤单单,完全生疏,只不过是猎奇的对象……”③
为此他心灰意冷,对生活感到厌倦,因为在如此陌生的人世间,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都将是徒劳无益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要求,至少是为了装点门面,他也需要作出某种举动,就此,他只好这样自慰:
我不需要自己到乡下去,用不着这样。我打发我的穿戴衣冠的躯体到那里去。……而我呢?我在此时卧在床上,身子裹在滑溜溜的黄褐色被子里。我觉得,在我卧在床上时,我的形体是一只大甲虫,一只鹿角虫或金龟子。④
于是,这种对生活的穷极无聊的厌倦在《变形记》中便寄托在格里高尔·萨姆沙所化成的大甲虫身上。也就是说,格里高尔·萨姆沙比拉班更其决绝,他干脆变作一只大甲虫,而不是仅仅在想象中如此期望而已。
事情的发生就象在童话中一样:正当某个陷入不幸的人愤愤不平地沮咒:“为了×××事,就是让魔鬼拿走我的灵魂我也情愿”的时候,魔鬼应声出现,出其不意地攫去了这个倒运的家伙的灵魂。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萨姆沙醒来之后,一边打算着起床穿衣,赶上上班的早车,一边想到自己目前生活和工作的恼人处境,不禁怒火中烧,发出诅咒“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就在这个瞬间,他感到肚皮上有点发痒,于是伸出一条细腿去搔,可一触到自己的新身体,他就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其中发生的变化,立即浑身起了一阵寒颤。也即是说,就在格里高尔刚刚道出希望魔鬼为他解脱生活的一切烦扰的刹那,他便真的变成了一只与人类社会绝缘的大甲虫。这样看来,这只大甲虫不是别的,正是格里高尔·萨姆沙对生活所感觉到的断念或者说绝望。在他发出诅咒的当口,那股时时在他下意识中《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即“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点明了变形的潜意识来源,)涌动着的绝望之念象魔鬼一样攫获了他,象一只大甲虫一样占有了他,使他在劫难逃。正因为这种绝望的体验在格里高尔显然并不陌生、因而自然不会引起他的震惊,他甚至还曾一度自信能够从中挣脱出来,重新过上以往那种虽浑浑噩噩却又极为正常的普通人的生活。然而,当“大多数人象在睡梦中斗争,就象做梦的人挥动着手想要赶去梦见的东西一样”⑤的时候,他却已经“从不安的睡梦中”清醒过来了,因而只能陷入更深一层的恶梦之中——他看到了生活中所本不存在的关于“救赎”一类的希望,于是他就此沉沦了,直到死亡。
埃德温·缪尔说得有理:“卡夫卡之所以难懂恰恰是因为他的天才所特有的独创气质,即以具体的形象进行思维。”⑥在《变形记》中,卡夫卡把现代人对自古以来一直奉为圭臬的有关生存意义以及人类最终获得拯救的宗教偏见所感受到的梦魇一般的绝望幻化成占据了格里高尔躯壳的大甲虫的形象。这个具有人的意志的大甲虫——绝望的表征,既非一类人的典型,也不是血肉丰满的鲜明个性,它是现代人类困惑的某一方面的形象化描绘,它把一个不合理性的反常世界以能为理性所解悟的方式勾勒出来,它从普遍人性的角度展示了现代人类的独特性,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强调独特性——绝望。”⑦
但是,现代人类的绝望,显然不再仅仅意味着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在《变形记》中物质上的匮乏尚在其次,精神上的无助得到了显著的突出。主人公虽然工作辛苦些,至少还是不愁吃、不愁穿的,甚至一旦家中发生变故,还有能力雇上佣人。事实上,正象格里高尔·萨姆沙的经历所揭示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绝望更多的是指一种有活路无出路的,虽生犹死的麻木,无奈的孤独与空虚状态,是人对他人,人对生活的自我隔离与弃绝。
表达这种绝望,卡夫卡独出心裁地采用了喜剧方式。这是富于开创性的。他为嗣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艺术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首先,仔细阅读《变形记》的开头,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格里高尔·萨姆沙变形之前,他已经陷入了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负担着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他不仅需要努力工作以使一家人衣食有着,而且还必须加倍辛劳以慢慢抵偿父亲欠下的债款。另一方面,他又对公司的工作及那里的一切极其反感,他讨厌公司里那个盛气凌人的老板,这位老板习惯于坐在办公桌上居高临下地对雇员发号施令,象个高踞于王位之上的暴君。格里高尔但愿能把这个老家伙气得从高高的桌面上一头栽下来。他也讨厌自己的那份工作,这份琐屑的旅行推销员的差事是那样令他疲于奔命,他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也仍是难以胜任。公司的秘书主任在他未能按时上班后前来登门问罪时,就曾指责他工作成绩十分不尽人意,推销出去的商品显著减少,他在公司里的职位也因之而岌岌可危。这就构成了格里高尔必须去工作尽职的责任与他决不愿意再去工作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到他声言让一切都见鬼去的时候,其内部张力已达到极限,尽管他曾经设想以请病假的方式来加以缓解,但在经过认真考虑之后,他只有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公司不相信它的雇员还会生病,在它眼中,“除了健康的懒人之外,再没有第二种病人。”因此,就算他真的病了,还是同样不能逃脱前去上班的责任。按照小说情节的传统描述,人们会预见到矛盾的最终爆发以及伴随而来的冲突和悲剧性结局,但情况却是急转之下,由于格里高尔的变形,便有足够的理由使这一矛盾转眼间化为乌有。谁还能指责一个大甲虫不去上班呢?更为有趣的是,在理智上,格里高尔竟然是并不期望自己化为一只大甲虫而回避工作的,他把“打发自己穿戴衣冠的躯体”上班去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表相与真我间的分裂、期望与实际间的抵牾、意图与结果间的落差,更突出了事物的可笑方面。
第二,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格里高尔·萨姆沙变形本身的喜剧因素。对于这一变形,索克尔曾经在他的《反抗与惩罚——析卡夫卡的<变表记>》一文中正确地指出了其中潜在的反抗的涵义,通过变形,格里高尔隐晦地表示了自己对不人道的现实生活的不满,对冷酷无情的社会的怨怼。但这一变形又是怎样一个不高明的反抗呢?这里我们不妨引用卡夫卡的一段议论:“消灭现世将仅仅是由个人为自己规定的任务,第一,如果现世是邪恶的话,也就是说,世道与我们的本意相矛盾,第二,如果我们确有能力去消灭它的话。第一点看,确实是这样,第二点,我们没有这个能力。”⑧格里高尔一样也没有这个能力,因此,他对社会的反抗,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浮夸的事实。尽管这一反抗并非主动出击,而是以退为守,力图为自己保有一方自由之地,但这还是打乱了世界生活的正常秩序。虽然了那咄咄逼人的可怖姿态曾经取得过骇退前来洞吓他的公司秘书主任的战绩,他那非同寻常的巨大体量也曾使那几个打他妹妹主意的房客感到惊惶不安。但这不过是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实际上,在它那咄咄逼人的巨大体量之下的,是一颗孤独的、怯懦的,极易受到伤害的心,他以这样一颗不堪一击的脆弱心灵来对抗冥顽不化的社会,其结果必然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在格里高尔的这种反抗里,我们不是同样可以看到和堂吉诃德斗风车相类的那种表面上虚张声势、实质上软弱无助的滑稽成份吗?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变形记》的结尾。格里高尔死了,他的干瘪的尸体被扫进垃圾堆里。随后,他的健忘的父母和妹妹愉快起来,一起下乡旅行。在和煦的春光下,他们的脑海中涌现了新的梦想,三人把家里的财产作了重新估算,老俩口在“刚刚获得的安宁”中⑨不禁欣赏起女儿“丰满的身段”来,“在旅途终结时,小姑娘第一个站起来。舒展了几下她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体。他们从女儿的姿态中似乎看到了他们新的梦想得到了证实,他们美好的打算得到了鼓舞。”⑩看来危机已经渡过,生活对这一家子又一次绽开了笑容。但在经历了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之后,这张笑脸又是显得多么讥讽和虚幻。这正是卡夫卡的深刻之处,试想,如果当初格里高尔仅仅是由于劳累过渡而病倒在床,随后又因为病体难支而不治死亡(这是十九世纪的作家们所热衷表现的),那么生活的意义并不会就此消亡,因为“一个人的遭遇”总是带有偶然性的,而偶然的事情发生于此时此地却并不必然地也发生于彼时彼地。但在《变形记》中恰恰由于主人公乃是在绝望——变形之后归于寂灭的,因而作者也就由他的死亡证明了人类生存意义的虚妄。这一结论是具有普遍性的。在这之后再见到格里高尔一家人的欢畅表情便感到格外空洞,因为这时我们还没有忘记小说前部主人公变形发生当天的一小段插曲,“格里高尔试图设想,今天他身上发生的事有一天秘书主任也可能碰到,谁也不能担保不会出这样的事。”(11)这就意味着,绝望这只大甲虫,正如一个附体的不祥的幽灵,他并不会随着格里高尔的寂灭而寂灭,它会不怀好意地继续在生活中游曳,寻找一个又一个牺牲品。相形之下,作者用在小说结尾的那堆令人欢欣鼓舞的词句,诸如“安宁”“青春活力”“新的梦想”“美好打算”等等,便都具有某种诡秘的反讽味道,体现出卡夫卡所特有的含蓄、冷峭的幽默。
可以想见,格高尔·萨姆沙的遭际如果到了雨果、莫泊桑、果戈理等笔下,一定可以敷衍出一篇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小人物的辛酸故事。可在卡夫卡的《变形记》——绝望的喜剧中,他的行动却不免时时令人哑然失笑。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以为,传统艺术观念的瓦解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在十九世纪以前的古曲艺术作品中,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规律的、理性的世界。这个世界中悲剧人物往往是那些维护正义、敢于抗争的非凡英雄,仅仅缘于他们自身属性方面某种不合理性的弱点,才使他们丧失了立足世上的必然性。而喜剧则是嘲笑承担这样一些事件和行为的人物,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违反了人类理性的常规,背离了正常的逻辑准则,使其自身呈现出滑稽、怪诞、荒谬、乖张等等特点,需要人们以理性来予以蔑视和匡正。可是,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原来那个假想之中的理性世界本身,就陷入了违背理性的发展进程。战争、屠杀、破坏、毁灭,人类文明几千年的发展到如今,反而最清楚地暴露了人性中野蛮、残忍、兽行无耻的一面,这确实是令现代人不寒而栗的,它与人们的理性期望相悖太远。因此,理性世界自身便受到了人们理性的怀疑。在许多西方人看来,它好比一位珠光宝气的冒牌贵妇,虽然诱人,却经不起任何打量,只为那些珠宝原来全是膺品,世界的存在本身非但不是理性的、逻辑的、为人的,相反却是混乱的,非人的,毫无规律与目可言的,正如卡夫卡所言“我从不知道常规是什么样的”(12)除了选择浑浑噩噩、随波逐流的生活而外,便只有落入对生存意义感到迷惘和绝望的深渊,又由于这种迷惘与绝望是在摧毁传统的理性世界的根基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对现世社会的反抗便也无力打出维护正义、争取自由的英雄主义的传统旗号,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的悲剧与喜剧之间的界限模糊了,昔日那些不满现实敢于抗争的英雄,在当代只能扮演看破红尘,无所适从的反英雄的角色,正象格里高尔·萨姆沙一样。在他自己的生活舞台上,格里高尔实际上只是这样一个丑角,他站在“看不见舞台、看不见观众席、看不见黑暗、看不见舞台灯光”(13)的巨大戏景之中,因为与整个舞台表演节拍不合,他的动作尽管十分严肃认真,却不免显得茫然无措,笨拙滑稽,洋相百出,在这个小丑的手心里,握着的不是巴尔扎克的手杖。“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14)而是卡夫卡的手杖,“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15)
注释:
①⑨⑩(11)见卡夫卡:《变形记》。
②⑤⑦(12)(14)(15)见卡夫卡:《乡村婚事及其它遗作》。
③④见卡夫卡:《乡村婚事》。
⑥见缪尔:《弗兰茨·卡夫卡》。
⑧见卡夫卡:《八本笔记》(1918年)。
(13)见卡夫卡:《1910-1923年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