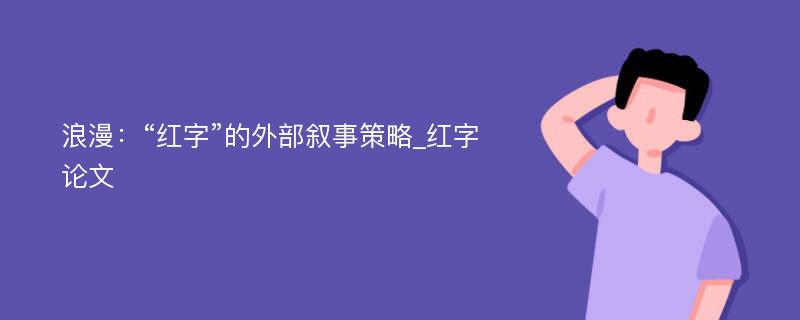
罗曼司:《红字》的外在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字论文,外在论文,策略论文,罗曼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50年2月,第克诺、里德和弗尔兹出版公司(Ticknor,Reed and Fields )为了捧红纳撒尼尔·霍桑这位“光辉灿烂的天才”,一连四期以“红字;一部小说”(The Scarlet Letter; A Novel)为题在《纽约文学世界》刊登广告,为《红字》的出版大造声势。① 可是,到了同年3月16日该书出版时,书名却突然改成了《红字,一部罗曼司》(The Scarlet Letter,A Romance)。 ② 《红字》从小说变成罗曼司,虽然只是一词之差,但它绝非作者本人心血来潮的一时之念。首先,“红字,一部罗曼司”为霍桑亲笔在该书手稿上写下的,而且他还把其后发表的所有长篇小说或命名为“罗曼司”(如《福谷罗曼司》),或者像《红字》一样都以“罗曼司”为副标题(如《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一部罗曼司》、《玉石雕像,或蒙特·本尼的罗曼司》),别有意味。再者,霍桑在这些作品的前言或后记里还直接或间接地谈及罗曼司以及它与小说的区别,显然是有意为之。与霍桑不同,惠特曼竭力反对罗曼司,他在1855年版的《草叶集》的前言中声称,“伟大的天才和各州人民决不能在罗曼司面前低三下四。一旦有了记叙完整的历史,就再也不需要罗曼司了。”③ 惠特曼所说的历史显然属于现实范畴,而罗曼司与历史之争也即罗曼司与现实主义之争。从此,关于罗曼司的争论成为美国文学史建构的热门话题。正如特伦斯·马丁(Terence Martin)在《哥伦比亚美洲小说史》中所说,“近来对‘罗曼司’这一术语的描述、分析以及辩论之多,或许没有任何文学术语能与之相提并论。”④ 事实上,霍桑对罗曼司的阐述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已经成为美国文学史中最重要的语汇,它不仅是确立以霍桑为代表的作家及作品的经典地位的关键所在,也是建立独立的美国小说传统的核心命题。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霍桑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罗曼司作家,也没有在《红字》的创作过程中把它当作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罗曼司处理。其副标题与其说是该小说文学范式的标志,不如说是霍桑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所采用的叙事策略,其目的是为了招徕读者、规避该小说婚外情主题可能招致的道德批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准确地欣赏《红字》叙事的艺术魅力,把握作家叙事策略背后所隐藏的非正统道德价值取向。
一
根据艾勃拉姆斯的分类,罗曼司作为一种文学范式主要分为中世纪传奇和散文传奇。前者12世纪起源于法国,后来渐渐流传到了其他国家,它主要指以诗体写成的骑士文学作品,如英国的亚瑟王传奇、罗马的亚历山大大帝传奇和法国的查里曼大帝传奇。后者又称为罗曼司小说,是现代小说的一部分,它是从中世纪传奇和18世纪哥特式小说演变而来的。按艾勃拉姆斯的解释,这类文学作品的人物善恶、主仆分明,主人公常常与社会格格不入,内心孤独,作品往往以过去的历史为背景,其故事情节一般也围绕着追求理想或寻找敌人的冒险行动而展开。艾勃拉姆斯认为,这类作品有别于简·奥斯汀和乔治·艾略特的现实主义小说,它主要包括“瓦尔特·司格特的《罗布·罗伊》、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爱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及美国小说中从坡、库柏、霍桑到梅尔维尔等人的一种重要创作模式,福克纳和索尔·贝娄的一些作品也属于这一类。”⑤
霍尔曼(C.Hugh Holman)则把作为文学范式的罗曼司按“互不相容的功用”分为两类:“在通常意义上,它所指的文学作品描写放浪形骸的人物、遥远或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极其激动人心的英雄事件、炽烈的爱情、或神秘或超自然的经历。在另一种更具哲理的意义上来说,罗曼司指那些相对来说不受现实主义真实性约束的作品,它们传达或深刻或超凡脱俗或理想化的真理。”所谓通常意义上的罗曼司实际上指的是那些带有浪漫色彩的传奇小说,而所谓更具哲理的罗曼司则是以霍桑为代表的经典美国作家的罗曼司作品,也即本土化了的美国样式的罗曼司小说。虽然美国文学中不乏第一类作品,但在霍尔曼看来,只有美国本土化了的第二类罗曼司才更具哲理:“尤其是在美国,事实已经证明,在探索深刻的思想、复杂的观念时罗曼司是一种严肃而又灵活的表达手段,霍桑的《红字》、梅尔维尔的《白鲸》、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以及华伦的《世事苍茫》等品质各异的作品都借助于这一技巧取得了成功。”⑥
霍尔曼在视罗曼司为美国小说的成功技巧这一点上并不孤立。他的立场与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查尔斯·威尔金斯·韦伯(Charles Wilkins Webber)、莱昂奈尔·屈林(Lionel Trilling)以及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等众多美国作家和批评家为区别英、美小说,确立美国小说独特传统所作的努力是一致的。⑦ 屈林在1947年的一篇题为“礼仪、道德和小说”的会议发言中说,“事实是,天才的美国作家并不直面社会现实。坡和梅尔维尔与它势不两立;他们所寻求的现实与社会聊无关系。霍桑目光敏锐,坚持认为他写的不是小说而是罗曼司——他就这样表达了他对自己作品缺乏社会肌质的认识。”⑧ 正如贝尔(Michael Davitt Bell)所说的那样, “屈林有关美国小说一直以来都有其独特传统的论点很快成为批评界的共识……紧跟其后的现代批评家们又各取所需,把他的种种观点转化为值得全国上下庆贺之事。”⑨
贝尔所指的批评家之一就是蔡斯。蔡斯在其1957年出版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一书中说,“我的主要的、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主题是罗曼司或罗曼司小说与小说自身之间的关系。”“大多数优秀的美国小说都是罗曼司,大多数优秀的英国小说则不然——换言之,事实是,罗曼司传统在美国小说史中是主要的,而在英国小说史中却是次要的。”他追溯了从库柏、威廉·吉尔默·西姆斯(William Gilmore Simms)到霍桑的美国小说的罗曼司传统,认为“自从它发源的那时起,美国小说就以最具独创性和最富特色的形式找到了它的归宿,靠吸收罗曼司的成分确定了自己的身份。”蔡斯认为,美国罗曼司小说除了要有“如画的风景和英雄的冒险经历以外,还要享有自由,不受普通小说对描写的逼真性、情节的展开与发展的限制。”⑩ 在蔡斯看来,“霍桑的作品首次实现了罗曼司对种种心理层面的探索……正如我们在其长篇小说(尤其是《玉石雕像》)的前言中所看到的,霍桑与库柏、西姆斯一样坚定地认为美国叙事作品命中注定的形式是罗曼司,而不是小说。”(11) 这样,蔡斯确定了霍桑作为罗曼司作家在美国小说独特传统中的地位。
通观以上批评家对美国罗曼司的定义和阐述,可以发现三个特点。第一,在他们对罗曼司的定义当中,罗曼司与现实主义小说相对立,与特定社会的主导文化格格不入。霍尔曼所谓美国罗曼司作家不受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约束,屈林对美国罗曼司作家与现实势不两立的姿态的强调,蔡斯有关罗曼司享有不受小说真实性约束的论述,无不强调美国经典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和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之间的游离状态,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把美国小说与中世纪骑士文学以及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区分开来。第二,霍桑是美国罗曼司小说的代表人物,批评家对罗曼司的阐述主要建立在霍桑对罗曼司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之上,是对霍桑有关罗曼司理论的归纳和阐释,同时也是对霍桑小说的归纳性描述。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批评家把霍桑的罗曼司理论等同于霍桑的小说,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视其小说为罗曼司理论在小说中的实际运用和美国罗曼司小说的典范。总而言之,与流行小说和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相比,霍桑的小说之所以是罗曼司是因为它缺乏社会肌质,背离了美国的社会历史现实。
但是,近年来,蔡斯等人建立在霍桑相关论述基础之上的关于罗曼司是美国小说的本土传统、独创性和美国性的观点受到了贝尔等文学史家的挑战。贝尔多次以论文和专著的形式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人们越看这些评论家的东西……越感觉到这些评论家不是把‘罗曼司’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形式加以描述……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惯用的标签贴在他们在美国小说或广义地说美国生活中所发现的一切独特品质上。”(12) 在他看来,霍桑的罗曼司是“叙事策略”,(13) 是“骗术”:(14) “霍桑的历史故事,也许最重要的是《红字》,与‘现实环境’紧密相连……虽然他关于罗曼司的评论表面上看来直截了当,但至少最终给我们的印象是有点儿言不由衷。”(15) 与其说霍桑“写的是罗曼司作品,不如说他是在论述罗曼司范式。”(16) 贝尔强调,“就其最本质的方面而言,《红字》是一部明显的现实主义小说……《红字》既全面又现实地展现了新英格兰历史的细节及其意义。”(17)
事实上,即使粗略地看一下《红字》或《福谷罗曼司》,我们也会发现霍桑的长篇小说并不缺乏社会肌质,也没有真正与社会现实“势不两立”。前者不仅以一篇半自传性的前言《海关》开始,交代该小说创作的背景和故事来源,而且《红字》本身对早期麻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社会历史也有比较精确的描述;后者虽然不是历史纪实,但它多多少少是根据霍桑1841年4 月开始的半年间在布鲁克农场的经历写成的,因而也显现了作者对作为美国现实一部分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的关注,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事实上,《红字》的现实性与罗曼司这一标签所隐喻的非现实性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为了认清这一矛盾的实质,我们必须对霍桑有关罗曼司的论述以及《红字》的创作过程作一番考察。
二
霍桑对罗曼司曾作过不同的论述:在《海关》中它是“真实世界与神话世界之间的”“中立地带”,(36)在《福谷罗曼司》的前言中它是“有点远离平常旅途的地带”,(18) 在《玉石雕像》的前言中它则是“某种诗或神话的领域。”(19) 霍桑关于罗曼司的最直接的论述出自《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前言:
当作者把他的作品称为罗曼司时,几乎不用说他是想在方式和素材上为自己争取一定的自由。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在写小说,那么他就会觉得没有权利去争取这样的自由。据称,后面这种创作形式的目标是非常细致的忠实性,它不仅要忠实于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还要忠实于合乎人类经验的方向而又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作为艺术品,前者——它必须严格遵循惯例,同时也会因为可能会偏离人类心灵的真理而犯下种种不可饶恕的大错——在很大程度上也享有相当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作者自己的选择或创造展示人类心灵的真理。(20)
这段话表面上说明了罗曼司作家在创作方式和作品素材两方面有选择的自由。但是,正如贝尔所说,“这话就其本身而言并不错,但事实上它并没有作深入的论证。奇怪的是,它不过是一个反证式定义:它告诉我们的是罗曼司不该做什么,至于它该做什么却几乎不置一词。”在贝尔看来,该前言的“目的在于藏匿而非揭示罗曼司背后的真实权威,”而且“事实证明,他的策略大获成功。”(21)
其实,霍桑对罗曼司的这一描述是一团迷雾,给人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必须从它的字里行间才能看出它所暗指的内容。首先,作者把他的作品“称为”罗曼司,不过是姑且给它这么一个称呼而已,并不是因为他写的真的就是罗曼司。类似地,当小说作者“承认”他所写的是小说时,他的作品又不一定是小说。这里的“承认”一词,英语原文是“profess,”该词兼有“声称”、“假装”和“承认”之意。从这个词意上来说,作者只是声称或假装自己所写的是小说,但无论是承认也好,假装也罢,作者所写的作品都有可能是罗曼司。其次,批评家往往以为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抬高罗曼司对内心真理的忠实,贬低现实主义对现实的表面忠实,蔡斯就是一个例子。根据他对霍桑以上这段话的分析,蔡斯认为,“把虚构作品与人类心灵联系起来,赋予了罗曼司普遍的人类重要性,”(22) “正是罗曼司的抽象和深刻使之能够表达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真理……人们可以用罗曼司能表达现实主义所无法表达的黑暗而又复杂的真理力量来加以说明。”(23) 然而,这并非霍桑的原意。虽然霍桑分别讲了罗曼司和小说的创作,但他的用词不偏不倚,使得两者都指向其对立面。如果当作者把作品称为罗曼司时,其作品可能是小说,那么当作者声称作品是小说时,该作品实际上又可能是罗曼司。实际上,霍桑在此绝非借贬损现实主义小说而褒扬罗曼司小说。他的措辞表明,他看到了罗曼司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在表达真理时的相对性:现实主义小说只是对事物的表面忠实,罗曼司小说也不一定就能够揭示人物心理或内心的真实。其实,霍桑已经在这段话中明白无误地说明了“罗曼司可能会偏离人类心灵的真理。”
类似地,霍桑在《海关》中对“中立地带”所作的论述也不是对罗曼司这一文学范式的无条件推崇:
如果在这样的时刻想像力拒绝活动,这倒是可以认为无药可救了。月光是最适合罗曼司作家认识他虚幻客人的媒介。在一间熟悉的房间里,皎洁的月光——散落在地毯上,把房里的东西映照得清晰可见,每样东西的细微之处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又与清晨或中午时分的清晰度大不相同……这样我们熟悉的房间地面就成了一块中立地带,它介乎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之间,现实与想像在那里交汇,影响彼此的本质。
……在这样的时刻,如果独自静坐的人面对这样的场景,仍然想像不出奇异的事物,并使这些事物呈现出真实的面目,那么他永远也不要再想写什么罗曼司了。(35—6)
这段话除了说明了理应有利于罗曼司创作的氛围——习以为常的房间里皎洁的月光是罗曼司创作的最佳时间和空间,并没有直接论及罗曼司作品的本质和规则。并且,即使是这样有利于罗曼司创作的氛围也无助于罗曼司创作。其实,在本引文的前面霍桑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深夜,闪烁不定的炭火和月光照亮了空寂的会客室,它(指精神的麻木)仍然盘踞心头,我独自静坐,企图绞尽脑汁唤起想像的场景,但愿这些场景会在第二天化作色彩斑斓的叙事跃然纸上,光芒四溢”。(35)“但愿”一词的英语原文“might”用来表达愿望、可能性极小或与事实相反的情况,这表明了炭火和月光照亮的房间并不一定能唤起想像的场景,更难使这些场景化作色彩斑斓的叙事跃然纸上。正如霍桑接下来所说,“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压在我身上,让我分心,”“我那不可触摸的美丽肥皂泡触及到某种现实的环境就破灭了。聪明的做法是把思想和想像力散布到混沌的现实中去,从而使它变得光明透亮,使得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生活重负轻松一些;坚定不移地从隐而不露的、我所熟悉的凡人凡事中寻找真正的、不可摧毁的价值”。(37)霍桑在此非但没有刻意张扬罗曼司的创作和罗曼司作品的真理性,反而肯定了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因此,霍桑所说的罗曼司的中立地带既不是《海关》自传性描写的有效领域,也不是创作《红字》的有效手法。
三
那么,霍桑所说的罗曼司到底是什么呢?他又为什么坚持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罗曼司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从《红字》的创作背景说起。
霍桑在《海关》中说,“也许如今我们这些人的子孙后代有时会大发善心,想起记述往昔时光的涂鸦人”。(45)与他五年后蔑称女性流行小说作家为“该死的涂鸦女人”时不一样的是,(24) 这句话中的“昔日时光的涂鸦人”是霍桑从他者的角度对自己的言不由衷的自嘲,并借着自嘲调和罗曼司和小说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霍桑故意以他者的立场来看待罗曼司作家,认为他们不切合现实,写的是过去的事,因而是往昔时光的涂鸦人。另一方面,由于未来的今天又是过去,从后人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现实又将成为未来的往昔时光,以今天的现实为素材的作家在后人的眼里又无异于往昔时光的罗曼司涂鸦人。所以,就今天而言,这位“昔日时光的涂鸦人”就是切合今天现实的作家。这样,霍桑巧妙地肯定了罗曼司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可见,在霍桑的自嘲背后隐藏着他对罗曼司和小说两种文学范式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事实上,当霍桑在《海关》中浓墨重彩论述罗曼司的创作氛围时,他所用的也是小说的现实笔法,并且也正是这种现实笔法给了它历史的维度和现实意义,从而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对此,霍桑在《红字》第二版序言中不无得意地说,“令作者大为诧异、又颇感可笑的是……他写的那篇有关公务生活的文章——《红字》的前言——竟在他周围的有识之士之中激起了这般空前的狂风怒涛”。(1)其实,“诧异”和“可笑”之说不过是说说而已,因为正如威廉·查瓦特(William Charvat)所说,“这篇随笔在霍桑的年代极其流行,弗尔兹对此心知肚明。与《红字》相比,许多读者更偏爱这篇随笔,这也是作者意料之中的事”(xxiii-xxiv)。
《海关》本身也可以看成历史的真实与文学想象的结合。它向读者明示的是历史的真实,也即作者的身世及公务员生活。但是,它通过表面的历史真实所要表达的却是文学的想像。作者把红字的来源夹在自己真实的身世之中,其目的是要把历史的真实性赋予虚构性的《红字》:“读者应该牢牢记住的是,那个故事里的主要事实出自于稽查官皮尤先生的那份文件,因而真实可信。那份原始文件以及那个红字本身——这是一件极其精巧的遗物——仍然在我的手中,随时都可以拿出来,让那些对这一记述极感兴趣、意欲目睹这些东西的人们一饱眼福”。(32—3)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以上这段话没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然而,霍桑被解职一事曾经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事件,因此把有关红字“故事”的来源与海关经历的描写结合起来,确实造成了“故事”真实性的假象。事实上,正如霍桑1850年9月17日致扎克里亚·波奇默(Zachariah Burchmore)的信中所示,当时真有不少读者对霍桑所讲的话信以为真:“很遗憾,那瓶香槟几乎喝完了,因为我接待了很多想看一眼那个红字的来客。由于拿不出那东西来,只好竭尽全力,以最好的方式满足他们。”(25) 我们在此感兴趣的不是那些读者怎么会这么缺乏想像力,竟然相信了霍桑编造的关于红字来源的故事,而是霍桑给虚构的故事披上真实性的面纱,吸引了读者,并且解除了他们对虚构作品的真实性的怀疑的用意。
除了《海关》中作者的身世,吸引读者的还有《红字》故事的主题。 霍桑在1850年1月15日给弗尔兹(James T.Fields)的信中说:
《红字》还有三章待写……或许你不会喜欢这本书,或者认为它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如果是这样的话(此话说来多余),我不会咬定你一定要履行出版该书的义务。《红字》的主题写起来很棘手,但在我看来,我处理这一主题的方式应该不会在这一问题上引起读者的反感。那篇题为《海关》的文章是全书的前言,因此请你先看它……我还没有想好书名,但在全书写完之前我可能会碰巧想出一个书名。(26)
这段话表明,《红字》的创作已经过半,而且作者已经在完稿的《海关》中把它定为“故事”,该小说的文学范式已经成了既定事实。这与《纽约文学世界》上的广告把它称为小说是完全一致的。再者,在这段引文中,霍桑说的不是他将如何处理这一主题(I will treat it),而是他是如何处理这一主题的(I have treated it),这说明此时主题的处理方法同样也是既定事实。因此,无论在文学范式上还是在主题的处理上,《红字》至此为止都是小说,而不是罗曼司。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霍桑放弃了“故事”和“小说”之说,在最后的手稿上写下“罗曼司”的。但是,该信表明读者因素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霍桑非常在意该书是否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担心《红字》棘手的主题会引起读者的反感。由此可以推断,在确定《红字》文学范式、主题的选择及处理方法时,霍桑关注的主要是读者因素。
虽然霍桑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红字》的棘手主题是什么,但从小说的实际情况来看,它明显是指海丝特的婚外情。其实,如果把《红字》当作罗曼司,那么它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作为爱情小说的特征;所不同的是,它涉及的是清教伦理势力强盛时期一个有夫之妇和一名牧师之间有违清教伦理的婚外情故事。正如克拉科修(Michael J.Colacurcio)所说,“也许,霍桑的罗曼司(指《红字》)真的写得更多的是性,而不是如我们过去所注意到的那样是罪恶感。”(27) 《红字》的婚外情主题也许是招徕读者的最佳选择,但是,不幸的是,在道德层面上它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容易为作者招致批评者的道德攻击。正因为如此,霍桑才认为《红字》的主题写起来很棘手。
四
在选定了海丝特的婚外情这一主题之后,处理这一敏感话题就成为更为棘手的事。摆在霍桑面前的两难境地是,如何借海丝特的越轨主题既诱捕读者、谋取稿费生存,又巧妙地规避道德批评。霍桑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法可以分为内在处理和外在处理两个方面。从《红字》文本的实际情况看,霍桑对《红字》文本的内在处理方式很成功,对此我们拟另文讨论。在此我们关心的是小说的外在处理方法。上文我们已经对霍桑在《红字》创作时的实际处境以及他给弗尔兹等人的书信进行了分析,看到了外部环境对《红字》创作的影响。但是,读者毕竟不是他的朋友,无从了解这些情况,他们窥视霍桑创作《红字》时的外部环境的唯一途径是《海关》。虽然该文在创作之始并非完全为《红字》所作,但它的副标题“《红字》的前言”暗示其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红字》所作的外在处理。
回顾《红字》的批评史,我们发现,不同时期的评论家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理解《海关》。里勃利(George Ripley)、阿伯特(Anne W.Abbott)等霍桑同时代的批评家大多看好其中的现实描写;(28) 马西森(F.O.Mathiessen)、(29) 屈林以及蔡斯等20世纪上半叶的批评家则更关注文中霍桑对罗曼司的论述;而齐夫(Larzer Ziff)、贝尔、贝姆(Nina Baym)等近期的批评家则往往结合以上两种方法,或分析霍桑的罗曼司理论与其人生观的联系,或探讨霍桑罗曼司理论的欺骗性,甚或把《海关》中的作者比作《红字》中的海丝特。(30)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批评家在审视该文时往往忘记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正是霍桑要诱捕的笨鸟,意识不到《海关》所要蒙骗的真正对象就是一部分作为读者的批评家,因而在不经意之中听从了霍桑的调遣。正因为如此,以上大多数批评家才会忽略该文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无论是作者对塞勒姆小镇的描写,对海关生活、同事以及祖先的记述,还是对红字来历的交代,或者是对罗曼司的论述,都是试图从外围为《红字》扫清障碍,其真正目的在于建立作者与读者(包括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界定作者的身份,以便把他们的目光引向作者所设定的方向,既堂而皇之地满足他们的窥视欲,又剥夺他们评头品足的权利。借助于这一策略,套用一句不中听的话来说,霍桑就可以像海丝特一样,达到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目的。
霍桑的第一种外在处理方式是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看似亲密的关系,这主要反映在《海关》的前两段文字中。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朝着这个目标来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喜欢坐在炉边与朋友大谈特谈我自己的生平和事务,但是创作自传的冲动竟然在我的一生中两次左右了我,把我自己和我的事务摆到公众面前。”作者的这句话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接下去,霍桑进一步拉拢读者,说作者的倾诉对象不是普通大众,而是“为数不多的能理解作者的读者,”因为他们“比多数同学和终生好友更了解他。”作者认为,“除非说话人与听者之间有某种真诚关系,”否则,“思想冷若冰霜,谈话也毫无感情可言”。(3—4)通过这一番说服,霍桑确立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基本确保了读者能以友好的心态按作者指定的方法阅读下文关于作者海关经历的描写以及《红字》的故事。
霍桑所采用的第二种外在处理方法与第一种方法既相关又相反。如果说第一种方法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第二种方法则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既疏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又为作者开脱责任。还是以《海关》的第一句话为例,上文所分析的内容只是作者有意要给读者造成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假象,在这一看似亲密的关系之下隐含着的却是冷漠的实质。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上文引用的这句话的译文有点别扭,这其实不是翻译的问题,而是我们为了体现原文的风貌,没对它作任何语言上的调整。它的英语原文用“It”这个形式主语替代了“that”引导的主语从句,但细看起来,这个主语从句的内容实际上并不合英语语法。分词短语“不喜欢坐在炉边与朋友大谈特谈我自己的生平和事务”的逻辑主语毫无疑问是“我”,按照英语语法分词短语的逻辑主语应当与主句的主语相一致的规则,主句“创作自传的冲动竟然在我的一生两次左右了我”的主语也应当是“我”。如果是这样的话,主句就应当变成“在我的一生中,我竟然两次为创作自传的冲动所左右。”可是,霍桑偏偏没用主格的“我”,而是用“创作自传的冲动”作为主语,这样一来,“创作自传的冲动”就成了“不喜欢谈论……”的主语,这显然不合语法、不合逻辑。霍桑这样不惜以牺牲文法为代价,为的是避免授人以柄,其意是说作者并无以隐私招徕读者之意,更不是出于什么“世俗的目的”,记述自己生平之事并非作者故意为之,而是创作冲动的结果。
实际上,霍桑一方面表面上不遗余力地与读者套近乎,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把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从而抽空作者与读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内涵:“然而,即使在我们所谈的内容与个人无关的时候,大凡无所不谈都会有失体面”;“我们会闲聊我们身边的事,甚至会聊及我们自己的事,但我们仍然会把内心深处的‘我’置于面纱后面。”这样一来,“也许作者既可以描写自己的生平之事,又不会侵犯读者或作者的权利”。(4)当然,读者并无权利可言,把“内心深处的‘我’置于面纱后面”的真正目的在于保护作者的自身利益,维护作者自身的权利。
霍桑的第三种外在处理方法与第二种方法相似。如果说第二种方法把作者的真实自我隐藏起来,那么第三种方法则把作者的真实身份掩盖起来。作者曾告诉读者,《海关》谈及的是作者的三年海关经历,但接着却对这一说法进行修正:“《海关》这篇随笔解释的是后面篇幅中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是如何落到我的手中的,并且提供其内容真实可靠的证据,这样做也算合乎规范,向来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人们的认可。”作者声称,“事实上,这就是……我与公众保持某种私人关系的真实原因,别无其他原因。”(4)然而,霍桑这么做绝对不是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从行文上看,这个“这”字在本句中是一个脚踏两只船的指代,它既可以指《红字》内容的真实性(即《海关》对红字来历的交代),又可以指省略号里的内容,也即“把自己置于编辑位置上的愿望,更具体地说,把自己置于这本故事集中那个篇幅最长的故事的编辑位置上的愿望。”(4)霍桑这么说的目的在于说服读者,让他们相信他自己并非《红字》(也即“篇幅最长的故事”)的作者,而是皮尤手稿的编辑,这才是“真实原因”。
霍桑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和自己的编辑身份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那就是逃避作者的道德责任。一方面,突出《红字》的真实性实际上是为了赋予小说历史和现实的真实性,从而既淡化它的虚构性,又重新界定作者的身份。从文学创作的层面上来说,清教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时起就敌视虚构文学作品对人类心灵的侵蚀和诱惑。新英格兰清教徒显然继承了英国清教对文学的敌视态度,而18世纪美国启蒙主义者又是清教理性的“嫡系传人”(布狄克语),(31) 因为他们同样怀疑文学的想像和虚构。例如,杰弗逊在1818年3月14 日给纳撒尼尔·伯威尔的信中就认为,“时下对小说的热衷是良好教育的障碍……当这一流毒毒害到理智,就会毁掉理智,抵制健康有益的阅读。平实而又不加修饰的理性和事实就会遭到拒绝。只有以幻想装束出现的种种无稽之谈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而且这般的装扮无可挑剔,其结果是华而不实的想像,苍白无力的判断力和对人生实务的拒斥。”据此,杰弗逊把小说称为“垃圾”。(32) 霍桑强调自己的编辑身份,表面上迎合了启蒙理性,否定了文学想像的作用。然而,由于《红字》本质上就是虚构,就是文学想像,因而编辑身份实际上突出了虚构作品的真理性,否定了作家的“故事书作家”的身份,赋予了作者身份以更严肃的责任,从而批驳了启蒙理性。借此,霍桑有效地反击了清教伦理及启蒙理性以文学虚构性为由对作家所作的道德攻击。
另一方面,在更现实的层面上,掩盖自己的作者身份还能帮助作者逃避《红字》故事中海丝特性越轨行为可能造成的对作者的道德谴责。当霍桑把自己置于编辑位置上时,作者的职责从《红字》作者的描写行为(representational act)转变为皮尤手稿编辑的再现行为(re-presentational act)。 前者是作者的创作活动,故事是由作者虚构的,所以作者必须承担作品的道德责任;后者是编辑的职责,故事是由他人写成的,因而作品的道德责任不在编辑。霍桑疏离自己的作者身份,主动承担并履行编辑职责,无非是为了说明自己仅仅再现了皮尤稽查官那个时代的老人们年轻时所听说的、在他们年老时口述给皮尤的、并由皮尤亲笔记录下来的、最后又被《海关》作者发现的海丝特的婚外情故事。因而《红字》的创作不过是海丝特生平故事的再现的再现的再现,其真实性和道德责任与《红字》的作者/编辑无关。即使要追究其道德责任,那也要从皮尤那里往前排查,一直追溯到海丝特本人才是。
至此,我们又转回到《红字》的副标题罗曼司上来了。从表面看,罗曼司这一标签似乎与霍桑的编辑的位置和《红字》故事的真实性不相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然而,正如贝尔所指出的,“罗曼司并非源自作者的艺术,而是来自于他的素材。”当作者把罗曼司的标签贴在所谓的真实故事上时,他所要告诉读者或让读者相信的是,《红字》故事的罗曼司特性并非出自作者的虚构,而是源于故事本身的真实性,《红字》是海丝特浪漫生平之现实的再现。换言之,与海丝特越轨的道德责任一样,罗曼司特性是《红字》故事本身所固有的,是作者作为编辑从海丝特真实的生平故事以及皮尤手稿中继承而来的,两者都与海丝特相关。按照这一逻辑,《红字》的罗曼司标签与其说是该小说的文学范式标志,还不如说是故事本身浪漫特性的标志。换句话说,《红字》的副标题“A Romance”应当理解为“一部爱情小说,”而不是文学范式“罗曼司”(Romance)。
当然,与作者刻意编织的与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作者掩盖自己真实的作者身份这两种处理方法一样,《红字》的罗曼司标签由文学范式的标志转变为故事浪漫特性的标志不过是霍桑蒙骗读者的策略。归根结底,无论是《海关》中关于“红字”来源的记述,还是皮尤手稿的真实性,还是海丝特的越轨行为,或者还是故事中红字从通奸的指代变为天使的象征,所有这一切,都是作者的虚构,是作者的描写行为,而不是编辑的再现行为。因此,《红字》的道德责任完全在作者本人。霍桑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既能用性丑闻来招徕读者,又能凭借罗曼司这一策略欺骗读者,把他们的视线从作者身上引到海丝特身上,从而掩盖《红字》在文学表现上的道德“越轨”,使作者免于道德责任。
注释:
① 霍桑的出版商弗尔兹(James T.Fields)在1850年3月5日致杜伊金克(Evert A.Duyckinck)的信中说,“真的,让我们一起努力,把那位光辉灿烂的天才放到他应有的位置上去,”参见Nathaniel Hawthorne,The Scarlet Letter,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eds.,William Charvat and others,Columbus:Ohio State UP,1983,p.xvii.以下引自《红字》及《海关》的内容仅在括号中标出在该书中的页码。译文参照姚乃强译《红字》(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年)。为了行文方便,引用时对照原文有所改动。另外,同样是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把“romance”译为“罗曼司”。
② 参见Nathaniel Hawthorne,The Scarlet Letter第2页后所附的《红字》手稿标题页复印件。
③ 转引自Joan Dayan,“Romance and Race,”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ed.,Emory Elliott,New York:Columbia UP,1991,p.104.
④ Terence Martin,“The Romance,”in Emory Elliott et al,eds.,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1,p.72.
⑤ 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5[th] ed.,Fort Worth: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88,p.119.
⑥ C.Hugh Holman,A Handbook to Literature,4[th] ed., 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80,p.387.
⑦ 梅尔维尔及韦伯的观点见J.Donald Crowley,ed.,Hawthorne:The 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0,pp.111—26,pp.126—34;屈林的观点见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Oxford:Oxford UP,1981,pp.193—209;蔡斯的观点见Richard Chase,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London:G.Bell and Sons,1958,pp.vii—xii.
⑧ 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p.200.
⑨(12)(14)(17)(21)(37) Michael Davitt Bell,“Arts of Deception:Hawthorne,‘Romance,’and The Scarlet Letter,”New Essays on The Scarlet Letter,ed.,Michael J.Colacurcio,Cambridge:Cambridge UP,1988,p.32,p.34,p.29,p.46,p.40,pp.36—7.
⑩(11)(22)(23) Richard Chase,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pp.vii-xii,pp.17—8,p.19,p.xi.
(13)(16) Michael Davitt Bell,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omance:The Sacrifice of Relation,Chicago and London:The U of Chicago P,1980,p.35,p.42.
(15) Michael Davitt Bell,“Nathaniel Hawthorne,”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Emory Elliott et al,eds.,New York:Columbia UP,1988,p.425.
(18) Nathaniel Hawthorne,The Blithedale Romance and Fanshawe,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eds.,William Charvat and others,Columbus:Ohio State UP,1971,p.1.
(19) Nathaniel Hawthorne,The Marble Faun:Or,The Romance of Monte Beni,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eds.,William Charvat and others,Columbus:Ohio State UP,1971,p.3.
(20) Nathaniel Hawthorne,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eds.,William Charvat and others,Columbus:Ohio State UP,1971,p.1.
(24) 语出霍桑1855年1月19日给第克诺(William D.Ticknor)的信,他还在信中称当时女性作家所写的流行小说为“垃圾”,但他的这一态度在同年2月2日给第克诺的另一封信中有所改变,参见Nathaniel Hawthorne,The Letters,1853—1856,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eds.,Thomas Woodson and others,Columbus:Ohio State UP,1987,pp.303—4,pp.307—8.
(25)(26) Nathaniel Hawthorne,The Letters,1843—1853,The Centenary Edition of the Works of Nathaniel Hawthorne,eds.,Thomas Woodson and others,Columbus:Ohio State UP,1985,p.364,p.305.
(27) Michael J.Colacurcio,“The Woman's Own Choice:Sex,Metaphor,and the Puritan‘Source’of The Scarlet Letter,”New Essays on The Scarlet Letter,ed.,Michael J.Colacurcio,p.111.
(28) 里勃利及阿伯特的观点见J.Donald Crowley,ed.,Hawthorne:The Critical Heritage,pp.158—9,pp.164—7.
(29) 马西森的在关论述见F.O.Mathiessen,American Renaissance:Art and Express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Whitman,London:Oxford UP,1957,pp.179—368.
(30) 齐夫的观点见Larzer Ziff,“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The Custom House,’”Nathaniel Hawthorne,Modern Critical Views,ed.,Harold Bloom,New York:Chelsea,1986,pp.33—9;贝姆的观点见Nina Baym,The Scarlet Letter:A Reading.Twayne's Masterwork Studies,Boston:Twayne,1986,pp.101—7.
(31) Emily Miller Budick,Fiction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The American Romance Tradi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P,1989,p.27.
(32) Thomas Jefferson,Writings,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