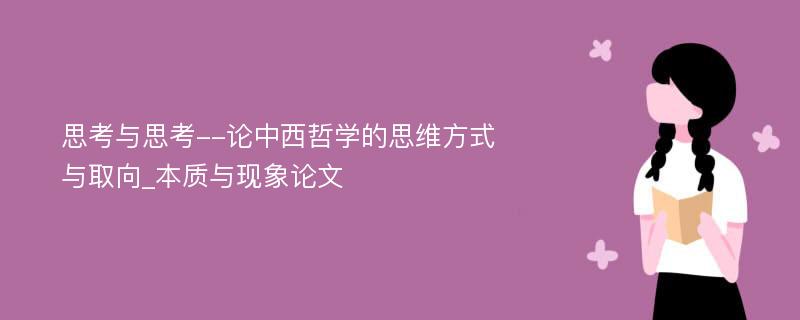
感思与沉思——试论中西哲学思维的方式与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中西论文,沉思论文,试论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哲学界重建中国哲学的努力有两条鲜明的思路值得注意:一是把本体论、方法论与道德哲学结合(牟宗三为代表);二是把本体论、方法论与逻辑学相结合(以金岳霖、冯契为代表)。第一条路线强调中国哲学的根基在于以道德体验、道德情感为基础的“智的直觉”。第二条路线则强调理性直觉与德性自证、思辩综合的统一。两条思路殊途同归,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归结为“思”的方式的合理性问题。思都是主体之思,对自身之“在”与所在之“世”的思是哲学之思的任务与使命。而自身之“在”与所在之“世”不断展开的性质又使思什么与如何思呈现出多样性。思什么与如何思是统一的,换言之,存在与方法是统一的,存在由方法规定,由方法而达存在。不过,方法或主体“思”的方式又生发于“思”的主体的生存论结构之中。进一步揭示方法论的生存论基础方可正确定位哲学的根基与法度。而合法性不仅仅是合乎法度,即合乎思的规则的事情,合法首先是“合时”,即合乎自身之“在”与所在之“世”的展开之时,合法性首先是合时性。在此视野下才能恰当地估量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一、“看”与沉思
西方哲学重视对视觉与“看”的研究,其“沉思”式思考方式也与视觉优先发展相一致而形成、发展。柏拉图在《蒂迈欧》中说,那种使人的身体保持温暖的、柔和的火焰会变为一种均匀而又细密的火流从人的眼睛喷射出来,从而在观看者与被观看的物体之间搭成一座实实在在的桥梁,这时外部物体发出的光线刺激便顺着这一桥梁进入眼睛,继而又从眼睛到达人的心灵。(《蒂迈欧》第45节)眼睛与心灵处理的是相同的对象,即事物的色、形、象及运动规律这些事物本身固有的“事实”。因此,眼睛是连接观看者与被观看事物的桥梁,通过眼睛可以把握对象。这个共同的对象被设定为物体固有的,因此,把握它就是如实地、不带成见地反映、呈现它。眼睛与其他感官相比,成见最少,最客观。所以,柏拉图称视觉是“最可靠的感觉”。(《斐多》第1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20世纪美国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从心理学角度对视觉的客观性进行分析:“(视觉的)这种远距离感受,不仅使自己的认识领域更加宽广,而且使得感知者不再与他探索的事件直接冲撞。这种使感知者避开感知对象对他自己以及他的所作所为产生影响的能力,使得他能够更加客观地把握周围的存在物及其行为。换言之,使得他能够直接研究这些客观存在物是什么,而不是这些存在物对他的作用和他自己正在做什么。……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乃是视觉,它是一切公正的观看或观照活动——的本原。”(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第6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不过,柏拉图对视觉经验的信任又是有限度的。在他看来,存在两个世界,即“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视觉可以把握“可见世界”中的存在物,而对于“不可见世界”的存在则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它还会扰乱灵魂,妨碍其对事物本质的把握。“一个人观察事物的时候,尽量单凭理智,思想里不搀和任何感觉,只运用单纯的、绝对的理智,从每件事物寻找单纯的、绝对的实质,尽量撇开视觉、听觉……要探求任何事物的真相,我们得甩掉肉体,全靠灵魂用心眼儿去观看。”(《斐多》第16~17页)普通视觉的观看就是“透过肉体的看”,灵魂用心眼的观看是摆脱肉体诱惑的“自由观看”。(同上,第47页)心眼观看事物用的是概念,概念是抽象而不是具体的,因此它不会变化,不会受肉体的干扰。不难看出,这种“观看”是不夹杂经验及一切存在要素的纯粹的思辩活动。摆脱了肉体及一切生存经验,使思考主体消隐、沉没,这就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世界最推崇,也是发展最完备的思考方式,通常称之为“沉思”——消隐、沉没思考主体的思考。
用“心眼观看”来称谓思考并不是无端由的。在柏拉图那里,理智所要把握的本质是“理念”这种“永恒的普遍形式”。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因,形式因始终被理解为目的因与动力因,即被理解为能动的、本质性的因素。相应于此,质料因则被当作惰性的、被决定的因素。形式等同于本质的观念在欧洲思想中根深蒂固。康德将形式等同于先验与本质正体现了这个传统,并以其在近代哲学中的权威地位而加强了这种传统。黑格尔称绝对理念为“概念的纯形式”,个体生命把个体的直接性“沉没于”抽象的普遍性才能够把握它。“绝对理念……本身就是概念的纯形式,这纯形式直观它的内容,作为它自己本身。”(《小逻辑》第237节,商务印书馆1995年)“形式”与视觉相对应,当然,把握这些理性的“形式”只能借助“心眼”(理智的眼睛)。胡塞尔以“范畴直观”、“本质直观”、“本质的看”来把握范畴、本质这个理性世界正是对这个传统的继承。当然,进行本质直观的前提必须是现象学还原,即放弃自然态度,包括主体一切的存在经验,达到先验自我。
如果说理性哲学强化了心眼的看,那么,科学及以科学为基础的思想则自觉强化了肉眼的“看”。不过,肉眼的看与思维不是相分的,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被称为‘思维’的认识活动并不是那些比知觉更高级的其他心理能力的特权,而是知觉本身基本构成成分。……一个人直接观看世界时发生的事情,与他坐在那儿闭上眼睛‘思考’时发生的事情,并没有本质区别。……我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去制止人们把知觉中发生的事情称之为‘思维’。至少从道理上说,没有哪一种思维活动,我们不能从知觉活动中找到,因此,所谓视知觉,也就是视觉思维。”(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第56页)视觉是一种思维,是一种与“沉思”思维方式一致的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肉体的“看”是完美的认识活动。真正的任务是指导、帮助视觉,使之达到更客观、更纯粹的水平。培根说:“在一切感官之中,显然是视觉在供给消息方面负有主要的任务。因此我们也就应当以主要的努力来为视觉谋取帮助。对于视觉的帮助不外三种:一是要使它能够看见不可见的东西;二是要使它能够看见离得更远的东西;三是要使它能够把东西看得更准确更清楚。”(《新工具》第21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通过一系列的帮助,肉眼就可以看见不可见的东西,可以更清楚地看,更客观地看。最重要的是,通过帮助(理性与普遍哲学的帮助),肉眼可以消除培根所认为的感官的最大的欺骗,即“对于自然的界划总是参照着人而不是参照着宇宙”(《新工具》第230页)。视觉较之其他感官主体要素介入的成分最少,在这个意义上,它最客观。但任何看总是主体的“看”,对对象的界划总是以主体为标准与尺度。因此,视觉之客观又不是纯粹的,更不是无限、绝对的。培根对视觉的帮助目的在于使之达到纯粹的看,这种企图贯穿于一切科学的追求中。这种企图就是使肉眼的“看”与心眼的“看”相一致,即消隐自我,沉没自身,即追求“纯粹的看”。
“纯粹的看”在哲学与科学,乃至宗教、艺术中都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果。但“纯粹的看”并不能在一切领域完成一切认识任务。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深刻地指出:“从存在论原则上看,我们实际上必须把原本的对世界的揭示留归‘单纯情绪’。纯直观即使能深入到一种现成东西的存在的最内在的脉络,它也绝不能揭示可怕的东西等等。”(《存在与时间》第16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在这里,海德格尔明显将批评指向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特别是范畴直观学说。世界及此在的存在是不断生成的,即使是周围事物,也首先作为“上手事物”呈现。而纯粹直观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论认识实际上已把它转化成了“现成事物”。因此,纯粹直观只是非源初的、第二位的认识。这不仅是说理论认识的存在者在存在论上无法摆脱“现身情态”这一生存事实,而且也表明理论认识必然具有相应的,现身情态的特殊情态,即对自然世界(而非周围世界)的现成存在者的先行态度。“领会”是对此在生存可能性的领会,生存的展开状态就是领会。领会是一种对存在的“知”。因此,它具有相应的“视”,操劳活动的寻视、操持的顾视、对生存整体的透视等。“视”作为此在的存在方式,又具有先行的结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先行掌握。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前提的范畴直观并不符合实情。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传统认识论中纯直观的优先地位从存在论上看也是成问题的。直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思维(理论认识)都是从领会中衍生出来的。因此,领会中的思即整个存在者对自身之“在”与所在之“世”的思才是哲学的真正方式。
海德格尔对纯直观的批判给传统的哲学观带来了震撼,他给予单纯情绪以优先地位虽然不大可能说能够扭转古希腊以来二千年的哲学传统,但却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家突破视觉优先而健全哲学生存论基础的努力。另一方面,这也大大拓展了哲学的“合法性”概念的内涵:哲学不仅要沉思,而且要感思。
二、中国哲学中的“感”与“感思”
西方哲学家对视觉的关注使得他们能够直接研究这些客观存在物是什么,而中国的哲学家则关注的是这些存在物对他的作用和他自己正在做什么,相应于此,中国哲学中,对“感”的强调则被放在了基础的位置上。在人与世界万物的交往中,人们最关注的不是看到或听到什么,而是“感到”了什么,即不是视觉、听觉之类的感官而是人心之“感”充当了联系人与世界万物的桥梁。在专论音乐的《乐记》中,这种特征也表现得很明显:“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噇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者。”(《礼记·乐记》)“乐”与“礼”、“政”、“刑”一样都关乎民心,所以一直受到极高的重视。尽管“乐”与听觉有关,但“乐”又非“耳”所能把握:“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同上)对声、音、乐的辨析鲜明地表露出了儒家关注的本体事实:伦理之物。按照这种区分,“耳”所对应的是对象是声、音,心所对应的是特殊的、伦理化的声音——乐。换言之,耳可以充当人与世界万物的通道,但其对应的对象只是具有较低甚至负价值的欲——“声音”。所谓“乱世之音”、“亡国之音”就是能极人之欲(怨以怒、哀以思等)的声音,或者说,它们是与人的欲望相关联的声音。声音、耳这对相互关联的现象在经过伦理定位后就失去被正视的资格。
与耳、声音遭受同样待遇的是目与所看。“耳目”两字的搭配已成为汉语言的习惯用法,“耳目之欲”同样被频繁使用。一般来说,绘画以形色表达为特征,它最重视目与所看。但在中国绘画中,目及与目相应的“色”、“形”、“象”却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地位。“色”在先秦就被早早地规定为主体的欲望或欲望的对象,“食色,性也”,“声色犬马”,“女色”等等言辞就表明了这一点。“形”、“象”的地位则自顾恺之起让与了“传神写照”,谢赫更以“气韵生动”放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模移写”之上。眼耳关乎神明,所以用眼去看说到底是用“心”看,与此相应,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形色,而更重要的是形色之后的“神”或“理”。这在宗炳的思想中得到完整的表述与发扬:“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宗炳《画山水序》)形色之意义不在其自身,而在其为神之栖所。因此,“形似”不如“神似”,“写形”“写真”不如“写意”,宋元文人画正是这种逻辑的产物。
当我们审视中国古典哲学范畴时,我们发现大部分的范畴都象黑格尔所说的那样缺乏纯粹性与抽象性。《论语》中的范畴,如“孝”、“悌”、“仁”、“义”、“礼”、“智”、“信”、“耻”、“忠”、“道”都建立在切己的生存感受基础之上。“本立而道生”。这些范畴的成立不仅不能摆脱经验与具体,而且它依靠个体的经验、体验这些“本”才能实现、成立。“孝悌、其为人之本与?”“孝悌”之所以是人之本是因为个体的存在首先展开于与父母的交往之中,其次密切交往的是兄弟。其所感相应地源于父母兄弟、指向父母兄弟,对他们的感可以说是本然地、自然地、最切己地。感而生情,从肯定方面看,孝悌最近(迩),也最强烈、最根本;从否定方面看,对个体最切己的是“耻”,所以孔子提倡“行己有耻”。“感”涉及他物、他人,但却以内在自我为圆点。“感”的秩序由厚而薄,由近而远,这决定了情感的秩序:“爱有差等”。不管肯定性的,还是否定性的,也不管远近厚薄,内在自我的“感”以“实”为好,所以,《中庸》以“诚”为本,以之为“天之道”;《孟子》立之为人人生而有的“四端”。有德者有言、有道,换言之,没有实感之得,言、道以及一般的范畴就没有意义(本不立则道不生)。
范畴不能离开“感”,或者说,离开“感”而抽象、纯粹的范畴没有意义,更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感”不是西方近现代知识论意义上的感觉,而是“心中的全部(咸,全也)味道(古代号称五味,咸味最为寻常,也最具有恒常性)”。“感”之官是由心统摄的身之整体,而不是眼耳等个别感官。眼捕捉形色的功能是次要的,其最重要的功能是传达内在的“神”。“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顾恺之对眼睛功能的看法具有典型性。耳、鼻、舌、身的功能亦是如此。而且,这些感官以顺为好,以逆为恶,听从它们容易使整个存在陷于不义。“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单凭这些感官一方面无法把握对象的真相,另一方面也不能使整个存在符合社会规范。儒家不信任感官,道家则要彻底堵住感官通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的音、象都不是事实性存在,因此它们非感官所能把握。“心”与人的整个存在相同一,“心”中全部感受才可使多样的范畴具有意义。“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庄子·渔父》)。道家追求的是真心由内而外地流露,儒家则追求内外一致的诚心。真心或诚心动起来,“哀乐”乃至一般的概念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同样,有真心或诚心之感,才能领会这些概念的意义。因此,惟有“心”能感能生。“感”有多样性,建立于其基础之上的范畴亦包涵着丰富而多样的“感”,且因“感”而有层次性。《易·咸卦·彖传》:“《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现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地本是二气感应而化生,由相感而相通。圣人则由感天地、感人心而通而知天地万物及人心。进一步说,由所感就可知天地万物的本质(天地万物之情)。“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传》)。圣人设卦观象,以简易的线条(爻)与图象(卦)表达事物的情状及其变化,并用这些简易的线条与图象动天地、通万物。圣人以及后人在使用这些线条与图象时必须有“感”才能通天地、通万物、通天下之故。
“感”不是情,不过感可生情,情为实,由感而知人生的实在。儒家立足于“感”,“感”是实在且可以推己及人。他们认为,这种“感”是确证人生实在的基础,换言之,无感则无实在的人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孟子·告子》)。儒佛关于人生实在与否的争论亦是如此:佛家把“感”空化而儒家实化,“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无切己的“感”而推是虚假的观念(儒家眼中的墨家,佛家),不把“感”推出去则是“私感”(儒家眼中的道家)。柏拉图为代表的西哲则相反:“真正的哲学家,……他的灵魂,尽量超脱欢乐、肉欲、忧虑、怕惧等等。他看到一个人如有强烈的欢乐、或怕惧、或忧虑、或肉欲,这人就受害不浅了。……害处在这里:每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受到了强烈的快乐或痛苦,就一定觉得引起他这种情感的东西非常亲切,非常真实。”(《斐多》第47~48页)超脱感情才可以客观地看:在科学中客观地观察(用肉眼看),在哲学中冷静地沉思(用心眼看)。
“感”的秩序也是进一步思考的逻辑原则,或者说是感思逻辑的原则。在儒家,爱有差等,以“爱”为基础的德目也是有秩序的,即以“感”由近及远,由厚至薄,由己至人。“修齐治平”的顺序是这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亦根据这个秩序展开。“感”是“思”的基础,亦是“思”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返身而识切己的“感”又称“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反省指向的“忠信”都是实有诸己的感受。通过省察自己切己的感受而认识自己,发展自己,这是儒家“知”即“知人”的首项任务与基石。认识他人、人群及人世间都基于自我内在的“感”。知人的方式是“恕”,即推己及人,把切己之感推给他人。同为人,己之所感,他人所感必不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人之欲与不欲在有了自身这个绝对的尺度条件下就可以把握住。
对于善感之心来说,对整个人起作用的首先是质料与形式统一的存在者,而不仅仅是作为形式的对象。因此,建立在“感”之上的“感思”与范畴亦不是形式性的,而是具体、灵活的实质性的范畴。“……者,……也”的定义方式就是这样,它是一种情境定义,是特定情境下对主体起作用或与具体情境中的主体相关的对象之所是。显然,这种定义更贴近一定时间维度中存在者之所是。如果说认识的任务是获取“本质”,那么,“感思”之所得就是这种一定时间维度中存在者的本质存在。有“感”就可“通天下之故”,就可以“通古今之变”,也可以“究天人之际”。
“感”的功能基础并不是眼耳等感官,而是整体性的心灵气质。儒家教化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变化气质”、“健全感受”。材质不同,但经过教化而可以变化气质,过者抑制之,不及者张扬之,其目标都是健全、丰富人之感。有了健全的“感”,才可能产生健全的感思。反之则不然。孔子批评宰我“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其所叹即感的缺失或遗忘产生不了健全的思考。只有具备良好的气质,才会产生合适的“感”。所以,儒家、道家都在做修养工夫,都在“正心”,但正心的目的不是使人无感无心,而是使其感其心合乎各自的标准(“得其正”):“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有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则不得其正,但无心则身亦不可得而修。《礼记·礼运》:“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圣人的责任是改变人情,使之能推能思:“人情者,圣人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大同社会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将“感”推及他人、万物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与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大同之下的社会是“感”不能推及天下,或“感”有限的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是谓小康。”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虽狭隘,但终归有“感”,因此它离大同不远。换言之,有感就有希望,能将此感推出去就可使大道呈现出来。圣人的使命就是唤醒众人的感,并使之推出去。《礼记·祭义》:“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贵有德,何为也?为其近于道也。贵贵,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亲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也。”这五种行为原则的基础都是切己的“感”,它们都是在对君、亲、兄、子自然亲切的“感”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近于”即是说它们离“感”不远。《礼记·丧服四制》说得更明确简洁:“丧有四制,……有恩有理,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由生而知死,鬼神亦是生的延续。“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同上)。鬼神在佛教、基督教都是很远的另一世界,而在儒家感思之中,鬼亦不远(“归土”)。
中国哲学独特的生存论基础与运思模式也决定了“感”之得与达的独特性:所感涉及物但不是物,它没有确定的形状,而是无形状的“意”。传达、表达“感”的不会是抽象、普遍的形式性范畴,而是贴近“感”之体的“言”、“书”、“象”与“意”。感化为言,感化为书,感化为象(包括实象与假象),感化为意,这样感就可以“达”(表达),感可表达就可以推,可以悟(无须推理直接领会)。不过,感悟是直觉而不是直观。就两者的身体基础或形下方面看,直观是视觉活动,直接地看;直觉是整个人的感,直接感觉到。就两者形上层面看:直观的形上层面即理智的看(心眼的看);直觉的形上层面即形上心灵的感。对于言、书、象、意能否及如何传达“感”,中国哲学进行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探讨。《系辞上传》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汉语言、文字以及艺术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表达心中之“感”。“言为心声,书为心画”。“言”与“书”不能完全达意就借助“象”。“象”有实象、假象。实象即拟诸形容,象其物宜(语言可以做,如“六书”之“指事”与“象形”,但不能完全做到);假象是以有形喻无形的想象(语言也可以做,如“六书”之“会意”,但不能完全做到)。“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手舞足蹈是一种“象”,但它不是为了展示“形”,而是为了表达“乐”之“感”。
通过以上简要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哲人在与世界万物的交往中集中关注它们对自身的作用,优先关注交往过程中的所感,从而把所感理解为本体论事实,在“感”的基础上生发出普遍的范畴,以“感”之远近厚薄作为思考方式,并探讨了概念之外的其他表达方式。由“感”而思当然不是剔除经验的“纯粹”,也不是远离具象的“抽象”。但感思却是理解、把握我们所在之“世”及世中之“在”的有效方式,同样也是中国人“在世”的重要方式。
三、感思、沉思与合法性
“感”把世界拉近,使之“来”,“看”把世界推远,使之“去”;感思关注外物对主体的意义而不能面向事物本身,因而不能正视事实界,沉思关注事物本身而不顾及外物对主体的意义,因而不能正视意义界;善感而重与行一致的“知”(知接、身知),重视存在中展开的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善看而重视独立的知识系统;与世界万物相遇展开感与感思,从而使静观主体、科学知识主体即认知主体不能建立起来,而与世界万物相遇展开看与沉思,则无法认识清楚自身只“在”与所在之“世”。中西方哲学家对这一点皆有高度的自觉。正如前文所说,合法的一个意思是合乎法度,即合乎思的规则。对于沉思与感思来说,合乎法度都是不成问题的。但应当看到,合法首先是“合时”,即合乎自身之“在”与所在之“世”的展开之时,合法性首先是合时性。思什么与如何思由我们自身之“在”与我们所在之“世”规定,在我们需要“感”与“感思”的时候,“看”与“沉思”就不具有合法性。反之亦成立。
当我们以合时性来理解合法性,面向自身之“在”与所在之“世”,认识到方法与存在的统一性,我们就会看到,当前的哲学应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每个人塑造成既能把世界拉近,使之“来”,也能把世界推远,使之“去”,来去自如的存在者,即如何把每个人塑造成兼具沉思主体与感思主体于一身的存在者。这样的存在者,在他需要感思的时候,他能悬置更具有科学性的“看”而去感而感思。在他需要“看”清楚的时候,他能“悬置”(而不是否定,不是牟宗三的坎陷)善感之心而去看与沉思。在此视野下,中国哲学合法性研究的使命就是探究“感思”是否曾经合乎中国人自身之“在”与所在之“世”的展开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