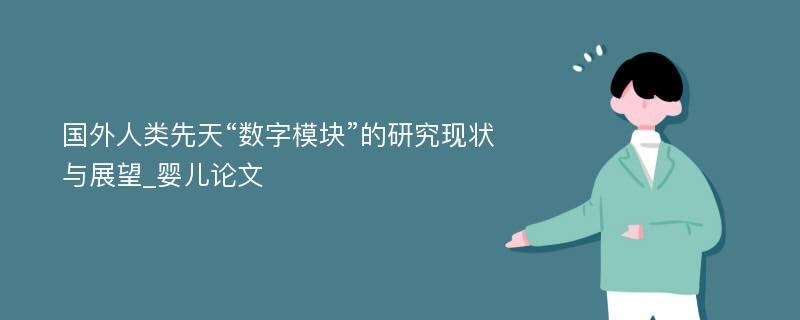
国外人类先天“数字模块”的研究现状及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天论文,现状及论文,模块论文,人类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目前,有关数能力(numerical competence)的性质和起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先天的“数字模块”作为儿童和成人的算术能力的基础。由此引发出来的议题有,该模块是如何产生的,它对数量的表征(numerical representation)有哪几种机制?如何在儿童发展中发生转变以拓展数字模块的功能?该模块系统能否和非人类动物的数能力系统相比较,以及非言语数量表征和言语符号数量表征的关系如何?或者说数字和语言存在哪些关系?本文旨在就这些议题对国外最新的研究进展进行介绍,并对未来发展作出展望。
2 作为数学能力基础的数量感
2.1 数量感的意义——算术能力的基础
数量感(numerosity)是指我们对集合的与数有关的抽象属性的知觉。数的独特意义抽象于物体本身,它不是指单个物体或某个物体的性质,而是任何集合的特性,这个集合可以是物体、声音或者其他抽象物(如:几个愿望)等。而通常所说的算术操作都可以定义为对集合及其数量感的操作,加法、减法、除法、乘法等可以看成是对集合操作的产物。数量感是数学能力的基础,这一点上已达成共识。但是就数量感如何起源的问题,经典皮亚杰理论和当代模块理论存在着分歧。[1]
经典的皮亚杰理论认为数量感能力的出现取决于一些事先即具有的能力的发展(先决条件),数学能力是与逻辑推理、抽象推理的能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皮亚杰认为,数量感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对集合中的物体的知觉线索加以提炼从而得出该集合的抽象的数量属性。要完成这种抽象的提炼,必须先具备一定的认知能力。他把算术看成是逻辑的一部分,认为数学能力是具有领域普遍性的。
而近来相关领域的研究[2] 表明,婴儿不需要语言和抽象推理能力,甚至不需要对事物进行操作就能对世界的数量属性作出反应。对于婴儿表现出的这种先天能力,Butterworth用“数字模块”(number module)来解释,而Spelke等人用两个“核心系统”(core system)来解释。他们都把数能力看成是领域特殊性的,认为大脑中存在着处理数量信息的专门系统。该系统具有自动化、封闭性等模块的特点,因此这两种理论都可以归于模块理论的领域[3]。
2.2 数量感的检测、再认和操作
“数字模块”理论假设人和动物都拥有基本的生物能力,即检测、分辨和操作数量感的能力。当前该领域的实验研究就是从数量感的检测、分辨和操作出发的。不同范式的运用对于“数字模块”理论及实验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同的研究者们使用不同的被试,如婴儿、成人或动物以分析数量表征的发生发展机制;他们还控制多种实验条件,例如习惯化—非习惯化任务中需要控制物品的连续量(continous quantity),包括图像面积和轮廓的连续量等等,以便于数字模块深层运作机制的研究,验证理论假设并提出更合理的理论解释。
下面介绍几个典型的实验研究范式。
2.2.1 习惯化—去习惯化范式
Starkey,Cooper第一次采用了经典的“习惯化与去习惯化”研究范式,以4—6个月的婴儿为被试,向他们呈现点阵,观察他们对不同数量的点阵的反应。研究发现婴儿看新数量的时间更长,得出婴儿对点的数量敏感的结论。此后,Starkey,Spelke[4] 以6~8个月的婴儿为被试,改用不同物品做刺激,发现婴儿总是对数量敏感。Van loosbroek,Smitsman[5] 对5~13个月的婴儿,Brannon[6] 对11个月的婴儿在控制不同实验条件的情况下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2.2.2 算术期望实验
Wynn等[7] 对4~5个月的婴儿进行算术预期实验,看他们是否对加减引起的数量感变化敏感,即是否能分辨不同的数量感。例如,舞台上有一个布娃娃,用幕布遮住,再放入一个布娃娃,然后拉开幕布。算术期望应该有两个布娃娃,而研究者设置另外一个不符合期望的只有一个布娃娃的结果。结果发现婴儿对于不符合算术期望的结果看得更久。减法操作的实验结果也相同。此后,该结果被多次证实,如Simon等[8] 在3~5个月的婴儿身上也发现了相同的现象。
2.2.3 比较选择任务
该类任务一般用于研究非言语数量表征,针对不能使用言语符号的被试(儿童或动物)。在实验中,主试在被试眼前往暗箱投放定量的食物,结果发现在小数范围内被试能选择较多的食物[9,10],这表明他们能够跟踪小数量集合的数目,即分辨不同集合的不同数量感。
2.2.4 操作任务
该任务采用被试主动操作的形式,用于研究人类和非人类的非言语数表征。例如,Platt和Johnson[11] 研究老鼠对特征数字的心理表征,任务规定老鼠按键次数和目标数相等时才能进食。Moyer和Landauer[11] 等对成人采用不使用计数的按键任务,研究成人对目标数的心理近似表征。后来Cordes等人[11] 对此任务做了小小改进,让成人被试一边说话,一边做非计数按键任务,以控制实验中的记忆因素。
3 数字模块的内在机制
有关数字的内在心理机制,目前国外的研究热点集中于究竟存在几个表征系统以及信息在表征系统间如何转换的问题。Butterworth[12] 在《数学脑》中提出“数字模块”的概念,强调它是人类数量感的先天机制。根据早期的神经心理学数据以及数字任务与记忆推理等一般认知任务的实验研究成果,他提出“数字模块”是一个高速的、自动的、领域特殊的认知模块,具有专门识别小数量感的大脑回路。Feigenson,Dehaene和Spelke[13] 提出数字“核心系统”的概念,该系统也同样具有上述认知模块的性质。不同的是,他们认为人类拥有两个数字核心系统,分别负责不同的数量表征。一个用于大数近似表征,另一个用于小数精确表征,并在婴儿早期就被激活。从实验数据上来看,这两个系统确实存在分离,但是它们能否用同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还尚待研究。另外,假如存在两个系统,信息在系统间如何转换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下面着重介绍这两个数量表征系统以及相关的进化机制和神经机制的研究情况。
3.1 近似数量感
Xu和Spelke采用习惯化范式实验研究得出,控制其他变量,婴儿能对大数量感作出反应。然而他们的数字分辨依赖于数量的比例,即存在比例限制。6个月的婴儿能分辨1∶2(8∶16,16∶32)的比例,但不能区分2∶3(8∶12,16∶24),而同等实验条件下,10个月的婴儿能分辨2∶3。这表明婴儿该系统存在发展性变化。然而,在控制连续量的情况下,婴儿不能分辨1∶2、2∶3、2∶4。他们还研究了儿童和成人的近似数量感,让被试在不使用计数的情况下估计点阵或声音序列的数量,发现了比例限制以及跨感觉通道的一致性。该研究还发现,非言语的数量表征也存在比例限制。[14]
3.2 精确数量感
通过对小数量的研究,Xu和Spelke[14] 还得出,人类拥有精确的数表征系统,能够精确追踪个体数量并表征物体的连续量。他们以10~12个月的婴儿为被试,发现在选择饼干任务、习惯化任务和搜索任务中婴儿能分辨物体的精确值。在控制数量的条件下,婴儿还能够表征物体的连续量。而早期的对点阵数量的目测任务的成人研究[15]表明,1~4范围内反应时和错误率都基本相同,但4以后反应时就持续上升。该结果有两种解释:一是小数量范围的表征机制不同于大数量,二是小数量的精确表征和大数量的近似表征基于同一个系统,只是因为小数量范围内产生的误差非常小,才被认为是精确的。目前,就此目测任务的解释而言,是否存在这两个系统还没有定论。
但是,Xu和Spelke声称,该两种系统确实存在分离。表现在:大数量的分辨和比例有关,而小数量的分辨仅仅和4以内的具体数有关; 大数量的分辨不受物体的连续量的影响,小数量却与此有关。这种分离表明大小数量表征是由功能不同的两个系统实现的:大数量激活近似数量表征的系统,可以比较数量的近似基数值;而小数量激活个体追踪系统,可以表征物体的连续量或个体的数目,并对此进行操作。
3.3 模块系统的进化机制
从比较心理学的动物行为研究数据[9,10]来看,动物也显示出和人类相同的局限,这表明数字模块系统有其系统发生的进化机制。老鼠的按键任务的结果显示,它们的数量表征的成绩曲线符合线形模型,目标数值越大误差也就越大,这表明它们也依赖数量的近似表征系统,同时该系统也具有跨感觉通道的一致性[6]。在灵长类动物中,也发现有近似的数量表征,他们能够完成5~9之间数距差3以上的数量分辨任务。同时,非人类动物也能表征小数量物体的精确数量,大猩猩在苹果片的选择任务中,能够正确选择4以内的任务。还有其他范式任务也证明这一点。
3.4 模块的神经机制
功能性核磁共振揭示,顶叶特别是脑顶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i,IPS)在数字加工和算术任务中被激活[16]。对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表明,IPS和脑角回(angular gyrus)对完成基本的算术任务有重要作用。Butterworth研究得出,简单的算术能力,例如估计小数量集合的数量,很可能是右IPS的功能[17]。然而目前为止,我们尚不清楚婴儿大脑中该部位如何因数字任务的操作而变,因此我们对数字模块的发展如何影响数能力的发展还不得而知。Isaacs,Edmonds等人[18] 利用分组实验研究表明算术能力缺陷病人的左IPS的灰质更少,由此推断灰质与低算术能力存在某种相关,但尚不清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发展性失算症DD(Developmental Dyscalculia)病人的系统性研究显示了遗传的重要性。双生子研究得出,同卵双生子同时患有DD的概率比异卵双生子要大。家族研究中也发现,同胞兄妹同时患有DD的概率是普通情况下的5~10倍。威廉斯综合症患者以及特纳综合症患者都表现出了基本数能力的缺陷。可以看出,目前基因机制的探寻尚处于起步阶段,而各种相关病症的基础还依赖于基因学的发展[2]。
4 数字模块的功能拓展
当前,“数字模块”的研究不仅仅集中在数的先天表征上,研究者们还关注“数字模块”功能的拓展——计数以及算术能力的发展。计数机制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计数原则的研究,而后开始了动物和人类的计数机制的综合性研究[11]。算术能力发展的研究热点目前集中于DD儿童算术能力缺陷的研究上[19]。
4.1 计数
人类的基本数能力和动物一样,仅仅是对小数量物体进行数目跟踪、算术预期,对大数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比较。然而不同的是,人们掌握了一整套的数词系统和计数原则。计数正是联系数字模块和文化概念工具的纽带,由此,数字模块的功能得以延伸从而超越了人类先天数字模块的局限。
Gelman和Gallistel[20] 总结出了几个计数原则:一一对应原则、固定次序原则、基数原则、次序无关原则以及物体种类无关原则。儿童学习数词之初,并不明白数词与集合数量之间的联系,只有在掌握了上述原则之后才掌握了相关的概念工具。
Gelman和Gallistel[11] 对计数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从研究动物计数开始,继而研究人类非言语计数机制,接着研究不依赖计数而是依靠感知小数的心理机制,最后拓展到言语计数系统的研究。他们倾向于认同Meck和Church[21] 的动物计数模型,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在非言语计数时,都使用依赖于计数原则的累加模型,能持续产生可数、有序、定量实数表征。随着各种数词和数符号的使用,人类在非言语计数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了数词与非言语系统的双向映射。Gelman认为,非言语计数系统为言语计数的掌握提供了相关结构,而儿童数词的学习在于掌握特定的言语计数系统。
4.2 算术能力的发展
算术能力的发展是建立在基本数能力的基础上的。儿童一般在掌握计数原则后开始学习简单算术。已有的算术能力研究包括儿童早期加法策略研究,Butterworth[12] 研究表明,儿童计数策略的提高基于对数量感的理解。另外,研究者对成人的算术问题也有初步研究,例如有关算术事实的形成机制的讨论,强化学习模型以及言语联结模型都强调学习的作用,后者更注重语言的作用。而Butterworth[3] 利用加法问题解决实验和乘法实验证明,算术事实的储存并非机械联结形成,而是以数字大小的形式储存,反驳了以上两种模型的观点。
算术能力发展的研究热点目前集中于DD儿童的算术能力缺陷的研究人[19],不过更多的是算术能力与其他认知能力的相关研究,以及初步的脑功能定位研究。Geary等人[19] 认为数能力的缺陷和语义记忆困难有关,并认为工作记忆的缺陷与DD相关。但Butterworth认为,数能力和语义记忆是相分离的,DD的根源可能是“数字模块”功能的问题。因此DD的应用研究必须加强对基本“数字模块”的研究,而DD的研究对“数字模块”的理论研究也有推动作用。
5 数字和语言的关系
一些不专门处理数表征的认知能力对获得算术技能是很重要的,这些认知能力包括工作记忆、空间认知、语言能力等等。这些认知能力和算术标准成绩之间的相关已经得到广泛的证实。但是,究竟是好的算术技能有助于提高工作记忆、空间或语言任务的成绩,还是所有这些任务的成绩受到一个共同的因素影响,它们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不清楚。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和语言的关系。
关于数字和语言的关系,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看法。Whorfan认为语言是数能力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而Butterworth、Gelman、Carlesmith、Carey等人把语言理解为促进数字基本能力进一步发展的工具[22]。他们认为,首先有必要区分数量感概念本身以及特殊数量感的表征,然后进一步分析,究竟是数量感本身依赖语言,还是特殊的数量感依赖语言。Gelman和Butterworth等研究了数词在数概念发展中的作用,通过DD儿童的数能力发展研究以及亚马逊印第安文化的数词研究[23],综合行为数据和神经科学的证据,得出数能力在系统发生的起源和神经基础上都与语言能力相独立。后天的数词系统虽然有助于计数和算术的学习,但对数量感本身并不产生作用。Dehaene等人[24] 曾提出了三重编码模型来解释人的数量表征系统,包括精细数量感、近似数量感和言语编码表征。该模型认为数字比较任务基于“近似数量感编码”,而算术事实以“言语编码”方式表征,两者如何作用于算术过程还不清楚,这一整合的模型尚需进一步实验验证。
6 评论及展望
从当今数能力领域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数量感的先天机制问题。习惯化—去习惯化范式的诞生为婴儿数量感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天地,同时也引发了数能力的领域特殊性的一系列研究。目前,在数量感有其先天的表征系统这一点上是没有多少争议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数量感的先天机制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后天数能力的发展。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研究者们从先天系统的运行机制上开始讨论,从系统发生的角度研究先天系统的进化机制,引申出人类与动物的数能力的连续性问题,并辅以脑成像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对此进一步阐述;从个体发生的角度着重研究先天基本数能力如何在个体发展中转变,由此引申出后天文化资源如言语数词体系与数能力如何相互作用的课题。[12]
从数字先天系统的运行机制上看,Spelke和Carey等人认为存在两种数量表征系统,即精确的小数表征系统和近似的大数表征系统,利用前者婴儿能够分辨4以内的数的增减,利用后者婴儿能分辨满足一定比例的大数集合。从实验结果上看,大数和小数范围的数量表征是分离的,但这种分离是理论解释造成的分离还是实际机制的分离?研究者假设理论上存在两种先天的数字核心系统,但相应的问题接踵而来:该两个核心系统之间的关系如何?人接受的数字信息如何在两个表征系统之间转化,以及什么因素决定某一情境下使用哪一种特定的表征系统?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寻两个先天系统的共同解释模型,在实验方面和动物行为方面寻找更多证据,同时还可以从脑损伤病人的研究中寻找两种机制的共同点和分离处,以加深对数字先天表征系统的认识和理解。
从个体发生的角度来看,后天文化概念工具的获取是个体数能力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数词的掌握有助于儿童计数能力的发展,以及后天一系列数概念的掌握。但是,对于具有先天数能力的人类为什么在后天数学学习中会遇到一系列困难?为什么掌握了文化工具的成年人仍会使用非言语近似数量表征系统?目前,有关先天数字模块与后天数能力发展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一方面先天机制的脑功能定位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难以从脑发育来研究数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从当前DD儿童的研究来看,先天缺陷如何影响数能力,是否由此导致了后天能力上的选择性缺陷?相关的问题还有,儿童数能力的发展是否存在一个关键期?要解决这一系列先天后天相互作用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探索数字加工机制以及文化因素的影响。目前DD儿童的研究有望在该方向上取得进展,同时Gelman等人对亚马逊印第安文化的研究也为语言与数字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例证。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DBA05004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4BJY003)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A0411)资助。
标签:婴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