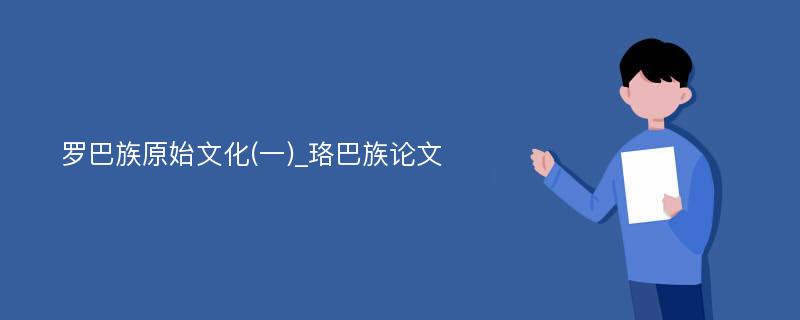
珞巴族原始文化(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珞巴族论文,原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原始的宗教崇拜祭仪
地处门隅东部和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的洛渝地区的珞巴族,其社会至解放前夕,还没有完全摆脱石器和木器工具,生产以狩猎为主,兼及刀耕火种,交换方式为以物易物,氏族和部落是其基本的社会组织。由此决定了珞巴族信仰的宗教完全处于原始和原初的阶段,他们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死,但还没有形成神灵与鬼灵的区别,凡精灵、鬼魂、神怪、妖魔等都统称为“乌佑”。乌佑种类繁杂,无所不在,故而祭鬼巫仪也繁复众多,这里择要举述几例。
1.自然崇拜祭仪
珞巴族认为天是男性,地是女性,天与地是兄妹俩,后来结为夫妻,开创了有性生殖的新纪元,创造了万物和人。米古巴、米辛巴、达额木、希蒙和巴达姆诸部落,每年外出交换前,都要在村寨内设置集体祭祀的火灶,把供物点燃成烟,以祭天的精灵;米古巴人,每年2月集体举行祭地仪式,在村外朝庄稼地多的方向搭一草棚,杀牛祭献乌佑,祈求丰收。祭日月:珞巴族神话中说,天地结合后生了个太阳“冬尼”是女性,生了个月亮“波罗”是男性,姐弟俩后来结为夫妻,因为他们拥有光焰和明亮,赶走了曾笼罩着宇宙的黑暗,所以阿迪人把他们看作真理和正义的监护人,在村落议事会议开始时,首先要举行向太阳和月亮祈祷的仪式。祭风、雨、雷、电、雹等自然灾害的精灵:阿帕达尼人在每年3月的科尔兰仪式中,以鸡祭祀“尼黑”乌佑,祈求免遭雹灾;祭祀“塔页”乌佑,祈求免遭雷击和淫雨;崩尼人则以猪、鸡作供,使人们免受淫雨之害。
2.各种狩猎祭仪
崩尼、苏龙和崩如等部落,每每出猎之前和猎获之后,都要举行祭祀仪式,巫师在悬挂于居室墙上的各种野兽头骨前,搭起一个祭台,供上猪、鸡、饭、酒等祭品,且要迷狂起舞,念诵咒语,祈求兽之乌佑赐以猎物和丰收,氏族内全体男子则需肃立于祭台前,以示虔敬;对凶恶的猛兽祭祀更为隆重,如有人被毒蛇咬伤,马上要请巫师杀牲祭祀;人们在神判时,也请蛇神来判断是非;刻有蛇头和蛇身图纹的手镯,除作装饰外,又被视为护身符。对山鬼石灵的祭仪:珞巴族居于高山峡谷林区,对险峻的高山十分崇拜,每当出征、出猎或外出交换时,均须杀牲祭祀山鬼。如,博嘎尔人在出征前后都要到“格拉另冬”灵石处,绕石转圈和祭祀;阿巴达尼人认为突兀而起的大石,是主要精灵聚居处,每逢“莫朗节”或其他节日必须进行祭祀。许多部落还保留着栽石立约誓盟的古俗,如米林的帕宗拜嗄、墨脱的东布村、卡布村和麻迪村都有用以誓盟的高大立石,立约誓盟时祭以牛、羊、猪、狗等物。还有对树精草鬼的崇拜:博嘎尔人称怪树精灵为“特凌阿宾”,草鬼是“阿岗姆得贝”,竹子精是“达吉日”。据说它们都很有灵气,故在狩猎祭仪中,都有这些灵物作祭器或供品,平时要倍加保护,不得随意砍伐或剖刈。
3.各种农业祭仪
崩尼人认为土地和庄稼是由一个叫“弱得玉洛布”的乌佑统管,凡砍伐树林、除草、开荒种地、收割开仓等,都要选择吉日,进行杀牲祭祀。遇到自然灾害时,在受害的庄稼地里搭祭台,杀猪羊作牺牲,请巫师跳鬼,念诵咒语,驱除带来灾害的女性乌佑。博嗄尔人在春播后,于主要作物地中央搭一祭台,供以粮、酒、肉等,以祈“斯金”地母赐福于人。米古人每年2月进行集体杀牛祭地仪式,在村外朝庄稼地的方向搭一草棚,草棚边放两个竹槽斜立着,将调好的包谷糊从槽上往下倒,槽中流的糊快而多,就意味着丰收有望;这时,一边念经祈祷,一边将一头早已准备好的牛杀了,把牛肉分生、熟两种切成小块,往草棚上抛掷,意为让牛神出来保佑庄稼丰收,驱赶各种病虫兽害。
4.图腾崇拜祭仪
苏龙部落内还保留着许多以图腾崇拜相联系的氏族组,像石鲫和石脚是一个氏族组,分别以哈意树花萼和竹屑作为自己的图腾,属于植物类;嘎根和嘎得是一个氏族组,分别以灶炭和灶灰作为自己的图腾,属于无生物类;布更和布耶是一个氏族组,分别以鸡蛋和青蛙作为图腾,属于动物类。在苏龙部落内所信仰的30多种图腾中,还有以自然现象如太阳、月亮为图腾的,以工具如刀作为图腾的。一则关于虎、刀图腾由来的神话中说,尼英、尼略两姐妹住在全为女性的村寨,她们为寻找配偶到处奔走,姐姐尼英遇到一只老虎,不仅不伤害她,反而还给她送肉吃,随后有了感情结为夫妻,生儿育女,繁殖成后来的巴得(虎)、育唧(刀)两个氏族。珞巴族对每一个图腾都有特定的崇拜仪式,以虎为例,他们称其为“哥哥”、“叔叔”或“爷爷”,不能直称虎,一般也严禁追猎或伤害它。如果无意中打死了老虎,就像对待长辈一样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要在家内设虎灵堂,供献祭品。出殡时,全家人列队守灵致哀,打虎者头戴孝帽,腰系孝绳,背着虎头骨和竹编虎身前行,巫师和本氏族的男性成员随后,边舞刀,边呐喊,把虎的头骨和偶像护送到设置在村外的乌佑住房,以示将虎魂送还。仪式活动一般要进行3至9天,期间大量杀牲,以酒肉待客,但女子及猎者家人禁吃虎肉。
5.祖先崇拜祭仪
米日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猪生的。有一则传说说,米日村的另一支珞巴族,一天带着猎狗上山打猎,遇到一头野猪,就让狗去追猎,野猪跑得很快,钻进了自己居住的洞穴中,狗和猎人们把此洞穴团团围住,等了很久却不见野猪出来,反而从洞中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大家冲进去一看,只有一个婴儿,野猪却不见影子了,猎人们议论纷纷,有说是鬼,有说是人,最后结果是先把婴儿抱回村去养着再说。这小孩长得特别快,最后成了米日人的土王,米日人都成了他的后裔。野猪因此也就成了珞巴族图腾崇拜之一,在现实生活中一般是忌讳捕食,即使在没有其他野兽捕食时,在捕猎到野猪后,也绝不会马上就吃,而要放一个晚上后才能食用。他们认为野猪刚打死,其灵魂还存在于肉体内,这时吃了肉,就把灵魂也吃了,那就会遭祖神猪灵的惩罚;等一个晚上以后,灵魂就离开了肉体,这时食用不会伤害祖神,但对捕获的野猪要进行一番祷告,大意为:我们是不想捕杀你的,但实在没一点别的兽肉可以充饥,请让我们为你念经,祈祷你早点离开肉体去再生,保佑我们打猎丰收,有更多的其他兽肉可吃,我们再不会伤害你!珞巴族认为妇女不育,或流产、早产、难产、死胎等现象是让卜乌佑干的,就需要杀猪驱鬼。杀猪时,从猪的腰间砍断,掏出肠肚等内脏,将鲜血淋漓的整个胸腔戴在该妇女头上,待该妇女头上、脸上和衣服到处沾满了鲜血才取走,并将该妇女的沾血衣服拿去烧掉。这样“让卜”恶鬼就会被驱除了。
6.占卜师“米剂”
“米剂”,是珞巴族巫师中的一种,一般由男性充当。珞巴族对巫师十分崇信。有一则神话说,巫师是站在人间和鬼界的门槛上,一次祖先大神达尼的两只眼睛被魔鬼摘走,无神看管,妖魔鬼怪统统跑出来,经过巫师面前来到人间为非作歹,达尼不忍心看到人们受害,就请求巫师作法,宰杀牲畜,以供祭献,驱赶鬼魔,从此开始实行祭祀和巫术。珞巴族举行巫术时,首先由占卜师米剂占卜问鬼,杀鸡看肝,卜定吉凶。米剂披头散发,头抹三道酥油花,呈“川”字形,身佩长刀,一手持鸡,一手持珞巴小刀,一边口诵自编卦词,一边杀鸡取肝,用水洗净,察看肝纹,以其正反两面肝纹的颜色、明暗、凸凹,以及血脉的粗细、曲折、起迄点等征像,判出祸源,触犯了哪种乌佑,需要何种祭祀。博嗄尔部落另约氏族的米剂达捏,在一次为病人举行的占卜中,问鬼的卦词是:
是来自左边的乌佑么?是来自右边的乌佑么?
使这个不幸的人生病的,是你或是你这个不安份的精灵么。
你们这些贪婪的精灵啊!我让不幸的人儿满足你们的欲望,
你们快快说出你们的渴求,我让不幸的人儿献祭供养,
你们不要藏匿你们的面孔,听从我的吩咐快来鸡肝里显像。
米剂在心中暗问一种鬼,杀一只或又一只鸡,直到肝纹所显示的卦像与所暗问的鬼灵相符为止。
7.祭司“纽布”
珞巴族祭灵跳鬼的巫师称为纽布,一般由女性充当。据说成为纽布的女巫,本人曾发过疯,裸体奔窜于各个村寨,抓破自己身上的皮肉,并敢于跳崖投江而竟然不死者。这就说明一种有威力的精灵或鬼魂附着其身了,于是让她向老巫师学习行巫,便成为新巫师。博嘎尔部落萨吉氏族所进行的跳鬼仪式是,在米剂占卜之后,纽布身披红色毛毯,手持大刀(或是削尖的竹竿和木棒),刀尖朝下,站在一个1.5米见方的晒箩里,从靠近火塘一边开始,脚不离箩,带动晒箩一步步擦地而转,同时人也自身旋转,进入一种如醉如痴的迷狂状态,并且一边转动,一边念诵咒语。达木人的女巫称为“巴木”,巴木跳鬼时头戴五块竹片做成的“山”形高帽,帽的两侧装有两只大耳朵,帽沿悬挂数条长及脐部的串珠,身穿长袖缟衣和裙子,左手持铜铃,右手持鼓捶,一边摇铃击鼓,一边念诵咒语。
二、奇特的部落氏族社会及其婚姻
1.部落的分布和迁徙
“珞巴”,这一族称来源于藏族对居住在广大珞渝地区的人种的习惯性称呼,意为“南方人”。在珞巴族内部,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族称,各部落都有自己不同的自称。在整个珞渝地区有20多个不同自称的珞巴人部落。从藏汉文资料和珞巴族的许多传说中可知,珞巴族大概是由青藏高原东南部一带的古老群体中的一支或数支蕃衍而来的。东部的米古巴部落是从北部的波密迁徙来;靠近下察隅的义都部落,他们的祖先也是从北部的巴塘(另一说是北边的藏区)向南迁来的;达额木部落原先住在墨脱一带,约于200年前,因门珞两族械斗,珞巴人败了向南迁徙至现在住地;据博嘎尔部落的传说,始祖阿巴达尼原住在工布一带,后迁到米林村的巴登嘎定居了一段时间,生了三个儿子,老大当邦带着家小往西南方向走,一直迁到南方的西巴霞曲流域,后来成为德根部落;老二当坚带着家小沿雅鲁藏布江往东、往南走,一直到墨脱及其以南地区,后来演变成希蒙、民荣两部落;老三当日带着家小先迁到米林西南的纳玉山沟定居,到他们的子孙当波和嘎尔波兄弟时,又顺着山沟往南,走到德楞邦地方,兄弟俩以射箭决定不同的去向,当波的箭落到阿多地方,他一家就迁到了那里,后来成为帮波部落,嘎尔波的箭落在果落双双,即后来的马尼岗,他一家就迁到那里,其后裔就是博嘎尔部落。住在珞渝最西南的阿帕塔尼部落,传说他们的祖先也是来自北方。
2.部落社会的组织形式
在珞巴族的部落社会里,构成部落的基本组织是氏族,如博嘎尔部落有萨及、东乌、另腰、海多、达芒、崩英和嘎若7个氏族;米古巴部族有波觉、嘎窝、雅西和米日4个氏族;最多的民荣部落有31个氏族。每个氏族以父子连名来维系父系氏族制度,即在每个人的名字前冠以父名,同样父名前又冠以祖父名。如某人的祖父名叫巴都,他父之名叫都戈,他本人名叫戈里,排列起来就是:巴都—都戈—戈里。但在日常生活里,人们习惯略去父名,男子在本人名前加“达”音,如“戈里”变成“达里”,女子在本人名前加“亚”音,如“戈佳”变成“亚佳”。
在珞巴族社会里,若干氏族组成一个部落,其部落组织并不很完备,既没有部落议事会之类的常设机构,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部落联盟。就其社会作用而言,部落组织远没有氏族那么重要。但是,珞巴族社会形态基本上还保留了部落制的社会组织原型,如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特的名称,一般是该部落的男性祖先的名字;有一定的地域;基本上各有自己的方言;有共同的节日活动;有临时的部落议事会和军事首领;部落可以包括不同血统的氏族;部落规模也可以有大有小,大的如希蒙、崩尼两个部落各有3万人,小的如玛雅部落仅有30余人;在一个部落中,尤其是人数比较多的部落,有某些特殊的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在珞巴族的各个部落里,氏族及家族组织普遍存在,氏族首领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充当氏族首领,要有一定的财产,要善于辞令,要有组织和指挥对外战争、和平、友好谈判,对内维护氏族的习惯规范、主持宗教仪式、调解内部纠纷等事项的能力。根据上述条件,氏族首领一般为自然形成,没有选举的惯例。氏族成员之间有多方面的相互义务,如在婚丧活动、兴建房子和集体狩猎时的相互帮助、支持等。血族复仇是氏族成员间的一项重要义务,血族复仇中,除开杀死凶手这一形式外,还有“同态复仇”,即不一定要杀死真正的凶手,只要杀死凶手所在氏族中同等条件的任何一个人即可。
3.原始游群和血缘婚的残迹
在人类发展的初期,曾经历过原始游群时代,在森林里过着四处巡游,居住山洞,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生活,人的群团组织不那么固定,群体组成时有变化。这种社会状况,在墨脱珞巴族传说里有所反映。墨脱东布地方的珞巴族传说讲到,他们的祖先是从附近浪错湖上的岩洞里出来的。达额木部落的传说说,他们的祖先也是从宫堆颇章的山洞里走出来的。他走出山洞后,信步向南漫游,来到古更一个石洞前没路了,他向岩洞下看去,发现那里有人,便跳下去,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的子孙就是后来的达额木人。这个传说反映了珞巴族还处于原始群团的时代,不以血缘为基础离合较易的特点。通过原始群团的长期生活积累了经验,逐渐形成以年龄比较接近为基础的、排除不同辈份之间的性关系的道德规范,进入了血缘家庭时代。这时,作为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性关系,是不在禁止之例的。珞巴族中普遍流传着兄妹结婚的传说,正是远古时存在过血缘婚的朦胧记忆。在许多兄妹成婚的传说中,博嘎尔部落的《达蒙与达宁》故事最为典型。相传达蒙与达宁是天父与地母结合后所生的一对姐弟,达蒙姐姐从事采集和农耕,达宁弟弟从事狩猎。他们一起生活久了,弟弟对姐姐有了感情,想方设法接近,但一再遭到姐姐的拒绝。为此,他们一起到了天上,找天父太阳评理。太阳说,地面上人类只有他们一男一女,虽然是姐弟,如果不结合,人类就难以延续。于是,天父太阳把他们两个关进鸡笼,强迫他们成亲,终于结为夫妻。传说中还说,其时达宁从事狩猎,把活的小野猪抓起来,交给达蒙驯养。达蒙除开从事动物驯养外,还经常采集野生植物。她还用麂子角挖地,用猴子的下腭骨松土。他们还用藤条和木头互相磨擦,借以取火。形象而又趣味盎然地记述了血缘家族时期的生产和生活的情景。
血缘婚的残迹,在今天珞巴族的亲属称谓上还留有明显的印痕。如公公、岳父均叫“阿多”;婆婆、岳母均叫“阿若”;侄子、侄女、内侄和内侄女均叫“厄奥”;子媳、侄媳、内侄媳均叫“雅纳”;夫的兄弟和妻的兄弟均叫“衣哥”;夫的姐妹和妻的姐妹均叫“盖纳”,等等。在珞巴族的现行婚姻制度中,对这些不同的亲属都有明显的区别,但其称谓却只有一种,这是早期兄弟姐妹曾经是互为夫妻所留下的印记。值得注意的是,在洛巴族的鬼灵中,每一对“乌佑”,既是兄妹,又是夫妻,反映了灵的观念和自然崇拜最初产生了血缘家族时期。
4.母系社会的族外群婚
由于原始先民的长期经验积累,认识到近亲结婚“其生不蕃”,加上人口的增殖和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原来那种孤立的血缘家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出现了禁止在家族内通婚,实行不同血缘集团之间的族外群婚。族外群婚标志着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开始。在母系氏族社会里,丈夫和妻子各自生活在自己所属的血缘集团内,一般说来,男女双方的婚姻生活并不是固定的、专一的,是一种群婚的方式,因而孩子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孩子属于母方的族团;血缘按母系计算。在氏族内,妇女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社会上确立了那种女权地位。
在珞巴族的神话传说中,也反映了他们历史上曾经过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崩尼部落中有一种称为“山区米里”的人,他们的传说里讲到,在北部丛山,有个叫“米育门”的地方,那里是真正的女儿国,全是妇女,她们有极其贵重、古老而又神圣的串珠、法铃和宝剑。村里年青的和年老的妇女分两处居住。外地男子如果意外地到了那个村庄,她们便极力留他过夜,当这个男子获准离开时,老年妇女就送给他宝贵的串珠和宝剑,以便引诱另外的男子前来;年青妇女也送给他新的串珠和剑。孩子生下后,她们首先看性别,如果是女孩,就万分高兴,如果是男孩,就毫不犹豫地把他弄死(维·埃尔温《印度东北边境特区的神话》P186,1958年西隆英文版。转引自《珞巴族简史》P14)。这个传说,生动地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特点。
崩如部落还有一个这样的传说:他们的始祖母叫列德罗登,住在天上,但天上不长百草树木,许多动物难以生存。一天,她命马佐布列鸟飞到地上去看看,鸟到地上看后发现有许多树木,就是没有草。返回天上汇报后,列德罗登又命支波布能公马再去地上观察,马看到了马佐布列鸟拉的那泡屎上长出了草。于是,列德罗登带着牛、马、羊等下降到地上,与阿巴达尼结了婚,生了六个儿子:玛雅、巴依、纳、达能、崩如、苏龙。始祖母列德罗登把牛、羊、马和达谢林分给了儿子们,这六个儿子的后代发展成了六个部落。这个传说,维妙维肖地描绘了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有崇高地位的情况以及一个母系氏族首领带领氏族迁徙而获得发展的形象。在母系氏族社会里,有威信的女子不仅是生产、生活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是举行原始宗教仪式和活动的主持人巫师。在珞巴族的一些部落里,妇女担任巫师的为数不少,如米林的珞巴族五个“纽布”(巫师)中三个是女的,其中唯一的大纽布也是女性。“纽布”,珞巴族又称其为“布乃”,意为母亲,可见纽布的地位以及它与女权的联系。舅权也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残存标志。在珞巴族社会里,虽然父权早已确立,并父系氏族组织比较完善,但作为外氏族成员的舅父,还有权分享外甥女出嫁的身价。如博嘎尔部落内,出嫁一个或二个女儿,要给舅父送一把刀,出嫁三个女儿时,要给舅父送一头牛。同时,舅父有保护外甥安全的义务,如果外甥被杀,其父不在世或无能力时,舅父应为其复仇。
5.部落和氏族社会的婚姻
在珞巴族各部落中,毫无例外地实行氏族外婚制。在博嘎尔部落内,任何人都不能在氏族内通婚,同氏族的人通婚被认为是这一氏族的耻辱,如果出现了此类情况,一般是当事者的父亲或叔父亲自出面惩治,严重的甚至把双方一起杀掉,扔进河里。与氏族外婚制相对应的是部落内婚制,如,无论是博嘎尔部落的男子或女子,只要与德根部落或藏族、门巴族人结婚,他如果是高贵骨头的话,地位就要下降,变为低贱骨头,且永世不能恢复。这种部落内婚制的局限也有例外,如博嘎尔人与南部关系较好的棱波部落通婚较多,在崩如、崩尼、纳等部落之间,相互也可以通婚。人口少的部落,如巴依、玛雅就禁止内部通婚,他们的一切活动,也以整个部落为单位与大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发生关系。还有实行部落内的等级内婚制,如义都、博嘎尔和阿帕塔尼等部落,其内部分为不同等级,实行等级内婚,各等级的社会地位不能改变。也有一些部落不存在婚姻上等级的障碍,如崩尼、崩如、纳、巴依、玛雅人中,男主人可以娶女奴隶作妻子。民荣部落的未成年男女,要住在特设的公房里,到结婚后成立新的家庭才离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