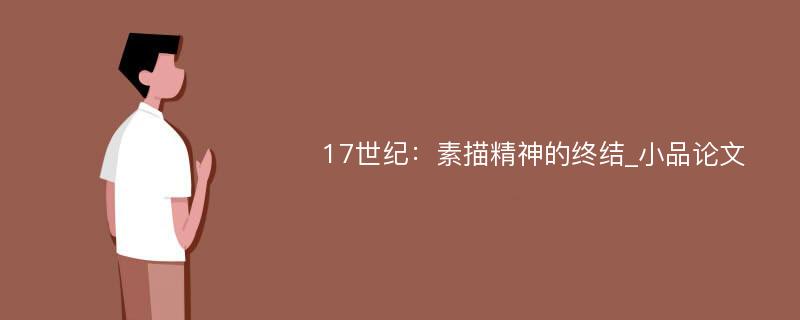
17世纪:小品精神的末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末路论文,小品论文,精神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5-0589-08
就语言形式而言,晚明小品与历代散文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全用文言文写作且一般不用骈偶之形式,是构成晚明小品作为散文一脉的基础。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主要在于其内质的变化,质言之,也即小品的精神有异于传统散文的“文统”。何谓小品精神?如果从晚明小品的哲学基础与文化品格角度加以观照,问题就有迎刃而解的可能。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主要取决于明代中后期时代的变迁,正是因为这一时代的变迁有别于宋元以前的社会风貌,才熔铸了晚明小品的独特精神。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开端,清人入主中原,是代表相对落后生产力的少数民族政权以武力征服生产力相对先进的汉族政权的结果,无情地阻遏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17世纪——也即明末清初这百年的历史,就是小品精神走向末路的历史。探讨这一文学现象,将有助于我们对“文变染乎世情”的深刻理解,而不仅局限于对某一文体兴衰的总结。
一
“小品”一词本为六朝时称谓佛经略本的用语,最早见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及南朝梁刘孝标注语。在佛经以外使用“小品”一词,则集中出现于明代中叶以后。自名其集者,如田艺蘅《煮泉小品》、朱国祯《涌幢小品》、陈继儒《晚香堂小品》、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等等;清初廖燕于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间,曾检自家以往“短幅杂著”九十三首,“目为小品,附《二十七松堂集》刻之”[1](第81页),可见这一习气之影响。明代以“小品”名选本者,如《苏长公小品》、《皇明十六家小品》、《闲情小品》等等;至于不用小品冠名而实为小品选本者,如郑元勋《媚幽阁文娱》、陆元龙《明文奇艳》、刘士鏻《文致》等等。明末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皆为自家小品的结集却并非以“小品”冠名者,二书被后人目为晚明小品的极致,至今脍炙人口。
这一已带有文体自觉意识的现象,发生于明代中叶以后不是偶然的。从哲学角度考察,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为散文小品的崛起奠定了时代精神的基础。阳明心学从“六经皆我注脚”走到“致良知”,发展了陆九渊之学。何为“良知”?王阳明《答聂文蔚》有云:“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2](第81页)然而“良知”又深藏于人心之中,必须善于挖掘才能发见,也就是要有一番“致良知”求诸内的修养功夫才能大功告成。他在《答顾东桥书》中又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2](第48页)良知乃人心中所固有,不假外求,恰与文人高扬主体意识的时代诉求不谋而合,这一哲学流派能对文学发生重要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明代唐宋派散文是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流派,正好处于前、后七子两次拟古主义高潮之间。其主将之一的王慎中任职南京礼部时,曾受王阳明弟子王畿的影响,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前“汉以下著作无取”的,拟古主张,取宋代曾巩、王安石、欧阳修的文章加以效法。唐顺之对于王慎中的转变,起先并不以为然,后来竟也随之转向,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注:以上内容可参见李开先《李开先集·闲居集》卷十《遵岩王参政传》一文。)。唐顺之的转向王学也是他与王畿直接交往的结果,他有《书王龙溪致知议略》一文,评论王畿《致知议略》,已显示出他对阳明心学“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悟性。唐顺之《荆川集》中的文章,其文化品格已近似于其后发展起来的晚明小品作家的作品了。至于他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一文中提倡写文章要“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本色”说,主张:“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唐顺之主张文人个性的张扬,这与其后公安派所倡导的“,独抒性灵”的性情之论的内涵已颇为接近了。茅坤为文从复古走向唐宋,也是因唐顺之而接受了王学的影响,这从他《复唐荆川司谏书》等有关文章中已可看出,恕不赘言。
值得一提的是,被一些论者划入唐宋派中坚作家的归有光,尽管其《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文章写得隽永有味,但其内在精神却与日后发展起来的小品精神难以同日而语。归有光一生维护程朱理学,对于阳明心学则壁垒森严,因而其散文的文化品格远较王、唐、茅三人单纯,不当被划入唐宋派。日本学者佐藤一郎认为:“归有光在文章流派上属于唐宋派,思想上属于朱子学的系统。”[3](第126页)结论前半部分因袭陈说,似有偏颇(注: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在讨论“唐宋派与嘉靖中叶文坛风尚”一节中,肯定“唐宋派追求主体精神的独立,倡导主体精神的自由表达”的同时,并没有提到归有光,表明作者并不认同文学史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的观点。黄毅《归有光是唐宋派作家吗》(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一期)一文认为归有光与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几乎没有交往,他们的思想倾向、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也不相同,因而“归有光不是一个唐宋派的代表作家,他充其量不过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反对前、后七子的同盟军罢了”。陈书录《明代诗文的演变》(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则认为:“正是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和茅坤等人开创了王学与文学相互融合的新阶段,在正宗文学领域引出了理性化与生活化并列,法式之工与自然之美结合的新思潮,”(第259)沈新林《归有光评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在肯定归有光“崇尚程朱理学,排斥陆王心学”的同时,却总结说:“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归有光是唐宋派的领袖和贡献最大的代表作家。”(第241页)拙作《明清小品:个性天趣的显现》(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也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加以讨论(第256页),但在此后的拙作《归有光文选·前言》中,笔者已将归有光与唐宋派加以区别,而非一概而论了。)。散文的文化品格问题,有时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然而若从艺术接受的角度加以审视,就会事半功倍。清代桐城派的散文文化品格也是以程朱理学为依归的,因而他们对归有光的散文大为推崇,并将他视为“文以载道”的文统传承中的一环;而对唐顺之等人,方苞、刘大槐、姚鼐等桐城派中人并没有特别加以垂青,可见散文文化品格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性。归有光抨击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是从散文发展的内部规律着眼的,不同于王慎中、唐顺之等人从个性解放的角度去迎击文坛拟古的潮流。然而两者殊途同归,就会令后人觉得他们之间仿佛有了一定的内在联系。几百年以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坛多将“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等量齐观,把他们当做封建文化的代表加以讨伐;而周作人、林语堂诸人提倡小品文,弘扬的却是公安派倡导性灵的文学主张,可见这一问题即小品的内在精神问题,绝非等闲,不容忽视。
晚明小品精神的最终确立是在公安三袁手中完成的,而其背后的动因仍与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脱不开干系。泰州学派是王学的一派分支,开创者即王阳明的半路弟子王艮。因为此派的平民色彩浓厚,兼之其离经叛道的价值取向,论者咸以“王学左派”称之。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有云:“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李贽晚于王艮四十馀年,为王艮之子王襞的弟子,又一度问学于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故与泰州学派甚有渊源。在思想启蒙中,李贽对阳明心学与泰州学派皆有所超越,他公开宣扬人有私心私欲,已具备近代的人文主义精神,而最能体现其进步文艺观的则是其“童心说”的提出。
晚明性灵派的三袁兄弟全都拜见过李贽,他们与李贽半师半友,气味相投,即源于对文艺启蒙的共识。从王阳明的“致良知”到李贽的“童心说”,显示了中国传统文人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一条思想解放的途径,而晚明小品也正是沿着这一途径才开放出朵朵异花奇葩。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的性灵说则是联结阳明心学与小品精神的纽带。换言之,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上,公安三袁将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转化为文学的小品精神。
公安派的性灵说所追求的是一种心灵唱叹的自由,欲获取这样的自由,就要自出手眼,打破古人的藩篱。袁宏道《叙小修诗》曾发议论道:“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4](第188页)以通变观看待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必然导致高扬主体意识的文论产生。性灵派文人大多尊重自我,率性而行且不与世俯仰;袁宗道《论文下》所谓“大喜者必绝倒,大哀者必号痛,大怒者必叫吼动地,发上指冠”[5](第285页),就是其个性的彰显。袁宏道尺牍有《聂化南》,更道出其性灵的本质:“且丈夫各行其志耳,乌纱掷与优人,青袍改作裙裤,角带毁为粪箕,但辨此心,天下事何不可为?安能俯首低眉向人觅颜色哉!”[4](第262页)但在封建社会,人格的独立一般只能局限于精神方面,而非政治性或社会性的,小品显然就成为精神上人格独立的一种载体。这一只能求诸内的精神诉求,发展至竟陵派,就走向“幽深孤峭”一途,而小品精神的末路也就隐约浮现了。
在走向自我的路径中,竟陵派比公安派走得更远。竟陵派以钟惺、谭元春为主将,《明史·文苑传》有论云:“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钟谭体。”在个性化写作的追求中,竟陵派向往幽、怪、奇、峻的风格,以充分发挥真、活、诚、灵的性情为职志,受到以正统文人自居的钱谦益“鬼趣”、“兵象”的讥诮(注:参见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第571页。)。钟惺对自己的求异思维毫不掩饰,他有《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泽民李端叔范文穆姜白石王济之释参寥诸帖》一文云:“古人作事不能诣其至,且求不与人同。夫与人不同,非其至者也;所谓有别趣,而不必其法之合也。宁生而奇,勿熟而庸。”[6](第308页)其论事可谓蹊径独辟,只眼独具。这一审美情趣,正是竟陵派“幽情单绪”说的底蕴。
可以说,没有公安派、竟陵派走向自我的精神追求,就不会有晚明小品的繁荣。晚明小品也正因为有了充盈的内在蕴涵,才具有了传统散文所难呈现的文化品格。
二
晚明小品若从文体的微殊加以区分,就有尺牍、序跋、游记、寓言、传记、笔记、诗话乃至清言等等。其中清言是一种类似格言警句式的文字,流行于明末清初,另有隽语、法语、清话、清记、语录、冰言、冷语等称谓,不一而足。其形式有别于传统概念的散文,而与发轫于先秦的“连珠”近似。若从内容观照小品,则又有抒情、咏物、山水、幽默、论学、品艺、怀旧等等的不同。可以说,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审视小品,都很难避免逻辑上的混乱;然而若从文化品格加以把握,我们或许可能对这一已于文体有所超越的文学现象,作出较为准确的估价,从而找到解悟其艺术精神的钥匙。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在士林文化中始终占有核心地位,晚明小品的这一文化品格与传统散文并无不同。儒家强调社会责任,这构成了封建文人士大夫的现实生活内容;然而从儒家祖师孔子那里也不难找出渴求审美与心灵自由的期盼。《论语·先进》牛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一章,即代表了孔子的一种人生价值取向。人生的现实与理想永远难以同一,两者的间距就是容纳文人士大夫诸多复杂情致的心理空间。当社会动乱频仍或走上物欲横流的畸形发展道路时,读书人的理想与现实就愈发背离,亟须一个宣泄情感的渠道。晚明社会正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于是散文小品——这种追求精神慰藉与心灵自由并有所隔膜于现实的文学样式,就成为一些文人抒情写志的利器。唐寅《菊隐记》开首即云:“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者。苟无济物之心,而泛然于杂处隐显之间,其不足为世之轻重也必然矣。”[7](第157页)这一番自我表白与《孟子·尽心上》中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说教如出一辙。至于屠隆《答李惟寅》中“身穿朝衣,心在烟壑”的向往[8](第87页),袁宗道《极乐寺纪游》中“予因叹西湖胜境入梦已久,何日挂进贤冠,作六桥下客子,了此山水一段情障乎”的心绪[5](第193页),更可见文人士大夫追慕闲适之趣的审美情调,这突出地表现了士林文化中“雅”的品位。
摆脱官场虚伪应酬,在物质生活有一定保证之后,随心所欲地追求“无官一身轻”的闲适之情,正是晚明文人士大夫欲冲破封建藩篱、追求心灵自由的理想。也许这种理想有时只是说说而已,碓以付诸实践,但此一种心态,却也不是汲汲于功名利禄的钻营者所能具有的。散文小品篇幅短小,又无韵律的限制,形式自由,与晚明文人之心态若合符契,于是小品的写作在反映士林雅趣上就有了其他文体所欠缺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小品文化品格中的士林文化基础造就了其鲜明的个性,从而有了享誉千秋的资本。
《论语·雍也》记述了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一段话。文人可以从山水反观自身;从而寻觅到精神寄托的所在。他们徜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与山水清景合而为一,并从中找到领悟人生的途径,暂时与纷披的物质世界告别,发现精神自由的天地。这就是晚明文人喜低回流连于山水之间的心理依据。如果把个人一时一地的感受写成率意而就的小品,就使瞬时的感受永久化地存在于世上,有可能在失落的现实中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袁宏道《游骊山记’》有云:“天子之贵,不能与匹夫争荣,而词人墨客之只词,有时为山川之九锡也。”[4](第1468页)其中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也反映出文人自恋心理的执著。
《论语·卫灵公》记孔子之语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之论,《孟子·告子上》也有“舍生取义”之语。在传统儒家理念中,忠君与爱国往往同一,晚明文人或称之为节侠心。明末天启进士陈仁锡议论西湖之语,可称正直文人的自我写照,其《题春湖词》中有云:“尝笑红粉心长,节侠气短;西湖不然,节侠心即红粉心。”[8](第561页)作者有感于西湖畔之岳飞庙与大好湖山相映生辉,写下此段文字,一片忠正之气灼然可见。这也是晚明小品绝非“嘲风月,弄花草”一类无聊文字的表证。王思任是一位性格倜傥诙谐的文人,然于大节面前绝不苟且,关键时刻能保持操守。清兵南下攻破绍兴后,年已73岁的他誓不投降,绝食而死。其《让马瑶草》就是一篇富有战斗力的小品文字。文中“夫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二语,怒斥南明奸佞马士英,铁骨铮铮,义正词严,至今脍炙人口。归庄虽未仕明朝,却也有遗民气节,明亡后誓不投靠清廷,志节可敬。其《跋登楼赋》有云:“虽桑梓依然,不敢云我土也。所不同于王仲宣者,无楼之可登,无刘荆州之可依耳。”[9](第282页)语语沉痛,一片爱国之情如在目前。晚明小品在打破“文以载道”的文统的同时,并没有舍弃儒家文化。
文字须有民间的滋养,才能不断发展,推陈出新。诗歌如是,散文亦如是。明代中叶以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已染有浓厚的市民阶层意识,标举性灵,强调个性解放,向某些传统意识挑战以及大胆承认私欲等等,无不折射出市井文化的辉光。一般而论,士林文化强调对传统的继承,趋向于保守;市井文化则重视现实的享乐,有移风易俗的力量。两种文化在冲撞交融的整合中,必然使其体现者产生某种躁动,而躁动的心态只有通过精神的运作才有望平复。从某种意义讲,散文小品(不是全部)恰恰可以充当创作主体的心理平衡器,而这也是晚明小品有别于历代散文的本质之处。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中有“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4](第193页)的文字,面对这样的小品,几百年后我们仍能谛听到作者那颗有意冲破传统的心在有力地跳动。在《叙小修诗》一文中,袁宏道又说:“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4](第188页)这一超越于士林文化之上的追求,与时代的脉搏相应共振,绝非个别孤立的现象。清初廖燕《山居杂谈》也有类似文字:“凡事做到慷慨淋漓、激宕尽情处,便是天地间第一篇绝妙文字,若必欲向之乎者也中寻文字,又落第二义矣。”[1](第415页)
袁宏道在其尺牍《徐汉明》中提倡“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的“适世”之道;于尺牍《龚惟长先生》中又写出文人放浪形骸之外的“五快活”之情景。张岱于《自为墓志铭》中对自家少年时代“十二好”的放荡生涯既不讳言,也无忏悔之意。这些文人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多方位追求,突破了儒家较为单调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市井文化品格在他们小品中的反映。
全面探讨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就应注意到老庄与禅悦对小品作家的深刻影响。儒释道三教合一之论,唐代以后即为社会所广泛认同,这无疑给文人士大夫“出处行藏”的人生取舍增加了多重选择。从哲学角度考察道家学说,主要体现在“避世”二字上,这与儒家的积极人世精神适相反对,然而两者又并非形同水火,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人士大夫在出世与避世的人生抉择中,常常是在朝以儒,在野以道,或者外儒内道,交相为用。从文化角度考察,中国政治与伦理等领域较多地打上了儒家的烙印,而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则较多地打上了道家的烙印。现代学者张岱年曾说:“儒、道两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固有文化的主要思想基础。”[10](第1页)竟陵派主将谭元春《又答袁述之》有云:“古人无不奇文字,然所谓‘奇’者,漠漠皆有真气。弟近日止得潜心《庄子》一书,如‘解牛’何事也,而乃曰‘依乎天理’;‘渊’何物也,而乃曰‘默’;‘惑’有何可钟也,而乃曰‘以二缶钟惑’。推此类具思之,真使人卓然自立于灵名洞逵之中。”[11](第772页)这是用道家学说阐释文艺创作问题,带有这一派的幽深孤峭的色彩。
袁宏道《德山麈谭》作三教会通之论,有意将老庄之说引入儒学,服务于其性灵说,因而晚明小品染有老庄色彩就非偶然了。向往老庄而外,禅悦之风盛行于晚明文人士大夫间,又使小品的文化品格向佛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转。明代万历以后,士大夫多喜谈禅,僧与士人交往也成风气。袁中道于《西山十记》之十有云:“今予幸而厌弃世膻,少年豪气,扫除将尽矣。伊蒲可以送日,晏坐可以忘年;以法喜为资粮,以禅悦为妓侍,然后淡然自适之趣,与无情有致之山水,两相得而不厌,故望烟峦之窕窈突兀,听水声之幽闲涵淡;欣欣然沁心人脾,觉世间无物可以胜之。”参禅在文人那里不是目的,只是通往心灵自由的一个途径。袁宏道《叙小修诗》中有一段著名的话:“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c4)(第187页)这一番话就直接脱胎于岩头与义存的参禅之语:“(岩)头曰:‘他后若欲播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师于言下大悟,便作礼起。”[12](卷7,第380页)可见性灵派与禅宗的密切关系。阳明心学即带有以禅诠儒的倾向,这无疑加强了小品的禅学品格。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一曾就此论道:“然释教之所以大明于世者,亦赖吾儒有以弘之耳。”[13](第187页)士人盛禅悦之风与民间好佛之尚,前者是追求精神的超越,后者多注重现实痛苦的解脱,目的或有不同,但基础也有相近处,那就是反抗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性的压抑。在小品的写作实践中,禅学与文学创作的联系主要通过意象或意境的营构而显现,我们在公安派与竟陵派作家的有关作品中不难发现这一特点。
小品中的禅味,自以清言中为多,如明洪应明《菜根谭》即是一部说禅劝世的清言小品集。其中多为独处自省、明心见性之语,故作达观中也隐约透露出几许苦涩的无奈。在心学盛行的时代,在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大背景下,晚明小品具有多重文化品格,就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标志出它不同于传统散文的内质所在。
三
17世纪的明末清初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王纲解纽”的社会趋势为小品精神的形成,营造了适宜的生态环境。清人扣关人主中原,中断了晚明走向近代的历程,也逐渐窒息了士林阶层要求个性解放的呼声,小品精神走向末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明末清初的文人士大夫总结明亡的教训,或归罪于朋党,或遗憾于“盗寇”(农民军),或抨击王朝的腐败,或痛惜人才的缺乏。也有一些文人从学术角度加以审视,认为学术之坏,也就是阳明心学的泛滥颠覆了明王朝的统治(注:有关论述可参见清人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二《学术辨》、张尔歧《嵩庵闲话》卷一中的有关文字。)。阳明心学于明末清初之际仍不乏信奉者,如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即是,但从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程朱理学还是逐渐占了上风,这大约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原则。特别是程朱理学得到清代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官方哲学以后,其对士林的影响就更不言而喻了。阳明心学是晚明性灵派文学家的哲学基础,当程朱理学取而代之,重新占据士人的头脑以后,这对于小品精神的传承无异于釜底抽薪,小品之所以在17世纪的中国走上末路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这一变化也并非突然而至,明亡以后,晚明小品精神也不是戛然而止,它具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这就是桐城派逐渐走上散文的统治地位,并最终取小品地位而代之的文学史历程。
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开创于桐城人方苞,形成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正好是晚明小品已式微之际。桐城派的形成并非是一种文学的自觉,诸多客观因素促成了它的出世。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本,论文讲究“义法”,技巧形式则以“雅洁”为主;发展至姚鼐,又提出文章四粗、四精之八大要素以及阴柔、阳刚之风格论,至于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的追求,也是桐城派的文章特色。桐城派散文有通经明道的实质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专制统制者的政治需要,但这不应当由该文派本身负责,时代风会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以清代桐城文派的产生为参照系,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晚明小品精神的近代性特色,从而对中国17世纪的文学发展脉络作出准确的把握。
如前所述,晚明小品源于公安派的崛起,袁中道《中郎先生集序》盛称其兄袁宏道云:“先生出而振之,甫乃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一洗应酬格套之习,而诗文之精光始出。”晚明小品正是以“精光”为其外在特色的。陈继儒是晚明小品家,其《文娱序》借他人之口指出“以文自娱”说,论小品写作则有:“芽甲一新,精彩八面,而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丽典新声,络绎奔会,似亦隆、万以来,气候秀擢之一会也。”[14](第24页)小品与传统散文迥异的风貌是与晚明的时代相应合的。陈继儒生当明嘉靖、万历至崇祯间(1558-1639),比袁宏道长十岁,却颇长寿,晚卒近三十年,差五年就可遭遇易代之悲了。袁、陈二人以当代人之眼光审视自己钟爱的文体,固如是说。廖燕生当明亡之际,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644-1705),当属一位完全的清代人,然而日人盐谷世弘于日本文久二年(1862)为廖燕集所写《刻二十七松堂集序》却将廖氏视为明朝人,并说:“盖明季之文,朝宗(侯方域)为先驱,冰叔(魏禧)为中坚,而柴舟(廖燕)为大殿矣。”[1](第1页)侯、魏二人以古文名世,属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家,不当入于小品文家之列;廖燕为文则多晚明小品习气,带有自觉继承的印迹。就此而言,将廖燕之文视为“朱明三百年之殿”,也并非大谬不然者。
廖燕对于晚明小品精神情有独钟,理解也极深刻,他有《选古文小品序》一文,将优秀的小品之作甚至比为“刺人尤透”的匕首。其文有云:“大块铸人,缩七尺精神于寸眸之内。呜呼,尽之矣。文非以小为尚,以短为尚,顾小者大之枢,短者长之藏也。若言犹远而不及,于理已至而思加,皆非文之至也。故言及者无繁词,理至者多短调。巍巍泰岱,碎而为嶙砺沙砾,则瘦漏透皱见矣;滔滔黄河,促而为川渎溪涧,则清涟潋滟生矣。”[1](第84页)如此论说小品,比上述袁宏道的“精光”说、陈继儒的“精彩八面”说都要深刻。置身于热闹世局之外,也许更能看穿事物的本质,廖燕作为晚明小品精神的传人,在时代氛围已然大变的情况下仍能执著于小品的写作,为明清之际小品的末路皴染上光辉的一笔。应当指出的是,廖燕于清初文坛并不处于主流位置,他少习举业,中途放弃,专以著述为乐,浸染晚明馀风,自主意识极强。其性格决定了他始终自外于主流社会,处于文坛边缘的地位;而这一边缘的处境又令他远离时代的政治——不像王士禛等身居官场的文人,必须俯首低眉于清统治者的专制淫威下讨生活———这反而玉成了他自我精神的熔铸。廖燕所处的时代为清顺治与康熙中,文字狱的阴影远不如其后雍正、乾隆两朝浓重,所以只要不与其王朝统治发生正面的冲突,就允许一些自外于主流社会的文人在书斋中发挥自我。廖燕如是,写过清言小品集《幽梦影》的张潮亦如是。随着清代专制主义的加强,文人的这块自由天地也被无情地剥夺了,虽也有史震林的《西青散记》一类的小品文字,也有郑燮情真语挚的尺牍小品文字,也有袁枚性灵说的提出,但与晚明小品精神终究隔了一层,其近代意识反而没有晚明人强烈。文坛起主导作用的是桐城派,作为正统散文的承继,有其是处,但终究缺乏超迈古人的革新精神。这是时代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晚明小品精神走向末路,于竟陵派已见端倪,如前所述,此不赘言。在晚明能继承公安、竟陵二派的性灵之风,于创作实践又有所发扬光大者是张岱(1597-1689)。他身历国破家亡的巨痛,既有过珠环翠绕、富贵温柔的生活,也受过辗转流离、贫困不堪的磨难。张岱将近“知命”之年遭遇国变,结束了他较为优裕的诗酒生涯,然而他没有就此消沉下去,作为一位坚守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著书自娱,以明遗民的身份走完了其生命的最后旅程。张岱一生著述宏富,约有三十馀种,内容涉及史学、文学、经学、医学、饮膳、地理等,其中《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部笔记与其一部文集,就是其优秀小品创作的渊薮。在《梦忆》、《梦寻》二书中,《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小青佛舍》、《飞来峰》等都是耐人寻味的小品之作,有自我徘徊于昔日梦境中的身影。张岱的梦是痴迷的,他并不愿从梦中走出,重回令人神伤的现实世界,去体味那梦醒以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他只想留连于梦中的虚幻,以涵泳于理想的精神世界。这一祈愿本身就是晚明小品精神的体现。正是主、客体的两相融合,造就了一代小品文的大师,给已走上末路的晚明小品抹上了一层亮丽的色彩。
在小品精神走向末路的历程中,有两位堪称过渡人物的文人值得我们瞩目。二人性格不同,遭际迥异,但二人皆具有的挥洒自如的晚明文人的气度,为17世纪的中国又添注了一笔不菲的文化遗产。他们就是金圣叹与李渔二人。
金圣叹(1608-1661),是一位才子,又是一位狂生,干事率性而为,又好发惊世骇俗之论,当时就颇为人所侧目。他有所谓“六才子书”的评点计划,但只完成了《水浒传》、《西厢记》二书的评点,《杜诗》只完成了一部分。他的评点文字与一些序跋文字都可纳入小品的行列,且不乏真知灼见。金圣叹文风汪洋恣肆,痛快淋漓,充盈着晚明小品的精神、然而这样一位有极强自主意识的文人却难以适应清初的政治环境,终因清顺治十八年(1661)的苏州学子“哭庙案”而为清廷所杀。他的死,预示了小品精神必然走向末路的命运。
李渔(1611-1679?),原为明诸生,家中富有;清兵南下,家道中落。李渔入清后不曾走应试求官之路,而是以著述、刻书与编演戏曲为乐。他是诗文家,也是小说家、戏曲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在他身上融会贯通,成就颇大。其诗文集名《笠翁一家言》,即包括著名的《闲情偶寄》这部小品精神甚浓的作品。《闲情偶寄》分为“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八部分,一望即知,这的确是一部包罗万象的闲适之作,其内在精神的潇洒超出了其外在形式上的严肃。其中发抒性灵的文字是与晚明小品精神一脉相承的。李渔曾在南京开有芥子园书铺,家中还养有戏班,从事经营性演出,堪称是一位亦儒亦商的文人。这样的“儒商”是晚明社会氛围下的产物,在清初尚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但随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空间逐渐趋于狭小,李渔式的文人毕竟没有蔚成风气。而李渔身后毁多于誉,也可证明小品精神的走向末路与时代氛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的17世纪向为历史学家所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前,论者多从政治、经济角度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而忽略了对文化的深入探讨。17世纪本是明清易代之际,而市井文化的繁荣,如冯梦龙“三言”、凌濛初“二拍”等话本和拟话本的出现,才子佳人小说的盛行,戏曲的普及,又无不回响着中国迈向近代的脚步声。因而,晚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也逐渐引起论者的兴趣(注:可参见《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所载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一文。)。晚明小品作为那一时代一种有代表性的文体,从有关文论的角度出发,结合其文化品格的讨论,拷问其由盛而衰的缘由,对于我们准确把握17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是大有助益的。
收稿日期:2003-04-20
标签:小品论文; 袁宏道论文; 儒家论文; 唐顺之论文; 归有光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散文论文; 叙小修诗论文; 王慎中论文; 廖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