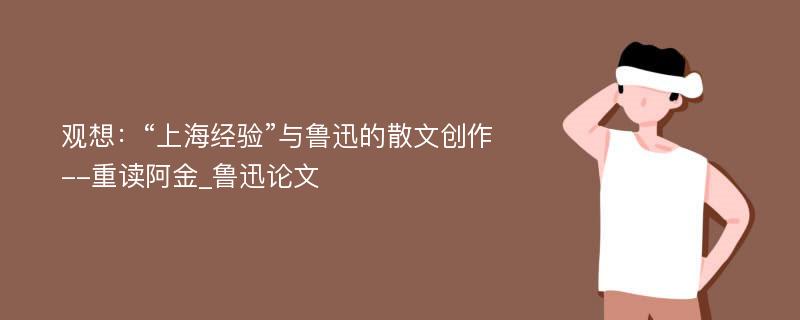
观看与疑惑:“上海经验”和鲁迅的杂文生产——重读《阿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杂文论文,上海论文,疑惑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杂文的意义生产:“阅读”《阿金》
《阿金》是鲁迅晚年所写的一篇作品。虽然只有短短2700余字,却是一问世便经历种种“阅读”,从而文本的意义也处于不断的生产当中。
查鲁迅日记,1934年12月21日记载:“下午作随笔一篇,二千余字,寄《漫画生活》”①,这篇“随笔”即《阿金》。但是文章未能刊出,要到1936年2月20日,才发表于上海《海燕》月刊第2期。期间,鲁迅将这篇文章收入了1935年12月30日编定的《且介亭杂文》,而在他生前未及付印,直至1937年7月由许广平以上海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小小文章的面世与传布,经历这么多的曲折,可以看作鲁迅众多写作语境的一个缩影。但有意思的是,《阿金》自手稿写出,提交发表所遭遇的审查、鉴定、删改、拒载,未尝不可看作一种对《阿金》的“阅读”,甚或这种“阅读”还带有别样意义的“认真”。
在《且介亭杂文》的《附记》中,鲁迅对所收各篇做了简短说明,重点记录与审查制度的遭遇: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②
从这琐屑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图书杂志审查制度的无理和严酷,同时也能体味到鲁迅的愤懑。可以说,自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特别是第二条所规定的“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审”开始实行,鲁迅的文章就不断遭遇厄运。以至于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友人的信中,不断谈及审查制度对自己的损害。如1934年10月13日致杨霁云的信里说:“近来有了检查会,好的作品,除自印之外,是不能出版的,如果要书店印,就得先送审查,删改一通,弄得不成样子,像一个人被拆去了骨头一样。”③同月31日致刘炜明的信中说:“近来他们方法改变了,名字可用,但压迫书店,须将稿子先送审查,或不准登,或加删改,书局是营业的,只好照办。所以用了我旧名发表的,也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文章。”④1935年1月26日致曹靖华的信里也说:“检查也糟到极顶,我自去年底以来,被删削,被不准登,甚至于被扣住原稿,接连的遇到。”⑤而在《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章里,他也是借古讽今地点破历来文字狱的罪恶。
那么,《阿金》是经历了检查制度怎样的“阅读”的呢?鲁迅索回原稿之后,写了如下议论: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⑥
检察官的“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文本”里的,是这样一些段落:
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
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
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⑦
鲁迅说,“毫无深意”的文章会“惹出大问题”来,常使他自己“参不透”。等到“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这些句子里频繁使用的是“巷战”这样的词汇,并且有死亡、炸弹等等联系,还涉及华洋主奴关系与人世和战状态,在检查者看来,这样的词汇语句呈现在文章当中,哪怕是描写里弄纠纷女佣吵架的琐事,也得一律删去。但鲁迅“总不懂”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于是只能按检查的逻辑推出一句同样毫无道理的费解之辞:“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日本学者竹内实曾经在《阿金考》中指出:“红线屡屡标识的‘巷战’,说的是1934年的‘上海事变’”⑧,接着便一条条罗列引述内山完造《花甲录》中对“上海事变”的记载,提示鲁迅与这一战争状况的关系。他认为鲁迅作为“一·二八”的直接经历者,当时没有详细的记述⑨,只是在两年后的《阿金》这篇随意杂谈中,写了“巷战”这词,于是刺激了检查官。而检查官毫无疑问知道中国民众对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南京政府的不满,因此这种删削或许可以成为他们维护政府的“爱国”行为。⑩
检查制度自然以捕风捉影为能事,而面对庞大的文字稿件,检查者高度紧张,“他们的嗅觉是很灵敏的”(11),试图在字里行间“读”出背后是否含有抨击时局、讽喻当政的意思。通过删改、压制,使原来的文章支离破碎,意义模糊甚至不知所云。鲁迅曾说,如果删改的文句还算通顺连贯,那么可能是编辑的手笔,若是文句不成片段,则必然是当局的剪裁了。他在《且介亭杂文》的《附记》里谈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12)也就是说,本来隐蔽在文字之中,或有或无、时隐时现的“意义”,首先在书报审查过程中被“阅读”了出来。而这种“阅读”的结果反而促使鲁迅在杂文编辑时,一边用黑点或黑扛的形式还原出删改的地方,一边在“附记”和“后记”等空间中叙述出删改还原的往来过程,“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原先的文章获得了强调、提示、重读的可能,并向着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开放,使得“杂文写作的时代”和“写作杂文的时代”错综交织,相互映照。这样,写作、发表(或未能发表)之后的二次编辑,本身恰恰又成为了一种新的杂文书写方式。通过这样的行动,鲁迅将杂文“编年”,“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因之,实现了“明白时势”、“知人论世”的“编年文集”创作。(13)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当年的检查制度未必不是“理想的”阅读者。而后来围绕着鲁迅这一“经典”建筑起来的层层解释,同样属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阅读”。延续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编写的《鲁迅年谱》,仍然是以“实际上寄寓了对国民党政府当局的抨击”(14)这样的评价来理解《阿金》一文。其出发点,是源自对鲁迅所谓“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这一非政治性题材的文章中,字里行间的“政治性”关注。竹内实曾评价鲁迅写作的“政治性”为“不过多么非政治的题材,鲁迅都能从中发现其政治的意味。这是因为,鲁迅的生活,实现了政治与非政治的交融。如果不是那样,他也不会以阿金为文。上海市民看到的现象,怎么竟成了使国民党检查官感到不安的对象呢?这就是鲁迅的特殊之处。他使这些现象,变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对象’。当这些琐事被鲁迅关注时,那个真实的阿金,便从总体上成了‘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时代’的一种象征。鲁迅将真事如实地写成了文章,这种真实也就在读者的心中,变成了对某一‘地方’和‘时代’的讽喻。”(15)以上说法自有道理,但在指出鲁迅“初次”创作中若隐若现的杂文意义生产之后,还需要补充的是鲁迅“二次”创作中更为明确的杂文意义生产。成为这一前提的,正是“不知何年何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到底在上海出现了”(16)。鲁迅虽在自己的叙述中说明“娘姨吵架”“与国政事变,毫不相关”(17),但可以认为,他回头复看被删改的原稿时,“总是参不透”、“悟出道理”或者“看不懂”的姿态每每激发他重新处理自己的文字,重新处理文字与大众媒介、文化环境的关系,使得原先称作“漫谈”、“随笔”的文章向着写作总体的“杂文”转换(18),“杂文集”编辑的“编年”方式又进一步深化了其意味,最终,杂文的意义不断在“我们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个总体境况里生产出来。
二、文本的意义纠缠:“阿金”阅读史
虽然《阿金》被鲁迅称作“随笔”或“漫谈”,但由于“阿金”这一中心人物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许多研究者都将它当成小说来分析,如锡金就认为,毋宁把《阿金》看作一篇作品,“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发展下来的最后一篇杂文化了的小说”。(19)何满子也说,“《阿金》是叙事体杂文,或可称为杂文味的小说”。(20)但不管怎么说,倘若不拘于某种简单的“文体”分类,而是考察《阿金》的具体写法,恐怕所谓“描写”应该是文章的重头,即便是后半部分的“议论”,也全都由这前半部分的“描写”生发而来。因此,描摹出来的“阿金”自然成为重要的分析对象,甚至成为了鲁迅笔下一系列经典人物的代表之一。
鲁迅是这样介绍“阿金”的:“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21)如果联想晚清以来的小说传统,我们不难发现“阿金”这两个字是文学作品中“娘姨”最常见的名号,甚至符号。例如《九尾龟》就有:“陈海秋刚要开口,早见娘姨阿金、大姐阿玉两个人勾肩搭背,一路嘻嘻哈哈的笑进来。”再如大名鼎鼎的《海上花列传》也写:“到了楼上,洪善卿迎着,见两位一淘来了,便叫娘姨阿金喊‘起手巾’,随请两位进房。”当然,熟悉晚清小说传统,编写过《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也不必追溯这长长的互文网络,就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如“阿金”这样普通的娘姨名字也遍地都是。(22)“阿金”这一称呼,正显示了其典型性。
因为这一“典型”形象,论者经常把“阿金”与鲁迅笔下的“阿Q”联系起来。何满子认为,“阿金这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和阿Q一样,都是国民性的平凡而又特异的标本。阿Q是未出未庄的阿金,阿金是出了未庄沐受了洋场洗礼的阿Q”。(23)“在鲁迅的作品中,有两个人物最能概括中国人的灵魂。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男的是阿Q,女的是阿金。这里没有性别上的区分,女人可以有阿Q相,男人也可赋有阿金性。要从社会背景即铸成性格的文化内涵来分,则阿Q身上更多的是封建半封建的精神结晶;而阿金,底子虽然也是封建半封建,却更涂上了一层半殖民地的色彩。阿金倘若蜗居于未庄,就是阿Q,或小D,即鲁迅所说的大起来和阿Q相同。阿Q倘若有幸到洋场上来混一阵子,就成了阿金。阿Q和阿金如果配成夫妻,那真是天作之合,珠联璧合的好一对佳偶。”(24)这种对照中,对与“阿金”之所以为“阿金”的背景提示,确实很富启发。只有在都市里、洋场中,“阿金”的行为才得以产生,放大,所以《鲁迅年谱》中评价说:“文中勾画了一个为外国人所豢养,狐假虎威,惹是生非的丑恶女人的形象”(25),这种对应读法,无疑是将“阿金”作为某种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来看待,伴随着对社会性质的分析批判,置放在鲁迅“国民性”批判的解释视野之中。
而从“阿金”这一表达符号本身,也很容易联系到《采薇》中的“阿金姐”。其实,鲁迅于1935年12月重读自己的文章,将包括《阿金》在内的36篇编订入《且介亭杂文》的时候,也正是写作《故事新编》中《采薇》等短篇之时。两个“阿金”相互之间当然有其联系。《采薇》里的“阿金姐”同样是一个女佣,并且是“首阳村第一等高人小丙君”家的婢女。“阿金姐”“聪明得很”,她“冷笑一下”,“大义凛然的斩钉截铁的”说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便击垮了秉节守义的伯夷、叔齐。对“阿金姐”的评价,在小说中便分为“聪明”与“刻薄”两歧,研究者也从此伸展出不同的阅读。固然有研究者认为“阿金姐”是小丙君的帮凶,给予负面的评定。但也不乏某种肯定的声音,王瑶曾在评论《采薇》时提及:“从小丙君、小穷奇的伪善言行的对照中,就越显出伯夷、叔齐的‘真诚’的迂腐与可笑。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创造了一个婢女阿金,她‘大义凛然’地对夷齐说:‘你们在吃的薇,难道不是我们圣上的吗?’她的话一下子戳破了这幕自欺欺人的喜剧,于是夷齐只能为他们所笃信的那套思想殉葬了。”(26)竹内实则更是认为:“嘲笑伯夷叔齐的,当然是阿金。而她的对手,则是两千年的信条。不妨说,竟是无知彻底笑倒了有学问的人。鲁迅极力刻画的阿金的泼辣,与伯夷叔齐学者似的愚蠢威严,在中国历史舞台的背景上,构成了无比的滑稽。要嘲笑具有长久传统的权威,当然并不容易。可当爆发出一次嘲笑,就让人觉得可笑得流出了眼泪。而阿金,便有这样的力量。鲁迅杂文《阿金》中的负面形象阿金,到小说《采薇》里,已被赋予了正面的、反封建的意义。用俗话讲,这也许可以称之为‘以毒攻毒’。”(27)由此可见,如果撇开“好”、“坏”这样简捷的道德评判,那么“阿金”这一形象至少包含着某种特定情境下斗争的辩证性力量。正是其自身某种毫无掩饰的直接表露,一种带着“泼妇”“泼辣”特性的反戈一击,才能同时揭穿内在其中的境况之虚伪、荒诞。
跟“阿金”相关,在鲁迅笔下的人物系列中,除了“阿金姐”,至少还可以联系出一串女性形象来,如《故乡》中的“豆腐西施”,说得读书人手足无措、无以言对;《祝福》中的“柳妈”,说得弱者震惊惶恐、疑惧不安。她们共同的特征便在于小人物身上“言辞”的力量,或则骗取财物,戳破他人,(28)或则提示迷信,蛊惑人心。而在“说破”的层面上,阿金正具有这种赤裸裸的能量,她会大胆地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大声地答复:“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如卜立德的一个解释认为:“作者自嘲说他恨阿金摇动了他三十年来的信念。他一直认为男性的作者‘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是冤枉,现在可是相信,像阿金的女人一旦有权势,一定会‘闹出大大的乱子来’。鲁迅自然用的是反话,实则他惊奇阿金的撒野,又敬佩她的胆量。但是他真的有点恨她。恨她在实际生活上比像他那样只善于打笔墨官司的文人强多了。”(29)她们的某种“真实性”对外在的严整和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竹内实在2001年为中文本《竹内实文集》第2卷“中国现代文学评说”作序的时候,对自己写作于三十多年前的《阿金考》仍然念念不忘。他说自己浏览了本书目录,“有几篇论文很值得听听读者的感想,例如《阿金考》”。(30)当年,竹内实参与《新日本文学》杂志关于鲁迅的系列讲座,觉得鲁迅杂文《阿金》中描写的女性,“很像是当时相当活跃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讲演时,虽“并没有提及‘文革’或江青的名字,不过自己的话里有那样的意思”。而等到十年之后,“江青终于下台”。竹内实忽然想起这篇文章,又重新读了《阿金考》。觉得当时对这位女士的讽刺,并没有什么效果。甚至觉得里面也称不上有什么讽刺,或者是中国话所说的“影射”。他写道,其实“当初并非是出于‘影射’的想法,才选择了这一主题与内容,而只是想揭示并品评一下至今仍可以在中国平民生活里见到的‘泼妇’形象。后来读了鲁迅的作品,才有了似乎可以扩展一下视野的念头。”(31)竹内实对“阿金”的这种“阅读”当然是上世纪60年代特定历史氛围中的产物,虽然问题性所在仍是指向日本自身的,但在作为“中介”的这一考论里,对“阿金”形象的理解,也不失为一种深有意味的提示。(32)特别是他在文章最后从“阿金”与《阿金》所生发出来的,对鲁迅写作之“现实”、“虚构”和“文学”之关系的讨论,颇具启发性。
三、观看与猜想:“我最讨厌阿金”
层层“阅读史”虽然不能替代我们的理解,但未必不在重读的过程中与我们不期而遇。因此,与其带着警惕和提防进入《阿金》,不如也把已有“阅读”看作围绕在这里弄故事中心或周边,同样需要面对的文本网络。而回到文本本身,我们遇到的也仍旧是“阅读”,是叙述者“我”对“阿金”这一人物的“阅读”,直接构成了叙述的基调、观察的视角和议论的位置。
翻开《阿金》,第一句显眼甚至有点突兀的话语,就是作者颇为决绝的判断之词:“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讨厌”这个词语在短短的文中还出现了五次:
这时我很感谢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
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
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足见情感的强烈程度。可以说,“讨厌”不仅是《阿金》一文先在的叙述基调,而且成为了极其主观的叙述视角。
叙述者对“阿金”的讨厌直接来自于她的“嘻嘻哈哈”、“大声会议”和“嚷嚷”(33),且不说具体吵闹的内容,就是这一种声音形式及其氛围便让叙述者极其不快。虽然像李冬木曾颇费周折、文本内外勘察论证的结论所说:“阿金”是“架空”的(34),鲁迅实际的写作环境也未必一直嘈杂,但这种上海都市中“嚷嚷”的现实性要素的确存在,并且对鲁迅而言,既是一种生活的环境,又是一种生存的体认。
1930年代,鲁迅初到上海之时,对这个大都会的深刻印象就是“闹”。他给许广平的信里常谈到“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35),或是“上海也还好,不过太喧噪了”(36),这里的语句虽短,却包含着多层的意思。在鲁迅的主观感受中,上海是“烦扰”和“生气”并存的,比他在北京抄古碑、在南方死气沉沉要强,上海的“喧噪”以外,有它的“也还好”之处。虽然随着鲁迅寓居上海的时日增加,与洋场上各种新旧势力、左右立场、华洋面孔的遭遇增多,对上海的认识更为复杂,但这一“闹”的初始印象或总体印象却是一以贯之的。而具体到鲁迅的居住环境,也常常是“颇不宁静”。如许广平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中就曾这样记述他们的住地:
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似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又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37)
鲁迅的多次搬家固然有种种考虑,但周围的纷扰,也是其中很重要的因素。1936年10月6日,鲁迅在写给曹靖华的信里说到自己在上海择居的三个条件:“一要租界,二要廉价,三要清静”,但他同时也感叹:“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38)。同月12日,在致宋琳的信中也谈到:“沪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谣传将有战事,而中国无兵在此,与谁战乎,故现已安静,舍间未动,均平安。惟常有小纠葛,亦殊讨厌,颇拟搬往法租界,择僻静处养病,而屋尚未觅定。”(39)这样一些记述中呈现的缺乏清净和僻静的氛围,便成为了“阿金”出场的舞台——租界的弄堂——喧闹的总体感觉,而阿金也成为了上海之“闹”的形象化与集中化的体现。
“阿金”直接间接地出场大致有六次,分别是:
1.夜晚与女友聚会,并宣布那赤裸裸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2.从晒台上直接摔下竹竿、木板来
3.半夜以后与男人的约会,并因“我”而散去
4.晚快边的大声会议,遭洋人踢骂
5.和老×的奋斗
6.对西崽遭打的回避
正是由这样一连串的“事件”,勾画出了一个“讨厌”至极的“阿金”。有意思的是,整篇没有一点对阿金的外貌描述,读者无从知道她的高矮胖瘦,因为作者说:“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然而通过一系列声音和动作,阿金却又跃然纸上,生动如漫画一般。
其实,《阿金》本来就是写给《漫画生活》的,(40)鲁迅曾在《漫谈“漫画”》中指出:“漫画的第一件紧要事是诚实,要确切的显示了事件或任务的姿态,也就是精神。”并且认为:“漫画要使人一目了然,所以那最普通的方法是‘夸张’,但又不是胡闹”,然后又修正说:“‘夸张’这两个字也许有些语病,那么,说是‘廓大’也可以的。”(41)因此,所谓“诚实”捕捉的阿金及其“精神”,也不无“廓大”的笔法。这样,阿金就并不是自然而然如实呈现在读者面前,她屡屡现身,每次都是渗透了“我”强烈主观感受之后的产物。如果说在乡村里,“我”还可以通过耳闻目睹记忆起“豆腐西施”的往昔故事,通过交往的口传信息了解祥林嫂的身前身后之事,那么,在都市中,我却只知道阿金现在是“我”邻居家的一个娘姨,不知道她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她向何而去,惟有眼前当下所作所为,构成了“我”对她认识的全部,同时也是认识方式的全部。虽说“阿金”的声音聒噪,但其“响亮”“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是紧跟在“我觉得”之后的。类似的,作者主要的感受方式都来自“我”的“观看”和“猜想”。如“我”和阿金最直接的一次遭遇,便是半夜三点的那次事件。“我”听到“谁来叫谁”,于是:
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
这里,“我”-男人-阿金三者的位置正好构成一个三角形状,在“我”好奇地观看男人与阿金的约会场景之时,却遭遇阿金“一看”,“一指”的翻转,反倒使“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其实,“我”仅仅是通过这一“观看”,建构起了自己的种种“猜想”,后果与阿金无涉,却影响了自己。而这种“看”与“被看”之关系的变化,又不禁令人联想起《祝福》里祥林嫂对“我”的追问,当年乡村里弱者的切切追问,使知识分子的“我”支吾以对,最后落荒而逃;今日城市中阿金的无需言语的“回望”,同样使“我”这个知识分子手足无措,并且“负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直到晚快边听见阿金“仍然嘻嘻哈哈”,“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才如释重负一般“很感谢阿金的大度”。虽则同为被看者的“回看”,需要区分的是,一个是悲剧,一个却仿佛喜剧,之前祥林嫂所追问的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这种带点“形而上”的问题,而说出“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这样“形而下”主张的阿金,则是不会如此回敬的。或许在她那里,“我”有意无意撞见的观看,确实是会被当成猥琐、无聊、偷窥他人“爱情”约会或“管闲事”来看待的吧。
至于“阿金”的其他状况,也都来自“我”的“猜想”,例如:“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这样的主观性叙述塑造出了“阿金”,也引导了读者对“阿金”的认识。叙述者对阿金的了解和讨厌,仅限于她在巷子这一公开空间的声音和行动,对她在主人家中的情况无从知晓。对于“阿金”的内心世界,叙述者也无论如何难以进入。只有“阿金”对“我”产生各种“影响”:“文章做不下去”,“有时竟在稿子上写下一个‘金’字”,“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而“我”对“阿金”则毫无作用,对“阿金们”的“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因此,我只能在领受她的“喧噪”之外,在她离开之后,在《阿金》中写下“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的句子而已。
那么,为什么作为知识分子的“我”面对下等人的娘姨阿金,会显得如此无可奈何,除了写下《阿金》,记录下自己的“讨厌”而别无他法?为什么会在“观看”和“猜想”里勾画出这样一个“阿金”来呢?
四、扰动和疑惑:“愿……也不能算是”
叙述者笔下,“阿金”固然“嘻嘻哈哈”“大声会议”的“嚷嚷”,却并非“有声有色”。虽然她自诩“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并且“好像颇有几个姘头”,但是“我”对她的形象却是另一种记忆。在“我”看来,“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幅模样来了”。阿金只是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阿金的冲击在于其响亮的声音和行动:“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我甚至为这种“扰动”的“力量”找出了更深刻的冲击之处:“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阿金是一个娘姨,原也是没有什么主张的,抵多是在“后门宣布的主张”,所谓“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但就算“我”意识到“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坦言“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对阿金的看法依旧是认定:“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这种“扰动”和“疑惑”的后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阿金“不再看见”之后,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并且“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叙述者补充说明这一段后事,或许重点不在于感叹“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也不是调侃讥刺《毛毛雨》之类的流行歌曲,而是在于新来娘姨的“雅气”。通过这种反差对比,在留白之处呈现出阿金身上所带有的“俗”来。
“雅俗之辨”是鲁迅1930年代杂文中一个常常论述的主题,讽古喻今、抨击时政、批评文坛多有从这个角度下笔的。仅在《且介亭杂文》中,就有著名的《病后杂谈》里所讥刺的“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的人物。而排在《阿金》之后,更有专门的一篇《论俗人应避雅人》,而两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仅相隔数日(42)。在这篇里,鲁迅因“看了杂志,偶然想到”:“浊世少见‘雅人,少有‘韵事’。但是,没有浊到彻底的时候,雅人却也并非全没有,不过因为‘伤雅’的人们多,也累得他们‘雅’不彻底了。”(43)可见,倘使揭穿了“雅”的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无此辈,何至于此呢?所以错处总归在俗人这方面”。“俗人”的坏处在于戳破“雅”,而这种“杀风景”的做法就是道出某种“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虽然尖刻批判“吃白相饭”这样的洋场奇观,但文章的最后还是会指出一点“吃白相饭”朋友的“可敬的地方”来,即“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44)这样说,当然不是从道德判断的意义上肯定阿金的主张,而是想说明,阿金这样的“俗人”身上的“伟力”之所由来。阿金“无情,也没有魅力,独有感觉是灵的”,这就像“小底梅花接老爷”那样,有一种嘻嘻哈哈中的冲击。并且“俗人”“阿金们”的“扰动”确乎并不受“雅人”的影响,他/她们只是一味的“俗”、“闹”下去,令洋人和洋巡捕无法,让“我”无奈。
重新细看《阿金》,有一个现象不可忽略,即“阿金”的出场恰恰多是跟“夜”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于“天一晚”聚集朋友嘻笑,而且于“半夜以后”同男人约会,还在“晚快边”大声会议。白天不事创作和译书的“我”尚能云端看厮杀似的,观察阿金和老×的奋斗,一到夜里,作为一个“作者”的作者便与阿金发生某种联系:阿金塞住“我”的路,“我”最讨厌阿金。
鲁迅是偏爱写夜,擅长写夜的作家,尤其是上海之夜。《且介亭杂文·序言》中就借此背景给出了自己的定位:“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45)而在《伪自由书》里,鲁迅也把自己定义为“爱夜的人”,描绘了一副夜上海都市经验的图景。有意思的是,与“爱夜的人”“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的,还有“摩登女郎”。她“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子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这会“碰着‘没落’命运”的摩登女郎,未必不是鲁迅在《南腔北调集》里所描述的“早熟”的“上海的少女”。尽管她们作为受凌辱者与孤独者同样领受夜的恩惠(46),但也就像霓虹灯下的“摩登上海”一样,她们“初学”的“雅”里泄露出自身的“不真实”来。至于霓虹灯外的“阿金”,这个平凡娘姨,则是不会“闪烁油汗”的,因为她有着“摩登女郎”或“上海的少女”所不具备的“俗”和“伟力”之“真实”。
有人曾把“阿金”的这种力量与鲁迅早年所赞扬的“摩罗诗人”相联系,这种评价可能过于高扬,因为“阿金”身上“奋斗”的“伟力”与“恶”的战斗力仍有很大差距。在鲁迅晚期杂文中出现的“阿金”,与他一贯批判的洋场“海派”“雅人”相比,自有一种文人不如的“真实”,只是舞文弄墨的“洋场恶少”们看似张牙舞爪,倒还是杂文能够直接对战的人物,而“区区一个阿金”,则需要鲁迅虚构出一篇在小说、随笔、漫谈、杂文之间不定的“小文”来处理。“爱夜的人”可以与“洋场恶少”/“摩登女郎”同时在夜幕之下,但麻烦的是,上海之夜还有区区一个“阿金”存在。在夜里,她似乎更具有能量,大声会议,宣布自己的主张,嘻嘻哈哈,扰动了四围的空气,甚至对“我”有所回击。虽然她是一个会讲一连串洋话的“阿妈”,但是连“邻近洋人的几句洋话”也不理,使“外国火腿”踢的效力,只“大约保存了五六夜”,与其把“阿金”说成一个“为外国人所豢养,狐假虎威,惹是生非的丑恶女人”(47),不如说她身上更多是带着一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而“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的潜力的东西,这种东西来自“上海”,来自“市民大众”。阿金恰恰属于上海最普通的市井世界,属于一再烦扰鲁迅的隔邻住户。在这世界里,有小市民也有劳工大众,如果说辛劳做工一天后回到家中,消闲、解闷、吹牛、谈天自然很是平常,喧闹嘈杂也是常事,但对于跟这个世界保持着距离,又远离不了“译书”的“我”,却实在“讨厌”。
回到所谓“漫画”,鲁迅指出:
廓大一个事件或人物的特点固然使漫画容易显出效果来,但廓大了并非特点之处却更容易显出效果。矮而胖的,瘦而长的,他本身就有漫画相了,再给他秃头,近视眼,画得再矮而胖些,瘦而长些,总可以使读者发笑。但一位白净苗条的美人,就很不容易设法,有些漫画家画作一个髑髅或狐狸之类,却不过是在报告自己的低能。有些漫画家却不用这呆法子,他用廓大镜照了她露出的搽粉的臂膊,看出她皮肤的褶皱,看见了这些褶皱中间的粉和泥的黑白画。这么一来,漫画稿子就成功了,然而这是真实,倘不信,大家或自己也用廓大镜去照照去。于是她也只好承认这真实,倘要好,就用肥皂和毛刷去洗一通。(48)
如果说,30年代的上海语境下,对于“雅”的“洋场恶少”、衣冠楚楚的文化世界,鲁迅能用“显微镜”放大美人的方式揭示其“虚伪”,让她承认“真实”;那么,对于“俗”的“阿金”,混杂喧闹的大众世界,鲁迅却只能是用“望远镜”来“观看”和“猜测”,并且面对“本身就有漫画相”的“真实”,要“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
《阿金》的结尾写道:“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叙述者对“很近于迁怒”的反省与“最讨厌”的决绝之间,隐隐存在某种张力。或者说,“讨厌阿金”的感觉是“的确的”,然而对于“塞住了我的一条路”,还是未能确定的“仿佛”。由此,我们可以说,《阿金》中通过叙述建立起来的“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与游移,才是作者最为在意的地方。并且这种困难在于,“我”不再是可以对阿金不闻不问的知识分子,阿金也不是跟“我”毫无关系的小民,“我”要依靠夜里译书,出卖文稿过活,“我”对自己文字的影响力没有直接的、亲身的感受;阿金在出卖劳力之后,有夜里自己的休闲和生活,她却能够用言辞直接扰动身边的空气。就是这样的“我”和“阿金”,不得不很现实地居住在同一个里弄,成为邻居,成为同一个上海屋檐下的市民。“近几时最讨厌阿金”的背后,其实是对这两者关系的难以处理,对关于两者的“信念和主张”“摇动”的“讨厌”。
于是,文章的最后才会写下“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这样颇为转折的句子。原本说“愿阿金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即可,但插进一个虚词“也”字,却让句意陡增一层,令人联想起背后可能带出的一系列“中国女性”形象:祥林嫂、豆腐西施、上海少女、摩登女郎……其实,鲁迅笔下的“女性”毋宁说是作为被剥夺了发言权,被男性/权力/文化压迫的弱者的隐喻。在这个意义上,处于这一谱系中的“阿金”,倒是跟《离婚》中的“爱姑”有几分相像(49),只是后者虽然也泼辣聒噪,却在七大人的“屁塞”之“雅”前败下阵来,而阿金则大有不把“雅”放在眼里的架势。再进一步的话,如果乡土中国“太阳落尽”之后出现的“女吊”是民间俗世之鬼,那么夜里大发“伟力”的“阿金”,未尝不是以上海为象征的都会里巷的俗世之鬼。就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说法一样,“阿金鬼”是粗野的、混杂的,却具有文化、文字不及的力量,本身就混杂了大众能够组织发动、对抗权势,又有待救赎改造、脱胎换骨的多重内涵,其开辟一条路和“塞住一条路”也只在“仿佛”的微妙之间。
附带一提的是,“鬼”有其字,却无其形,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想到‘阿金’两个字就讨厌”,却“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吧。
注释:
①《日记二十三》,《鲁迅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2页。
②参见《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219-221页。
③《341013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227页。
④《341031致刘炜明》,《鲁迅全集》第13卷,第245页。
⑤《350126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3卷,第359页。
⑥《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221页。
⑦参见《阿金》,《鲁迅全集》第6卷,第205-208页。以下引用皆出自该文本,不再另注明。
⑧竹内实:《阿金考》,《竹内实文集》第2卷,程麻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⑨关于鲁迅与“上海事变”关系的分析,可参看竹内实的《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鲁迅》,《竹内实文集》第2卷,程麻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文章从鲁迅日记1932年2月1至5日的“失记”出发,追索了鲁迅那时的生活。
⑩竹内实:《阿金考》,《竹内实文集》第2卷,第136页。
(11)《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63页。
(12)《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219页。
(13)《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3页。
(14)参见《鲁迅年谱》第4卷,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15)竹内实:《阿金考》,《竹内实文集》第2卷,第138-139页。
(16)《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476页。
(17)《350129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3页。
(18)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跳出以往研究中对《阿金》“文体”定位的游移。部分评述参见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得“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
(19)转引自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得“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
(20)何满子:《世纪末读鲁迅晚年杂文》,《深圳特区报》,1999年2月16日。
(21)有意思的是,这里对“阿金”一人便有“女仆”、“娘姨”、“阿妈”三种不同的“命名”,而后来许广平提到这篇文章则说是“描写里弄女工生活的小文”。参见许广平:《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2)竹内实在《阿金考》里写道:“鲁迅搬家时把女佣留给了魏金枝和柔石,这就是作为普通名词的阿金。”李冬木指出《竹内实文集》中该句译作“鲁迅搬家的时候,魏金枝和柔石有一个女佣,人们都叫她阿金”有误,现据李译改。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得“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
(23)何满子:《世纪末读鲁迅晚年杂文》。
(24)何满子:《阿Q和阿金》,《上海滩》,1996年第2期。
(25)《鲁迅年谱》第4卷,第150页。
(26)王瑶:《〈故事新编〉散论》,《王瑶全集》第6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27)竹内实:《阿金考》,《竹内实文集》第2卷,第46页。《阿金考》中竹内实对《采薇》的观察,甚至还有一种与30年代上海左翼文坛的对应读法,他“猜测阿金有周扬的影子,而小丙君则是影射着田汉、穆木天”,并将伯夷叔齐采薇糊口的“辛苦工作”与心境同鲁迅腹背受敌的状况相联系。
(28)“豆腐西施”对于闰土偷碗的告发,究竟是真是假,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公案。历来的研究里,有基于阶级论的视点,维护闰土的清白,也有侦探破案般,指出闰土实为小偷。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参见藤井省三:《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董炳月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29)卜立德:《为豆腐西施翻案》,《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
(30)《阿金考》收入《竹内实文集》第2卷,2002年版。此外相关的论述,还可以参考《江青的走红与垮台》,收入《竹内实文集》第6卷,程麻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31)参见竹内实:《竹内实文集》第2卷《作者前言》。
(32)据说毛泽东1967年在武汉梅园招待所读《鲁迅全集》,还向人说过“叶群是阿金式的人物,江青也差不多。”这样的话。转引自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
(33)关于里弄邻里吵架和娘姨关系的研究,可参见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4)参见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得“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
(35)《两地书·一二二》,《鲁迅全集》第11卷,302页。
(36)《两地书·一三一》,《鲁迅全集》第11卷,315页。
(37)许广平:《景云深处是吾家》,《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第228页。
(38)《361006致曹白》,《鲁迅全集》第14卷,第163页。
(39)《361012致宋琳》,《鲁迅全集》第14卷,第167页。
(40)《且介亭杂文·附记》,《鲁迅全集》第6卷,第221页。
(41)《漫谈“漫画”》,《鲁迅全集》第6卷,第241-242页。
(42)《阿金》写于1934年12月21日,《论俗人应避雅人》作于12月26日。
(43)《论俗人应避雅人》,《鲁迅全集》第6卷,第211页。
(44)《“吃白相饭”》,《鲁迅全集》第5卷,第219页。
(45)《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4页。
(46)参见钱理群对《夜颂》的分析,《“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读〈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里的杂文》,《鲁迅作品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7)《鲁迅年谱》第4卷,第150页。
(48)《漫谈“漫画”》,《鲁迅全集》第6卷,第242页。
(49)如日本学者中井政喜就认为:“从呈现了鲁迅民众观的作品谱系来看,爱姑是第一次出现的反抗和斗争的新的民众类型。”参见中井政喜:《关于鲁迅〈离婚〉的札记——从鲁迅之民众观等来看》,《言语文化论集》,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语言文化研究科,2008年第2期,第36-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