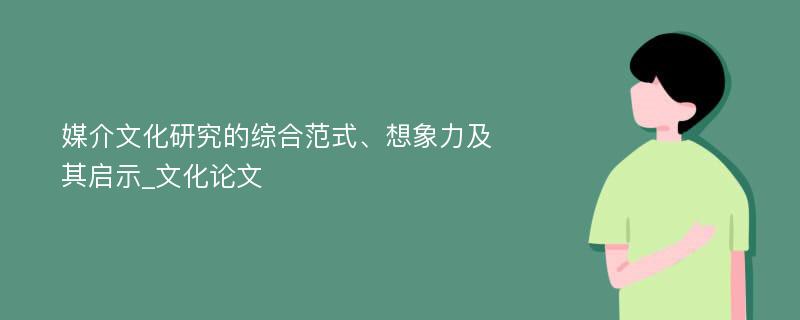
媒介文化研究的综合范式、想象力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媒介论文,想象力论文,启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文化研究在国内逐渐成为显学,吸引了文艺学、文化学、社会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各个学科的相关研究常常囿于单一视角,难以融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媒介文化研究虽然表面上很热闹,但是在国内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却处于边缘地位,研究者少,有分量的研究实绩不多。从研究范式的角度分析表明,上述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式难以包含媒介文化的研究范式,这种状况不仅使媒介文化研究与各个学科研究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也造成媒介文化研究方法的深层次混乱。鉴于研究范式在学术研究之中的核心地位,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媒介文化的综合研究范式及其对于当代中国众多学科研究的价值。 一、媒介文化研究的综合范式 相对来讲,北美媒介文化研究好像较为“冷落”,相关的评论综述在国内学界并不多见。其实,北美媒介文化研究十分复杂,一方面或多或少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学派和英国伯明翰学派等文化研究的观念、方法,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非常鲜明的自身特色。如美国的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资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美国研究强调多学科视角,偏重宗教、地区、性别、种族、城市、全球化、美国化等题材的研究,并一直影响至今。①同时,北美尤其是美国的解构主义思潮研究颇为红火,与当时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研究相互唱和。尤其是以保尔·德曼、哈洛德·布罗姆、杰夫里·哈特曼和希利斯·米勒等理论家为代表的“耶鲁学派”强调欧美文学的解构主义阐释方法,对于北美乃至世界范围的媒介文化研究皆有较大影响。 我们知道,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文化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美国进行的。阿多诺、霍克海姆等理论家目睹美国大众通俗文化的兴起,以精英主义的视角猛烈而悲观地批判大众通俗文化。受此影响,“批判式的”北美媒介文化研究虽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长时间处于边缘地域,但是其传承式的研究一直并未断绝,相继出现了诺姆·乔姆斯基、赫伯特·席勒、丹尼尔·贝尔等理论家的社会文化批判,其研究范围涉及西方政治批判模式、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大众传播垄断机制、消费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影响等重要论题。而北美学界十分活跃的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文化研究,其主导的研究视角仍然是批判式的。例如,尼尔·波斯曼将媒介文化批判置于当代教育学和语言学的广阔背景下,着重剖析大众媒介文化对人们的负面影响,批判技术垄断产生的超量信息对人类社会生活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尤其在1992年出版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他将技术分成“技术工具”、“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将希望寄托在教育以及人文精神的弘扬方面;②凯瑞是美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将传播研究分为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两种类型,一生致力于传播仪式观的研究,着重挖掘与探讨传播仪式观的价值与意义,强调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③他真正地从“作为文化的传播”视角,深入分析大众传播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媒介文化(文化研究)在传播学研究中的价值与地位。 近20余年来,美国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从多学科角度进行传媒研究的学者,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詹姆斯·卢尔(James Lull)、约翰·彼德斯、马克·波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卢尔是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传播研究系荣休教授,他研究兴趣广泛,尤其关注文化与传播的关系研究,他于2007年出版专著《文化点播:危机世界中的传播》,以中东与美国为分析重点,探讨了“9·11”之后全球媒介与大众文化的进化之道。④彼德斯是美国依阿华大学传播研究系主任,他早年的专著《交流的无奈》从宗教、哲学、文学等不同视角研究西方传播思想史,视域广阔,独树一帜。⑤近些年来,他从更为广阔的历史、法律、哲学、技术、自然生态和宗教语境研究媒介史和文化史。⑥波斯特是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学系、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几十年来致力于西方文化思想史、批判理论、新媒体研究。他善于从哲学思辨、思想史、历史、文化的角度考量媒体发展及其重要作用,具体探讨新媒体与后现代语境中主体、信息方式、现代性等前沿而重要的理论问题,敏锐、智慧而兼具理论深度。波斯特新近开始重点研究全球数字技术传播对个人、社会与政治形态的影响,通过事例分析了影像挪用的启蒙与困惑、数字时代犯罪新形式、身份盗用与身份认同、伦理、知识产权、文化抵抗等新问题,并探讨信息机械为进步变革提供的机会。⑦ 凯尔纳的研究强调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宏大背景,早在1995年出版的《媒介文化: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与政治》一书中,他就强调“批判性的、多元文化的和多重视角的文化研究”,以里根和兰博、恐怖片和青春片、说唱音乐、麦当娜、时尚、电视新闻和娱乐节目、MTV、作为文化文本的海湾战争、网络朋克小说为例,在语境中分析意识形态、霸权、亚文化抵抗、现代性认同等诸多文化问题;⑧在2003年出版的《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一书中,他以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分析了美国麦当劳快餐文化、体育文化、辛普森案件、电视文化、政治选举等方面的社会文化的奇观化与奇观文化现象,极具理论新意与现实意义;⑨2009年,凯尔纳与朗达·海默共同编辑出版了《媒介/文化研究:批判的路径》一书,在其中,道格拉斯·凯尔纳再次强调了政治经济的、文本分析的、受众导向的媒介文化批判性视角的重要意义。⑩雪莉·特克尔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她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与人格心理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是有执照的临床心理学家。她30多年来结合自己的专业优势,重点进行人类与技术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包括了移动通信技术、社会化网络、社会化机器人等)之间的关系研究。早在1984年出版的《第二自我:电脑与人类精神》一书中,雪莉·特克尔就探讨了新型电脑文化的形成及其机械化对人们意识与自我观念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焦点小组方法。在2011年最新出版的专著《群体性孤独》中,她再次大规模采取田野调查及临床研究两种方法,将研究对象拓展到移动通讯、即时通讯、社交网络、推特、大型在线游戏等最新领域,探究技术对人们关系的深刻影响,呼唤人性、同情、真实和爱的坚守与复苏。(11)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新闻、电影艺术学院的詹金斯教授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的研究。詹金斯的研究可谓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一个最新发展,他自称自己的研究就是作为玩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协商,(12)在这种双重身份的融合中,他更加深入地分析《幸存者》、《美国偶像》等美国最新真人秀节目的粉丝团与游戏玩家、博客社区等媒介受众群,强调了传媒技术新语境中传播互动与参与等因素的最新发展及其对社会文化各因素的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北美传播学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紧密,尤其是美国传播学研究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思想之间的传承关系尤为明显。(13)根植于社会科学研究之中的美国传播学研究传承了美国实用主义原则,强调效果研究,与战争动员、政治选举说服与美国的自由媒体市场关系密切,出现了传播研究的“经验—功能学派”。(14)麦奎尔将其总结为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dominant paradigm),这种“主导范式”将“大众传播具有强大作用的观念与社会科学所形成的典型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调查方法、社会心理实验与统计方法结合起来”,它假设“良好社会”具有一种规范功能,是民主的、自由的、多元的、协商的、秩序的和充分告知的,并可以通过目前的组织手段解决不平等、不公正和社会的张力与冲突。同时,西方大众传播还自视在支持和表达“西方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5)这一研究的特点是:(1)秉承客观科学乃至技术乐观论的研究态度;(2)注重传播效果研究,成果丰富,由此衍生出美国传播学研究之中公共关系、政治传播、健康传播、营销传播等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学科;(3)运用了把关人、沉默的螺旋、二级传播、意见领袖、使用与满足、皮下注射等范畴;(4)强调定量研究方法。总之,这种传播研究方法注重以社会调查或实验方法进行数据搜集,进而进行传播的功能框架与过程研究,这种方法虽然颇受争议,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当代媒介文化研究。同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社科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中,美国学界有关文化的研究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多学科、跨学科等交叉特征明显,出现了文化社会学、传播社会学、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心理学、跨文化传播等新兴研究领域,极大地开拓了当代媒介文化(文化研究)的题材与视域,成为我们进行媒介文化研究的宝贵理论资源。 近些年来,国内外传播学界有不少学者致力于传播学研究的学派界定与范式转变等方面的研究。在传播研究范式的分类方面,各方众说纷纭,美国学者麦奎尔在他不断更新的《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将传播研究分为主导范式和批判范式两大范式,主导范式包含传递模式和宣扬模式,批判范式则包含仪式模式和接受模式,由此可见批判范式所包含的文化视域与方法的重要性。潘忠党认为传播学研究分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陈卫星则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3个学派,陈力丹认为有经验—功能、技术控制、结构主义符号—权力等3种范式,胡翼青认为可以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3种研究范式,等等,(16)同时,国内从传播学角度对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梳理与论述也不断出现。(17)细致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发现,上述传播学研究的各种范式分类大多有意无意地将媒介文化研究划并到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之中,因此,国内外的相关著述常常将媒介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归并到传播学的门类之下,并以科学建制、教学与学会、期刊等方式进行固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媒介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异常丰富而驳杂,分属于不同学科之中,很难从单一学科的角度进行归类总结。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媒介文化研究究竟处于传播学研究的何种位置?媒介文化研究的范式与上述传播学研究范式有何异同? 从法兰克福学派到结构主义学派,他们的文化研究大多强调单一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像结构主义符号学范式的文本研究尤其强调方法的独特性与文本的封闭性;到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其实也是把北美定量研究的传播学作为靶子的,这就促使其研究侧重诠释研究范式与批判研究范式的结合,并影响到其后欧美的媒介文化研究。在科伦教授看来,美国的传媒研究倾向于聚焦经验范式,而英国的传媒研究是同通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强调的是诠释研究范式与批判研究范式。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之中有关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争议在西方学界一直很激烈。不过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强调二者的融合,(18)例如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威廉斯起于文学研究,兴于传播与文化研究,合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他在1981年出版的《文化社会学》一书中,强调文化研究的综合性,认为文化研究是人类学、社会学、艺术和知识活动(包括哲学、新闻、时尚、广告等)领域的综合。(19)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学院的舒德森教授侧重于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新闻、大众文化与政治民主、公共文化,极大地拓展了新闻研究的领域;(20)伯克维兹从社会的、文化的路径来研究新闻,特别是新闻叙事、集体记忆、媒介与恐怖主义,重点从新闻作为社会产品和文本的角度广泛探讨了新闻的社会塑造及其社会意义;(21)2011年,他又编辑出版了《新闻的文化意义》一书,这本书收录23篇论文,探讨了新闻的文化实践、新闻的阐释共同体、新闻范式修复、作为文化文本的新闻叙事、新闻作为集体记忆等问题。(22) 美国学者凯瑞曾谈论过他的研究经历,认为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传播的传递观占据美国思想的主流地位,因而从文化、社会学等角度对传播学的研究进行深度拓展。(23)凯尔纳认为,文化研究最好是社会理论、文化分析、历史、哲学和特殊的政治干预等研究相结合,这样可以克服由媒体、文化和传播等分支领域的专门化研究,进而超越现有的学术分类的标准。(24)麦奎尔在总结西方传播学研究模式时,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总结为传播学研究“主导范式”的“替代视角”(the alternative perspective),“这一范式在各个方面拓展了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具有特殊的价值,媒介经验与社会文化经验的互动和参与皆汇聚于此。”(25)结合上述北美和英法等欧洲国家的研究状况,我们发现当前欧美尤其是北美地区的媒介文化(传播学)研究远远超越了麦奎尔所谓的“替代视角”,其研究内容、领域、视角与方法等方面多学科特点尤其明显,体现出媒介文化研究综合范式的成熟。这一综合范式灵活而充满生机,是传播学与文化研究各种范式的综合,跨学科而超越学科,带动媒介文化研究、传播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研究整体水平的提升。 二、媒介文化研究的想象力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论及二战之后面对社会、私人生活的变迁与战争威胁而感到惶恐的人们时认为,人们不仅仅需要信息和理性,“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26)米尔斯实际上是在强调社会学研究要弘扬社会之道并发挥其日常生活的价值,促进我们反思所谓的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吉登斯在分析“社会学的想象力”时则将其引申为社会学分析不可或缺的3种感受力,即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27)哈贝马斯认为,任何一种认识都起源于知识要素的旨趣。他认为人类知识要素的旨趣有三种类型,并与不同的认知旨趣相关:“经验—分析的科学”与技术的认知旨趣相关;“历史—解释学的科学”与实践的认知旨趣相联系;具有批判倾向的科学的研究与人类解放的认知旨趣相关联。(28)可见,人类旨趣虽然是可以分类的,但是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而分类,而是未来人类的“解放”,因此,批判的哲学要逃避实证主义的陷阱。晚年的哈贝马斯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沟通理论,强调大众传播对于公共领域的动力和力量,希望由此重建人类民主政治的理想。(29)同时,他还不断对世界重大事件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些观念在物欲横流与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语境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甚至有些顽固、保守,但是,所谓的学术研究已经演化成了哈贝马斯一种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不懈地探寻着西方哲学思想中的对话传统,也就成为一种富有生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涉及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方面,理查德·约翰逊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曾将文化研究分为三类:基于生产的研究、基于文本的研究和鲜活文化的研究。这三种研究都强调了政治研究取向,但是各自的取向又可能约束我们对文化理解的更新,因此,文化研究需要这些研究模式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与“真正的同一性”。(30)约翰逊的这一总结多少概括了法兰克福学派、法国结构主义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特色,论及了文化研究的综合范式与未来发展。这么看来,媒介文化研究的想象力是什么? 我们知道,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特征,但是库恩认为,范式又产生于众多竞争模式,并且足以提出众多新的问题。(31)范式实际上就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范式的演变与其学术研究内在机制、研究人员状况等方面因素有关,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尤其是文化背景的变迁。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认为,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从问题意识出发,而不是从方法出发。因此,他提倡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一个好的理论必须要比一个差的理论能解释和概括一个复杂故事中更多的现象。从这个原则出发,我进一步提倡社会科学叙事的出发点不应该针对一个复杂事物中的一个或者是少量几个问题进行解释或者理解,而应该是对多样问题同时进行解释或理解”。(32)当代媒介文化覆盖一切,尤其是日常生活,由此,媒介文化研究综合范式的出现与流行就势在必然。目前,西方学界虽然对有关文化的定义、文化研究的范围、方法和文化研究的历史等问题还存在很大争议,(33)但是这些争议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文化研究本身的活力,西方不断再版的一些“文化研究教程”和“文化研究读本”类的书籍,其研究的问题域蔓延到笑话、政治权力、地理、传播技术、人类学、生物学、语言转向、后殖民、后现代日常生活、后女权主义、休闲文化、亚文化、明星文化、粉丝文化、视觉文化、虚拟文化、数字媒介文化、新媒介文化、融合文化、全景机器、文化政策、全球化、新社会运动等各个方面。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传播研究系教授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本身是知识分子的实践,不仅要求归属于某处,而且要求归属于知识分子的集体事业之中。它不仅挑战各学科之间的界线,更为重要的是,它挑战了学术与外面世界的界线。”(34)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他再次强调文化研究的超越学科的意义,认为文化研究是各个学科的相互的、共同语境的思维,“我一直认为文化研究是在邀请人们介入对话和合作实验,进行转化与改革的实践自我反思,异常努力地建构新的组织空间。如此,文化研究既是艰巨的又是生机勃勃的,既是令人沮丧的又是充满希望的,既是谦虚的又是高傲的。文化研究就是实现我作为政治的知识分子的道路。”(35)因此,用文化的视角看媒介与传播,读出它的文化意味,展现与阐释媒介与传播之中的文化因素,另一方面,又使其深深地根植于日常生活之中,不回避丑陋,而是揭露批判之,更为重要的是,促使人们深信与坚守基于内心与社会的美好与感动,媒介文化的想象力就此展开。 威廉斯在196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认为英国近代以来的变迁经历了两百年,包含着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文化革命及其复杂的互动过程,因此,他将当时英国的文化危机当作“漫长革命”的一部分来看待分析。(36)而对于英国理论家伊格尔顿来讲,文化不仅是我们赖以生活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它还是我们为之生活的一切,“在承认其重要性的同时,让文化回归其原有的位置,现在该是这样做的时候了。”(37)究竟让文化回归到什么位置,对于伊格尔顿来讲,就是文化对生活的批判、指导和进行价值判断的超越位置。凯尔纳认为,媒体的滋生促进了新的文化形式的产生,逐渐占据了人类的思维和日常生活的主体。(38)正是基于媒介文化的重要意义,凯尔纳强调文化研究应当超越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生产、使用和消费的语境,运用媒介文化来解析这些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把社会文化看作一个充满征服与抵抗、压制与斗争、同化与异化的竞技场,旨在追求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秩序,促成社会进步和变革的出现。因此,文化研究最终应当成为诊断式批评与社会变革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各种主宰和征服性的文化霸权进行有效批判。其中的诊断式批评更是突出将人们熟悉的各种媒介文化现象的“神话”层层剥开,解析其社会语境、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及其在复杂的社会冲突中所发挥的功能。(39)看来,凯尔纳等人更加强调了大众媒介文化研究植根于社会批判理论的质疑与批评功能,把当代大众传播看作一个推行霸权和抵抗霸权共存的话语场;而斯坦福大学传播学院的费什金教授多年致力于探索大众传播作用于协商民主与公共领域的实践之途,通过众多成功案例开辟了当代政治传播的实践领域。(40)因此,从广义的角度分析,人们还是希望大众传播成为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进而促进与保护社会民主的发展。具体到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自由贸易的背景下,大众媒介文化的繁兴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富于时代意味的社会现象之一。细细想来,我们60多年来的所谓精英文化是什么?政治文化的权威性依旧吗?我们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生的国人,有几个没有痴迷过流行歌曲、电视剧、大片或者电子游戏、网络文化呢?赵旭东在反思中国本土文化建构时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对现代化的追求更深层次的意旨就是对现代性的张扬,“这种张扬是通过对上述所谓社会工程的整体规划而得以实现的。由此所带来的对政治权力的强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是今天我们对现代性在中国的滥觞加以反省的现实基础。”(41)中国当代的社会进程及其社会文化矛盾实际上也是其自身“漫长革命”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文化应该回归到什么位置?我们身处其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此时,也许正是需要我们展开媒介文化研究想象力的时候! 三、中国媒介文化研究:问题域分析 我们重点分析了媒介文化的综合范式,其研究的实际状况远远比我们分析的要复杂,体现出西方相关理论资源的异常复杂性与丰富性。总的分析,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虽然经历过不少次的“断裂”,但是,西方相关理论的学术脉络源远流长,即使是所谓的后现代思潮也没有一派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他们批判也好,继承也好,或明或暗地都拥有其理论资源,即类似库恩所谓的“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一样的“基础思想”,(42)一直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每一位媒介文化研究的后来者。由此,这些学术资源不仅增强了媒介文化研究的流派传承,也使其研究人才辈出,(43)促进其研究结合语境流变而不断增强的研究活力。 我国内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经过30余年的积累与发展,众多学科开始或强或弱地呼吁“中国学派”的研究与组建。目前,对于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文艺学、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研究之中,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对此话题也有一定的探讨。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的不少困惑与问题。也许,在目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我们30余年的学术积淀毕竟还是太短暂了。对于“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有学者就认为学科理论缺乏原创性和应有的理论积累,(44)因此,从传统思想与当代问题出发,整理与挖掘其中的学科价值与实践意义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也可能为非西方化的传播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45)陈卫星在对中国传播学进行本土性反思时认为:“在中国,传播学今天所面临的学术挑战是一个二元命题:既有技术扩散与社会转型的复杂角色冲突,更有源于研究对象的本土性所提出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挑战,即现代性的挑战。”因此,“只有回到本土语境,重新梳理本土文本,从文献到考证,从事实到经验,从模式到理论,从中提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传播学叙事。”(46)由此,我们不妨搁置其理论建树问题,而去结合亟待我们分析与研究的“真现象”以及其中的“真问题”——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各种现象——进行相关理论资源的整合借鉴欧美媒介文化研究的综合范式,强调中国意识,进行针对现象的问题域研究。从这一层面分析,“真问题”必定是社会文化现象与日常生活方式,所谓的研究范式也必定是灵活的综合范式。而对于媒介文化研究,就是将媒介叙述及其传播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以文化的视角分析传媒系统,从传媒系统中挖掘出文化的内涵、价值与意义。这就应该超越所谓的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审美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区别,结合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语境,分析文化现象、特征及其当代政治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其核心的关键词是中国当代语境、文化现象、问题域、综合视角。在此基础上,超越所谓的学科体制的限制,广泛吸纳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我们倡导的媒介文化研究将从各种典型现象入手,注重其感性、日常性、实践意义等方面,把文化研究、传播学研究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相对避免众多人文社会理论研究对此存有的偏颇,使媒介文化研究既具有批评性、概括性,又具有建设性与实践性,由此来突出我国当代媒介文化研究的特质与实际价值。因此,与其沉溺于我国的文化研究学科体系建设等宏大问题,不如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我国新闻传播业与社会文化的各种现实问题上,通过大规模的系统研究来探讨媒介文化研究的实践特色与意义。 结合中国的现实语境,我们大致将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研究分为8个问题域:(1)政治媒介话语与意识形态。从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一直到目前的文化研究与媒介批判,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与研究视角,由此形成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与多学科融合的飞地。如著名学者卡斯特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出著名的“信息时代”三部曲,政治与权力是其重要议题;十多年后,卡斯特又于2009年出版大部头新著《传播权力》,认为传播技术的革新导致全球传媒工业的转型,全球政治与权力也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网络社会的权力就是传播权力。”(47)反观中国当代政治与意识形态,我们发现其复杂性远远超越其他国家的媒介文化形态。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48)第一个30年的“文化革命”经历以及第二个30年的各种文化思潮争议、(49)现代化的状态、媒介机制与社会状态、政府治理转变(50)等问题,都令人目眩神迷。鉴于特殊情况,该主题研究适合以分散议题的方式进行适当分析。(2)中国媒介版图。比较而言,中国新闻传播业的革新虽然相对滞后,但是30余年来,其“局部”变革仍然十分令人惊讶。目前,国内媒体组织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媒产业的革新方面步伐加快,这样,一些深层次的固有矛盾也显现出来,表现出媒介文化最为复杂的特征。(3)广告文化。广告曾在第一个30年被取消,后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广告从信息传播的“依附式”的状态,发展成为当今国内新闻传播业的主导逻辑与媒介文化的主体文本之一。比较而言,国内广告文化又与西方发达的广告文化有着不少的本质区别,显示出不同话语力量的博弈。(4)媒介性别话语。女性主义是一个理论与实践意义非常强的当代思潮,是我们分析媒介文化一个极为有力的视角。(5)体育文化。体育是集合政治、民族、种族、经济与娱乐、无意识等各种复杂因素的一个场域,也成为中国当代媒介文化最为耀眼的一个部分。(6)新闻文化。新闻看似是一种技术含量不高的技艺——写作的技艺,与文学写作相比,它是速朽的、非个人的、非艺术化的,并且是可以教授的,但是,新闻又是高度组织化、现实化与强意识形态化的,其外延的蕴含远远超越了艺术创作。从这一层面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感知新闻报道与喧嚣的现实之间复杂微妙的关联和冲突,新闻文化的分析需要多视角与祛魅式分析,而且似乎永远也不会过时。(7)新媒体与网络文化。新媒体技术促生网络文化等新文化形态,这成为欧美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近20年来,我国以政府主导力量推动新媒体硬件设施的高速发展,成为网民最多的“网络大国”,新媒体文化形态深深嵌入社会文化的众多肌理之中,尤其在日常生活层面,网络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构成当代媒介文化最为重要的部分。(8)视觉修辞与图像传播。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在近些年促进了图像的超大规模制作与传播,所谓视觉文化的研究也成为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视觉文化融合了哲学、修辞学、艺术学、影视学、摄影、文化研究、人类学、历史等方面的内容与方法,成为当代媒介文化研究之中极富创意的研究分支。 布朗特林格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经过60、70年代理论与规范的论战,文化研究的出现表现了当前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危机和矛盾,文化研究“不是围绕某个议题的紧密、连贯、单一的活动,而是有关倾向、议题与问题的松散的学术小组”。(51)结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所谓的媒介文化(文化研究)学科建制的实践与反思固然很有意义,但是进行所谓的“跨学科、多学科抑或反学科”的媒介文化(文化研究)研究无疑是一条更为可行之路。目前,我国内地媒介文化(文化研究)虽然相当热门,但是不同学科间的相关研究还是存在较大隔阂。在学习借鉴各方经验的同时,内地媒介文化(文化研究)研究大规模地整合现有的相关学科、研究人员、研究硬件、网络等方面的资源,全面译介海外相关研究资源,打通分布在各学科相关研究人员的资源、观念、方法等方面的壁垒,重点研究媒介文化(文化研究)有关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问题域、方法论、价值与意义,进而形成超越学科而又契合当代社会文化转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范式。目前,大数据技术高速发展,为媒介文化研究、传播学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综合研究范式的更新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因此,通过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研究,我们希望突破媒介文化(文化研究)研究在学术资源、学科建制、课题申报、成果发表与成果评选等方面的弱势,更希冀由此强化国内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学等学科有关媒介文化研究,增强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内涵与学术积淀,进而促进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整体水平高层次的发展。 ①Bruce Burgett and Glenn Hendler,eds.,Keywords for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7; Brian T.Edwards and Dilip P.Gaonkar,eds.,Globalizing American Stud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②参见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页。 ④James Lull,Culture-on-Demand:Communication in a Crisis World,Oxford:Wiley Blackwell,2007. ⑤参见彼德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⑥John Durham Peters,Courting the Abyss:Free Speech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John Durham Peters,The Marvelous Clouds: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 ⑦Mark Poster,Information Please: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igital Machin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 ⑧Douglas Kellner,Media Culture:Cultural Studies,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London:Routledge,1995. ⑨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⑩Douglas Kellner,"Toword a Critical Media/Cultural Studies," in Rhonda Hammer and Douglas Kellner,eds.,Media/Cultural Studies:Critical Approaches,New York:Peter Lang,2009. (11)参见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12)Henry Jenkins,Fans,Bloggers,and Gamers:Exploring Participatory Culture,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6,p.2. (13)参见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 (14)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15)Denis McQuail,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6th ed.,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10,p.63. (16)陈力丹:《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2期。 (17)孔令华:《论媒介文化研究的两条路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媒介文化观差异之比较》,《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杨击:《传播·文化·社会:英国大众传播理论透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18)R.Burke Johnson and Anthony J.Onwuegbuzie,"Mixed Methods Research:A Research Paradigm Whose Time Has Come," Educational Researcher,vol.33,no.7,2004,pp.14-26. (19)Raymond Williams,The Sociology of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13-14. (20)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徐栓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迈克尔·舒德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 (21)Daniel A.Berkowitz,Social Meanings of News:A Text-Reader,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1997. (22)Daniel A.Berkowitz,Cultural Meanings of News:A Text-Reader,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11. (23)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第11页。 (24)Douglas Kellner,Media Culture:Cultural Studies,Identity and Politics between the Modern and the Postmodern,p.27. (25)Denis McQuail,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Sixth Edition,p.69. (26)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页。 (27)安东尼·吉登斯:《批判的社会学导论》,郭忠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9页。 (28)Jü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a General Perspective," in Jürgen 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Boston:Beacon Press,1971. (29)Jürgen Habermas,"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Media Society:Does Democracy Still Enjoy an Epistemic Dimension? The Impact of Normative Theory on Empir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vol.16,no.4(November 2006),pp.411-426. (30)Richard Johnson,"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nyway?" Social Text,vol.16(Winter 1986-1987),pp.38-80. (31)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32)赵鼎新:《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文汇报》2011年7月4日,http://ewenhui.news365.com.cn/wh20110704/. (33)John Hartley,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3,p.8. (34)Lawrence Grossberg,Dancing in Spite of Myself:Essays on Popular Cul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22. (35)Lawrence Grossberg,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p.294. (36)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Peterborough:Broadview Press,2001,pp.10-12. (37)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 (38)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第107页。 (39)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第35—38页。 (40)J.S.Fishkin,The Voice of the People:Public Opinion and Democra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41)赵旭东:《反思本土文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46页。 (4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63页。 (43)Andrew Edgar and Peter Sedgwick,Cultural Theory:The Key Thinkers,London:Routledge,2002. (44)参见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5)Shelton A.Gunaratne,"De-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Social Science Research: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Media,Culture & Society,vol.32,no.3,2010,pp.473-500. (46)陈卫星:《关于中国传播学问题的本体性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2期。 (47)Manuel Castells,Communication Pow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53. (48)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49)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文艺争鸣》2004年第5期。 (50)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3期。 (51)Patrick Brantlinger,Crusoe's Footprints:Cultural Stud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New York:Routledge,1990,P.IX.标签:文化论文; 传播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范式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学论文; 想象力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