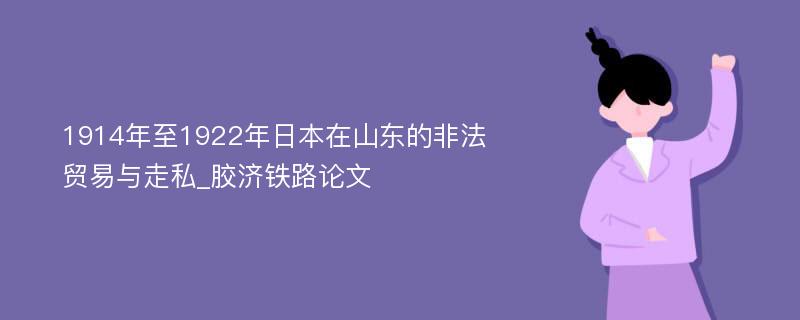
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山东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打着“对德宣战”的旗号,出兵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在此后的八年间,日本在对山东实行军事占领的同时,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其掠夺的方式,除倾销商品、输出原料、投资设厂、举行“合办事业”外,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法贸易和走私。如套购中国通行的制钱、铜元;贩卖吗啡、鸦片等毒品;私售枪支;运销私盐等等。本文即拟对此作些初步的分析和研究。
一、非法套购制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各国的军事工业所必需的原材料铜和锌的价格扶摇直上。而当时中国通行的制钱,则基本上是由铜、锌两种材料铸成,其中铜的含量为1/2,锌的含量为1/4,其余1/4为杂质。日本的奸商、浪人见有利可图,便利用日军武力占领山东的时机,在山东境内掀起了一股非法贩卖中国制钱的恶浪。他们以低价收购中国制钱,经熔化提取铜锌后,再高价出售给欧战各国,从中牟取暴利。
日商在山东贩卖制钱的非法贸易,大约开始于1915年5月间。青岛铃木商店首先染指此业,其它日商乃至中国不法商人纷纷仿效继之。据青岛日本守备军司令官大谷喜久藏统计,到1916年在胶济铁路沿线专门收购制钱的日本商人已多达5,000余人。①胶济沿线各站及附近城镇村落的旅馆、饭店、客栈大多为日人盘踞,成为从事制钱交易的据点。
结成团伙、武力抢劫,是日商掠取制钱的手段之一。据日人西原龟三记述,1916年在山东约有十余名日人被打死,都是这类结伙抢劫的日本商人。该年6月初,有十余名日人结队到日照县某村庄抢夺制钱,其中有三、四人被村民打死。日本官宪和军队开赴该地,搜查“凶手”,竟火烧全村而归。②
假游历为名,深入山东内地,直接收买,是日商掠取制钱的又一手段。据统计,仅1915年7月间,在泰安、齐河、禹城三县境内查获的、无游历护照的日商私贩制钱案即达四起。③那么,持有游历护照、未被查获的当难以计数。为防禁日人假游历之名私运制钱,1916年10月4日山东督军张怀芝曾电示中央:今后凡外人办理游历或通商护照时,交涉员应分辨明确加以戮记,声明不得贩运制钱。1916年10月1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也曾为此向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发出照会:日人持用游历护照,不得在鲁省内地贩运制钱,请转饬该处领事官严切禁阻,以重约章。④由此可见,日人以游历为名私贩制钱的现象较为普遍,故而才引起了山东地方当局和北京政府的极大关注。
雇佣汉奸,代为收买,是日商获取制钱最常用的手段。为引诱中国不法商人为其效劳,日人往往诱以小利。例如,1916年时,“制钱行市每百斤约值大洋17元左右,而日人均照20元预先给值,故内地奸民争为效用。”⑤按照中国法律,华人贩运制钱,须治监禁一月之罪。但日人倚仗治外法权和日本驻军的庇护,“一经查获,即有日人出头干涉,指为代买,虽欲充公,诸多窒碍”⑥,致使中国禁令难以实行,坐视日人牟利。
通过上述种种方式,日本商人从山东各地攫取了大量制钱。最初,日商是将原物运走。将制钱从各地车载船装或雇佣苦力腰缠、肩挑运送,络绎不绝地汇集于胶济铁路沿线各站;然后运往青岛;再由青岛装船水运日本神户、大阪及其它港口。日本国内的精炼业者再将这些制钱熔化,提取铜锌,以高价卖给交战各国,其中1/3卖给了沙皇俄国。甚至有一部分又返销于我国。据日人统计,1916年,仅大阪一地专门熔化中国制钱的精炼业者,规模较大者即有40家,小者37家;从神户到冈山之间约30家,合计达107家⑦。后来,由于中国政府对输出制钱取缔甚严,同时为便于运输,节省运费,日商又在山东各地设立熔炉,就地冶铸成铜块后再运往日本。据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林久治郎在给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的报告中供称:1915年在青岛市内经营制钱熔解铜块业者仅有铃木商店和中松洋行两家,但到1916年则激增至十四、五家。⑧出现了所谓“采买之车络绎于通衢,化铜之炉径设于商埠”⑨的局面。
查制钱禁运法令,约章规定甚严。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五款第一项规定:铜钱不仅不能运往外国,而且禁止内地贩运,虽能由通商此口运往彼口,然尚须遵章具保核准发给运照方可。1871年的《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26款也明文规定:“两国制钱,除照章转运别口外,各不准贩运出洋。如有商人私贩,查拿入官。”⑩可见,制钱禁运,既有中英条约所明定,又为中日条约所援用。而日本商人在山东内地私贩制钱,并运往日本,显系违约犯禁的不法行为。但对于日本奸商的这种违法犯罪行径,日军占领当局最初竟采取了支持甚至奖励的措施。不仅通过准许日商利用胶济铁路装运制钱,对运铜出口的船只发给出港证等方式支持这项贸易。(11)而且,胶济铁路还曾一度向贩运制钱的日商提供优惠运价予以鼓励。制钱运输,本来按贵重物品处理,照普通货物的三倍支付运费。但胶济铁路却从1915年7月1日起,对制钱运金准收平价。因遭到中国政府的抗议,才不得不从12月1日起宣布运金复旧。(12)
日商在山东的不法行为,特别是某些日本浪人结伙抢劫、威逼强购的野蛮行径,曾遭到山东人民的抵制和反抗。由此而酿成的冲突事件,层出不穷。中国的有识之士也纷纷致电山东当局和北京政府,要求严禁日人收买和销毁制钱。并建议政府设法按市价收购制钱,自行销毁,改铸铜元,以资流通,以杜绝日商私毁私贩之弊。(13)德国驻华领事也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指出日人在鲁收买制钱及运铜出口,不仅有违中英条约及中国中立条规,而且有损中国贸易,望严饬取缔禁运。(14)
山东地方当局和北京政府对此出曾采取了一些防禁措施。1916年11月18日,山东督军署发布禁令,命山东各县严行查禁日人收买制钱。(15)并多次照会济南日本领事林久治郎,要求对查获的日商予以严惩。北京政府外交部也多次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1917年后为代理公使芳泽谦吉),要求转饬山东日军当局严切禁阻,以维睦谊。(16)1916年5月,北京政府又训令天津、青岛各海关,实行新订铜块出口办法。规定:凡出口铜块,如查出有制钱痕迹,则没收之。又报运铜块出口之人,于出口之前,应先向卖出之人,领取该铜块并非由制钱熔毁之证明书,交海关查阅。(17)
在上述背景下,济南日领林久治郎虽不得不于1915年11月19日发出了禁止日人贩卖制钱的告示,(18)但实际上不仅未予切实禁阻,反而采取了纵恿、包庇的态度。在山东的日本驻军更明目张胆地为虎作伥。如1917年3月,日商偷运制钱七、八十车到济南,不服军警检查,并纠集日本陆军胆敢行凶,轰毙我岗警,扣押我军人。(19)在日本领事和山东驻军的庇护下,日商更有恃无恐,肆意妄为。国际条约不准贩运的明文规定和中国政府的防禁措施,在恃强凌弱的侵略者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由于日商的大肆掠购,山东以至于河北、河南、山西境内流通的制钱大量被运往日本。据日人统计,仅1915至1917年的三年间,日商运到青岛的制钱及熔铸铜块合计达101,094.5吨。(20)而1917年后,直到1922年底交还山东前,日商的这种违法活动从未停止,究竟又从山东掠走了多少制钱,则难以计数了。通过这种非法的贸易,无论是在山东从事制钱收购、还是从事制钱熔化、制钱输出业的日商,均攫取了丰厚的利润。
日商私贩制钱,给中国造成了严重危害。制钱是当时中国货币流通的主要承担物,在山东,“铜元本不敷用,向赖制钱以为辅币”(21),日商的大肆掠购,致使山东以至邻近各省的制钱日少,严重影响了市面流通。制钱行情的上涨,又间接引起了银元价格的昂贵,导致了金融恐慌。(22)某些日本浪人为获取制钱,结伙抢劫,甚至焚烧房屋,残害居民,伤毙巡警,不仅破坏了国际公法,侵犯了中国主权,而且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公开贩卖与走私鸦片
日俄战后,大连是日本向中国大陆走私鸦片、吗啡等毒品的最早基地。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后,青岛又成了与大连并驾齐驱的鸦片走私基地。
日本在山东的毒品贸易,最早是由日本的奸商、浪人依恃已攫取的殖民特权,在日本占领军的庇护下秘密进行的。最初,他们是以邮包的形式,免于青岛海关的检查,通过日军占领当局在胶济沿线各地设立的邮便局,发送到各地的“药房”或店铺销售。因为日本在华所设邮便局的邮包一概不许中国海关查验,故而日军邮便局成为输入毒品的主要机关,小包邮寄成为日本奸商最初的贩运方式。(23)
从1916年起,日本商人更与日军占领当局相勾结,并在其庇护下,手执青岛日本军政署(1917年后改称民政部)的输入许可证,明目张胆地用轮船运入青岛港。该年1月,大阪商船平安丸持青岛军政署的输入许可证输运鸦片途中,被上海税关扣押。由此可见,青岛日本军政署从这时起已直接参与了输入鸦片的活动。(24)由于青岛税关为日人把持,且根据1915年8月6日中日双方签订的《会订青岛重开海关办法》的规定,日人继承了德国在青岛海关的一切特权,凡军用物品均可免税入港,不受海关检查。据此,日本的不法商人在青岛日本军政署的庇护下,更多地将鸦片装入木箱,贴上“军用物品”的封签,用轮船“合法”地运入青岛。以致在胶济铁路沿线各地的日人药房中,贴有“军用物品”字样的木箱随处可见。(25)日人私运到青岛的鸦片和吗啡,最初来源于台湾总督府制造的烟膏。台湾总督府向青岛输出自制烟膏的收入额:1915年为5万日元,1916年为22万日元,1917年为21万日元,1918年为21万日元。(26)后来也从印度直接输入生鸦片。他们将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市场上收购的鸦片,先运到日本的神户港,然后再转运青岛。仅1918年1月初至9月底,通过这一途径运入青岛的鸦片至少不下2,000箱。(27)1918年日本陆军出兵西伯利亚后,更强行收购西伯利亚沿海州出产的鸦片,用军用船只运入青岛。(28)
青岛日本军政署作为日本鸦片商的后台和鸦片贸易的直接参与者,不仅负责保护鸦片的安全进港,而且负责庇护鸦片的公开推销。“当中国警察在胶济铁路沿线对贩卖吗啡的日本商店突击检查时,日本宪兵竟把被捕的日本人救走,并且强行对执行公务的中国警察处以罚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庇护的有效程度可以用从来没有一个日本人曾经因为贩卖吗啡及其它违禁品在中国受到惩罚的事实来衡量”。(29)
在青岛日本军政署的纵容、庇护下,居留在山东的日本奸商、浪人无不从事毒品的贩卖和销售。他们在青岛、济南和胶济沿线各站,以开设药房、商店或洋行、旅社、妓院为名,售卖毒品。日人在山东各地所设的药房“无一处不贩卖吗啡”,“凡日本娼妓所到之处,即吗啡所到之处”(30)。据日人统计,到1919年2月,日人在济南所经营的196家“新事业”中,有63家为销售吗啡的“药店”。(31)日本关东厅事务次官藤原铁太郎在1923年的《鸦片制度调查报告》中也透露,“在济南有2,000余日本人,他们大多参与违禁品的活动”。(32)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鸦片毒品贩卖网。有些日本商人甚至深入山东内地,四处兜售。1915年4月18日和5月22日,兖州镇守使署就曾连续查获了两起日人无照赴济宁卖“药”案。(33)
据“胶海关历年贸易报告”资料统计,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青岛港输入鸦片和其它毒品的数量十分惊人。1913年德占时期,鸦片输入已高达1,600余斤,而在日本统治时期,每年都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其中,1916年输入熟膏6,313斤、波斯土2,660斤,台湾土2,740斤,合计达11,713斤;1917年输入熟膏4,500斤;1918年为5,500斤;1919年为750斤;1921年为3,720斤。(34)仅五年的统计,共达26,183斤。事实上,日本走私运入青岛的鸦片远远超过海关报告之数。据当时的报纸揭露,1917年输入青岛的鸦片,“其确数则当50倍之”海关报告之数。(35)仅1921年,被海关查获没收充公的鸦片即达500多斤,被海关烧毁的吗啡为1,975英两,还有519英两的可卡因和吗啡赠送给了山东省内各医院使用。(36)至于那些装入木箱贴上“军用物品”标签的鸦片,其数目更无法计算了。据最低估计,用“军用”名义运入青岛的鸦片,不会少于海关进口统计数的3倍。(37)从青岛进口的大量鸦片,不仅行销于山东各地,而且辗转远销于江苏、安徽一带。
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大连等地的鸦片走私活动,曾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为蒙骗世人耳目,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日军占领当局的鸦片收入,青岛日本民政部实行了鸦片专卖制度。1921年1月29日,以日军警备司令部的名义颁布的章程规定:“非得官方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口、制造或贩卖鸦片”(第4条);除持有医师证明,需要长期吸烟,并领有官方吸烟执照者外,任何人不得吸鸦片烟”(第6条);“任何人请求吸鸦片烟前,须向宪兵队提出申请,详列姓名、年龄、地址、职业等内容,并获得批准”(第7条);“领有营业执照的鸦片贩卖商人,须将每笔销售数量登记入帐,并供稽查人员审查,鸦片烟不得售与无吸烟执照的人”(第14条)。(38)依据上述规定,日军占领当局完全控制了鸦片的贩运和销售,确保了它从鸦片毒品的公卖中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据史料记载,日军占领当局将鸦片专卖业务委托给了中国的买办奸商、号称“烟土大王”的刘子山经营。刘交纳了20万元的保证金后,挂出了“大日本鸦片局”的招牌。该局为总局,下辖七个分局,批发、零售鸦片。日方与他约定盈利七三折账,日七刘三。(39)仅一年时间,刘子山便获利”一百万两”,(40)而日军占领当局获利之巨,也就不言而喻了。
日人在青岛的大规模鸦片走私活动,造成了山东、江苏、安徽三省鸦片毒品泛滥成灾,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据1921年底调查,仅青岛一地按章领有执照的烟民即达3,114人。(41)受害者之多,由此可见一斑。不知有多少人为此而倾家荡产或吸毒自毙。而日本的鸦片商人和殖民当局却从中攫取了巨额的利润。据记载,仅1918年1月至9月,日本便从购自印度、经神户运到青岛的2,000余箱鸦片中征税200万英镑。(42)据当时日人调查,青岛日本军政署的鸦片收益每年均超过300万日元。(43)通过这种可耻的毒品贸易获得的庞大利润,“就成为日本发展青岛和在那里建立日本商业霸权所用的资金来源”。(44)
还应当指出的是,1912年10月23日在海牙缔结的《国际禁烟公约》曾明文规定:缔约各国应会同中国政府制定切实办法,以阻止从各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内,将鸦片、吗啡等毒品私运进口。(45)而日本作为该约的签字国之一,此项活动,显系不顾信义、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的犯罪行为。
三、私售枪支
日本帝国主义还利用其控制下的青岛海关,以“军用品”的名义将大量枪支运入青岛,出售给山东内地的土匪,从事非法的“军火生意”。
从当时被山东地方当局查获的日人私贩军火案看,日本军火走私商通常采用勾结不肖华人代为出售或直接潜入内地出售两种方式进行军火交易。如1914年9月13日日人福田在烟台曾将手枪7支、子弹700发交给华人许廷发代为出售。(46)1915年5月7日,日人工原觉、山里完、石田信等三人以“游历”为名,携带军火,潜入莱芜县境内,被当地政府查获。(47)
驻扎在青岛和胶济沿线的日本守备军更是军火交易的最大供应商。他们为笼络、控制胶东的巨匪孙百万等人,不仅将大量的军械出售给土匪,而且还派遣了大批特务、军人到土匪中充当“顾问”。辛亥以后,山东匪患严重,萘毒百姓,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得到了日本驻军的策动和援助。(48)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外人私售军火的。即使按照日本法律和中日条约,日商向中国走私军火也属禁止之列。例如,1871年的《中日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25款明文规定:凡系违禁货物,如火药、大小子弹、大小鸟枪并一切军器,概应禁止两国商人均不准贩运进出口,违者将货入官,按律惩办。(49)1902年中国与各国签订的《通商进口税则善后章程》第三款也明文规定:“洋枪、枪子、硝磺并一切军械等物,只可由华官自行贩运进口,或由华商奉有特准明文,亦准放行进口,如无明文,不准起岸,倘被查拿,即行充公。”(50)
应当指出的是,即使按照上述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也有权将查获的枪弹扣留没收,将犯禁的日人送交日本领事按照日本法律惩办。但事实上,日本在华领事往往借助领事裁判权,百般袒护日本罪犯,甚至胁迫中国官署发还被没收的枪弹。如日人福田私售手枪子弹案发后,烟台镇守使署依法将枪弹没收,并将福田送交烟台日本领事惩办。日本领事却以“枪弹为日人所有,贵署不得没收外人之物,且为该领审判福田所必用”为词,蛮横要求将枪弹移送日本领事馆。中方表示:依照1902年的《通商进口税则善后章程》第三款,枪弹当归中国没收,若审判福田需枪作证,自可将枪支移送,但用后仍须交还。而日领竟蛮不讲理,声称该约与福田之事无关。(51)藐视中国主权,无视中外约章,毫无信义和公理可言。
四、运销私盐
按照中国盐法,各盐区所产之盐,只能由特许盐商凭引票(特许证)运销,销量多少(引数)、行销范围(销岸)等均有定章,不得侵越。否则即为贩私,为法律所不容。在德国统治青鸟时期,山东巡抚孙宝琦同青岛德督曾议订了《胶澳盐滩合同》九条。其中第二条规定:德政府为副中国禁止夹带私盐入华境之美意,允“由山东政府特派熟悉盐政专员来青,或附属在胶海关办事,稽查租界内产盐、运盐、卖盐及其他关于盐务一切事宜。”第五条规定:本场产盐,限销胶澳地区,“设官店售卖,该官店须领有德辅政司盖印执照,照内载明购盐之数,准其持照买盐。此项执照,应以租界内需用盐斤之实数为度,山东政府所派专员得有随时稽查之权。”第六条规定:无论华洋商民,所产之盐“只准其卖与官盐店,此外不准私卖,如违究罚。”(52)上述合同,“除第二条,山东应派盐政专员尚未派往外,其他各条德人均已遵行,向无异议”(53)。但自日本占领青岛和胶济铁路后,却无视中国盐法和中德原有定章,不仅竭力开辟胶澳盐滩,设立制盐工厂,并免纳中国盐税,将大量青盐掠运出口至日本、朝鲜、香港等地,而且纵恿、包庇日本奸商在胶济沿线非法贩卖私盐。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破坏了中国盐务,影响了中国的盐税收入,违背了国际公法。
日本商人将胶澳盐斤贩运到山东内地,是利用日军占领下的胶济铁路用火车装运的。他们将从胶澳日中盐商经营的盐场中非法购到的盐斤,装入木箱、麻袋或草包,有时在封面封以咸鱼,稍作伪装,充作货物,搭乘西行的列车,输送到胶济沿线各车站。卸货后先存入货房,然后串通不肖华商,四处兜售。仅1915年4月至7月间,在胶济沿线各车站被中国缉私人员查获的日人运销私盐案即达十余起。详见上页表。
查获日人在胶济沿线运销私盐案一览表 (1915年4月至7月)
¥
资料来源:根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版编:《中日关系史料、邮电航渔盐林交涉》,第376-378页有关资料编制而成。
上表所列仅为三个月间被中国官言查获、并向驻京日使提出交涉的数例案件。由于日本奸商受到沿途日本驻军的庇护,中国缉私人员无法进入车站检查等原因,致使某些案犯的姓名及运销私盐的数量无法详知。但上表业已说明,日人在胶济沿线走私盐斤的活动是十分猖獗的。
驻守在胶济沿线各站的日军,不仅纵恿日商用火车装运私盐,而且无理干涉、阻挠中国缉私人员执行公务,对被查获的日本案犯百般袒护,或推诿辩解,或阻挠检查、没收,或掩护转移。例如,1915年4月13日,日人木村八造由青岛运盐一车,欲在昌乐车站卸货。昌乐县知事查知后,前往车站与日队长福住弘交涉。日队长自知违禁,只得推诿辩解说,该商“因初次来华,不知中国盐务章程,既经查禁,必速令载回原处”。不料,该商却转车至城东二十里朱留店站卸货,又被警佐陈其昌查获。正交涉间,昌乐站特务曹长伊滕春吉又出面袒护,谓“该商此次初犯,求限三日,仍令其装回原处,并由站看守,不准私卖”。但后来查明,这批私盐并未运回青岛,而是运到坊子车站被转手出售。(54)
更有甚者,日本驻军和走私商人竟敢恃强行凶,侮辱、殴打中国缉私人员。例如,1915年7月2日,当侦知日商佐滕初太郎将私盐运抵潍县车站后,昌潍缉私汪委员立即率巡警赴站稽查。经与日军少佐相良宪太交涉,同意由中方将私盐没收,随即备车装运。然离站不久,佐滕却率日军三十余人蜂拥而至,口称捉贼,将盐夺回,并用竹棒殴辱汪委员。(55)后经多次交涉,日方始允将案犯递解回国。
日本奸商和驻军的蛮横不法举动,激起了山东人民和地方当局的极大愤慨。山东盐运使和外交部驻山东特派员同驻济南日本领事屡次交涉,要求严惩贩私日商,将查获的私盐由中国官吏按照缉私条例实行没收,由中国委派缉私委员在胶济沿线各站和列车上随时查缉。但日领不是以“路权握诸军人”、“车站自由运货,不能任人干涉,私贩违背中国法律,论交谊可代为取缔,归日本司令部没收,全数运回青岛”为词,予以拒绝;便是以须“请示本国政府”为由,拖延搪塞。(56)这清楚地表明了日本领事的袒护态度。
北京政府财政部盐务署和外交部也多次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日使电达日政府,严禁胶济铁路运送私盐,并训令驻鲁日军切实禁运。(57)由于盐在中国实行专卖制,为各国所公认;盐税仅次于关税,为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根据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同五国(英、德、法、俄、日)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盐税收入成为对列强各国的担保款。而日商在胶济沿线的走私活动,不仅破坏了中国的盐法,影响了中国的盐税收入,而且“债约所关”,也必然会引起其它列强的不满,导致国际性的交涉。对此,自知理屈的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经过中日间的多次交涉,1919年3月25日,北京政府财政部盐务署特派委员周大钧、山东盐运使代表邱洵与日本驻济南代理领事官补山田友一郎、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事务官千秋宽,在济南签订了《山东铁道运盐及取缔之协定》。协定规定:胶济铁路输送食盐时,必须以山东盐务官署所发护照为凭,否则概行拒绝(第一条);胶济铁路各站发觉私盐即予没收,并引渡给中国官宪(第三条);居留在铁路沿线的日人所需之盐,以每人每年30斤为限,由济南日本领事发给护照,送交山东盐务官署加盖印章后,由胶济路自由输送(第8条);为山东盐务署官员往来之便,由胶济铁路给予长期免费一、二等乘车执照各一张(第七条)。(58)综观这一协定,日本虽确认了中国的盐专专卖制和缉私权,但却攫取了对沿线居留日人所需之盐自由输送的特权,破坏了中国历来不容外人插手国内食盐运销的禁令。而且,由于胶济沿线的居留日人并无定数;山东盐务官员虽可利用免费乘车执照在列车上“往来”,但对其缉私权限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加之,胶济铁路仅干线即长达394.6公里,沿线车站达55座之多,仅靠一、二名缉私人员往来稽查,实在是势孤力单。这一切,就为日人继续利用胶济铁路运销私盐提供了可乘之机。事实上,直到1922年底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铁路之前,日人在山东的盐业走私活动从未中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种种商业活动,既非正常的“贸易”方式,也远远超出了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在华商业特权。它不仅破坏了中国历来的禁令,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重灾难,而且违背了历次中外通商条约和章程,粗暴残踏了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原则,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侵略行为。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⑨(11) (15) (16) (17) (19) (20) (21) (22)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1230、1212、1215、1214、1222、1227-1228、1218、1223、1213、1231-1236、1231、1217、1227、1214、1216页。
③ (33) (46) (47) (51)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896-898、896、752、896、752页。
④ (14) (18)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第1093、1041、874页。
⑩ (49) (50) (58)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4、324;第2册第100、1486-1487页。
(12)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一),第284-285、282-283页。
(23) (25) (42) (44) 《日人之吗啡鸦片两贸易》,《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第202、203、202、202页;(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卷,中译本,第781、784、783、783页。
(24) (26) (28) (43) 山田豪一:《1910年前后日本对华走私鸦片吗啡的秘密组织的形成》,《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第265、265、268、265页。
(27) 〔美〕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下册,中译本,第572页;《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卷,第783页。
(29) 《清末民初政清内幕》,下卷,第781-782页。
(30) (35) 《日人之吗啡鸦片两贸易》,《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第201、203页。
(31)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上,第121页。
(32) (39)江口圭一:《日中鸦片战争》,《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第87页。
(34) (41) 《帝国主义与胶海关》,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67、278、296、312页;第312页。
(36) (38) 《胶海关1912~1921年报告》,《帝国主义与胶海关》,第161、160-161页。
(37) 《胶济铁路史》,山东人民1961年版,第47-48页。
(40)胡汶本等:《帝国主义与青岛港》,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45)内容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史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第368-371页。
(48)山东省出版总社青岛分社编:《青岛史话》,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52) (53) (54) (55) (56) (57)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邮电航渔盐林交涉》,第358、356、377、377、378-379、379-3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