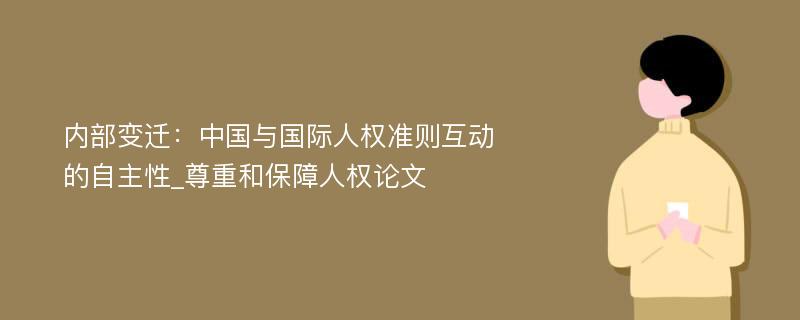
内发的变革: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互动的自主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人权论文,中国论文,性问题论文,自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界有关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讨论中,“国家社会化”成为主导性的研究议程。“参与”、“融入”、“内化”等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关键词。①但是,近来也有学者开始质疑相关研究忽略行为自主性(agency)问题,指出“社会化”其实是双向互动的过程。遗憾的是,与这种理论反思相对应的经验分析还有待展开。②作为相关讨论的延续,本文通过梳理改革转型中的中国与变化发展中的国际人权规范之间的互动,旨在论证中国政府构建自我身份与参与规范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补充并修正已有研究。③
本文分三节展开:首先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观念的变化和发展,揭示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历史延续性,特别是中国政府转变观念与推进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接着分析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国际人权规范建设的参与,突出中国政府在其间树立自我积极身份,改造国际人权规范的努力;最后围绕中国崛起与人权规范的未来做简要探讨。
一、人权理念的转变与人权事业的发展:被动接受还是主动转变?
国内外学者已从多个角度对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行了研究。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态度及作为评价较低。在他们看来,来自西方世界的影响是促使中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部分“接受”国际人权规范的原因。④中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作为主要是抵挡西方压力、装饰政权合法性的权宜之计。⑤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的基本特征是将外部影响(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作为动力,而将中国自身的因素作为其间的干预变量。这种近似于“刺激—反应”模式的思维框架在中国国内也有较大的影响。面对这些批评,国内的理论工作者从未停止回应的努力,但相关研究的学理性和针对性都还存在不足。⑥
本文认为,以“外部影响”与“社会化”逻辑为中心的论述存在着较大局限,它既不能解释改革初期中国在人权领域已出现的变化,也不能解释国际压力在九十年代中期逐渐消减之后,中国在人权领域所取得的持续进步。此前,已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以及国际人权规范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其约束力与影响力有限),强调规范的接受还是一个过程,存在程度的问题。⑦不过,这里一个更根本的疑问是,规范的“接受”和理念的“转变”可能并非来源于外部影响,而是由主动的思考和选择所驱动。主流解释回避了这样一个简单而基本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在意西方的批评?如果继续处在“文革”那样的历史阶段,中国完全可能对西方的指责置若罔闻。只是中国自身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取向伴随改革进程发生了历史性转变,西方国家作为“他者”的意义才得以重新界定。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树立一种“中国中心观”,将相关问题放在中国自身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下重新加以审视。⑨
本节以下的论述将力图说明,建立在自我经验反思基础上的改革开放决策改变了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实现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基本关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风波的主动反思是中国人权观念话语出现的关键背景,奠定了中国人权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方向;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进程的持续推进,则是中国人权事业拓展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动力来源。改革进程推动了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观念更新与制度调整,也构成了中国“接受”国际人权规范的内在限度。总而言之,本文认为,与“社会化议程”的设定恰恰相反,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其自身,而外部干预更多发挥的是“干扰变量”的作用。
(一)改革进程与中国人权观念的变迁
本小节首先讨论中国人权观念的转变,主要以人权话语的发展为中心展开。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政治定位,经历了从“讳言人权”到在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予以确认,再到写入党章、宪法和国家发展行动计划的过程。这种转变是主动反思与求索的结果。党和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反思和调整,对中国社会人权观念的进步与人权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1)
1.对于“文革”的反思与改革初期关于人权的讨论
悠远的文化传统与近现代的历史遭遇,对中国的人权理念发展影响深刻。不过,对人权理念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更重要且更直接的影响,还来自于新中国的历史经验。“前三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革故鼎新,在人权保障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过严重失误。(12)特别是一段时间内,“人权”成为理论的禁区,甚至“谈人权色变”,也给西方势力攻击中国提供了口实。(13)中国政府对于人权问题的理解就建立在对这段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基础上。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开创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局面。1982年12月通过的现行宪法,提高了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并对之做了较为全面、具体的规定,构成了此后人权事业发展的基本框架。在反思“文革”、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人民”逐步取代了“阶级”,主流政治话语发生重大转变。一个时期内,思想解放得到鼓励和提倡,社会各界对“民主”、“法制”与“人道主义”表现出了很高的热情。(14)国门再开,西方的各种思潮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受限于各种因素,这一时期对于“人权”的讨论还颇多忌讳,(15)但是,在相对开放的总体气氛下,与“人权”实质相关的许多概念在政治和日常话语中的积极意味却日益增进,为观念及话语的调整准备了社会基础。(16)
这一时期,以“胡娜事件”为标志,中国外交中(特别是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也已开始显现。(17)1985年6月6日,邓小平针对国外的批评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18)考虑到当时依旧讳言人权的状况,这一表态从与西方人权观相区别的角度提出了可以讲人权以及讲什么人权的问题,恰恰为话语转变提供了权威依据。(19)
2.从忌谈人权到发表政府白皮书
八十年代末期,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在中国国内一部分人中影响较大。中国领导人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一部分,是“争夺下一代”的斗争,必须予以反击。(20)政治风波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政治教育和对外宣传的角度提出了人权话语建设的问题。“人权”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地位发生决定性转变。(21)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就指出要弥补思想政治教育失误的问题。(22)当年7月,江泽民更明确将人权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作为发生动乱的根源之一,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人权,教育青年。(23)从反思动乱教训、加强政治教育的考虑出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人权问题”。中共中央在1990年底的一份文件中提出,“要理直气壮地宣传我国关于人权、民主、自由的观点和维护人权、实行民主的真实情况,把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帜掌握在我们手中。”(24)在此背景下,中国党和政府决定不再回避,而是组织力量对“人权”进行研究,构建并发展自己的人权话语。1991年3月2日,中宣部在中央领导指示下召开了专门的人权问题座谈会,部署人权领域的研究工作。(25)人权问题研究的禁区就此打破,甚至一度出现了“人权热”的情况。(26)借助高层表态的转变,理论界迅速修正了对人权问题的认识。(27)“人权”在此后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得到了政府及社会的大力扶持。“人权”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客观上也起到了传播人权理念的效果。
人权话语的构建也有对外宣传斗争的考虑。西方世界将“人权攻势”的矛头指向中国,使“人权”上升为影响中国国际声望的重大问题。(28)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并在1991年11月1日正式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人权从此成为中国对外关系表述的重要项目。(29)需要指出的是,白皮书作为首份肯定人权的政府文件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它肯定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第一次从“人权”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行叙事,构建了中国人权话语的基本框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30)
总之,在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通过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人权观,“人权”在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地位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在改革遭遇波折、社会思想一度陷入保守沉闷局面的情况下,来自中央的一系列表态,打破了人权“姓资姓社”的束缚,对于“人权”概念正面性的确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奠定了构建独立人权话语的基本格局,客观上也为进一步思考、讨论与传播“人权”开辟了空间。
3.改革的推进与人权话语的进一步发展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进一步打破了思想束缚,扭转了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局面,开启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进程。此后,改革再次进入快车道,人权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权保障机制也逐步建立。1997年十五大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人权由政府对外宣示的主题进入了党的核心文件。(31)2002年11月,十六大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尊重和保障人权”被确立为新阶段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并且强调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尊重和保障人权”。(32)这一时期,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及政府文件中明确纳入“人权”概念。国家领导人也在多种场合表达了中国遵守国际人权规范的意愿,并签署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33)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权话语的发展变化表现出三个特征:首先,强调人权议题上的国际对话与合作;其次,政府比以往更加经常地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重要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最后,建设中国自己的人权理论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重视和强调。(34)在理论话语中,“人权”本身不再是有争议的话语,讨论的中心变为“应该如何更好地推进人权”的问题。在制度和实践层面,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有关人权保障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有序展开,人权保障机制逐步建立,在刑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或修订过程中都力图体现人权的基本理念。人权开始日益“嵌入”到中国的政治话语和实践中。
人权话语和人权理念也开始进一步向社会扩展。1991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50周年,中国各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改革的持续推进,孕育了更多人权事业的支持力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改革的渐进拓展,社会政治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35)在媒体等的推动下,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普通民众人权意识的发展与社会力量的兴起,成为巩固人权事业成果、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4.改革的深化与人权理念的成熟:写入宪法和国家发展规划
随着国内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发展人权已成为保证国家政治稳定和改革深入推进的重要因素。回应形势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人权理念的发展又取得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成就。十六大以后,尊重和保障人权被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2004年3月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明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入宪”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36)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将之纳入和谐社会构建。(37)2006年,“十一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人权事业第一次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又首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执政党的章程。2009年4月,中国政府颁布了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中国由此成为第一个制定此类计划的大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发展,推动了人权话语的稳固和成熟,也推动了人权保护机制与实践的扩展完善。
(二)行为自主性的解释
对中国在人权话语上的变化,国内外学者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判断,但基本上都将之看做一个“社会化”的进程,外部的影响和压力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中国自身的因素仅仅是作为从属性的干扰变量或者说条件变量。(38)与之不同,本文认为,虽然外部环境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单纯强调外因的解释存在一系列问题,我们应当转换视角,更多地注意中国政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关注中国转型变革的内在动力。
首先,在八十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对于国际制度的参与程度一般。出于各种考虑,西方国家并没有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施加多大压力。考虑到中国政治的现实环境,来自“社会”自下而上的影响也极有限。但是,中国的人权理念和实践却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显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党和政府总结自身以往政策经验,正视中国国情,总结历史,自我批评,特别是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关键判断实现了自我身份与目标的再定位。这才为之后的各项转变奠定了前提与基础。“融入世界”的进程是由中国自身启动的,而非来自外力的推动。既有研究的一个关键疏失,就是对这一阶段的历史经验缺乏足够的讨论。(39)
其次,从1989年到1992年,在人权问题上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确实影响了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政策和观念。本文并不否认这一时期的某种“刺激—反应”特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府的一系列举动绝不是消极的应付,也不存在同外部影响的简单对应,而是根据自身情况针对环境变化所做的调整。如前文所指出的,一方面,人权话语的转变首先是根据政治教育和对外宣传的需要主动做出的(其中内部考虑更为重要),同时以建立中国自己的人权话语为中心展开;另一方面,对外部批评的回击被有意识地限制在人权领域内,没有影响到对外关系的全局。这只能从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自我身份和发展战略的调整中得到解释。还应指出的是,西方各种形式的施压反而加深了中国政府的敏感与疑虑,其实构成了对国内人权事业发展的干扰和限制。
再次,虽然西方世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这并没有维持多久。1994年克林顿政府放弃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之后,来自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权的压力大为消减。但恰恰是在此之后,中国政府对人权建设给予了更多的重视,社会各界也得到了更大的空间来讨论人权问题。这背后关键的变化同样来自中国内部。邓小平南巡讲话所开启的又一轮思想解放,打破了此前部分由外部压力所造成的国内保守的沉闷气氛。对于国家定位与发展战略的政治决断维持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动力。此后,追求经济增长、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目标促使政府有意识地调控内外部因素及力量,推进话语转变与制度调整。随着执政理念的转变,“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中国政府对人权问题的讨论逐步放开,社会力量得以出现和发展。决策层很清楚人权话语转变可能带来的冲击,并且始终在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手段加以节制与引导。
最后,伴随改革进程的深入,出现了新的问题和要求,也创造了新的资源和条件,构成了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力量。政府的推进与社会的参与,推动了人权理念的巩固、扩展与完善。
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从破除人权禁区到将人权确立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变化。这种政策和观念的调整的推动力,不仅来自现实需要,更基于中国领导人对经验的反思和对未来发展战略的规划。身份改变是关键的,但这种改变更多地来自自主反思,而非外部影响。正是由于改革与开放带来了自我身份和执政理念的转变,才促使中国政府重新界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寻求以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来回应外界的人权压力,并通过渐进性与功能性的制度变革来回应问题,推动国内人权事业的发展。党和政府有意识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成长方面。社会性因素日益成为巩固和发展人权的力量,只是目前还不足以引领其发展。总而言之,改革作为不断深入的过程,推动着中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外部因素更多是影响中国人权发展的条件变量和干预力量,而非如“社会化”论述所设定的是它的源头和动因。
二、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建设:被动顺应还是主动参与?
在人权理念调整的同时,中国也开始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在国际人权规范建设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此节讨论中国在国际人权规范建设中的作为。在此问题上,国内和国外的已有研究大多以“融入”和“参与”为关键词,认为“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中国逐渐融入国际人权机制的过程”。(40)与之不同,本文认为我们应当同样注意中国在其中塑造积极身份和改造国际规范的努力,关注中国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一)新中国参与国际人权规范建设的经验
中国是国际人权事业发展最早的参与者,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4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国际人权机制规范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一波三折”的复杂过程。在“前三十年”中,中国较少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发挥的影响也有限;(42)改革启动之后,中国逐步参与到国际人权机制中,但基本以了解与适应为主;(43)1989年到1991年间,由于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动,中国在国际人权问题上较为被动;此后,中国政府开始主动参与国际人权活动,一方面与西方继续展开对话及辩论,另一方面也在多边场合为发展国际人权规范、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而努力,重新树立了自己在人权领域的声望。(44)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的互动突出地表现为一个消解消极身份、构建积极形象的过程。
1.政治风波前后:认同威胁与身份对立
在国际人权问题上,中国政府始终的一个关切,就是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丑化”的疑虑。(45)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发生了政治风波。中国政府平息事件的做法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强烈反应。他们不仅进行了严厉的“制裁”,还利用国际舆论和国际组织“羞辱”中国。从1989年到1991年,中国在国际人权机制中从一个相对主动的参与者一时间变成了被动的应付者。虽然中国代表以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为依据做了艰苦的辩驳,但是1989年8月和1991年9月“联合国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还是通过了不利于中国的决议案。(46)
中国与西方世界在人权问题上的斗争,集中体现为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较量。“六四”风波后,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了全面制裁,其国内也反应强烈。(47)人权不同于一般的外交纠纷,人权规范也不同于一般的国际规范。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对美国压力的抗拒,被认为是对美国价值信仰的挑战。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的“人权外交”是“和平演变”的伎俩,背后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的颠覆企图。西方世界的制裁、孤立以及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攻击,也使中国普通民众怀疑他们的动机。(48)特别是美国国会议员以人权状况为由阻挠北京申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点燃了中国人的反美情绪。如有学者所言,“这一回杠杆的使用,比任何其他一个事件更使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相信,美国不仅反对中国政府,而且反对中国。”(49)来自西方世界的多重压力引起了强烈反应,在中国和西方世界间激发起某种形式的“身份对立”。(50)
虽然西方软硬兼施,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多边外交等各层面促使中国接受他们的人权标准,(51)但是,所有这些“社会化”策略在这一时期恰恰起到了反作用,造成了彼此间的“身份对立”,也阻碍了中国“融入”国际人权规范的进程。人权再度成为外交和内政中的敏感话题,中国政府在接受和参与国际人权规范机制上也趋向保守。(52)西方对中国的压力主要通过孤立中国实现。这恰恰阻碍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不利于中国国内支持和推动改革的力量。(53)西方的人权攻势一再使中国在国际场合蒙受“羞辱”。中国民间对制裁和攻击的怀疑和反感日渐上升。人权委员会上的中国问题议案被普遍看做“反华”提案,并没有得到多少同情与回应。西方的种种作为即便确实如其所标榜的是为了推动中国接受和遵守国际人权规范,其实际效果也恰恰适得其反。(54)
可见,西方世界的“社会化努力”并不是中国行为改变的原因。无论是胁迫还是诱导,强制还是说服,“社会交往”是一个主体间互动的开放过程。各种所谓的“社会化”手段如果在错误的环境下被错误地使用,还存在制造并激化身份对立的风险,其结果很可能是负面的。这恰恰是以往的“社会化”研究经常忽略和回避的。
2.中国对于国际人权外交的积极投入
在参与国际人权活动的过程中,中国进一步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权理念,学习国际社会已有的规范准则及外交技巧,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中国在人权领域改变不利形象、构建积极社会身份的需要。中国政府经过调整,开始重新构建身份,同西方展开竞争,努力促使国际人权领域发生有利于自身的变化。
(1)逐渐形成并提出系统的国际人权主张
面对西方的强大压力,不少人预测中国将从责难自己的国际人权机制中退出,结果却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55)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国际人权斗争中,中国政府既顶住压力,适时采取了一些灵活做法,维持了对外关系的大局,又开始了主动回击的努力。(56)在外交互动中,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如果只强调“不干涉内政”,利用主权原则抵御人权攻势,短期内或许有效,但从长远看,还有必要形成具体系统的主张,动员支持与同情力量,同西方展开论辩与竞争。(57)
国际人权规范体系本身是复杂的。不同的价值和规则内部存在复杂纠葛。以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为标志,中国政府正面承认了人权“国际性”的一面,逐渐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的国际人权论述,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人权领域的规范辩论中。(58)首先,在对人权规范的定位上,中国肯定人权具有“普遍性”和“国际性”,但同时强调应界定国际干预的正当范围,提出了人权内容的“全面性”与人权发展的“相对性”主张;其次,中国重视发展权,特别提出了“生存权”概念,针对西方对民主和政治权利的片面强调,倡导国际社会尊重人权内容的“完整性”;(59)最后,在程序性规范上,中国倡导人权领域的平等对话与合作,释放诚意。(60)这些主张都能从国际社会已有的规范及价值体系中找到支撑,重新框定了辩论的议题,有理有据,难于辩驳,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的人权攻势构成了反制。
(2)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积极参加联合国人权机制
国际社会的成员构成是复杂的,中国可以在其中寻找到支持力量。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过程也使中国认识到,自身的主张与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更为接近,更容易获得同情。中国也就把人权外交的基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以之为依托,努力赢得更多支持。(61)在多边人权外交中,中国政府重视与发展中国家接触和磋商。(62)这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间的协调,也较好地维护了自身的立场。(63)中国还积极推动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机构机制。(64)经过共同努力,人权领域的斗争态势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中国自己也从中受益。(65)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已经改变了在国际人权斗争中的被动局面,西方人士也承认,“到1996年,北京已经成功地使其对外经济、政治关系不再受到人权因素的干扰。”(66)
(3)深入参与规范讨论,发挥自身影响
世纪之交,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影响很大,中国与西方的人权论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完善了国际人权政策,调整了对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认识及对外表述,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建设,除继续以发展中国家为依托,还与西方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对话交流。(67)
首先,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加入国际人权机制,履行相关义务。至今,中国已加入包括《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内的25项国际人权公约,并积极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创造条件。中国政府认真履行了提交报告和接受条约机构审议的义务,积极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开展合作。在处理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关系时,中国政府表现出越来越开放和自信的姿态。中国相继提出了对人权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人权高专)的职责进行渐进改革的建议,特别是在设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68)
其次,中国进一步充实和调整了自身在国际人权规范问题上的立场。这一时期,“新干涉主义”成为国际人权规范辩论的焦点。(69)中国政府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上进一步澄清了自己的观点,并在联合国人道主义维和行动方面作出了灵活调整。(70)中国开始支持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国际人道主义干预,接受了“预防性外交”的概念,成为联合国维和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71)这些调整既有效规避了政治风险,也维护和促进了自身的国际形象。(72)
此外,中国政府倡导合作对话,与各大洲的许多国家建立起人权对话机制。(73)从1996年开始,中国陆续同与自身有着较大分歧的西方发达国家及组织进行了一系列人权对话,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法国、挪威、瑞典、日本和欧盟等。尤其是中欧间多种形式的人权对话颇为活跃,成效明显。(74)中国还积极倡导和参与非政府层面的人权合作,举办了一系列人权研讨交流活动。(75)一个以对话协商为主的程序性交往规范正在形成。另一个变化是,中国在阐明己方立场的同时也开始揭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权问题,批驳这些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搞双重标准的做法。(76)200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1999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此后,针对美国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国每年也以“国新办”名义撰文揭露美国人权纪录,针锋相对地做出回应。(77)
经过努力,中国在国际人权外交中的处境日益改善。在政策实施中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西方各国对美国强硬的人权攻势表现得越来越“冷淡”。1998年之后,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也渐渐去中心化。在人权领域,中国的政策立场得到联合国大会越来越多的支持票。(78)中国还在依旧不断地充实并完善国际人权政策。2008年12月,《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胡锦涛致信中国人权研究会,将推动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与建设和谐世界联系起来,表达了中国在新形势下参与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积极姿态。(79)
(二)构建积极身份的解释
前面的论述说明,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理念和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规范主张逐渐丰富,同时也更加协调。在实践中,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总体姿态从被动走向主动。人权外交上日趋积极,在国际人权领域的身份积极性也不断加强。
如何解释这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本文认为,目前主导学界类似问题讨论的“社会化”研究框架不能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在1989年前后,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权最为关注、压力最大的阶段,这些努力并没有产生积极效果,甚至可以说阻滞了中国对于国际人权机制的接受?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的人权压力,无论是制裁还是诱导,其强度都大为减轻,但是中国接受国际人权规范和参加规范建设的积极性却持续上升,而这一时期,中国“体系内”的基本身份没变,国内的制度和观念结构也无太大调整。如果中国的基本行为特征是“融入”,为什么中国只选择加入一部分国际人权机制?如果目的是规避外部制衡,为什么中国不是妥协顺应,而是同西方展开了颇为激烈的论辩交锋?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中国在参与国际人权机制上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特别是从社会心理学的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得到启发,强调国家对于建构自我身份积极性的追求。(80)本文认为,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改变了中国对于国家身份积极性的界定,开始寻求主流国际社会对自身积极身份的认可,在不同的触发条件下,通过各种机制,努力寻求国际体系中的积极社会声望。中国对于国际人权规范讨论和建设的参与,突出地表现为一个改变不利身份与建构积极身份的过程。
中国与西方在国际人权领域的互动,很大程度是身份与理念竞争的过程。为了获得积极身份的承认,中国反思历史经验,在把握现实变动的基础上调整和放弃“不合时宜”的观念及做法,或是将以往的某些规范主张(例如反对种族主义等)继续进行强化,或是根据形势的变化倡导新的规范主张。中国充分注意到现有国际秩序规范系统的复杂性,一方面有选择地接受某些规范,另一方面组织自己的理据,重新框定议题,与西方展开辩论。基于国际社会成员的复杂构成,中国以发展中国家作为依托对象,团结和动员发展中国家,逐步改变了在人权外交中的不利地位。身份积极性的追求还表现在中国人权规范主张的连续性和选择性上。中国的人权规范主张以“集体人权”为中心展开,侧重经济与发展权利的实现。这一点同中国国家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一致的,有利于展现自身的优越性。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内外部环境变化刺激了中国对于建立积极身份的需要,推动中国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进入到国际人权规范的建设和讨论中,进一步充实自己的规范立场;同时又通过各种机制,对话辩论,增信释疑,有所作为,进一步树立自身在人权领域的积极身份。中国对西方主导下的国际人权规范的接受与参与是有选择和有限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影响也将进一步显现。
三、中国崛起与国际人权规范的未来
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中国与国际人权机制的关系经历了从消极应对到积极活动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秩序本身也在经历深刻变化。(81)有关中国崛起与国际人权规范未来关系的疑问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大热点。(82)
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的互动,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这一历史性命题的缩影。相关争论与现存国际体系的问题特征密不可分。(83)不过,我们这里也有必要将目光转向中国自身。我们强调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互动的内在动力和自主性,就不应漠视其中所蕴含的限定性。正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道路固然给中国发展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也构成了中国可以被接纳加入其中的基本根据。不过这条发展道路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步暴露出来的某些特点,同样也构成了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融合的内在限度。”(84)这是个涉及多方面多层次的复杂问题,并将随着中国崛起的实践不断展开。(85)
本文所倡导的分析框架强调国际规范系统的多元性和复杂性,重视国家的行为自主性,尤其关注国家对于积极身份的追求在国际规范建设中的影响。从这些认识出发,本节针对中国崛起与国际人权规范的未来发展,陈述一些初步的想法。
单极的体系环境与特殊的地缘政治束缚,决定了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将是艰巨的。(86)值得注意的是,崛起中的中国还面对如何适应国际社会规范变动的问题。(87)近年来,西方世界对于国际社会规范的界定越来越表现出“从强调秩序到强调正义”的趋势。主权原则的地位弱化,而人权规范则成为衡量国家“正当行为”的新标准。(88)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依旧被西方世界视作潜在的“问题国家”。(89)随着人权、民主越来越被西方世界视作国际社会合法性的核心,中国必然要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90)权势的和平转移本身就很困难,如何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维持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和平共处,尽可能地化解价值观与规范立场上的冲突,更是十分微妙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有着“权力困境”,同样还面临着“身份焦虑”与“价值困境”。
现实中,中国与西方世界事关“人权”的麻烦也从未停歇。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这种摩擦也表现出“国际化”的趋向。中国在缅甸问题、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一度受到西方政府和舆论的攻击。有关“人权”的争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跨国社会互动的层面。北京奥运火炬在欧美国家传递受阻等一系列事件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反应,反过来又使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加重。(91)可以说,“人权”的纷扰折射的是中国发展崛起中所面临的深层问题。它已经不再仅仅局限在政府间的层面。
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是崛起的中国在价值和规范层面必须索解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就是要吸取教训,尽可能避免陷入各种“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努力化解由人权问题造成的身份对立,避免由此牵连并激化其他矛盾,造成总体性冲突,延误国内发展转型的进程。中国还远不是个成熟的大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应当认真听取各方善意的批评建议。我们有必要保持谦逊包容的姿态,改革国际秩序的努力更要十分审慎,注意“有理、有利、有节”。(92)当然,西方世界也应意识到,无节制的攻击指责只会制造对立,既不利于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也有碍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
其次,国际社会的构成是多样的,国际人权规范本身也是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下多元价值与文化的协调,需要各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共同努力。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人权规范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积极发挥自身影响,努力有所作为。中国的崛起已进入一个新阶段,建立更为积极的国家身份是一种自然的要求。(93)作为一个在单极压力下崛起的大国,我们更应当注重正当性的塑造。中国也就有必要明确价值立场,组合出一套符合自身道义和利益需要的规范叙述,构建自己的道义身份。(94)
由此进一步思考,本文认为,人权领域的外交摩擦在深层次上还反映出中国自身在当前这一特殊发展阶段所面临的身份难题和价值困惑。如布赞所提醒的,和平崛起需要中国有新的思维,既要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自身的认同和理想,也要更清晰地说明中国希望促进国际社会形成怎样的形态。(95)崛起背景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需要国际与国内统筹思考的问题。(96)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急剧的发展变革导致了多种价值与传统的激烈冲撞,社会核心价值观模糊。(97)尤其是近几年,中国的转型进入关键期,内外压力增大,改革的难度空前加大,决策的复杂性前所未有。无论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对成为世界大国尚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自身定位和规范立场正在经历艰难调整。(98)“伦理与价值”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外交的重大困惑。(99)这也给中国与国际秩序规范的关系带来了深刻的不确定性。
如有学者所言,中国“改造世界的前提是改造自己”。(100)在此意义上,中国崛起与国际人权规范发展的未来,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政府及社会对于国家理想图景和发展道路的选择。这将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并且取决于某些关键历史时刻的政治决断。(101)旧邦新命,值得我们每个人寤寐思之,上下求索。
本文由“第六届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博士生论坛参会论文”修改而成,基础则是本人提交给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第六章。作者感谢论坛上李滨教授、刘鸣研究员等老师的点评,感谢《外交评论》匿名审稿人及林永亮等同学在文章修改过程中所提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注释:
①以“国际化”或是“社会化”为中心,国内外学者的诸多研究都体现出这种倾向(国外学者的代表性研究当属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Social States: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1980-200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特别是中国学者对建构主义研究纲领下的“社会化”问题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讨,领军学者的倡导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秦亚青教授曾提出,应当将“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作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75—176页)。受此影响,大批年轻学者,特别是在读研究生参与其中,选择将社会化作为论文研究的核心框架,在诸如环境保护、核军控等具体议题上出现了大量经验实证研究成果,不过基本都还属于理论应用和检验型范畴。值得一提的是,外交学院的学术团队及其主办的刊物《外交评论》在其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②参见景晓强、景晓娟:《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外交评论》,2010年第1期;蒲晓宇:《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再思考: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25—27页。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质疑“社会化”路径的局限,并不是要拒斥它,而是试图将“社会化”逻辑同“行为自主性”考虑结合起来,从而深化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③这里之所以选择人权规范作为讨论对象,除了这一议题本身的重要性,也在于对它的梳理和讨论能够更好地暴露社会化思维的局限,刺激我们思考另一种研究路径的可能。
④代表性的观点可参见Robert Weatherley,The Discours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London:Macmillan,1999; Robert Weatherley,"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hinking on Human Rights in the Post-Mao Era",The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17,No.2,June 1,2001,pp.19—42。有学者认为,全球范围内对于中国人权记录的批评促使它重视人权保护和国际人权机制。Rosemary Foot,Rights beyond Borders: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还有学者关注联合国如何监督和影响中国对于国际人权规范的遵守。Ann Kent,China,the United Nations,and Human Rights:The Limits of Complianc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9.在这些研究中,中国被看作相关国际制度规范的接受者。Andrew J.Nath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The China Quarterly,No.139,September 1994,pp.622—643.国际形象的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政府人权政策改变的原因。John Cooper and Ta-ling Lee,Coping with a Bad Global Image:Human Righ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93-1994,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7.
⑤对中国领导人是否“内化”了国际人权规范的问题,多数西方学者的回答是否定的。Rosemary Foot,Rights beyond Borders: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Human Rights in China,p.261.
⑥在国内国际关系学者的现有研究中,最具学理价值的是王学东的《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冷战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该书强调中国崛起所面临的权力结构压力,以构建声誉的理性考虑来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积极性,不过,虽然一再试图辩解,作者在行文中的“纠结”也很明显,很难回答中国的态度是否属于“权宜之计”的疑问。
⑦参见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38—40页。
⑧对相关文献的评论,参考陈定定博士论文相关部分,见Dingding Chen,Transform from within:Chinese Agency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Ph.D.Dissertation,Department of Politics,University of Chicago,August 2007。笔者在研究思路上也受到了该文的启发,与之相区别的是,本文在此更强调这种自主性调整所带来的局限性,并且引入了社会身份理论的视角研究中国对国际人权事务的主动参与问题,对经验事例也做了更细致及时的扩展。
⑨这里有意思的参照是温特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讨论,参看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
⑩以话语为中心展开,是因为话语和理念未必直接对应,但却是理念最集中的外在表现。本文不讨论“内化”等问题,但在相应处会介绍具体实践的变化。此处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提醒。
(11)董云虎、常健主编:《中国人权建设60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页。
(12)对于建国初期人权的成就,可参见董云虎、常健主编:《中国人权建设60年》,第14—22页。只不过,这些努力和成就都不是以“人权”的名义进行的。
(13)董云虎:《“人权”入宪: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人民日报》,2004年3月15日,第10版。
(14)郭道晖:《新中国人权六十年》,“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 id=39836,2011年4月7日登录。
(15)人权研究的第一次热潮大致是从1979年春到1980年春,目的在于批判各种自由化言论。此时,理论界对“人权”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参见罗艳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人权问题”》,《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1期,第17页;另参见董云虎:《“人权”入宪: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16)Ann Kent,Between Freedom and Subsistence:China and Human Right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84; Dingding Chen,Transform from within:Chinese Agency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Norm,pp.68—74.
(17)此一时期西方世界对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介入,参见Rosemary Foot,Rights beyond Borders,pp.83—112。关于“胡娜风波”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4—147页;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第116—119页。
(18)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19)关于这一时期有关人权问题的相关讨论,还可参见陈佑武:《中国人权意识三十年发展回顾》,《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第4—6页。
(20)实际上,从1989年上半年起,高层领导人已经开始正面谈论人权问题。1989年4月,李鹏在答中外记者问时指出:“人权问题中国是重视的。……我们所不允许的,只是外国某些人士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李鹏同志答中外记者问》,《人民日报》,1989年4月4日。5月,李鹏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又提出:“我们不认为自由、民主、人权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社会主义国家也应是自由的、民主的,享有充分的人权。”《李鹏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5月17日。
(21)董云虎、常健主编:《中国人权建设60年》,第26页。
(22)邓小平:《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
(23)《1989年7月2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7月21日。
(24)董云虎:《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10周年回顾》,《人权》,2002年第1期,第25页。
(25)这些课题包括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西方人权学说、发展中国家人权、社会党和民主社会主义人权观、中国人权建设、国际人权约法等,基本建立起了此后中国人权理论研究的学科框架。其成果就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人权研究资料丛书”。
(26)这也被称为人权理论研究的第三次高潮。前两次高潮发生在八十年代,相关介绍参见罗艳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人权问题”》。
(27)林建云、周金榜:《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研究研讨会述要》,《人民日报》,1990年8月13日。
(28)参见赵启正:《我对中国人权的未来充满信心》,原载《人权》杂志,此处来自“中国人权网”,http://www.humanrights-china.org/china/rqzt/zt200200462894718.htm,2011年3月9日登录。
(29)例如,此后国务院总理每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有关对外政策的部分都会阐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参见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第166页。
(30)董云虎:《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10周年回顾》。
(31)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189.htm,2011年3月9日登录。
(32)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7/content_693542.htm,2011年3月9日登录。
(33)中国政府1997年签署并于2001年正式批准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在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34)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人权发展50年》,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853.htm,2011年3月8日登录。
(35)参见唐亮:《渐进·民主:变革中的中国政治》,新加坡:八方文体企业公司,2004年。
(35)罗艳华:《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历程与特征》,载王缉思等主编:《北大国际论丛201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37)董云虎、常健主编:《中国人权建设60年》,第28页。
(38)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参见Titus Chih-Chieh Chen,Capped Socialization:How Have International Norms Changed China,1860-200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2008,Chapter 4.另外,也有学者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认为对外开放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政治上有选择与限制地放开对人权的讨论,但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更深层次的自我身份定位的变化。参见Ronald Keith,"The New Relevanc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China's Changing Human Rights Theories",China Information,Vol.10,No.2,Autumn 1995,p.40。
(39)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标志,中国与西方的战略接近就已经开始,但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自我身份却并未转变。从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的历史转变是如何开始的,观念和身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或许才是中国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学者最应该着手研究的问题。
(40)参见罗艳华:《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历程与特征》,第52页。
(41)可参见Paul Gordon Lauren,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3,pp.160—198。
(42)参见田进等:《中国在联合国——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世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208页;萨穆尔·金:《中国和联合国》,载伊莉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华宏勋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43)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先后批准和加入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承诺接受有关国际人权机制的规范和约束。参见《中国人权大事记1949-1999》,中国人权网,http://www.humanrights.cn/cn/jbyfz/rqlc/fzlc/1949dsj/index.htm,2011年3月7日登录。
(44)罗艳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人权问题”》,第17页;沈雅梅:《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际人权政策及其演变》,外交学院硕士论文,2003年,第9页。
(45)董云虎、常健主编:《中国人权建设60年》,第285页。
(46)这两个提案分别是法国专家路易·于耐起草的“中国问题”决议草案,以及由荷兰专家特奥·范博文起草的“西藏局势”案。中国外交部提出了严正抗议。关于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参见Rosemary Foot,Bights beyond Borders,pp.113—130;谷存德、郑杭生主编:《人权:从世界到中国——当代中国人权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Ann Kent,China,the UN,and Human Rights,p.58;沈雅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际人权政策及其演变》,《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第64—65页。
(47)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下卷),第188—192页;李云龙:《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5页;Harry Harding,"Breaking the Impasse over Human Rights",in Ezra F.Vogel,ed.,Living with China: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W.W.Norton,1997,p.1091。
(48)牛军:《后冷战时期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与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4期,第6页。
(49)Robert L.Suettinger,Beyond Tiananmen: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1989-2000,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p.170—171.
(50)中国最高领导人一度对形势做出了十分严峻的判断。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4页。
(51)关于这些手段的总结,可参见董云虎、常健主编:《中国人权建设60年》,第295—305页。
(52)参见焦世新:《中国融入国际人权两公约的进程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第134页。
(53)Andrew J.Nath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pp.635—637.
(54)1996年之后,美国奉行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对中国签署两个最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起到了推动作用。参见焦世新:《利益的权衡——美国在中国加入国际机制中的作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44—188页。
(55)Ming W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Defining and Defending National Interest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1,p.119.
(56)参见罗艳华:《东方人看人权——东亚国家人权观透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57)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处理有关人权问题的专门机构的历届会议。1993年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曼谷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亚洲区域筹备委员会,并担任了亚洲区域筹备会和世界人权大会的副主席。在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时,中国派出的代表团在规模上与美国团不相上下,投入了充分的人力和智力资源。
(58)莫纪宏:《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59)参见沈雅梅:《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际人权政策及其演变》。
(60)高广温、王成福主编:《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治国决策述要》,第568—569页。转引自沈雅梅:《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际人权政策及其演变》,第16页。
(61)Ming W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p.125
(62)Ibid.,pp.116—117.
(63)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此处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讨论。事实上,一段时间内由于中国需要在人权问题上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因此减少了中国外交在其他问题上的回旋余地,突出地表现在领土问题上。参见M.Taylor Fravel,Strong Borders,Secure Nat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China's Territorial Dispu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Ming W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p.126;沈雅梅:《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际人权政策及其演变》,第37页;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第182—183页。
(64)范国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国别人权》,《人权》,2002年第2期,第55页。
(65)参见吴建民:《胜利在郁金香盛开的时候——记53届人权会上与反华势力的斗争》,《世界知识》,1997年第10期,第4—8页。
(66)Ming W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p.121.
(67)沈雅梅:《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国际人权政策及其演变》,第22页。
(68)Ann Kent,China,the United Nations,and Human Rights,p.74.参见罗艳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设立及其背后的斗争》,《人权》,2006年第3期,第56页。2006年5月9日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投票选举中,191个成员国都参加了秘密投票,结果中国以146票的高票当选。
(69)国内学者对“新干涉主义”的研究,可参见魏宗雷、邱桂荣、孙茹:《西方“人道主义干预”理论与实践》,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
(70)周琪:《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人权》,2010年第2期。国际上对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急剧增多,联合国维和行动越来越同有争议的人道主义国际干预缠绕在一起。Rein Mullerson,Human Rights Diplomacy,London:Routledge,1997,p.7.
(71)周琪:《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
(72)相关讨论可参见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第12页;陈琪、黄宇兴:《国际干涉的规范维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4期,第12—13页。
(73)Ming Wan,Human Rights i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p.124.
(74)相关活动的记录,可参见“中国人权大事记”相关部分。
(75)罗艳华:《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合作的历程与特征》,第58页。
(76)中国联合国协会编:《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发言汇编(1997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70—172页。
(77)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9年美国的人权状况》,《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2月28日,第5版。
(78)Richard Gowan and Franziska Brantner,"A Global Force for Human Rights? An Audit of European Power at the UN",Policy Paper for 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ccessible at http://ecfr.3cdn.net/3a4f39dal1b34463d16_tom6b928f.pdf,2010-09-12.
(79)《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致中国人权研究会的信》,中国人权网,http://www.humanrights.cn/cn/dt/xwtt/t20081221_396759.htm,2011年3月9日登录。
(80)对于该理论的基本主张及其与社会化理论的比较,参看景晓强、景晓娟:《身份建构过程中行为体的施动性——基于社会化理论与社会身份理论的比较研究》。此处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81)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1—14页;秦亚青:《国际秩序:理想信念与制度设计(年度点评)》,载王缉思主编:《世界和中国2007-2008》,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82)西方世界普遍质疑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发展”概念并没有回答“崛起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刘永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文版前言,第vi—vii页。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目前对于“和平崛起”的言说确实很大程度上是“内向性”的,并没有很好地考虑“他者”的观念和感受。
(83)张小明:《中国的崛起与国际规范的变迁》,《外交评论》,2011年第1期。
(84)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85)这一认识受到了牛军教授、张小明教授一系列论述的启发。
(86)参见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87)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1—242页。
(88)关于这一点,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学派”讨论较多,参见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第259—261页; Tim Dunne,"'The Rules of the Game are Changing':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 Crisis After 9/11",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44,No.2,March 2007,pp.269—286; Jack Donnelly,"Human Rights:A 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4,No.1,January 1998,pp.1—23。
(89)Yongjin Zhang,"System,Empire and State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7,No.5,2001,pp.43—63.
(90)Andrew Hurrell,On Global Order:Power,Values,and the 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第263—267页;王缉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第11—14页。西方世界一直倾向于用自己的标准来评判其他国家,这种倾向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得更为突出。参见许振洲:《全球化与单一思想的威胁》,《欧洲》,2000年第2期。
(91)David Scott,China Stands Up:The PRC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New York:Routledge,2007,pp.83—98.
(92)贾庆国:《对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思考》,载王缉思等主编:《北大国际论丛2010》,第10—11页。
(93)这也有助舒缓在发展中遇到的“权力困境”。参见王学东:《外交战略中的声誉因素研究》。
(94)陈琪、黄宇兴:《国际干涉的规范维度》,第12—13页。
(95)巴里·布赞:《中国能和平崛起吗》,《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2期,第32页。
(96)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崛起”主要是以中国自身作为思考的中心,却很少考虑新的身份形成后又如何相应地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这恰恰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参见牛军:《“中国崛起”: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思考》,《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6期,第45—46页。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讨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或者关注中国的软实力,但是相关讨论却很少从主体互动的角度来思考。
(97)俞新天:《中国对外战略的文化思考》、潘维:《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载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办、李稻葵主编:《中国与世界观察》(第5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9—40页。
(98)秦亚青:《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4页;章百家:《目标与选择——新中国对外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及启示》,《现代国际关系》创刊30年纪念专刊,2010年;Ann Kent,"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Global Governance,Vol.8,No.3,July September 2002,pp.343—364。
(99)牛军:《伦理与价值:当代中国外交的困惑:编者按》,《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如该专辑所指出的,有关中国外交伦理和价值的思考与讨论,是中国社会正在兴起的有关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思考与讨论的一个部分,一个必然的延伸。
(100)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另参见时殷弘、宋德星:《21世纪前期中国国际心态、外交哲学和根本战略思考》,《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101)这些决断必然事关中外关系的基本调整。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第28—29页。
标签:尊重和保障人权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人权理事会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