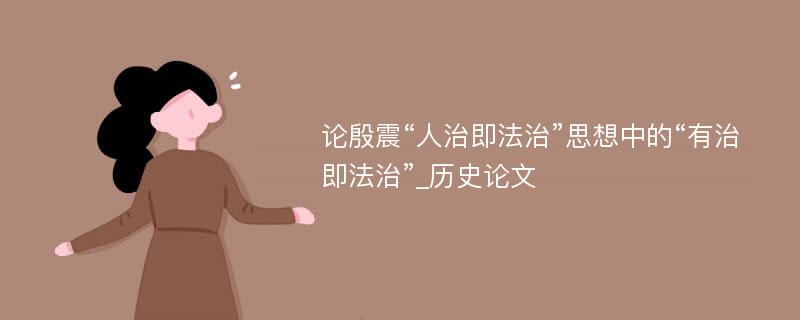
论胤禛“有治人,即有治法”的吏治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吏治论文,治法论文,思想论文,论胤禛论文,有治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胤禛(1678—1735),姓爱新觉罗,年号雍正,庙号世宗,是清入关定都北京后的第三代皇帝。尽管学术界对他的政治手段和为人诋毁多于赞誉,但从宏观、历史角度分析,胤禛仍是清代卓有政绩的并具有独特的政治法律思想的政治家。尤其他的“有治人,即有治法”的御吏思想,是其法律思想的闪光之点。
官吏是保证国家法律、法令得以贯彻实施的媒介,吏治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优劣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政权安危。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有丰富的吏治思想和理论。先秦儒家“人治”理论强调圣君贤相的榜样、楷模作用,而法家则强调以“术”驾驭群臣,“术者,因往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谋群臣之能也”〔1 〕。这些吏治思想成为胤禛御吏之道的思想底蕴并被其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他在重视并运用法律手段推行政策的同时,更注重依靠人(官吏)的力量。表现在法律思想上,就是重视“人治”,严格吏治,他常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政举,朕有治人,即有治法。”〔2〕在他看来, 即使是好的法律也需恰当的人来推行,否则,遇到不当的官吏反被他们利用成为贪营取巧的工具,其中的益处只能流于形式,而于民生无益。同时,法律的不完备会由良吏加以补充、完善,法律的久而生弊会由良吏加以纠正。故他坚信“有治人,即有治法”。由于康熙末年废弛政事,对贪官酷吏也一味姑息纵容,导致官吏贪污受贿成风,激变民众,从而严重危害着清政权。因此,胤禛在打击朋党、巩固皇权的同时,注重对官僚队伍的整饬,以保证官吏奉公守法,忠君守制,真正做到吏治清明,民生安定,天下一统。
一、清查亏空,耗羡归公,惩办贪官
胤禛从乃父玄烨手中接过来的清政权并不是完美无弊的。由于玄烨晚年身体状况不佳,废立太子又使他心力交瘁,导致玄烨放松对吏治的整饬;官吏任意私加火耗,征收上来的钱粮也不如数上交国库反而中饱私囊,因此,官吏贪浊,国库空虚。对于这种情况,胤禛自言“知之甚悉”。为了加强国力,必须清查赋税。清查赋税,就涉及到官吏问题。为此,胤禛从清查赋税入手,大力惩治贪官污吏。胤禛掌权的第一个月,就下达了全面清查钱粮的命令:“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其亏空之项,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别处分外,其实在侵欺入已者,确审具奏,即行正法。倘仍徇私容隐,或经朕访问得实,或被科道纠参,将督抚一并治罪。即如山东藩库亏空至数十万,虽以俸工补足为名,实不能不取之民间额外加派。……既亏国帑,复累民生,大负皇考爱养元元之至意,此朕所断断不能姑容者。”〔3〕确定了清查的方针、政策和有关问题, 并于元年正月设立“会考府”,由怡亲王允祥、舅舅隆科多、大学士白潢、尚书朱轼会同办理。胤禛要求允祥严格执行清查法令,并对他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不能清查,朕必亲自查出。”〔4 〕表示他绝不宽容拖欠,一定重惩贪官的决心。在清查过程中,为使贪官退出赃银,保证归还国库,主要采用抄没籍没的手段。对于涉及到的贵族和高级官僚,也不宽贷。对此,胤禛义正辞严地说:“若又听其以贪婪横取之赀财,肥身家以长子孙,则国法何在,而人心何以示儆。况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吏,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5〕事实上,贪官一经被人告发, 就革职离任,而不似以往留任以补空,因为留任会“贻累百姓”。对于清还完毕还可以当官的,由大吏奏请。
另外,为整饬贪官,胤禛还实行了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雍正二年七月,胤禛经过考证,接受了湖广总督杨宗仁、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决定实行耗羡归公,即将州县征收的钱粮尽数提交藩库,不留于地方,以防止地方州县官任意私加火耗。而养廉银制度又为各级官吏提供了基本的为政、养生保障,从而打击了地方贪官,限制了私征滥派,也相应地取缔了与火耗相关的陋规恶习,有利于澄清吏治。
二、“量才授官”、“不限成例”
胤禛在推行清查亏空、耗羡归公以整饬吏治的同时,提出了新的用人思想。他接受并运用先秦法家的“术”治思想,主张根据需要而设置官职,根据人的才能任命官吏,由君主根据履行职责情况,分别予以赏罚。对此,胤禛十分欣赏,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形成了“量才授官”、“不限成例”的用人思想,建设了适应雍正王朝统治的官吏队伍。
1.“因任授官”、“因事授权”
胤禛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调整、设置官职,并相应地赋予一定的职权,以发挥其作用。“观风整俗使”就是他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的一种官职。雍正三年十月,浙江发生了汪景祺案,四年出现了查嗣庭案,加上浙籍人士与江南人士垄断科闱、官员散布于满朝内外、幕僚充盈各衙门以及杭州发生反对摊丁入粮运动,胤禛对浙江的印象不佳。四年八月,浙江巡抚李卫奏折中说:该省“民刁俗悍,动辄钱粮挂误,命案参黜”,以致“大吏屡易其人,守令席不暇暖”〔6〕。 使胤禛认为“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绅衿“好尚议论”,浙江人是“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决定加以整顿。因此,于当年十月设专职官员——“观风整俗使”,派往浙江,“查问风俗,稽察奸伪,应劝导者劝导之,应惩治者惩治之,应交于地方官审结者即交地方官审结,参奏提问者即参奏提问,务使绅衿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凌之习”〔7〕。八年,以浙江风俗已渐改移,总督李卫又善于训导, 不再派“观风整俗使”。七年,胤禛以湖南“风俗不端,人情刁恶”,广东“盗案繁多,民俗犷悍”,分别向两省派遣“观风整俗使”,加以整训。〔8〕可见,“观风整俗使”这个官职是针对特殊情况设置的。 另外,胤禛还设置“宣谕化导使”,使陕西民人“笃尊君亲上之义,消亢戾怨怼之情”〔9〕。因此,吴振棫在《养吉斋》中评论说:“雍正间,或用人惟贤,或因事授权,往往不拘定制。”胤禛或因酬劳宠臣立制,或为特殊情况所需事竣即裁,反映了他“因任授官”、因事授权的用人思想,并为推行他的政令起了积极作用,有利于官吏队伍的建设,维护政权统一。
2.“量才授官”,“不限成例”
胤禛提出“量才授官”的用人原则。即根据每人的操守品德和才能决定授予何种职位。他对鄂尔泰提出的“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能济事,因材、因地、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10〕的理论十分欣赏,批道:“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在才能与品德两方面,胤禛更注重才能。他指示鄂尔泰:“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厚老成人,然亦不过中医之法耳,究非人力听天之道也。”体现了他对人才的驾驭、使用思想,他宁可用恃才傲物不易驾驭之人,也不用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因为“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11〕只要有才干,即使是身分低微、官职低也应当爱惜,教育他们改正缺点;对于不能办事,于事无补的,即使是“善人”也要他另谋去处,让出缺位给有才能的人。朝廷用人与不用的标准是能否办事。能办事就用,不能办事则不用,因为朝廷绝不是养闲人之处。所以,对于传统的官吏标准即清(廉洁奉公)、慎(忠诚谨慎)、勤(勤劳王事),胤禛认为这是对高级官吏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之外,大吏还必须胸怀全局、目光远大、办事能够瞻前顾后、驾驭属员,即好的官吏应当兼有才能和忠于职守的品德。湖广提督岳超龙在奏折中表示:“惟有益思正己率属,砥砺官方,以仰报高厚之恩。”胤禛则告诉他,唯有正己率属还不够,“若不知训练兵丁,涤除陋习,不过自了一身而已,与木偶何异,旷职之愆,仍不能免。”〔12〕他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湘抚王国栋,认为“王心有余而力不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许之,然不能扩充识见,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任。”于是将王国栋内调,并以此教育其后任赵弘恩。〔13〕吴桥知县常三乐,“操守廉洁”,但“懦弱不振,难膺民社之寄”,胤禛作出裁断:“照他居官罢软,殊属溺职,相应参革。”可见,胤禛的用人原则是十分严格的,表现出一个有为君主的求实从严的精神。
基于“量才授官”的思想,在任用选拔人才去庸人时,胤禛的思想及措施与清朝定制发生了矛盾。他为了整顿吏治,建设一支良好的官吏队伍以革除弊端,不惜破坏定制。他坚持“朕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14〕,“唯期要缺得人,何论升迁之迟速,则例之合否耶!”〔15〕对于有为有守贤能之员,不必按资历升转,也不论升迁快慢,可以越级提拔,以鼓励官员奋发向上。对于督抚、藩司之职,只要其人可以胜任,也“不悉拘资格,即或阶级悬殊,亦属无妨”〔16〕,甚至“不必拘定满汉,亦不限定资格,即府县等员,官阶尚远者,果有真知灼见,信其可任封疆大僚,亦准列于荐牍之中”〔17〕,颇有不拘一格降人才之意。
3.行赏罚以驭群臣
胤禛作为封建皇帝,不仅确立了用人原则,而且还拥有一套驾驭群臣的方法,这就是运用教育和强制手段赏贤罚庸,充分发挥各级官吏的才能。
(1)赏赐。这是胤禛最常用的褒奖宠信贤臣的方法, 有赏赐世职、加衔、加级、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辔等方式,以奖励“公忠奉职、勤慎持己”的官吏。胤禛还注意关怀一些官员的身体。雍正三年,两广总督孔毓珣折奏广东按察使宋玮“才守兼优”,可惜有病。恰在他的奏折未到之前,胤禛已命宋玮赴京引见,见到孔的奏折后,即命宋玮暂停来京,并让孔转告宋,等病可以走路了再来,“切勿任伊勉强扶病而行”,免得赶路把他拖垮,〔18〕表现出爱才惜才之意。不仅如此,胤禛还关心官吏的家属。陈时夏任浙江巡抚,意将在云南的八旬老母迎养任所,胤禛就令云南督抚把陈母送到江苏,并特地指示:“起程日期一听其母之便,在路随意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驿定限。”之所以如此,目的在于让陈时夏安心任事,为国效力。对此,胤禛本人直言不讳:“朕既擢陈时夏,欲其宣力以报朝廷,自不忍令伊垂白之母暌违数千里之外,两相悬切。”〔19〕可见,他关心赏赐臣下,一是为赏功,二作为驾驭手段,使臣工感激莫名,效忠图报。但不能否认胤禛用人方法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2)对于有不同见解的人,只要不同政治斗争相联系, 不但不迫害,反而予以使用和信任。左都御史、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朱轼,因曾反对耗羡归公和西北用兵而不安于位,以病乞休。胤禛挽留他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感激涕零,不再言去。〔20〕
(3)对于贪酷、庸碌无才、沽名洁己的官吏分别予以惩处, 以儆戒百官。如:对清理亏空中钱粮不能补完的,不论高级官吏还是地方官吏,一律依法处分,或抄家或罢官,或斩杀,决不宽贷。
应当看到,胤禛对臣下的赏罚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而是将官员的日常表现、主观心态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因此,他对同时发生的同一事件,同一性质的错误,却做出不同的处分。如雍正五年,黄河清时,诸臣表贺,云南督抚杨名时和鄂尔泰的贺表都不合格,通政司题参,胤禛把杨名时交吏部议处,对鄂尔泰免予查议。大臣们不服,胤禛解释说:“观人必以其素,不以一事之偶差而掩其众善,亦不以一端之偶善而盖其众愆。”而是根据每个人的平常表现、主观状态,分清故意和过失、操守优劣,综合考虑作出决断。“或为有心之过,或为无心之失,朕无不悉之体之。…鄂尔泰公忠体国,其办理之事,陈奏之言,悉本至诚,恺切之心,以为事君之道,此等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其本章错误之小节,朕不但不忍加以处分,并不忍发于部议。至于杨名时,巧诈沽誉,朋比欺蒙,从不实心办事,毫无忠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今若因恕鄂尔泰之事并宽杨名时之过,则赏罚不当,于朕公平待下之道转失之矣。”〔21〕主张赏罚必当,这与传统的用人原则不同,因此,时人批评他用人不得法,说他“进人太骤,退人太速”,不像康熙宽厚,官吏队伍比较稳定,任职较长。而胤禛自有一番理论,他说雍正朝用人变化迅速,是因为“事无一定,又不可拘执,有时似若好翻前案,不知其中实有苦心,总欲归于至是。”为了达到最佳的任官办事效果,“或一缺而屡易其人,或一人而忽用忽舍,前后顿异,盖朕随时转移,以求其当者,亦出乎不得已。”〔22〕对一个职位屡屡换人,颠来倒去,或此时用彼时舍,都是为了“归于至是”,出于“量才授官”、“因能授权”的考虑,实现合理任免,做到人尽其才,最终是为了有效地统治天下。这也是胤禛对其用人原则的说明。
4.对臣下以威相制
胤禛主张对臣下百官要以威相制,使其绝对服从君主,恪守君臣之道。康熙四十八年,胤禛随康熙巡视京畿,在归途中,康熙责备同行的鄂伦岱等结党,鄂伦岱以国戚自居,不知畏惧。胤禛说:“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杀戮。”〔23〕主张运用法律的力量打击乱臣贼子,树立君主的威严。即位后,为了维护皇权的神圣性,胤禛时时提醒大臣们要实心奉行“君为臣纲”,并通过惩罚违法者儆戒百官。雍正二年四月,胤禛因平定青海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尚未行礼即就坐,言官参劾他们失仪。而胤禛则认为,国有大典,君臣有定分,他们不守本分,就是藐视君上,犯了大不敬罪,按律应当立即斩首,只因即位之初不便轻易杀人,先行监候。随后祭坛、献俘等典礼,朝臣皆敬谨如仪,才将二人放回原籍。胤禛还认为,臣下百官仅以君主绝对忠诚。他常用任免、处分官员等司法、行政大权来表现君主的威势,对天下百姓则动辄发兵征伐镇压,使百官加敬加慎、尽职尽责,使百姓俯首听命。
在封建社会,君主以“一人治天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势,包括对百官的任用、罢免和赏罚。胤禛为了振纲饬纪,剔除积弊,提出新的用人,重用有才能的官员,摒弃庸懦之员,以致不顾定例,这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尤其他对有才干的人,不分大员、“小人”都加以“惜之,教之”,更是真正使用人才、保护人才的方法。他对有不同政见的人,仍予重用,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宽大胸怀。这些思想对于整饬吏治、建设良好的官吏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也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好南面之术,用君主的威势来驾驭群臣,因此,他不可能始终如一地奉行正确的用人原则。
注释:
〔1〕《韩非子·定法》。
〔2〕〔17〕《清实录》第7册,第352页;第8册,第53页。
〔3〕《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谕。
〔4〕〔5〕〔9〕《上谕内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谕、 四年七月十七日、九年四月初八日谕。
〔6〕《朱批谕旨·李卫奏折》,四年八月。
〔7〕《雍正朝起居注》,四年十月初六日条。
〔8〕《上谕内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谕。
〔10〕〔11〕《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
〔12〕《朱批谕旨·岳超龙奏折》。
〔13〕《朱批谕旨·赵弘恩奏折》。
〔14〕《朱批谕旨·石麟奏折》。
〔15〕〔16〕《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
〔18〕《朱批谕旨·孔毓珣奏折》。
〔19〕《朱批谕旨·杨名时奏折》。
〔20〕《清稗类钞》第3册第18页。
〔21〕《上谕内阁》,五年四月十九日谕。
〔22〕《雍正朝起居注》,三年四月十六日条。
〔23〕《雍正朝起居注》,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