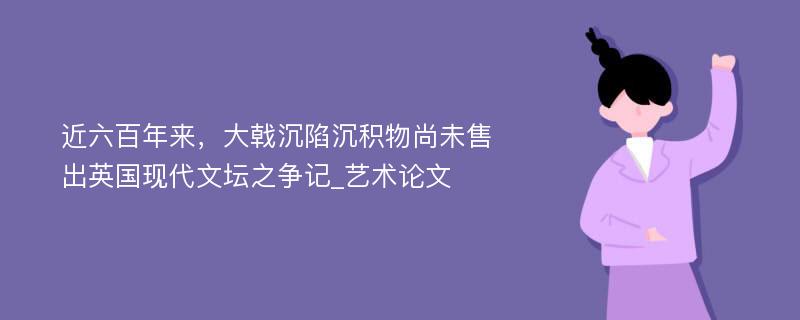
折戟沉沙铁未销——英国现代文坛争鸣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折戟沉沙论文,英国论文,文坛论文,铁未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年前,中国文坛就人文精神的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心与心碰撞,真理对灵魂的敲击,在慌乱的世纪之交频频迸发出智慧和思想的火花。后来又有聪明与世故,崇高与媚俗的正面交锋,四方有志之士或竞相上场过招,或不时喝彩和鸣,几度寂寞的中国文坛一下子剑戟铮铮,唇舌齐舞,好一派热闹景观。
有人说,百家争鸣乃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人向来喜欢唱和与驳难。穿越时间的隧道,细读世纪初各种新旧思想和观念的激烈交火以及二三十年代群“儒”舌战的文字;再跨越广袤的空间,找到那曾经用洋枪洋炮轰开“泱泱大国”之门的英伦岛国,那里的现代文坛也是批评和争鸣此起彼伏,潮涨潮落。那些操洋文的文人们对现代文学艺术的思考,对传统与革新的自由争辩,倒也说明了唱和与驳难似乎更是天下文人共有的禀性。
新与旧的更迭,始与终的交替,总能触发文学内部某种固有的契机。站在世纪的交叉点,我们洗耳恭听当下社会有识之士驳斥“小说死了”的危言,静眼观望文坛种种新潮与旧涛的起起落落,在资料的沉沙中捡起几片“未销”的断戟,抖去时光积淀的层层尘埃,“磨洗”空间淤塞的斑斑锈蚀,英国现代文坛几场硝烟弥漫的鏖战似历历在目。艺术的执著与宽容,观念的激进与保守,人性的亮丽与平和,构成了一道欲说还休的域外风景线。
威尔斯和詹姆斯之间的“大论战”
世纪回眸,亨利·詹姆斯和威尔斯是当时享誉英国乃至欧洲文坛的大文豪,他们围绕小说的本质和目的的辩论构成了20世纪英国现代文坛最著名的论战之一,有人把他们之间的争执和纠葛称作是一场“大论战”。
1898年,威尔斯和詹姆斯两个初次相识,同年便开始通信联系。他们之间的通信向来为文坛所津津乐道,现在更成了追溯“大论战”来龙去脉的重要佐证。其时,威尔斯32岁,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小说创作和评论已小有成就,前途无量;而詹姆斯时年55岁,名作《华盛顿广场》和《淑女肖像》已经出版,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大作家。詹姆斯极为赏识威尔斯的文学天赋,威尔斯每有新作问世,詹姆斯便写信鼓励和赞美,奖掖后进的姿态充溢字里行间。后来由于相距甚近,两人不时促膝晤谈,获益匪浅的威尔斯甚至认为,詹姆斯是他“思想、观点、谈锋和风趣的不竭源泉”。
由于文学,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也由于文学,友谊出现危机。文人相争自有它本身的规律,或出于真诚,或出于执著。点滴的分歧和矛盾,些许的裂痕与嫌隙往往会引发一场笔墨大战。
1911年,威尔斯的小说《新马基雅弗利》出版,两人的书信开始出现明显的变音。詹姆斯一改往日明断的评价,第一次对威尔斯的创作手法提出直接的批评:“我似乎感到(《新马基雅弗利》特别让我感到这一点),你的伟大天赋没有得到很好的证明,因为你如此虐待和胁迫像我一样的读者而让他们受罪。我的意思是指(像我一样)全力尝试种种新手法之人,这些手法与你的手法迥然不同;而对他来说,我们所实践的艺术之伟大趣味在于种种精心之策划与构思,而你却粗暴随意地将之践踏于脚下。”詹姆斯认为威尔斯“虐待”和“胁迫”读者,小说创作不讲手法,这种不留情面的指责往往让人心存芥蒂。但威尔斯没有正面反驳詹姆斯。他在1911年开始准备的论文《小说的范围》中这样表明自己的观点:
……我对小说范围的声明:小说即是社会的调节器,理解的载体,自检的工具,道义的展示所,礼仪的交换地,习俗的工厂,法律与成规、社会教条和观念的批评者,小说是得力的忏悔处,知识的启动器,自我质疑的种子。
威尔斯深受狄更斯等现实主义小说家的影响,十分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和工具效应,在这一点上与詹姆斯、沃尔夫等现代派作家产生严重分歧。在《医生的岛屿》一文中,威尔斯首先赞扬了英国早期小说“松散自由的形式,散漫芜杂的闲话,自由遨游的权力”,然后明确地区分了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异同:
小说如同戏剧一样,它是倡言道德的强大工具。……过去的小说与我称之为现代小说的作品之间存在着可以界定的区别。……前者在道德价值和品行标准方面有确定感,而今天的小说则全然皆无。
另外,詹姆斯极力反对威尔斯所使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手法,认为这一“糟糕透顶的自传形式奉松散、即兴、廉价和简易为圭臬”,因而缺乏间离超脱的效果,缺乏“美的化学变化”,而“美的化学变化”是小说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威尔斯却不愿苟同詹姆斯的观点,他极力推崇笛福、狄更斯、菲尔丁等人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小说,高度评价作品中小说家自由任意的评论和闲话,认为这些评论和闲话构成了他们小说最主要的成就。
1912年3月,两人的友谊出现裂痕。由詹姆斯、 康拉德和萧伯纳等人组成的皇家文学社下属的学术委员会邀请威尔斯入会,但遭到拒绝。詹姆斯知道后尽力劝说,而威尔斯则毫不客气地回信:“我坚决反对这样的文学或艺术的学术机构,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反对这些组织对技巧和单一标准的倡议。 我强烈感到自己宁可与豪尔·凯耳( Hall Caire)一道逍遥于学术委员会之外,也不愿入会与你、高斯(Gosse )、吉尔伯特·莫莱(Gilbert Murray)和萧伯纳共事。我坚信,我们这个世界,我是指富有创造性和表现性的作品世界,是不需要任何规范的。”(1912年3月25日信)后来詹姆斯再次挽留, 但威尔斯不为所动。威尔斯把这次事件称为“不听命”,但两人之间仍然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
1912年9月,随着威尔斯小说《婚姻》的出版, 两人的书牍之辩重新开始。詹姆斯10月18日致信威尔斯,指出自己在阅读这部小说时,“完全放弃了‘批评的原则’,形式的标准,愉悦的期待,无法顾及创作技巧或创作的神圣法则。”尽管这封信表面上彬彬有礼,但詹姆斯声称自己放弃了批评的原则等,这无疑是说威尔斯的小说毫无形式,不讲技巧,根本不是艺术品。而威尔斯一直拒绝承认存在着“创作的神圣法则”,相反,他却认为小说的创作不应受制于任何先在的标准,小说唯一的缺憾即是小说家想像力的缺憾。由于视詹姆斯为尊敬的长者和前辈,威尔斯一直恭恭敬敬地回应他的指责,不时谦虚地称自己的小说是“早产的婴儿”,它们和詹姆斯的成就相比显得“拙劣和粗糙”。
1914年,两人的矛盾公开化。詹姆斯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年轻一代》一文,公开指责威尔斯的小说缺乏艺术性:“《新马基雅弗利》、《婚姻》和《激情朋友》等小说表明,(他的小说)只存在素材的堆积,而不存在对怎样运用素材的兴趣,因此,我们一遍又一遍的询问自己,这样一种遭人忽略的疏漏状况竟会对小说的数量不产生任何致命的影响……”直到此时,一直为尊者讳的威尔斯才开始对詹姆斯进行公开的批评。他在小说《波恩》一书中增加著名的一章《论艺术、文学和亨利·詹姆斯先生》。小说假借作家乔治·波恩之口,采用戏拟的手法,对詹姆斯进行批评和议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威尔斯把詹姆斯比作是“一头高贵但很痛苦的大河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体面而捡拾一粒落入自己巢穴角落的小豌豆”。威尔斯这样评价詹姆斯的小说:
在他的小说中,你找不到带有特定政治观点的人物,找不到带有特定宗教观点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物从属于明确的党派或具有各种欲望和冲动,没有一个人物一定靠近具体客观事物。
詹姆斯读到这一章节之后,写信称两人之间的论辩缺乏“共同的焦点”,而这导致“交流的桥梁坍塌”。威尔斯致信詹姆斯表示道歉,并企图阐明两人的分歧:“对你来说,文学像绘画一样本身就是目的;对我来说,文学像建筑一样是一种工具,有它的用途……我宁愿被称作新闻记者而不想被尊为艺术家,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1915年7月8日信)詹姆斯回信说:“我认为你对文学如(是)绘画和文学如(是)建筑的划分是完全空洞无用的。……是艺术创造了生命,产生了趣味,形成了重要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替代艺术过程的力和美。”三天后,威尔斯写信说明两人对“艺术”一词理解的歧异,詹姆斯是否回信尚不得而知。几个月后,即1916年2月,詹姆斯病逝, 威尔斯亲自前往料理后事。
在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估量文学艺术的价值时,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倾向,即追求文学艺术功利性的态度和追求艺术完美的唯美倾向。前者强调文学艺术的目的性和社会效用,强调文学艺术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召力,文学艺术应该服务和作用于现实生活,应该具有影响和改变现实生活的巨大功能;后者认为艺术本身即是目的,文学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其自身形式的美,而美即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表面上看来,詹姆斯——威尔斯的尖锐对立似乎代表了文学中功利和唯美两种倾向的二元对立,但实质上他们的论争反映了世纪初艺术家们在重新审视和观照文学艺术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层歧异,也映照出他们在探寻文学艺术的本质、目的和手段时所体现出来的真挚。
英国文学自乔叟开始的现实主义传统,历经现实主义巨匠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洗礼,及至18世纪现实主义在勃然兴起的小说中扎根,再至19世纪蓬勃发展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价值坐标越来越偏向功用和实效的一端,威尔斯“宁愿被称作新闻记者”的“宣言”至少在观念上把这种价值取向推到了一个极端。19世纪末逆现实主义传统而反动的唯美主义运动扯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招摇地走向另一个极端,詹姆斯对威尔斯的回应和反驳显然是这股思潮在20世纪初的延续和再现。詹——威之争不仅仅是一对挚友之间的私人之争,也不仅仅是局限于有限时空内的文学论争,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学踏入20世纪所面临的价值选择之争。是固守传统还是勇于革新,文学中永远存在着的这一对矛盾往往以极端的二元对立的形式呈现出来:死守现实主义的传统经常导致功利的艺术家们极力追逐文学的社会功用和社会效果;勇于艺术形式的革新往往会使另一部分艺术家们悄然躲进唯美的象牙之塔。詹——威的论战只不过是功利和唯美这一对立两极的具体表征和一个比较有趣的范例。
威尔斯与詹姆斯的论战实质上还是文学艺术中永恒的焦点问题,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詹姆斯对小说这一艺术形式的界定,对小说与生活的联系的强调,以及对文学艺术的整体把握,早在1884年的论文《小说的艺术》中就有最为充分的阐述。这篇文章也是詹姆斯与一位文学批评家论争时撰写的争鸣文章。詹姆斯认为小说是“直接地再现生活的艺术”,小说应该强烈地透出“现实的气息”,“一部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试图反映生活。一旦放弃这一企图,……它将陷入一种奇怪的境地”。在这篇经典性的文章中,詹姆斯主张小说的每一个细节都要留下“一个直接的、个人的印象”;“小说的至高美德”就是体验现实,这种对现实的体验只能来自作家的“巨大感受性”;而小说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小说家的主体经验。由此可见,詹姆斯由外向内转移文学的关注中心在当时就已经初露端倪。后期的詹姆斯过分追求艺术的形式,似乎忽略了对现实生存的有力关注。实际上,詹姆斯只是不像威尔斯那样对具体的生存环境和人类外在的生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是把自己的艺术触须伸入到人类的内心世界,追求对人类内在真实的把握,试图捕捉捉摸不定的人类意识和思绪,揭示或脆弱、或忧郁、或贪婪等等的内在情感和精神世界。
威尔斯宁作“新闻记者”不愿作“艺术家”,主张要让阅读小说的读者有所裨益和收获,让他们在享受小说娱乐性的同时,认识到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从而达到改变人们的情感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目的。威尔斯在小说中不屑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疏于创造鲜活的人物性格,坚持认为“解决问题是小说写作的基本任务”。威尔斯认为,在一个自己的社会中,小说因为对人们业已接受的观点的研究和对社会变化中人们道德困境的探索而表现出自身的价值。他极力推崇狄更斯、斯泰因以来的文学传统中那些具有实用理想和容纳广阔生活内涵的小说,批评詹姆斯有关艺术地再现个体意识的小说观念。威尔斯在《波恩》一书中严肃地考察了作家的社会功能。在这本书和在以后同即将离世的詹姆斯的通信中,威尔斯屡屡标榜自己的作品只是偶尔带点艺术趣味的新闻,这一自谦的说法倒也揭示了他的艺术追求中独特的一面,也给许多攻击他的人抓住了口实和把柄。
客观地说,詹姆斯后期的创作确实存在某种唯美主义的倾向。世纪末唯美主义在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无限夸大“艺术高于生活”,这对钦慕欧洲文化致力小说革新的詹姆斯来说不可避免地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唯美主义者认为:“艺术将生活看作其部分素材,重新改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新的形式……”,“文学总是先于生活。它不是模仿生活,而是按照自己的目的来浇铸生活。”唯美主义者还认为:“艺术除了表达自身之外,从不表达任何东西。艺术犹如思想具有独立的生命,纯粹按照自身的线路发展。”因此,詹姆斯指责威尔斯和贝内特等人“把生活当作一个巨大无比的桔子,为了写小说而无休止地挤压它”,指责他们对生活不加任何精心的选择和组织,不作任何艺术的加工和创造,因而他们的作品难免失之粗糙和缺乏艺术性。詹姆斯认为“小说即是一门艺术形式,……它不一定要到达什么地方”。詹姆斯对艺术形式的过分强调最终滑入了极端,雕饰出“沉闷繁琐”的所谓“后期詹姆斯风格”。
在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急功近利是一种短视,“唯美是图”是一种褊狭。威尔斯对艺术“工具论”和“新闻性”的强调非常接近艺术上的急功近利,而詹姆斯重视“艺术过程中的力和美”非常类似艺术中的“唯美主义”。詹姆斯——威尔斯之争,究其实质,并不完全是功利和唯美之争,而是世纪初英国文坛对文学艺术的本质、目的和手段的一次直接的审视,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对文学艺术的一次再思考。文学艺术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文学艺术的价值何在?是唯功利的,还是唯美的?是介于二者的中间地带,还是外在于二者而存在,或其他?这场论争并没有随着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剧烈动荡而结束。一战以后,现代主义昂然崛起,各种科学成果纷至沓来,各种社会思潮汹涌而至,人们更喜欢从崭新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生存,更倾向采用独特的态度来看待文学艺术,新与旧的对立,现代与传统的交锋不可避免。
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正面遭遇战
20世纪一二十年代,英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文学艺术如何面对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如何灵巧而机智地作出自己的回应和反拨?文学艺术如何不断开拓新的空间、不断寻求新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新的社会内容?文学艺术的探险者和叛逆者们往往不会满足于固有的观念和既定的传统,他们积极主动地在艺术的世界中进行着大胆的实验,希望开拓出多种可能性的艺术空间。詹姆斯之所以被称作“现代实验小说的先驱”,就是因为他在世纪之交的英国文坛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他在小说形式和技巧方面的革新和实验,尽管流露出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但是其中对“生活中真正的经验和感悟”的关注,其中从外部社会向内心世界的转换,为英国小说的创作“拉开了现代主义的序幕”。自此,自菲尔丁、奥斯汀以及狄更斯、萨克雷以来的现实主义的小说传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世纪初爱德华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三杰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更成了创新求变的现代派作家攻击的首要目标。现代派从发轫走向辉煌、从稚嫩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不断发难传统不断突破传统的过程。
如果说詹姆斯和威尔斯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只是现代对传统之战的序曲的话,那么现代主义的猛将沃尔夫对现实主义小说三杰的责难则是一场正面遭遇战。詹姆斯和威尔斯是一对好友,而沃尔夫与三杰的对阵则是陌路相逢。20年代前后,现实主义三杰已经功成名就,而现代主义小说实验如火如荼,沃尔夫为了给自己的创造性实验寻找理论依据,首先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发出挑战。与詹——威的“大论战”相比,沃尔夫与三杰的对阵剑拔弩张,火药味浓。
沃尔夫的发难肇始于1919年,她在4月10 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现代小说》一文,矛头直指“爱德华时期的小说家”,也即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对他们的小说创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我们并不是同古典作家们争论。如果说我们是同威尔斯先生、贝内特先生和高尔斯华绥先生争论的话,那么其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还健在人世,他们的作品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这些缺陷活生生地存在着,还呼吸着空气,每时每刻都可以见到。我们只好直言不讳了。……如果要我们用一个词来概括我的意思,那么我们会说这三位作家是物质主义者。他们关注的只是躯体而不是心灵。
这篇论文不仅是沃尔夫本人“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宣言,而且也是沃尔夫向传统作家正式开战的挑衅书。沃尔夫指责现实主义三杰“关注的只是躯体而不是心灵”,在她看来,“物质主义者们”只是偏重于逼真细致地描摹外在的物质环境,而完全忽略了人的主观情绪和感观印象的内在世界,他们只不过是把生活中“琐屑、短暂的东西变成看似真实、永恒的东西”,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生活溜走了”:
我们叹了一口气,放下手中刚刚看完的小说,脑中不断出现这样一个念头——这(小说)是否值得一读?其意义究竟何在?难道是人类的心灵时常会出现毫厘之偏差,带着精良仪器前来捕捉生活的贝内特难免会出现一英寸或二英寸的谬误?结果,生活溜走了;而失去了生活,其他一切也就失去了价值。
现实主义三杰的小说注重外部的生活,忽略了人的内心生活;而外部生活是表面的短暂的,内心生活才是真实的永恒的,才是生活的核心。因此,小说必须进入人物内心的世界,直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内在感受:
向内心看,生活似乎远非“如此”。仔细观察一下一个普通日子里普通人的大脑吧。头脑接受千千万万个印象——从细碎的、奇异的、转瞬即逝的印象一直到用利刀镂刻一般的印象。这些印象像无数原子一样,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生活不是一连串左右对称的马车灯,而是一圈明亮的光晕,是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我们的意识始终被包围着。
“内”与“外”是沃尔夫和现实主义三杰的分歧所在,也是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异所在。沃尔夫讨伐现实主义三杰,贝内特首当其冲。沃尔夫指责贝内特把人物生存的外在环境称作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并手持照相机般的“精良仪器”一丝不苟地捕捉和记录着外在生活。沃尔夫认为小说家的任务应该是“尽可能不带任何杂质地”表现“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定的内在精神,不管它显得多么有悖常规和错综复杂”。沃尔夫十分推崇乔伊斯的小说《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并认为乔伊斯是“偏重精神的:他不惜一切代价来揭示内心深处闪烁不定的一团火焰……”。
沃尔夫和贝内特对峙的另一焦点便是对“真实性”的不同理解。贝内特注重“外在的”真实,沃尔夫强调“内在的”真实,其实质仍然是“内”与“外”的差异。贝内特认为,小说家必须创造“真实的”令人信服的人物,“一部优秀小说的基石在于性格的塑造,而不是其他什么”。针对贝内特的观点,沃尔夫于1924年5月18 日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的演讲。在演讲中,沃尔夫说:“现在我们必须回顾一下阿诺德·贝内特先生所说的话。他说,只有人物是真实的,小说才有生存的机会;否则必然会夭折。但是,我问自己:什么是真实?谁又是生活的评判者?一个人物可能对贝内特来说是真实的,而对我来说又是相当不真实的。”沃尔夫对贝内特等人极尽揶揄和奚落:“我似乎觉得,要是找他们讨教如何写小说,如何塑造真实的人物,真好比向制鞋匠请教如何修钟表。”沃尔夫认为,小说创作必须按照意识活动的本来方式来表现意识活动,这样才能达到内在真实,而内在真实与现实主义的酷肖和逼真等外在真实相比是更高程度上的真实。贝内特等人从来没有考察过人物的内心,从来没有关注过人类的内在本性,因此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必然会“死亡”,也必然会导致小说的“死亡”。
贝内特是当时能够左右评论界的小说家和批评家,对于沃尔夫的“挑衅”,“有时真想和弗吉尼亚·沃尔夫打上一架,但是没有机会”。对于别人的怂恿和撺掇,贝内特说:“经常有人对我说,沃尔夫和我之间有宿怨,我敢说她也得到过同样的信息。或许,我和她是文学圈内不知有此宿怨的两人……真的,沃尔夫是一个趣味高雅的王后,我是一个趣味低下的凡人。但是,世界是由各种趣味的人组成。”面对沃尔夫的批评和指责,贝内特不失时机表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对沃尔夫的小说加以评论:“我未能发现这部小说(指《达罗维夫人》)的道德基础是什么。至于性格的刻画,沃尔夫给我们讲了一万件有关达罗维夫人的事情,却没有把她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到灯塔去》出版后,贝内特这样评价:“她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了进步。”由此可见,贝内特强调社会道德基础,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明显秉承了英国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与狄更斯、乔治·艾略特等人的小说一脉相承,即通过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事件的叙述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等来反映社会人生。但贝内特并没有完全受制于英国小说的传统。年轻时旅居法国的经历使他有幸结识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并熟读法国作家左拉、莫泊桑的作品,他在作品中借鉴和融入了法国自然主义的创作手法和技巧,极力对剧烈变动中的社会作不折不扣的忠实记录,对工业化冲击的外省小镇生活作客观、冷静、中立的描述,他的作品浸透着自然主义的悲观和宿命论的倾向。以《老妇谭》为代表的作品表现了人生无常、命运不可揣测的主题,流露出无可奈何、一切徒劳的消极情绪。贝内特以照相机般的视角来原原本本地捕捉和记录生活中零星琐碎、细枝末节的东西,放弃了对生活素材进行必要的剪裁和艺术加工,因而无法提炼、概括和塑造出最典型最集中的文学形象。他拘泥于自然主义艺术所标榜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但无法达到现实主义传统所提倡的典型性真实性。贝内特在手法上讲究酷肖和逼真但显得刻板和机械,人物刻画趋向类型化但显得单一和呆板,忠实记录生活的同时又偶或对生活进行主观的阐释和评论,因此贝内特被沃尔夫称作是现实主义三杰中的“首恶”。
沃尔夫攻击三杰的《现代小说》和《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是现代主义的两篇经典文章,典型地概括了现代主义文学“向内心转移”的根本特点。沃尔夫将本世纪以来的英国小说家分为两组:一组是威尔斯、贝内特和高尔斯华绥;另一组是福斯特、福特和劳伦斯,这也是我们现在所经常区分的现实主义作家和现代主义作家。沃尔夫认为,贝内特等人所使用的是一种陈规刻板的创作方法,所表现的是繁琐细碎的外在生活,完全忽略了人的“永恒的”、“实在的”、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在什么是“生活”、“现实”、“真实”等文学基本问题上的不同理解,正是沃尔夫和贝内特等人产生严重分歧的重要原因所在。显然,现代主义作家所理解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所理解的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迥然不同。现代主义作家所处的20世纪,哲学、心理学等现代学科迅猛发展,人们对现实的理解也不断深化和发展。现实不再仅仅是外部的社会现实,它还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的现实,这在世纪末的今天似乎已是一个文学常识。贝内特等人把文学的视角对准的是外在的现实,而沃尔夫等现代派作家把文学的触须伸向了微妙多变的内在现实。外在现实的种种特点要求贝内特等人只能采用人物刻画、环境描写等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揭示和探微又要求沃尔夫等现代主义作家使用意识流、内心独白、象征隐喻等实验性表现手法。贝内特用小说记录人生,威尔斯把小说当作工具,高尔斯华绥用小说来进行道德改良,现实主义三杰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与人类社会的密切关系,他人试图用文学来反映社会,演绎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对外在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生活方式等方面所带来的深刻变化;现代主义作家对人的内在现实的关注,深刻揭示出20世纪现代西方社会和西方人的精神危机,独特地表现了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所面临的全面解体。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构成了现实的全部内涵,“现代主义并不是对传统的摒弃,而是对传统的扩展。”因此有人称,现代主义文学实质上是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新发展。
回首英国现代文坛,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论争确实以沃尔夫对贝内特等人之战最为激烈,也最为典型。他们之间的批评和反批评充分反映了新旧更替时期文学观念的冲突和文学的多样选择。论争双方各持己见,各执一端,虽然各有千秋,但也难免失之偏颇。贝内特在人物真实性的问题上所追求的客观性,他所热衷的堆积外在具体和细枝末节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现实主义,落入了“自然主义”机械教条的泥坑。沃尔夫对人物内心世界灵活多变的意识活动的探索,为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广阔的空间,但是她对现实主义的极力贬低和对狭隘的内心世界的表现,又将导致文学作品难以揭示错综复杂、内涵深邃的社会生活,导致文学作品缺乏丰富多彩和千姿百态的生活气息。贝内特固守传统的做法不免机械和呆板,而沃尔夫与传统彻底决袭的态势则显得偏激。
补遗:劳伦斯的出击
劳伦斯是英国现代文坛遭受非议最多的一位作家。他的小说《虹》因“有伤风化”而遭到查禁,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因涉嫌淫秽而被禁出版。性题材的尝试和性心理的渲染难以见容于当时的习俗和传统,“血性意识”的推崇和严重的法西斯倾向向来为西方评论界所诟病;而他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病魔缠身的一生颇让人同情和感慨。一方面,他的小说保持着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种种特征,不像沃尔夫等人的小说那样充满对形式和技巧的革新实验。在论文《道德与小说》(1925)和《小说为什么重要》(1925)中,劳伦斯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自己对新时期小说艺术的认识和审视。在《道德与小说》一文中,劳伦斯开门见山地指出:“艺术的职责在于揭示一个洋溢着生气的时刻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人类总是在种种旧关系的罗网中挣扎,而艺术总是走在‘时代’的前面,艺术本身总是落在这洋溢着生气的时刻的后面。”劳伦斯认为,艺术揭示出的“人与周围世界之间这种比平时完满的关系,对人类来说,就是真正的生活。它具有第四向度的永恒性和完满性。同时,它又是存在于瞬间的。”“而道德则是在我和周围世界之间永远颤动着变化着的灵敏的天平,它引导着也伴随着一种真正的相互关系。”“小说并不是因为小说家有个什么主导思想、主要意图,就必然成了不道德的。不道德的根源在于小说家不由自主、不知不觉的偏好。”“小说是一种完善的手段,可以向我们展现出我们之间像彩虹般变幻无常的活生生的关系。……如果小说家不把拇指伸进天平盘的话。”在《小说为什么重要》中,劳伦斯认为,“除了生命,什么都不重要。就我来说,在活东西之外,哪儿我都看不见丝毫的生命。生命称得上伟大的,只有活人。……一切活着的东西都美好神奇。一切死的东西都依附着活的。宁可做活的狗,不做死狮子。但是宁可做活狮子而不做活的狗。这就是生活!”而“小说是唯一能生动地展现生活的书”。“在小说中各个人物什么都不能干,就是能活。要是他们墨守一定的程式老是那么好,或者老是那么坏,或者甚至于老那么反复无常,那他们就没有活气,小说就一命呜呼了。一个小说人物非活不可,要不他就等于零。”“生活里始终有是有非,有善有恶。……是与非是一种本能——然而是人全部知觉的本能,是从肉体、理智、精神几方面同时产生的。而唯独在小说中,一切事物才得到充分的展现……”由此可见,劳伦斯的小说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观念血脉相连。
另一方面,他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大师的地位似乎已经不可动摇。他的现代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方面,其中心理学的内容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精神分析与无意识》(1921)、《无意识之狂想》(1922)等论文表现出对人类意识领域、性心理等问题的强烈兴趣。小说创作中,劳伦斯抨击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特别是对人的本能欲望的扼杀和摧残,主张通过释放和复活人的原始本能和全部自然本性来建立一种“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以摆脱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生的压抑。他的小说融合了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和现代主义的心理探索两大典型特征。
在现代意识和传统观念激烈交锋之际劳伦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现实主义三杰之一的高尔斯华绥。 他的著名长篇论文《论高尔斯华绥》(1928)比沃尔夫的《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晚四年发表, 但是其措辞之犀利、态度之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劳伦斯的论文同沃尔夫的“檄文”一样在当时文坛产生很大影响,但他对高的问难并不是在传统与革新的小说观念层面上,而是在人物的形象和道德的层面上。高尔斯华绥被公认为是20年代的文坛巨擘。他在系列小说《福尔赛世家》中把表现时代精神和揭露社会罪恶作为己任,其中《有产业的人》不乏“严肃的内涵和洞见的火花”。这部作品对资产阶级物欲至上和自私自利的品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但同时作者又给他们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因此,这部小说所受到的批评和指责不绝于耳,而劳伦斯的批评最为严厉。劳伦斯认为,这部小说
具有成为一部巨著,一部伟大的讽刺作品的因素。它开始时旨在揭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人的全部力量和弱点。但是,作者并没有勇气将这项任务进行到底。小说的成就在于它那种新鲜、诚挚和异常尖刻的讽刺。小说是对于现代人的深入讽刺,它以高超的技艺和诚挚而富有创造性的热情,从内部着手,加以描述,颇有新意。它摆开架势,仿佛真的要揭示出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的全部奇怪秉性;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它悄然熄灭了。
劳伦斯对高的指责显然不是在现代主义所推崇的内心世界的层面上,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德批判的层面上。劳伦斯严厉批评高的社会批判缺乏坚决性,人物讽刺缺乏彻底性。小说“具有的崇高笔触的讽刺,不久便嘶的一声熄灭了。我们看到众多高尔斯华绥氏的‘叛逆者’,但如同其他现代中产阶级的叛逆者一样,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叛逆行为。他们仅仅是反社会的人。他们崇拜自己的阶级,但他们假装比别人更胜一筹,并回过头来嘲笑自己的阶级。他们的‘反’是福尔赛式的……”在劳伦斯看来,小说中的人物老裘利恩和索姆斯,无论是物质至上还是反物质至上,他们都是“社会的人”,而社会的人是“被阉割的人”。“阉人”是没有行动能力的,他们是不会叛逆自己的阶级的。文章最后,劳伦斯谴责高尔斯华绥“粗鄙”,是典型的“廉价的愤世嫉俗”。
高尔斯华绥秉承英国小说批判和讽刺的伟大传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弊端,暴露资产阶级人物的种种缺陷,但他主张调和妥协并希望通过道德改良来改变社会和人性。因此,劳伦斯主要抨击高的小说缺乏鲜明的艺术形象,社会批判缺乏应有的彻底性。劳伦斯对《有产业的人》的批评为我们提供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强相争之间的一个侧影。他的批评在当时影响很大,有评者指出:“劳伦斯的观点比沃尔夫对物质主义的攻击更为彻底。”
结束语
有人说,传统往往具有拒变斥异的惰性力量,因而常常处于恒定不动的状态。但传统又是变动不居的,没有一成不变、一以贯之的传统,因为孕育于传统之内或游移于传统之外的新异因素不断冲击、对抗和颠覆着传统。而对文学传统的相沿相袭和持相异相反的态度存在于任何时代的文学之中,文学就是在传统和变革的相互对峙和自由交锋中得到不断发展的。现实主义小说三杰恪守传统坚持条律,他们反映社会批评现实抨击时弊,固然名垂青帛;而现代派大师们极力表现主体的感官体验,试图揭示主体内在精神世界,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的小说创作,功绩同样不可湮没。对于文学中出现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自然主义倾向以及极端表现内在自我的倾向,应该采取更为审慎和辩证的态度,而不可轻率地一律棍击而毙之。
回首英国现代文坛人物,伟岸的人格,飘逸的形象,即便是过火的言语或偏颇的观念,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中国作家曾经说过,对于文学来说,真诚的对话和自由的争鸣怕是要比毫无节制的吹捧和泼皮牛二式的叫骂更为有益!
标签:艺术论文; 詹姆斯论文; 沃尔夫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小说论文; 文艺论文; 威尔斯论文; 贝内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