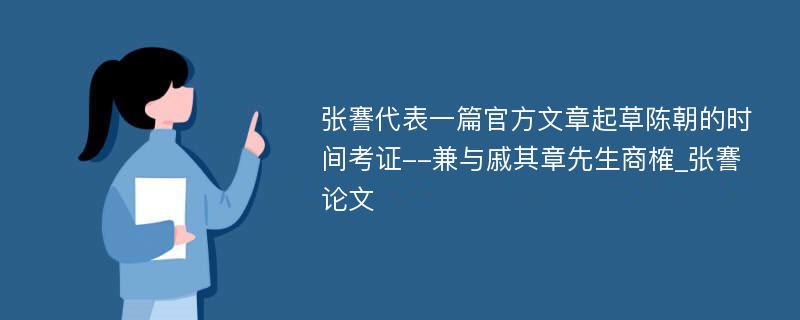
张謇《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拟稿时间考辨——与戚其章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陈论文,朝鲜论文,事宜论文,时间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2007)01-0077-04
《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是张謇基于“护藩固圉”国防理念,防止朝鲜“为日人所有”,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为国子监盛昱祭酒所拟。疏中条陈“援护朝鲜八事”,集中体现了张謇护朝、御日、保国的军事谋略思想。此疏对于研究张謇的国防思想极有价值。
对于此疏的拟稿时间,原本十分清楚。《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全集》收录此疏题下均注为“清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然而,在1995年召开的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戚其章先生提交的《张謇〈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考》论文中,对此疏的写作时间问题进行了新的考证,考证的结论是:“此疏必定是作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但也不会晚于七月初四日”,“将拟疏的时间定在七月初三日,是比较恰当的”。[1]
诚然,此疏写于何时无碍于我们对张謇的总体评价,但对此疏拟稿时间有前后相差10个年头的两种说法,若要考察张謇国防观的嬗变,其拟稿时间的考定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有鉴于此,本文对此疏拟稿时间作进一步考辨,疏谬之处,祈请戚先生赐教。
能佐证张謇此疏拟稿时间的历史资料主要有二:一是“日记”;二是《啬翁自订年谱》。“日记”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记载称:“为意园拟陈朝鲜事。(意园盛祭酒所居)。”[2] 254《啬翁自订年谱》称:“十一年乙酉(1885)……十月,……连三夜,为伯熙(系盛昱字——引者)拟陈朝鲜事”[2] 847。
“日记”是张謇逐日记载其当日的所作所为。这种流水账式的逐日记事不会有时日上的误差,也不会有记载事实上的虚假不实之处。从《啬翁自订年谱》的内容看,“年谱”是张謇事后参照日记写成。所不同的是,“年谱”所记载情事简明扼要。由此可见,“日记”和“年谱”所载光绪十一年十月为国子监盛昱祭酒“拟陈朝鲜事”即是《张季子九录》中收录的《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是不争的事实。
从“日记”和“年谱”记载的张謇与盛昱交往,以及张謇和盛昱对朝鲜问题关注程度来看,此疏拟稿时间应是光绪十一年十月。
光绪十一年四月,张謇府试结束后即赴京应试。张謇在京期间,屡屡与盛昱接触,并引以为友。据“年谱”记载:四月至京,“先寓杨梅竹斜街和含会馆”,后“移寓内城东单牌楼观音寺胡同文昌关帝庙。识黄仲弢绍基、……宗室伯熙盛昱、……,与为友”;“六月,国子监考到,取第一名,录取第四名。与伯熙谈朝鲜之危,不亟图存,必为人有,因以前策(指光绪八年(1882)在朝鲜时代吴长庆拟《朝鲜善后六策》——引者)示之,共太息而已。”[2] 846-847七月下旬至十月底,张謇与盛昱交往频繁。“日记”作了详细记载:七月十六日,“伯熙来久谈,知吉林旗丁多改汉籍,以避征调。……朝鲜之徘徊两可,必有为人割据之势,真可慨也”;九月二十四日,“例谒监临,晚谒盛祭酒”;十月十三日,“往见常熟师、意园”;二十四日,“为意园拟陈朝鲜事”;二十五日,“与意园讯”;二十六日,“再与意园讯”[2] 253-254。
此期间,张謇与盛昱的频繁交往,主要由于他们对朝鲜问题共同关注。由此,张謇为盛昱代拟条陈朝鲜事宜疏顺理成章。
史实表明,光绪十一年四月赴京起,张謇屡屡接触朝鲜问题。壬午事变后,尤其是1885年4月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后朝鲜出现复杂多变的局面,促使张謇进一步思考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据“日记”记载:四月二十六日,“抵天津,见亚甫,遇朝鲜乞留防兵之使臣闵泳翊”;“二十七日,雇车行抵杨村,以步先讯识王仁安提督恒风。临行,泳翊眷眷,至欲下泪。盖日使与李相既定撤兵之约,闵诣李相,凡数日不获一见也。我兵一撤,恐东事益不可问耳。闵固亦浮华少年,至是与言,乃颇沉切,人不可不更忧患如是”;十月十四日,“知朝鲜复以奸人将通款于俄,上表乞援,我固料必至此也”;十月十五日,“知朝鲜事,李相力主不援之说”[2] 244-254。
作为宗室,盛昱十分关心朝鲜问题,并敢于直言己见。《清史稿》记载道:“朝鲜之乱也,提督吴长庆奉北洋大臣张树声檄,率师入朝,执大院君李昰应以归,时诧为奇勳。盛昱言:‘出自诱劫,不足言功,徒令属国寒心,友邦腾笑。宜严予处分,俾中外知非朝廷本意’”[3] 12454。盛昱对吴长庆最后处理朝鲜问题有如此尖锐的批评,表明他在壬午兵变前后的几年间密切关注着朝鲜事态的进展及清政府的对策。
综上所述,对朝鲜问题共同关注、直言不阿的相似品格,张、盛在频繁交往后,对解决朝鲜问题必然会产生相同认识,由此必然导致张謇为盛昱代拟“条陈朝鲜事宜疏”。
戚先生考证后认定拟此疏时间在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笔者理所当然应顾及此时张謇的“日记”及“年谱”中对有关问题的记载。
毋庸置疑,光绪二十年张謇赴京应试期间,对朝鲜问题依然极为关注。“日记”载:光绪二十年六月,“六日,闻朝鲜事言人人殊。上常熟师书”;“七日,为叔衡拟历代边事类目”;“十日,……为萧小虞拟‘条陈东事’疏”;七月,“十八日,见常熟,知朝局又变,可为太息痛恨于无穷矣”;九月,“四日,叔衡领衔合翰林院三十五人上请罪北洋公折。余单衔上推祸始,防患将来,请去北洋折,均由掌院代奏。”[2] 363-367“年谱”载:二十年甲午,“六月,……二十六日,太后万寿朝贺。日本以是日突坏我北洋兵舰二”;“七月一日,上谕声罪日本。朝议褫海军提督丁汝昌,李鸿章袒之,朝局大变”;八月,“……闻我军溃平壤,退安州。日兵扬言,分道入寇”;“九月,翰林院五十七人合疏请恭亲王秉政;又三十五人合疏劾李鸿章;余独疏劾李:战不备,败和局”[2] 853。
观“日记”与“年谱”,并没有戚先生所认定的七月初三张謇代他人拟朝鲜事宜疏的记载。“日记”中有六月十日“为萧小虞拟‘条陈东事疏’”的记载。有关萧小虞官职等问题,笔者手头尚缺史料,无从考证,暂存疑。但戚先生认定拟疏时间为七月初三,据此,似可肯定为萧小虞“条陈东事疏”与“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不属同一疏。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某公”是指盛昱(当然,戚先生未对“某公”的身份作考证)。那么,光绪二十年间张謇与盛昱有何交往呢?有关史料表明,此时张、盛有交往,但没有代拟疏的可能。“日记”载:六月十一日,“诣意园”;六月十八日,“诣意园”[3] 364-365。可见,此时,张謇念旧交,赴盛昱寓所作礼节性的拜访。而此时的盛昱已因病退出政坛。据《清史稿》载:盛昱“十四年,典试山东。明年,引疾归”[3] 12455。
以上仅就张謇“日记”、“年谱”等第一手史料,考证《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拟稿时间。下面,就此疏所涉及的相关事实作些不成熟的考辨。
其一,疏称:“觊觎之者,无过于俄罗斯、日本二国。俄之据库页岛,经营珲春,侵该国之图们江,而招致其民人十余年矣。”[4] 22这是张謇疏中“条陈援护朝鲜八事”行文之首,是对当时中朝所处的国际环境陈述的一段文字。考辨的关键是:张謇所说的俄据库页岛,经营珲春,侵该国之图们江而招致其民人“十余年”,究竟始于何年代?以此时间来推断此疏拟稿的年代。
库页岛位于黑龙江口外。据史料记载,唐代属黑水都督府管辖,至清初,为吉林三姓副都统辖地。18世纪中叶后俄日相继侵入,俄占北部,日占南部。然岛上土著居民依旧向清政府交纳贡物。1860年11月,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的《北京续增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稜河;自白稜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二十里。”[5] 149俄国通过上述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后,与日本屡次争议划定岛上境界,延至1875年议定俄以千岛十八岛交换日占南部,全岛归俄属[6] 2221。
据此,可以认定:张謇所说的“俄之据库页岛,经营珲春,侵该国之图们江,而招致其民人十余年”事实,应是1860年以后逐渐出现的状况。由此而论,“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中所说的“十余年”,判定此疏拟定时间为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是合适的;如此疏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拟定的,那么,疏中应用“二十余年”,才能与史实相符。
其二,疏称:“今闻日本忽以重兵胁制该国王,令向来不属中国之约。恃强犯顺,情事显然”。此为戚先生“可疑之一”,认为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签订后“9年的时间内日本无一兵一卒留于朝鲜,哪里有什么‘重兵’呢?”
诚然,根据1885年4月18日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中日双方为处理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而入朝的军队,于1885年7月21日自朝鲜撤回各自国家。[7] 783然而,自此至1885年11月张謇拟疏期间,确有日本将袭击朝鲜汉城传闻。据台湾学者郭廷以编著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记载:1885年10月13日,“朝鲜新党朴泳孝等上书国王,自辩无罪,痛斥中国。金玉均致函江华留守李载元,谓将雇日人二百袭汉城,约其内应(是夜袁世凯已知)。”[7] 787次日,“朝鲜国王以朴泳孝的书示袁世凯”[7] 788。25日,袁世凯自朝鲜至天津见李鸿章。
窃以为,如此重大的消息不会不在京城官员中传播;而广交京官为友且十分关注朝鲜问题的张謇,是不会不知道此消息的。这一消息,构成张謇疏中“今闻日本忽以重兵胁制国王”的依据,似在情理之中。虽至1885年11月底,未出现日本“以重兵胁制国王”情事,但以传闻的口气在草拟此疏中写上,不能说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吧!
其三,疏称:“流虬去而安南随之,安南去而暹罗、缅甸随之,此已事之鉴也。”此为戚先生“可疑之二”,认为清政府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吞并是通过1886年7月签订的《中英缅甸条款》,“若此疏拟于光绪十一年,怎么能以肯定的语气论断翌年将要发生的事呢?”
诚然,清政府“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是在1886年7月24日签订的中英《缅甸条款》中所规定的。但我们注意到,英国对缅甸“事实上”的吞并在光绪十一年底前即已完成。1885年8月,英国木商公司因私运木材,被缅甸国王处230万卢比罚款,并取消其租山契约。为此,英印总督与缅甸国王交涉。缅甸国王拒绝英印总督调解条件后,英国遂加速对缅甸的侵占和吞并的步伐。10月22日,印度总督要求缅甸将木商交付仲裁,允英使驻扎缅京,管理缅甸外交,接着,英印当局派兵入侵缅甸[7] 788。11月13日,英军自伊洛瓦底江进攻缅甸;23日,英国占领缅甸故都阿瓦;25日,英军侵占缅甸京城蛮德勒(瓦城);29日,英军掳缅甸国王锡保,送往仰光;12月29日,英外相令英署使照会中国总理衙门,“自明年1月1日起,英国合并缅甸”[7] 791。
必须指出的是,1885年下半年英国在侵占缅甸过程中,清政府与英国进行多次交涉。如,当英使“管理缅甸外交”,并派兵侵入缅甸时,清政府命驻英法公使曾纪泽“竭力向英法辩阻印度运兵往缅甸”[7] 788;又如,在英军进攻缅甸首都当天,李鸿章与印度辅政司马科蕾进行交涉缅甸问题[7] 790;再如,在英军掳缅甸国王后,曾纪泽即电告总署,“主以八幕为我之商埠,英灭缅甸,我占八幕。”[7] 790从时间上看,英国吞并缅甸之际,即是张謇在京广交京官之时。身处京城且一向关心“边事”的张謇,在疏中写了“缅甸随之”,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其四,疏称:“数年以来,宿将凋谢,唯湘军之刘锦棠、淮军之刘铭传、王孝祺尚在。此外,如云南提督冯子材、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并曾于关外著有战绩”。此为戚先生“可疑之三”,认为所列宿将,除刘锦棠外,余皆中法战争时的名将。而疏中对中法战争名将中“战功卓著者还有王德榜”“避而不谈”,“这是很难想像的”。
我认为,第一,王德榜系湘系人物,中法战争期间署广西提督。从行文看,如把王德榜列上,应排列在刘锦棠之后。但当时王的官阶与知名度,显然不能与刘锦棠齐名,故疏中不列王德榜之名是在情理之中。第二,就王德榜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绩而言,并非“战功卓著”,只能说“战绩平平”。1884年4月中旬,王德榜署广西提督后率部驻兵越南谅山前沿,6月,因“援谅山不力”而革职;次年3月,王配合冯子材获谅山大捷而开复原职。中法战争结束后,朝廷于6月27日褒奖有功人员,“予苏元春、冯子材、王孝祺、岑毓英轻车都尉云骑尉世职有差”[7] 781,而王德榜不在其列。显然,张謇在此疏中“避而不谈”是事出有因的。退一步讲,即便王德榜“战功卓著”,疏中不列王德榜之名亦不能成为“问题”的,因为中法战争中受褒奖有功人员中名列首位的苏元春(1845~1907)亦未列其中。
我想,张謇疏中上述列名,主要出于行文上的方便,张謇不会在对“宿将”战绩详细考证后一一列出;以疏中不提王德榜来论证此疏写于1894年,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其五,疏称:“就目前形势而论,既分大队援护朝鲜,不知内地防军兵力足支与否。”此为戚先生“可疑之四”,认为光绪十一年六月中国军队全数撤回旅顺,“何来十月‘分大队援护朝鲜’之说”?
此段文字是张謇所拟疏中“条陈援护朝八事”中的第六件事。为对戚先生所引此段文字有个准确的理解,兹将疏中第六件事的全文移录于次:
“请量增劲旅,屯驻北洋,以便战守之资。北洋之防,以天津、旅顺、山海关、烟台、威海为最大。此外各小口甚多,断无各处设防之理。就目前形势而论,既分大队援护朝鲜,不知内地防军兵力足支与否?应请饬下北洋大臣量增劲旅:为守计,预于天津屯扎一枝;为战计,须于威海屯扎一枝;以便分别策应。惟不得有名无实,致将来又多一撤兵之累。”
观第六件事全文,对戚先生所引这段文字,可理解为:根据北洋各口设防需要和目前中朝日间复杂多变的形势来看,既然分派大批军队援护朝鲜,北洋大臣就应该从内地防军中调足够的兵力驻屯北洋。这里的“既分大队援护朝鲜”一句,不应理解为已经或正在派大批中国军队援护朝鲜,而应理解为准备或将要派大批中国军队援护朝鲜。
事实上,在光绪十一年十月下旬张謇拟此疏前的一个多月里,清政府确实准备派军队援护朝鲜。据郭廷以《中国史事日志》记载:光绪十一年九月十八日:“李鸿章接10月20日(九月十三日)朝鲜国王来函,请派兵驻汉城附近”;十月初一,“以朝鲜遣使请兵,命李鸿章察酌情形,随时调拨。”[7] 788
可见,张謇疏中“既分大队援护朝鲜”之说,与当时清政府的派兵援护朝鲜准备是一致的。另外,张謇“日记”中,在光绪十一年十月十五日写道:“知朝鲜事。李相力主不援之说”[3] 254,足以证明当时张謇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朝鲜国王请兵、清政府令李鸿章随时派兵入朝的内情,这为他十月下旬撰写此疏第六件事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此疏倘若是张謇在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所拟,那么,此疏中理应涉及六月二十三日的丰岛之战、六月二十七日的牙山之战和七月初一的清政府对日宣战等中日重大战事和中国对日应战的重大决策。然而,此疏对此均未涉及,仅建议朝廷调军队援朝,称:“拟请饬下北洋大臣于旅顺防营中,择曾在朝鲜带兵、明白耐劳之员,统帅十余营,由间道前往,规平壤为后路,助前敌之声援,通奉天之行便”。由此可以断定,此疏绝非是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三所拟。
综观《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全文,此疏是张謇基于复杂多变的中、朝、日三国形势,为防止朝鲜“为日人所有”而提出的统筹护朝、御日、保国全局之方略,是备战之策,绝非中朝、日开战后的应战之疏。由于1885年年底至1886年初中朝与日本的矛盾并没有进一步激化,更没有出现军事冲突,故此疏未见上奏朝廷。综观张謇一生,为诸多官员代拟奏章,如“代夏学政”、“代吴长庆”、“代鄂督”等,凡有关官员已陈奏者,皆标明官员职务和名字。此疏以“代某公”相称,显然是未奏陈而作为文稿留存于张謇书斋,成为后人研究张謇的重要资料。
末了,应对此疏拟稿时间作确切认定。综观前述考辨可知:光绪十一年七月十六日与盛昱“久谈”后开始酝酿;十月二十四日起“为意园拟陈朝鲜事”,“连三夜”,二十六日“再与意园讯”。据此,可认定《代某公条陈朝鲜事宜疏》写于光绪十一年十月下旬(1885年11月底至12月初)。
标签:张謇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朝鲜历史论文; 清代论文; 中国朝鲜论文; 历史论文; 李鸿章论文; 光绪论文; 英国公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隋朝论文; 唐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