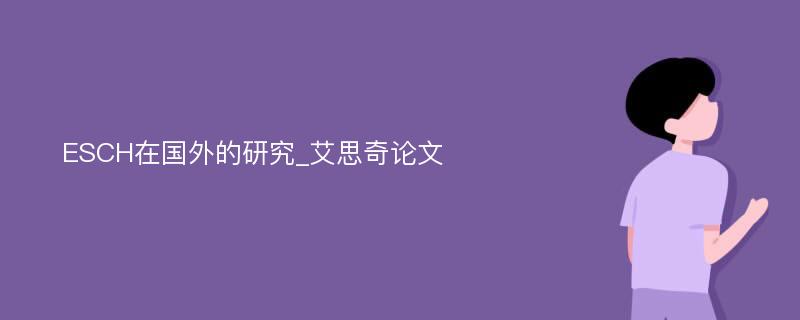
艾思奇研究在国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国外论文,艾思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思奇是现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关于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革命史上的作用和影响,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同时也是国外学者,特别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对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发生发展有浓厚研究兴趣者的研究对象。国外学者研究艾思奇的成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引人注目之处。其中影响较大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成果有:[德]沃纳·麦思纳的专著《哲学与政治在中国——三十年代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1986年出版),[美]乔舒亚·福格尔的专著《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1987年出版),[美]泰瑞·博登霍恩的长篇论文《艾思奇和重新构建1935年前后的中国身份》(1994年出版)。此外,华裔美国学者伊格纳修斯·曹发表于1972年的《艾思奇:中国共产主义的传道者》和《艾思奇的哲学》长篇论文,可以说是国外艾思奇研究的最早成果。
国外学者对艾思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大众化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乔舒亚·福格尔在他的著作中,不仅将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与民国以来许多进步思想家所做的文化通俗化工作进行了比较,而且还与中国历史上宋朝以来的儒家学说的传播表现出一种朝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作了分析比较。福格尔指出: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是朱熹将儒家经典删减为4种必读的经书(即《四书》), 并且加以重新解释,目的在使儒家学说为更多的人学习掌握。特别是到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广泛接触西方和日本思想,使近代知识大众化的倾向继续发展。福格尔还讲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20至30年代,从事大众化工作比较著名的有俄国的布哈林,他和普列奥津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一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第一次有意识的通俗化。 他的另一本书《历史唯物主义——一个社会学的体系》,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典型。艾思奇曾认真阅读过布哈林的这两本书。中国国内从事大众化工作的有巴金等人。乔舒亚·福格尔最后指出:艾思奇做的哲学大众化(即通俗化)工作,超出了同时代人,甚至是前人的探索。他不仅用通俗易懂的中国语言来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复杂内容,而且告诉读者,哲学不只是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人才能掌握的东西。他的特有才能在于将他的艺术才能运用到科学、客观真理的阐述上。艾思奇自己说:“不怕幼稚,只求具体明白”。〔1〕这正是艾思奇哲学大众化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
二、《大众哲学》一书受欢迎的原因
伊格纳修斯·曹认为:《大众哲学》受欢迎是因为它满足了当时中国许多青年“思想和感情的需要”。他指出:《大众哲学》对那些在国家屈辱、沮丧、混乱之际的中国青年特别有吸引力。该书从精神和民族感两方面激励这些青年人,使他们振作起来,投身到改变国家和个人命运的伟大斗争中去”。〔2〕乔舒亚·福格尔则提出:《大众哲学》特别受欢迎的原因在于,“艾使用了将复杂的哲学问题用不复杂的方法来表述的语言和技巧。”〔3〕而沃纳·麦思纳则完全否认《大众哲学》的哲学意义和大众化特点,认为它不是哲学论文,而是党内政治斗争的“复本”〔4〕。泰瑞·博登霍恩批评了沃纳·麦思纳的观点, 认为他的缺点是还原主义太严重,并且在许多事实上出了错。例如他没有考虑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刊登在一本销量很大的大众化杂志上而不是刊登在党内出版物上:他更忽略了艾思奇写作《大众哲学》时还没有正式入党这一事实。〔5〕
泰瑞·博登霍恩自己主要从《大众哲学》本身的内容结构和写作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这两个方面,集中分析了这本书受大众欢迎的原因。就其内容结构而言,泰瑞·博登霍恩从4 个角度作了分析:一是《大众哲学》的那种令人感兴趣的和与众不同的外形。他说:“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当时有一本其外形与《大众哲学》完全相似的著作。该书有四大章,若干节,每节均有标题以及解释性的大标题。每章各节的大多数段落前有一方小框,框内简略归纳该段落的内容。这一特征是最富有创新和重要的。读者很少会看到有两整页长的内容。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说,该书的外形不象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炼、便于间断地阅读。无疑,《大众哲学》外形上的新鲜和简洁对它受欢迎起了很大作用。”;二是《大众哲学》独特的结构形式。“它的章节一般遵循一个固定的结构:先提出一个根据普通常识提出的哲学问题,然后很快他就将这个问题改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并从日常生活中提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命题,最后又再次说明或回答他最初提出的问题。他的结论一般是过渡性的,以便过渡到下一个章节去。《大众哲学》的结构形式虽不如它的外形那样有新意,然而它也对这本书受欢迎起了作用”;三是《大众哲学》中所使用的那种不同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比喻和举例。“艾思奇使用的比喻方法和所举的例子,目的都是为了说明他的哲学观点。他所举的例子,虽然是教诲性的,但却没有儒家说教中的伦理语气。他对所选例子的关心远不如他的那些儒家先驱,也不如他的同伴和追随者。从艾思奇使用比喻和举例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具体运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朴实无华的比喻和举例使读者获得许多新知识,增加了《大众哲学》的吸引力。”;四是简单明了的语言。“《大众哲学》里没有任何古词或暗语,是用1000个普通字写成的。作者在书中既不炫耀自己的语言知识,也不滥用或夸张地使用语言。他自愿丢弃了那种半土不洋的、学究气的语言,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语言说话,这就使他的著作有了一定的可信性和权威性。”〔6〕
泰瑞·博登霍恩还分析了《大众哲学》受欢迎的外部原因(即社会历史条件)。他指出:“30年代的中国,由于日趋严重的外患内忧,对中国现状的失望感和个人前途的不测感困扰着许多人。《大众哲学》针对这些普遍存在的沮丧和失望,努力向它的读者灌输个人的自信感和拯救民族的信心。为此,书中对中国人民经历的社会与经济苦难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指出应对这些苦难负责的一些群体。书中用既有哲学意味又大众化的方式对个人、社会和民族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所作的全面分析,在那个时期是独一无二的。在那个痛苦、失落的时代,艾思奇的这些分析在感情上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大众哲学》的魅力大部分来源于这些分析。”〔7〕
三、艾思奇与30年代苏联哲学的关系
伊格纳修斯·曹认为:艾思奇的哲学受益于30年代苏联哲学,特别是苏联哲学家马克·米丁。艾思奇十分推崇米丁,曾把米丁的著作《新哲学大纲》作为人类历史上哲学的最高成就,介绍推荐给中国读者。艾思奇一生都没有走出苏联哲学设置的圈子(即哲学的目的性——党性——方法论的逻辑怪圈),在1957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中,艾思奇仍在说着米丁在《新哲学大纲》中说的一些话。〔8〕
乔舒亚·福格尔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第一,艾思奇是30年代苏联哲学在中国的主要译介者之一,作品有《新哲学大纲》、《哲学选辑》等;第二,艾思奇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在苏联哲学、特别是米丁的影响下写成的。苏联哲学界把形成逻辑当作形而上学批判,艾思奇在自己的文章著作中也批判否认形式逻辑;苏联哲学界不提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艾思奇的文章著作中也不讲异化问题;米丁为斯大林提供许多哲学著作以支持他掌权,艾思奇也以同样的方法和态度为毛泽东服务;第三,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如何在哲学方面摆脱斯大林影响的任务就落在艾思奇身上。这对艾思奇来说是个艰巨任务,因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与斯大林思想关系密切。但他克服了个人的一切困难,迅速写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一书。这是中国人第一本试图摆脱斯大林主义影响,系统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9〕
(《哲学动态》1996年第6期)
注释:
〔1〕〔3〕参见乔舒亚·福格尔的《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一书第四章“通俗化和《哲学讲话》的通俗化”。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1987年出版。哈佛当代中国丛书第4辑。
〔2〕参见伊格纳修斯·曹的《艾思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道者》,载《苏联思想研究》1972年第4期。
〔4〕参见沃纳·麦思纳的《哲学与政治在中国——三十年代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第65—66页,1986年出版。
〔5〕〔6〕〔7〕参见泰瑞·博登霍恩的《艾思奇和重新构建1935年前后的中国身份》一书的前言和第3部分,1994年出版。
〔8〕参见伊格纳修斯·曹的《艾思奇的哲学》、《艾思奇:中国共产主义的传道者》,载《苏联思想研究》1972年第4期。
〔9〕参见乔舒亚·福格尔一书的第6、7 章“艾思奇和共产主义运动”、“艾思奇的声誉鹊起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