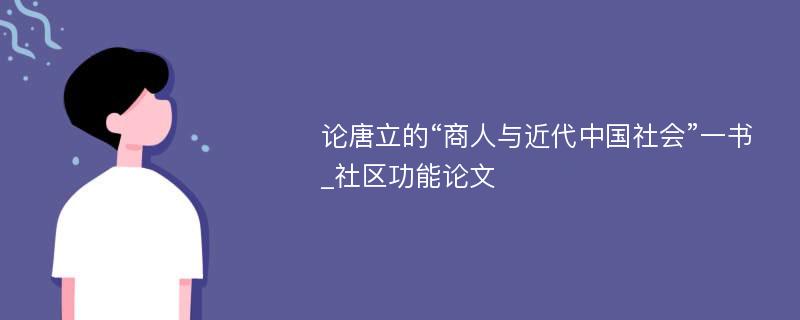
评唐力行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世论文,中国论文,商人论文,社会论文,唐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唐力行教授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以下简称《商人》)是一部全面研究近世商人的学术专著。该书把握商人的发展脉络,揭示商人的发展特色,探讨商人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填补了中国商人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空白。《商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1995年香港中华书局推出了该书修订本,随后,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繁体字本。本文就《商人》的主要特色略作评介。
一、架构起商人阶层研究的系统
作者对商人的研究是从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与动态两方面展开的。该书首先将商人置于历史长时段中加以纵横两方面的考察。就纵向而言,数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或分或合、或治或乱,商人却始终难以摆脱统一与抑商的两难境地以及财富与地位的两难境地,这种两难境地一直延续到近世社会。就横向而言,商人的分类与分层也甚少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商人的分层也有新的见解,作者给出了一个经济、社会与政治多元综合的标准。将商人划分为财产、声誉、权力皆备的官商;财产、声誉兼得的富商巨贾;仅仅拥有财产的下贾、奸贾或走私商;以及一无所有的小商贩。这比以往学术界仅仅以资产为标准,将商人分为上、中、下贾更为科学和合理。正是在这种纵横结合相对静态的背景下,作者对近世社会展开了动态的研究。
近世前期,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商人群体进行了初步的心理整合。这种整合贯穿于商人组织由血缘向地缘过渡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商人群体的认同标准由血缘性的宗族关系扩及地缘性的乡土关系;其二,价值观的整合,结果是商帮的形成。而商帮的形成标志着商人已以群体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阶段,商人的两难境地依旧,除了极少数商人投资兴办手工工场或以包买商、帐房等转化为早期资本家外,传统商人的分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近世后期,在资本主义走向成熟时,商人群体再度进行心理整合,这种整合则贯穿于商人组织由地缘向业缘乃至跨行会的商会过渡的全过程。与前一时期的心理整合有所区别,商人对自身的认识,已不再着眼于士商平等的地位,而是将商人置于“四民之纲”,置于“国本”的重要地位。此次整合的结果是商会的建立,商人融注于资产阶段,成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对近世商人的研究是以其两次整合为主导线索的。近世商人的两次整合以及伴随着整合而展现的商人层次的分化和组合是动态的,尤其是近世后期动态更为明显。四个层次都游离出一批商人成为新式企业的创办者。此外还增加了一个层次,即权力与财产相结合的买办。买办中不乏积极投身于发展民族工业、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资本家。他们共同组合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但是,这种“动态”受制于“静态”,近世商人的两难境地不变,显示着“静态”的传统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强固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不是由资本主义萌芽自然发展而来,因此,这一“动态”是被动的,是因封闭的社会系统被打破而造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商人心理整合的滞后性:当中国商人开始融入资本家行列时,其整合仍旧是浅层次的,并未突破传统民本主义的窠臼。在西欧,资产阶级形成之际,已完成人本主义的心理整合。在中国,则是在资产阶级已形成20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时,才高扬起人权与民主的旗号,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带有许多传统商人的遗传因子。《商人》一书借用社会学的方法,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架构起商人阶层研究的系统。不仅成功地再现了商人阶层整体的历史,还提供了一个考察中国近世社会的新视角,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
二、对商人与社区生活研究领域的新开拓
商人与社区生活是一个微观研究课题。对商人与社区生活相互作用的细部考察,可以深化对商人在近世社会中独特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作者选择相对稳定、封闭的徽州社区作为研究对象,就妇女问题、社区的基本结构、社区生存空间的开拓等问题加以考察。认为徽州的家庭——家族结构在近世初期发生了较大变化,形成了小家庭——大宗族的格局。而徽商的活动对家庭——家族结构的变化起了关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徽人经商疏散了徽州的人口,抑制了人口的增长;徽州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的裂变以及扩大并加固了宗族的血缘群体。这使得徽商的经营活动与宗族势力休戚与共,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的扶持。徽州小家庭——大宗族结构的形成,又从四个方面反作用于徽州的社会经济:使徽州的社会结构富于弹性与流动性;有利于徽商的经营活动;导致儒家学说在徽州的昌盛;强化了对佃仆和妇女的压迫。作者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徽州商人妇的命运,指出:在商品经济与宗族制度同生共荣的徽州社会,出现了“妒妇比屋可封”与“新安节烈最多”的杂糅,以及商人肉欲横流与理学道貌岸然的结合。作者还成功地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徽州的历史地理和历史人口进行了微观考察,具体探讨了商人与社区生存空间开拓的内在联系,以揭示徽商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最后,作者还探讨了社区对徽商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宗族势力与徽商的紧密结合增强了徽商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宗族势力又使徽商因袭了沉重的传统包袱,限制了徽商的发展。正是在社区研究的坚实基础上,作者令人信服地得出了近世资产阶级陷入了一个挣不脱的怪圈的结论。亲缘、地缘网络一方面帮助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启动,另一方面又制约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在经济上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具有浓厚的“商”的特征;文化上造成由反孔到尊孔的反复;政治上则难以摆脱专制大一统的桎梏,因为血缘、地缘恰恰是专制统治的基础。在社区研究中,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商人》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新探索
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是一个综合的因素。作者认为,传统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生产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不能对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诞生于16世纪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在这些方面,16世纪的中国与以前相比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商人》一书转换视角,探索当时世界市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海商所起的作用。16世纪兴起的私人海外贸易冲破了明王朝海禁的罗网,使中国这个封闭的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如所周知,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社会生产规模是受市场制约的。海外市场刺激着中国部分地区生产规模扩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又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使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并以此为起点,造成近世社会经济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样,商人不可或缺的作用显示出来了:他们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马克思语),是中国封闭的社会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中介。作者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原因作了新的探索。由此可知,世界各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并非遵循同一个模式。如果没有世界市场这一外部因素的刺激,中国传统社会内部虽然也可能萌发资本主义萌芽,但这一进程将大大延缓则是不容置疑的。作者同时又指出,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过分依赖于海外市场,造成了它的先天的脆弱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衰,受制于历朝统治者的外贸政策,而资本主义萌芽的脆弱性又导致商人的软弱性。这又从一个新的层面揭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
《商人》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并借用人类学、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谱牒学的多种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例如《商人》一书探讨中国商人发展变化是以商人群体的心理整合作为切入点;区域研究时对县以下都、图人口密度以及名族密度的统计等,这些在国内史学界均为新的尝试。社会史研究除了需要扎实的历史学功底,还需要学习和运用其他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这方面,《商人》是一本相当成功的学术论著。
《商人》一书也有不足之处,如对近世后期商人及其活动的研究仍可深入探讨,我们期望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