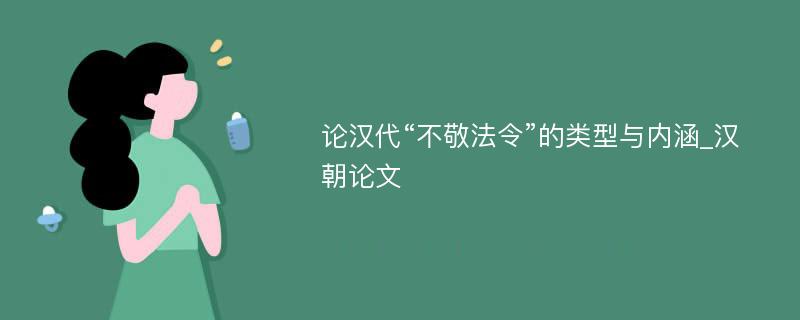
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内涵论文,类型论文,不奉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皇帝制度的建立,皇帝颁下的文书,被冠以“制书”、“诏书”等尊美之称,以显示其至尊地位。君主专制制度要求臣子对皇帝的诏书必须无条件地贯彻执行。“谨奉诏”成为常见的文书用语(注:如《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载:汉文帝下诏议废收孥相坐之法,丞相陈平、周勃回奏:“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可见,“谨奉诏”才是臣子对皇帝旨意应持的基本态度。),因为它体现了合乎规范的君臣伦理。臣子“不奉诏书”、“奉诏不谨”、“奉诏不敬”,则是相关政令、乃至于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罪名。在汉代的历史记载中,类似材料可以说不胜枚举。汉武帝设置十三部刺史,规定其执掌为“以六条问事”,其中的第一条是针对“强宗豪右”而设,而第二条就是整肃吏治的首要规定:“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孙星衍等辑:《汉官六种》,《汉官典职仪式选用》)显然,郡守一级地方大员“不奉诏书”是监察制度的重点所在。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大员,以此坐罪者,皆可能被免官。(注:西汉后期,翟方进弹劾政敌司隶校尉陈庆“奉诏不谨,皆不敬,臣谨以劾”。结果是陈庆“坐免官”。(《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列传》)另外,辅政大臣王凤指令他人劾奏潜在的政敌冯野王“奉诏不敬”,虽然期间有人为冯野王出面求情,冯野王还是难免被罢官的厄运。(《汉书》卷七十九,《冯奉世列传附子野王传》)东汉末年,名臣钟繇在自劾文书中列举自己的失职之罪,就有“轻慢宪度,不畏诏令”、“不承用诏书,奉诏不谨”之说。(《三国志》卷一三《魏书·钟繇传》注引《魏略》)汉律对“奉诏不谨”有惩治的规定,还有其他文献可证,如《晋书》卷三十《刑法志》有“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之说,从其上下文判断,此处所谓的“旧典”,就是指汉家法典。)汉武帝时期,还有如此规定:“不奉诏,当以不敬论。”(《汉书》卷六,《武帝纪》)事涉“不敬”之罪,就可能被逮捕下狱。甚至朝廷出动大军征讨半割据的边境大藩,也可以借“不奉诏”的罪名而行事。(注:淮南王刘安上书谏阻武帝出兵征讨闽越,就有如此表述:“越人名为藩臣……壹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列传》))汉代的思想家董仲舒,还曾经借解释“公羊学”的原理而对惩治“不奉诏”的合理性加以阐述,有“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春秋繁露》卷十五,《顺命》)之说。
可以说,在汉代,不论是国家的政令,还是法律条文以及政治理论,“不奉诏”都构成了犯罪。但是,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往往存在着与规定、理论相悖却可以获得“合理化”生存空间的情形。汉代的“不奉诏”也是如此。本文将致力于条述其不同类型,并借以探索其背后的社会内涵。
一、“军中权宜”型
临敌决战,往往有战机稍纵即逝、胜负决于须臾的时刻,由军中将帅独立地作出判断,对于争取胜算而言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信息交流极不便利的古代,如果君主对前敌指挥干预过多(即所谓“兵自上御”、“兵自内御”),往往会贻误战机、甚至造成全军失利。因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不仅是兵家受命统兵时所坚持的前提要求(注:孙子对吴王阖庐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毅然将阖庐的两位宠妃斩杀以立军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也是专制君主不得不“割爱”放权而必须接受的特殊原则。请看汉代名臣冯唐对汉文帝论君主御将之道:“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史记》卷一百二,《冯唐列传》)所谓的“阃内、阃外”之制,是司马迁感叹“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的精华之所在,但自秦汉以下的专制君主是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的。因为对于军权的控制,始终是君主梦寐以求的。但是,当大战在即、君主既然已经命将出兵时,他就不得不承认前线高级将领的临机决断的权力——“阵前不奉诏”就成为“君命有所不受”的具体内容。
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用兵过程中,大将周亚夫就有过一次“不奉诏”之举。当时,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弟弟,在诸侯王中抵御叛军的态度也是最为坚定的。梁国又地处叛军的必经之地,因此受到吴军主力的围攻。梁国形势危急,先向大将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却根据自己的用兵方略,抢占要地,而后“深壁而守”,对梁国的遣使求救,“亚夫守便宜,不往”。梁孝王刘武只好直接上书向皇帝求救,景帝下诏给周亚夫让他尽速发兵救援梁国,但是“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楚兵乏粮,饥,欲退,数挑战,终不出。”经过三个月的攻防战,周亚夫的预期目标实现了,吴楚叛军被平定。诸将纷纷赞赏周亚夫当时“不奉诏”的做法是高明的决策。但是,“由此梁孝王与亚夫有隙”(《汉书》卷四十,《周勃列传·附子周亚夫传》)。恐怕汉景帝对周亚夫的疑忌,也未尝不是开始于此。
如果说,汉景帝对周亚夫军中“不奉诏”的行为,表现出的态度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宽容;那么,东汉初年的光武帝刘秀对待部将王梁的态度,则要严峻得多了。
建武二年(26年)春,发生了汉军镇压“檀乡”军事集团的大战。(注:“檀乡”之号及东汉对之镇压的过程,《后汉书》卷二十一《任光列传》的记载简明扼要:在徐、兖交界拥兵自重的力子都,归降更始皇帝,受拜为徐州牧。稍后,力子都为其部曲所杀,“余党复相聚,与诸贼会于檀乡,因号为檀乡。檀乡渠帅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与五校合,众十余万。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阳,遣大司马吴汉等击檀乡,明年春,大破降之。”)光武帝刘秀命令大司马吴汉“率大司空王梁,建义大将军朱祐,大将军杜茂,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偏将军王霸,骑都尉刘隆、马武、阴识,共击檀乡贼于邺东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余万人。”(《后汉书》卷十八,《吴汉列传》)从汉军参战将领地位之高、数量之多以及受降人数之众,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场大战、恶战。此役对于刘秀政权的稳固意义重大,据《后汉书》卷二十六《伏湛列传》,伏湛在上疏中有如下文字:“陛下承大乱之极,受命而帝,兴明祖宗,出入四年,而灭檀乡,制五校,降铜马,破赤眉,诛邓奉之属,不为无功。”此处列举的均是与刘秀“受命而帝”直接相关的重大战役,“灭檀乡”赫然居其首位。
参与此役的汉军将领,除了统帅吴汉之外,地位显赫而且贡献特殊的就是王梁了。王梁“从平河北,拜野王令”,又擢拜为大司空,封武强侯。刘秀对他有特殊的倚重之心。在进击“檀乡”之时,刘秀特意下诏:军事指挥权完全归属大司马吴汉,而王梁为了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既不禀报大司马吴汉,也不向朝廷请命,多次征发野王境内的军队参战。“(光武)帝以其不奉诏,敕令止在所县,而(王)梁复以便宜进军。帝以(王)梁前后违命,大怒,遣尚书宗广持节军中斩梁。广不忍,乃槛车送京师。既至,赦之。月余,以为中郎将,行执金吾事。”(《后汉书》卷二十二,《王梁列传》)因为王梁在一役之中多次“不奉诏”、“前后违命”,光武帝刘秀对其恼怒到遣使斩首的程度。幸亏所派使者宗广意存宽恕,王梁才逃过一劫。笔者还有一个猜测:刘秀对王梁的“痛下杀手”,可能有安抚统帅大司马吴汉的用意。“有诏军事一属大司马”在先,王梁的擅自调兵在后,首先冒犯的就是军前统帅吴汉的权威。假设王梁是此次战役的最高统帅,刘秀必定会容忍他的“不奉诏”而擅自行动。所以,刘秀的“天威难测”,应该同时含有伸张君权、伸张统帅之权的两个意义。而在“天威”得以彰现之后,王梁不仅被赦免,还继续得到重用。
由此看来,军阵之中的“不奉诏”行为还是容易得到宽赦。其原因如前所言,主要不在于君主的“开明”,而在于指挥战争所需要的特殊权力,在于君主对统兵将领的依赖与笼络并存的心态。
二、“拒绝任命与赐予”型
皇帝任命某位臣子出任某一官职,通常情况之下必须应命赴任,即便是对新任命有所不满,也不能有所表露。反之,即便是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不愿意就职的想法,也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了。例如,汉宣帝认定时任少府的萧望之“材任宰相”,为了考查其政事能力,任命他为左冯翊。萧望之根据一般惯例,认为从少府出为左冯翊属于贬职“左迁”,推测自己有不合皇帝心意之处,立即移书称病。汉宣帝得知,猜透了萧望之的心事,派人前来解释本意,萧望之这才放心地就职视事。(《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列传》)这个事例说明,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臣子是不能拒绝皇帝所任命的新职务的。
如果有臣子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新职,那么,在行为的定性上,就属于“不奉诏”了。汉武帝时期的耿直大臣汲黯,就是此类不多见的代表性人物。
在创立五铢钱之初,民间的“盗铸”现象严重,其中尤以楚地为甚。汉武帝以为淮阳是楚地的要害之处,必得名臣就职才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召拜汲黯为淮阳太守。不料,汲黯并不了解武帝的用意,也以为由朝臣改任地方官是外放受贬,所以出现了汲黯抗命的一幕:“(汲)黯伏谢不受印绶,诏数强予,然后奉诏。”在殿上,君臣二人还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武帝宽慰汲黯:“君薄淮阳邪?……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汉书》卷五十,《汲黯列传》)汲黯这才到淮阳郡赴任。两汉时期,以隐士身份而抗命于皇帝征召的名士不在少数,但是身入仕途之后,敢于抵制皇帝任命者,确实不多。汲黯此举,不应该简单地视为留恋中央官职,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这样的信息:在改变大臣的职务时,皇帝也应该对臣子的意愿有一定程度的尊重。
按照常规,皇帝赏赐臣子礼物,不论价值高低,均是表示欣赏、信任、宠幸,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被赐予者是要感恩戴德的。偏偏汉代就有面拒皇帝赏赐的大臣,这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奉诏”行为。汉文帝时期的名臣卫绾,以谨慎守礼而得到皇帝的信任。文帝决定赏赐他宝剑。不料,质朴的卫绾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汉书》卷四十六,《卫绾列传》)此举使得汉文帝十分意外。
此类的“不奉诏”,主要表现出当事人的谦逊自守、处事有度,在意外降临的“皇恩”面前,保持着难得的清醒。它以个人的道德修养而引人注目,但在政治运作方面却不具备太多的意义,故存而不论。
三、“为国持正”型
自战国以降,“尊君卑臣”不仅凝化为制度规定,同时也熔融为政治伦理。现实的问题在于:如果群臣必须惟君主的意旨是听,一旦君主的决断出现失误而群臣不加以阻止,那么国家的利益岂不是要遭受损害?明于治国大道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确实在这一方面颇多匠心设计。于是,出现了辅政制度、职在谏诤之官、草诏与封驳之制等等,其用意都在于防范皇帝个人的错误意旨破坏国家的根本大计。然而,在皇帝(特别是有雄心、有能力而又敢于独断专行的皇帝)执意要做某件事情、并且带有“即时”性质的场合,上述预设的制度就会失效。当皇帝敢于置制度于不顾而强行发号施令时,好像只能仰赖有大臣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不奉诏!”形势才有可能得以扭转。这是地地道道的“触逆鳞”之举,其危险性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就已经说得十分透彻了。如果没有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身家性命的境界,是做不了这样的事情的。因此,这种类型的“不奉诏”,是最具有社会意义、从而最值得研究的,当然也是最令人钦佩的。
试举汉代的几个显例,借以展示当事人的铮铮铁骨、大丈夫气概。
汉初的耿直大臣周昌,可当得起直谏第一人之称。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而改立戚姬所生之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莫能得”,其中以周昌的面折廷争最为激烈。周昌为人口吃,又在盛怒之下,他对刘邦声明:“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书》卷四十二,《周昌列传》)好一个“期期不奉诏”!为此,刘邦对他油然而生敬意。稍后,刘邦不得不改变初衷,保留太子地位而封如意为赵王。为了保证自己身后赵王如意不至于被人杀害,刘邦留意为赵王寻求一位可以信赖的丞相,结果周昌当选。在刘邦死后,大权在握的吕太后开始了她的复仇举措,囚禁了戚夫人,随即宣召赵王入京。传宣诏命的使者多次往返,赵相周昌拒不应命,他对使者说:“高帝属臣赵王,赵王年少,窃闻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赵王并诛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诏。”(《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吕太后大怒,只好先征召周昌入朝,她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周昌先后两次声明“不能奉诏”,公开对抗汉高祖与吕太后两位专制统治者,是冒着相当风险的;从他的用意而言,不带有任何利己的因素,他比在位的最高统治者更在乎国家的根本利益。
汉景帝时期的大臣窦婴,也以“不奉诏”之举而赢得了声誉。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胞弟,也是窦太后的少子。窦太后不脱老妇人常态,因为喜爱少子的缘故,欲令梁王为景帝的继承人,即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安排继统序列。一次,景帝与梁王按照家人之礼,共同奉陪太后宴饮,景帝可能是出于安慰母亲的考虑,对梁王说:“千秋万岁之后传王。”窦太后果然面露喜悦之色。当时虽然不是在朝会的场合,没有形成正式的诏旨,但是景帝一语既出,就应该为“君无戏言”而承荷起许诺。窦婴也在场,当即对景帝的失言提出批评:“汉法之约,传子適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此话一出,实际上就是“不奉诏”的公开表态,也是一种驳议,取消了景帝言论的合法性。景帝以“默然无声”承认了窦婴的批评是正确的,也就撤销了自己的许诺。
西汉后期的名臣史丹,以朝廷公卿“不奉诏”的潜在可能性,阻止了汉元帝晚年废立太子的打算。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重病缠身,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王皇后、太子刘骜却难以得到进见的机会。元帝病情稍为缓和,竟然对王皇后、太子产生了更多的不满。他多次向尚书询问景帝时改立胶东王为太子的故事,皇帝有废立太子之心,在宫廷之中已经不再是秘密。为此,太子长舅王凤与王皇后、太子皆忧心忡忡,不知如何应对。说当时的政治高层疑云密布绝非危言耸听。史丹凭借有元帝的特殊信任而得以伴陪在侧,他在与元帝单独相处之时,涕泣跪奏:皇太子之立长达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但是,定陶王得到皇帝爱幸却广为人知,近来更有道路流言,以为太子位置有动摇之议。言谈至此,史丹极力强调:“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汉书》卷八十二,《史丹列传》)元帝有感于史丹的涕泣极谏,特别是他所分析的改立太子的诏旨一旦公布,就可能出现朝廷公卿共同抗旨的紧张局面,这使得元帝不得不明确表态:不会有改立太子之举。一场政治危机得以消弭。史丹所言公卿“以死争,不奉诏”的局面尽管没有出现,但从元帝的反应可以想见,一旦形成事实,只要皇帝不是肆行无羁的暴君,就不得不作出让步。因此,如果官僚集团群体性“不奉诏”见诸实行,对于纠正皇帝个人的错误决策,是可以发挥相当作用的。
还有一种情况:皇帝的言论不属于原则性错误,而只是一时失言,鲠直的臣子也可以用“不奉诏”的方式表示抗旨。东汉初年的循吏任延对光武帝刘秀的驳论,可称之为一段历史佳话。建武初年,任延为九真太守四年,深得民心,离任之时当地吏民“生为立祠”。后转任武威太守,光武帝亲自接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任延却毫不客气地反驳:“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光武帝之言,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为官之道,务实却难免俗气,特别是此话出自皇帝之口,更为有失体统,在听到了任延坦荡无私的批驳之后,他只好叹息认错:“卿言是也。”(《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任延》)
在以上所举四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共性:公开声称“不奉诏”、“不敢奉诏”的臣子,其见识均在皇帝之上,他们的态度一旦表达,就会光明磊落地坚持下去;而皇帝则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或失言,还需要通过尊重抗旨者的方式,借以完成纠正错误的过程。
公开宣称“不奉诏”而抗旨者,也并非都能够体面“收场”,毕竟这是“触逆鳞”的行为,万一“真龙天子”动怒,当事人受到迫害也是难免的。 东汉延光三年(124年),安帝受人蛊惑,下诏命令公卿以下朝官集会讨论废立太子。大将军耿宝等人秉承皇帝旨意,认为太子当废。时任太仆的大臣来历,却持不同意见。他与太常桓焉、廷尉张皓联名上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安帝在盛怒之下不予采纳,是日遂废太子为济阴王。来历认定太子无罪,皇帝的旨意应该纠正,于是邀约了光禄勋祋讽、宗正刘玮、将作大匠薛皓、持书御史龚调等十余位大小臣僚,“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他们援引法律来证明,即便是太子的属官确实犯罪,皇太子也不该坐罪被废。安帝对来历等人的举动极为恼火,派中常侍奉诏威胁他们:“父子一体,天性自然。以义割恩,为天下也。历、讽等不识大典,而与群小共为讙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岂事君之礼?……若怀迷不反,当显明刑书。”面对皇帝要治罪的强硬表态,参与进谏者莫不失色。将作大匠薛皓率先改变态度,表示“固宜如明诏”,这是见好就收的聪明人。来历却瞧不起薛皓的见风使舵而出言相讥:“大臣乘朝车,处国事,固得辗转若此乎!”其他人先后退走,只有来历“独守阙,连日不肯去”。安帝大怒,竟然下旨罢免了来历兄弟的官职。(《后汉书》卷十五,《来歙列传·附曾孙来历传》)值得注意的是,来历的愤然抗旨之举,本来出自于维持政局稳定的公正体国之心,与上述周昌等人的“不奉诏”本来别无二致,但竟被安帝加以“与群小共为讙哗,外见忠直而内希后福,饰邪违义”的政治罪名。可见,“不奉诏”的处置结果,包括当事人的命运,其实是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君主专制体制之下,“人治”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体现之一。
秉持正义而“不奉诏”者遭受迫害的事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出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长远考虑,部分思想家不得不设计出某些理论,借以对君主滥用权力实施约束。西汉后期的学者刘向,假借他人口吻,就臣子应该如何对待君命的问题,语重心长地指出:“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病君谓之谀,逆命利君谓之忠,逆命病君谓之乱。”(《说苑》卷二,《臣术》)其中,他把“逆命利君”作为忠臣本质特征的表述,是大有深意的。他还对“辅弼之臣”寄予特殊的期望:“有能比和同力,率群下相与强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窃君之重,以安国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弼。”(《说苑》卷二,《臣术》)稍加思量,其实所谓的“忠臣”、“辅弼之臣”,他们的共同点恰恰在于——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也是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他们应该有“不奉诏”乃至于强迫君主按照正道行事的意识和能力。
四、“政令失御”型
在正常情况之下,皇帝的诏旨不仅仅是其个人意旨的表达,更是国家政令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皇帝的诏旨如果在下达执行的过程中被以各种方式所搁置,那就意味着出现了“政令失御”的问题。此类的“不奉诏”行为,大概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人公开表态,抵制是在暗中进行的;二是“不奉诏”者自身不是公正的化身,恰恰相反,他们代表了官僚集团中的黑暗势力。
“山高皇帝远”的俗语,是对此类“不奉诏”行为成因的最好说明。在边远地区,一直存在着“鞭长莫及”的实际问题。地方军政长官对中央的离心离德往往也从此开始。“今者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下土边远,能诣阙者,万无数人,其得省治,不能百一。”(《潜夫论》卷四,《班禄》)这一分析还道出了其危害性:地方官“废忽诏令”得不到惩治,百姓就难免蒙受劫难了。
这种现象已经是司空见惯,有时候最高统治者实在不愿意“装糊涂”了,也会在诏书中把这一官场“潜规则”予以揭破。和帝逝世之后,殇帝即位之初,临朝称制的邓皇太后下诏大赦天下。为了避免大赦令形同虚设,她在诏书中强调:“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后汉书》卷四,《孝殇帝纪》)邓氏是高明的政治家,把政令受阻的严重问题表述为官员的“持重”之举,但遮羞布掩盖不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被各级官员打折扣是半公开的秘密。汉安帝曾经借着大雨成灾,在救灾的诏书中,指责“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乡吏因公生奸,为百姓所患苦”,进而指出,朝廷虽有“养老令”和赈济贫困的规定,但是“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明知国家的法令、皇帝的旨意被地方官吏大打折扣,朝廷除了下诏谴责之外,并没有实际的制裁措施、纠正之策,这里透露出多少无奈?
这一类型的“不奉诏”,折射的是政令不畅的政治弊端,是吏治昏暗的表现形式之一。在集权制的体制体系之内,“令行禁止”一旦成为官样文章,那么任何立意高远的法律、制度、政策,都会归于名存实亡。不论在哪一个历史时期,一个讲究效率的政府,一个想维持社会公信度的政府,都应该设法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
以上列举的四种类型的“不奉诏”行为,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社会意义。分析这一现象,有助于了解古代政治的实际运作状况。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其中“为国持正”型的内涵是最为丰富的、作用与影响也是最值得肯定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当着皇帝的意旨明显有失误的时候,朝臣的反对意见能否得到事实上的合法存在权。如果我们要对古代的“开明政治”加以界定的话,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考量当政者对“异议”的宽容度。如果一个皇帝不允许“不奉诏”有事实上的生存空间,那就是专制独裁到极点了。在政治运作层面,如果将缓冲区间和调适空间压缩得过小,就会造成缺乏机动性和调控性的困境,减少了从容回旋的余地,这绝非国家之福。
标签:汉朝论文; 后汉书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西汉论文; 周亚夫论文; 光武帝刘秀论文; 王梁论文; 东汉论文; 汉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史记论文;
